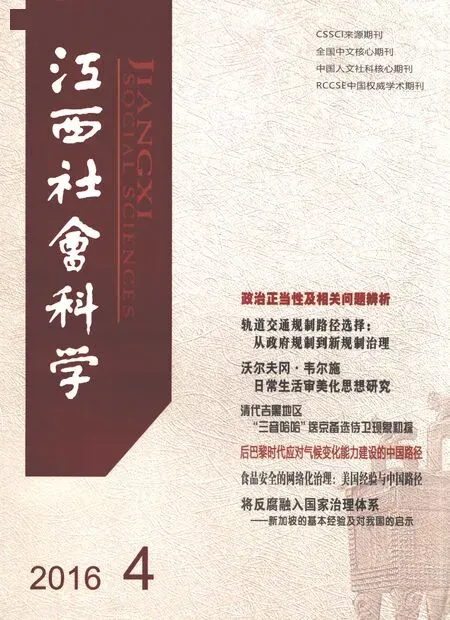政治正当性及相关问题辨析
2016-03-06张传有杨伟清
■张传有 杨伟清
政治正当性及相关问题辨析
■张传有 杨伟清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旨在考察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道德条件,或者说旨在探讨什么样的政治权力可以得到道德证成。政治正当性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基于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即非自愿性、强制性、垄断性、笼罩性以及深远性。就政治正当性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区分国家正当性与政府正当性,进而区分国家正当性的对内与对外两个不同维度。
正当性;政治权力;道德证成
张传有,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2)
杨伟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但政治正当性又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究竟什么是正当性?当追问特定对象的正当性时,我们想知道些什么?用来限定正当性的“政治”这一概念又意指何物?政治正当性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政治的正当性为何特别重要?政治正当性内部是否存在一些重要的区分?
本文试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以澄清政治正当性的确切内涵。文章主要考察“正当性”这一概念,力图给出与正当性追问相关的问题意识;接着讨论什么是政治正当性,以及政治正当性为何值得特别关注;最后给出一些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相关的重要区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政治正当性这一概念,并不讨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是另外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笔者会在其他地方深入讨论。
一、正当性
我们首先从对“正当性”这一概念的分析开始。若认真反思和观察自己生活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对正当性的追问几乎随处可见。当一个教师制定某个课堂的游戏规则时,课堂中会有某些学生挑战这些规则,质问这些规则的正当性。当一个大学中的管理部门按照教师职称的高低而分配不同的教学和科研要求时,该大学的教师当然有理由要求相关部门对这些规定的正当性给出解释。当家长为孩子安排了过多的培训课程,使得孩子毫无喘息之机时,有些孩子会抗议家长的安排,索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样,去医院就医时,当看到医生开出的花样众多的检查时,有些病人就会进一步询问某些检查的必要性,也即是其正当性。或者,当某人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实践,已经熟知并能灵活运用某一国家的法律,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当律师,并试图开展律师业务时,却被告知必须要先参加相关的考试,并取得律师资格证书,方可以正常执业,他会有理由愤怒,并挑战相关规章的正当性。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遭遇正当性问题的追问,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正当性的反思和质问。追问正当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追问者。这些条件主要相关于行为主体,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行为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理性反思精神和能力,倾向于在理性的基础上衡量和评估生活中遭遇的事件和对象。如此才有可能产生独立的理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有可能和当前面对的某些规定或安排冲突,这就会带来疑问,进而引发对这些规定或安排的正当性的挑战。我们不能期待一个无知的或教条的行为者会有经常的正当性之问,因为没有理性的能力和反思的精神,就不可能产生我与他者之间的分裂或冲突,我与他者就会处在一种平和的状态,就会倾向于接受他者及其相关的安排。
第二,行为主体需把自己看作具有自主性的自由且平等的存在者。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的这一身份有充分的体悟和认同,珍视自身的自主选择权,珍重自我自由的程度和范围,珍爱自己的平等地位,才会对社会中那些旨在削弱人们的自主性、限制人们的自由以及戕害人们的平等身份的制度和实践提出质疑和挑战,追问其正当性。①
与第一个条件相比,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原因在于,理性反思的开启并非自然而然的,它需要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要么是外在的某种引导或激发,要么是内在的价值认同或承诺,如对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体认。当这些人们深以为然的重要价值遭到削弱或制约时,就必然会想要寻求解释,从而开启理性反思之门,进而引发正当性的疑问。一个有良好教养、理智成熟的人,若心中没有一点平等的观念,就不可能去质疑种族歧视制度的正当性,也不会反思异性婚姻制度的合理性。同样,一个奴隶无论如何聪明,若深信一些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另一些人则是当主人的,则他大概也很难去追思奴隶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即便没有成熟的理性能力,单单是对这些价值的深沉认同在很多时候也足以引发对正当性的质问。故而,就这两个条件而言,第二个条件似乎是自足的,可以独自启动正当性之问,而第一个条件好像是不自足的,需要以第二个条件为前提。
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些引发正当性之问的例子。我们可以追问一下,在那些场景下,为何有人会产生正当性的疑问?这种疑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疑问?什么样的答案才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些疑问?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引发人们正当性质问的对象是一些规则、制度、要求或安排。这些对象以不同的方式或程度构成对人们的约束和限制:要么限制了人们自主选择的能力和范围,要么束缚了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要么不符合人们所具有的平等身份和地位。如此一来,那些具备理性反思精神,崇尚个人自主、自由和平等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生发疑问,追问这些对象的正当性。
当人们提出正当性问题时,人们究竟企望什么?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人们企望有人能对相关的制度、安排或要求给出解释或说明。解释者主要指的是相关制度、安排或要求的制定者,但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他人。所谓的解释其实就是要提供一种证成(Justification),证成相关制度、安排或要求的合理性,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的疑虑。其二,人们并不企望什么,而是已经断定相关的制度、安排或要求荒谬之极,无任何合理性可言。所谓的正当性提问,看似在表达疑问,实则是一种肯定的断言。但这种断言的根据何在?事实上,在断言的背后必定潜藏着这样的信念,即相关的制度、安排或要求绝对不可能得到证成。因此,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正当性都与证成活动密不可分。当人们求索正当性时,即是在求索一种证成的具体实践。
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正当性究竟要求什么样的证成?或者说,当人们提出正当性问题并企望一种证成时,他们企望的是什么类型的证成?哪些证成是他们想要的?哪些是不想要的?这些问题看上去很难有统一的答案,似乎需要就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一个无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企望的当然是一种高度利己的证成,而一个陷入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念而不能自拔的人想要的无疑是有利于自己立场的证成。因此,这里必须对索要证成的人作一些必要的限定。我们假定这些人是一些具有道德感的理性的存在者,他们愿意遵循人们共同认可的道德原则,会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福祉的影响,也即是罗尔斯意义上的明理的(Reasonable)人。②这一限定当然仍有些简单,但我们不妨在直观的意义上理解明理的人这一概念。
现在我们可以问,对明理的人而言,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证成?当一个大学的老师质问大学的管理部门为何给不同职称的人分配不同的工作量时,他希望管理部门能给出恰当的理由来证成这种安排。但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恰当理由呢?不妨设想一下管理部门可能会给出的理由,如这种安排是该大学的传统,或这是校务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或这会对职称低的教师起到激励作用,促使他们更努力工作以晋升自己的职位。再想象一下该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他或许会说,传统并不能保证某种安排的正当性,很多古老的传统因为不道德或不合理已经被废除了,只有当传统自身的正当性能得到保证时,这一理由方可成立;校务委员会的讨论结果也同样不能确保这种安排的合理性,重要的是校务委员会究竟基于何种理由对教师进行区别对待,不同职称的教师之间除职称差异外,还有哪些重要的且有道德关联性的差异可以证成校方的安排;诉诸激励的论证似乎涉嫌歧视,已经预先假定职称低的人会更懒惰一些,而且若职称高的教师也同样需要激励,那它也违背了平等待人的要求。从该教师的回应可以看出,当他质问传统自身的道德性,追问不同职称教师之间的道德差异,质疑校方的安排涉嫌歧视,未能平等待人时,他主要诉求的是道德的理由去挑战校方的安排,因此他希望给出的应该也主要是道德上的理由。
同样,当学生质疑教师设置的课堂规则,患者追问医生开出的各项检查,或试图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质问律师资格考试的正当性时,他们心中其实都有一些道德疑问,如教师是否滥用了自己的权力,随意设定不合理的规则,医生是否有悖医德,任意开列各项检查来创收,或管理律师资格考试的部门是否主要为了经济效益才出台相关规定。他们希望被质疑者能给出充分的道德理由来为相关的安排或规定作道德上的辩护,以回应这些道德疑虑。
至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正当性之问是在索取一种证成,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证成,即道德证成。当然,把正当性之问解释为索取一种道德证成,这不是基于纯粹的概念或语义分析,而是必定基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对正当性这一概念的某种理解。如此一来,必然会有人质疑,你依据的可能只是多种解释中的一种而已,为何单单选取它?对此问题,笔者只能回应说,正当性这一概念也许可以有别的解释,但道德证成构成对它的一种最主要的解释,至少这是笔者的直观理解。
可什么又是道德证成呢?简单点说,所谓的道德证成就是诉求道德而非其他理由所做的证成。当然,这又会引发一个问题,即何谓道德理由?道德理由即是建基于道德原则、权利、责任或义务之上的理由,如自主性、感恩原则、功利主义、康德的定言命令、密尔的不伤害原则等理由。考虑这样一个情形:某人乙被甲杀掉了,甲被告上法庭,甲为自己辩护,理由是因为乙试图伤害他,他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失手杀掉了乙。这时我们会同意,甲诉求的是道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为正当的自我防卫是公认的道德权利或原则。但假如甲的理由是,因为乙曾经侮辱或伤害过他的家人,他是因为报仇才不慎杀掉了乙,那这个理由即使根本不是道德的理由,也至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道德理由,因为它涉及我们究竟是否有道德权利因曾经受过的伤害而报复。或再想象下述场景:甲乙二人约定去影院观影,甲未能赴约,乙指责甲失约,甲为自己辩护,理由是,在去影院的路上看到有小孩子溺水,甲入水救人,并随后护送孩子入院,导致自己未能守约。我们会同意,甲给出了一个道德证成,因为他诉求的是力所能及地救助他人这一道德义务来为自己辩护。但若甲的辩护理由是自己当时心情不好,不想赴约,那这显然不是诉求道德理由的辩护。
二、政治正当性及其重要性
现在我们大致澄清了正当性这一概念的意涵,即寻求正当性就是寻求道德证成。但我们仍然没有涉及政治正当性这一概念中用来限定正当性的“政治”这一概念。我们的问题是,“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政治的”所指为何?政治的正当性问题究竟有何独特性因而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最好还是从生活中的事例说起。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存在形形色色的约束和限制。前面提到的事例中已经包含了特定类型的约束和限制,但还有另外一些约束和限制我们也特别熟悉。如,驾驶员不可醉酒驾驶,不可闯红灯;收入达到一定数额的人必须纳税;要进入大学必须参加高考;有些国家还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服兵役。并且,凡违背相关规定的,都必须承担一定的后果,或接受相应的强制性惩罚。这些约束和限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以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我们当然可以质疑这些法规的正当性,由此产生法的正当性问题。
但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法规来自什么地方?法规显然是由具有立法资格的立法机关制定的,而立法机关被赋予了制定法律的政治权力。因而,追问法的正当性就是追问立法机关的正当性,而追问立法机关的正当性从根本上是在追问立法机关享有的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正当性。所谓的政治正当性是一个简化的说法,更完整的表述是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或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政治正当性中的“政治”指的即是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当然,立法机关并非唯一拥有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机构,执法和司法机关同样分享政治权力。因而,政治正当性指的是国家或政府机构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可以想象,有人会不接受这里给出的对政治权力或政治正当性的界定。他们会说,凡是存在权力或支配关系的地方就存在政治,而存在政治的地方就有政治正当性问题。若我们承认教师和学生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或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权力或支配关系,那就会存在师生政治、家庭政治或医患政治,我们就有必要发起政治正当性之问。可以看出,这一反驳对政治和政治权力采用的是一种泛化的理解,因而对政治正当性问题给出了广义的解释。而我们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正当性给出的是狭义的解释。若广义的解释能够成立,那狭义的解释就会面临一个挑战,即为何单单把国家或政府机构所掌控的政治权力提出来,追问它们的正当性?要回应这个挑战,就必须指出它们所掌控的政治权力的特殊性,以证成这种区别对待。
我们必须要问,国家或政府机构的政治权力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它们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属性?我们将从五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来做论述。
第一,这些权力的运作丝毫不以人们的自愿性活动为前提。对于国家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人们似乎突然就被抛入某个政治社会中,被迫接受该社会的规则体系,被动地承受着政治权力的支配,并无多少真正自由选择的余地。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政治社会是封闭的,我们是因生而入其中,因死才出其外,并不能自愿地选择进和出[1](P135-136),因而自然也就无法自由选择是否承受特定国家或政府机构的政治权力。与此相对的是,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当人们身处某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时,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自由选择或自愿参与的影子,固然这里的自由或自愿会因事情的不同而存在程度上的千差万别。例如,因为你选择了做一名教师,就要承受学校设定的规则,即便你可以质疑并试图改变它们;因为你选择了去看医生,就需要接受医生的支配或指导;因为你自由地加入了某个组织或团体,就要接受组织或团体领导的权威。
第二,与人们的非自愿性紧密联系的是这些权力所特有的强制性特征。这是为很多学者所特别强调的一点。所谓的强制性指的是这些权力会运用强制性的力量来确保人们服从规则,会制裁或惩罚那些犯规者。而且,只有这些权力可以诉诸暴力,可以通过剥夺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的方式来强制行使。与这一点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在很多组织、机构或单位中,人们也会感受到来自于规则体系或有关部门的强制力,如与这些规则相伴的惩罚措施或实际发生的惩处,但它们至少无权以暴力的方式对待我们,无权囚禁或没收我们的财产,更不要说夺走人们的生命。此外,从心理层面来说,由于很多组织或单位是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和退出的,那人们实际感受到的强制力就会微弱一些,而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强制力的感受就要强烈得多。
第三,国家或政府机构的政治权力还具有鲜明的垄断性或排他性。③它们声称,唯有自己有权威对生活在某个国家或国家中某地域的所有人制定和执行规则体系,并裁决围绕规则体系的争执,而其他组织或机构则无权染指这些领域。这种特征显然不适用于在国家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机构、组织或单位。它们虽然也有制定、执行并裁决规则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只能应用于特定机构、组织或单位中的人们。而且,在很多时候,它们还需要与他者分享这种权力。例如,一个大学虽然有权力制定内部的规则系统,但这种规则系统必须与立法和教育部门制定的法律与规则相容,因而需要与这些部门共享管理大学的权力。同样,某个医院虽然被授权可以制定自己的院规,但它只能在政府医药部门设置的框架中这样做,因而必须与政府部门分享管理医院的权力。
第四,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力还具有明显的笼罩性特征。所谓的政治权力的笼罩性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阐发。从时间维度来说,生活在特定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从生到死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脱政治权力的约束,甚至死亡之后的遗体处置问题也要符合政治权力的规定。就空间维度而言,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脚踏在特定国家的领土上,就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政治权力带给你的后果。但在存在权力关系的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当孩子不能接受家长的支配时,可以选择暂时逃离家庭,规避家长的权力。而且,孩子会成长,独立组建家庭,至少部分摆脱父母的规约。当你选择在大学工作时,你是在特定的时间进入,也会在特定的时间退休,大学无法支配你的一生。若你无法忍受大学糟糕的环境,还可以选择离开,结束大学施加于你的权力。也就是说,很多其他的权力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具备笼罩性。
第五,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力对人们的影响要更为深远。这是因为,这些权力部门确立的是社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系统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这是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或单位的规则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前面已经谈到,即便是这些组织、机构或单位的规则系统也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和政府制定的规则系统的烙印。如果说生活的本质就是规则下的游戏,那政治权力对生活游戏的影响显然更广泛和深入。国家和政府部门确定的规则系统的好与坏很多时候会直接决定人们生活的质量,规定人们生活的目标和期待,影响人们生活的机会和对自我的理解。试想一下,如果市场经济被计划经济所取代,或以自主招生系统代替高考制度,人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缺乏成熟市民社会的地方,由于政治权力受到的缓冲和制约更少,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将会产生宰制性的影响。此外,对很多弱势群体来说,政治权力可能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是他们在苦难的社会中获得一丝安慰的最后希望,但邪恶的政治权力却会让他们跌入深渊,彻底丧失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期待。④
以上我们给出了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即非自愿性、独特的强制性、垄断性、笼罩性以及深远性。这五大特征可以把政治权力与其他权力关系很好地区分开来。就这五个特征而言,它的非自愿性、独特的强制性以及垄断性特征使得它与其他权力关系存在质的差别,因为这些是其他权力关系完全不具备的一些特征;它的笼罩性和深远性使得其影响力在程度上远远超越其他的支配关系。一种权力和支配关系,其特征越独特,影响力越深,要求越多,就越需要得到证成,且是更充分有力的证成。故而,政治权力而非其他权力关系的正当性问题就自然会凸显出来,得到更多的关注。
现在我们可以对政治正当性的问题意识稍作概括。当人们追问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时,是希望相关人员或部门能对政治权力或权威的具体运作给出道德上的证成。而所谓道德证成其实就是指出政治权力或权威的运作因为满足了何种道德条件因而是正当的,故政治正当性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是探究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正当性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两种理解的实质是一样的。很多学者都是采用其中的一种理解来界定政治正当性。如,柯克雷(Mathew Coakley)认为:“政治正当性理论通常聚焦并捍卫某种正当性的条件,也即,它们会阐明一个国家或政治体若要被认为是正当的就必须拥有的特征,并试图表明,这些特征如何以及何时可被满足。”[2]在内格尔(Thomas Nagel)看来,政治正当性的历史是 “力图找到一途径能向那些生活在被强行给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证成这些制度的正当性,并同时探寻,若使证成成为可能,这些制度必须是什么样的”[3]。而柯普(David Copp)的观点是:“当我们评估一个国家的正当性时,我们的关注点是评估它统治的道德权威何在…正当性问题是要解释一个国家如何具有道德权威去做那些统治国家的事情…问题是要理解何种条件下,一个国家能具有统治的权利。”[4]布坎南(Allen Buchanan)则认为,政治正当性理论是一种有关政治权力道德性的理论,其主要目标是回答两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在何种条件下,行为者对政治权力的运用可得到道德证成。”[5]
三、与政治正当性相关的问题区分
我们现在清楚了政治正当性问题的实质。可我们马上又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当谈论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正当性时,政治权力或权威的概念略显宽泛和抽象,需要具象化。该如何具象化?其中的一个办法是进一步追问,在现代国家中,究竟谁拥有政治权力或权威?其实是国家和政府。因而,我们不如讨论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问题。虽然该问题仍有些宏大,但已经具体了不少。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应该是具体的政治官员拥有政治权力才对,故应讨论政治官员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但这一看法的问题是,政治官员的权力及其边界其实是由国家和政府规定并确立的,脱离开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问题根本就无法讨论政治官员的正当性。也就说,我们必须先讨论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问题。
欲讨论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国家的正当性和政府的正当性是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然,这就需要对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作简单的讨论。按照拉兹(Joseph Raz)的看法,“国家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它的政府则是其行动的代理者”[6](P70)。布坎南的观点是:“国家是一个运用政治权力的持续存在的制度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存在一些角色可以授权角色的占据者以诸多不同的方式运用权力,而政府就是由这些角色的占据者或者至少是由较重要的角色的占据者组成的。⑤政府来来往往,但国家岿然不动。”[5]将拉兹和布坎南的意见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三点区别:其一,从时间上来说,国家存在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政府,政府可以更替,但国家仍旧存在。这一点特别符合人们日常的直觉;其二,国家是持续存在的制度系统,而政府则是由在制度系统中占据不同地位和角色的人员构成的;其三,政府只是在特定时间内代理或代表国家处理相关事务,自身并不构成国家。⑥
这三点内容密切相关,相互支持。正因为政府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代理国家事务,那它的代理资格就可能被取消,政府就可能被替换,但国家并不会因此消亡,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国家能比特定政府更持久。同时,若政府只是由不同角色和地位的占有者构成,那当占有人员发生系统的变化时,也就是当政府变化时,这并不会影响这些角色和地位以及规定角色和地位的制度结构,即不会影响国家的存续。也因为政府只是特定时间内国家事务的代理者,可以下台,因而政府只能由占据不同地位和角色的人员构成,而不能包括规定地位和角色的制度结构,否则政府的更换就是国家的毁灭。
若我们接受关于国家和政府关系的这三点看法,那就意味着国家的正当性和政府的正当性并不能合二为一。国家的正当性是政府正当性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若国家不正当,则政府就不可能正当,而即便国家是正当的,政府也可以不正当。我们先从政府和国家的代理关系来解释。假定甲是政府,乙是国家。若甲是乙的业务代理,但乙的业务根本就是不正当的,那甲怎么会有正当的代理资格呢?正如若乙没有贩毒的正当权利,则甲也不可能有代理乙贩毒的正当权利。可即使乙的业务是正当的,甲的代理也并不一定正当,因为甲可能是未被乙授权过的非法代理,也有可能是,虽然乙曾经授权,但甲违背了授权协议。因此,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之关系,即国家的正当性未必能保证政府的正当性,但国家的不正当必定导致政府的不正当。
我们也可以利用国家与政府关系的第二点得出同样的结论。若国家是持续存在的制度结构,而政府只是制度结构确定的角色和职位的占有者,那若制度结构是不正当的,也即若国家是不正当的,角色和职位的占有者就不会是正当的,也即政府就不会是正当的。但即便制度结构是正当的,角色和职位的占有者也可能不正当,因为他们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占据了这些角色和职位,也有可能是背弃了与角色和职位相关的职责或要求。⑦
考虑到国家正当性和政府正当性的上述关系,国家的正当性问题在逻辑上要先于政府的正当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国家正当性问题上。但国家的正当性仍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限定。我们需要追问,是国家哪个方面的正当性?
现代国家通常都会声称有权利做以下一些事情:有权为生活在特定地域上的人们制定、执行并裁决法律规则,有权挫败那些试图做同样事情的竞争者,有权要求人们服从法律规则,有权控制特定的领土,如限制和约束人们对领土上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控制内部和外部的人进出边境,有权要求外面的国家、机构或人员不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尊重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等。这些都是极具争议性的主张。对这里的每一个主张或行动,我们都可以追问其正当性,探讨其道德证成问题。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答案一定是一样的,很可能有些主张可以得到证成,有些则毫无合理性可言;有些主张的证成条件容易满足,而有些则要困难得多。
就这些主张而言,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两个维度,即对内的和对外的维度。对内的维度指的是它声称有权对内部人员所做的事情,而对外的维度则是对外在他者的要求和行动。我们可以分别追问这两个维度的正当性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把国家正当性问题区分为内在的正当性和外在的正当性两个方面,并且要给予每个方面以单独的考察。⑧
四、结语
最后对上文的论述作一个总结。我们首先从对正当性这一概念的分析开始,指出其实质含义是道德证成,然后进入政治的正当性问题,阐明了政治的正当性就是探寻对政治权力或权威的道德证成,并进一步追问,为何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特别构成一个问题,为此考察了政治权力的五大特征,随后进一步把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具体化为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并论证了国家的正当性之于政府正当性的逻辑优先性,最后又区分了国家正当性的内在和外在维度。
注释:
①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自然权利论者或自由主义者而言,那些削弱或限制人的自主性和道德权利的制度与实践之正当性是很成问题的。韦尔曼清楚地阐述了政治正当性问题如何对自由主义者构成特别的挑战,关于他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见Christopher H.Wellman.Liberalism, Samaritanism,and Political Legitima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5,1996,P212-13.
②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明理的人是与理性的(Rational)人相对而言的。罗尔斯给出了明理的人具备的两种美德:其一是愿意提出并遵循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其二是愿意承认判断的负担,并接受其后果,即在证成强制性的政治权力运用时需诉诸公共理由。而理性的人恰恰欠缺的就是这两点。欲详细了解罗尔斯的相关论述,可参见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8-58.
③布坎南特别强调政治权力的这种垄断性,他认为,只有这一点才足以把政治权力和单纯的强制区别开来。要详细了解他的相关论述,可参见Allen Buchana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Ethics,vol.112,2002,P690.
④这里对政治权力的深远影响的阐述参考了罗尔斯对社会基本结构重要性的论证。他关于此问题最全面的论述,参见John Rawls.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2-57.
⑤布坎南这里给出的对国家和政府关系的理解预设了关于制度的某种理解,即制度的核心是公共的规则体系,它会界定一些职位和角色以及相伴随的权利、责任、权力与豁免。按照这种理解,政府就是由占据这些职位和角色的人员构成,它当然会不同于国家,因为国家是由相对抽象的规则体系以及在规则体系下确立的职位和角色构成的。这也正是罗尔斯心中所理解的制度。罗尔斯的观点详见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5.
⑥这三点中的第一和第三点尤其为莫里斯(Christopher W.Morris)所强调。欲详解其观点,可参见他的著作An Essay on the Modern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0-46.
⑦西蒙斯(A.J.Simmons)利用洛克的解释框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按照洛克的解释模式,国家因成员的一致同意而获得了正当性,这种同意会授予集体一些权利,当这些权利为一个中央权威所运用时,足以维系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只有当国家授予政府运用这些权利的资格时,政府才是正当的。因而,若国家是不正当的,政府就一定是不正当的,因为政府的统治权利需要国家的授予,但国家的正当性并不能保证政府的正当性,因为即便国家是正当的,国家可能并没有授权某个政府去统治。西蒙斯的相关论述,参见A.J.Simmons.Justification and Legitima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09, 1999,P747.
⑧这里对国家正当性内在和外在维度的区分,来自于西蒙斯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西蒙斯对国家正当性问题的区分可见于其论著Politic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34-35.
[1]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Mathew Coakley.On the Valu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Politics,Philosophy&Economics,vol.10,2011.
[3]Thomas Nagel.Mor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6,1987.
[4]David Copp.The Idea of a Legitimate Stat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8,1999.
[5]Allen Buchana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Ethics,vol.112,2002.
[6]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责任编辑:赵 伟】
B82-069
A
1004-518X(2016)04-0005-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西方现代政治伦理思想研究”(13JJD7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