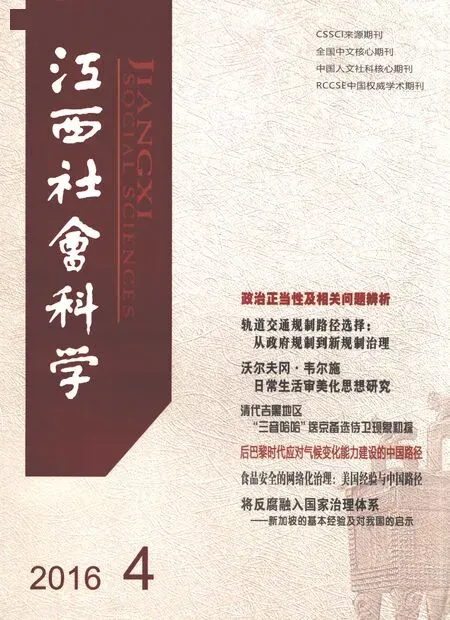墓志中所见唐代晚婚女考论
——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中心
2016-12-19王丽娜
■王丽娜
墓志中所见唐代晚婚女考论
——以《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为中心
■王丽娜
唐代晚婚是一种社会意识,通过分析社会实际及墓志中女性的婚姻实态,可将当时女性晚婚年龄定为24岁及以上。墓志中的这些晚婚女大多出身良好、家境优越、知书达理、身体无恙,所嫁理想。皇室女晚嫁主要因宫廷政治斗争以及战乱的波及。其他晚婚女则多因自身择偶时间过长,高门和良士是其选择的标准,她们自身的优越条件以及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其晚嫁的基础和条件,同时男性对仕途的渴求以及蓄养姬妾的风气又促使他们愿意接纳晚婚女。
唐代晚婚女;墓志;乐安孙氏女;晚婚原因
王丽娜,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目前学界对唐代晚婚女性已有一定关注,如姚平、张国刚、李志生、万军杰、蒋爱花等都曾对唐代女子婚龄问题做了探讨①,但所及层面仍有不足,多以孤例说明单个原因,而后叠加,进而总结晚婚缘由,而没有将晚婚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她们所处的环境、心理状况以及愿意娶其为妻的男性心理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墓志文字虽然充满了大量溢美之词,但相较于其他史传文献,它确能提供相对较多的和具体可用的真实样本②,因此,本文集中整理了唐代墓志集大成者 《唐代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下简称《续汇编》)中的墓志资料,以期对唐代晚婚女做一探析。需要说明的是,文本所探讨的晚婚女只限于初婚女性,不包括再嫁情况,又因墓志所载女性多属社会中上层,故文本结论不可涵盖唐代所有女性。
一、晚婚年龄界定
区别于近现代政策、法律对晚婚年龄的明文规定,在唐代,政府实际并没有对晚婚做出严格界定,有据可查的明确规定女性婚龄的诏令大概有两次:一次是太宗贞观元年(627)二月四日,诏曰:“宜令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1](卷八十三《嫁娶》,P1527)一次是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1](卷八十三《嫁娶》,P1529)从这两条诏令看,虽然指出女子15岁、13岁要结婚,但并没有如汉魏时有治罪、加税等手段强制女性到时结婚③。太宗时“婚姻及时”只是作为官员的考核要求之一,且不会直接造成离任、贬职等严重后果;而玄宗朝更是几无惩罚,只说“听婚嫁”,似乎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可以”、“能”的意思,或许敕文更为确切的表述应是男子15岁、女子13岁可以结婚。且两条诏令均对女年作“已上(以上)”补充,所以其中的15岁和13岁也不是确切的年龄所指。
虽然政府并未规定何时为晚,但“晚”确也存在于唐人观念中,如白居易《赠友五首》曰:“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2](卷四二五《白居易二·赠友五首并序》,P4678)其中的“多过期”即是诗人对晚于正常婚配年龄的表述,此外,唐墓志中还有对女子不能及时婚配而深表遗憾的描写,如《唐故江夏李氏室女墓志铭并叙》云:“吾家道素空,不及早嫔于大族以显其懿范,故其追痛之大,倍于常理也。”[3](P2323)
既然晚婚不是政策、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唐人脑中的日常观念,那么界定晚婚年龄就必须立足当时的社会实际。唐代小说《玄怪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4](卷二《韦氏》,P17)韦氏女在既笄(通常认为是15岁)五年内,先后有3人求聘,期间韦母没有表现出任何催促之意,这个事例一则更具体地说明唐代13、15岁的规定并不是强制性的,二则说明女子20岁成婚是很正常的社会实际。且上列白居易诗中“二十女有归”一句也透露出唐时女子的正常成婚年龄应该包括20岁,或者说20岁成婚在当时人看来并不为晚。其实,从女性的生理周期看,20岁是女子心智、生理刚好发展成熟时期,应是结婚的最佳年龄,孔子也说过“十五许嫁而后从夫,是阳动而阴应,男唱而女随之义也,以为绩祖紃识认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义,妇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渐乎二十,然后可以通乎,此事通乎,然后乃能上以孝乎舅姑,下以事夫养子也”[5](卷一五一《昏礼》,P13)。
当然,考虑唐代晚婚问题,必不可忽视礼法。《旧唐书》中就记有太宗之女衡山公主因礼法推迟结婚一事:“是时,衡山公主欲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志宁上疏曰:‘……伏见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礼。’窃按《礼记》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固知须终三年。《春秋》云:‘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即史策具载,是非历然,……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此理有识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说也。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后成礼。”[6](卷七十八《于志宁列传》,P2698-2699)且唐代律法对女子违礼成婚也定有严厉处罚,《唐律疏议》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疏议曰:父母之丧,终身忧戚,三年从吉,自为达礼。”[7](卷第十三,P257-258)“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仗一百。”[7](卷第十三,P258),因此,在唐代遵礼成婚不仅是社会共识,人情所致,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故女子在出现上述特殊情况时必须要推迟结婚,其年限一般为3年。
综上,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晚婚在唐代更多是一种社会意识,并不同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晚婚概念。根据女性的生理发展以及唐人的实际生活可知,女子在20岁结婚的情况较为合理且颇为常见,但20余岁即可视为晚婚。同时,女子成婚必须符合“有故”推迟3年的礼法规定,这3年等待期并不是自然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的被迫之举,必须为之,且是被世人所接受认可的行为,因此,似可将这3年看成是正常婚龄之后的过渡区间,依此,笔者对晚婚的理解更倾向于张国刚、蒋爱花的观点④,认为应该在正常婚龄之外有个过渡范围,而这个过渡笔者认为更多是因礼法规制造成,故定为3年较合适,即似可将20岁的正常婚龄往后推3年,把23岁定作唐代女性的最晚正常婚龄,那么晚婚即可定作24岁及以上。
但也正如前面分析所得,晚婚只是一种个人观念,故由于生活环境、知识储备等各方面差异,不同阶层、群体脑中对晚婚的定义必然也会大不相同,所以如要确切界定墓志中女性的晚婚年龄,还必须探究她们的婚姻实态。因此,笔者将《汇编》与《续汇编》中明确载有女子婚龄的记录列表如表1所示(由于笄年具有不确定性⑤,因此本文对志文中所见幼笄、弱笄、副笄、微笄、将及笄、殆将笄岁、近笄、笄、笄、笄年、笄岁、笄缨、笄栉、笄丱、纵笄等情况均不做统计)。

表1 《汇编》与《续汇编》收录墓志中女子婚龄记录
通过表1可知,女子出嫁主要集中在13~21岁,均超过总人数的5%,其中18岁时出嫁人数最多,为38人,21岁以后出嫁人数明显减少,故晚婚应该是处在21岁及以后。但为了更便于分析晚婚女各自的情况,我们对晚婚比例进行量化,计算可知,21岁及以上结婚的占总样本的20.77%,22岁及以上结婚的占15.49%,23岁及以上结婚的人数占11.27%,婚龄在24岁及以上的占10.56%,25岁及以上的占7.04%。那么从实际来看,如果把界限定为21岁,即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晚婚,如此的高比例恐怕在人们心中难以用少数来表达,也不符合社会主流;而如果定作25岁,则100人中只有7人属晚婚,比例之少似用超级晚婚更妥。
再看学者的数据,明确统计唐代女性初婚年龄,并确切说明晚婚比例的有蒋爱花与万军杰,且两位学者断定晚婚范围的方法均是通过各自的数据比例。万军杰认为20岁及以上属于晚婚是因其计算得到,20岁及以上年龄结婚的女子占到了总样本的13.77%[8](P107)。万的统计样本并不仅限于《汇编》与《续汇编》,且其将幼笄、初笄、逾笄等不确定的名词表述全部数字化,如此虽增加了样本数量,但笔者认为稍欠准确。蒋爱花把晚婚年龄定为23岁及以上的主要依据是在其统计中,23岁及以上的结婚人数占到了总数的8.91%[9](P35)(蒋的统计有部分讹误与遗漏,笔者对其进行了补正,故与本文数据稍有不同)。由此可知,约10%是学界对晚婚比例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较符合社会实际状况的比例。所以从本文统计的数据看,不能定作21岁(20.77%)和25岁 (7.04%)。再比较22岁的15.49%、23岁的11.27%和24岁的10.56%,这三个均在10%左右,故均可作为晚婚界限,但为了更确切地提取样本,具体分析这一群体的特点,一般在数据上倾向于选取更小的范围,故本文将晚婚年龄界定为24岁。
综合唐人观念以及数据分析,本文拟将唐代女性的晚婚年龄界定为24岁及以上,这样的考察方法一则避免了仅从数据大小区分早婚、晚婚的不确定性,二则也更加符合唐人心目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晚婚情况。当然,因笔者主要考察的是《汇编》与《续汇编》收录墓志中的女子,多为中上层女子,并不能涵盖所有女性,所有阶层、情况,故以她们为材料定义的24岁及以上可能无法作为唐代所有女性的晚婚年龄。
二、个案分析——《唐许州长葛县尉郑君亡室乐安孙氏墓志铭并序》
《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15《唐许州长葛县尉郑君亡室乐安孙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若人归之五岁,不幸以元和二年六月廿七日夭殁于东都康俗里第,凡春秋卅二。”[3](P1959)意为孙氏结婚五年后卒,享年32岁,即孙氏出嫁时已有27岁,大于24岁,是典型唐代晚婚女。从其墓志记载可知,孙氏出生于普通官宦之家,所嫁也非皇亲国戚,与墓志所见大多数女子情况类似,故其具有普遍意义。而难能可贵的是在《唐代墓志汇编》中还收录了其父与其母的墓志,这就为探究孙氏晚嫁提供了更加明晰的素材。在唐代传世材料相对匮乏的今天,分析孙氏的明确度、可信度显然优于其他晚婚女,因此,笔者将孙氏作为墓志中一般晚婚女的代表详加探析,以求点面结合,深入揭示唐代晚婚女状况。
(一)孙氏女家庭背景
根据《汇编》元和015记载孙氏是“赠右仆射文公之孙,桂州府君之第二女也”[3](P1959),出生官宦人家,依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议婚》云:“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2](卷四二五《白居易二·秦中吟十首并序·议婚》,P4674)可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贫女常会晚嫁,如孙氏这样的红楼富家女理应是早嫁,那么,为何她却迟至27岁才嫁予郑氏,确实值得探究。
据贞元026孙父墓志《唐故中大夫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州本管都防御经略招讨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孙府君墓志铭并序》[3](P1855-1857)记载,孙氏父孙成自任官以来,屡次升迁,历任左内率府兵曹参军、监察御史、陇右节度判官兼掌书记、长安县令、信州刺史等职,但贞元五年(789)时,孙成不知何故卒于桂州刺史任上。此时孙氏女刚好14岁,正是适嫁年龄,遭此丧事必然要延后成婚,这不仅是唐代礼法规制,也是人情所致,因此,孙氏若想出嫁也必须在3年之后,而这3年正是笔者前面所论证的过渡期,是被世人接受的延迟期。但需要注意的是丧期并不能明确解释孙氏晚嫁,因为就算推迟3年也应是17岁成婚,而不该迟至27岁。
当然,孙成的去世无疑会使整个家庭面临困境,永贞006孙母墓志《唐故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孙府君故夫人范阳郡君卢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初府君廉省桂林,天实降祸,男子未仕,女子未笄,乡关日远,云水天际。”[3](P1945)试想,当时“其孤惟肖、保衡、微仲、审象等,皆童稚差肩,哭踊过礼,提挈江缴,辛苦风潮,行道所怜”[3](P1857),是何等凄凉的景象。那这是否就表明此时的孙家属于白居易诗中的贫女之家呢?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因为在此句之后,紧接写道:“夫人提孤稚,奉帷,克询龟筮,返葬瀍洛,门户再立,戚姻如归。”[3](P1945)孙母带着尚未做官的四个儿子和未出嫁的孙氏女,仍能将丈夫返葬瀍洛,并能再立门户,这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之后四子均入仕,“嗣子右金吾胄曹惟肖、进士保衡、右羽林录事微仲,讨武县主簿审象”[3](P1945),这也需要事先能承担一定的教育经费,由此可知,即使孙父逝世,孙家生活也还是较为宽裕的。而且从孙父、孙母的志文中可知,孙家早至齐时就世代为官,五代以内有明确官名可考,其中祖为朝散大夫、宋州司马,赠秘书监,烈考为刑部侍郎,赠右仆射文公,而孙成本人也是崇文馆明经及第出身,这说明孙家不仅门第显赫,而且应是书香世家,且孙成自任官以来,屡次升迁,也说明孙家实力雄厚,而况身为河东观察判官、摄北都副留守、检校尚书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的孙父仲兄在孙成去世之时尚且在世;且孙氏母亲为范阳卢氏,齐姜冠族,卢氏之父为邓州南阳令,卢氏的外甥(裴氏)是将仕郎守、尚书考功员外郎。这样的家庭背景就保证了即使孙父去世,孙家的生活也不至穷困潦倒,不会因难以支付嫁妆导致晚嫁。
(二)孙氏女自身条件
既然不是家庭经济原因,那是否孙氏女本身存在某种缺陷导致晚婚?孙氏墓志记载其“组文绣之事,精能而不怠;诗书图史之学,耽玩而有得”[3](P1959)。且依据孙家历代为仕的背景,孙氏女应该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动遵礼法,方明柔婉”[3](P1959)。
从身体状况看,一,其生有1女的记载证明孙氏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且身体应属健康;二,因铭文是由其仲兄保衡编撰,弟审象书写的,故从“自其构恙也,惟四三昆弟心祷于上下神□目治于古今方术”[3](P1959)的记载中无孙氏母出现的情况可推知,孙氏女得疾时孙氏母可能已不在世,而孙氏母逝世是在永贞元年(805),当时孙氏女已经30岁,实已结婚3年,所以,孙氏得疾一定是在结婚后某日,由此可判断孙氏女晚嫁不是由于婚前有病。
(三)孙氏女心理探析
以上分析可知,孙氏女生于官宦世家,经济宽裕,自身条件优越,从客观上讲定不会无人愿娶,而其究竟为何27岁高龄才出嫁,或许墓志中“中外敬异,为择所从,以郑君高门良士,故仰而归之”[3](P1959)的记载,隐约为我们提供了孙氏晚嫁的心理动机。“为择所从”表明了女方的主动选择,而其之所以最终选择郑君,墓志中也明确说明是“以郑君高门良士,故仰而归之”,意孙氏选夫重在两点,一是良士,二是高门。良士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所有女子选择丈夫的必要条件,此点毋庸置疑;而对高门的重视则反映出唐人重视门第的风气,且不说《氏族志》编撰的动机,单从志文中对门第的大幅叙述就可窥见唐人的门第观念,关于门第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就孙氏而言,父亲的去世使得家势骤然下降,故想要寻求与其父在世时家境相当的良士定然不易,这可能是孙氏女在正常婚龄无法得到满意对象的重要原因,而逮兄弟均为官,家族再旺时,选择高门也就不成难事。
当然这样推断的前提是高门男子在选择妻子时也要重视门第家境,且能接受大龄女子。其实,唐代士人的门第观念较女性更为突出,王梵志有诗云:“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但得身超后,银财物莫论。”[10](卷四,P488-489)即意男性娶妇要选择大家之女,而女性选夫则不用强求高门,而且高门男子大多要奔竞于仕途,所以他们更愿意寻找能够佐成其家的女子,而晚婚女良好的家世,较高的文化素养刚好满足这一需求。而男子为何会接纳大龄女子,笔者认为这应和唐代男子蓄养姬妾有关,从墓志记载看,晚婚女多有嗣子、别子,并多描述其“抚鞠无异等”[11](P1018),“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辩”[11](P853)等,这都表明其丈夫身边除晚婚女外,应还有其他女子相伴,因此他们不会因为年龄而排斥能佐其家的晚婚女。
由此可知,家庭背景优越、自身条件突出的孙氏女晚嫁并不是由于无人愿娶,而更多的是孙家或孙氏自身择偶时间过长。而唐人重视门第的风气以及女方自己对良士的渴求是其愿意花费大量时间挑选夫家的重要原因,当然自身的优越条件是其有资本和自信无顾年龄等待心仪伴侣的基础。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的大环境也为其晚嫁提供了可能,由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胡化”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允许女性在选择丈夫时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而男性蓄妾成风以及追求仕途的渴望又促使男方愿意接纳条件优越的晚婚女性。或许这就是孙氏女之所以晚婚的原因。
三、墓志中所见其他晚婚女情况
孙氏女只是晚婚女中的一位,以24岁出嫁为限,在《汇编》与《续汇编》中共出现有31⑥位晚婚女(包括孙氏),她们的情况是否均如孙氏女一般,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了解晚婚女的出生背景、经济状况,笔者首先统计了孙氏以外30位晚婚女的祖父、父亲所任职位,其中有8位家世不详,2位为皇家女,其余20位均出自官宦之家。
两位皇家女,一是太宗子吴王之女信安县主(《汇编》开元056)[12](P1192-1193),一为玄宗子李瑛之女博平郡主(《续汇编》建中001)[11](P723),因其特殊的出身,她们的婚姻必然与政治动态紧密相连。信安县主之父是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但在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会房遗爱谋反,遂因事诛恪……有子四人:仁、玮、琨、,并流于岭表”[6](卷七六《太宗诸子列传》,P2650)。这场政治斗争使当时年未胜衣的县主因之也受到牵连,故“(县主)夙惧凶悯,竹园无讬,桂苑幽居,陪奉献陵,多历年所”[12](P1192),直到42岁才得嫁元思忠。而博平郡主父是玄宗第二子李瑛,曾任皇太子,之后因武惠妃的加害,加上李林甫的怂恿,“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6](卷一百七《玄宗诸子列传》,P3260)。当时博平郡主只有7岁,故墓志称其“长于保姆之手”[11](P723),到天宝中期,李瑛案已得到一定平反,且博平郡主此时也到了宜嫁年龄,但郡主却迟至肃宗朝的上元元年(760)才出嫁,假设还是由于这场政治斗争的余波,那她为何又不在宝应元年(762)以后,即李瑛案彻底平反之后结婚,《旧唐书》载:“宝应元年,诏雪瑶、瑛、琚之罪,赠瑛为皇太子。”[6](卷一百七《玄宗诸子列传》,P3260)且郡主实际在其29岁即上元元年时就已经“宠膺封号”[11](P723),所以,笔者认为除却这场政治斗争的余波,天宝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也应是郡主婚事一再耽搁的重要原因。综上,皇家女晚嫁与宫廷动乱、国家战争有着直接联系。
其余20位官宦之女,父亲在中央六省、御史台、九寺任职的有4位(除去同时担任刺史的官员);在东宫任职的有2位;担任刺史一职的有4位;另有观察推官1人,司仓参军1人,录事参军1人;在县级任职的有7位,其中县令3个,县尉2个,主簿2个⑦。从品级⑧上看,五品及以上的高官有8位,占总数的40%,大大超过唐朝高官的一般比例。如此家庭背景整体上甚至较出嫁年龄最为集中的18岁女子更为优越,38位18岁出嫁女中有8人家世不详,1位是高密公主之女,1位父亲不为官,乐田园之事,但其曾祖、祖父均为朝官,1人出生妓肆,其余27位女性父亲均在朝为官。这27位为官父亲中,在中央六省、御史台、九寺、将作监任职的有6位;东宫供职的有2位;就事于地方的有河南府功曹1人,州刺史1人,州都督2人,州司马2人,州司功参军1人,州录事参军事1人,郡长史1人,县令5人,县尉1人,县丞2人;另有县开国男1人,郡开国公1人。计算他们的品级可知,五品及以上约有7位,占25.93%。可见,从整体上看晚婚女的家庭背景较为优越,甚至要优于正常出嫁女。
再看晚婚女的文化程度,她们的志文中普遍明确记录其拥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一是多识字知书,如《唐秘书省秘书郎李君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并序》记宇文氏:“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常侍公每贤之,为人曰:‘是女当宜配科名人。’”[3](P2426)《唐郎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曰:“(崔氏)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丝桐、讽诗骚以为娱。”[11](P853)二是多精通音律,如《瘗琴铭有序》记:“(庄氏)蚕桑之暇,癖嗜丝桐,家有美材,命工精断。音律既协,性命相依。”[12](P256)《唐故魏王府参军李缨亡妻弘农杨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女工刀尺,悉尽其能,至于丝竹,多所留心,就中胡琴,尤是所善。”[3](P2461)笔者猜测晚婚女之所以文化素养较高也应该与她们多出生官宦世家,家资充裕有关。
从生育记载看,30位晚婚女中,23人明确有亲生子女记录,占总数的76.67%;有1人难产而死,不知孩子是否出生(《汇编》显庆044);另有3人生育记录不明,或难以确知家中子女是否有其亲生(《汇编》贞观090、《续汇编》咸通064),或因下泐辨认不清(《续汇编》长庆016);只有3人确定未曾生育(《汇编》元和115、大中033、咸通019),这个数据只占到10%,且这3人婚期都不足1年,在时间长度上并不具备生子的可能。以上数据明确表明,晚婚女多具有正常的生育能力,并无异常。
从死亡情况看,30位晚婚女的平均卒年为47.33岁,60岁及以上死亡的有10人,而统计有确切卒年记载的35位18岁出嫁女可知,其平均寿命为45.49岁,且卒年在60岁及以上的仅有9人,在数量和比例上均低于晚婚女。另外从墓志记载的死亡原因看,晚婚女中有2人记载不明(《汇编》大和073、大中068),2人当寿而夭(《汇编》贞观090、《续汇编》建中001),1人遽罹娩难(《汇编》显庆044),1人因瘴毒外侵(《汇编》咸通019),其余24位均遘疾而亡,且多记录得疾时间均同孙氏女,是在婚后的某年,尽管这些数据不能表明女方的身体素质,且不排除墓志记载会有隐晦之处,但就此仍可推断,晚婚女在婚前多处于健康状况。因此,从寿命和死亡原因两方面大体可以判断出,与正常出嫁女相比,晚婚女体质在整体上并不羸弱。
通过以上数据统计和分析可知,墓志所见其余30位晚婚女在文化程度、生育能力以及身体状况上大都与孙氏女情况类似,具备良好的自身素质,甚至整体上要优于18岁正常出嫁女;而家世的判断则更进一步表明她们身处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可以说,这一群体的普遍特点即是出身良好,家境优越,文化素养高、身体无恙。
孙氏女出嫁长葛县尉郑君,主要是因其为高门、良士。而其他30位晚婚女所嫁也多为官员,其中23人丈夫有明确的官职记载,占总数的76.67%,为了更加量化地探究晚婚女所嫁情况,笔者将晚婚女逝世前丈夫所任官品与其父亲进行对比,在可供比较的14个样本中⑨,丈夫品级高于父亲的有6个,品级相似的有3个,另有5个样本显示父亲品级高于丈夫,由于墓志是在女方逝世后不久所撰,故样本中父亲与丈夫的官品也未必是他们生前的顶峰,但从总体上看,晚婚女所嫁夫家与娘家的家世、门第大体相似。由此可知,晚婚女虽然出嫁时间较晚,但其所嫁仍是“门当户对”。
因此,墓志所见晚婚女中除两位皇家女因身份特殊,情况稍有不同外,其余晚婚女特征大都与孙氏女相似,故而造成她们晚嫁的原因也多与孙氏类似,主要是因为自身的主动选择,而不是由于无人愿娶的被迫之举。这种女方的主动选择也常见于墓志记载,如《唐泗州下邳县尉郑君故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云:“先夫人亦抚念有加,每为选求良匹,以大中三年夏四月归于郑氏。”[5](P2382)甚至还有因择偶时间长导致终生未嫁,留有遗憾的情况,如《唐工部尚书杜公长女墓志铭并序》记:“(杜公)比常话于宾友间,意者求贤以配之。况公望高天下,宗族当今为大,凡谓甲门清才,求之皆未许嫁,谁谓如是之不幸耶!”[11](P941)而正如之前对孙氏晚嫁的分析,也正是由于这些女子拥有比一般女子更为优秀的自身素养、社会地位,她们才有可能晚嫁,因为金钱、寿命、素质涵养等都是保证女性能长期不出阁的基础,而社会对女性的宽容以及男性追求仕途和享乐的风气又为其晚嫁提供了可能。
四、小结
在唐代,晚婚并不是政策、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存在于人们脑中的主观意识,因而不同群体所认为的晚婚期限也会所有不同。通过对婚姻实态的考察,大体可将墓志中女性的晚婚年龄界定为24岁及以上。在这些晚婚女中,皇室女情况特殊,晚嫁主要是因宫廷政治斗争以及战乱的影响,如信安县主与博平郡主。其余女子则多是由于自身选择时间过长,错失了最佳结婚年龄,《汇编》元和015中的孙氏女即为一例。出身良好,家境富裕,知书达理,身体无恙等是这类女性能够主动选择夫家的基础,而男性对仕途的渴望以及蓄妾成风的现实又使得他们愿意娶晚婚女为妻 (需要强调的是晚婚女婚后多为妻子),同时,当时社会对门第的看重也促使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多重门第,少看年龄,当然唐代女性地位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晚婚提供了可能。因《汇编》与《续汇编》所收女性多属社会中上层,且笔者总结的晚婚女特点也是就墓志中女性而言,故本文结论不可适用全部唐代晚婚女。诚然,相较于墓志中的正常出嫁女,晚婚女所占比例很小,但她们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女性,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主动寻找心仪伴侣,这本身就体现了女性的自主以及社会的进步,故应引起关注。
注释:
①如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一章《笄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65-75页;李志生:《唐人婚龄探析》,《北大史学》2001年,第15-28页;万军杰:《唐代女性的初婚年龄》,《华夏考古》2014年第2期,第106-112页;向淑云:《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三章《婚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7-282页;、蒋爱花:《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第一章《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焦杰:《中晚唐公主“难嫁”原因新探——从太和年间的公主入道现象说起》,《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19-127页。
②正史中有关女性结婚年龄的资料极少,李树桐采用正史得到的样本仅有25例,而李斌城、姚平、蒋爱花、万军杰通过墓志得到的样本分别多达304、299、480、581例,优势明显。
③战国到魏晋时期,国家明确规定结婚的最晚年龄,如若超期,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国语·越语》记越王勾践曾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汉书·惠帝纪》曰:“令:女子年十五以至三十,不嫁五算。”《晋书·武帝本纪》记司马炎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④蒋爱花、张国刚认为在最佳婚龄以外还应有个过渡,即早婚和晚婚指的是过渡年龄组以外的结婚范围,其中,张国刚更是将范围缩小至大龄晚婚。但他们均仅从数据上判断应该有过渡期,并未对其进行阐释。参见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蒋爱花:《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⑤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一章《笄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有详细论述。
⑥《续汇编》神龙021中记录任氏婚龄是30余,因志文中余“几”不明确,所以未列入表1对结婚年龄的统计,但30余岁显然大于24岁,应属晚婚范畴,故笔者此处分析晚婚女情况时将任氏包括在内,共得31位晚婚女。
⑦只统计晚婚女生前其父所担任最高实际官职,不统计试职、赠职。
⑧笔者对品级的计算主要依据《唐六典》,但《唐六典》并不能完全对应唐后期的情况,故此项统计只是大致情况,略有出入。
⑨除去晚婚女的丈夫或父亲品级无法判断的样本以及2位皇家女样本。
[1](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全唐诗[M].(清)彭定求,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唐代墓志汇编(下)[M].周绍良,赵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唐)牛僧孺.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五礼通考[M].光绪六年九月江苏数据重刊本.
[6](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万军杰.唐代女性的初婚年龄[J].华夏考古,2014, (2).
[9]蒋爱花.唐代家庭人口辑考——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10](唐)王梵志.王梵志诗校注[M].项楚,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周绍良,赵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2]唐代墓志汇编(上)[M].周绍良,赵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42
A
1004-518X(2016)04-01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