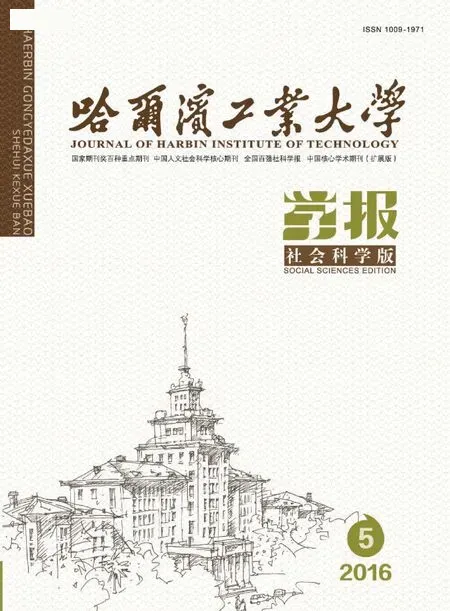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
2016-03-06邹庆华
邹庆华
(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
邹庆华
(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生态环境问题纷繁复杂,既要考虑系统性和整体性,又要考虑复杂性和局部性,必须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协同思想为中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公民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占据特殊的主体地位,公民的生态意识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在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目标的指引下,把生态意识融入到公民生态意识培育体系构建中,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生态教育经验,拓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视野;转变公民原有生态观念,提升公民生态意识教育水平;增强政府正面引导推动,培育公民参与生态实践能力;更新政府生态治理理念,推进生态相关制度全面建设。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民;生态意识
“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是中共十八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构想。可见,如何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探索,协同治理理念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公民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理念的确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以,生态文明的标准规范建设及其运行模式也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公民生态意识中的心理预期与目标要求,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的内在驱动力。公民内心所持有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理念决定了公民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自我认知、价值取向与态度原则,这是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的本质规定和价值标准。新时期,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发挥教育的先导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来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才能使公民的生态观念发生质的转变,进而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这是当下中国缓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
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对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现实要求
生态环境问题纷繁复杂,进行协同治理更是千头万绪,既要考虑系统性和整体性,又要考虑复杂性和局部性,必须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有统有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1]在协同治理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和公民社会等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打破了原有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模式。各协同主体在自觉自发原则和自身实力能力定位的基础上,遵循事物客观规律,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公民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主体中地位特殊,具有双面性,既是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者和消费者,又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这双面性决定了公民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特殊主体地位,也说明公民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人是生态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践主体。”[2]因此,要实现广泛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提升公民主体的生态意识。公民首先要明确自己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意识到自身不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对象,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产品的享有者和消费者,而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主人,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和过程,是治理工作的实践者,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对政府治理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只有全体公民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识,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因此,公民生态意识培育是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前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必然结果,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促进。
公民的生态意识水平不仅关系到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然而,生态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在不断审视由于不合理的生态实践而引起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渐进形成的一种对于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全新理性认识。实质上,它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意识,反映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念和价值取向。生态意识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意识,将会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更新公民的生态理念和约束公民的生态行为,从而促使生态环境“善治”早日实现。所以,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中,需要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全新理解,重新定位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实现公民生态观念的深层次转变。公民有了生态意识,就能使其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意识转化为公民个人自觉的生态行为,更好地与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广泛协同,更加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从而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公民生态意识的现状
随着西方协同治理理念的引入,中国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构想,而在实践中,公民作为重要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主体,由于缺乏生态意识的支撑,显露出生态知识缺乏、生态意识淡薄、参与度不够和知行不统一等问题,难以与其他治理主体展开有效协作,使生态治理陷入困境。
一是公民生态知识缺乏。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生物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其本身有一定的循环规律,如若人类的需求超出生态系统的负荷,就会出现森林消失、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和物种灭绝等现象,威胁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人是生态系统循环中重要的因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生态规律认知不足,对于生态失衡未引起警觉,依然盲目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造成了有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难以恢复或不可恢复,生态问题严重。只有公民对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态危机和生态规律等一系列有关生态的知识有了科学的认识,才能更好谈及公民生态意识的改善和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二是公民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意识反映了人类主体对自己生存发展于其中的生态存在即社会—生态系统的深层把握[3]。当前,有些公民虽意识到如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想法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却举步不前。这种知行不统一的现象源于部分公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存在着许多错误心理,这是影响公民生态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有些公民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所采取的一些治理措施治标不治本,根本无法改变生态环境现状;有些公民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政府的职能,与公民个人关系不大,即使公民个人做到了自省,但是生态环境整体上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改变;还有相当一部分公民依然存在“竭泽而渔”的心理,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生态发展的长远效益。生态环境问题无法回避,公民消极应对的心态更是不可取,唯有端正生态思想,才能有利于自身生态意识的提高。
三是公民生态行为有待养成。生态行为是人们把日常生活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理解、认知和情感等付诸一定生态实践中的一种实际行为。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公民存在很多不环保行为。如政府提倡“低碳生活”概念,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了公民太多的不“低碳”行为:乱仍废旧电池、使用一次性餐具、出门必开车、痴迷皮草等等。其实,低碳生活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模式并不能成为公民拒绝低碳生活的理由,只要公民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主动去约束自己,节约身边各种资源就会留下每个人的“碳足迹”,否则这些不环保的行为就会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应该构建公民日常生态规范,养成公民良好的生态行为。
四是在生态治理中,公民存在严重的参与不足。“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4]公民是最广泛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参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帮助和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并实现公共生态环境利益。新形势下,中国公民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表现出了许多不足:从公民参与地位看,公民应该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治理主体之一,然而,公民在操作层面上多属被动参与,公民也仅仅是参与政府的一些生态环境宣传工作抑或是事后尽到监督的义务,加之某些政府人员对于公民参与还存在着思想上的障碍,公民很难深入到政府的决策之中,这些都使得公民的主体地位名不副实;从公民参与途径看,由于公民治理主体的地位得不到确立,这间接影响了公民参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途径。当下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单一的,主要以个人环保行为和参与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活动为主,其他提倡的途径如生态管理听证会、民意调查、发展社区和公民论坛等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未实施。从目前来看,中国生态治理并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局面,尤其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更是陷入困境。
三、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策略
树立和增强公民生态意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要增强公民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环境的良好风气,政府就需要从多元层面探索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相应策略。
(一)借鉴发达国家生态意识教育经验,拓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视野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做好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应拓宽国际视野,借鉴国外先进生态教育经验。同时,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实际,找出国外与中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契合之处,通过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培育模式来塑造中国公民的现代生态意识。
倡导政府主导的培养模式。美国在1970年举行的超2000万人参与的社会性游行环保运动无论在集会的规模、大众参与度方面,还是对提升公民生态意识水平,以及对世界环境历史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这场运动极大地发挥了公民广泛参与生态的力量,引发了公民生态观念的变革,提高了公民的生态意识水平。显然,这种培育公民生态意识的途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目前,中国公民生态意识较弱,缺少生态自觉性。因此,亟须培育中国公民主动承担相应环保事务的生态意识。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统筹规划,成立专门的培育机构,并给予更多经济上的支持。中国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暂时离不开政府的引领,随着生态意识培育的普及和公民认识水平的增强,公民会逐渐养成自觉的生态意识,全民环保时代即将来临。
依托社区组织的培育力量。国外公民生态意识水平较高的根源不仅在于有自下而上的生态教育机制和生态实践,而且还在于社会中各种民间组织的自发性引领示范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发达国家社区组织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领域的教育作用日益显著。英国较早实行了居民自治,让居民自己做主人,像爱护自己家园一样爱护环境。这种自治的社区组织汇集众多民众,融合众多教育功能于一体,熏陶并增强了公民很强的环境意识,营造了全员参与、全民自觉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相比之下,中国社区组织机构仅在起步阶段,还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不尽完善,开展生态活动也只是政府行为,目的性太强,并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新时期,社区组织可以在政府的行政指导下,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社区组织要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和业务素质,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生态意识、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基层组织,在和公民直接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资本优势,对进一步普及和提升中国公民的生态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推行德法共治的教育手段。新加坡享有“花园城市”的美誉,一方面源于政府对于环保事务的高度重视与管理,另一方面源于公民深入内心的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国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也要学习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推行德法共治的生态意识培育方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性,革除生态领域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机制、体制,树立公民生态法制意识,使公民生态意识培育逐步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同时,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营造良好的生态意识培育环境,使公民循序渐进地确立生态法制观念,提升公民生态人格与素质,自觉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生态行为的示范者,培养和造就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态公民。
(二)转变公民原有生态观念,提升公民生态意识教育水平
目前,中国生态意识教育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教育规模小、体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影响力较小、教育水平低。新阶段,公民生态意识教育需要在教育内容、方式、主体和对象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是丰富生态意识教育内容。目前,中国生态意识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生态环境方面的科普知识的普及和教育,这有助于为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提供基础知识,有利于提高公民生态认知水平。新时期,公民生态意识教育要不断融入新的内容,加强对公民生态国情、生态法制、生态旅游、生态消费等内容的教育。生态国情教育,即对公民进行关于中国生态环境现状与问题的宣传与教育;生态法制教育,是使公民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生态消费教育就是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节约资源,科学消费;生态旅游教育就是对旅游者进行生态旅游常识的灌输,有的放矢地引导旅游者的生态价值观念和旅游行为方式,降低旅游者不必要的个人需求和消费,唤醒旅游者强烈的生态意识,使游客成为理性而又富有情怀的生态旅游者。
二是完善生态意识教育方式。目前,中国公民生态意识教育的方式主要有学校课程教育、媒体宣传和人员培训等。新时期,应创新生态意识教育方式,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显性教育是利用公开的宣传、教育手段,通过集体授课、培训和开展专题研讨活动等形式向教育者灌输和宣传生态教育的内容,进而提高其生态意识水平。隐性教育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或一个场景、一个故事潜移默化地把良好的生态意识融入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习惯中,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践行生态保护理念。讲文明、爱环境、少消耗,使公民切实理解和懂得生态环境对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显性主题教育和隐性生活渗透相结合,使公民生态意识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增强中国公民生态意识的有效教育方式。
三是扩展生态意识教育的主体和对象。目前,中国公民生态意识教育的主体相对单一,主要是由学校来承担。为此,应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大众传媒等一切资源和力量。在这里,政府能够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保障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大众媒体能够发挥信息平台作用,使生态教育普及范围加大;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生态素养,实现绿色生产和循环经济模式;民间组织要善于沟通,使教育活动落到实处。同时,要不断扩大生态意识教育对象。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过程教育,每一阶段每一个人都经历生态意识教育。
(三)加强政府正面引导,培育公民参与生态实践能力
提高公民生态意识教育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公民生态意识有所转变和增强,然而,公民生态意识的塑造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教育层面,它还是一个实践问题,急需公民在参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生态实践中养成。新时期,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视域下提升公民的生态意识,政府应增强对公民的正面引导与培育。
一是提升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意识。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受传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公民生态知识还很匮乏,生态观念比较狭隘,对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往往存在依附、顺从、消极和被动等心理,导致有些公民在参与生态实践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不敢参与或无所适从的心态,这大大阻碍了公民生态实践行为,使生态环境治理活动受到影响。因此,新形势下,政府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利用网络宣传生态环保的典型事迹,设立网络论坛,进行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和环保知识竞赛等,从而加强网民之间的互动。政府要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权益,鼓励公民谏言献策,并广泛征求民众意见,支持公民生态实践行为。
二是激发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热情。作为人数众多但权益处于相对弱势的治理主体,会因为种种原因使得个人生态利益受到损害,进而削减了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热情,也就无法实现公共生态利益的实现。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公民首先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努力,这间接促进了全社会的生态利益,而这种公共的生态利益最终也会满足公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还原为公民的个人利益。因此,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现的当务之急。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既要确保公共生态利益,又要保障公民个人的生态利益。从公民的层面说,公民要合理表达个人利益的诉求,增进对公共生态利益的认同,公民的个人利益需求得到表达和满足,拥用话语权和主人翁地位,就会更加关注和支持生态治理工作。因此,政府的支持和协调,将会激励广大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是转换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形式。“个人的自我目的不可能自我实现,而必须在与他人追求共同的理想中才能实现。”[5]在缺乏政策保障和整体计划的前提下,更会与其他治理主体产生分歧和消耗,影响公民参与生态实践的热情。真正有效的公民参与生态实践应该是以有组织有秩序的民间团体方式出现,才能发挥实际作用,产生预期效果。尽管这些年中国环保组织发展很快,但因其缺少组织性和行动力,社会影响力还比较弱。新阶段,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扶植政策,支持环保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和社区机构等民间环保机构,在资金、组织、权益各个方面,保证环保组织的独立性、民间性、组织性和志愿性,帮助他们采用多种方式投入到生态保护工作中。
(四)更新政府生态治理理念,推进生态相关制度全面建设
制度能使公民、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刚性制度约束下进行理性的行为选择。公民的生态意识不仅需要理论教育和实践培养,更需要政府支持和重视。
一是建立利益协调制度。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建立利益协调制度首要的就是协调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各方面利益就是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通过建立利益协调制度,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合理化解矛盾,公正分配利益。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从制度上保证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协调,促使社会公共生态利益效益最大化。正确处理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政府就必须置身利益之外,只做引导和协调,只做管理和服务,行政上不干预,利益面前不伸手。
二是实行社会协同制度。社会协同制度是指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平台,推动落实各项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从而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新时期,为了促进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广泛协同,政府要树立多元共治理念,综合运用行政管理、道德约束以及法治手段,改变传统的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引导社会主体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并通过健全社会组织投入体制,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力量,营造志愿性、公益性服务力量发展的健康环境。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与其他主体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协同关系,使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各主体成为真正的践行者,保证生态环境治理取得良好效果。
三是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责任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生活的自然环境予以珍惜和保护的应尽职责,也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维护生态环境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使命。生态责任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态问题及其治理的一种态度和考量。在现实生态环境治理中,各治理主体表现出失职、失责、消极冷漠等现象,致使中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工作进展缓慢。为此,必须利用各种制度和教育手段增强各治理主体的生态责任感,进而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政府应切实落实好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客观公正地对各治理主体的失职、失责行为,实施责任追究。政府可以采用责任倒追、量化考核、主体负责人问责制等方式,科学合理地落实生态责任,使生态责任成为公民自觉的生态价值理念。自然赋予了人们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赋予了人们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的责任和使命。当我们履行生态责任的时候,确实要付出不少努力和代价,但同时我们也收获了自然的回报。因此,各治理主体落实好各自的生态责任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任务。
[1]俞可平.重构社会秩序走向官民共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4):91.
[2]方世南.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J].政治学研究,2005,(2):41.
[3]包庆德.论生态存在与生态意识[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0.
[4][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7.
[5][美]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ZOU Qing-hua
(College of Marxism,Jiamusi University,Jiamusi 154007,China)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omplicated.Both the system and the integrity should be considered,and the complexity and loca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well.The necessary participation by a number of the main duties is greatly needed to form a joint force.Synergetic theory provides a new way to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ur country.Citizens occupy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The 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level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our country'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economic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must be realized.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ivation system of the 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We must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dvanced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o broaden the vis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to transform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concept of citizens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positive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ecological practice capacity,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environment;cooperative management;citizens;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82-058
A
1009-1971(2016)05-0115-06
[责任编辑:王 春]
2016-07-05
2015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际认同研究”(2015M571431);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策研究”(LBH-Z14128);佳木斯大学2016年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梦’视阈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2016JW2017)
邹庆华(1977—),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意识形态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