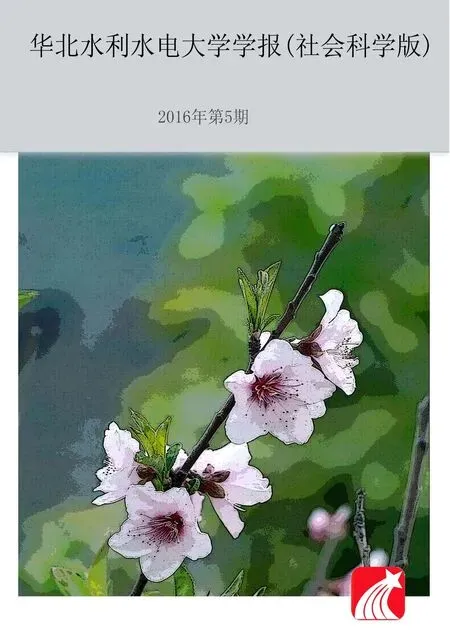游仙题材之汉乐府论略
2016-03-06杜涵
杜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游仙题材之汉乐府论略
杜涵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游仙题材的汉乐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初至武帝时以贵族乐府为主,其游仙题材的表现主要同祭祀相联系,语言古奥典雅,是武帝大一统的君权与渴望升仙的愿望的集中表现。游仙题材的民间乐府绵延两汉,通过对“列仙之趣”的描述表达普通民众的一种超越生死、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状态。而文人乐府游仙诗重在寄寓,往往借游仙以抒怀,成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寻求济世理想破灭后的心灵慰藉的方式。
汉乐府;游仙;贵族乐府;民间乐府;文人乐府
游仙诗在魏晋时期盛极一时,成为一个重要的诗歌主题。虽然第一首明确以“游仙”为名的诗歌当属曹植的《游仙诗》,然而早在汉乐府中已有部分诗歌具有明显的游仙意识。这些诗主要存在于贵族乐府的《郊祀歌》《铙歌》以及众多民间乐府诗当中。《郊祀歌》虽为祭祀诗,但其中如《练时日》《日出入》《天门》《华晔晔》等篇章,主要描写汉代帝王对升仙的希冀和神光降临的经历,具有明显的游仙色彩。而民间乐府如《王子乔》《长歌行》《董逃行》《善哉行》《陇西行》和《古艳歌》等篇章则描写羽化成仙的经历和仙界的美好,颇具游仙意味,为魏晋时期游仙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将汉代乐府诗分为三类:“曰贵族,曰民间,曰文人。是三类者,亦可视为汉乐府之三个时期。自汉初迄武帝,为贵族乐府时期。自武帝迄东汉中叶,为民间乐府时期。自东汉中叶迄建安,为文人乐府时期。”[1]34从贵族到民间再到文人乐府,其中多有游仙长生主题之表达。贵族乐府多为皇帝、近臣、贵族的祭祀、宴飨之作,主要包括汉初三大乐章,即《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与《铙歌》。“是三歌者,性质虽同,而施用则别。《安世房中歌》用之祖庙,《郊祀歌》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铙歌》则凡朝会宴飨,道路从行,及赏赐功臣皆用之。”[1]34其中,《郊祀歌》与《铙歌》中的部分篇章带有浓郁的游仙色彩。
一、游仙题材之贵族乐府
《郊祀歌》十九章是帝王的祭祀歌曲,用以祭祀天地。《史记·乐书》云:“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2]1177-1178可见,《郊祀歌》是由汉武帝主持并亲自参与了部分篇章的创作。《郊祀歌》虽用以祀天神及祖庙,然而却不同于前代之祭祀歌,其中多首诗歌旨在娱神及表达逃离现世、与仙人同归的愿望。其中,第一章《练时日》是迎神曲,接下来的五章《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祭中、东、南、西、北五帝之五神,其后的《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则咏太一、天地与日神,而后几首《天马》《天门》《景星》《齐房》《后皇》《华晔晔》《五神》《朝陇首》《象载瑜》则分咏祥瑞,最后一章《赤蛟》是送神曲。值得注意的是,《郊祀歌》十九章有相当一部分篇章带有明显的升仙色彩,如《练时日》写神灵莅临与作者交接的喜悦;《日出入》表达作者渴望成仙、成龙上天的愿望;《天门》写天门敞开,作者求仙之历程;《华晔晔》则是对神光积坛之描绘,均颇具游仙意味。《宋书·乐志》亦云:“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光,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己。商周《雅》《颂》之体阙焉。”[3]550可以说,《郊祀歌》在继承《诗经》之《雅》《颂》传统之外,进一步加入了娱神的因素,借此表达汉武帝渴望升仙的愿望。
《铙歌》十八曲之《上陵》一曲“大略言神仙事”。逯钦立先生按:“《古今乐录》所疑非也,此上陵与本文山林,殆皆上林之误。”[4]158可见上陵即上林苑,是汉代帝王著名的游猎之苑。较之《郊祀歌》之古奥佶屈,此诗颇有“句格峥蝾、兴象标拔”之誉[5]7,描写了神仙下界之奇景,并表达了诗人希望神仙赐予甘露,饮后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诗的写法同《郊祀歌》中的《天门》《华晔晔》颇为相似,无外乎咏叹祥瑞仙迹而已,当同属贵族乐府。
二、游仙题材之民间乐府
与艰涩古雅的贵族乐府相对应的是民间乐府。由于汉代帝王对仙道的狂热追求,民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方士群体。在他们的鼓吹和附会下,神仙思想与神仙故事在民间也影响广泛,由此出现了一批描写“升仙”经历的民间乐府诗,多为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如《王子乔》《长歌行》《董逃行》《陇西行》及《艳歌》等。同是写升仙,民间乐府与贵族乐府在描写对象、升仙途径及诗人态度等方面都大有异趣。
首先,描写对象不同。贵族乐府的《郊祀歌》可谓礼神之曲,而升仙主题的民间乐府则重在描写“列仙之趣”。世俗上虽常常“神仙”合称,然而“神”与“仙”却各有渊源。《说文解字》将“神”释为:“天神,引出万物者也。”[6]3指出了神创造万物的主宰性。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和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相关。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等诸神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作为郊庙祭祀乐章,《郊祀歌》通过娱神,“合好交欢虞太一”[4]150,达到获得神力、人神共乐的目的。然而这种奢华、庄严、神秘的祭祀乐歌与乐舞仅能帝王享有,向太一主神与五帝求得长生似乎只能是帝王贵族的专利,而民间则将升仙不死的希望寄托在王子乔等散仙身上。相比之下,民间乐府游仙诗中的神仙则显得更加亲切近人。如《王子乔》中对王子乔的描写:“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来游,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成仙的王子乔超越生死,潇洒自由,同庄子所描述的得道的神人(至人、真人)颇为相似:“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7]186“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7]90可见,仙的文化意蕴同道家对“道”的颂赞紧密相连。与《郊祀歌》中庄严崇高的神不同,民间乐府中的仙与其说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不如说已成为人们渴望的一种完满飘逸的人生状态。
其次,升仙途径不同。贵族乐府的《郊祀歌》为祭祀乐章,无论是咏诸神还是赞祥瑞,其目的都在于感念神恩,希望得到诸神的保佑与赐福。在《练时日》《天门》《华晔晔》等篇章中,诗人用华丽的语言淋漓尽致地铺叙了神灵降临的全过程,其中渗透着明显的宗教般的虔诚与狂热。钱志熙对郊祀的场面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郊祀乐’中,除了一个规模甚大的‘合唱队’和一个规模与之相类的‘舞队’外,还有扮演神灵的巫倡……纵使没有直接出现‘灵’的扮演者,也应该有引导想象中的‘灵’的巫祝。他以种种悬拟的动作将‘灵’带到人间,并通过这种悬拟动作告诉人们‘灵’的每一个行动,从而引起祭神者、‘合唱队’、‘舞队’以及布置牺牲的人员。总之是一切在场之人带着某种狂热情绪,沉浸在神秘的体验之中。”[8]54在如此虔诚狂热的娱神过程中,诗人委婉地表达了祈神赐福、引领升仙的愿望:“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4]150
在《郊祀歌》十九章中,《天马》可谓最直抒胸臆表达武帝升仙梦想的一章,共有两首。《汉书·武帝记》曰:“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4]150歌曰:“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蹑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4]150“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歌曰:天马徕,从四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4]150渥洼马和大宛马神骏异常,在诗中被作者幻化为天马,成为引领武帝逝昆仑、登天门、观玉台的坐骑,武帝羽化登仙的渴望在天马身上得到了表达与寄托。
无法奢望祈求太一主神与五帝为导引或求得天马为坐骑登临仙界,民间将升仙的希望寄托于服食仙药。在《长歌行》中,诗人生动逼真地讲述了自己获取仙药的经历:“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4]262
在《善哉行》中,同样有关于仙人赠药的情节:“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4]266世俗心理无法仅仅满足于民间乐府游仙诗对“列仙之趣”的描述,诗人必将寻找一个使仙与人发生联系的情节,这个情节即为仙人赠药,服之使人延年益寿,长生不死。这同当时整个社会流传的升仙长生的民间传说紧密相关。《列仙传》中所载山图遇仙人赠药的故事或可视为其时人们慕仙心态的代表:“山图者,陇西人也。少好乘马,马踢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服之一岁,而不嗜食,病愈身轻,追道士问之,自言五岳使,之名山采药,能随客,使汝不死。山图追随之六十余年,一旦归来,行母服于家间。期年复去,莫知所之。”[9]127在汉人对升仙长生的祈望中,自然而然出现了民间乐府以亦庄亦谐的形式对遇仙求药故事的表达。
第三,诗人对升仙的态度不同。属贵族乐府的《郊祀歌》本是祭祀乐章,其庄重古雅的言辞与太一诸神等描写对象无不营造出一种庄严神秘的气氛。由于武帝本人是《郊祀歌》的组织者和创作者,十九章除了表达武帝祈神赐福、引领升仙的愿望外,还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帝王君临天下的意气和社会强盛繁荣的风貌。在强盛帝国的祭祀典礼中,诗人对诸神的赞颂充满了虔诚与狂热。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武帝在亲自祭祀甘泉圜丘时,“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10]1045此记载可谓《华晔晔》一章之脚注,武帝亲自参与了迎神接神的活动,其庄重虔诚可想而知。
同古奥典雅的《郊祀歌》相对,升仙主题的民间乐府语言则显得直白通俗。一些套语轻松诙谐,为诗篇增添了不少幽默色彩:“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4]289“今日乐上乐”虽为乐府古艳歌的套语,然而用在此处则颇具戏剧色彩,作者似乎兴高采烈地说:“今儿个真高兴,一起去天上逛了一圈。”由此可见,神仙的仙宫对普通民众来说并非如《郊祀歌》中需乘天马腾云驾雾般遥不可及,而是就在人境之中,或设在五岳之巅:“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4]264,或就在太山之隅:“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4]267。而天宫神仙们的生活无非是世俗生活的折射。住的是金銮宝殿:“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4]264还有美女歌舞升平:“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级。鸣吐衔福翔殿侧。”[4]261或是美酒佳肴,众人侍奉:“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芋。姮娥垂明珰,织女奉瑛琚。”[4]289诗中描述的神仙生活正是王侯贵族宴飨场面的变形,只不过侍奉的仆从舞女变为了青龙白虎、嫦娥织女。可见,升仙主题的民间乐府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少了贵族乐府的宗教般狂热与虔诚,却带有浓郁的世俗性和娱乐性,是世俗生活的变形与延伸。
三、游仙题材之文人乐府
汉代文人乐府的创作与此时期的文人心态密切相关。在政治上,随着西汉大一统王权的建立,文人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才华,“修齐治平”成为士人人生的目标和追求,文人们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来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定,希望通过维护清明政治为国“立德”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思想上,儒家的入世思想成为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由此确立的君臣观念也在对六经的倡导中深入人心,文人们在这个价值体系中怀抱着对圣主明君的希冀和忠诚。在经济上,随着大一统王权的建立,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国力强盛,疆域日渐开拓,四夷来服,汉代臣民心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大汉雄风的气度随处可见。以上三点形成了汉代文人心态的主流,即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治国济世的愿望。而与此同时,在文人匡政济世的思想洪流之中,还涌动着另一股暗流,即士不遇之悲。同前者一样,文人们对自身的“不遇之叹”同样贯穿于整个汉代,究其原因,或可归为以下三方面:首先,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必将削弱群臣及辅政文人的权力,造成君权与臣权的对立。其次,将高昂的匡政济世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同君主“遇”与“不遇”的机缘中,必将使大批文人“济世”的希望化为“不遇”的失望,由此产生了汉代众多感士不遇的文学作品。再次,乱世中的高压政治极大地打压了文人的济世之志,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其政治热情濒于熄灭,为了个体生命的保存及精神上的慰藉,文人们转而投向道家思想,以其超逸的人生状态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作为安顿生命的港湾。这一点在东汉中后期表现尤为明显,在外戚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党锢之祸中,文人们带着破碎的政治理想投入到道家的山林梦想之中。
王允亮从汉代“七”体与“设论”两种典型文体交映的现象中同样发现了汉代文人思想的双重性与矛盾性,即以“七”体为代表的招隐思想和以“设论”为代表的遁世思想[11]。在儒家的济世与道家的遁世思想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升仙题材的文人乐府诗形成了其独特的寄寓性特点。
《淮南王》传为淮南小山所作,崔豹《古今注·音乐》曰:“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方士相携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4]276全诗如下:“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渡河河无梁,愿化双黄鹄还故乡。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里,苦身不已。繁舞寄声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4]276全诗渗透着浓郁的苦闷和超离现实的渴望。与其说此诗是淮南小山之徒思慕升仙归去的淮南王,不如说是其借咏淮南王升仙之事以抒怀。当理想在现实中受挫,“我欲渡河河无梁”“徘徊故里,苦身不已”,诗人将希望寄托于飘渺的天外世界:“愿化双黄鹄还故乡”“徘徊桑梓游天外”。由此可见,西汉文人在现实政治中壮志难酬,于是转向道家黄老学说,游仙成为其抒怀之途径。淮南小山的另一影响深远的楚辞体作品《招隐士》,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其释为淮南小山悯伤屈原之作:“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12]232而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13]165考其文意,后者之解释似更符合实情,在招隐的同时又显然含有对屈原逝江的悯伤和对其名德显闻的倾慕。一言以蔽之,即文人对立身显德扬名之志的表达,同汉乐府《淮南王篇》的遁世之愿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也正是汉代文人济世与遁世双重复杂心态的集中反映。
《善哉行》为汉乐府瑟调曲,《曹子建集》第六卷亦收此诗前四解,然逯钦立先生认为此诗非子建之作:“子建拟善哉行为日苦短云当来日大难。”[4]26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全诗六解如下:“来日大难,口燥舌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辙,以报赵宣(三解)。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4]266。从全诗来看,诗人面对疾苦的社会现实,徘徊于宴饮酒歌与服药求仙的选择之间,是生命意识觉醒之后充满矛盾的生命态度的体现。面对“来日大难”,诗人先是放情游乐,而后又名山求仙,在得仙人赠药、即将升仙时又忽然忆及亲人旧故在世间的疾苦:“饥不及餐”,于是又转而回到了“弹筝酒歌”的纵情享乐中,与此同时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升仙的企慕,希望能如淮南八公,“参驾六龙,游戏云端”。钟嵘在《诗品》中称郭璞之游仙诗“非列仙之趣也”[14]12。从内容上看,《善哉行》亦已超离了贵族乐府与民间乐府对“列仙之趣”的描写,而是借游仙以“坎壈咏怀”,即使不是子建所作,也应出自东汉末年的落魄文人之手,同魏晋时期的游仙诗主旨更为接近。
借游仙以咏怀是文人乐府游仙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仲长统的《见志诗》中则更为明显。且举《见志诗》其一为例:“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4]204-205
全诗充满了对庄子“至人”的企慕与赞美,描述了一种仙人般超脱悠游的理想生活,表达了鄙弃人世、超然世外的愿望。然而,仲长统作为汉末建安名士,此超然旷达之论也仅是在乱世中的寄寓而已,是其建功立业、匡政济世的理想破灭后的无奈选择。
四、结语
由上可见,游仙题材的汉乐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初至武帝时以贵族乐府为主,其游仙题材的表现主要同祭祀相联系,语言古奥典雅,是武帝大一统的君权与渴望升仙的愿望的集中表现。游仙题材的民间乐府绵延两汉,通过对“列仙之趣”的描述表达着普通民众的一种超越生死、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状态。而文人乐府游仙诗重在寄寓,往往借游仙以抒怀,成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寻求济世理想破灭后的心灵慰藉的方式。
[1]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9]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王允亮.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J].河南社会科学,2010(7):166-168.
[12]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4]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王菊芹)
An Analysis of Poetry about Immortals in Han Yue Fu
DU H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Poetry about immortals in Han Yue Fu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Han dynasty to Emperor Wu Period, aristocrat poetry, whose theme is connected with fete, takes the dominant role. It reflects the emperor Wu’s desire for unification and immortalization. Folk poetry is prevalent during the whole Han dynasty. By depicting the immortal world, it expresses ordinary people’s wish to lave a luxuriously life before and after death. By contrast, the intellectual poetry conveys the disillusion and depression against reality, providing a way for them to search comfort in the immortal world.
Han Yue Fu; immortalization; aristocrat poetry; folk poetry; intellectual poetry
2016-04-21
杜涵(1981—),女,河南郑州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
I207.2
A
1008—4444(2016)05—01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