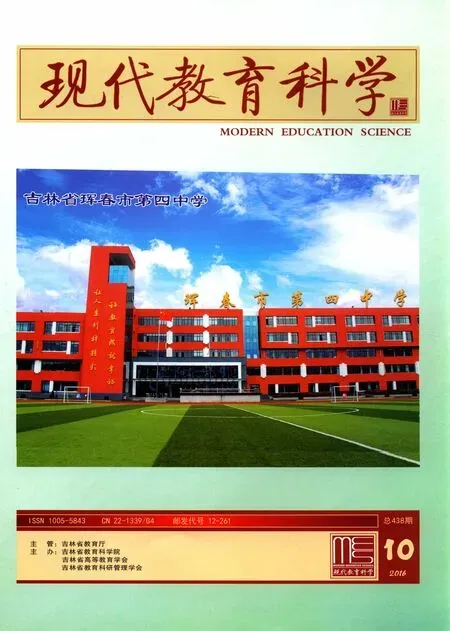多元论与外语教育: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及其超越
2016-03-04郝成淼
郝成淼
(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多元论与外语教育: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及其超越
郝成淼
(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现行的外语课程政策采纳了“二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认为外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这突破了长久以来“一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即认为外语是工具性课程。然而,“人文导向”与“工具导向”的实践“纠结”使现行外语课程政策陷入了困境。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全球公民身份教育”的过程中,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适逢外语高考改革,学界近年来引入“多元论”来研究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提出了“多元目标英语课程”等理念,外语课程性质观正经历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的新突破。
外语教育 外语课程政策 外语课程性质 多元论 “一带一路”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10.021
一、外语课程政策与外语课程性质
“课程政策的目的在于解决特定的课程问题。唯有在教育场域中有效地实施,转化为教育工作者的实际行动,才算是实实在在的”[1]。外语课程政策作为直接指导教学实践的外语教育政策,其核心政策文件是外语课程标准(或称教学大纲、教学要求)。迄今,我国没有整体性的外语课程政策,而是分语种、分教育阶段进行制定,但基本上都包含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等组成部分。纵观我国既有外语课程政策文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不同语种、不同教育阶段的外语课程政策文件均开始对“课程性质”进行明确阐述,“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成为共同措辞,改变了20世纪长期采用的隐性表达方式。
这是学界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围绕“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外语课程性质论争在外语课程政策文件中的反映,凸显出外语课程性质已经成为外语课程政策文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然而,现行外语课程政策实施10多年来,“人文导向”与“工具导向”之间的抉择与平衡成为外语课程实践中的“纠结”[2],世纪之交所定的显著提高外语教育质量的预期目标未能很好地实现,“外语降温论”反而在近些年变得再度热烈,我国外语课程政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器”、“变”、“通”所揭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理对于破解当前我国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颇有启发。课程性质对外语课程政策而言堪为“道”,课程目标、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等则为“器”;“道”若不达,“器”复何用?重新审视外语课程性质问题,以求裁“变”而行“通”,对外语课程政策极具现实意义。
二、外语课程政策的现实困境
(一)“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交锋与妥协
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并不囿于外语语言技能教学的内部层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必然要面对战略性、规划性以及价值抉择等变革趋势[3]。从建国至20世纪末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语一直被视为一种工具,外语课程相应地被视为工具课程,“工具性”主宰了这一时期外语课程政策的课程性质观。在这一时期的外语课程政策文件中,“课程性质”虽没有明确表述出来,但“工具”一词贯穿始终。其修饰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交流、斗争工具”逐渐调整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习、交往工具”,映照出外语教育价值理念的巨大变化。
“外语教育的性质问题很需要研究和讨论”[4]。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工具性”外语课程性质观遭遇了“人文性”外语课程性质观的强烈质疑与批评,提出外语教育不是工具性训练,而是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经过“人文性”与“工具性”这两种“一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的交锋和妥协,催生了“二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即提出外语教育“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这被我国最近10余年来所有教育阶段的外语课程政策文件所采纳,成为当前主导性的外语课程性质观。但是,“工具性”与“人文性”在外语课程政策文件中的“牵手言和”并不能平息学界的歧见。
(二)“外语降温论”背后的社会无意识
“社会无意识”是随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概念,指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那些被压抑的因素。“对集体记忆做进一步分析,有可能触及记忆者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社会无意识,被压抑的各种意念会以种种曲折的形式呈现出来”[5]。自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是在国人对外语地位的争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外语热”长期属于人们或追捧或挞伐的内容。探索社会群体有关外语教育的集体记忆,对近些年“外语降温论”背后的社会无意识进行分析,有助于化解当前的争议,明确发展方向。
外语跟母语的掌握路径存在很大差别。母语主要经历的是习得过程,即在自然交际中逐渐掌握;而外语主要经历的是学习过程,即需要有意识的人为介入才能逐渐掌握。鉴于外语学习的难度系数明显高于母语习得,“外语考试与培训热”作为“外语热”的异化形态呈现于世,“劳民” 、“伤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群体有关外语教育的集体记忆。再加上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外语教育会影响学校教育、造成学能浪费、冲击母语文化等批判更是将其引至“误国”的社会观感之下。近些年,“外语降温论”背后的社会无意识正是社会群体对外语教育“劳民”、“伤财”、“误国”的扭曲记忆。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背景下,合作与共赢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潮流,外语教育在各国均受到特别重视,“外语热”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现象。事实上,对于提升国际化水平、促进文化多元性、推动学科建设、创造经济价值、助力个人发展等方面来说,外语教育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在近40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从语言角度来看,对外开放的语言文化甚至社会心理基础系源于改革开放开始之前百余年的外语教育及中外交流;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流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是受益于外语教育的相应提升,另一方面又为外语教育提供了不竭的现实需求”[6]。所以,对“外语降温论”背后的社会无意识进行因势利导非常具有迫切性。
三、外语教育的“多元论”新视野
(一)我国外语教育的新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面临施教规模巨大但高级专业人才依旧匮乏的尴尬局面[7]。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水平正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迈进,外语教育必须顺势而为地推动转型升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外语教育确定了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统一的战略性目标。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以期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统筹国际、国内语言生态,平衡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开发语言资源,建设外语智库,构筑话语体系等重要课题,为我国外语教育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战略性契机。正如学界所言,“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8]。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八年发展战略规划(2014—2021年)》中将“培养有创造力、有责任感的全球公民”作为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提出“学会共存”是任何教育体系的关键支柱,倡导致力于包括全球公民身份教育(GCE)、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和健康教育(HE)三大主题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是,“全球公民身份教育”在世界多样性环境中已被视为教育得以通过开发学习者知识、技能、观念与态度而达至建构更加公正、和平、宽容和包纳的社会的一个框架范式[9]。毫无疑问,在推进“全球公民身份教育”的过程中,强而有效的外语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要素。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同其成员国及合作伙伴所推进的“全球公民身份教育”也充实了我国外语教育转型和升级的学理基础。
(二)多元论对外语课程政策困境的超越
鉴于外语课程政策所采纳的“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外语课程性质观造成了外语课程实践中“人文导向”与“工具导向”之间的“纠结”,人们逐渐开始寻求突破“二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以破解现行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这主要包括两种思潮:一种是回归“一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提出尽管当前外语教育已强调人文性,但外语作为工具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化。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具有外语能力,外语对人的素质锻造作用远不及母语。有学者主张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数学为大众”理念,推崇“外语为大众”,即人人学有用的外语,人人掌握外语,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外语[10]。但是,回归非此即彼的“一元论”又恐使外语课程性质观陷入“人文性”与“工具性”无休止的交锋之中。
另一种思潮是推出“多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多元论”可谓历久弥新,在现代,主要强调尊重社会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近年来,学界开始引入“多元论”来研究我国外语教育定位、实施原则等政策问题[11]。龚亚夫指出,语言课程是以一系列社会与政治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必须重新思考我国英语教育定位,全面认识其核心价值,化解“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理念流于口号的问题,主张重新构建我国英语教育目标和能力模型,提出包含社会文化目标、认知思维目标、语言交流目标等内容及其具体描述的“多元目标英语课程”概念[12]。“多元目标英语课程”对英语教育核心价值的探寻已经远远超出课程目标的范畴,而是对我国英语教育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人的发展等方面关系的重新建构,彰显了外语课程实施中社会、人、语言之间多维度的交互关系,从根本上指向了外语课程性质问题,超越了“二元论”的外语课程性质观。
四、余论
基于培养大批“国际化人才”的战略性目标,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全球公民身份教育”的过程中,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彰显。外语课程性质作为外语课程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已然成为外语教育研究中的显性课题。当前,外语高考改革作为社会广泛关切、亟待凝聚共识的问题,被列为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更新外语课程性质观、促进外语教育政策系统改革的重要契机。
然而,囿于现行外语课程政策的困境,对于外语高考改革这一重大的外语教育政策改革举措,外语界却如束定芳所言,几乎“集体失语”[13]。语言政策规划(LPP)理论认为,通过系统性的作为,可以形塑社会各界有关语言的法规、观念及实践,最终实现预期的语言变化。如今,我国外语课程性质观在经历从“一元论”到“二元论”的第一次突破之后,正在经历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的第二次突破,努力寻求从顶层设计上提出外语教育改革思路[14],这非常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1]肖磊.论课程政策的象征效用[J].上海教育科研,2015 (10):33-36.
[2] 谭业升.中国外语教育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记“第三届中国外语战略与外语教学改革高层论坛”[J].外国语,2015 (1):107-112.
[3] 沈骑,夏天.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变革[J].教育评论,2014 (1):45-47.
[4] 杨自俭.关于外语教育的几个问题[J].中国外语,2004 (1):14-16.
[5] 程寅,黄锦章.网络造句背后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无意识[J].当代修辞学,2011 (6):1-11.
[6] 郝成淼.给“外语热”降温?——从外语教育政策角度理性思考当前争议[J].语言教育,2014 (2):8-13,25.
[7] 胡壮麟.对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几点认识[J].外语教学,2015 (1):52-55.
[8]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人民日报,2015-09-22(7).
[9] UNESCO. Education Strategy (2014-2021)[EB/OL].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12/231288e.pdf, 2014.
[10] 刘尧.外语教育改革:“外语为大众”[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08(3).
[11] 许瑾.语言多元论视角下的国际化人才外语素养[J].江苏高教,2011 (5):95-96.
[12] 龚亚夫.论基础英语教育的多元目标——探寻英语教育的核心价值[J].课程·教材·教法,2012 (11):26-34.
[13] 束定芳.外语高考改革新攻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1):56-60.
[14] 龚亚夫.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基础英语教育的改革[J].外国语,2014 (6):18-19.
(责任编辑:申寅子)
Pluralism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Policies
HAO Chengmiao
(SchoolofForeignStudies,SuqianCollege,Suqian,Jiangsu223800,China)
Current curriculum policy adopted the “dualism”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nature view, thought that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combine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m, it broke through the long “monism”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nature view, which holds that foreign language is instrumental course. However, the practical entanglement between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and humanistic orientation actually throws the curriculum policies into a dilemma.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GCE), the significanc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s further highlighted. Coincided with the on-going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in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 plural perspectiv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FLEP) in China, and the coming-up of new concepts like “Multi-goal English Curriculum” is witnessing another breakthrough, from the dualistic perception to a plural percep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policy;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nature; pluralis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6-05-29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15年度项目“‘一带一路’与‘建设新江苏’背景下的外语政策规划研究”(2015SJD812);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立德树人与英语教育——英语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再研究”(NAFLE0114004);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文号:苏教师〔2016〕15号;培养对象:郝成淼);宿迁学院“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文号:宿院人〔2015〕10号;培养对象:郝成淼) 。
郝成淼(1981- ),男,湖北建始人,硕士,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语教育政策、语言文化战略。
G40-011.8
A
1005-5843(2016)10-00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