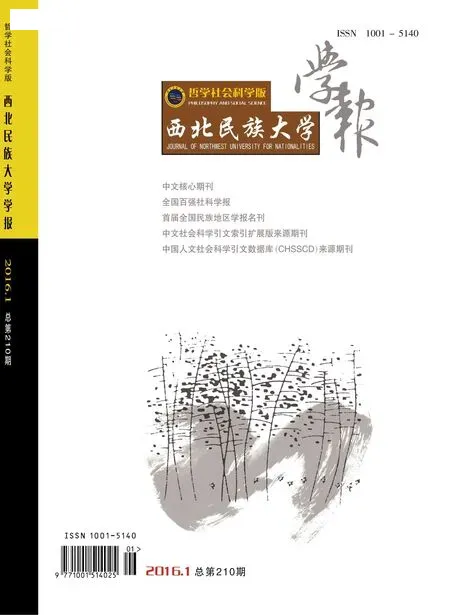中国西部生态移民的时空跨域比较研究——对双海子和黄草川的个案比较研究
2016-03-01饶凤艳张文政
饶凤艳,张文政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中国西部生态移民的时空跨域比较研究——对双海子和黄草川的个案比较研究
饶凤艳,张文政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甘肃省内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与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黄草川村,是两个不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生态移民村,分别经历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探索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同时来自不同的地理空间,有着不同的安置方式。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安置条件和搬迁理念,导致二者存在不同的迁移效果,形成的移民社区存在显著差异。对裕固族占多数的双海子移民村和藏族占多数的黄草川移民村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分析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方略。
[关键词]生态移民安置;时空跨域;民族地区
20世纪60年代左右生态移民概念被正式提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1]。生态移民是一种由于原居住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为了保护其生态环境而引起的一定规模的自愿或非自愿人口迁移[2]。在国内研究中,多以西部为出发点展开生态移民研究,甘肃的生态移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3]。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的移民安置始于1999年,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领导下,肃南县委县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实施异地搬迁工程。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华藏寺镇黄草川村的移民安置始于2012年,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提出,天祝县委政府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城镇集群,实施就地扶贫搬迁工程。年代、地域、政治背景以及搬迁理念的不同,造成了各具特质且有显著差异的移民安置效果。国内已有文献显示对不同时期、地域的生态移民进行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文献集中于一个区域或者一定时期进行研究。本文通过不同时期、地域生态移民情况,比较双海子裕固族为主的村落与黄草川藏族为主的村落生态移民在历史背景、安置方式与适应性状况的不同,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工作提供参考。
文章通过文献和实地研究方法,利用问卷和访谈两种资料收集方式,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对双海子村和黄草川村移民进行访谈并展开问卷调查,同时访谈部分生态移民政府工作管理者,进行印证比较研究。
一、对两个民族地区生态移民的历史背景和安置方式的比较
(一)生态移民历史背景的比较
1.双海子村生态移民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肃南县可利用草原面积不断减少,2009年天然草地可食牧草产量与1980年相比平均下降26.03%,而草原实际载畜量却呈持续上升趋势,草原退化问题严重[4]。20世纪末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带动下,为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和保护祁连山区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张掖市肃南县委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推动生态移民的异地搬迁工程。双海子村隶属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政府,村内60%都是裕固族村民,汉族和藏族居民占35%,其他民族居民占5%。现双海子村居住113户居民约400人,大多是由当初十几村落组织聚集而成,在移民之前都从事着畜牧业生产。
2.黄草川村生态移民的历史背景
刘学敏、陈静认为,生态移民不仅有改善生态系统的目的,还有城镇化的作用和性质[5]。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随后《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新农村建设应注重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全国各地针对所辖属的乡镇村庄,纷纷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展开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概念迸发萌生,2007年张荣寰学者首次阐释之,他主张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通过人权生活化、新型城镇化、产业自优化三方面动能转型。2012年,武威市天祝县委政府应承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落实“生态立市”和“生态立县”战略,加快推进石羊河流域源头生态保护治理步伐,全力推进“下山入川”工程。
3.比较研究
双海子村与黄草川村的生态移民相隔10多年,期间经历了西部大开发时期和新型城镇化探索时期,分别是裕固族和藏族占主要比重的重组生态移民村落,目的皆是为了保护祁连山区自然环境和石羊河流域源头的生态系统,牵扯到十几个村落的村民。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大多是由政府主导型的移民活动,前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比较强烈,而后者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更注重移民活动的“生态功能”。双海子村与黄草川村移民的历史背景和优劣比较(见表1)。
(二)生态移民安置方式的比较
1.双海子村生态移民的安置方式
双海子村生态移民迁移方式以易地搬迁为主,安置方式主要是整体搬迁,集中居住的模式。将原来居住在不同地域社区的十几个村落的农牧民,共同集中安置在一个迁移地。尽量不拆分村落原有的社区居住共同体,新社区仍按照迁移前形成的聚居群体居住,不拆分,不混合。保持原来的社区熟人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秩序。20世纪末的中国西部乡村,经济发展落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双海子村生态移民的移民安置和生存条件低,补偿水平也比较低。房屋补贴由国家一次性发放,每户300元,由村民自建。截至目前,双海子移民房屋220m2,院落30m2。每人补偿5亩耕地,每户平均4口人,每户平均20亩地。草场补贴随经济水平不同,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现在每人每年2 800元[6]。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于耕地种植和家畜蓄养。
2.黄草川村生态移民的安置方式
黄草川村生态移民主要采取就地扶贫搬迁的迁移方式,按照部分搬迁,集中安置的原则,将原来周边十几个村落的牧民,依据“下山入川”方针,将居住在海拔2 800米左右高深山区的10个乡镇的200户924人,以自愿的方式,搬迁至海拔2 400米~2 500米之间。2012年生态移民的安置和生存条件较过去有了部分提高。天祝县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移民搬迁工作的意见》提出,3年内不收回村民原承包的耕地和草原,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过程中涉及的移民原承包地的钱粮补助通过乡镇级别一次性发放,县级通过筹集资金对举家搬迁的移民给予现金补助,补助标准从每人600元~1 000元。为转变牧民生产生活方式,提高牧民适应度,黄草川村着力开发撂荒地3 100亩,用于建设日光温室、发展设施养殖,增加农民收入。现在全村共有360座温室大棚,每户平均2个温室大棚,6个养殖小区正在建设。生态移民点的房屋由政府补贴6.8万,牧民小部分自筹的方式[7]。房屋样式、结构等由政府统一设计建造而成。黄草川生态移民点房屋沿河坐落,共5列。但是房屋坐东朝西走向,违反常规建筑学“坐南朝北”原则,白日不利于天然采光,加之北方漫长的冬季影响,屋内长期较寒冷[8]。黄草川移民基本每户房屋250m2,院落35m2;每户分配2座温棚,每座占地2亩,每户平均4亩地。由国家补贴大部分建筑成本,牧民小部分贷款的方式建造而成。田野调查发现,社区内日光温棚现已有20%坍塌或废弃。移民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日光温室种植与出外打工。

表1 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安置方式及优劣比较
3.比较
二者移民具有相同之处。首先,移民采用自愿的方式,有利于移民工作开展,减少阻力。其次,二者的移民安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效地保持了原有的社区网络结构和社会秩序,保护了原有的聚居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不同社会背景及地域特征下,不同的移民搬迁理念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劣之处。在移民安置点房屋施工和设计方面,双海子村民更具有自主性,移民的主动性和满意感比较强;在经济补偿方面,双海子移民安置房屋补贴低于黄草川,二者草场补贴基本相似;在土地补偿方面,双海子移民高于黄草川。造成这种土地补偿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三方面原因:①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第二次修订,《国家土地管理办法》日趋严格,其中《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不论单位或个人,不允许在确定的土地利用规划区进行土地开发行为。有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必须经过县级以上级别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才能从事种植、畜牧、捕鱼等生产活动。如果未经批准开垦,是违法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由于双海子村移民早于黄草川,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双海子移民私自开垦荒地的情况时有发生。②天祝县“生态立县”理念影响,黄草川移民拓荒受严格限制。③黄草川所在的武威市天祝县人口密度高于双海子所在张掖市肃南县,人均土地占有量低。据2014年甘肃统计年鉴显示,武威市天祝县人均占地面积3.299km2/100人;张掖市肃南县人均占地面积63.33km2/100人。
二、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比较
生态移民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简单转移,还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是一项规模宏大,问题复杂的系统工程。以移民主体出发,承袭上千年的传统风俗习惯发生变化,从牧民到农民、从游牧到农耕、从散居到聚居,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9]。在陌生地域重构下的生产系统、社会组织、社会网络及文化体系给移民带来冲击。面对移民社会适应、迁入地社区凝聚力维持等问题。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帮助移民早日融入新环境,实现移民真正达到社会适应。
本文从微观层面上,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及政策背景下甘肃典型的生态移民村落——双海子村、黄草川村。从经济、文化及移民主体三个方面,分析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和社区整合情况。生态移民生活的指标基本包涵四个方面: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与生产生计方式适应。使用李克特量表测量方法,受访者根据自身的适应情况,根据5个标准在各个指标中选择,从非常不适应到非常适应,以0至5分评分,使用量化表通过标准化的回答分类,来提高本项研究的测量层次,并以此评估不同社会适应指标的强度[10](见表2)。

表2 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社会适应性比较
(一)生态移民对家庭经济影响比较
从双海子到黄草川生态移民,跨越了10年的变迁,正由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阶段转向加速发展阶段。农村移民的生活需求也从“温饱”逐渐转向“小康”。无论任何时期任何政策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真正使生态移民在经济上、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适应新环境。然而,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经济状况,即贫困问题仍然是移民奔小康过程中无法忽视的屏障。
在搬迁过程中,生态移民不仅脱离了原有的物理生态空间,更是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系统,面临着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巨大的差异带来的不适应,导致的是移民收支状况的变化,即牧民经济效益的差异[11]。生产方式的适应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生产生活的不适应可能带来移民回迁,对我国生态移民工作带来了困难。本文将“贫困问题”化解为生态移民活动包括移民方式和生产方式变迁对家庭经济影响问题展开探讨,并分析二者的差异及原因。
1.移民对经济补偿认同度的比较
生态移民是为了保护迁出地生态环境,促进其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农村移民工程。而这种搬离原有生产体系的生态移民是对移民原有生态权利,或者说是生存权利的剥夺或转移。所以这是对生态移民的一种公益征收,政策制定者应当对移民给予一定的补偿[12]。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和优化,移民群体的生态权益也不应被损坏。这种移民的经济补偿某种意义上会促进移民恢复迁移前生活收入水平,弥补搬迁过程中生产方式变迁的不适。所获得各种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迁移过程中的缺失,促进移民有效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调查表示,双海子和黄草川生态移民对移民安置模式中的经济补偿状况整体都较为满意。
(1)双海子生态移民对经济补偿认同度
20世纪末的中国西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一致,社会阶层差距普遍较小。虽然双海子村生态移民在最初的移民活动中获得的经济补偿较少,但是移民前后生活水平差异不大。加之后期持续跟进的优惠政策,例如草场补贴的持续上涨等,因此双海子村生态移民满意度高。在土地补偿方面,由于肃南县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土地量较多,双海子村生态移民分配的耕地有效地填充了移民搬迁带来的损失,弥补了移民过程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缺失。
(2)黄草川生态移民对经济补偿的认同度
由于21世纪以来,人民消费及生活水平持续增加,西部移民成本也在不断提升。尤其移民房屋专项补贴方面,由双海子村移民时的300元增加到黄草川移民时的68 000元。但在移民过程中,由于黄草川政府和移民间信息不对称及政府工作上经验不足(在移民安置房屋建造时政府主导性较强,统一设计的房屋考虑不周,采光较差;公共设施利用率不高,例如厕所,未能考虑乡村本土具体情况,不仅利用率不高,而且无人处理情况下垃圾遍地,影响居住环境),导致黄草川移民经济补偿认同度较低。同时,黄草川所在的天祝县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占有量低,黄草川生态移民所配给的耕地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经济补偿认同度。52.7%黄草川生态移民在移民过程中经济补偿认同度差或者非常差(见表3)。

表3 双海子和黄草川生态移民补偿认同度比较(%)
2.移民活动对移民生产与家庭经济影响强度的比较
(1)移民活动对双海子生态移民的生产活动与家庭经济影响强度
从居住环境、生产方式适应及养殖情况来说,双海子移民的生产适应情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受影响程度较低。双海子村全村分为深井子方田、湖边子方田、贺家墩方田、黄土坡方田、上井方田、马蹄方田。前四个方面的人分别从莲花乡的四个村搬迁而来,迁出地与迁入地距离不远,居住环境相差不大;移民在搬迁之前从事游牧生活,移民活动对于牧民的生产方式影响很大。田野调查发现,虽然迁移后双海子村民分配的耕种土地数量较多,但是质量偏低,盐碱度较高。但是通过双海子移民勤劳的耕作和改善,盐碱地逐渐转变为肥沃的土壤。同时移民在迁入地从当地汉族村民邻居学习如何耕地,生产方式适应障碍较少,生产较早恢复;另外,双海子移民虽然不能像过去一样过着游牧生活,但许多牧民带着对土地“过去的记忆”,开始在自家耕地上种植干草(即牧草,其较好打理,费时较少的经济作物[13]),用以饲养牲畜和售卖,不仅增加牧民经济效益,还能为无法继续放牧的牧民圈养牲畜提供饲料,弥补移民心理缺失,形成了农牧业兼顾的民族发展道路。另外,双海子村积极鼓励村民成立农民合作组织,双海子村远近驰名的“双海西瓜”更为移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2)移民活动对黄草川生态移民的生产活动与家庭经济影响强度
从居住环境、生产方式适应及养殖情况看,黄草川移民的生产适应情况较差,家庭经济状况受影响程度较高。武威市政府为改善村民恶劣的居住环境,实施“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黄草川村移民多数由祁连、旦马、毛藏等10个乡镇生活在海拔2 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村民搬迁组成,气候和环境更加适宜居住;但是入川后黄草川移民采用温室大棚的耕作方式,较双海子生产方式变化更大,这种完全差异性的劳作方式,使牧民应付不来。首先,温室大棚是一种技术上要求较高的耕种模式,种植作物基本为经济作物,具有良好的经济收入,但是耗费精力较多。黄草川居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多为葫芦瓜、西红柿,葡萄等,皆耗时长且耗水多。其中移民种植的酿酒葡萄,采用小枝子种活要三年才能结果[14]。其次,当地汉族邻居也不熟悉温棚的耕作方式,所以藏族移民无法就近获得技术指导。虽然黄草川基层政府派专业人员对于温棚的种植给予指导,但是移民接受技术知识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黄草川移民还未能较好地恢复生产;黄草川移民基本没有圈养牲畜的生产活动,温棚基本用于种植番茄、葡萄等经济作物,没有种植饲草的土地和空间,无圈养牲畜的饲料,圈养行为随之逐渐减少。土地无法满足收入和情感的寄托,许多黄草川移民选择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夏季移民社区成为“空城”,移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强。生产上的不适应,不仅降低了移民生产效率和劳动积极性,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负面效应,从而影响生态移民工作的顺利开展。
(3)比较
双海子村属于移民早期阶段,我国生态移民工作处在探索时期,搬迁的农村移民起初对于生活的维系存在疑虑。但是经过西部大开发的发展和移民对土地的改良和耕作,其经济状况和移民适应程度不断提升,目前处于稳定阶段。相较而言,黄草川移民仅仅经历2年的迁移和调适,异地生产方式的不适应,导致社会整合和经济适应程度较低,现处于波动发展阶段,黄草川生态移民家庭经济状况受影响程度较高(见表4)。
(二)生态移民文化调适比较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某种外部因素在一定时期造成了社会的失衡,文化变迁正是调适这一现象,寻求新的社会平衡的过程[15]。生态移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其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文化的调适,文化的调适反过来会通过个体特定的社会行为影响生态环境。“新”来者面对变化,在语言、风俗、生产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适现象。本文将从语言、风俗和社会网络三个方面对移民文化适应进行分析。

表4 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家庭经济与生产强度比较(%)
1.语言
“语言不仅承载着一个族群的文化,还联络着不同个体间的信息。语言是不同民族之最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16]。”移民对迁入地的语言的掌握程度,一定强度上影响着移民者进行文化调适。调查发现,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对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都比较高。
(1)双海子村移民掌握当地语言的程度
双海子村移民对当地语言的掌握经历了不适到适应的渐变过程。双海子移民多数属于裕固族。裕固语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它分为东部和西部两种,两者之间差异较大,相互之间无法交流,即便如此,操裕固语的人都自称为“尧乎尔”[17]。田野调查发现,双海子村几乎都会说汉语,无论刚会说话的孩子还是80多岁的老人。30岁以上的人群相互交流过程中使用裕固语比较多,在未成年人中使用的情况比较少。移民对当地汉语言的掌握程度较高。
(2)黄草川村移民掌握当地语言的程度
黄草川移民多数属于藏族,移民无论年轻或年长,都会说汉语,村民之间沟通障碍较少。天祝藏族自治县总人口约22万,其中居住有三个主要民族即汉族、藏族、土族,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66%、32%和6%[18]。藏族有语言有文字,然而作为移民的藏族民众历史上长期与汉族居住在一起,普遍都能够很好地掌握汉语。另外国家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各界推广汉语普通话的政策,加之以电视为主导的汉语大众传媒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各族民众对汉语的掌握。
2.风俗
风俗习惯“指人类世代沿袭与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它是人们生活在群体中日常逐渐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规范和习惯”[19]。从草原移民而来的牧民,信奉着传统的草原文化,遵循草原文化习俗。城郊农区文化移民安置地汉族农民众多。牧民与农民体现出很多不同:例如接人待物、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宗教活动、信仰等等。因历史沿革和地域的独特性,形成各自鲜明的特色。对待风俗习惯的差异和日常活动的不同,移民主体存在两种反应:新文化适应主义和原有文化中心主义[20]。
(1)双海子村移民对迁入地风俗习惯的适应情况
双海子生态移民对迁入地风俗习惯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较高(见表5)。对于双海子村裕固族移民来讲,饮食与汉族人相似,宗教信仰现象比较少。最为注重的节日是春节,对这一节日的理解和涵化逐渐与汉族相同。裕固族移民不清楚裕固族春节如何欢度,多数访谈对象认为裕固族“春节”风俗和汉族基本一样。1958年后裕固族传统习俗逐渐消失,因此双海子仅有很少数70岁以上的移民知道一点裕固族春节习俗,能够回忆出儿时本民族传统的过年习俗和方式。

表5 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对迁入地风俗习惯接受和认可程度比较(%)
(2)黄草川村移民对迁入地风俗习惯的适应情况
黄草川村移民相较于双海子村移民对迁入地风俗习惯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较低。黄草川村藏族移民虽然同汉族人都过春节,然而,在衣食住行宗教活动等诸多细节上保存了藏族原有的传统文化因子,甚至宗教信仰文化出现交融现象[21]。首先在服饰方面,藏族移民春节时必须穿着藏服以表示对他人的尊重和重视。其次在宗教活动方面,例如春节这样的盛大节日藏族移民一定会去距离黄草川村6公里以上的华藏寺寺院拜佛、点酥油灯、给僧人拜年、煨桑、念平安经、叩头等;有些移民还会在春节期间到更大的寺院从事比较隆重的宗教活动,例如分别在正月十四和十五观看法舞、“晒佛”、欣赏酥油花,他们将之称为“毛木兰”。虽然藏族移民慢慢地接受了汉族的过春节的方式,但却对其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应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例如黄草川的藏族移民张贴春联时,却用藏文书写。饮食方面,虽然春节也吃饺子,但是主要原料为牛、羊肉而不是猪肉。田野调查发现,有些汉族移民也存在信仰藏传佛教的现象,信仰文化展现出不断交流融合的趋势。
3.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个体和群体进行交流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体系[22]。人与人之间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不仅是进行物质交流活动的运送渠道,还是信息联络、经验交流,加强经济文化互通的桥梁,更是维系感情和人际关系的纽带。牧区生态移民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巨大改变。牧区居民由过去简单且不频繁的人际交往逐渐向复杂且频繁的社会交往过渡。由于移民工程造成地理空间转移,导致移民原有社会网络不同程度被打破,移民在迁入地重构社会网络成为必然需求。
(1)双海子生态移民的社会网络现状
如其他牧区生态移民一样,双海子生态移民也经历了由不适到适应的渐变过程。迁移前牧民在牧区过着一种散居的游牧生活,由于地理环境的广阔,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人与人之间接触不频繁,社会交往单一,摩擦少。迁移后,散居变聚居,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新”社区较“旧”牧区居住更加密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繁且复杂,造成矛盾摩擦增多。但同时,牧民迁移后不再从事粗放型的游牧方式,而是逐渐转变为集约型精耕细作方式,生产的重点不再是劳动力,而是技术。因此,“业缘关系上的邻居”逐渐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移民与当地居民间潜在的社会资本逐渐萌发。一位双海子村50岁的裕固族村民回忆,“现在我们种庄稼的技术都是从汉族邻居学的,他们总是把地种的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另外,裕固族移民与当地汉族居民通婚现象较多,拉近了相互间社会距离,移民社会网络渗进本地居民初级群体里,降低二者异质性,促进移民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
(2)黄草川生态移民的社会网络现状
同双海子生态移民相似,由散居变为聚居,牧民移民社会交往较过去更加频繁且复杂,人际交往摩擦增多。在日光温室种植方面,当地汉族居民同藏族移民都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汉族邻居无法给予移民相应的生产指导,割裂了业缘在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的纽带和联络作用。调查发现,黄草川生态移民认为与本地居民的关系都是“打招呼的点头之交”,当遇到困难时,黄草川生态移民社会支持大多来自于其迁移前的亲朋好友。另外,藏族移民几乎不与本地居民通婚,孤立了相互间的社会关系,异质性增强,造成移民小团体,社区社会资本水平低下。

表6 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生活满意度比较(%)
(三)生态移民主观评价比较
移民对迁移后生活质量和满意感的主观评估是测定移民内心真正达到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参数。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s)是一定时期内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衡量标准对其生活状况和质量的主观评价,是一种认知层面上的幸福感[23]。调查发现,黄草川生态移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双海子,82.7%双海子生态移民比较或者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53.6%黄草川生态移民对现有生活比较满意,还有21.6%的黄草川移民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见表6)。
三、生态移民问题的多元善治方略
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健康发展,生态移民离开了世世代代生存的故土,为国家整体利益发展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两文提出:“无论任何人,都有诸如生存权利一样与生俱来的生态权利,跨越空间,跨越时间。”[24]西部的生存环境改善不仅关系中东部地区的生态改善和人民发展,还关系不同代人生态权利的伸张,最终实现不同时空跨域的个体的生态正义,包括社会公平和环境公平。着眼于眼前抑或者长远,中国西部的生态移民都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生态移民关乎众多群体、地域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他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会派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生态持续恶化、土地矛盾、农业生产技术缺失等等社会问题。一些生态移民在迁移后呈现负发展现象,一些生态移民仍游离于迁入地主流社会群体之外。生态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移民工程和区域人地关系协调活动,涉及面广、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因此,为改善移民社会适应状况,扩大移民生存发展空间,需要以人为本,关注人性,重视人的解放和发展,采取多路径、多维度、多层次的多元善治方略。
(一)加大资金投入,提倡激励型扶贫机制
贫困问题一直是生态移民奔向小康生活无法忽视的屏障,生态移民要想取得保护环境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双重效益,必然有成本的付出,包括安置成本、生活成本、就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非货币付出的心理成本、社会关系网络损失和风险成本[2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资价格、生活花销及劳务需求水平不断增长,选择移民而放弃原有的居住环境可能获得的收益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可能性心理失衡及不确定风险,社会网络损失等现象凸显,移民成本逐年增加,因此,提升移民补偿力度和实施激励型扶贫机制势在必行。首次通过“他助”即政府鼓励社会各界囊括企业、第三组织、个人以合法的方式进行扶贫活动。其次,通过“自助”激发受助者群体的脱贫意识,展开脱贫行动。“他助”激励外部扶贫者付诸扶贫活动,“自助”是针对贫困者自身进行激励的扶贫形式。目前“他助”意义上的扶贫方式效果不甚理想,“自助”扶贫模式亟待引入到移民工作中。中国西部生态移民生活状况依然普遍较差,部分移民仍处于绝对贫困。应扩大移民发展空间,鼓励移民群体挖掘自身潜力,积极建立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农业产业化,推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协调整合[26]。双海子村移民正是通过建立“双海西瓜”农民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二)重构社会网络结构,扩大社会资本利用范围
法国学者布迪厄较早将社会资本概念系统运用于社会学中,认为社会资本是各种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的集合,与社会网络紧密联系[27]。帕特南理解的社会资本三要素,即信任、规范和网络性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权威、传统习俗规范及社会关系网络规则,具有强烈的逻辑契合性。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不仅造成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而且迁移过程社会网络被打破的同时,社会资本也在变迁。这种民族移民引起的社会资本变迁具有十分独特的民族烙印[28]。首先,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群众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如生产技能缺失、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和社会经济组织机构解体等都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云南金平县苦聪人移民定居后,由于种植作物的类别改变导致生产技能不适,给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都带来损失,造成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大量苦聪人返山[29]。其次,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存在基础。第三,社会资本是少数民族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整合不同群体间利益,重构社会网络,扩大社会资本利用范围,是完善社区治理和促进社区和谐的重要问题。以黄草川移民为例,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困难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移民搬迁后生产方式从放牧转变为温棚种植,差异较大,造成移民生产技能缺失,导致移民经济发展滞后。其次,移民没有在迁入地形成较为发达的社会网络体系,也没有刺激性的因素促使移民形成常态性社会交往机制,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匮乏。最后,黄草川移民文化适应水平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缓慢,不仅在移民安置地未能建构起相互信任和规范的社会网络,还制约潜在的社会资源的利用效果,影响移民发展。
(三)加强社会工作介入,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
经过比较研究,生态移民各个主体即移民、当地居民和政府相互之间关系复杂,黄草川生态移民村因为政府与移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移民参与度不高,未能针对社区需求开展服务,移民安置点内政府规划建立的公共设施(例如公共厕所)利用率不高,社会资源浪费较大。2011年民政部在《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更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有利于政府了解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因此,作为政府与移民之间的第三方,应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整合不同的社会资源,协调各主体间的平衡及支配权,作为社会福利的传递系统和心理服务的解压器,以“共同承担、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与政府和移民之间沟通合作,形成良好的社交支持网络[30]。提高政府参政、议政能力,为移民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促进移民和当地居民的交往和互动,有效化解移民的社会性困境,激活社区活力,增强社区归属感,使社会工作介入成为移民工作的“安全网”。
(四)关注文化与生态保护,转变移民安置战略
田野调查发现,双海子与黄草川生态移民对于本民族语言和风俗在不同程度上的丢失有所察觉,对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20岁到30岁移民中重新苏醒起来。另外,移民对于迁入地生态系统在开发与挖掘过程中不同程度被破坏的现象也开始警惕。双海子村在移民迁入的十多年里地下水位急速下降,过去“双海泉眼”已经不见踪影。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若强调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注重移民人权生活化,在尊重移民自由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移民文化的传承及迁入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生态移民,要通过多种手段帮助移民共同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和风俗,营造良好的文化活动氛围,同时提高移民生态保护理念,形成良性的社区交往机制。促进移民、当地居民及政府形成共同的文化传承持续机制和环境保持的共同承担机制,建立移民自身的自我开发和保护精神[31]。对于各级政府,要从根本上转变移民工作的刻板心态,移民不是负担和包袱,而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成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还是后代人生存环境保护的关键要素。
(五)重视移民新生代,助推移民长远发展
在移民迁入地出生并且成长的一代人通常被称之为移民新生代[32]。政府及社会各界针对第一代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关注较多,而对于移民新生代的关注和报道较少。田野调查发现,西部生态移民新生代多数处于童年社会化时期,而社会整体对于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导致移民的社会边缘化,移民新生代的童年社会化相对匮乏。另外,移民活动造成移民文化的部分丢失和淡化,移民新生代对于其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极其淡泊,处于这样一个幼儿发展的关键时期,移民新生代的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生态移民不是一代或者两代人的问题,而是不同地域不同时空影响下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双海子和黄草川是西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移民社区,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异,例如移民时间、背景、地区、适应程度等等。经过比较分析,双海子从1999年开始迁移,经历了十几年的融合和发展,基本完成了社会整合和社会适应。但是黄草川移民却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症状,移民在生产技能上的缺失、经济上的不适应,融入当地社会较为困难。在借鉴双海子生态移民部分成功经验的同时,纠正移民在主观和客观认识上的偏差,克服生存与发展困境。本文在更大范围内参考不同类型生态移民的安置情况和社会适应状况下,深度挖掘黄草川移民社会整合过程中障碍和困难,为生态移民社会管理和迁移规划提供参考。需强调的是,生态移民是一个涉及面广,关系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工程,涉及不同主体间权利,关系到移民的主观满意程度和客观适应情况,需要不同社会群体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1]李东.中国生态移民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西北人口,2009,(1):32-35.
[2]皮海峰,吴正宇.近年来生态移民研究述评[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4-17.
[3]侯东民,张耀军,孟向京,蔡林,周祝平.西部生态移民跟踪调查——兼对西部扶贫战略的再思考[J].人口与经济,2014,(3):17-24.
[4]杨文晶.资源整合视角下裕固族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以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生态移民村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43-245.
[5]朱广印.牧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14,(9):31-35.
[6]李静,杨哲,刘继杰.生态移民之后的移民生计方式变迁与文化变迁——以甘肃省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为例[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4):78-82.
[7]王富贵,汪慧玲.政府应该为生态移民做什么——基于祁连山保护区天祝县的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2010,(1):57-61.
[8]邓学才.住房朝向与冬暖夏凉[J].建筑工人,2006,(3):39.
[9]王永平.生态移民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4.
[10]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1.
[11]迈克尔·塞尼.移民-重建-发展[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73.
[12]廖小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视域下少数民族的生态权益保障[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3):31-35.
[13]贾祖璋,贾祖珊.中国植物图鉴[M]北京:中华书局出社,1958.147.
[14]曾辰.极端干旱区成龄葡萄生长特征与水分高效利用[D].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15]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 译.译林出版社,1999.
[17]赵利生,熊威,江波.族群认同的嵌入性——公共话语、社会空间、象征符号的作用:以肃南县明花区双海子村裕固族移民故事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9,03:76-81.
[18]天祝县统计局天祝县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1-05-05].http://www.gstianzhu.gov.cn/huarui/news/tzjj/tzjj/2011/55/KD2D.html.
[19]潘伟杰,孙锐,宋永化.文化的力量———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文化立社区初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0]赖韦文,朱洁怡,谢英美,向安强.新丰江与三峡水库农村移民的时空跨域比较研究——以广东博罗为中心[J].西北人口,2015,(1):21-27.
[21]何俊芳,王浩宇.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5-19.
[22]叶继红.集中居住区移民社会网络的变迁与重构[J].社会科学,2012,(12):61-67.
[23]姚本先,石升起,方双虎.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J].学术界,2011,(8):218-227.
[24]董燕燕.关于生态补偿与生态正义[J].改革与开放,2010,(14):92.
[25]吕静.陕南地区生态移民搬迁的成本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6]张文政.西北民族地区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现实意义、影响因素和理性选择——基于甘肃藏区的调查[J].甘肃社会科学,2014,(2):197-200.
[27]Narayan and Pritchett,Social capital: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ee Dasgupta and Serageldin,Social capital: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the World Bank,1999.
[28]Yang Du, Albert Park, Sangui Wang.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4)133.P.688-709.
[29]罗承松. 文化认同与移民社区建设——以镇沅县恩乐镇易地安置的苦聪人社区为研究对象[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1):73-76.
[30]拉毛才让. 社会工作专业模式介入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3):6-9.
[31]Randall, Alan. Resource Economics: An Economic Approcah to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M].Grid Publishing, Inc. 1981.
[32]陶格斯.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责任编辑戴正责任校对戴正)
[作者简介]饶凤艳(1990—),女,安徽临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部农村发展与行政管理;张文政(1975—),男,甘肃民勤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3XDJ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青藏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建构与社会稳定研究”(项目编号:12BSH034);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YB056);甘肃省高校科研项目“甘肃藏区生态移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3A-068)
[收稿日期]2015-07-13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