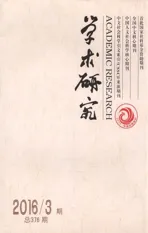我本农家子,白衣入翰林——施议对教授的词学研究
2016-02-28邓菀莛
邓菀莛
我本农家子,白衣入翰林——施议对教授的词学研究
邓菀莛
[摘要]网上有云,施议对以20世纪中国第五代正统词学传人自居。证之于先生,曰:无不可。先生治词道路大略分三段。第一、传旧阶段,词学集成工程的规划与实施;第二、创始阶段,今词与今词学开辟与创立;第三、再上层楼阶段,新世纪词学关注与推进。前两个阶段,标志性成果有《当代词综》的编纂、《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出版及《人间词话译注》刊行。“词学三书”出版,则为第三阶段标志性成果。
[关键词]施议对治词之道传旧与创始实证与通变真传与门径
施议对是当今词界颇具个性特征的人物。晚生因收看先生在超星学术视频上的讲演,得先生教诲,并承厚爱,允为探寻其治词之道。以下,谨将探寻所得略加归整,与读者共享。
一、《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近百年词学研究集成之作
施议对,字能迟,号钱江词客,又号濠上词隐,台湾彰化人,生于福建泉州。1964年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并考取杭州大学研究生,从夏承焘学词。“文革”中断学业。1978年重新报考,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从吴世昌学词,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遗产》编委。1991年移居港澳,先后担任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词学教学及研究50年,出版著作《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人间词话译注》《施议对词学论集》《当代词综》等近30种,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施议对论学四种》亦于近期刊行。
在众多著作中,《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应是施先生的一部代表作。这部著作计上、中、下3卷14章,凡30万言。撰写于吴世昌门下,攻读硕、博期间。里面的内容如先生说,这是他20年间在夏承焘、吴世昌教督之下,学词经验的一个总归纳。这部著作,有学者编纂词学史资料,曾将其划归词乐一类著作。其实,先生说,他的这部著作说及词乐并不错,但并非专门的词乐著作。所谓词与音乐,两个方面最多也只是一半对一半,而他说音乐实际为说词,说的是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比如,这部著作的上卷4章,题称“唐宋合乐歌词概论”,实际是一部唐宋词发展史;中卷6章,题称“词与乐的关系”,所说是词与音乐之间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下卷4章,题称“唐宋词合乐的评价问题”,论说歌词合乐利弊,探讨歌词发展路向。先生将这部著作看作词学真传之所在,既要将夏承焘说词、填词的精深体验运用到词与音乐关系的研究上,又要将吴世昌说词、填词的敏锐见解运用到词与音乐关系的研究上,因而,先生这部著作真正是一部词学研究专门著作,颇得学界前辈的赞赏,被推尊为“近百年来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集成之作”(启功语)。此后,凡撰著有关词学研究著作,尤其是硕、博学位论文,在引用书目或参考文献时,都不会忘记提及先生这部著作。此著于198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归《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该社于1989年4月第二次印刷。2008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再版。据说,日本京都大学户川芳郎见此书,曾命弟子前往寻访,计划翻译为日文出版,但未成事。
前几年,曾大兴教授在有关先生的访谈问,是否同意刘尧民《词与音乐》某些观点?先生答复:
上世纪四十年代,刘尧民先生撰写《词与音乐》,在当时算是一项“垦荒的工作”(罗庸语)。几十年后,一直到当下,这部著作对于后学,应当仍有启导作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结撰硕、博论文,只是想在其基础之上,有所承接、有所添加。当时的著眼点,在关系二字上。刘说词与音乐,因为是词史的第一章,原题“词之起源”,其所论列,较偏重于音乐对于词的制约。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既说制约,又说反制约。以为:“(词与音乐)二者在发展演变中,经历了从互相融化到互相脱离的漫长过程。”(见《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绪论)刘氏强调一个方面,所谓“音乐之赐”,我顾及两个方面,词与音乐。刘以为,词不能没有音乐,离不开音乐。我以为,词可以脱离音乐。到底离开不离开,脱离不脱离呢?我觉得,最好不要离开,不要脱离。但是,从实际上讲,是离开、脱离,离开、脱离,才能发展。那么,什么时候离开,或者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呢?我以为,温庭筠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不必等到宋。据《旧唐书·温庭筠传》记载:温庭筠其人,“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弦吹之音,乐音的音;侧艳之词,文词的词。文辞的词,就是语言文字的字,或者词汇。以之追逐弦吹之音,即将音乐转移到语言文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用文学的语言去追逐音乐的语言。这一记载说明,温庭筠的时候,所谓倚声填词,只要注意文字的声,用文字的声去应合乐音的音。词之所以填者,自此时开始。因而也说明,温庭筠的时候,词已经可以脱离音乐。那么,这个时候的倚声填词,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就词与音乐二者的关系看,所谓用文字的声去应合乐音的音,应当说,这仍然是歌词合乐的一种形式。后世所谓“音理不传,字格俱在”,即以字格追寻音理,同样属于这一情形。[1]
《词与音乐》与《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部论述词与音乐关系的著作。先生这段话,对这两部著作相同与不同之处进行客观评述。刘尧民偏重于音乐对于词的制约,先生则主要说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既说制约,又说反制约。这是两部著作最大的不同处,也是先生研究词与音乐关系的立足点。先生所说词学真传的八字真言“音理不传,字格俱在”,就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
二、《人间词话译注》,今词与今词学的开辟与创造
先生治词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教学与科研,都依遵“述而不作”这一古训严格要求自己,也用以启导学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朱熹注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2]述与作,两个方面的意思不能够分割开来。而就先生的治学经历看,述与作,传旧与创始,正是一个互相交融、互相促进的过程。如果说,撰著《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让自己懂得什么叫发明师说,什么是词学真传,那么,撰著《人间词话译注》及《人间词话译注》增订本,则进一步让自己懂得什么是史观与史识,如何进行开辟与创造,包括具体的方法与途径。两著标志两个不同的治学阶段。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由黄寿祺门下到夏承焘门下,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夏承焘门下到吴世昌门下;一个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由大陆移居港澳,直到21世纪初。两段各20年。
《人间词话译注》的撰著,起自1983年春。当时,夏承焘命先生合作译注。但中间搁置多年,直至1988年秋才完成全稿。而夏先生已于两年前归赴道山。这部书稿于1990年4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初版,1991年5月又由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出版。2003年9月,长沙岳麓书社印行增订本,2008年12月该社印行增订本新版。此后,该社又接连推出阅读无障碍本(2012年8月第一版)、插图本(2015年8月第一版)以及“周读书系”便携纸皮书系列(最近待刊)。这部著作,包括题解、原文、译文、附注4部分。所录词话,以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本为底本,得142则。据滕咸惠注本补录13则,并据《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补录一则,合156则。前言题称《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解读王国维,明确王国维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批评模式。王国维之前一千年,以本色与非本色看待词与词学;王国维之后,境界说出现,有了另一选择。译注本各个部分对王国维以及《人间词话》的解说,恰到好处,颇得好评。初版刊行,由此岸传播至彼岸,并在彼岸印行新版。伴随著先生的行迹,1993年在香港也曾准备刊行增订本。当时先生撰《王国维与中国当代词学》一文,拟为增订本的导读。文中指出: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标志著中国新词学的开始。这是计划中的港版增订本。由于种种缘故,此本的出版计划未实行,而“导读”则发表于1994年8月19日及26日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移居港澳,又经过了十个年头,至2003年9月,《人间词话译注》重新回到大陆,《人间词话译注》增订本在长沙出版。增订本将前言移作后叙,另增加了前论,说明三个问题:一、著书立说与里程标志;二、人文精神与文化阐释;三、走出误区与回归本位。三个问题合为《词学三题》,发表于《学术研究》2003年第10期。此时,经过20年的思考与实践,从《人间词话译注》到《人间词话译注》增订本,先生的史观、史识已渐明晰,词学理论逐渐构成体系。先生述作之值得注视者,大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期分类的史观与史识。分期分类,这是述与作的基础。译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首先确定的史迹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手订稿64则,最初刊行于1908年11月13日及1909年1月11日和2月20日,详《王国维治词业绩平议——〈人间词话〉前言》。先生指出:1908年是个关键年份。这一年,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标志着中国新词学的开始。指出:“千年词学史,其发展演变可以王国维为分界线:王国维之前,词的批评标准是本身论,属于旧词学;王国维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无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为新词学。”[3]先生的这一判断,为千年词史以及百年词史的撰著明确了界限,是史观与史识的体现。为确定这一史迹,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既竭力加以宣扬,自己有关词史、词学史的撰述亦据以立论。1995年,先生撰著《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依此判断,将百年词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并将蜕变期词学分为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再评价阶段、反思探索阶段。提出:1908年为新旧词学,亦即古今词学的分界线。[4]经过一再申述,一再实践,先生的这一判断,目前已成定论。
第二,词学史上三座里程碑的确认与标举。由于史迹的确定,史观与史识的形成,慧眼独具,以之说词,自然不同一般。在先生看来,1908年不仅是编纂百年词史、词学史的关键年份,而且也是编纂千年词史、词学史的一个关键年份。立足于此,先生首创中国词学史上的三碑之说。他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李清照的本色论和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看作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提出:“三座里程碑,三段里程,三个里程标志。第一段,一千年,属于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属于王国维地段;第三段,吴世昌地段,目前尚无立足之地,可能是今后一千年。”[5]三碑之说,这是先生建造中国词学学的基础。所谓中国词学学,“这是研究词学自身存在及其形式体现的一门学科”。[6]依据这一定义,先生另文将词学学这门学科的意涵概括为六个方面和三种批评模式,简称三碑与六艺:
词学学对象,应当确定为词中六艺及词学史上用作里程标志的三种批评模式——本色论、境界说以及词体结构论。词中六艺,包括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这是赵尊岳为饶宗颐《词籍考》撰写序文所提出命题。对于一般所说词学,六个方面,大致可窥全豹。这是一种面的展示。而三种批评模式,为灵魂,亦纲领,乃线的贯穿。[7]
此说表示词学确实存在。它的形式与形式体现,主要说词学批评模式及批评模式的运用。至此,先生有关词学学这一门学科的建造,其轮郭已初步确定。这是在史观与史识导引下进行的理论前沿建造。
第三,境内与境外的区分与判断。这有关王国维境界说的正名问题。这里暂且不说作为名词的境界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只说作为批评模式的境界应当如何理解。作为名词的境界有一定内涵与外延;作为批评模式的境界,除了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还必须考虑它的运用。在三碑说的理论说明中,先生曾说及王国维的理论创造,指出:王国维倡导境界说,是探其本,而非仅仅探其面目的理论创造,属于“向上一路”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层面的提升。因此,先生曾在相关文章中说了以下一段话。
我以为,王国维的理论创造,亦可以下列三个层面加以表述:①拈出疆界,以借壳上市,为新说立本;②引进、改造,将意境并列,使之中国化;③联想、贯通,于境外造境,为新说示范。[8]
先生以为:三层意思,三个步骤,展现出一个过程,这是层面提升的过程,因而,对于王国维所探求的认识,也当逐层、逐步细加推断。依据先生的理解是,王国维所说境界包涵三层意思:其一,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是一个疆界,一个具备长、宽、高这样一种体积的容器;其二,王国维所说的境界就是意境,是由叔本华那里引进并加以中国化的意和境所构成的意境;其三,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是境外之境,它所要呈现的意思在境外而不在境内。[9]三层意思,合而观之,可以获知王国维境界说所说的境界,并非一般所说情景交融的艺术个体,或者主观与客观统一的艺术整体,而是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的艺术本体。这就是境外造境的意思。[10]先生这一阐释,究竟是否合乎王国维创立新说的原来意思,可以通过作家与作品的解读加以验证。例如,李煜《虞美人》,是对往事的怀念与追寻。如果只是看境内,必定以为作者所怀念的是故国江山、旧日宫殿;而从境内看境外,则以为作者所怀念的并不仅仅是故国的雕栏玉砌,而是春花与秋月,亦即像春花秋月一样美好的人和事。[11]两种解释,一种在境内,以帝王身份看李煜;一种从境内到境外,以释迦、基督身份看李煜。两种解释,究竟何者较为切近作者的本意似颇难获知,而何者较为切近王国维创立新说的原意,则不难获知。由此可见,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层面区分。这就是形下层面与形上层面的区分。先生依据王国维有关释迦、基督的论断说李煜,用层面提升的方法说境界,为王国维境界说正名,代表一种通过作家、作品深入研究所确立的史的识见。
以上三个方面叙述,着重在史观与史识的锻炼及形成。经过对于一千年、一百年词与词学历史的分析、归纳与解释,包括哲学的综合、演绎与规范,先生形成了自己的史观与史识。依据于此,先生提出今词与今词学两个概念,撰著《今词达变》,推举今词七家,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与再设想。在这过程中,先生以分期分类为纲领,为词史、词学史的编纂指示方法与途径,又以存在与存在的形式体现,为词学学科的创立发凡立例。[12]这是先生在传旧的同时,于创始上取得的成就。
三、再上岳阳楼,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使命感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经历两个20年,这期间施议对功成名就。先生似乎应当歇一歇了,但步入新世纪十余年来,先生仍然活跃于学术前沿。传道、授业、解惑,不遗余力。单就2010年以来的六年中,先生出版专著达13种,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先生热爱诗书事业,对于大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词学,有深厚情感。他了解词学的过去、熟悉词学现状,对于未来亦有充分把握。他的一系列著述,于字里行间往往体现出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的使命感。20世纪5代词学传人,从晚清民国一路排下来,先生将自己列归第五代。这是在词学蜕变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先生说:
这一代传人,1935年之后出生。崛起于上世纪之最后二十年。可以看作是共和国的第三代。由于时代所赋予,包括物质与精神,这一代既大大优越于前辈,其开辟与创造,自然比前辈优胜。对于百年词学,这是充满希望的一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因先天不足,后天补救不得力,或者不得法,这一代,也可能让人感到失望,或者困惑。既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亦可能是垮掉的一代。[13]
先生以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第五代词学传人,是一个时代词学成败的关键。先生担忧,蜕变期的词学可能由于这一代的推波助澜进一步蜕变,有责任告诫新一代,从蜕变期的误区当中走出来。因此,继《百年词学通论》之后,先生撰著《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一文,明确提出:
就历史发展进程看,二十世纪词学,由晚清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统共经历三个时期,两次过渡。三个时期,分别是开拓期、创造期及蜕变期;两次过渡,包括由古到今的过渡以及由正到变的过渡。进入新世纪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由变到正的过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一过渡,就是对于旧世纪词学蜕变的反动,或者说一种否定之否定。把握新世纪词学研究路向,似应着眼于此。
面对眼前的抉择,先生说:“新世纪词学只有纠正旧世纪词学的失误,实现由变到正的转换,才能走上继续发展的道路。”[14]为著推进新世纪词学的发展,除了以蜕变、误区一类语汇相警戒,先生还以前辈传人的经验相勉励。在一次词学研讨会,先生演说《二十一世纪词学的前世与今生》,将正在行进中的21世纪词学,与过去一个世纪的词学相比对。提出:上一个世纪的词学创造期,是出大师的一个时期。如果历史能够重演的话,新世纪的第三代,1995年以后出生的人士,可能是出大师的一代。[15]先生将中华词学的未来,寄希望于新世纪新的一代传人。
在新世纪新的开拓期,十几年来,继《宋词正体》《今词达变》之后,先生又推出《词法解赏》,三部著作合为《施议对词学论集》的第一、二、三卷,网上称“词学三书”。三部著作是先生在这一阶段所出版标志性的著作。此外,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先生曾筹划、主持举办两届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曾多次前往国内外多所高等学府发表演讲。其中,几个讲演挂上超星学术视频,诸如《词与音乐》《新宋四家词说》《词与词学以及词学与词学学》等,颇得好评。
以上所说三个阶段,先生既引为骄傲,亦时时有紧迫感。目前除了写作、讲学,指导研究生,还有前辈倚声家论学书札急待整理出版。先生的案头依然堆积如山,其忧与乐似亦无有穷尽。故有词曰:
吴楚东南坼。洞庭秋、洪波不起,众山沉寂。胜状巴陵今何处,江畔行吟骚客。襟袖冷,层楼攀摘。素月分辉明河共,莽乾坤、一例花霏色。忧与乐,总难测。后先天下依时易。古仁人、居高处远,忧民忧国。浩浩汤汤莫能御,隐曜日星樯楫。尘扑面,笼纱弄碧。历历几番沧桑换,数从头、为问去来迹。烟水静,梦中觅。[16]
这是2015年仲秋,应邀赴湘参加中南大学所办“潇湘情,中华韵”2015年两岸三地大学生吟唱文化交流节活动,先生再次登上岳阳楼所填制的。歌词布景、说情,以今论古、以古证今,说家国也说自己,联想、贯通,将巴陵胜状和行吟骚客连成一片。杨雨说:“参酌古今,眼前景与今昔情融合无间,且议论高卓而有韵味。”可谓知言。先生善于通古今之变,勘破忧乐,于迷茫烟水中寻觅沧桑变换及自己去来的足印,此词可看作一篇微型的岳阳楼记。先生亦颇为自得,以为形上词创作的实践。
四、余论:融夏、吴二家之长,成独有之治词风格
施议对出身贫寒,网友都知道,他的祖父是个补鞋匠。先生自小读不起书,曾感叹过“读书难”。[17]一名普普通通的的农家子,何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呢?记得十年前,在中山大学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彭玉平教授宣读邱世友教授给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顾吾兄从学于夏、吴二大家,得通变之思于吴(世昌),得实证之学于夏(承焘),斯二者词学专家,各以其治学特点授兄,而兄则融二家之长,成独有之治词风格。
珍重师承,不忘师恩,先生曾以五言古诗《戊子金谷苑送别有作》记录这段心路历程:
三月十七日,转头已再周。平生多少事,行退且无忧。
一棹烟波远,大江滚滚流。崇楼天欲蔽,蕖影立沙鸥。
我本农家子,白衣入翰林。始随永嘉夏,声学度金针。
后逐海宁吴,袒诚款实襟。古粤移居晚,空阶寒气侵。
唧唧复唧唧,当户未成匹。斟酌仰南斗,几箧文史溢。
幸得素心人,光照临川笔。登高知几重,太白连太乙。
其中说及追随两位导师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人的情景。一位永嘉夏承焘,授以绝学,度以金针;一位海宁吴世昌,思虑款实,精诚其心。古粤移居,太白太乙,叙说自己在港澳如何继续进取。[18]
先生的治词风格、治词之道,已逐渐引起学界注视。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赴美出席缅因词学讨论会,学界已有北施(施议对)南杨(杨海明)之称;近一、二年,学界又有“词坛四杰”之议,四杰指施(议对)、杨(海明)、邓(乔彬)、刘(扬忠)。[19]对此,先生均不以为意。但十几年前,流寓海外的刘再复,在其《漫步高原》的著作中,以《施议对:词学的传人》为题,称扬先生的词学,先生却颇以为意。[20]先生说,他喜欢“词学传人”这一称谓。以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并曾据以为文,对于20世纪五代词学传人各自的位置、职责进行历史的论定。先生外出讲学,也喜欢以之为标榜。网上有云,施议对以20世纪中国第五代正统词学传人自居。证之于先生,曰:无不可。
施议对先生之词学,取精用宏、覃思独运,传旧创始、融汇贯通,已渐进入化境。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21]晚生见识肤浅,对于先生的治学及治学之道极为景仰,却缺乏全面了解,体会不深,颇难得其要义。疏漏之处,敬希大方之家有以教之。
[参考文献]
[1]曾大兴:《登高知几重,太白连太乙——施议对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
[2]朱熹:《论语集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施议对:《王国维与中国当代词学》,《大公报》1994年8月19日、26日艺林副刊;《人间词话译注》(增订本),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4]施议对:《以批评模式看中国当代词学——兼说史才三长中的“识”》,《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5期(1995年冬季)。
[5]施议对:《词学三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10期。
[6][12]施议对:《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词学》第17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7][8]施议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新文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9]施议对:《从诗歌到哲学的提升——古典诗歌研究与人文精神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开题报告》,《学苑效芹》(《施议对论学四种》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0]施议对:《中国古典诗歌讲堂实录》(未刊稿)。
[11]施议对:《文学研究中的观念、方法与模式问题》,《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
[13]施议对:《百年词学通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14]施议对:《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5]施议对在“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讲话录音。
[16]施议对:《貂裘换酒·再上岳阳楼》,《澳门日报》2015年10月14日新园地副刊。
[17][18]施议对:《学词与填词》,据超星学术视频(video.chaoxing.com)。
[19]王兆鹏、汪超:《把词当作艺术品来研究》,《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2日。
[20]刘再复:《漫步高原》,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21]司马迁:《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责任编辑:陶原珂
作者简介邓菀莛,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16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