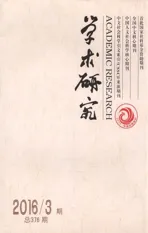新境与新径:当代广东的“荒政书写”*
2016-02-28张永璟
张永璟
新境与新径:当代广东的“荒政书写”*
张永璟
[摘要]荒政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实践、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是政府向灾荒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荒政书写考量着政府的应变能力、治理绩效与施政良心。当代广东面临孕灾土壤更“肥沃”、救灾预期更高、成灾损失更惨烈、灾荒种类层出不穷等新问题,要用“制度化、体系化、全民化”三位一体的理念,借助科技、市场来应对荒政,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从而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关键词]广东荒政荒政场域荒政题材荒政理念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5XZW01)的阶段性成果。
何谓“荒政”?荒政指的是“救荒政策,它是政府对自然威胁(包括水旱地蝗震等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预防、治理和补救的政策行为。”[1]这里用的是狭义的荒政概念,因为它只提及自然威胁而没有提到“非自然”的人为威胁、生态灾难、科技发展的负面威胁等内容。实际上,这些“非自然”威胁更为来去无踪、更为防不胜防。因此,当今广东的政治谱系中必须用广义的荒政概念,因为层出不穷的灾祸已成为其治理选项中的“新常态”项。这些“新常态”项又倒逼政府要学会用创新的方法来应对自然威胁、科技失控、网络瘫痪等新灾旧难。何谓“荒政书写”?应对荒政的文字实践皆称之为荒政书写。随着社会结构日益扁平化,社会治理渐由一元转向多元,加之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和自媒体的广泛应用,荒政书写也渐由官方、一元书写,变成了群体、多元书写。然而媒体的深度参与、文学的切入、文化的观照长期以来一直缺位,广东的“荒政书写”该是补位纠偏的时候了。
一、荒政书写的新场域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荒政书写,于文学家而言是簇新的时代话题,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赓续;于文化学者而言,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文化合题。于媒体而言,是一个亟待向深度掘进的长期课题。
(一)无可争辩:广东的孕灾土壤更“肥沃”
广东灾荒的危害之大、种类之多有多方面的原因。北枕五岭、南面南海,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穿全省。热带、亚热带气候,使得广东自然条件颇为优越;但同时也较易引发各种自然灾害,如陆地灾害、海洋灾害、北方南下的寒潮灾害等。风灾、旱涝灾害自古就易发、频发、大发。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南海……遂溪等地就曾发生过大旱灾。[2]当今的旱灾、水灾,在岭南更习以为常。惜乎此类题材,并未成为岭南文学的重要一极。有此一极,岭南文学才能称得上完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媒体越发达,有时反使得荒政书写难于做到从容、理性。广东就面临此窘境:纸质媒体有《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并存,网络媒体有腾讯公司、网易公司争雄。据201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广东IPv4地址数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网络域名数位居全国首席。媒体的威力在广东更演绎到了极致:远的如“孙志刚事件”,近的如“深圳的暴力抗法事件”,[3]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达的媒体与网络,使广东荒政书写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既要面对自然的原生灾害,还要面对层出不穷的人为次生灾害。文学家、文化学者皆可在其中,书写出各自的特色。
(二)无法否认:人们对荒政处理质量有了新的要求
这种新的要求来源于比较的非理性。荒政书写须直面这种社会惶悚所带来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压力。比如,人们会从国内比较的角度要求广东的荒政书写要能与北京、上海比肩;而这种比较是不太结合实际的,因为广东没有毗邻首都的地缘优势。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网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网分别显示,上海的常住人口不到2400万,而广东省的常住人口接近1.1亿;上海全市陆地面积为6340.50平方公里,而广东全省陆地面积为17.98万平方公里。如果荒政来临,广东将数倍艰难于上海。“非典”时期的广东,媒体先后失语,导致谣言扩散,引发抢盐、抢板蓝根疯潮,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北上广”的称谓潜含着“广”必须与“北上”比肩的预期。非理性,使得广东的荒政压力更大。让非理性的个体、群体成为文学笔下的形象链,让非理性形象走进广东文学形象的长廊之内,成为广东文学创新的命题。
(三)无法逆转:一旦成灾,损失更惨烈
作为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广东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得一旦发生不测其损失也将愈来惨烈。比如珠三角地区高层、大型、重型建筑鳞次栉比,若发生不测,这些重型建筑地下工程多、软土层很厚,遇到地震,成灾风险很大;此外,珠三角上游水库林立,一旦地震迭加次生及人为地质作用,成灾风险不难想见。广东还是劳动力输入大省,其政治经济权重比较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广东的灾荒问题会迅速放大成为全国性的灾荒问题。2008年冰雪灾害的龙头在广东,经过媒体的密集报道,成为全国焦点,就是一例。实际上,早在1930年广东就发生过严寒,“冻毙者200余人”,[4]但其时广东经济不发达,来粤务工的人数也很少,才没引发如2008年那样的严重连锁效应。惊心动魄正是文学的书写偏好。“惊、泣”一直是文学魅力的核心要素。荒政实践的常态化,为岭南的创新书写提供了契机。荒政书写可用形象、故事来预警世人,从而拓展文学的入世功能;用灾害想像、细节描写来充实人们的视听感受,从而提高其科学素养;用荒政书写文化,使其融入善政、善治社会实践,为文化研究寻找到现实根基。要将多元信息反馈给社会,单靠政府和媒体远远不够。政府书写多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呈现,受众有限;媒体书写,最强调时效性,其影响力也极为有限。以情感性、形象性、审美性见长的文学要“补位”。若然,荒政书写才能深入人心,才能提醒人们居安思危。文化的根本功能,是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的情怀,熏陶人的心灵。如果说文学书写是形而下的“取精”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文化实践就是形而上的“用宏”。取精用宏,应该成为广东荒政书写的一体两面。
二、荒政书写的新题材
广东的“荒政书写”,就政府层面而言,早就设有专门用于荒政的机构——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并有24小时在线的官方网页;与此同时,还有完备的诸如“一案三制”制度设计;队伍建设颇为健全。广东应急办网站获得2015年度中国政务网站领先奖。相对于政府而言,媒体的书写就薄弱一些,比如广东媒体获得的以荒政为写作对象的新闻大奖很少,就连围绕荒政的报告文学也不多见。文学的切入、文化的观照最为薄弱。因此必须用打组合拳的方式加强广东的荒政书写。
(一)“防歹书写”应该加强
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有精彩的一面,也有危机四伏的一面,比如防暴恐形势日益严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这不仅必要而且及时。2014年5月6日,广州火车站砍人事件说明广东已成为暴恐分子的目标场所。在广东制造事端,传播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大。这更要求负有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使命的广东,必须及时亮剑。主动出击的不只是政府,应该还有媒体、文学家、文化研究者等。媒体的“虚位”、文学切入与文化研究的“缺位”的情况必须及时着力扭转。试问:广州火车站砍人事件后还有媒体持续地宣传如何防暴恐的常识么?至于文学方面的书写更是少见。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文体,何曾见到有以此题材的大作品问世?从每年社科获奖目录上看,广东式的“平安文化”研究也较少。做好“防暴恐、防宗教极端势力”是善政的底线要求。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要为人民提供一个生命与财产皆有保障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空间。应该说广东的荒政书写,就政府层面而言,成绩有目共睹。遗憾的是媒体书写、文学书写、文化书写跟进不够,所以说“防歹书写”必须加强。
(二)“防病书写”大有可为
民生之艰,不只是生活方面的物质匮乏。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民生的温饱已基本解决,但疾病问题日渐突出,成为新的“哀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广东这方面的文学题材取之不尽。相应的文化研究,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广东人口基数大,一旦有地方病暴发,迭加效应相当明显。这就是广东“防病书写”的意义所在。据监测数据反映:地中海贫血已成两广地区高发的地方病。[5]筛查结果显示广东约有11%的人携带地贫基因。广东每年约诞生1万名地贫患儿,其中约1000个是重症患儿。患儿很少能活到20岁以上。由于治疗代价昂贵且难以治愈,通过产前诊断阻止重症患儿出生是目前首选预防措施。这是“明天的荒政”,但对于广东来说,今天就必须全力以赴着手书写,如广州本土民生新闻《新闻日日睇》2016年1月适时推出“清远地贫调查”就是一例。广东是“富病毒”省,病毒变异倒逼善政创新。2003年非典型肺炎袭击广东,近年有“埃博拉”病毒,高铁、地铁、城际快线在带来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感染对象,这都对荒政书写提出了新的挑战。新闻日复一日的警示,文学形而下的劝勉抚慰,文化形而上的指引与导航共同组成书写的新应对。
(三)“防震书写”不可或缺
防震书写于广东而言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课题。政府书写、媒体书写、文体书写、文化研究,在这里都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广东本身就是一个“富震”省份。据记载,1923年9月13日广宁就发生过5.5级地震,烈度7度。“全圩百十户多震塌。”[6]1925年“和平县1月27日上午十时地震,屋宇损坏颇多,为数十年所未见。”[7]1949年以前破坏性较大的地震共35次,其中宋代1次,元代1次,明代10次,清代13次,民国期间10次。[8]1600年的汕头南澳就发生了7级大地震,1918年南澳又发生了7.3级地震。整个东南沿海地震带近百年以来发生过11次6级以上的地震。1969年阳江发生了6.4级地震。1983年,汕尾(当时的海丰县)连续半个月小地震,都是2—3级,多达几百次。1994年12月30日和1995年的1月10日,这10天在北部湾连续发生了6.1、6.2级地震。地壳震动若应对不及时、不妥当就会引发社会、政治的震荡。这些统计数字于媒体而言,正是新闻背景的重中之重;于文学创作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创作原料;于文化研究而言,古为今用,善莫大焉。
防新丰江之震是广东荒政书写的特有课题,更能彰显广东的荒政智慧。新丰江水库引发地震,业已经过科学论证。这个题材是全国范围内都没有的。1961年新丰江水库刚蓄水,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小地震。1962年发生6.1级地震,烈度有8度,震中距水库大坝仅1.1公里。这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书写题材。广东的软土层的分布广泛,震级低、震源浅的地震也会产生较高烈度。历史资料还表明,珠江三角洲内4.5级地震即可导致Ⅶ度的破坏,而在一般情况下,5级左右的地震才可导致Ⅶ度的破坏,后者能量约8倍于前者。[9]广东的防震必须“小题大做”,不然损失会更惨烈。因此,政府的主导、媒体的宣传、文学的切入、文化的观照,都需要不遗余力。
(四)“防核书写”要迎头赶上
广东核电站最多、核产业最发达。地震会直接、间接地引发核泄漏;一旦核泄漏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广东境内有大亚湾、阳江、台山3座核电站。东西两座核电站都与发生过地震的地区近在咫尺。新丰江水库与大亚湾距离很近。阳江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自1969年发生过6.4级地震以来,近年大约每4年就有1次4级左右的地震。[10]早在2009年,广东省政府就明确了“核电与核电产业双轮驱动”思路,制定出了《广东省核产业链发展规划》,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披露,到2020年,核电产业链要达到2000亿元的产值规模,并拉动相关产业增加值4000亿元。这就要求广东更要以科学眼光和风险意识去识震、避震、抗震,这成为媒体书写、文学书写、文化研究的簇新话题。
(五)“防非理性书写”责无旁贷
不能人为地遮蔽负能量的书写,比如“散步维权”。散步维权就是通过集体散步的温和方式来引起更大的关注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诉求。散步维权开辟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渠道,但它无疑会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比如,广东番禺建垃圾处理厂的新闻一再发酵。又如“2013年7月13日上午,广东江门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宣布取消中核集团鹤山龙湾工业园核燃料厂项目,对该项目不予立项。至此,纷扰了一周时间的江门‘核风波’事件最终以民意的胜利而告终。”[11]“散步维权”不仅在江门,也不限于只与“核”有关,建变电站、建化工厂都会引发“散步维权”。与“散步维权”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目前来看对“散步文化”的研究还不太充分;散步者的心态、思想、言行举止的描写在文学天地里还付之阙如;媒体所讲的故事也存在不少的偏颇,建设性明显不足。
三、荒政书写的新细节
政府书写、媒体书写、文学书写、文化研究都必须注重细节经营。有了细节,政府书写就有着力点;媒体讲故事,才能具体生动形象;文学书写才能使其笔下的形象丰满、灵动;荒政文化研究才不凌空务虚。首先,荒政书写的细节要具有科学化、精细化理念。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荒政书写提供了空前强大的支撑力,这也是当代荒政书写不同于以往的最大辨异所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加快了荒政书写的升级换代。科学思维有助于找到最优的应对路径与方法,从而将生命财产的损失降至最低、将社会恐慌与振荡降至最小。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有助于提高预见性、针对性、前瞻性,从而使荒政书写的绩效事半功倍。这一方面,文学书写大有可为。因为,文学与科学的联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充分、具体。写好与科学有关的细节,正是文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进路。比如广东为提高公众和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意识与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策划创意了“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活动。这些活动背后肯定有不少精彩的故事,通过报道和讲述,“事故”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了。其次,荒政书写的细节要渗透协同理念。其一,救荒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部门的单打独斗都会力不从心,一定要打组合拳方能奏效。这些故事讲好了就是“为生民立命”。其二,制度化、体系化、全民化。有制度才能构建荒政书写的长效机制,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全民化之所以重要,皆因为荒政的服务主体是全民,如果荒政书写质量低下,受害、受损、受伤的当然是绝大多数民众,因此发动他们参与荒政书写,是救人自救的题中之义。互联网时代的“全民记者”“全民报道”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可能。再次,荒政书写细节要坚持创新理念。广东经济发达,现代保险业也较为发达。促进广东保险业服务广东省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保险业防灾减损和经济补偿的能力,广东大有可为。比如,完善灾前预防、灾中减损、灾后补偿的保险服务机制;开创涉灾险种藉以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探索创立台风海啸等巨灾风险的指数保险制度;开展公众聚集场所责任保险试点;创设暴恐险种等,广东具备善做善成的基本条件。如何使这些素材与理念走进各类书写的中心,考验着新时代广东荒政书写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赫治清:《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2][8][9]梁必骐:《广东的自然灾害》,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2、227页。
[3]林捷兴:《禁摩限电陷入困境完善规划禁不如管》,《深圳特区报》2015年4月28日。
[4][6][7]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87、93、137页。
[5]曹斯、林亚茗:《新技术助力阻断广东“地方病”》,《南方日报》2011年10月24日。
[10]刘特培、秦乃岗等:《阳江Ms4.9地震活动特征、影响场及应急对策》,《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2005年第6期。
[11]王小明:《广东江门“核”危机》,《中国经营报》2013年7月20日。
责任编辑:王冰
政法社会学
作者简介张永璟,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