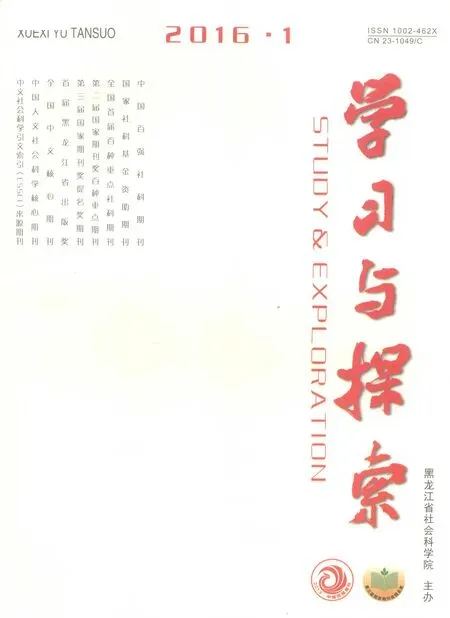从“意识形态高浮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
2016-02-27赵学存
赵 学 存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合肥 230601)
从“意识形态高浮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
赵学存1,2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合肥 230601)
摘要:朱光潜在1979年提出的“意识形态高浮论”下启20世纪80年代初由钱中文、童庆炳等主张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文论生成的重要源头之一,推动了对文学性质的科学认识。但是把文学的基本特性与意识形态相关联,仍然限制了这一话题的更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朱光潜;“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20世纪80年代;审美文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一直是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它生成于新时期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就其思想脉络看,朱光潜提出的“意识形态高浮论”倒是它的理论前身,为它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理论方法。揭示“意识形态高浮论”的生成与影响,分析它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在联系,就是为了更好地清理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文论建设的正反经验。
一
20世纪50—70年代,文艺被统一地认为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功利化的文艺观,被极端地发展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社会各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长期以来形成的极“左”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明确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1]。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学界开始讨论“异化”“人道主义”“人性论”“美的规律”等问题。受其影响,文艺界开始讨论“共同美”“形象思维”等问题,并以“审美”“为文艺正名”。在这些讨论中,朱光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他主张的“意识形态高浮论”,经理论界争论反思,主张让文艺脱离上层建筑,并与政治拉开距离,从而启发人们探讨文学的自性问题。
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的基本内涵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但它们又是不同的因素,不能将它们画等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存在,而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精神意识,具有虚幻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层建筑比起意识形态来距离经济基础远较邻近,对基础所起的反作用也远较直接,远较强有力。”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2]。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朱光潜研究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总纲,发现译文与原文有出入。译文是: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3]
朱光潜认为:“按原文直译,不致产生上层建筑等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只适应上层建筑的之类误解,原文‘现实基础’是放在前面作为‘经济结构’的同位语,而译文把它挪至句尾,‘与之相适应’的‘之’字,依中文代词少有放在所代之前的习惯,就有可能被认为代上文‘上层建筑’,而实际上‘之’字仍是代‘现实基础’的。”[3]因此,他建议将译文中“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改译为:“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在这基础上竖立着上层建筑,与这基础相适应的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3]
其实,原译文的“之”代指它前面的“其”即经济结构。从语法和语感来说,原译文的意思与朱光潜改译后的意思是一致的。这里,朱光潜意在指出由于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解而产生的一个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适应上层建筑。它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从属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理论基础。而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并不决定于上层建筑。
在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上层建筑不等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决定于上层建筑时,朱光潜引用了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引用了恩格斯在给施米特的信中称意识形态为“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的话。可见,朱光潜绑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让意识形态“高浮在空中”。他不仅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而且让意识形态高浮于“社会存在”的上空,这样的理论用意,就是要为意识形态松绑,将其从依附于上层建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文艺从政治的笼罩下解放出来。
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的思想渊源是其前期提倡的文艺审美本性观。他曾认为,“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4]。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孟实文钞》到40年代末的《谈文学》以及《文学杂志》的“编辑后记”等文中,关于“趣味”的主张可视为朱光潜文艺审美本性观的具体内涵。“趣味”即“诗性的佳妙”,是人的内心生活、情感、社会真相通过诗人、艺术家点铁成金的眼睛自然地呈现出来的,给人以新奇或深厚的回味[5]。夏中义教授细审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的《后记》,指出:“不难确认朱所心仪的京派趣味,实是一种有厚度的审美回味。”[6]钱念孙研究员也认为,所谓“纯正的文学趣味”就是“对作品艺术性的尊重”[7]。以这种“纯正的趣味”为标准,朱光潜严肃而辛辣地批评了当时文学十个方面的“低级趣味”。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无艺术性的“口号教条”趣味。朱光潜强调文艺不可作为宣传工具:其一,文艺以创造“一种合理慰情的意象世界”为目的,它本身没有其他目的,如果有其他目的闯入,这与文艺自身没有关系。因此,“文艺在创作与欣赏中都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文艺有自身存在的理由,“不是任何其他活动的奴属”[8]56。其二,艺术创造的“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目的与要教训人的“道德的或实用”目的不可合二为一,创作、欣赏都必须聚精会神,“顾到教训就顾不到艺术,顾到艺术也就顾不到教训”。在文学史上,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挥极深刻的教育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在开始创作时就设定这个教训的目的,“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8]56-57。其三,“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朱光潜并不反对宣传,但他深刻地认识到拿文艺作宣传工具会使人由厌恶宣传所采用的形式因而厌恶所宣传的主张。
朱光潜6岁起接受过十年的私塾教育,不过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其中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以至于使他形成了一种人生哲学,即“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业”。在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期间,朱光潜深受西方美学资源的影响,如康德“无所为而为”(朱光潜语,即审美无功利)的美学观、叔本华的艺术解脱观、尼采的日神精神、布洛的“距离说”、克罗齐的直觉理论等等。正是吸收了这些美学思想,朱光潜才反对文艺工具论,坚持文艺审美本性观。
尽管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只是以区别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来松动政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几乎是对“禁区”的挑战。此论一出,引起不小的争论,有反对的、有反思的、也有声援的。
这些争论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朱光潜的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理论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原典是矛盾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第二,虽然朱光潜的理论有问题,但他提出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启发人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的不同,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它表现得缓慢而又有延续性。第三,声援者受到朱光潜的启发,认为文艺、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像“天上的云霞虹霓与大地的关系”,前者是已经超出了上层建筑的“天上的云霓”。
考察朱光潜与“商榷”者们的文献,可以感到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的用意是要将文艺的上层建筑性的固守扭转向文艺的自性的探讨。因为只有从自性的角度来看文艺(或其他思想意识),它(或它们)才不是上层建筑,其实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它们自身。否则,从马克思的文艺的社会结构功能角度看文艺(或其他思想意识),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所显示的那样,它(或它们)一定是意识形态,并属于上层建筑。而朱光潜恰恰就从自性的角度考察到意识形态(文艺或其他思想意识)不是上层建筑,又到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去找对结论有利的相关表述。结果,“商榷”者们一对照原典就逮住了他的错。需要说明的是,主张文艺的审美自性观,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上层建筑观,只是两者考察文艺性质的角度不同。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即使朱光潜想表达他的文艺审美本性观,也要顾及自己的主张与原典是否一致。
这场争论让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及其措施相比的独特性。随着争论的深入,“上层建筑”这一概念“逐渐地从文学理论术语中淡出了,与之相反,‘意识形态’概念则在文学理论术语中得以继续保留”[9]145。
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论的“审美”建设似乎是沿着两条路起步的,一条是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从上层建筑中区分出意识形态,并让它高浮,为归属意识形态的文学从政治那里松绑;另一条是沿着“共同美讨论——形象思维讨论——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进行讨论[10]。前者到达“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后者到达“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此时,一个简明的文学定义呼之欲出。在此基础上,钱中文明确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后来,童庆炳等学者也加入其中进行阐释和传播,也有不少学者表示质疑与反对,审美文论研究至此达到一个小高潮。
1982年,钱中文先生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11]。钱中文指出在多种文艺意识形态论中,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并对审美反映作了阐释:与一般的反映不同,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现实进入审美反映,就成为审美的心理现实;审美反映与表现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审美反映的丰富性在于它的具体性和主观性,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12]。他认为审美反映与哲学反映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特殊的反映,而“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特性在于“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3]。钱中文还系统地阐释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他指出:
文学观念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分成多个层次,各层次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因而形成文学观念的多本质性,文学概念整体不是各层次本质的相加;从社会文化系统来观察文学,把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的第一层次本质特性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并进一步强调文学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结合的结果,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由此,文学以情感为中心,又是情感和思想认识的结合;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有目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有阶级性,但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全人类性;是“审美意识的形态”[14]。
此后,钱中文就文学的各层次本质又进行了界定与阐释:文学的第一层次本质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第二层次本质体现在文学的存在形式上,如语言结构、创造与再创造中的本体论问题;第三层次本质指文学本体的发展,如语言、题材、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创作流派等等[15]。
童庆炳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始就从审美的角度探讨文学的属性了。1983 年,他在论文《文学与审美》中提出审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文学以审美价值为主,同时融合其他功利价值;文学题材富于诗意,文学真实是诗意的真实,文学典型浓缩了审美价值;文学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的审美把握:以情感为基本自由元素,来融合感知、表象、想象、理解等心理因素的过程。随后,他又提出“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文学的基本特征”[16]。
在此基础上,童庆炳于1992年开始,在其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中一直将“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加以阐释与传播。他所主张的“审美意识形态”与钱中文的内涵大体一致,但有所不同:其一,审美意识形态是与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平等相处的,它是独立整一的,并非“审美”和“意识形态”相加而成的“审美的意识形态”[17];其二,“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教育的、道德的、宗教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可以溶解于审美意识形态中,正是由于这一点文学才是无比广阔与自由的[18]。
至此,我们可以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基本内涵概括如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的特殊性在于其审美性;因此文学的属性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融合的结果。但是,细审“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论述,我们会发现,论者循着70年代末以来的“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明显倾向于“审美”而淡化“意识形态”。他们或特别强调审美反映与一般反映的区别,或将“审美意识形态”淡化为“审美意识的形态”,或将“意识形态”模糊为一般思想的、精神的形式;在承认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时,不仅同时强调其审美性,而且提出文学本质是多层次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只是其第一层次本质;“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第一原理”的前提是其内涵的独立性、整一性特征,而且这一原理并不影响文学其他观念的有效性;政治、道德、历史、宗教等因素是通过“审美意识形态”的融合才能走进文学的。因此,有争论者认为“审美意识形态”对“审美性”的过于强调,导致“意识形态性”成了空虚的点缀[9]163。
这种“名不副其实”的做法,可从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那里找到示范:朱光潜一方面明确在不否认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把两者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却意在把意识形态从上层建筑中拨出来,让它与上层建筑平行,甚至要它成为“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高浮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在80年代复杂的语境中,它们都在强调文学的特殊的自性方面做努力。“意识形态高浮论”诞生于“为文艺正名”的开端阶段,它针对“文学是上层建筑”“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否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让人们明白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努力从理论基础的层面否定“工具论”“从属论”。这样,到1982年的时候,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具有特殊性”“文学是以审美的形象反映生活”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共识的前提下,“审美意识形态论”水到渠成地诞生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除钱中文、童庆炳二先生外,还有王元骧等其他一些学者。他们接着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努力地阐释,使新时期文学审美论得以丰富,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进而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文学的本质问题。
但是,今天来看,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为文艺从政治那里松绑,这是它的功绩,但它将文学不证自明地默认为意识形态,这实际上也束缚了人们对文学自性的进一步认识。“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偏正短语,其重心落在了“意识形态”上,“审美”成了一种修饰,“意识形态”就会占领“审美”。“意识形态高浮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质疑:“文学是意识形态吗?”因为意识形态是与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含文学)的倾向性形态,极端情况下,它可使思想意识(含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革”后,人们对意识形态有了厌烦甚至恐惧的心理,将文学审美本性与意识形态挂起钩来,尽管用审美来限定或修饰它,其结果与文学审美本性的差距还是不小的。由此可见,不脱离意识形态来寻求、定义文学的自性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共同的不足之处。
三
之所以说不脱离意识形态来定义文学的自性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不足之处,原因有三:其一,把马克思关于文艺在社会结构系统中是意识形态的表述作为文艺本性观;其二,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即“阶级功利性”的专有名词,用它来定义文学本性不符合文学存在的事实;其三,它有可能使意识形态“占领”审美,有可能使文学再度沦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
“审美意识形态”论者强调这一概念的整一性、兼容性,意在说明组成这一概念的两个部分(即“审美”和“意识形态”)组合起来,经过阐释,并不矛盾。然而,这似乎不是文艺意识形论的主要问题。它的主要问题是对马克思关于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的误解。周忠厚教授考察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法汉词典》,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沿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兰西院士德斯图·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ologie)一词的原义: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并具有政治意图和阶级性的思想体系[19]。而在马克思原典的一些论述中并未完全将文学艺术作品排斥在意识形态之外而专指理论思想体系。例如,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明显与上一句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相对举,这里的意识形态应该既包含思想理论体系,也包含文学艺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如思想体系),而是一个被赋予“阶级自觉性”内涵的专用名词,专门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语义场”,来解释意识的阶级自觉性在阻碍或促进社会形态更新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简明地解释为“意识的阶级性形态”。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0]。
这段话论述了一个社会形态变革更新时,其物质方面和意识方面的变动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物质方面的变化是明确的,而社会意识会“克服”这种革新。因此,“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为了标示这种意识 “克服”革新的阶级自觉性,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即意识的阶级性形态。而社会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都是这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形式”就是指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各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如法律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意识、艺术想象、哲学思想等等。同理,我们可以解释《序言》中另一处的疑惑。“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为什么用“社会意识形式”而不用“意识形态”?那是因为在“社会意识形式”后面有“与之相适应”这个说明,说明了“社会意识形式”的阶级自觉性,这样达到了与用“意识形态”相同的表达效果。
可见,马克思关于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意识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意在阐明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阶级斗争中,这些思想意识成了影响这一进程的力量。它们表现为意识的阶级性形态,马克思用“意识形态”指称它们。至于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思想意识的本性是什么、定义是什么的问题,不是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文艺意识形态论的主要问题是对马克思关于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表述的误解。这就如同在特殊境况下菜刀可以成为武器、但我们却不能说菜刀原本就是武器一样。
一(或一类)事物的本性即本质属性是该事物存在的依据,也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征。本性可以不是某事物的唯一的、独有的性质,但却是它必须具有的性质。马克思意识形态特别强调“阶级性和阶级自觉性”[19]。众所周知,文学的阶级性不是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比如在阶级尚未产生或阶级意识尚未自觉的社会形态中的那些歌谣、神话是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性的;同一时期内,也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充满意识形态性。规定文学的本性是意识形态或以意识形态为文艺下定义,这不符合文学存在的事实,也将文学缩小到一个狭小的境地了。
我们说文学的本性是审美,这便是说文学可以具有多种性质,其他事物也可以具有审美性,但是审美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性质。除审美性外,文学的其他性质并不构成决定文学能否成为文学的依据。否则,它就变成了非文学的其他事物了。人们常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形式,艺术即指其诗意的审美性。文学的审美性通常是指康德主张的“无功利性”,即非物质占有性、非道德伦理性、非理智认识性等,其内涵是以文学技能创造出语言形式、文学形象来表达情绪、情感或趣味从而满足人们对无功利的、诗意的精神体验的需要。值得说明的是,文学的审美性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植根于无所不包的世界里而生长出的动人的花朵。因此,文学必然富有审美之外的其他性质,但是,这些其他性质不是所有历史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具有的,唯有审美性符合这个条件。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代,一些作品中强烈的爱恨情仇的情感体验简直就是对阶级敌人的控诉与审判,这些作品成了意识的阶级斗争形态,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这是文学不期然而然地成了意识形态,并非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即使文学被利用成意识形态工具,其“利用的价值”还是它的审美本性。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文学定义,给我们的困惑是文学既然是自觉地捍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式,那么它如何同时又是无利害的审美体验?就文学本性来说,审美和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进一步看,正因两者是对立的,在特殊时代里,意识形态才会以它神圣的使命和强大的威力占领审美,使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工具论被不断强化,直至“文革”时期到达极端的程度。而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极左思潮被否定、语境发生重大变化后,“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才先后出现。但是,80年代的语境与50—70年代的语境之间的关系并非彻底“断裂”。1949年以来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济基础没有变,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结构中各要素对其的适应,从根本上说也没有变。也就是说,80年代政治对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思想文化界的规训并非完全放任。政治上的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指向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这些与思想文化界期望的人性、人道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民主,有很大出入。一旦思想越过意识形态底线,政治的控制之手便显示出来,从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可见一斑。但两者在批判、反拨“文革”意识形态及长期以来的极左思维模式方面达成高度的“共识”,在此“共识”下许多问题得到拨乱反正,诸如人性、人道主义、共同美、形象思维、文艺审美性等等得以顺利讨论,并且有的还得到承认。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这个“共识”使得20世纪80年代政治对思想文化的规训方式与之前相比显示出更多的隐蔽性特点。这种规训方式不是用20世纪50—70年代时所采用的开批斗会、投监狱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体制内”引导,还有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认同”方式:“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并非通过外在的控制而是通过内在‘认同’来实现的”[21]。
正是在如此复杂的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下,从“意识形态高浮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尽管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进展,特别是文学的审美性得到广泛共识,但“意识形态”却是文艺理论界无法逾越的思维定势。就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内涵来说,说文艺是意识形态与说文艺是上层建筑,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两者都不是从文艺的本性来定义文学的。从“意识形态高浮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学人们为寻求与定义文学的审美本性做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意识形态”概念来寻求或定义文学的审美本性,其适宜性值得推敲与反思。“意识形态高浮论”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和方法的源头,它们对审美论的贡献与束缚是相通的。这是80年代特殊而又复杂的语境使然。我们揭示“意识形态高浮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在联系及其生存语境,目的在于清理与反思80年代文论建设的正反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3.
[2]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
[3]朱光潜.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J].文学评论,1978,(4).
[4]朱光潜.无言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5]朱光潜 .孟实文钞[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9-23.
[6]夏中义.朱光潜美学十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9.
[7]钱念孙.朱光潜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5).
[8]朱光潜.谈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董学文.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赵学存.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论的确立途径[J].合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11]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J].文学评论,1982,(6).
[12]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J].文学评论,1984,(6).
[13]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J].文艺理论研究,1986,(4).
[14]钱中文.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J].文艺理论研究,1987,(6).
[15]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3-136.
[16]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5.
[17]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J].学术研究,2000,(1).
[18]童庆炳.怎样理解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教程》编著手札[J].中国大学教学,2004,(1).
[19]周忠厚.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83.
[21]李杨.重返八十年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
[责任编辑:修磊]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1-0140-06
作者简介:赵学存(1977—),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13BZW002)
收稿日期:2015-11-15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