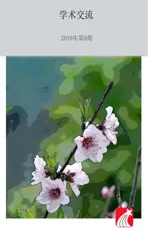儒学推己及人之可能、困境与未来走向
2016-02-27万勇华万光军
万勇华,万光军
(1.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2.山东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014)
中国哲学研究
儒学推己及人之可能、困境与未来走向
万勇华1,万光军2
(1.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2.山东政法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014)
推己及人是儒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体方面,是君子在推,前提是自觉认同群体、努力维护群体。推己及人问题包括在性质上推与不推、及与不及,在内容上是推优还是推劣,在方向上是顺推还是逆推,在方式上是平等推还是差等推。儒学十分重视推己及人,作了多方面的理论思考和现实努力。相对于墨家的视人如己和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而言,儒学中的推己及人需要在逆推上加以扩展,在平等推甚至优等推上加以提升。
儒学;推己及人;可能;困境;未来走向
推己及人,俗称将心比心,乃是儒学关注的重要话题。那么,儒学推己及人如何可能?它面临哪些困境?其未来走向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分析。
一、儒学推己及人之可能
在儒学推己及人中,既有己又有人,既讲自己又顾他人群体,体现了一种自觉认同群体、积极维护群体的立场。但进一步追问谁在推己及人、为何推己及人、如何推己及人,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谁在推己及人?显然是君子在推己及人,主体是君子。君子之所以推己及人,是因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有道义担当,有自觉使命,积极主动地把自己与群体结合起来。自孔子开始,儒学君子就一贯重视群体(同群、同类),随之就对推己及人加以重视,如孔子讲:“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 至于孔子讲君子不仅要“修己以敬”还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孟子讲“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和“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国语·晋语一》讲一般人(为仁者)“爱亲之谓仁”而君子(为国者)“利国之谓仁”,显然都认为君子要有更大视野,承担更大责任。相对于君子,小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人人都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群体,只会争不会让,甚至不择手段、不顾道义,因而不会有真正的推己及人。可见:能自觉认同推己及人、真诚做到推己及人,就是有道君子;有道君子不仅修己,还积极倡导建构有序和谐的良性社会,也就必须注重推己及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推己及人的主体一开始主要是君子,泛化之后也指向一般人。从君子应该做到、能够做到,到一般人应该做到、做不到不可以,体现了道德的泛化和强化,体现了儒学影响的扩大和对和谐融洽社会的共同期盼。
儒学不但认同应该推己及人,在如何推己及人上也作了多方面考察:
首先,在性质上,推己及人包括推与不推、及与不及。在儒学这里,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其中的立人、达人、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是一种推,也是一种及,是应该推、愿意推、能够推的统一体,也是应该及、愿意及、希望及的组合体。当然,愿意及与能否及并不完全等同,需要继续思考。
其次,在内容上,推己及人是推优、推善而不是推劣、推恶。儒学推己及人默认的主体是君子,君子的最大优势就是道德操守,君子推己及人就是推其善。孔子讲立人、达人,孟子讲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展现的是主体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一种与人为善。孟子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公孙丑上》),希望人人都将这些善端扩充推广。孟子还区分不为与不能(《孟子·梁惠王上》)、自暴与自弃(《孟子·离娄上》),目的也是告诫人们应当为善、必须为善。可见,儒学最终以性善论为其主流立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推己及人、推优推善的实质就是性善的多维呈现与不断践行。相反,法家虽也在一定程度上讲推己及人,但往往注重主体自我的恶劣品质,难以与人为善,可谓推劣、推恶。法家往往只顾自己而不推人,为了顾己而全不顾人,人人互相利用而无尊重,互相提防而无信任。推优推善有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美好社会,推劣推恶则与这样的社会相去甚远。如果说推优推善是真正的推己及人,那么推劣推恶实质上不是真正的推己及人,至少在儒学看来是如此。可见真正的推己及人不但要推、要及,不能不推、不及,更要推优推善,不能推劣推恶。
需要指出的是,推优推善还涉及互动与反馈。孔子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讲:“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推优推善自然容易出现良性循环,而推劣推恶难免出现恶性循环。孟子区分了逢蒙与羿、庾公之斯与子濯孺子两案的不同结局,对于后者的以善相推欣赏有加。*《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中国文化中也有“要学管鲍分金,不学孙庞斗法”“冤家宜解不宜结”等说法。相比而言,儒学的推优推善很可能出现互谅互让甚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美好局面,而法家的推劣推恶难免面临请君入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尴尬。可见,无论是建立良性政治关系还是良好人际关系,推优推善都是首选。
再次,在方向上,推己及人是一种顺推而非逆推,是一种内推而非外推。推己及人是由己及人,由内及外,考虑到了人的自然之性,注意到了自觉与自愿,使得愿推与能推相结合,使之易于理解、易于接受,也易于推行。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论证了三年之丧的必要性,孟子称君主好货好色只要推而广之做到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就可以(《孟子·梁惠王下》),这就体现了儒学的顺推,顾及了每个人的自然因素,从而让人更容易接受。在此,顺是方向,也要加上性质。顺推既是一种顺,也是一种推;既是一种顺势而为,也是一种推优推善。儒学实质上讲的是顺优而推、顺善而推,不是顺劣而推、顺恶而推;或者说,若是劣、恶,则要节制、返归,例如荀子讲人性恶、好利疾恶,顺势会出现种种局限,于是就要“化性”。换言之,儒学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推的,而对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不推,例如孔子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卫灵公》),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就分欲与不欲、善与不善,有所选择而非一概相推。
最后,在方式上,推己及人涉及平等推与差等推。一方面,在理论上,推己及人中的己与人当然是同类,“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因此,推、类、类推、类比、推比等所体现的应是平等。《诗经·伐柯》讲“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彰显的都是平等;即便《大学》倡导的“絜矩之道”*《礼记·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使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也是平等。这种平等在学习上有所反映,如孔子讲“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后生可畏”(《论语·子罕》),韩愈《师说》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更典型地反映在人格问题上,如孟子讲“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讲“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儒学又出现了明显的差等推。典型的如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其中亲亲、仁民、爱物的差等顺序显而易见。又如,针对墨家人人都需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点,孟子偏偏区分劳心与劳力,辩称劳心者不劳动是合理的:“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伦理上,儒学也有“三亲不断”,如郭店竹简《六德》:“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制度上,分封因血缘亲疏、功劳大小等而有差别等级,还出现了差等的推恩令。外交上,经常推行远交近攻。可以说,差等推有一定基础和根据,但也存在一定争议。
二、儒学推己及人之困境
儒学由君子修身出发,力图建立由己及天下的有序和谐的美好社会,因此十分重视推己及人。当然,推己及人作为重要论题,涉及面众多,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推己及人是自然本能还是社会道义?推己及人应该是平等推还是差等推?推己及人应该是顺推还是逆推?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会使儒学更上一层楼,解决不好会使儒学面临困境。
(一)推己及人是自然本能还是社会道义
推己及人实际上是推其仁爱之心,是一种仁爱之推。这种仁爱之推本质上是自然本能还是社会道义,其实就是它本质上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有分梳的必要,但分梳清楚并不容易。一方面,应当承认仁爱之推在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有一定的联系(重合与交叉),即便是对出于本能的仁爱之推,也应肯定这种联系。如,孟子所讲人无条件地救孺子之举动,虽然不易分清到底是出于自然本能还是社会道义,但此举动本身无疑值得表扬。本能之爱具有普遍有、永远有、必然有、当下有等特点,与文明道德的要求相符合、相重叠,这是其值得肯定之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仁爱之推本质上不是自然本能,而是一种社会道义,是一种对自然本能的超越。自然本能之仁爱不能说是不爱,但有可能是蒙昧之爱、狭隘之爱、有限之爱;社会道义之爱则是文明之爱、大度之爱、博大之爱。如农村老人在孙子生病时可能会求助于巫婆而非医院,这一仁爱不能说是不爱,却是蒙昧之爱而非文明之爱。而孔子讲的仁,乃是包含知的仁。*《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语:“未知,焉得仁?”按:此语另有其他解法。孔子还讲,君子(仁者)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论语·雍也》),这也涉及文明。《孟子·告子上》里,孟子与告子在仁义内在与仁内义外上有明显分歧:告子“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主张仁内义外,是一种自然狭隘之爱;孟子“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主张仁义内在,是一种社会大度之爱,即对自己弟弟和他人弟弟都应爱。告子只爱与自己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亲人,似乎无可厚非;而孟子主张与自己无自然血缘关系的人也应去爱,显然更为可取。孟子的仁爱属于社会大爱,显然胜过告子的自然狭隘之爱。在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我们还可以比较易牙蒸子与《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易子救孤。易牙蒸子以献,齐桓公以为忠臣,而管仲以为,“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史记·齐太公世家》),不合人情、不值得信任;程婴易子救孤,难能可贵,世人以为美德。究其理:易牙可以不献,程婴不得不献;易牙为自己,程婴为他人;易牙为功利,程婴为道义;易牙违反自然性,程婴超越自然性;违反自然性也不符合社会性,超越自然性则维护了社会性。如果仅仅立足自然性,则程婴之举难以成立;而如果超越自然性,则程婴之举受到肯定赞美实属必然。综言之,推己及人是推仁爱、是大爱,它虽与自然性有一定联系,但是本质上应属社会性。立足自然性而不断向社会性超越应属题中之意,局限于自然性而不向社会性超越则难免出现不足。
(二)推己及人应该是平等推还是差等推
形式上,推己及人就是将心比心;理论上,推己及人就是类推,其所蕴含的都应是平等推。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事实上、在现实中出现了差等推,出现了平等推与差等推并存、甚至差等推逐渐压倒平等推的尴尬局面。这种尴尬局面在孔子那里还不明显*《论语·宪问》中孔子所讲修己—安人—安百姓是范围的扩大,并未涉及程度的递减。另,《论语·雍也》中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博而非薄,是广博而非摊薄。又,孔子对儿子与学生一视同仁。这引得陈亢大为敬佩——《论语·季氏》:“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远其子”当然不是疏远儿子,而是平等对待学生与儿子,不偏私。这种态度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总会受到人们的敬佩。,在孟子这里就十分明显。孟子在理论上、形式上讲过平等推,如“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但在现实中、在事实上出现了很多差等推,如亲亲—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同室斗而救、邻人斗不救(《孟子·离娄下》),“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万章上》)。不仅如此,孟子的差等推还在理论上、范畴上有所表现,即出现了两种本——本源之本与本末之本。[1]《孟子·离娄下》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告子下》云:“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显然,前者是本源之本,后者是本末之本。前者重视源而不忽视流,可以说是沟通源与流;后者重视本,难免忽视末,可以说是重本而轻末。就推己及人而言,把自己理解为本似乎不成问题,而把他人、集体置于本源之本还是本末之本后面则会出现明显不同的局面:自己是源,他人、集体是流,当然要努力融合二者,这显然是一种平等推;自己是本,他人、集体是末,则顾己不顾他人、集体似乎理所当然,这显然是一种差等推。本源之本、平等推会维护集体,本末之本、差等推难免削弱集体。儒学要维护集体,就应倡导平等推、本源之本,慎言差等推、本末之本,谨慎对待由平等推向差等推的过渡,避免差等推压倒平等推之尴尬。与之相关,儒学中平等推与差等推并存、过渡的局面在儒学内部似未引起足够重视,但在外面遇到坚决倡导平等、反对差等的墨家时就出现了轩然大波。墨家倡导兼爱,是一种绝对平等,反对交相别是反对差等。客观而论,墨家以兼爱取代交相别,以平等取代差等,的确是提出了尖锐问题,的确看到了儒学的困境。这一问题和困境,儒学(尤其是孟子)回应起来难以镇定从容,即便是呵斥辱骂(“无父”“禽兽”)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儒学中还有另一种差等,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孔子那里就是克己。克己是克制、节制自己,即严以律己;不是克制、节制别人,而是宽容、厚待别人,即宽以待人。比如面临别人的无端指责,孔子是“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孟子则是三次反省后反击*《孟子·离娄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不难看出,面临无端指责,孔子是内省而不反击,可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孟子是内省后去反击,近乎严以律己、严以律人。因此,孔子是谦谦君子,人际关系相对缓和,而孟子是严峻大丈夫,人际关系相对紧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是平等,而是差等,但这种差等不是常规的对自己宽容、对别人严格的差等,而可谓超常规的差等,它在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努力缓和人际关系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推己及人应该是顺推还是逆推
一般而言,儒学的推己及人由己及人、由内而外,当然是顺推。顺推体现了自觉与自愿,既合情又合理,是应该推、能够推、愿意推的结合,容易操作和理解。因此,儒学主要采取顺推方式,推行时间长、范围广,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与此相对,墨家重视“视人如己”的逆推。墨子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不难看出,墨家视人如己是由人及我、由外而内,是逆推。儒学推己及人有时会出现差等推,墨家视人如己则绝对是平等推;儒学推己及人必然是身—家—国—天下的顺序,墨家则基本相反。推己及人与视人如己有同有异。其同在于都是以仁爱待人,推的都是仁爱,这与道家不推仁爱、法家推恶有原则性区别。其异在于:推己及人虽然体现了主体的自觉与自愿,合情又合理,还可能顾及了人的自然因素与现实因素,但难免有些想当然、自以为是,对他人难免有些忽略,方式难免有些简单,这时顺推有可能推不出去(推而不及人),再考虑到差等推推出去时有可能所剩不多,即有可能使儒学的推己及人在性质上终不成立、在数量上大打折扣;而视人如己虽然考虑自己,但首先考虑别人,虽然落实到内在自我,却是由外而内,体现的是更高程度的自觉,必然顾人容人,结局也更能真正落实,并且极有可能就是平等。
当然,全面理解推己及人还涉及“爱人如己”。在西方,基督教有着被视为“道德黄金律”的爱人如己之说,即“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12)。爱人如己所推的是爱(而非恶),与儒学推己及人相一致;其直接表明爱的主旨,亦与儒学推己及人相契合。但其方式是包含他人的逆推,与儒学忽略他人的顺推差别较大;而且是优等推(如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与儒学的差等推差别明显。爱人如己容易出现平等(甚至优等),这正是西方社会最终高度重视平等(使之与自由、博爱成为三大基本理念)的一个基础;推己及人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受制于差等、等级,也就影响社会向前向上的发展进程,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三、儒学推己及人的未来走向
从更广的视域看,道家讲个性、重自由,注意到了人与人的差异,故基本上不存在推己及人问题。杨朱只是自利而不利人,只顾自己而完全无视他人、集体,当然也就不会推己及人。法家在集体中看到了人的自私和现实利益的有限,以为人人如此、始终如此,因此其虽然关注推己及人,是顺推,但难免是推恶、推劣,是差等推。墨家在集体中看到了差别、分别的局限,因此极力主张平等推;看到了由己及人顺推的尴尬,因此倡导视人如己之逆推。
与道家相比,儒学推己及人更多地看到了人与人的相同性或相通性;与杨朱相比,儒学推己及人体现了正视他人、维护集体的积极立场;与法家相比,儒学推己及人强调人的自觉自愿,它是推优推善,力图建立和谐融洽的美好社会;与墨家相比,儒学的顺推与差等推在现实中推行起来更为容易。
当然,儒学推己及人并非十全十美,仍有扩展、提升的必要。其一,就扩展而言,应当在坚持顺推的同时强调逆推。儒学在顺推上已经讲得很多、做得很多,接下来需要对逆推多加关注和推行。顺推、逆推都是推己及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只侧重其中某一方面,会使儒学推己及人存在缺陷,难以完全实现人我之间的平等,无法推动人我之间的协调发展。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儒学推己及人更加完备,真正实现人我平等,促进人我共同发展。其二,就提升而言,应当在差等推的基础上向平等推甚至优等推靠拢,努力实现从以差等推为主到以平等推甚至优等推为主的转变。这可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其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儒学差等推虽然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根据,但在现实中容易出现偏差,比如推出去时所剩不多、推些残羹冷炙还自以为义,而与之相反,墨家视人如己的平等推和基督教爱人如己的优等推体现了主体的高度自觉,显示了对于他人的无比尊重,因而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许在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差等推的局限性尚不明显,因而优等推似乎不重要;但在社会发展异常迅速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差等推的不足就暴露无遗,因而优等推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人们都采用优待别人、优推别人的方式从事生产和服务,那么精品意识、效率意识就会产生,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
总之,儒学推己及人要想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须与时俱进,逐步扩展,不断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1]万光军.本源之本与本末之本:儒学群己伦理的两重向度[J].道德与文明,2011,(1):90-94.
〔责任编辑:余明全〕
2016-03-13
教育部2015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项目“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研究”
万勇华(1977-),男,安徽芜湖人,讲师,博士,从事道家思想研究;万光军(1973-),男,山东新泰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儒家思想研究。
B222;B82
A
1000-8284(2016)09-00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