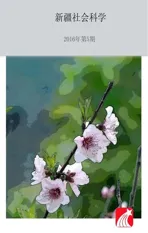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格局及伊斯兰教在该国的未来走势
2016-02-26艾山江阿不力孜地木拉提奥迈尔
艾山江·阿不力孜 地木拉提·奥迈尔
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格局及伊斯兰教在该国的未来走势
艾山江·阿不力孜 地木拉提·奥迈尔
文章结合国内外吉尔吉斯斯坦宗教趋势的研究资料,从其宗教格局现状、伊斯兰教发展的回顾与经验启示、独立之后伊斯兰教发展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当前伊斯兰教走势受宗教极端组织的影响和渗透,呈现正统与极端、正教与邪教、传统与异化交织并存的复杂局面。
吉尔吉斯斯坦 宗教格局 伊斯兰教 俄罗斯文化
一、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格局
吉尔吉斯斯坦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主体民族为吉尔吉斯族;人口较多的民族依次为乌兹别克、俄罗斯、乌克兰,而人口较少的民族依次为东干、哈萨克、塔吉克、维吾尔、朝鲜等民族。目前,由80多个民族组成的吉尔吉斯斯坦多民族布局形成了多重宗教并存的格局,境内伊斯兰教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直到2009年,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在逐年上升。*2001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另据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的统计数字,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人口2009年为473.04万人,占吉国总人口的86.3%,比2001年上升了6.3%;其中世俗穆斯林(just muslim)为64%,坚守逊尼派哈乃斐教派的穆斯林22.3%。到了2012年,穆斯林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Pew Research Center,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October 2009.另有报告显示,2012年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人口为83%,*Kyrgyz Republic 2012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1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比2009年下降了3%。据吉尔吉斯斯坦学者引述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吉国穆斯林人口2013~2015年又急剧上升至90%左右。*苏来曼·卡伊托夫:《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现状》(学术报告),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部资料),2015年11月18日。
另外,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宗教信徒。数据显示,基督教是吉国第二大宗教,信教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5%,近一半人自认归属于东正教;其中,基督教新教徒约为1.1万人,分别归属于浸礼会社团(48家)、路德宗社团(21家)、五旬节社团(49家)、长老会社团(35家)、灵恩堂社团(43家)、基督复临安息日教社团(30家);此外还有耶和华见证人教信徒约0.48万人、罗马天主教信徒约0.12万人。*Kyrgyz Republic 2012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除基督教外,犹太教信徒约为0.15万人,佛教徒约0.1万人,巴哈伊教信徒约300人。2011年,吉国境内正式注册的宗教组织达2 200所,*张宁:《吉尔吉斯斯坦宗教管理体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其中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占86%、基督教宗教组织占9.8%、其他宗教组织占4.2%。
从上述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格局的统计资料看,伊斯兰教在其独立前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直接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宗教的总体发展趋势。
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回顾
1.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族中的本土适应
16~18世纪,受当时蒙兀儿汗国强行推动的伊斯兰教及其社会文化的冲击,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吉尔吉斯族各部落先后皈依伊斯兰教。此时伊斯兰教及其基本宗教礼仪逐步渗透到吉尔吉斯族上层社会生活中,同时也成为其统治下层牧民的有效工具之一。然而,吉尔吉斯族千百年来奉行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文化并没有因为伊斯兰教的传入而消失,相反伊斯兰教在与游牧部落社会生活及信仰体系的对话中逐渐展现出融入游牧社会的属性,无论是吉尔吉斯族在18世纪中亚境内的迁移中、还是在19世纪乌兹别克人建立的浩罕汗国强力推行的伊斯兰教进程中,都未能从本质上取缔吉尔吉斯族的萨满文化信仰习俗及社会文化礼仪。可以说,吉国境内的伊斯兰教本土化历程显现出其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多重信仰空间,同时也定型了当代吉尔吉斯族文化记忆的多种信仰模式。也正是这一牢固的民众基础和“防御体系”使得伊斯兰教在近代吉尔吉斯族的文化适应中不得不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发展态势。可以说,直到20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族的全面融入也从表面上呈现出外在的伊斯兰教和内在的萨满文化并存的信仰模式,这一信仰模式在中亚游牧族群中传承已久,构成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地区的本土范式之一。
2.吉尔吉斯族伊斯兰教的俄罗斯文化烙印
1788年,沙俄统治者在奥伦堡建立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古兰经》俄文版的出版,等等,反映了沙俄统治者对伊斯兰教实行利用与控制的两手策略;*④ 田霞:《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研究》,200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6、7页。同时,沙俄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通过牧民迁移等方式对吉尔吉斯族精英群体灌输了俄罗斯工业文明理念,并产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化的工业文明理念和欧洲生活方式作为当时的文明范式,对吉尔吉斯族精英群体带来了很大冲击,从而推动了吉尔吉斯族从游牧步入工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为苏联时期的社会转型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
3.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族伊斯兰教信仰的“信仰真空”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穆斯林,特别是吉尔吉斯族,同其他民族一道先后经历了几次宗教信仰的“大扫除”。在“十月革命”初期,以列宁为核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大力推行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取消特权、民众组织形式存在的宗教合法性等一系列宗教政策:1917年12月发表《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1918年1月23日,又颁布了经列宁签署和修改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废除了沙俄时期的东正教特权,并把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规定写进了苏维埃宪法,④推进了苏维埃初期各种宗教的合法发展。列宁逝世以后,当时联盟中央对中亚宗教问题的态度发生了突变,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伊斯兰教都遭到了挤压,甚至被强行镇压。斯大林时期,由于过度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错误坚持“宗教在任何条件下只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绝对观点,*③④⑤⑥ 邓浩:《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世界民族》1997年第4期。导致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教受到了强行限制。1928~1941年卫国战争前夕,在苏联推行的“反伊斯兰运动”影响下,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的宗教组织被强行关闭、宗教活动严格受限、宗教人士严密监视。1940年,吉国境内只留下了90座清真寺。*艾来提·托洪巴依:《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在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战事需要,苏联中央政府针对中亚伊斯兰教群体的限制有所放松,一度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宗教群体成为“卫国同盟”,中亚穆斯林群体成为反抗法西斯战争的卫国同盟军,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中央掀起第二次反宗教运动(1959~1964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又一次受到重压,仅仅6年间清真寺几乎全被关闭。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65年,中亚等地的清真寺总共只剩下三四百座。③在这一次反宗教运动中,赫鲁晓夫执政的苏共中央不仅打击了伊斯兰教组织机构,而且还通过激进的方式大力宣传科学无神论,试图将伊斯兰教彻底消除。1963年4月,苏共在吉尔吉斯斯坦党组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反对宗教残余”,力图把一切宗教偏见、宗教迷信彻底铲除。④不仅如此,这一运动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便是盲目打击民间信仰习俗、过多干涉民俗生活,导致民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开斋节)、饮食习惯(清真食品)、封斋、麻扎崇拜等先后被限制或边缘化,这严重伤害了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民众的宗教感情和民俗情感,助长了民众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同时也为吉国穆斯林与执政群体之间的隔阂埋下了不良“种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赫鲁晓夫时期种下的不良“种子”开始发芽,呈现地下蔓延之势。原苏联虽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清真寺数量和伊斯兰教学校数目严格控制,但地下讲经点层出不穷,出现了当时所谓的“地下穆斯林”称谓。据统计,当时的中亚国家,地下秘密清真寺数量达到1 000多座。⑤虽然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对伊斯兰教的控制达到“最高境界”,然而吉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之早期形成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到1985年前后,民众对伊斯兰教的“回归”以及民族认同的重构心理达到了不可掩饰的地步。随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活动中,长期压抑的宗教情感和民族认同得以宣泄,到1989年前后,当时的不良“种子”已枝繁叶茂,形势已面临失控的局面。1990年9月,苏联政府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法》,使吉国地下宗教活动最终得以合法化。⑥在这一特殊时期,苏联的瓦解、苏共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导致了中亚国家意识形态出现“信仰真空”,使得伊斯兰教成为填补当时吉国穆斯林群体这一“真空”的首选信仰体系。
三、独立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发展特点
经历了苏联时代无神论教育和政教分离,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初就宣布建设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民主国家,也陆续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随着独立之初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民族传统文化振兴运动,各种境外宗教团体也纷纷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凭借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伊斯兰教信仰基础,加紧扩大势力版图。独立之后的25年间,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和机构剧增,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与非伊斯兰教宗教团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1.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和机构日益剧增
苏联时期受制于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穆夫提*伊斯兰教教职称谓,指教法说明官。统一管理的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独立之后(1993年)归属于吉国半官方性质的非盈利机构——穆斯林宗教管理局统一管理。该局由全国伊斯兰教团体组成,监督管理境内所有清真寺、伊斯兰教宗教学校、伊斯兰宗教人士、宗教印刷品和用品、组织宗教活动和朝觐等;*张宁:《吉尔吉斯斯坦宗教管理体制》。它的管理体系分为5级:依次为穆斯林大会(5年一届)、神学家和教法学家乌理玛委员会(5年任期)、州和市级伊斯兰教法执行官卡孜、主麻(周五聚礼日)清真寺负责人哈提甫和普通清真寺负责人伊玛目。据资料显示,1990年吉尔吉斯斯坦有清真寺39座、1999年上升为1 200座、*苏来曼·卡伊托夫:《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现状》。2003年增加为1 600座、2004年达到1 612座、*艾来提·托洪巴依:《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2007年增长为1 650座(正式注册的清真寺为1 623座)*Kyrgyzsta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Democracy.,截至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清真寺数量达到1 800座;2004年伊斯兰教宗教学校为48座、2015年增加到65座;截至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机构为10个*再米娜·伊力哈木:《近期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及影响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宗教法庭为9个。从吉尔吉斯斯坦宗教组织总数来看,到2012年底注册登记的宗教组织为2 397所,其中,1 913所为伊斯兰教宗教组织;*Kyrgyz Republic 2012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在25年时间里,增长率达到49.05%,1990~1999年,由于吉国独立后所奉行的宽松宗教政策,其增速达30.7%,但2000~2015年,由于吉国政府针对宗教组织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和限制,增速减缓,增长率达到1.5%。这也显示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明显感受到对宗教组织数量的任意放行,必定对境内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伊斯兰教宗教组织通过独立后25年时间已形成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未来趋势不可忽视的主导地位,这与吉境内非伊斯兰教宗教组织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2.境外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政治群体不断扩大势力,对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来,哈乃斐教法学派被广泛推崇并融入中亚穆斯林社会生活,成为中亚穆斯林的传统教派。独立后,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各类伊斯兰教宗教组织的增多,加之传统哈乃斐教法学派力量的薄弱,为境外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政治势力各类观点的滋长提供了平台。境外传播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各种政治宗教势力利用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政策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以及注册登记手续的便利,近15年间大力扩建自己的传播基地。
独立之初,来源于沙特的瓦哈比派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宗教组织中首先占据一席之地的境外派别。它先后向吉境内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组织捐赠了100万卢比(1993年)、在奥什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修建或兴建的清真寺中,属于瓦哈比派的就占半数,从而在吉南部城市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许涛:《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宗教概况》,《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8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瓦哈比派以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为中心,宗教权威超过了传统哈乃斐教法学派的伊玛目,一度成为凌驾于地方当局的伊斯兰教教派组织。直到本世纪初,瓦哈比派已经在吉南部城市形成了自己的坚实基础。由于它所提倡的教规教法更多地体现原教旨主义思想,例如禁止烟酒、赌博淫秽、音乐舞蹈和华丽服装及金银首饰等,向独立之后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穆斯林描绘了简朴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普通民众和基层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这一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改变不仅需要生活的简朴,而且还要求信徒背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基因以及民间信仰体系,遵循阿拉伯式的生活方式,因此,瓦哈比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传播大多局限在奥什和贾拉勒阿巴德等城市,没有传播到吉北部传统文化根基牢固的乡村社会。瓦哈比派对城市穆斯林群体生活方式的改变虽然当时很少造成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但恰恰这一基础性改变为20~40岁的穆斯林中青年群体接受各类异端宗教思潮开辟了一块容易发芽的“精神良田”。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吉境内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解放党”就是看准了这一时机,乘虚加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成立于1952年的“伊斯兰解放党”(又称伊扎布特,英文简称HT)源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由塔吉·纳巴哈尼所创。1995年,“伊斯兰解放党”经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苏畅:《伊斯兰解放党与中亚安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6年第2期。另据其他研究资料,“伊斯兰解放党”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时间为1997年。虽其宣扬“和平的圣战”,但由于其政治目标带有明显的宗教极端性,上世纪末先后被中东国家所禁止。“伊斯兰解放党”起初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利用当时吉南部城市失业率高、贫困人群多的社会背景,利用各类宣传手段,通过一定的慈善救助等行为,招募了不少成员。2003年,“伊斯兰解放党”虽被吉尔吉斯斯坦列入宗教极端组织行列而加以禁止,然而这一组织通过亲戚邻里、秘密公社、家庭教育等不同方式不断增加组织成员,据不完全统计,1995~2008年,该组织成员发展迅速,约有1.5万人。*肖斌:《吉尔吉斯斯坦宗教极端组织中的女性化》,《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从2013年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公开宣扬自己,并以纳伦河投毒抹黑政府形象为标记,进入政治目标的第二阶段。*④⑤ 再米娜·伊力哈木:《近期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及影响分析》。从这一时期开始,由于吉政府加大对“伊斯兰解放党”的打击力度,该宗教极端组织调整策略,与吉国其他宗教极端组织,如“瓦哈比主义”(Wahhabism)、“萨拉菲”(Salafi)和“巴亚特”(Bayat)联手,初步形成了“联盟”。据吉国巴特肯州警方表示,该州有90个宗教极端组织,④大多数为上述四种宗教极端组织。2014年,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各类地方性宗教极端组织纷纷“效忠”于“伊斯兰国”(ISIS)。先前宣扬自己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圣战”的“伊斯兰解放党”联手其他宗教极端组织,从2014年秋季开始派送成员前往“伊斯兰国”参加“圣战”活动。据2014年的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来自中亚国家的4 000多名武装分子为“伊斯兰国”参战,其中,吉就有500名武装分子参战,并有可能回流本国,加剧吉国内的反恐形势。⑤
从上述宗教极端组织的发展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宗教极端势力中瓦哈比派的影响局部清除了吉国穆斯林以往遵循的哈乃斐教派的影响,形成了滋长宗教极端组织的“温床”;而“伊斯兰解放党”通过政治组织形式联合了基于这一“温床”下形成的各类宗教极端组织,通过“社会化”“政治化”和“暴力化”途径构成了吉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潜在威胁,为吉国宗教极端组织向“激进化”迈进铺垫了道路。随着“伊斯兰国”的成立,吉国内的宗教极端组织明显趋于国际化,一方面为“伊斯兰国”参战,另一方面反扑国内官方宗教组织的领导人和宗教人士,向其公然开展袭击或迫害行为。
3.吉尔吉斯斯坦世俗群体和伊斯兰教哈乃斐教派支持者仍然占据主导优势,但也出现与传统民间信仰重构的分化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斯兰教宗教极端组织的各类暴恐行为严重影响了吉国内的社会稳定,也冲击到吉国世俗精英群体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忍耐底线。他们纷纷提出抗议和谴责并提出各种方法恢复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的正常发展,保护吉尔吉斯族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吉国世俗穆斯林精英群体通过大力宣扬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信奉的哈乃斐教法学派,以抵制宗教极端思想对吉国穆斯林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吉政府通过宣传其传统文化习俗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来清除宗教极端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本土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侵蚀。对传统的回归从其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底蕴来看,正好反映出吉国世俗群体的伊斯兰教本土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中,伊斯兰教成为了表面的符号,而民俗生活中的传统礼仪及民间信仰中的萨满教(文化)成为了实质内容,伊斯兰教中的天使为萨满所用,而伊斯兰教观念中的撒旦作为给人类带来不幸和灾难的恶鬼而成为萨满法术活动所针对并加以驱逐的对象;伊斯兰教殉道者的墓地成了萨满及其信徒们膜拜并乞求力量的圣地;萨满也由原来处于被排斥和被取缔的角色一跃成为毛拉或阿訇,集萨满巫师和伊斯兰教教士于一身;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也开始从事为人祈福求安、治病驱灾、占卜问卦、失物寻踪、预言未来等萨满的活动,等等。伊斯兰教在吉尔吉斯斯坦本土模式的回归,在世俗群体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应和赞许。
吉尔吉斯斯坦世俗穆斯林群体信仰模式的传统回归虽然从整体上引导了吉国伊斯兰教世俗社会的中道之路,但从另一方面也诱使一些基于原始宗教信仰的新兴宗教浮出水面。1991~1992年,吉国一些政治派别指出苏联时代“7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剥离了吉尔吉斯斯坦各族人民的很多优秀民族精神财富”,“苏维埃政权夺走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提倡“找到自己真实的历史”*② 苏来曼·卡伊托夫:《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现状》。,其结果是脱离了伊斯兰教外衣下的民间信仰组成体系,把民间信仰中的原始宗教和英雄崇拜等逐渐 “神圣化”,人为重构地方性宗教。
除此之外,吉尔吉斯斯坦民间也有一些相似的呼声,通过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回归“Tangirizim”(腾格里教)、Manasizim(玛纳斯教)、火崇拜(Zardoshitizim)等,希望以此对冲或消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这种观点和做法甚至得到了一些政治派别和政治家们的支持。巴基耶夫时期吉国意识形态进入最混乱阶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督教、犹太主义组织的传教活动更加频繁。吉尔吉斯斯坦学者阿里木别克·拜萨罗夫(Alimbek Baysalov)总结当时的情况:“四个吉尔吉斯人朝四个方向朝拜。”②对此,吉国世俗学者群体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当前吉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趋势错综复杂,不及时用严格的法律手段加以制止、用传统文化对冲和洗礼、用正统伊斯兰教教法疏导和引领,难以促成吉尔吉斯斯坦面向现代化的世俗国家道路。
责任编辑:刘 欣
B96
A
1009-5330(2016)05-0068-06
艾山江·阿不力孜,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地木拉提·奥迈尔,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