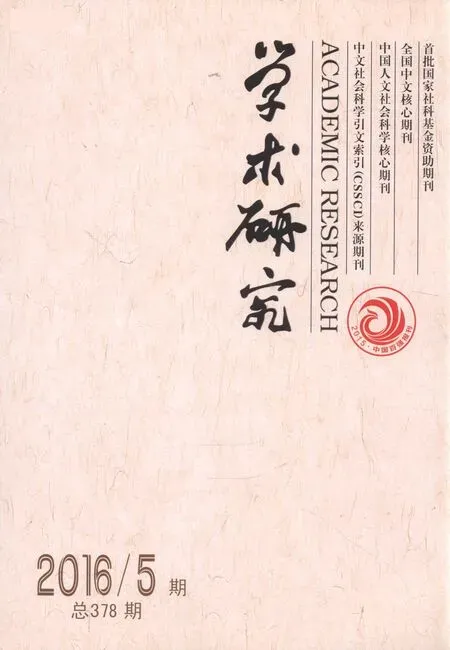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对乌坎事件的再分析*
2016-02-26马卫红黄荣贵
马卫红 黄荣贵
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对乌坎事件的再分析*
马卫红黄荣贵
[摘要]乌坎事件因媒介使用产生广泛影响,现有研究较多从媒介工具效用角度分析媒介在乌坎事件中的问题界定、动员、框架化等作用,而不去追问村民为何使用媒介、为何改变原本有效的媒介策略等关乎媒介使用的根本问题。互联网时代媒介与抗争行动之间形成复杂的互构形态,呈现出媒介多样性与媒介制度、行动者与媒介、媒介管控与突破、公众的态度四个维度,显示出集体行为中媒介作为一种动力机制的可能。这为重新反思媒介角色带来了新的理论指向。
[关键词]乌坎事件互联网互构媒介工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Z03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SH043)的阶段性成果。
乌坎事件表明,互联网时代媒介已成为一个能影响集体行动发展的重要变量。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乌坎村民如何利用媒介动员和框架化,而此事件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强调媒介工具效用,还在于它展现了互联网时代媒介与抗争之间互动互构的复杂形态。本文重新思考乌坎事件的媒介现象,反思当前媒介工具视角的解释,并从媒介与抗争运动互构的角度进行再分析。有关乌坎事件的资料主要来自三方面:笔者搜集的相关新闻报道和网络平台信息;公开发表的深度评论性采访与报道;以及已有的学术研究文献。
一、对乌坎事件的再审视:当前媒介效用研究的缺陷
乌坎事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事件爆发,2011年9月21日数千人到陆丰市政府集体上访。因对政府的答复不满,上访村民回村后围攻村委会和边防派出所。22日防爆警察整队进村,遭到村民有组织拦截。第二,激烈冲突,11月21日,4000多村民再次集体上访。汕尾地级市政府介入,拘捕5名积极分子。12月11日薛锦波猝死使事态急剧恶化。第三,事件转机,12月21日省工作组进入乌坎村,官民协商解决问题。省工作组承认乌坎诉求的合理与合法,答应以五个原则回应村民的诉求。随后,2012年3月新村委成立。虽然新村委成立后乌坎村土地问题仍未全部解决,[1]但从事件的角度来看,2012年3月新组织机构成立及解决问题的协议达成可视为事件的结束。
乌坎事件之所以最终得以转机,与媒介使用有密切关系。现有代表性的研究强调,媒介把乌坎事件转化为公共议题,发挥公共空间生产、框架塑造和传播作用。[2]在组织动员中,媒介塑造了专业化的抗争运动,获得社会同情和支持,使“离场介入”成为可能。[3]然而,现有分析没有充分关注乌坎事件所展现的更为丰富的媒介现象和问题,比如,既然媒介作为一种工具是有效的,为何乌坎村民最初没有先采用媒介策略而是选择上访?当境外媒介明显促进维权发展时,乌坎村民为何转换媒介策略?地方政府如何使用媒介?其效果和影响如何?乌坎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媒介行为如何相互影响?忽视这些问题,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集体行动中的媒介作用及其变化。
事实上,乌坎事件的媒介表现显露了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中媒介研究的主要缺陷。当前的媒介研究主要把媒介作为一种具体的手段,着重强调网络的跨地域性、及时迅速等特征,将潜在的行动者与行动机会联系起来,[4]更能展现媒介作为组织动员及框架化的工具性作用。[5] [6]媒介是抗争工具成为集体行动研究者的共识,“媒介化抗争”成为一种有效的抗争策略,[7]尤其是底层群体,更依赖媒介作为发声的渠道。[8] [9]这种媒介工具视角在互联网时代开始显现出明显的不足。
首先,它是媒介中心主义,认为媒介支配着抗争运动。应该看到,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传播中抗争者会选择媒体,并决定给哪些媒体提供什么信息;不仅有媒体塑造的框架,还有抗争者自我表达的框架,被抗争方的框架及旁观者对媒介的使用和信息传播等,这些要素共同塑造抗争的全过程。
其次,它忽视互联网时代媒介与抗争行动之间的互动互构现象。媒介工具效用侧重分析策略,认为谁掌握了丰富的媒介技术,谁就可能获得抗议成功,并且多关注抗争者对媒介的使用,不关注被抗争者的媒介行为。它忽视了网络媒介最突出的特点——互动性,[10]互联网媒介环境下,媒介的策略性使用所产生的媒介事实会反过来塑造抗争行动。因此,互联网媒介对行动者既有赋权又有限制,互动与互构是互联网媒介与行动者关系的突出特征,这是当前媒介工具视角未予以充分关注的。
最后,它不能解释媒介效果差异。就集体行动传播而言,无论同一地域还是不同地域,都能观察到不同的冲突性议题获得的传播机会不同,同类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机会也不相同,甚或相反,而不同的冲突性议题却获得相似的传播机会。虽有少数研究试图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下对其加以解读,但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是仍然无法解释同一属地的媒体对同一议题为何态度和立场不同;二是只看到政治机会结构对媒体的制约,没有看到二者制约与反制约的博弈,更没有分析行动者在面临媒介传播和政治机会出现张力时如何行为。
可见,媒介工具视角忽视了媒介的策略性和工具性有着重要的前因和差异化后果,因而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对集体行动中媒介现象的理论洞察。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之于集体行动的意义已经超越工具性,构成一种有自身运行机制的生态系统,媒介不仅仅是动员手段和信息传播的工具,还有自身的运作机制,它被行动者使用,但不受制于任何人;它对行动者的行动赋权并提供机会,同时也会施加限制和障碍。
二、媒介作为一种动力机制:媒介与抗争行动互构的四个维度
互联网以其相互连接性构成了一种新的媒介场域,人们在互联网空间进行信息交换并建构新的意义,从而产生新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改变了媒介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媒介、信息、行动者构成一种新的关系。所以,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中的媒介研究要以媒介关系研究为重点,分析由媒介多样性构成的权力域和结构关系,以及各类行动者在其中展现出的获得媒介权力的可能性和能力。
媒介与抗争运动的互构形成一种动力,推动抗争事件的发展和演变。互构动力机制分析,不是媒介框架建构与竞争的分析,也不强调媒介技术的更新,而是观察媒介与行动者在抗争事件中相互选择和互动的过程。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分析互构关系。第一,媒介多样性及媒体制度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媒介多样性往往能为集体行动提供可用条件,媒体制度的封闭性与开放性能解释这种可用条件是否被启用。媒体的异质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媒体的异质性程度越高,会使抗争者拥有越多施加影响力的机会。第二,行动者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抗争事件的各类行动者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是分析互构关系的核心,从中可以观察媒介如何成为行动者的有利因素或不利因素。这里的行动者既包括抗争者,也包括被抗争者。第三,媒介管控与突破可能。媒介管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在任何社会,国家都是重要的媒介体制塑造者,媒介在这种环境下常常面临政治服务与专业主义的双重局面。第四,公众态度的一致性程度。冲突性议题与有影响力的网络传播者联合后会迅速形成微信息的大传播效应,从而引起权力阶层对该运动更为重视,增加抗争行动者与权力阶层对话的可能性。因此,公众态度与抗争者是否一致是另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
在这四个分析维度中,媒介多样性与媒体制度是这一动力机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它奠定了抗争行动发生的媒介条件;行动者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是媒介条件发挥作用的基础,它决定了在抗争行动中媒介多样性环境起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媒介管控与突破重在分析行动者利用媒介相互制约的过程;媒介公众的态度反映了旁观者利用媒介对抗争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四个维度从启动条件、作用基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勾画了互构关系对抗争事件产生动力的机制。乌坎事件突出体现了媒介与抗争事件的互构动力,下文结合乌坎事件中的媒介现象展开分析。
(一)媒介多样性与媒体制度
媒介多样性是互构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但前提条件的存在不意味着一定能构成推动力。乌坎事件伊始,多样化的媒介技术已经存在,但乌坎的年轻人并没有首先选用。当寻找传统媒体曝光未果后,[11]更多的媒介工具才被征用,多样化媒介发挥作用。以70后、80后、部分90后为主的抗争者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工具,如博客、微博等自媒体。他们联系国内外媒体,通过qq空间、网络论坛、微博等平台向外界发布信息,还制作了歌曲《情系乌坎》。视频是乌坎村民使用的另一个有效的媒介工具,乌坎年轻人自采、自拍、自编《乌坎!乌坎!》电影短片在村内播放,并上传到国内外视频网站扩散。
媒体制度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共同作用激活了乌坎事件的媒介多样性条件。首先,乌坎当地的媒体制度具有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既来自于政治机会结构的影响,也出于当地媒体的立场选择。另一方面,乌坎因地缘优势受益于一定程度的媒体制度开放性。乌坎临近香港,有很多村民迁往香港,通过这些联系找到香港媒体入村报道很便利。后来的事件发展显示,海外媒体使抗争行动者获得媒介的强力支持,海外媒体带来的开放性为乌坎事件创造了更大的传播空间。
(二)行动者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
媒介作用的发挥不是媒介技术力量的佐证,而是抗争事件中各类行动者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的对比,他们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使媒介产生不同的影响。乌坎事件中主要的直接行动者有乌坎村民、当地政府、境内媒体和境外媒体。
村民在乌坎事件中对媒介的使用体现出较高能力,他们内部有清晰的信息生产者、信息发布者和信息评论者。他们知晓循环使用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借此开拓政治机会。抗争者从经验中领悟如何抓取信息、传递信息。自发设立新闻中心对外宣传,通过网络生成议题,挑选一些传统媒体进行报道,使议题流动引起更大范围的公众关注和政府重视。在乌坎村民所处的媒介机会中,境内外媒体可以带来不同的机会可能性,乌坎村民在摸索中领悟到何时适合用哪类媒体。乌坎抗争者利用境外媒体获得了更多的媒介机会,有力地作用于地方政治权力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抗争者也不总是与境外媒体构成统一战线。
强大的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与能力并不一定对任何行动者都能产生有利的媒介机会,尤其在网络场域,现实中强大的组织显现不出优势,反而弱组织化或者弱小的个体更能显现出现实环境中并不具备的力量。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网络权力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网络上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强权主体,各方实力非常接近。[12]所以,现实中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能力和握有媒介技术的优势并不能继续在网络场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媒介机会不是单纯由媒介技术产生的,而是在各行动者的信息获取、生产、互动和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中展现无遗,地方政府除了能影响当地媒体或境内媒体外,在网络信息较量中并不占优势。
乌坎事件中,媒体本身也在塑造媒介机会。尽管乌坎村民主动给媒体提供框架信息,但是媒体往往会自己选择有引爆点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不总是如实报道事件,因意识形态、专业主义以及媒体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媒体有自己的信息选择。不同的媒体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力。境内外媒体的信息生产使乌坎抗争者要应对信息的混乱,学会识别可利用的媒介机会。
(三)媒介管控与突破
乌坎事件在自媒体传播和境外媒体的关注下产生了世界瞩目的影响,也引起政治权力的警觉。政治权力体系对媒介和行动者做出回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尽快给事件定性,12月9日汕尾市发出乌坎事件通告,称“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为非法组织,并将事件定性为“一小撮群众闹事”。第二,控制国内媒体和网络传播,在省工作组进乌坎村协调之前,境内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一直比较保守,而且薛锦波之死后境内媒体集体失语。第三,向村民和境外媒体施压,指责村民“勾结海外反动势力”,抨击境外媒体“三烂”(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别有用心等。
面对危机,政府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汕尾、陆丰市政府希望通过控制媒体、分化积极分子等手段快速控制局势,但让地方政府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媒体产生的机会可能性压缩了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适用空间。地方政府上述三种回应不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让乌坎抗争者赢得了更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对于地方政府的定性和指责,乌坎村民通过网络澄清游行上访的不是“一小撮”,而是实际参与者达4000多人;他们吸收前车之鉴,11月21日游行之前在网络发布信息,告知公众并请境内外媒体报道。针对勾结境外势力的指责,抗争者在新闻中心旁张贴中英文《告媒体朋友书》,提示媒体不要使用具有挑衅性的词语报道,并强调乌坎村拥护共产党、只是维护自己正当权益,不是“起义”、不是反共、更不是勾结境外势力分裂国家等。同时,利用微博和博客,以及在自家新闻中心接受采访等方式澄清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看似快速的网络管制与网民的突破形成博弈。乌坎的网络使用者采取多种应对措施,除了申请不同社交平台的多个账号身份之外,在信息传播中他们会分散与主要节点的联系,尽量不频繁与固定节点互动。主动注销账号或者同一时间启用不同的账号。一项针对乌坎事件的传播网络分析显示,网络节点中出现一批具有相同地位的节点,并未出现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节点。[13]互联网的多节点特征使得政治力量在网络中难以发挥如现实中的强大控制力。
(四)公众的态度
互联网时代,媒介传播信息能否起作用,还要看信息引起了怎样的公众态度和反应。互联网使乌坎事件中抗议者的声音跳出地方政府的权力网络和境内媒体的话语控制,获得更开放、充满更多商议空间的公共讨论机会。
政府虽然对网络信息实施严格审查,控制重大的冲突性议题的网络传播,但是,突发事件信息往往在网络审查者还没有注意之前,已经快速传播并引发一波热烈讨论,即便信息被删除,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留在网民心中。[14]乌坎事件的信息经互联网传播后,引起不少网民自发探访乌坎村,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网络信息的主要发布者,用亲身经历和信息传递来声援抗争民众。这些行动使乌坎事件在国内获得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
乌坎事件展示了互联网时代媒介已从抗争行动的技术工具生长为一种与抗争行动相互建构的关系。行动者对网络场域的运用,各种媒介、信息等要素的组合与互动,不仅有助于扩大抗争事件的影响,还能为事件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在这种互构关系中,媒介对不同的行动者产生的影响不同,对有的行动者是有利影响,而对有的行动者却是不利影响。通过对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关系分析,不仅让我们清楚乌坎事件中媒介如何使用、何人使用,还有助于我们分析媒介使用者为何受限,以及为何改变原本能带来工具效用的媒介策略等。这些问题是当前媒介工具视角无法解释的,也正是这些问题才能揭示互联网时代媒介与集体行动的复杂关系。
三、互构关系的概念化:重新思考集体行动中的媒介角色
上述乌坎事件的分析,展现了抗争者、被抗争者、境内外媒体在事件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政治权力体系受到媒介挑战时的回应及其效果的有限性。这其中,互联网使抗争者和被抗争者的制约与反制约成为可能,它是突破地方性政治权利控制的重要方式,因为它处在科层体系之外,形成了与传统媒体不同的另一个舆论场。越是传统媒体被控制而不得报道的冲突性议题,在互联网上获得的传播机会越多、速度越快。但是,乌坎事件中也显示了互联网时代媒介的限度,比如,虽然境外媒体帮助抗争者开拓了机会,但这种有目的、有计划地邀请境外媒体报道的行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指控。
乌坎事件的媒介过程可能很难复制,但它展现了互联网时代媒介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的确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角色,提示了重新思考集体行动中媒介角色的必要性。在集体行动研究中,媒介作用的分析长期分散在不同的理论视角,如政治机会结构论、框架建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把媒介作为一个从属的变量来考察。然而,如乌坎案例所示,互联网时代媒介与集体行动的互构已经形成一种可以影响事件发展的动力机制。因此,重新思考和概念化集体行动中的媒介角色对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媒介环境论和媒介赋权论均以媒介与行动者为着眼点,关注媒介与行动者的互动性和反馈性,强调观察媒介与行动者的互构关系。就媒介环境论而言,它视媒介为行动者的基础环境,关注行动者在媒介环境中的行为选择。但是,它所暗示的媒介生态的和谐平衡与集体共识和认同的达成是一种理想状态。[15]在集体行动中,更常见的是各种混杂信息以及难以判断好坏的群体极化(而不是群体认同)在媒介作用下形成,并推动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更多地体现出在冲突中的共生,而不是在和谐平衡中的共栖。就媒介赋权论而言,它强调媒介对行动者的增权与扩权,[16]这里的行动者多指处于媒介弱势的行动一方。然而,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抗争事件中的行动者是多元的,不仅指抗争者,也指被抗争者,甚至是媒介本身。并且,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可能增加也可能弱化行动者的权利,乌坎事件中媒介对抗争者不全是增权,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对被抗争者而言也是如此。
如果把媒介构成集体行动者的机会条件和可能性视为一种“媒介机会结构”,它体现了各类行动者在媒介多样性构成的权力域和结构关系中以媒介推动行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媒介机会结构”不排斥媒介工具视角,它试图弥补或完善媒介工具视角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信息、行动者三者关系的看法。如前述分析,媒介工具视角强调媒介的工具性和效用,认为掌握媒介技术的多寡会有强弱与实力差异。从乌坎案例中可以看出,媒介提供了一种机会可能性,强弱可通过媒介机会的利用发生转化,是一场实力较为接近的角逐。信息扩散的范围和广度,以及信息生产的主动性留下了进一步分析的空间。在媒介机会结构的视角中,媒介的使用者和信息的生产者是与事件相关的各类行动者,信息环境是竞争性的、不可控的。网络扩大了信息权的分布,信息的网络传播意味着权力分布更加广泛,导致权力扩散,在网络场域中的弱势行动者会因此而获益,权力平衡成为可能。
同时,如果把媒介机会结构进一步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论指向,其核心是更加关注媒介如何推动或者阻碍了行动者、从而影响了集体行动的演变,它包含了三个根本问题。第一,谁的媒介机会?同一种媒介场域,不同行动者的机会不同。第二,对什么的媒介机会?即不同议题或事件的媒介机会差异,或者同一种媒介结构场域对不同的议题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三,媒介机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媒介到底怎样推动或者抑制了集体行动。
在我国的政治生态中,媒介机会结构的充分激活和功能发挥是对政治机会结构的反应,现实政治机会结构的压力越大,媒介征用的动力就越足。大多数抗争事件在开始往往进行有节制的行动,但当地政府的应对不当,往往使行动者走向大范围逾越界限的抗争。因此,如何有效地处理抗争事件,避免它借助媒介机会结构扩大化,是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唐逸如:《当民主理想照进乌坎现实》,《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
[2]周裕琼、齐发鹏:《策略性框架与框架化机制:乌坎事件中抗争性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3]王金红、林海彬:《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离场介入——基于“乌坎事件”的实证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网络的视角》,《求实》2009年第2期。
[5] R.Kelly Garrett,“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vol.9, no.2, 2006, pp.202-224.
[6]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2013年第3期。
[7]陈天祥、金娟、胡三明:《“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8] M.S.Gleiss,“Speaking up for the Suffering(br)Other: Weibo Activism, Discursive Struggles, and Minimal Politics in China”,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37, no.4, 2015, pp.513-529.
[9]桂勇、王正芬:《互联网对中国集体行动的影响》,《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
[10]张碧红:《从媒介工具化到媒介社会化——微博的个体表达与社会影响》,《学术研究》2012年第6期。
[11]武孝武:《乌坎僵局》,《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
[12] [美]约瑟夫·奈:《论权力》,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43-162页。
[13]廖卫民、何明:《乌坎事件传播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分析》,《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
[14] A.Rauchfleisch and M.S.Sch覿fer,“Multiple Public Spheres of Weibo: a Typology of Forms and Potentials of Online Public Spheres in China”,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8, no.2, 2015, pp.139-155.
[15]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
[16]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责任编辑:王冰
经济学管理学
政法 社会学
作者简介马卫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60);黄荣贵,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5-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