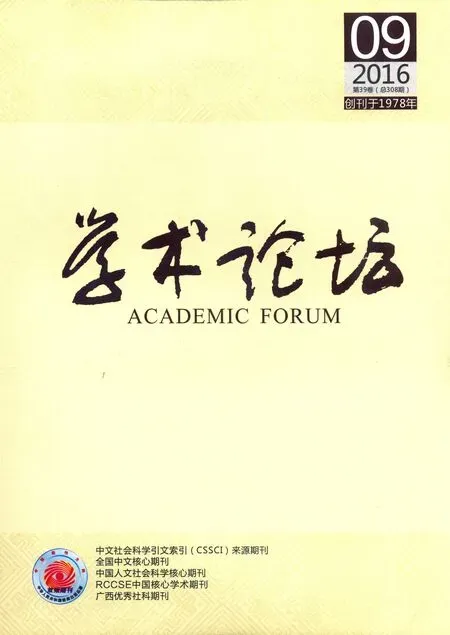“明明德、亲民、至善”对医护工作人员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启示
2016-02-26简红江何国蕊何国忠
简红江,何国蕊,何国忠
“明明德、亲民、至善”对医护工作人员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启示
简红江,何国蕊,何国忠
医学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在医学伦理语境下,《大学》中“明明德、亲民、至善”所折射出的深蕴义理,在建构和谐医患关系中,应成为医务工作者自我生命伦理行为的根本要求,成为医务工作者重构患者生命价值的伦理责任,成为医务工作者营构医患关系的终极使命。
医学伦理;三纲领;医学人文精神;和谐医患关系
当前,和谐医患关系作为医学伦理中重要内容之一,已经成为医学领域或医务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医学伦理所涉及的内容看,不管是医学临床、医学科学研究,还是与医学相关领域,其中“医学人文精神”[1](P13)已成为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事实上,自医学诞生那一刻起,医学人文精神就已经以伦理与道德观念孕育于医学母体中。纵观医学发展历程,尽管中外医学发展有着不同的路径,但对伦理与道德都有着共同的夙愿,即在医学实践中应该有着怎样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医学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视域高远,体现了生命伦理的实践诉求。医学伦理是医学与伦理学双重学科的媾和,同时,其他学科的发展,也增进了医学伦理价值与道德规范的深远时空评判。《大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一,有着厚重的伦理思想与道德规范积淀,自古及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整体和谐发展,对形成“医学人文教育乃医学教育之根本”[2]仍有一定的启迪。
一、“明明德”:医务工作者自我生命伦理行为的根本要求
(一)道德价值判断是生命伦理行为的基础
“‘伦理’主要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具体行为准则。”[1](P5)由此,医学伦理主要是指医学实践领域中,尤其是在医疗救治、医疗服务等医务实践活动中,医患双方于治疗进程中,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来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态势。显然,医学伦理重在医患双方行为是否符合既成的规范约定。如果医患双方行为符合既成的规范,则是医学伦理行为的表现;反之,则不是医学伦理的行为。然而,医患双方行为最终是受各自内心世界道德价值判断支配的。而内心世界道德价值判断的最高意志表现,主要体现为精神的最高原则,此即道德原则的最高追求。不管医患双方表现出怎样的外在行为,但在双方各自内心世界里,都有衡量各自行为或对方行为的道德尺度。可见,道德约束或规范是医学伦理行为的基础。即有什么样的道德境界,就会表现出相应的伦理行为。医学道德是医学伦理的无形枷锁,医学道德是医学伦理的基础。虽然医学伦理也会不断促进医学道德升华,促使医务人员不断提升对医学世界的深入认知,但医学道德作为一种信念,会自觉地存在于医务人员的内心之中,会自发地指导或约束着医务人员的行为。
从我国近年所发生的医患冲突事件中可见,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医患双方伦理行为失范,而是存在着深刻的心理道德认知问题。道德认知作为外在行为的基点,有着较稳定的价值判断尺度。道德标准是千百年来,生活在一个共同地域内人们形成的共有认知,人们会不自觉地运用此种标准来衡量自我行为,或他人行为是否合符道德标准。而伦理规范侧重于对医患双方行为的约束,医患双方行为是不确定的,一旦行为超越规范,就表现出不伦理行为,进而可能引发医患双方的冲突。由前述可知,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依此,对医务人员而言,加强医德教育、提升医德境界是夯实其医学伦理行为的内在要求。在医患关系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的医方,应有极强的道德心理素养与至柔的伦理行为。这就要求在医务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要深入领悟道德内涵,适度把握医患伦理行为,积极建构和谐医患关系,此即当前中国“医学伦理文化建构”[3]的现实要求。
(二)“明明德”应成为医学伦理内则根基
认知思维表明,医学伦理准则具有内外双重架构。医学伦理准则具体明确的规约,是医务工作者外在行为伦理与否的评判。同时,医学伦理准则还有其内在的道德价值尺度,反映着医务工作者内心活动伦理与否的评判。可见,医学伦理准则是显性规范与隐性心理认同的重构。由于思维认知习惯使然,人们往往只注重显性准则与外在行为的比对,而忽视了隐性道德尺度与外在行为的关系。事实上,这一忽视埋下了医患关系失范的根源。据此,加强医务工作人员道德价值判断尺度教育是不断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不良行为发生之必然。
“明明德”是《大学》“三纲领”首句。第一个“明”是“发扬、弘扬、彰显”之意,作动词用。第二个“明”是“光明的、正大的、伟大的、博大的”之意,用作形容词。而“德”本是“得到”之意,是个体内心对经验世界的美好认知与感受。由是“明明德”之意为:弘扬光明正大的德性。其是个体内外兼修的知行观。它要求个体是发自内心的领悟,在此基础上,秉承文明信念,让自己的行为符合他人与社会群体之要求,从而不断提高个体道德境界。相对医学伦理外则而言,“明明德”对个体内在世界要求得更高。因为“明明德”侧重个体自我的内修外治,而医学伦理外在规范的普适性,是适合大众的一般行为准则。因此,基于医学伦理语境下,不断加强医务工作者“明明德”之教育,以道德促动医学伦理“以人为本”的生成情境,是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明德”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尺度。其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重要的文化观念,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产生着不可磨灭的辉煌。其所承载的积极思想观念,对我国历代医学伦理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传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到载誉盛名的扁鹊、华佗、张仲景,再到王履、楼英、李梃、陈实功、李时珍等历代著名医家,无不呈显出“明明德”的精深妙意。他们立身行道于百姓疾苦之中,甚而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明明德”的宇宙人生观。由此可见,“明明德”的社会进步观,对当代医学伦理建设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社会主义医学伦理道德观具有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核心要点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是义务论、公益论与价值论的完整统一,而价值论则处于最基本的地位,它是医务工作者履行义务、实践公益的基础。患者作为服务的对象,无疑将医务工作者的义务职责、公益使命与价值生命高度凝练在一起,从而为医务工作者展示“明明德”的外在行为提供了必要前提条件。由此,各级医务工作人员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伦理的力行者、普及者与弘扬者,践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与“人道主义”的医学道德原则,正是“明明德”内涵与时俱进的人本观体现。
可见,“明明德”光正恢宏的精神品格,体现了时代进步性。因此,将其置于医学伦理语境之中,作为医学伦理内则根基,是提升医务工作者心灵境界,明达医学伦理行为,不断促进和谐医患关系建构的道德要求。
二、“亲民”:医务工作者重塑患者生命价值的伦理责任
(一)医患关系中身心地位的生命价值判断
中国现代医学伦理职责就是要有效地处理好医患关系,让医患双方在和谐氛围中实现各自内心世界的初衷。这是对生命的价值肯定,对社会的责任承担,对自然的关爱。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以生命价值为中轴的侧面体现。在医务实践中,医务工作者借助现代多种医学仪器,通过对患者病况适切诊疗分析,本着“治病救人”与“救死扶伤”的人道宗旨,竭尽全力,实现患者的可能康复。这不是简单地对人的生命价值判断,而是以人的生命价值为尺度的生态文明反映,是“人性化的医疗”[4]哲学观企盼。相对医者而言,患者希望医务人员借助现代仪器,诊断并准确发现病因,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实现生理与心理的基本康复。由此可见,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是包括个体生命价值、社会与自然在内的系统伦理诉求,其中,生命价值是医务工作的核心基点。
既然生命价值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内容,那么处理好医患关系,就是对生命的诊视,是对社会、对自然的伦理关爱;反之,则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社会、对自然伦理的践踏。基于此逻辑,在医患关系中,医务工作者扮演着重要的生命价值重构角色。因为在患者生理与心理处于极度虚弱的状况下,他们渴望能及时得到医务人员对其病况的精准诊治方案。正是这种身境与心境的错综杂然,他们会不自觉地对生命产生种种奇想,事实上,这种奇想基本上是本能的反应。而医务人员作为救治主体,有着理性的健康的自觉的思维惯性,能依据诊断的病况,居高临下地思考患者的身心世界。由此可见,医患双方的身心地位决定了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生命重视的清晰性与至上性。因此,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必然要求医务工作者主动而不是被动接近患者,自觉而不是自发地与患者交流。这是医患双方心灵沟通的不二选择。其是在医学伦理语境下,医务工作者践行“亲民”的写真,是实现患者敞开心扉,看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激发医务工作者珍爱生命的深刻揭示,是对《黄帝内经》“倡导医者珍视生命”[5]品格的承继与弘扬。
(二)“亲民”是患者生命价值再现的伦理要求
基于上述立论,在医患关系中,医务工作者是承载生命价值的根本法器。由于患者生命价值总是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医务工作者能否再造患者生命价值的有利趋势,不仅是对患者生命价值的判断意义,而且是对整个人类或生物界生命价值判断的意义。医务工作者对患者生命价值的诊视,一是体现出医务工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关爱;二是体现出医务工作者具有的宇宙情怀。“亲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伦理文化元素之一,对医务工作者系统认知生命价值,有着不可或缺的道德启示。
根据程颐对《大学》中“亲民”的解释,认为“亲”作“新”解,就是使人不断革新、自新,因此“亲民”即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6](P3)由是可见,“亲民”表达出人的修养境界变易更新。在医患关系这对矛盾体中,“亲民”就是医务工作者融注于患者,修养境界不断提升的真切反映,是医务工作者自身生命价值与患者生命价值同存共生的创新过程。
一是医务工作者要能立于自身生命的意义,从自我生命中,开发出精彩的动人篇章,促成自我生命的新生,这是让患者生命焕发新枝的前提。只有十分肯定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判断,医务工作者才能找准释放生命光辉的基点。即医务工作者在原则规范内,能适时把握革新工作的思维,不被僵化的陈规紧缚,置医务工作于天宇之中,增强自我事业热情,而不是单纯地为着私利生存。深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融医务工作与吾身于一体,积极实现生命创新动力,在医务实践中体悟自我生命与天地宇宙合一的真情实感。将天的无私健行,地的广厚大德,筑成自我革新、创新的基源。
二是医务工作者还要让患者重新释放生命价值的希望。丰富的医学史病例告诉我们,不管患者处于何种疾患状态,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就是引领患者对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这不仅是医务工作者的职业使命,而且也是其道德心灵的向善行为。在医学伦理语境下,对医务工作者而言,“亲民”就是让患者从一个病态的身躯里走出来,用最诚挚的心灵语言,激发患者对生命价值的新认识。对患者来说,他的病躯就是一种“恶”的呈现,而他对生命价值的希冀就是一种“善”的渴望。由此,医务工作者就要树立患者战胜疾病的自信,从病态的躯体与心理到康健的肌体与心境的恢复。在这一逻辑下,“亲民”一则体现了医务工作者自我除旧革新、弃恶趋善的高尚心界;二则体现了医务工作者帮助患者敢于弃旧向善,勇于面对疾病,创新生命的人本观念。
可见,在医学伦理语境下,“亲民”是医务工作者在自我生命价值肯定基础上,对患者生命价值的升华。在现代医学实践中,“亲民”所展示的,不仅是医务工作者内心道德境界的场景,而且是其外在伦理行为的精致描绘。在医患关系矛盾体中,重释“亲民”的现代医学伦理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医务工作者重塑患者生命价值的使命与责任。
三、“至善”:医务工作者营构医患关系的终极使命
(一)医务工作者的生命伦理认知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
生命伦理是对当代医学伦理的高度认知,对医学伦理提出了更高的期盼。自20世纪70年代初,范·潘塞勒·波特等使用了生命伦理概念,生命伦理观便成为医学伦理学领域内最具鲜明的个性化用语。尽管生命伦理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但其在医学伦理语境下的主旨,主要体现为人的生命的至上性。医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的生命的根本需求,而且也是自然界中所有生命体的需求。然而,“一些常规应用的医学技术可能会给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7]从而导致生命伦理问题的出现。在生命伦理视野下,医学伦理所体现的生命是个体的、社会的与自然的系统生命观,它是合符道德、伦理、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于一体的宇宙生命媾和。因此,医务工作者作为熟悉、掌握与运用医学技术的先行者,深谙生命伦理的内涵,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前提。
虽然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提出发端于西方,但从人类文化发展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生命伦理观所展示的人道主义,是“仁爱”之心在“生命、道德、科技、社会、自然”整体基础上,对人的创造性激发,是生命质量的最高表达,也即是人的生命的“至善”追求。依此,医务工作者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处于医学伦理的时代前沿,从生命价值的“至善”观念出发,把患者的疾苦视为己苦,把患者的利益视为己利。把患者生命与自我生命结为一体,在医务实践中,实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生命伦理真有意蕴。其中“立”与“达”所揭示的不仅是医务工作者与患者内在德行修养与康健肌体的双重夙愿,而且是医务工作者与患者生命创造本质的伦理体现。可见,在这样一种“立己利人”的生命伦理关怀情景中,医务工作者成为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基点。尽管医学伦理准则主要发生于医学领域内,但在社会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的生命“至善”追求,是社会关系“至善”的有机构成。因此,医务工作者的角色地位,决定其不断充实自我生命“至善”观念,构建医学领域的和谐医患关系,体现医学伦理“民本意识”的社会使命。
(二)“至善”是医患关系和谐的最高原则
“至善”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之一,在中国哲学语境下,侧重于人的身心境界的极至追求。而人不是孤立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体。人的身心境界完善与否,是社会关系和谐与否的根本反映。当前,医患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之一,是关涉民生问题不可回避的焦点之一。如何更好地建构和谐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内心的愿景,而且是社会责任与使命的表达。医务工作者作为医患关系的调解器,如何让医患关系这杆天平产生应有的积极社会效应,从根本上看,就是在现代道德、社会与医学伦理背景下,增强生命“至善”观念的社会意识,为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储备厚重的生命道德素养。
“至善”是《大学》“三纲领”的最高追求,它以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为基准,将“个人、家、国与天下”这些要素紧紧聚合在一起,系统阐述了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一到众,由普通百姓到圣王君主,由个人到天下走向和谐一体的完整逻辑路向。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尽管这一主张,具有理想人格化特征,但立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传承与弘扬角度看,其所表达的理想人格,在医药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让后人仰慕的伟岸形象。如传说的医家伏羲、神农、岐伯、雷公、少师;古代医家伊尹、医缓、医和、张仲景、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苏耽、秦承祖、李修、沈应善、刘完素、张元素、沙门洪蕴,直到晚清的唐宗海、朱沛文等,这些中国古代优秀的医药学家,就是立于生命“至善”的观念,在医药事业中孜孜以求,渐趋实现自我医德的最高境界。用自己的善行敦化受业者,以拯救百姓于病痛疾苦之中为己任,自觉地寓目于“个人、家、国、天下”和谐一体的道德追寻。虽然他们“至善”的医德境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至善”的医德观念对生命价值所产生的意义,对当代医务工作者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启发性。在当代医学伦理语境下,“至善”的医德观念已经远远超越单纯个人品德最完善的境界,它的深刻意义在于普遍化与社会化,而且应该成为医务工作者妥善处理医患关系的重要信念。
鉴于以上论述,医务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自我内化“至善”观念,在医务实践中,将“至善”观念达以知行合一的境状。即医务工作者要体现自身的高尚情操,不管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医治患者、护理患者等具体医护过程中,话语轻重急缓的适度性、规则康健幽雅的得体性、肢体行动的贞洁性等,无不展示出一位医务工作者对生命价值存在的珍视情怀。因为医务工作者对生命价值存在的极强认同度,会潜移默化地感染患者的视听,从而激发患者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愉悦感受。可见,医务工作者“至善”观念对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独特功能,无疑也显示出“提高医学伦理地位”[8]的秘诀。
医务工作者的“至善”观念不是其独有产品,而是在以医务工作者为传播载体的基础上,走向他人、渗透于社会的共享资源。医务工作者发育、培植、生长、成熟“至善”观念,就是要把自我完善的道德境界呈现于患者面前,从心灵层面上,让患者体认到世界的美好,树立患者对生命存在的坚定信心。通过对医务工作者“至善”言行的领会,体察到医务工作者生命魅力是实现患者自我肌体康复的重要依托。这就在心理上达到了医患间的零距离接触,是和谐医患关系生成的首要环节。和谐医患关系的评价机制,不是以单纯的外在医务设施的完备与否来衡量,而是以医患双方内心世界融通媾和的境况为最终杠杆。因为人为设计的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偏离医患双方内心真实情景。同时,以“至善”观念为根本的和谐医患关系,作为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内容之一,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民生关注点。由此可见,历练“至善”观念的医务工作者,同样体现着建构和谐社会的天然使命。因为医学伦理作为和谐社会建构的有机部分,它的视野应该是宽广的,而不是狭窄的,所以医务工作者所拥有的“至善”观念是超越时空的境界。它不是个人生命“至善”情怀的流露,而是群体间生命“至善”芳馨的交互溢放。
四、结 语
从根本上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核心任务就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和谐医患关系不是仅有医患双方的二维空间反映,而是包括“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科技、生命等多维要素的立体反映。和谐医患关系涉及学科的多维性,内容的丰富性,领域的广泛性,这就必然要求多学科理论的参与,补充、完善与实现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由此可见,本质上,和谐医患关系就是医患关系的协调、平衡的生态体系反映。然而,道德或医德境界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根基,脱离这一根基奢谈和谐医患关系,尤如痴人说梦,残壁挡车。因此,在医学伦理语境下,分析“明明德,亲民,至善”之经本,旨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觅寻当代和谐医患关系建构的仁道本源,为构筑当代创新、协调、绿色的医患关系,提供一孔之见。
[1]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杜宏.医学人文教育乃医学教育之根本[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3,(6).
[3]程亮.当代中国医学伦理文化构建面临的挑战与问题[J].医学争鸣,2015,(2).
[4]杜治政.医学人文与医疗实践结合:人性化的医疗[J].医学与哲学(A),2013,(8).
[5]曹变玲,李亚军.《黄帝内经》中的医德教育思想[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4).
[6]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7]van Manen M ichael A..The Ethicsof an Ordinary Medical Technology[J].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2015,(7).
[8]Sokol Daniel K.Once a Month,or the Secret to Raising the StatusofMedical Ethics[J].BMJ,2015,(27).
[责任编辑:刘烜显]
简红江,遵义医学院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贵州 遵义563003;何国蕊,同济大学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上海200433;何国忠(通讯作者),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昆明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44
G02
A
1004-4434(2016)09-0025-05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伦理探究”(JD-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