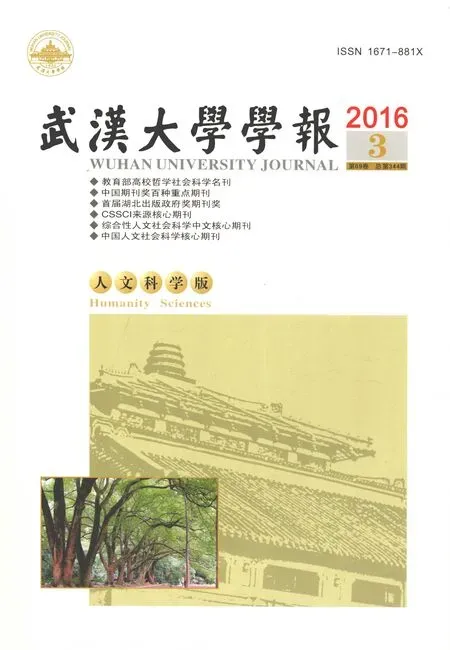近代中国的知识进化论及其反思
2016-02-21黄燕强
黄燕强

近代中国的知识进化论及其反思
黄燕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观包含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主张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近代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这种观念,但在那个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无论是持守传统者,抑或是主张西化者,还是科学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进化论思维,并将其引入文化论辩中,形成或保守、或激进的文化(知识)进化观。根据近代中国学界的知识进化论及章太炎对此提出的俱分进化的反思,我们应当尝试超越东西、古今文化之争,也要超越知识单线进化的观念,回归常与变相统一的文化观,以此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知识(文化)进化论; 中体西用; 东西古今之争; 俱分进化; 近代中国
19世纪中后期,进化论占据了西方学界的主流,不仅是查尔斯·达尔文系统地阐述了生物界的进行规律,奥古斯特·孔德也提出了社会与人类理智发展阶段论,赫伯特·斯宾塞则引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建构了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观、历史观、道德观、文化观和知识论等*关于文化或知识进化理论,参见凯特·迪斯汀的《文化的进化》,李冬梅、何自然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关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参见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文化与知识方面而言,晚清的“中体西用”论者还坚信传统文化(知识)含有普遍的、确定的常道,其发展是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但在20世纪初,随着各种进化理论的东渐及其迅速地深入人心*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此前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竞争也,进化也,务要优强,勿为劣弱也。”(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年10月):“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载许纪霖、田建业:《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这时无论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的西化论者,抑或科学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知识进化的观念,并据此来开展其东西、古今文化之争的议题。
然而,知识(文化)必然是单线进化的吗?知识只在求变求新而没有普遍的、确定的常道?进一步追问,知识必然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那么,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彼此可否沟通?近年,我们尝试超越东西、古今的文化之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来反思知识进化论呢?带着这些问题意识,本文旨在探讨近代中国学界的知识进化论及人们对此提出的相关反思。
一、 “中体西用”论与文化的常和变
经与权(常与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经者,常也,指亘古不易、普遍永恒的常驻性;权者,变也,指因时义之所宜的变通性。经(常)是自然和人事所遵循的必然之则,权(变)则是实现经(常)的方式,二者既相反,又相济。中国哲人很早就用这对范畴来描述文化发展的辩证法。《诗经》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中就包含经与权、常与变的文化观,而经和常是“本”,权和变不是彻底地、全盘地否定这个“本”,乃是根据、立足于“本”来实现文化在新环境、新时代的“新命”,从而维持文化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即返本开新。孔子讲“因与损益”的文化观,“因”指文化思想中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常道,而“损益”指因应社会存在、时代精神的变化,对原有文化进行减损或增益,以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引用孔子的“殷因于夏礼”章,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在董氏看来,天亘古不变,道也永恒确定,而载道之书即为常经,故汉儒提出“经为常道”的命题。古代经学家虽奉儒经为常道,但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中,仍然显露了经学家在追求确定性之常道时,既有因循地继承,也有维新式的变革。
常与变相统一的文化观表现为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参见李存山:《中国文化的“变”与“常”》,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体”与“用”的哲学范畴见于《易传》,但并不连在一起,《荀子·富国》篇始将“体用”并举。魏晋玄学家把“体用”与有无、本末之辩相联系,唐宋学者进而以“体用不二”来表述道与器、理与气的关系。故在近代以前,“体用之辩”更多地呈现形而上的意义;而在近代,“体用”则与古今、中西的文化之争等问题相结合*杨国荣:《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向文化观、知识论的领域扩展。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主要表述一种文化理念,其内在含义有:
第一,文化具有连续性的常道,也有阶段性的权变,故文化的发展要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中体西用”的“体”即是恒常的道,指儒家内圣的道德伦理学,属观念上的价值体系;“用”则是变化的器,指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属物质上的工具层面。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王韬:《弢园尺牍》卷4,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56页。邵作舟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类似的话语,李鸿章、薛福成、张之洞等都曾说过。作为“体”的中学是形而上之道,作为“用”的西学则是形而下之器,“中体”与“西用”的结合,就是道与器的统一,道不变而器日新,故“中体西用”论蕴含常与变的文化观,是在谨守常道而求其变通。正如代表传统价值观念的“中体”是主导之维,指称物质器技层面的“西用”是从属之维,则“中体西用”论所蕴含的文化发展之常与变的关系,是以普遍的、确定的恒常之道为主导,而以特殊的、不确定的变化之器为辅助,前者保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后者实现文化发展的创新性。这与孔子的“因与损益”文化观相一致。
第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观照,一种文化既有优点,也存在盲点。“中体西用”论就预设了这种观念,前引王韬的话便含此意。又如汤震说:“盖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失其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有时暗合于道。”*汤震:《危言》卷一《中学》,郑观应、汤震、邵作舟等撰,邹振环整理:《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他们都认为,中学之所长在“道体”,所短在“器用”,而西学之所长在“器用”,所短在“道体”,要“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之道”*汤震:《危言》卷一《中学》,第273页。,即“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载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1册,第160页。,使中学与西学在体用模式中互补互通。这反映了他们承认中西文化皆存在盲点,故在信守儒经为常道的同时,也认识到诠释经书的经学和儒学,在工具性的技艺之学方面不如西学。当然,说中学以道胜而西学以器胜,这明显带有中学本位主义的立场,那是尊经时代所必不可免的,是传统士大夫受儒经信仰之心灵积习的影响而使然。但与民国西化论者彻底的、全盘的否定性思维相比,“中体西用”论者是较为理性和包容的,并表现出自觉的文化反思意识,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
第三,以传统经学和儒学为主体来吸取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中学与西学。尽管严复曾指出,“中体西用”模式背离了“体用不二”的原则,片面地以道体来定义中学及以器用来规范西学,忽略了中学与西学均有体有用的特质*参见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一文。严复在文中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根据“体用不二”原则,他在《原强》篇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观。民国期间,他发表《民约平议》、《与熊纯如书札》等,揭露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弊端,说这些非中国所宜适用。这表明晚年的严复已超越文化进化观而回归传统。。但并不尽然,晚清的开明学者如郭嵩焘就强调“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张树声的《奏议》提倡“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征引其言而发挥其说,详细列举了西学之体与用所指称的知识对象。可见,“中体西用”有时只是一种态度的宣称,表明持论者的文化本位观念而已,其在实事求是的文化研究上,已然突破了体用分离的思维,承认西学有体有用、有本有末,且基于中西文化的一致性与共通性的前提,致思于中学与西学的融会贯通。但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所有体用模式所表达的世界文化结构之设想,其结果都可能由体用之二元走向“体”之独尊的一元论,令世界文化结构因而失去对称与均衡,故要超越体用的框架来描述世界文化的多元普遍性。
“中体西用”论的常变结构虽以常为主变为次,然近代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都在变,思想、知识也在变,“变”成为历史与文化的主题,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道器关系的转向体现了这一点。谭嗣同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谭嗣同:《报贝元征》,载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196~197页。作为形而上之体的“器”是变化的,作为形而下之用的“道”必然随之而变,故道不是普遍的、恒常的,载道之书也非常经,“经为常道”的信念因而动摇,至民国则渐趋瓦解。严复说:“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严复:《天演论》,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69页。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宣扬进化论而抨击旧文化之弊。这预示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将要兴起一种崇尚“苟日新,又日新”的进化主义,从而将古代“变中有常”的文化观,修改为“变中求变”。求变求新的观念与晚清东渐的进化论相结合,形成一种进化的文化观,可称之为“知识(文化)进化论”。进入民国,教育部“废除读经”所反映的求新求变的文化观,就内含知识(文化)进化的逻辑,其必然结果就是否定“中体西用”论。这使20世纪初的文化论争,从体用模式转向了东西、古今之争。
二、 东西、古今之争中的知识进化论
体用模式包含空间上的东西之争问题,今人将持守“中体西用”的东方文化本位者称为保守派,而把主张“西体中用”的西化论者称为激进派。如上所述,前者的文化观是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把常与变辩证地相统一,追求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后者引入进化理论,把认识过程描述成单线直进的现象,文化和知识则在不断地向前进化。激进论者接受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阶段论,视中国为封建专制社会,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半开化的,而西方是现代社会,其文化代表了先进与文明,中国文化应接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法则,被当作糟粕而淘汰掉,至多美其名曰为“国粹”、“国故”,而作为历史材料来研究。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和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论,就显示了进化的文化观与知识论倾向。陈序经宣称:“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化得多。”*陈序经:《东西文化观》,载田彤:《陈序经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5页。胡适说:“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大公报》1935年3月31日。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说:“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的进化观念(这话说来很长,将来再说罢)。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他要应用进化观念来研究一切哲学问题,这包括文化问题和知识问题。他们在比较东西文化时,明确地引入了“进化”概念,以此来界定东西文化的优劣。他们曾反复地申述,欧洲文化是现代的、进化的,而其“之所以成为和趋向为世界文化,是因为她是日新月异、比较优高的文化”*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下)》,载田彤:《陈序经卷》,第131页。。即是说,欧洲文化不断地向前进化,中国文化则长期停止不前,而文化前进的动力则源自“竞争”。根据“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法则,高级的、现代的欧洲文化应普适为世界性文化,低级的、落后的中国文化则要被彻底地放弃,接受全盘的或充分的西化。所以,“全盘西化”又译作“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原题: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载《中国基督教年鉴》1929年卷,收入《胡适全集》第36卷,第383~393页。,即“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潘光旦语,见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载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23日。,表示要与传统决裂,故西化论思想内含知识进化的逻辑,主张“重估一切价值”。
陈序经等人的知识进化论与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等基于科学哲学而建构的知识进化理论有所不同。一方面,陈序经等接受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文明发展阶段论,把文化(知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简单地对等起来,认为现代社会对应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知识)只适应于传统社会,不能进行创造的转化。陈序经说:
文化是由人类所创造,过去的文化,只是前人努力得来的结果。现代和将来的文化,还要今日的我们善继善承地不歇地去发展与创造。*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载田彤:《陈序经卷》,第96页。
过去的文化属于过去的时代,现代社会需要与之相应的文化,这要求我们去重新地创造,而非继承传统。张季同(张岱年)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
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除地域的不同外,尚有时间上阶段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西洋文化实优于中国的,因而中国文化中应保持而发展者少,西洋文化应介绍而吸收者多。*张岱年:《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这里的“时间”指过去、现代与将来,“阶段”指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中国文化属于过去和形而上学,西方文化属于现代和科学,从而将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简单地对等起来。但是,孔德把人类理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各划分成三个阶段,并将二者互相对等起来,这是有问题的。正如卡尔·波普尔指出的,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不可预测的,孔德和密尔设想的动态的共存规律与连续规律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亦非科学的假说*参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83~94页。。因此,知识进化论者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定义为前现代社会,说中国文化处于形而上学阶段,这既忽略了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也忽略了与此相应而起的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之生长,所以才会认为传统文化是陈旧的、无用的、惰性的,而看不到其与现代性相契之处。
另一方面,知识进化论者认为,知识是单线直进的,其随着时间的前行而不断地发展、创造,现在的知识一定超越过去的,将来的知识又必然优胜于现在的,一切知识都是历史性的,没有常道的确定性,所以他们不注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只崇尚知识的变化与增长。“中体西用”论者还相信中国的道德伦常具有普遍性与恒常性,陈序经反驳了这一点。他说:
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一般人所称道为国魂所在。他们忘记了道德上的信条,并非施诸万世而皆准,放诸四海而可用。他们忘了道德也不外是文化的一面。旧的道德只能适用于旧时境。时境变了,道德的标准也随之而变。*陈序经:《东西文化观》,载田彤:《陈序经卷》,第87页。
陈独秀更进一步说: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独秀文存》,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冯友兰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近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有些人常把某种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为一谈,这是很不对底。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可变者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者则无此问题。”(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399页)他认为道德伦理蕴含常道,不可与社会发展阶段论对等相谈。张岱年有类似观点,参见其《首先之“变”与“常”》一文,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9~162页。
在他们看来,传统道德、礼教、政治等都不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不再适应于新时代,必须随时代之变而变。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过,以“封建社会”来界定传统社会的性质是否可信*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对中国古代为“封建社会”的观点,提出了严正的挑战。,而简单地套用社会发展阶段论,又根据社会形态来定义文化的性质,宣判封建社会的“封建文化”是毫无价值,是“丑恶病态的东方文明”(吴稚晖语),要拥抱日新月异的西方文化。这是只见文化之变而不见文化之常的单线直进式思维。然卡尔·波普尔重视知识进化中的因果连续性,强调新知识与原知识存在密切联系,新知识是在继承原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须遵循原知识的理论范式。托马斯·库恩在探讨科学革命结构时,尽管他使用了“不可通约性”这个词,但他同样强调新旧范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承认旧范式的价值是为新范式提供理论的、实验的基础*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真理、合理性和科学知识增长》章,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10~360页。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通过革命而进步》章,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145页。。这与近现代中国知识进化论者的单线直进观是很不同的。
东西之争是从空间维度来谈文化进化,与此相对的古今之争,则从时间维度来论文化之共殊。冯友兰较早地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的界限”,他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冯友兰:《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载《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他用类型与个体(共与殊)的理论来区分古、今文化,说西洋文化指近代底或现代底文化(今),中国文化指中古底或传统底文化(古),而西洋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属同一类型,故中西文化均非完全独特的个体,彼此存在共通性,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也就不是把传统彻底地抛弃,而是像西方那样由传统开出文化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参见陈来:《冯友兰文化观的建立与发展》,载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1~190页。。“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从共殊的角度指出,中国文化既有特殊性,也有时代性,有适合现代社会之需要的文化内容。他们试图说明文化是共性与特殊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发展要尊重各种独特的民族文化。
然而,古与今是一对时间范畴,用此来区别定义东西文化的性质,多少显示了知识进化的观念。如前引冯友兰的话,他把中西文化分别归结为“中古底”与“现代底”类型,便显露了文明发展阶段论和历史进化论的影响,就像常乃惪宣称的那样:“一切文化都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常乃惪:《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载《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4号。又如张岱年说:“文化以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新形态,社会关系改变,则文化必然变化。”*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5页。这是把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观点。事实上,在那个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无论是主张西化者,抑或持守传统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进化思维,并将其引入文化论辩中,形成激进或保守的文化(知识)进化观。
但又不像西化论者主张知识单线直进那般,保守主义者讲文化的时代性,把文化区别为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主要说明文化发展是常与变的统一,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在坚守常道基础上的新变结果。冯友兰说:“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冯友兰:《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载《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311页。冯友兰用了一生来思考和解决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而其前提是承认传统文化含有不变的常道,在常之中求变。张岱年也说:“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一贯的发展。”*张岱年:《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3页。新与旧的统一即是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同一性。
因进化的观念而令文化有新旧之别,然后演化为古今东西之争。论古今者,以为东西文化是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样式”,东方属中古底类型,西方属现代底类型,它们的差别映现在时间坐标轴上。争东西者,执持静与动、消极与积极、保守与进步、直觉与理智、艺术与科学等对立范畴,以为文化价值之衡准,如主静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是无意义的,主动的、积极的西方文化才有价值,前者属于过去,后者主导现在与未来。然则,无论是古今之争,抑或是东西之辩,都蕴含一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其最终的问题是:中古的、东方的文化应否存在和如何存在?激进的西化论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们根本不认为东方文化还有存在的必要,诸如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或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探讨等议题,自然不会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文化保守者虽带有进化的观念,却不认为文化的衰老是最终性的、整体性的,故相信传统文化还有确定的常道,要以常道为基础来求文化之变。
可以说,西化论者是彻底地接受知识进化论,并以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将传统界定为有机的统一整体,全盘地否定之*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5~132页。。他们认为,一种文化如同一个有机体,在自然的生长过程中,从幼壮走向衰落是一切生命故事的必然过程,所有文化都会在一定时间之后走向终结。而且,文化的再生是不可能的,因文化的衰老现象源自其内在精神的衰老,这种衰老是最终性的,也是整体性的,既无法恢复生机,又不能与异质文化相融,便只有将西方现代文化这一完整的统一体全盘地移入中国,“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2页。。在文化(知识)革命的运动中,不歆羡乐观主义的连续性,而追求末日式的断裂性。在此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知识进化运动,其核心理念就是知识进化主义。
三、 科学:知识进化的完美形态
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之一,科学观念获得了当时人的普遍认同,乃至成了部分学者的价值—信仰体系。正如胡适所描述的,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人们都不敢公然地表示其对科学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岳麓书社2012年,第9页。。人们赋予科学无上尊严的地位和权威,这使科学从纯粹知识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实体,深入至人们的思维与思想中,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和认知。这个时期的人热衷地讨论着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教育、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关系问题,就是要把科学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科学来改选整个世界,包括文化与知识。
当时人之所以如此崇拜科学,因其相信“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12期。,科学知识是确定性的真理,是知识进化的完美形态。如吴稚晖、李石曾说: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吴稚晖、李石曾:《新世纪之革命》,载《新世纪》1907年6月第1期。
革命推动社会的进化,科学则推动文化、思想、知识的进化,而且是比社会进化更为根本的进化。陈独秀说:“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他和吴稚晖一般,视科学为人类社会、知识进化的动力因和目的因。这不仅指自然科学领域的客观知识,也包括与主观心性相关的人生、道德等领域的价值观念。如蔡元培说:“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函》,载《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只有经过科学证明的道德,才具有现代性,才能在“优胜劣败”的知识进化链中继续挺立。
基于这种认识,科学主义者宣称,一切文化与知识都要接受科学的洗礼或改造,以科学为其前进的目的。丁文江概述了科学在知识论领域占据统领地位的演变史:从17世纪开始,宇宙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相继地科学化了,玄学最后也要向万能的科学投降*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17页。。故丁文江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论”一词*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12~16页。,其意思如胡适一言蔽之曰:“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胡适1929年6月3日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0页。他们相信科学是知识进化链上的完美者,其余的总难免被“淘汰”的命运。胡明复更进一步说:“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之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载《科学》1916年第2卷第7期。《在创刊号底卷头》说:“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精神作用,无不成为科学底对象,科学底疆土。”(《二十世纪》1931年第1卷第1期,第3页)诸如此类的话语,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贺麟在《文化的体与用》说:“我承认中国一切学术文化工作,都应该科学化,受科学的洗礼,但全盘科学化,不得谓为全盘西化,一则科学乃人类的公产,二则科学仅是西洋文化之一部分。”即便是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者如贺麟,也追求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他们表达了一种共识,即杨国荣指出的:“知识之域的每一进展,都意味着科学领地的扩展,科学在此似乎构成了知识发展的极限:知识的任何增长,都无法超越科学的界域。”*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页。因科学是知识进化的完美的、最终的形态。
但知识必然以科学为归趋吗?唯有真的知识才是合法、合理的吗?假使美和善的知识是未经实证而非真的,那就不是知识了*孙中山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见《孙文学说》,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页)这种见解流行于那个科学至上的年代里。?崇拜科学者相信科学知识是绝对的、确定的真理,却未曾如波普尔那样地认识到:“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库恩指出,任何科学范式都会经由革命而重建,故科学知识也有时代性,而非永恒的、确定的常道。又当科学主义者宣扬“科学方法万能”、“哲学科学化”时,波普尔则批评了“归纳万能”说,且指出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有其哲学的根据,哲学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继承托马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Paul)则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存在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参见赵克:《论“划界”何以可能》,载潘德荣、童世俊、付长珍:《六十年哲学的反思与六十年的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所以,把科学精神、科学知识还原为方法,以方法为追求知识的目的,又以客观、实在为知识的最终本质,那是对知识发生方式及其增长机制的误解。
同时,知识在进化中累积,这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表现出革命性的倾向,故知识与真理具有过程性和历史性。当波普尔说:“知识的增长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时*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桥、曾聪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他一方面揭示科学不能提供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一方面又强调选择前后的知识之间的连续性,他论述三个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在说明知识的“进化”绝非断裂性的飞跃。反观科学主义者,他们是那样坚定地信仰科学,又如此斩截地在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划下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把传统与现代悬隔起来,宣称中国文化形态在现在和未来都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与重建。这样的自信源于单线直进的进化论,崇尚断裂性的飞跃,不关心新旧间是否存在连续性。比较而言,波普尔是谨慎的,他对“进化”与“进步”作了恰当的区分,而未把两者等同起来;他虽然提出了科学知识进化论,却在知识的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显得有些犹豫,故不愿意向左转而拥抱激进。
近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与西化论者一般,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受了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相信某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然历史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律或决定论,没有什么真理(科学知识)可赋予人们预见未来的能力,未来不是一个定数,世界本来就是非决定性的*参见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伊·普里戈金的《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等书。。科学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信仰科学,相信科学方法在一切领域都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有效性,因而是普遍必然的,是确定性的,可用来定义生命与历史的本质。盖“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历史遵循着必然的、普遍的社会学规律,人们只要把握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根据确定的因果律,“由因求果,由果推因”,便可大规模地“解释过去,预测未来”*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第24页。,科学也由此成了“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陈独秀:《〈新青年〉宣言》,载《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号。。但是,不仅波普尔详细地分析了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同样拒绝所谓的“决定机制”,即任何特殊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5~359页。。
科学主义者还认为,唯有经过科学洗礼的知识才是现代的,而所谓现代知识就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并表现出解决现代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有效性。如此说来,科学知识进化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崇尚知识的有用性,把功利效果作为判断知识和价值的准则,故科学主义者往往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功利原则相结合。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的胡适、张东荪等,他们的科学观和真理观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而根据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来评价知识,属于中古底类型的中国文化已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自然成了无用的国故学,而必须从西方引进“新文化”。新与旧相对,在倡导“新文化”的科学主义者那里,“新”不只是一个时间状语,“新”更是一种实用的标准,代表文化的有用性,“旧”所指称的文化是没有用的、与现代社会绝缘的。
四、 俱分进化的反思
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大多相信,进化与进步、优越、美善、积极等关联*吴丕说:“进化一词作为生物学名词,本来并没有进步之意。由于斯宾塞的努力,这个词汇具有了现代含义,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进入中国以后,进化一词既有原意上的进化,也有进步的意思。凡是发展、展开、变化、进步,都可以用‘进化’一词来表示。”(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但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是把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象征着现代性与实用性。然而,进化必然会导向真、美、善吗?进化真的是万能公式,可以毫无保留地应用于文化与知识领域?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当年的科玄论辩中,梁启超、张君劢等已对科学主义发表了中肯的批评,但论题主要在科学与人生观的领域,较少涉及进化的文化观与知识论。且玄学派多少还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如梁启超根据“人类德慧智术进化”之“公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不过,梁启超晚年在批评科学主义时,对进化论有所反思。,并采用文化有机体理论,把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划分为:胚胎、全盛、衰落、复兴等时期,这隐含着一种知识进化的观念。当时能对知识进化论提出反思的学者,大概要算章太炎了,以下就主要介绍章氏的观点*关于章太炎的“反进化主义”思想,可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中《章太炎的“反进化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8~197页。。
针对时人崇信进化论的现象,章太炎曾直下针砭地说:“望进化者,其迷与求神仙无异。”*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2页。在《四惑论》一文中,章太炎说:“昔之愚者,责人以不安命;今之妄者,责人以不求进化。”(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6~457页)他强烈批判那种“你不进化,我强迫你进化”的主张。“进化”虽合理,但如尊其为普遍必然的公理,那就等于迷信。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指出,进化的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因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6页。,进化也与退步、差劣、丑恶、消极等关联*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93页。。章太炎提醒人们,不可仅从正面角度单向地表彰“进化”,要知道“进化”也有负面效应,就其趋向苦、恶、丑的倾向言,名义上说是进化,本质上乃为退化,故进化与退化并存,进化不是万能公式。虽然,章太炎在文中说:“惟言智识进化可尔”*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386页。章太炎《五无论》说:“今自微生以至人类,进化惟在知识,而道德乃日见其反。”(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42页)文章以知识为进化、道德为俱分进化的意思与《俱分进化论》一致。,他承认进化论适用于知识领域。但章太炎撰写《辨性下》一文,修正了那种知识“单线直进”的看法,他说:“我见者与我痴俱生。……意识用之,由见即为智,由痴即为愚。……痴与见不相离,故愚与智亦不相离。……痴与见固相依,其见愈长,而其痴亦愈长。”*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辨性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7、198、202页。随顺语义,由末句可衍伸为:其智愈长,而其愚亦愈长。因知识的积累固然提升了人对物的认识,并用名言以陈述之,然物皆为空而非实有,名与物似相一致,实则相离,故语言所陈述的关于名与物之关系的命题,根本地是非真的,又何来知与物相符合的真理(知识)。可是,人们常常执著于物的表相和名言自身,视其为道、天理或真如本体,落入遍计所执性或依他起自性的迷妄中而不自知。这便是愚,它因智而起,与智相依而相长。故章太炎说:“凡人类思想,固由闭塞而渐进于开明,然有时亦未见其然,竟有先进步而后却退者。”*章太炎:《诸子略说》,载章太炎:《国学概论(外一种:国学讲演录)》,岳麓书社2010年,第220页。思想、文化与知识在其历史过程中,是进步与退步并存的。
既然知识是进化与退化并存,胡适所谓“将来只有科学知识”的宣称,章太炎自然不会同意。在章氏看来,科学固然是一种知识形态,但科学不可能成为全部人类知识的唯一形态或最终形态,一切合理性的知识并非只在归纳与演绎相互为用的科学方法中才能实现。如科学主义者批评传统的人生观、道德伦理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也就是非知识性的,他们要运用科学方法来造就一种科学的、唯物的、自然主义的,可称之为真知识的人生观与道德伦理。章太炎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他说:
近人谓:“道德由于科学”,与晦庵穷知事物之理而后能正心诚意者何异?必谓致知格物,然后方可诚意正心,则势必反诸禽兽而后已。……科学之影响,使人类道德沦亡, ……如云以自己之旧民,作现在之新民,则弃旧道德而倡新道德,真“洪水猛兽”矣!*章太炎:《〈大学〉大义》,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0~331页。
又云:
科学者流,乃谓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此其流弊,使人玩物而丧志,纵欲以败度。*章太炎:《适宜今日之理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336页。
首先要说明,章太炎理解的“科学”指“诊察物形,加以齐一,而施统系之谓”的系统学问*章太炎:《规〈新世纪〉》,载《民报》1908年第24号,第43页。,即系统地研究物或器之形态及其内在联系的知识。这未免稍有偏颇,忽略了科学的精神层面。其次,章太炎反对有神论、唯我论、唯理论和唯物论等本体论思想,谓其或以虚幻的神与上帝,或以主观的自我意志,或以虚构的绝对精神,或以具体的物质粒子,来作为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体,说它们错误地以主观代客观、以精神代实在或以局部赅全体。再次,章太炎欣赏主观唯心主义,又批评感觉论、唯理论和先验论等在认识论方面的不足,他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惟心论”,宣扬“万法惟心”、“追寻原始,惟一真心”的理念,心、真心是“真如”或“阿赖耶识”,为万物本体,是全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根源*此段论述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8~290页。。
结合章太炎的科学观与认识论等,然后我们能更好地领会前引两段话的意思。应该说,章太炎没有完全地排斥科学和西洋哲学,他也“有取于西洋”,对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在批判之余亦取材于是,但西洋哲学偏向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而不注重道德实践,即重本体而轻工夫,这在接受阳明心学的章氏看来(晚年认同心学),离开工夫别无本体,如不内证于心而付诸行,又何来知识,怎么能达到知行合一的道德境界。章太炎认为,仅从训诂(科学方法)中求得的哲理,即使人人都能给予经验性的证明,但只要“未证之于心”,那便是外在的、与己无关的东西,“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如“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将工夫转化为本体。因心是“吾人的精神界”,本体之心在工夫之展开过程中证得*章太炎:《国学十讲》,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270页。。基于阳明心学传统,章太炎认为本体无内外,心、性与良知皆是本体,故精神本体不待外求,无须“致知格物,然后方可诚意正心”,道德的修持虽然不是完全地与关于物的知识无涉,但心体、性体与良知本体的呈现绝不依赖于物或物的知识。因此,章太炎批评“科学者流”,若以心性合物,以物的知识规范心性,那与禽兽之以性逐物全无分别,这种所谓合于科学的新道德,必然“使人玩物而丧志,纵欲以败度”,最终令人类道德沦亡。
概括言之,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修正了单向度的知识进化论,批评了那种宣称“将来只有科学知识”的科学主义论调,也否定了科学的人生观与道德观。章太炎之所以如此,除了看到进化与退化辩证统一的原理,原因还有:其一,由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可见,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哲学创作均以继承和转化中国文化为职志,尽管他也在求文化之变,但那是奠基于文化之常,是在常之中求变。其二,章太炎不赞同把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相对等的说法,并反驳了西方的文明发展阶段论,指出那是西方进行文化侵略的悖论,西方列强借此来“扩张兽性——是则进化之恶,有甚于未进化也”*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450页。。他深刻地揭露了“进化”的消极性及知识(文化)进化论所隐含的侵略性。其三,章太炎认识到文化的共殊,主张文化多元论。他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除魏、周、辽、金、元五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第431页。“可相通”指文化的普遍共性,“不可相通”指文化的特殊性,“此乃对‘文化多元论’之认知——文化既各各相异,各有其特性,唯有相互尊重,而不能也不必要求甲文化臣服于乙文化”*关于章太炎的文化多元论,参见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4~58页。单世联:《进步论与多元论:章太炎的文化思想》,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由此,章太炎批判“文化帝国主义”——以外国制度强加于本国,及“文化通性论”——承认公理、法则与永久模式,也反对西化论者的文化激进主义。
一些与章太炎同时或稍后的学者,如蔡元培、梁漱溟、钱穆、杜亚泉等,曾撰文反思过进化论。如蔡氏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纠正“强权即公理”说,梁漱溟批评单线直进的“独系演进论(unilinear development)”,钱穆称人类历史发展既有强力与斗争,也有仁慈与和平,杜亚泉则批评了进化论偏重物质层面而忽略了精神层面*参见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第167~173、181~183页。梁漱溟早年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柏格森生命进化哲学的影响,表现出一种乐观的进化观,而在后来的《儒学复兴之路》等文章中,则对单线进化论做了修正。。只是,这些反思仅就进化论而立论,并未深入涉及知识(文化)进化论的本质问题,故略而不谈。要强调的是,进化论的确存在局限性。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赫胥黎就已批判性地修正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近百年来,诸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进化论口号与观念,中外学者都已提出质疑和反思,且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取代之,希望建构一个和而不同、多元共荣的文明世界。章太炎之所以要反对进化主义,反对公理主义,就是意识到文化或知识进化论必然要导向独断的、一元的文化霸权主义,造成世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庄子“齐物”的平等主义,才真正蕴含对人权、人道和多元性文化的深重敬意。
总之,我们已经认识到要超越体用模式与东西古今文化之争的思维。同时,我们还应超越知识单线进化的观念,用齐物的平等眼界来通观世界文化。这不是要否定人类知识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长,超越是如文章所论述的:第一,要认识到文化发展有常有变,应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第二,要反思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论,不能把文化形态与社会形态简单地对等起来。第三,求真的科学知识并非完美知识的唯一形态,可爱的、美和善的知识不一定是真的或可信的,却也可能是完美的、确定性的。第四,知识既进化,也可能退化,进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退化的也不一定就是差的,在评价知识的价值时,应放弃“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走出彻底否定与全盘西化的逻辑。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
●作者地址:黄燕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Email:hyq4413@aliyun.com。
●责任编辑:涂文迁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 China
HuangYanqia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outlook,which contained dialectical unity of invariability and variability,advocated for invariability in variability and seek variability in invariability.The neoteric “Chinese learning for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theory inherited this idea.However,in that era,which the biological evolution,social Darwinism and scientism was popular,whether those who held traditional or those advocating westernization or science advocates,they more or less accepted the thought of evolution and brought it in the cultural debate,to form conservative or radical cultural (knowledge) Evolution View.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knowledge and to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all points rose by Zhang Taiyan.Finally,it points out that we once jumped out the debate of Orientalism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bat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ulture,we must have knowledge beyond the concept of a single line of evolution,returning to the unity of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invariability and variability,in order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 words:knowledge (cultural) evolution; Chinese learning for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use; Western ancient dispute; all views evolution; modern China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创新项目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