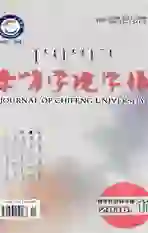西方民族概念引入近代中国源流考
2017-01-05王烨
王烨
摘 要:中国本土“民族”概念具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演进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念是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基础。近代“民族”一词在汉语中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相对封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鸦片战争之后,各种西方文化随之涌入,“民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明显受到了西方民族—国家、种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一词才逐渐被普遍使用并具有了现代性内涵,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关键词:民族;西方民族概念;近代民族概念;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37-04
民族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自身形成发展演化具有客观实在性,民族其形成以及发展、演进,拥有客观实在性。伴随着历史变迁,民族作为历史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关于汉文“民族”一词来源,在我国学术界曾引起广泛争论。之前学界曾长期认为,中国古代并无“民族”一词,近代流行的“民族”,作为汉语言词汇,是由西方国家传入。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已证明在古代汉语典籍中有“民族”一词出现,是本土的词汇,绝非近代的“舶来品”。对此,学者郝时远著文《中文“民族”一词之源流考辨》当中,特地举出了10余个例证来证明“民族”曾经是古代汉语名词之一[1]。但是,需要指出,古汉语中“民族”,其意多指为“家族”或者“宗族”而非现代意义的“民族”。例如,南朝宋齐时期《夏夷论》(顾欢著)中的“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这是我国古汉语中所能找出的“民族”最早出处,而所谓“民族弗革”,这4字指的是国人族属,也就是华夷之分[2]。类似于现在的民族概念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多用“民”“族”“人”“种”“类”“部”等指代。由此可见,就古汉语而言,其表示的是某一群体或者是庶民大众,而非现代汉语当中的基于某些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具有近现代民族的含义。
近代“民族”一词在汉语中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相对封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鸦片战争之后,各种西方文化随之涌入,“民族”一词开始大量出现,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先驱吸收西方民族思想使得中国“民族”概念由古典表达系统向现代形式转型。“民族”一词才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
一、 西方“民族”概念的演变
西方“nation”(民族)一词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ethnos等词汇,均指以出身、血缘等因素为纽带的“自己人”或外来人[3]。在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拥有相近出身或者是一定血缘的族群,通常来自于一个共同地域。“nation”在拉丁语中进一步表示“生活在共同地域”人群的含义。
在中世纪时期民族一词主要指代同源或同乡关系,真正认识当时民族概念,还需要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特征相联系起来。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存在天然的种族优劣关系。封建等级制度与基督教是中世纪两个最为明显的社会特征,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与“特权世袭”来统治下层人民,由于统治阶级往往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因此,他们不停宣扬自己拥有高贵的血缘,使下层人民认定是上帝派他们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因此,霍布斯以这一民族概念来论证当时英法等国拓展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是上帝指示的,具备正当性。洛克更是认为当时美洲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存在,“在他们尚未联合起来、共同定居和建成城市之前,他们所利用的土地还是属于共有的”[4]。由于民族概念在古代社会具有表示人们相同出身与血缘关系的原初内涵,由此,在欧洲中世纪时,“民族”概念是与“等级”概念紧密相关的,是指那些具备特权地位的社会中的“贵族阶层”。
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的概念在近现代先后具有很大的差异。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极大推动了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著名的“宗教改革”以及席卷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等,所宣扬的以人为本,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种全新国家的诉求中,“nation”民族概念在此时也发生了改变,逐渐演变成一个与“民主”同样具有政治高度相关的词汇。例如哈贝马斯就指出,近现代以来的“国民”和“民族”有着同样的外延,“人民”以及“民族”,成为具备相通性的两个概念,它们都可以指代一个国家之内的公民[5]。由此,“一个民族”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这个理念之下,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演变出的公民内涵,并逐渐对世界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虽然,这些“民族国家”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群体,可是,基于构建国家这一历程当中,人们接受了“民族”这一概念新的内涵,于是,“nation”的原有内涵,即生活在共同地域、语言、风俗相同的人们共同体的基础上,同时也表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接受相同政府管理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安东尼·史密斯认为,“nation”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自同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6]。哈贝马斯形象的提出“民族”概念在近现代可谓拥有“两副面孔”。公民享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往往生活着众多血缘、语言、历史归属等众多民族,因此当今世界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国家也往往是多民族国家,而“民族”概念,也就从中世纪原有的“贵族”内涵拓展成为现代的“公民”内涵,不仅具有了内部族群凝聚力,也体现出外部政治整合的作用,其成为人类社会团结的纽带。
二、西方“民族”概念传入近代中国的理论溯源
在当代西方学界中,“民族”概念对应的理论,呈现多元内涵并存的差异格局,可以归结为4种理论体系:原生主义理论体系、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族群——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7]。与中国近代时空对接的西方语境下的民族概念,主要是在原生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包含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基于“民族——国家”理论(即“nation-state”)发展而来的现代内涵。
鸦片战争之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有教无类”的民族观,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局在鸦片战争之时,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由此,中华民族迎来了亡国灭族的极大危机,中国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付“变局”,这时候传统天下观以及民族观显然无能为力,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巨大的民族危机激发了部分与西方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萌生新的观念,“民族”的现代性内涵随之传入中国,经过西方民族理念不断涤荡,传统民族观念在中国知识界逐渐淡化和消解,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最终形成。
(一)具有国家实体观的近代民族概念
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传统中国的“国家”概念是天下、邦国、家室的总称,是一种普世价值的大一统王国,在君王政体的统治下,中国没有西方的联盟、共同体等概念,也没有组织或者统治等管理学概念,更谈不上国家的主权想法等等。而当鸦片战争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开中国大门,不仅对我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封建文化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更多是让封建社会“天下主义”的国家实体观面临了严峻的考验,这一时期,对民族概念的阐释不再是局限于对地域、经济、文化等诸特征的阐释,更多的是倾注进了强烈的国家意识与民权意识。
1874年前后,中国学者王韬最早把“民族”的现代概念介绍给人们,其《洋务在用其所长》文章中表示:“夫我中国天下至大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富饶,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顽。”随后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们也将“民族”一词在文章中广泛使用。梁启超提出“民族帝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概念,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把“民族”一词介绍给国民:“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梁启超所指的“民族”,明显差异于古代概念,不再强调地域或者血统,其中拥有一定的民族相关情感、意识因素,同时也包括更多政治寓意。
梁启超在1903年将“民族”定义为“民俗沿革”之结果,这其中,梁启超指出,拥有重要的8项特质,分别是:(1)“其始也同居于一地”,所谓“非同居不能同族也”,而后,可能是同一民族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分居到各地,造成一个地域可能有好多民族;(2)“其始也同一血统”,但是,久而久之,也将吸入他族的不同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即指外表相似;(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指生活、风俗等相同。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其诸子孙,是之谓民族。此概念就是梁启超根据欧洲法学家布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对民族相关论述翻译而成的。作为欧洲政治史上基于“国家学说”理论的著名代表之一,布伦奇里的“民族”概念,是国家学说理论中的一个内容。首先,布伦奇里民族定义最大特点在于对民族过程进行了历史观察。他认为“同地”与“同血统”仅针对民族形成的初期而言,伴随历史变迁,基于现象根源学说,民族分地而居或者不同民族聚居,再或者民族同化等等,这些现象也呈现普遍性发展。其次,伯伦奇里肯定了建立多民族的国家的可能性,同时认为,可能会“合多民族”为“一国家”,这样,“其弊虽多,其利也不少”。再次,布伦奇里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建立国家的唯一准则,民族成员的“国民资格”是“国家所最渴需者”。基于对于伯伦奇里民族理论的接受,梁启超逐步改变了之前将民族定义为“同血统、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的认知,而是指出:“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即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布伦奇里的这种阐释,在近代中国民族定义的探求中起到了一种指导的作用。如孙中山:“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8]总结这一时期民族定义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民族”概念都是指代“nation”,这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极为契合。
(二)具有种族含义的近代民族概念
“ethnic”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thnos”,早期人类学家主要用其指代种族遗传因素为基础,具有相同文化与历史的相对于现代文明的小型社会群体,这一词汇在古希腊时期史籍《历史》一书中也彰显了“部落”在古希腊时代(tribe)或“种族”(race)的含义。随着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当时掀起一股全世界殖民扩张主义浪潮,西欧白人社会在面对“新大陆”不同种族及其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情势下,用ethnic来形容种族之别的含义也被突出地加以强调,“成为指称一个非欧洲人的、文明程度低下的共同体(诸如在南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或者技术水平低下的社会(诸如亚洲或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欧的白人”。
通过中国古籍文献可以发现,基于“民族”这一提法,其中指代是多样性的,例如“族”“种族”“部族”乃至“氏族”等等,当然也有“家族”或“宗族”一说,可从其内涵意义分析,这里的“族类”划分标准包含着民族要素。这与西方以地域、血缘、种族为区分依据的原生态民族概念相契合。随着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19世纪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西方进化论学派所传达的“ethnic”(民族)概念,也逐步被中国学术界所了解并加以运用。当西方《民种学》(林纾、魏易1903年译)引入基于人类学视角定义的“民族”概念,人们对于“民族”一说,也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费孝通学者认为:“民族”在中国素来拥有广泛内涵,既包括不同发展水准的“民族集团”,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集团”;再如,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定义“民族”侧重于“种族”因素,所倡导的是倾向于“种族”的革命。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受到西方人类学民族定义的影响。另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成立后,大批人类学者深入中国民族地区,将处于资本主义前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类学著作。
(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民族概念
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研究就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多本著作中探讨过民族国家问题,并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基础上对民族的形成进行说明,认为国家在民族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指出,“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覿ten)”,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覿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与这两种民族形式的转化并行的是“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因此,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概念区别于古代民族,它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部落不同于民族,只有“各部落融合为统一的人民时,民族方才产生”。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一切民族的独立,认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民族的辩证观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之后,相关民族定义、民族运动、民族自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在中国得到翻译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由陈望道在1920年翻译并出版。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各个时期的论著中,论述民族时,多次提到的语言、地域、共同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共同感情、工业条件等与民族形成息息相关,但却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关于民族的定义。列宁虽明确提出过地域、语言、心理、生活条件4个民族特征,却同样没有对民族下过确切定义。直至斯大林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首次提出对民族的定义的初步看法。随后在1929年撰写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将之前的定义进一步完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此时才正式形成。
1929年,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斯大林在1913年所作出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后,经济和文化等因素逐渐被运用到中国近代民族概念的诠释中去,“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观点,逐步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虽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专门针对民族概念作出界定,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其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1935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到“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这一观点明显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在民族概念的表述上,具有种族优劣论的“血缘”要素逐渐被忽略,更多的侧重点放到民族的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的因素上来。
纵观我国近代“民族”概念源流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民族”一词所表达含义除去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血统宗族观念外,同时吸收了西方政治性的民族——国家理论,人类学族群、种族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从而融汇形成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与话语形态。对近代汉语“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演化进行的探讨和分析,对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中国化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中国“民族”概念的与时俱进性
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现出新时代“民族”概念的时代意义。应该说,这一概念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模式,建立起更加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状况的民族概念。首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很强的局限性,将民族的“四要素”固定于“人们共同体”前,并强调“缺一不可”;而我国新时期阐释的民族概念则将“人们共同体”作为首要条件,其他构成民族的要素置于之后,这样是对民族特征的一种开放性的阐释,使得民族相关问题的认定具有更多灵活的空间。为今后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空间和领域。其次,新时期对民族概念的阐释中,强调了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性与必然性,显示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这一概念的提出,针对现阶段国内国际的情况,突出国家的安全理念,使我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将民族升到了涉及国家安全的位置。第三,一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宗教无小事”,所以,将宗教的因素在民族定义中加以强调,就是为了说明在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过程中,重视宗教的影响和作用的必要性。
“传统”与“发展”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没有僵死不变的传统,也没有毫无根基的发展。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对其探索、研究和争论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客体内涵的独特性与多重性。纵观近代西方民族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演化过程,由最初原生态的民族概念体系到近代对民族概念的积极探索,一直到21世纪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全新阐释,不仅体现了民族概念在我国经历了一种交流、借鉴、吸收、消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民族概念的与时俱进性。
参考文献:
〔1〕〔2〕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6).
〔3〕徐晓旭.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世界民族研究,2004,(2).
〔4〕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20.
〔5〕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4.
〔6〕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
〔7〕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论述.民族研究,2008,(4).
〔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620-621.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