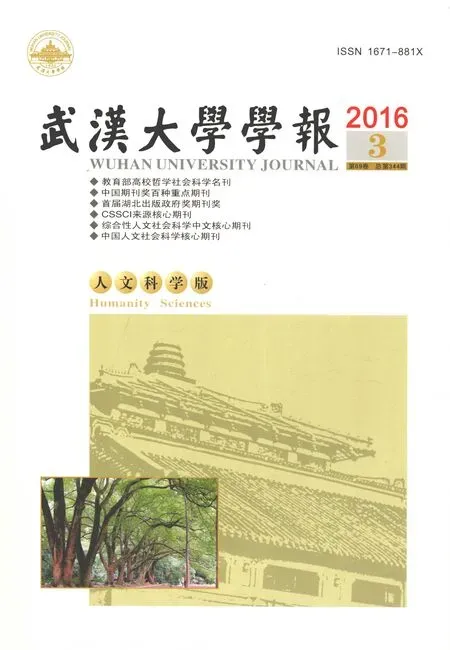游牧·块茎·无根
——西方文化旅居者在华实践研究
2016-02-21刘学蔚
刘学蔚

游牧·块茎·无根
——西方文化旅居者在华实践研究
刘学蔚
摘要:“文化旅居者”是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型国际流动人口群体,被视为“陌生人”的一种最自由的异化类型。在当今中国,以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华进行跨文化传播交际实践的西方文化旅居者越来越多。对他们的考察,是直击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东西方文化主体是如何去建构新型跨文化关系的。德勒兹的哲学阐释了一种多元、动态的生成观,而非静态的差异结构;而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生成他者和建构关系的过程。这些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的“游牧式”跨文化旅居经历、“块茎式”的跨文化实践方式和“无根性”的跨文化思维代表了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实践的一种“反模式化”的革新,也为德勒兹的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学领域的渗透及应用提供了案例支撑。
关键词:文化旅居者; 跨文化交际; 德勒兹
一、 作为文化旅居者的在华西方人
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旅居者”(sojourner)概念是由芝加哥学派华裔学者萧振鹏(Paul C.P.Siu)于1952年提出来的,萧对其的定义是“在某个海外国家旅居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被同化的陌生人”*P.C.P.Siu.“The Sojourn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2,58(1),p.34.。本研究的“旅居者” 指的是旅行或暂时居住在某个地方的国际流动人口,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他也是“陌生人”(stranger)的一种异化类型,却又区别于“定居者”(settler)和“边缘人”(marginal man)。无论是边缘人理论还是旅居者理论,都是芝加哥学派移民研究的产物,并从同化论的角度来审视移民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移民研究在21世纪再次成为了学界关注的重点,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刘学蔚:《从“陌生人”到“旅居者”——西方移民研究思潮略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07~108页。。在这个背景下对国际流动人口的考察是移民研究的扩展,在研究视角上也不再局限于同化论,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议题。
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一个在中国旅居的外国人群体,更具体地来说,是持有某种文化交流目的来到中国并暂居于此的西方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了不确定的停留方式,有些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有些人则是比较频繁地来到中国。他们虽然具有传统“旅居者”的多项特点,却又明显区别于他们。因而,笔者使用了“文化旅居者”(cultural sojourner)这个概念来定义该群体,它与“陌生人”、“边缘人”及传统“旅居者”的共性和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齐美尔所讨论的陌生人“并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漫游者”,而是“今天来、明天停留在这里的潜在漫游者(potential wanderer):尽管他没有继续迁
移,却并未失去来去的自由”*G.Simmel.“The Stranger”,K.Wolff (Trans),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London & New York:Free Press:Collier MacMillan,1950,p.402.。文化旅居者具有陌生人的“自由”的特性,甚至比陌生人更加居无定所;然而,陌生人在身份上保持着与客居社区的疏离,文化旅居者则尝试着将自己的品质和文化带入客居社区,并努力拉近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
其二,边缘人是陌生人的一种异化类型,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指涉一种新的人格类型。“他和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割裂;即使他被允许这么做,但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也不能很快地被这个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一个生活在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之边缘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是不可能互相渗透和完全融合的”*R.E.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p.892.。文化旅居者和边缘人一样,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在多个社会和多种文化中都处于边缘;但边缘人以差异为耻,希望同时被两个社会接纳,却遭遇了双重的偏见或拒绝,文化旅居者则以差异为荣,即使在某个阶段被某种文化深度影响,也随时有变化的可能性。
其三,传统的旅居者和边缘人一样,都属于他者眼中的“陌生人”,是两种文化相遇及冲突的产物。边缘人有强烈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意愿,但遭到了排斥,最后在两种文化之中都处于边缘。旅居者只是暂居在另一种文化之中,并没有强烈融入旅居国文化的意愿,而是保持了本族文化的传统和习俗*P.C.P.Siu.“The Sojourn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2,58(1),p.34.。文化旅居者和传统旅居者一样,带着特定的工作或任务奔赴异国他乡,但与较少参与客居社区生活的传统旅居者相比,深度参与客居地的社会文化生活恰好是文化旅居者的首要目标。另外,传统旅居者具有内群体倾向,拒绝异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文化旅居者则具有共文化倾向,不断在与异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寻找共同点,并以此建构与他者之间的跨文化关系*刘学蔚:《从“陌生人”到“旅居者”——西方移民研究思潮略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08页。。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中国,以自主、独立的方式来华进行跨文化交流实践的西方旅居者越来越多,他们之中有进行跨国、跨界创作的艺术家、民俗文化爱好者、田野工作者、背包客和沙发客、自由撰稿人和写书人、游走于世界各个角落的音乐及戏剧表演家等等。笔者对95位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观察,这些研究对象来自8个西欧国家(43人),2个北欧国家(15人),2个东欧国家(3人),2个北美国家(17人)和1个南美国家(6人),此外,还有11位研究对象拥有双重或多重西方国籍。他们来华的次数从2次到7次不等,其中来华2次到4次的研究对象共计69位,占总人数的72.6%。从在华停留的时间来看,以多次(3次及以上)且短期(单次停留时间不超过1年)的方式来华旅居的研究对象共计41人,占总人数的43.2%,长期在华旅居(单次停留时间在3年以上)的研究对象共计27人,占总人数的28.4%。从年龄分布来看,25到40岁的研究对象共计74人,占总人数的77.9%,60岁以上的有2人,20岁以下的有3人,在整体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从学历上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研究对象共计36人,占总人数的37.9%,并且高学历的研究对象多以长期的方式在华旅居。
由于这些西方旅居者在中国(或曾在中国)从事与文化传播和交流有关的实践活动,他们对中国所持有的热情、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中国人之间所发生的直接的交流与交往、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动性及深入程度等方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要高于主流外国人群体的。而他们在中国的旅居方式、交际方式、自我表达方式及交流内容等,也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特点。
法国概念大师吉尔·徳勒兹所创造出的一系列概念,其本身就具有跨越谱系和学科界线的特点。这些概念作为平面(plane)上的点(point),可以从一个场(field)跳到另一个场,每一次的跳跃和再现都能带来新的创造,不仅可以移入新的环境,还可以加快新环境的建造速度*陈永国:《游牧思想:吉尔·徳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页。。正因为如此,徳勒兹的游牧美学和差异哲学才会为不同的学科领域加以应用,并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通过对研究对象长期的观察,笔者注意到徳勒兹的块茎论和游牧美学等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影响,而德勒兹也有更多的观点和概念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身份的塑造、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语言交流与表征等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这是20世纪的经典理论在当今时代背景中的实践应用,也说明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且具有中介力量和开放性的块茎图示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它正在21世纪的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引起共振。
二、 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的“游牧式”跨文化旅居
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中国的文化地域版图逐渐成形。具有高度文化宽容心态的中国文化/亚文化场景并不排斥外来者的参与,因而西方文化旅居者在中国所进行的“草根式”跨文化交流和“游牧式”跨文化体验也在21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我的95位研究对象在华的旅居足迹遍及整个中国,其中有67位研究对象去过10个以上中国的大小城镇,不仅在数量上高达研究对象总数的70.5%,而且不少人还去过一些连中国人都罕有听闻的小乡镇。相比大多数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外籍游客等主流外国人群体而言,这些西方文化旅居者在中国的旅居经历,可谓是更接地气的跨文化体验。
“游牧式”的跨文化旅居体验不仅指涉地域上的流动性,更指向文化身份上的多样性、交融性和不确定性。徳勒兹眼里的“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s),其复数的、多元的主体身份通过各种行为、方式和关系所构成。比如瑞典人丹尼斯,作为当地“正派朋克场景”(straight edge scene)*正派朋克(straight edge),指的是1980年代在美国亚文化场景中发起的一项运动。正派朋克拒绝朋克音乐圈内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和习惯,他们不饮酒、不吸烟、坚决抵制毒品,一部分人还提倡严格素食,甚至连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比如可口可乐)也不喝,因而被视为朋克音乐圈里的“节制派”和“修行者”。的创始人,他组建了多支享誉世界的乐队,创办过3个独立厂牌,不仅是音乐家、词作家、写书人和亚文化推手,还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环保人士、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和7寸黑胶收藏者。从1999年起,他先后5次旅居中国,把自己的音乐带到了中国的十余个城镇。虽然这些演出并未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宣传,但他的国际名声和多元文化身份仍然受到了国内媒体和亚文化圈内人士的关注。很多1990年代末的中国亚文化青年对“正派朋克场景”、“严格素食主义”和“DIY理念”的接触和了解,或多或少都与丹尼斯的到来有关。来自美国和委内瑞拉移民家庭的美国人杰夫是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曾游历过20多个国家,并多次在南美和北非国家的NGO做义工。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当他以“沙发客”(couchsurfing)的方式在21个中国大小城镇旅居的时候,发现最有助于和中国人之间拉近心灵距离、展开有效交流的,恰好是自己的“佛教徒”身份,这一点不同于他旅居其它国家时的感受。杰夫曾在武汉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群体举行的户外唱诗活动,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并没有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排斥一个外来者,而这个信奉佛教的美国人也欣然乐意与在场的中国基督教徒分享自己对美国社会和多元宗教的看法。如果说单一的文化身份容易让人陷入交流和认同的困境,那么多元的、复数的文化身份不仅可以打破性别、种族、阶级、意识形态等种种对立的社会文化符码,在跨文化实践中,也有助于跨越文化的藩篱,打破森严的等级,形成多样的交际圈,让文化主体在不同的交际领域都可以游刃有余地与他者进行交流与交往。
巴特森用“原”(plateau)来描述一种强度的持续之域,这个设想启发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文化取向和思维模式的思考。有学者认为,这两位后结构主义大师所提出的“a thousand plateaus”概念,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千面原”,而非“千高原”。因为从字面上来看,“千高原”所指涉的是高潮的持续化,或“强度的稳态化”,而“千面原”恰好是德勒兹所强调的“非高潮观”以及“居间”这个“风姿多彩、变化生成的平台”*麦永雄:《千高原》,载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在徳勒兹的论述中,贯穿着对“生成”(becoming)的强调,而非“存在”(being)。高潮也是一种“存在”,是“生成生命”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这个瞬间以高潮的形式存在,往往会遮蔽人们对整个动态生成过程的关注,对高潮的过度追求也会让交际主体忽视文化生成、创造和交流过程中的丰富内容。反之,游牧式的跨文化旅居则通过空间的高频率转移和交际对象的不断变更给旅居者提供了文化再生成和再创造的可能性,这也是很多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所持有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由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猴子马戏团”于2011年秋天骑着他们改装的双层自行车从欧洲来到中国,在沿途的城镇和乡村免费为人们演奏音乐,为孩子们表演杂耍,以此方式与客居地人们进行交流。他们行走的路线几乎是随机的,他们的表演没有重复的观者,甚至连简陋的舞台也没有,而他们的“报酬”有时只是为了“换取”在当地村民家中借宿一宿的机会。对“猴子马戏团”来说,这种旅居方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表演内容。由于很多人对他们改装的双层自行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们便即兴举办了几场有关自行车改造的讨论会(workshop),希望将自己的DIY理念传达给对之感兴趣的中国人。这种新鲜的跨文化交流形式和他们每一天所面临的差异的多样化,不仅有利于激发旅居者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更有助于他们和暂居社区之间对话的展开和情感的分享。
三、 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的“块茎式”跨文化交际实践
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交际双方通常都有一个明确的身分,这个身分的背后隐藏着等级、阶层或种族等制约因素,这显然是不利于建立平等且开放的主体间关系的。我们不难想象,在外籍教师和他们的中国学生之间,在外国留学生和他们的汉语老师之间,在外籍管理者和他们的中国员工之间,在外籍游客和中国游客之间,所涉及的交际情境及其探讨的具体话题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说,除了与某种特定的工作或任务有关的交际情境之外,他们彼此之间都很难获得深入交流和交往的机会。而且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交际双方往往都不会轻易去逾越这个身分的界线。
的确,交流的困境无处不在,现实中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总是和各种“不平等”挂钩。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民间的文化实践者,他们都在为寻找打破“不平等”的方法做着不懈的努力。到了德勒兹那里,他与加塔利一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概念“块茎”(rhizome)*G.Deleuze & F.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London and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3,pp.1~27.。块茎,即植物茎中的一种呈现为块状的变态,它没有根基,因此也不固定于某一点,而是不断生成新的块茎,并在地表蔓延。块茎就是徳勒兹论述中的“点”,这种生成新的块茎并蔓延的过程是他所论述的“生成”,而块茎与块茎之间具有随机性的链接是“网络”,也是“关联”。这个以“和”的逻辑为基础的“关联生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跨文化交际的表达式——每一个交际主体都是具有差异的独立个体,却又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结并建构关系,从而呈现出不确定的、多样化的、开放式的结果。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美国人奈文在北京创建了自己的独立厂牌“根茎”,专门帮助中国音乐家和艺术家在海外发行他们的黑胶唱片。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在中国宣传DIY文化*D.I.Y.(do it by yourself),是在国际音乐亚文化场景中甚为流行的反商业化理念,在音乐创作、唱片录制、发行与宣传、组织演出等方面都提倡“自己动手做”的方式。各个DIY社区之间通常会互帮互助,并抵制任何商业化的操作。在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地的DIY社区已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网络,对中国亚文化场景的影响也在近年来迅速扩大。,支持本土的DIY社区,二是增强中国的亚文化DIY场景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加强社区之间的合作意识,相互宣传与合作,相互邀请与造访。奈文告诉笔者,“根茎”这个名字就源于德勒兹的“rhizome”,当他读到德勒兹的块茎理论之时,突然发现自己心中早已萌生的一系列想法在德勒兹那里有着如此精准的阐述,因而立即行动起来,并以“根茎”命名了自己的厂牌。
现实中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很多时候都会被简化为拿着西方的工具去搭配中国的情感,有时又加入了些许中国的工具和西方的情感,但这种搭配一不小心就会变得牵强,从而难以触及交流的实质。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并不停留在表面上的“跨越”(cross-),而在于文化之间“关联”和“关系”(inter-)的建构。然而在实践中,哪怕是持有积极跨文化态度的交际者,也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跨文化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更具互惠性的、和谐的主体间关系。本研究所聚焦的这些西方文化旅居者(以奈文为典例),就以其独特的跨文化实践和交流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丰富的案例。这95名研究对象既包括独立音乐人和表演者(37位)、文化推手和活动策划人(15位)、其他类型的艺术家(12位)、摄影师(9位),也包括博士、学者和田野工作者(21位)、独立撰稿人和媒体活动家(11位),还有建筑师、民俗爱好者、背包客、环保人士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西方人。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同时涉及多个领域并拥有多个文化身份,因而每次造访中国的目的和交流的话题都各有侧重。他们看似独立的个体,却又相互之间形成网络。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并不是单向的,而指向一种双向的互动,并看重关系的维持。并且,维持和中国人之间建立起来的跨文化关系,又成为了他们一次又一次重返中国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结识这些研究对象的途径也得益于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从人到人,从圈子到圈子,从点到网络,从一个“场”跳跃到另一个“场”。这种新型的跨文化关系的建构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变得高效而便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由于这些西方文化旅居者的肩上背负着独特的实践使命(其中大多数是自我赋予的),深度体验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其本身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实践内容。他们中的有些人因而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包括方言)、文化和历史,有些人深入中国的农村和山区,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劳作数月,还有些人努力进入中国人的文化圈、亚文化圈、社交圈,与他们探讨各种话题,交换经验和组织活动。笔者观察到,在这些研究对象当中,很多人的行走路线和日程安排都是随机的,在火车上偶遇的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让他们萌生一个新的想法或计划。
德勒兹的块茎图示启发我们,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并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掉“等号”,让它变成一个开放的表达式。现实中的跨文化实践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文化差异和冲突也会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层面给交际双方带来困扰。掌握足够沟通技巧的跨文化交际者往往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想听什么、想看什么,从而游刃有余地对交际过程进行操控;而笔者认为,更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者,可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去追求差异的共存。这种共存的关系需要通过情感上的渗透互通以及持久的对话和交往来实现,而非对对话过程的单向操纵和掌控。在对这些西方文化旅居者的观察中,笔者也看到了文化主体之间进行互动、协商、分享意义并重组意义的动态过程,他们对“关联”的寻求和对“关系”的维持正是“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在这种跨文化实践中的体现。
四、 在华西方文化旅居者的“无根性”跨文化思维
为了更清晰地论述块茎的特点,徳勒兹将“块茎结构”、“树-根状结构” 及“胚根结构”进行了对比。徳勒兹认为,“树-根”系统(arborescent system)的基础是经典的主客体二元对立,虽有多样化的表象,却有同一的根。它总是立足于一点,具有单一性、中心性和根性,无论枝叶如何繁茂,却总是可以回到同一。如今,经典二元论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其所表现出来的多元性并未让“树-根”系统遭到毁灭,而是进入了更高层面上的多元统一,这就是“胚根系统”(radicle system)。而在德勒兹看来,呈现出“无中心、非等级制、非表征”特点的“块茎系统”(rhizome system)是唯一充满活力并带希望的*G.Deleuze & F.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22.。
在传统的殖民主义霸权语境中,地理上的“中心”是靠边缘地区及国家来衬托的。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殖民”,不单指占据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更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主流文化对大众的统领和支配,以及利益集团对亚文化及次文化的收编与遏制。主流文化便是典型的树状模式,呈现出等级分明的特点,无法撼动和移动的是它的“根”。相对树状逻辑的主流文化而言,次文化和亚文化犹如块茎和野草,其蔓延是随机的,一切皆为生命,一切皆平等,这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全新体验。“块茎”理论的提出旨在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秩序,是拥有多重出品和入品的“反谱系”(antigenealogy),它“可分开,可连接,可逆,也可被修正”*G.Deleuze & F.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p.22.。德勒兹的块茎图式决不仅是“形态”上的隐喻,更直指人们的思维模式。德勒兹认为,长期主导我们的这种主从有序的树状思维模式彻底僵化了人们认识世界和创造文化的方式,是囚禁人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囚牢。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去冲出这个囚牢呢?
交流是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跨文化交际尤其如此。当异文化激烈相遇和碰撞的时候,“关联”的产生正是一个创造过程。交际主体在彼此之间探寻着某种相通的心智和链接,他们对不同沟通方式的尝试相当于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如果说交际主体达不到“忘我”的状态,必然会将对方的文化特性和试图表达的信息以自我的方式进行解码,从而阻碍移情的发生。59岁的自由撰稿人R先生(德国,匿名)先后6次旅居中国,对中国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尤其感兴趣。R先生觉得,多年在华的旅居生活让自己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当他乘坐火车的时候,已经可以非常自然地和陌生人打开话匣子了。在R先生眼里,火车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无论旅途有多远,他的第一选择永远是硬座。他所期望的交谈对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以及去城市谋生的农村妇女等等,每一次乘坐火车的经历都给他提供了很多与这些中国人交谈的机会。他告诉我,当他去德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都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德国人了,或者说“德国人”这样一个身份在他离开德国以后,就变得不重要了,“倘若无法忘记身份,你的这个身份会在潜意识里引导你的思维方式,并影响你和他人的交往过程。有的时候,它会让我用德国人的方式去思考或行动,将德国文化作为参照物去审视异文化,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想踏入这个陷阱中去。”在21世纪的当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平台的开放,传统的交流模式和格局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所有的不可能都逐渐变为可能。如果拥有“未编码”的身体和心智,交际主体便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不再仅仅是“我”,也可以成为“你”,可以成为“他”,可以成为任何一个有利于交流发生的主体。这种“无器官”和“无根性”的思维方式体现出来的丰富的创造流、情感流和想象力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中的文化制造者所缺乏的。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R先生那样去追求交流中的“忘我”状态,但在特定的交流情境之中,放弃自己的某种身份或立场去思考问题,以此去探寻多元的出口和入口,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却是很多文化旅居者所采用的重要交流策略;而移情,也就悄然不知地在这种“无根性”的状态下发生了。
在这项研究中,我所关注的西方旅居者大都具有多重的文化身份。他们并没有给自己贴上一个“白人”的标签,而是采用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标签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以多元的途径来建构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identity”在这里不光指的是国籍、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社会身份”,更强调他们试图追寻的“文化认同”。对认同感的追寻与确证涉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些西方旅居者的多重文化身份令他们具有更开放的眼光、更宽容的胸怀和较高的移情能力,从而更容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视角下去审视他者,换位思考问题,在不同的圈子内发展多样的跨文化交往。这些看似边缘的文化旅居者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大大推动了中外民间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而中国越来越宽容的对外政策也给交际双方提供了跨文化实践的土壤。
另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一直在反思这些经济上并不富裕的西方旅居者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不辞万里地来到中国,做着这样一些过程颇为艰辛且得不到经济回报的事情,到底是何种强大的力量驱使着他们的行为。而通过观察他们在华的旅居生活,笔者逐渐清晰地觉察到他们对跨文化交流所持有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和渴求。德勒兹的哲学,也指向一种可以穿越任何边界的欲望的蔓延与传播;这种欲望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它以流动的方式来生产万物。的确,交流的欲望及欲望的生产充斥在这些西方文化旅居者和中国人建构跨文化关系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欲望和他们的旅居经历、交际体验,以及他们接触到的异文化、异乡人息息相关。丰富的跨文化旅居经历让交流之欲望源源不息地生产出来,为跨文化交际的生动性和持续性提供了重要动力,只要欲望不息,对有效跨文化交际的追求就不会终结,旅居过程中的一切困难都无法扼杀他们心中的交流愿景。这种欲望没有受到文化之“根”的限制,而是在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交际网络中自由地流动和生产。它们此起彼伏,旧的欲望在此处消亡,新的欲望在彼处产生,并为他们一次次重返中国提供动力和契机。
五、 结语
徳勒兹的哲学阐释了一种多元、动态的“生成”观,而非静态的差异结构。而跨文化交际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生成他者和建构关系的过程,是言说者和行动者的自我文化价值与他者文化价值在对话和交际过程中的双重呈现、变更和交融。一个理想的跨文化交际环境,它首先是非同一性的,不仅存在差异,肯定差异,并且还能够生产差异。而一个理想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也指向一种非等级制的交往互动模式的建立,和一种多维度的跨文化关系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个体都是相互独立的,却又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和相互中介。
让我们回到跨文化传播与交际研究的核心问题上来:这种交流是否自由和有效,是否能形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并有助于和谐跨文化关系的建构。虽然跨国、跨文化的交往在当今中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无论是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还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仍然是无法被对方深刻理解的“他者”。而文化旅居者,作为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个新型的国际流动人口群体,他们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诠释及表达带入了暂居社区,持续地、高强度地和他者之间进行交流。他们对异文化敞开胸怀,在交流过程中寻找着相互联结的中介元素,这种跨文化交际实践对交际双方的文化和价值观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促使着意义的生产与重新生成。在这个群体之中,每一个个体都相互独立、各具特点,却又因共享的文化价值观而凝聚在一起,形成网络。因而,他们能打破国籍、种族、阶层、性别、宗教等因素带来的种种限制,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寻找多元的出口以及颠覆文化界线的可能性。
这些文化旅居者类似于文化意义上的罗姆人*罗姆人(Rom):英国人称其为吉普赛人,法国人称其为波希米亚人,西班牙人称其为弗拉门戈人。这诸多的名称都是其它民族赋予他们的,而吉卜赛人自称为“罗姆”,在吉卜赛人的语言中,“Rom”的本意就是“人”的意思。。和罗姆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表现为地域上的流动性,更旨在与他们随机选择的社区之间产生文化上的交流和关联。他们所实践的这种跨文化旅居方式正是德勒兹理论中的“块茎”:没有永久的根基,在异文化背景中随机蔓延,生产和建立新的关系与网络,并继续蔓延。这种旅居方式基于图示,却并非制造模式,而是在描绘地图,具有开放性和反中心的特点。虽然每一个关系或关联都有被切断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会有新的关系和关联被不断生产和创造出来。这样的跨文化实践为我们和他者之间跨文化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而这些与中国产生诸多关联的西方“游牧者”的文化旅居体验也代表了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实践的一种“反模式化”的革新。
◆
●作者地址:刘学蔚,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wane_juventina@aliyun.com。
●责任编辑:桂莉
Nomadic, Rhizomatic and Rootless——A Study on Western Cultural Sojourners’ Practice in China
LiuXuewe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ultural sojourne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group that has appeared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s treated as the freest alienated type of sociological form of the “stranger”. Today, there’re more and more Western cultural sojourners come to China, taking part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dependently and autonomously. An important issu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be addressed here is how a new mode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has been construct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Deleuze’s philosophy describes a plural, dynamic view of “becoming”, not a static structure of the “differences”, whil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its essence, a process of becoming others and relations construction. The “nomadic” sojourning experiences, the “rhizomatic” way of practice and the “rootless” way of thinking of those Western cultural sojourners, represent an anti-modelization reform of intercultura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providing typical cases to the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Deleuze’s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cultural sojourn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illes Deleuze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