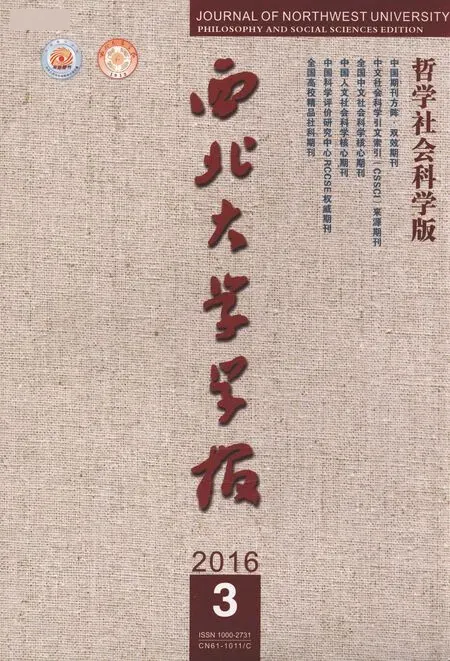《风筝》:兄弟失和的哀悼与忏悔
2016-02-20王兵
王 兵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中文系,陕西 西安 710100)
【文学研究】
《风筝》:兄弟失和的哀悼与忏悔
王兵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中文系,陕西 西安710100)
摘要:《风筝》以旧作重写的方式创作于周氏兄弟失和不过两年时间,很可能是鲁迅借此向周作人发出的深情忏悔。作品通过主人公自我角色从施恩者到虐杀者和忏悔者的认知过程的描绘,表现了鲁迅勇于解剖自我的思想特色,也折射出鲁迅经过与许广平恋爱、弥补了正常婚恋情感体验的缺失而产生的对于兄弟失和的深刻反省。兄弟失和使周氏兄弟从不同角度体察了人性的偏狭,周作人由此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宽容观,而鲁迅则通过文学作品深化了新文化运动反省忏悔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忏悔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它与作者在1919年发表的随笔《我的兄弟》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描写更加细致,情感更为沉痛。这种旧作重写“炒冷饭”式的创作,通常产生于作家情感体验枯竭的阶段,而鲁迅的情况并非如此。《风筝》的写作时期,是鲁迅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个创作旺盛期。在现实层面,兄弟失和、与许广平恋爱这两个重大事件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沉寂与分化,都对他造成了强烈冲击。在创作层面,鲁迅从“遵命文学”转向了独具个性的心灵抒发,笔触所及更为宽广。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在思想情感和题材内容上都积淀深厚且有爆发力,此时的“炒冷饭”显然属于特异的创作现象,它不会是无话可说的应景之作,而是话中有话、包藏衷曲的寓言。结合鲁迅这一时期曲折的情感经历,就会发现这一作品蕴藉丰厚、意味深长。
一、旧作重写的良苦用心
《我的兄弟》记叙了一个不喜欢放风筝的兄长粗暴地毁坏了弟弟制作的风筝,日后觉悟自己的过错而向弟弟祈求原谅的故事。这个看似平常的作品,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显示了以小见大、以浅见深的意义。类似文中描写的残暴剧,在一个专制意识浓厚的社会背景下,随时都有可能上演,大到君臣政体,小到父子家庭,都弥漫着《狂人日记》揭示的“吃人”气息。鲁迅假借一个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批判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封建意识,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突破了几千年文化自大的牢笼,自觉地反省传统文化的弊端,发出了反叛专制礼教的呐喊。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涌现出的现代作家及其创作,大多表现了这一反省批判的时代精神,而鲁迅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从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他就借狂人之口深刻反省了“无意之中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罪行。此后,在《一件小事》中更集中地反思了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的灵魂。《我的兄弟》也属于这类作品,它以勇敢的自我忏悔精神,批判了专制意识的罪恶,表现了时代的文明与进步。
如果说《我的兄弟》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作者自述的“遵命文学”,即更多顺应时代潮流而弘扬富有时代精神的思想理念的话,那么,《风筝》则假借同样的情节表达了个人心灵深处真实的情感体验。从《我的兄弟》到《风筝》,情节内容和思想主题完全一样,情感的表现却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平实的叙述到激情的抒发,笔力沉痛激越,反省忏悔的深度和力度都增强了。显然,在创作《风筝》时,对于旧作触及的内容,鲁迅有了更为直接痛切的情感体验,这使他重提旧作,以反刍的方式在旧作重写中抒发了新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慨。
在《风筝》创作之前,鲁迅情感经历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兄弟失和,如果把《风筝》的创作放在兄弟失和的背景下看待,那么,借“风筝”而提起“我的兄弟”,通过旧作重写强调文中兄长对于弟弟的忏悔,就显得大有深意。兄弟失和之后重读鲁迅在兄弟怡怡时期所写的《我的兄弟》,文末的感慨“阿!我的兄弟。我能请你原谅么?”“然而还是请你原谅罢!”更加感人至深。由此推想,鲁迅很可能是借文抒情,表达了对兄弟失和的深刻反省,并向弟弟周作人发出了真情的忏悔。这种在兄弟失和的伤痛中发出的心灵呐喊,较之前作,更令人感到字字滴血,句句情深。
二、兄弟失和的反省与忏悔
《风筝》写于兄弟失和事件发生不到两年时间,那么,文中表达的兄长对弟弟的忏悔之情与现实生活中兄弟失和的联系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界历来没有将二者相对应,也从未认为文中兄长的忏悔是鲁迅针对兄弟失和而发出的真情告白。这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许广平曾经引用过鲁迅的一段话:“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1](P87)这似乎印证了《风筝》将贬抑的对象指向兄长只是一种艺术虚构。二是长期以来人们确信在兄弟失和一事上错在周作人一方,鲁迅是受害者,应当忏悔的是周氏夫妇而非鲁迅,因此,《风筝》的情感内涵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实有之情的表现。鉴于以上原因,学界普遍认为鲁迅创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自我忏悔,而是借此启发周作人珍惜兄弟之情,表达自己对兄弟失和的伤痛与惋惜。显然,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兄弟失和的褒贬倾向和鲁迅言及创作一般规律的固化认识前提下产生的。假如这一前提尚可质疑,那么结论便失去了足够的说服力。其实,在预设前提下进行的研究也需要突破预设前提的限制去探索,以避免这一限制对研究造成误导。那么,在《风筝》一文的研究上,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它限制了人们对文中情感内容的判断理解,阻碍了对文学作品与作者情感体验密切联系的关注,进而也遮蔽了鲁迅在这篇作品里彰显的“直面人生”和“解剖自我”的创作特色呢?
关于兄弟失和这件事,如同世间许多复杂的纠纷一样,也许很难黑白分明地以简单的对错来论断。的确,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一直扮演着长兄如父的角色,对周作人及其家属都恩重如山。正因为如此,对于兄弟失和,无论当事人鲁迅,还是作为旁观者的亲友,以及历来的研究者,都会自然地将错误的矛头指向周作人夫妇,而鲁迅则被认为是恩将仇报的受害者。这种认识随着周作人后来沦为“汉奸”更加得到了强化。在周氏兄弟的天平上,人们的褒贬态度是非论断已趋定向,尽管周作人在这件事上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在文章中时时流露出难以辩解的委屈,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还原真相,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看法,但都未能逾越鲁迅在此事件中属于受害者的认识,因此,《风筝》所表现的兄长的忏悔就缺少了现实依据性。
考察鲁迅这一时期的创作则会发现,在兄弟失和之初,他的确怀有相当强烈的怨愤委屈之情,以至于病倒,并写下了《复仇》《颓败线的颤动》等宣泄愤懑之情的作品。但很快,鲁迅的心态就发生了转变,相继发表的《风筝》《弟兄》《伤逝》等作品在情感基调上有了明显变化。在这类作品中,强烈的愤懑化为冷静的反思,外向的抗议转为内部的剖析,一种痛切的忏悔之情萦绕在字里行间,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在《墓碣文》中抒发的“抉心自食”“自啮其身”的创作情怀。这时的鲁迅,已经从自发的情感宣泄迈向了自觉的理性反省阶段,精神视域和情感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升华。
从《风筝》和《我的兄弟》的故事情节上看,兄弟之间的冲突源于身份和志趣的差异。“我”已长大成人,又生活在“父亲死去之后,家里没有钱了”的环境中,沉重的压力和使命感使“我”嫌恶放风筝的游戏,认为是“没出息”的表现。而小兄弟却喜欢风筝,他“苦心孤诣”地制作了一个风筝,这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而“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于是“我”粗暴地毁坏了他的杰作。后来,当“我”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得知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才明白自己犯了“精神的虐杀”的错误,因而追悔莫及。这是一个强势方本着善意期望弱势方有出息,却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忽略了年龄和个性差异而导致的专制压迫的故事。
这一故事情节的寓意很可能就是兄弟失和的症结所在。兄弟失和虽然原因复杂,但从两人的不同个性和情感经历上看,可能是双方在家庭生活和人生追求的情感理念上发生分歧而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对待大家庭的态度有了差异。鲁迅因不满包办婚姻,夫妻一直分居,因此在情感上没有小家庭的观念。加上手足情深,以及从小培养的、在家道衰败的变故中强化了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使他对大家庭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因此,他期望兄弟三人不分家。而周作人却不同,由于年龄较小又长期在长兄鲁迅的护佑之下,他的家族使命感并不十分强烈,加之是自由恋爱,于是很钟情于小家庭。周作人在日本结婚后夫妻恩爱,也很喜欢日本的环境,本想以学习法文为由继续在那里生活,但鲁迅认为“法文不能变米肉”,再三劝说并亲自赴日本促使其回国,为此,周作人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的诗句,表达了他的无奈之情[2](P47)。在周家卖掉绍兴祖屋迁居北京时,周作人提出分家的要求,但“鲁迅坚持不肯”[1](P90),于是在北京八道湾组建了大家庭生活。许广平曾引据鲁迅日记说迁居过程中的卖房、买房、办理各样事务都是鲁迅一人办理,周作人在此期间携家眷到日本探亲,没有付出任何劳动而坐享其成,此乃“好逸恶劳”的“封建少爷脾气”[1](P89)。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周作人的逃避,也可能是对不得不屈从于长兄意志而采取的消极态度。
周作人对小家庭的倾心历来遭到“自私”的谴责, 这一方面是因为与鲁迅对大家庭的献身形成了鲜明对比, 令人有高下之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族意识的思维习惯所致。 其实, 从尊重个性自由的现代立场看, 周作人也并无大错。 夫妻恩爱想分家过小家庭生活, 这与夫妻隔膜欲固守大家庭结构同样可以理解。 周作人的家庭是较为特殊的异国婚姻, 在适应环境和人际关系上都面临着思想观念、 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等多方面的挑战, 对此, 周作人会有更多感触和顾虑, 其苦衷是他人难以感同身受的。
周氏兄弟的另一个分歧是对待经济生活的态度。定居八道湾之后,家庭的经济大权由鲁迅移交给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此时恰逢教育部欠薪,又因搬家负债、日方家累过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鲁迅对羽太信子奢侈的持家方式产生了强烈不满,多次劝说责备周作人,而周作人却对妻子表现出更多的理解同情,这一情感分歧也是导致兄弟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
说到羽太信子的奢侈,主要表现在喜欢购买日本用品、生病去日本医院就医以及日常生活较为讲究等,这与周氏兄弟在困境中成长又经多年单身生活而养成的极其简朴的习惯形成了反差。其实,若从羽太信子一方考虑,她虽然出身平民,却生活在经济发展较中国优越的日本,生活方式自然不同于一般中国人。况且背井离乡来到中国,青睐品质更好的日本用品和医药,也在情理之中。其实鲁迅也信赖西医,常请日本医生治病,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关注的角度不同。鲁迅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忧患大家庭经济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也历来崇尚俭朴的美德,因此要求羽太信子具备符合传统习惯和现实环境的持家理念。但周作人则更多从妻子的角度出发,看到了不同生活环境下生活方式的差异,把这种“奢侈”当作富有艺术情调的日本文化而加以理解认同。他在《日本的诗歌》一文中写道:“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 就在平常家庭装饰,一花一石,或日用食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种风趣,这是极普通易见的事。”[3](P120)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的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4](P101)周作人在中日习俗的比较中发现,相对于国人“干燥粗鄙”的生活,那些看似奢侈无用的东西,其实是“必要的”人生趣味。这种崇尚余裕、闲适和享乐的生活态度,在传统观念里很容易被看作是玩物丧志,但以现代的人生观念和艺术审美来衡量,则是合乎常情的。
周氏兄弟定居后在人生追求的理念上也产生了差异。鲁迅自幼在情感心理上缺乏家庭生活的乐趣,家庭带给他的多为烦恼负累,使他不能无所顾忌地从事个人理想的追求,这使他将日常的家庭生活视为阻碍人发展的羁绊。定居后他移交经济大权,以为从此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解脱出来,和弟弟一起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已颇有影响的事业之中,不料大家庭生活更为琐屑,这使他深感失落和焦虑。周作人却不同,由于情感体验的差异,对于婚后的日常生活,他不仅不觉平庸,反而沉溺其中并深得其趣。两人这方面的冲突在日本留学时已初露端倪,当时周作人正与妻子恋爱,因沉湎于儿女情长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鲁迅看重的翻译工作,这“没出息”的表现令鲁迅十分懊恼,情急之下竟以拳相击[5](P5)。婚后的周作人,更加心仪于品味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审美和人生乐趣,在草木虫鱼、衣食住行的琐屑事务中寻求生命的体验与哲思。他反对将艺术与生活、理想与人生相割裂,在肯定凡俗生活和庸常人性的基础上构建艺术与理想的大厦。这种立足于常态生活和平凡人性的审美追求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超越性人生理想,在价值取舍上产生了分歧。
综上所述,源于身份、成长经历和婚姻状况不同而导致的志趣差异使周氏兄弟在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中难免产生诸多矛盾,而鲁迅长期形成的主导地位以及他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具道德优势,于是很可能对相对弱势的周作人一方造成威压,进而导致失和的爆发。这与《风筝》所反映的内容极为相似。
兄弟失和后,鲁迅经历了痛切的回味与思考,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情感体验。《风筝》的主人公对自身角色从施恩者到虐杀者和忏悔者不断推进的认知过程,也形象地折射出鲁迅对兄弟失和的反省与忏悔。
三、人性的偏狭与伟大
在《风筝》一文中,兄长是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弥补了知识的欠缺而觉悟了自己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也许是经历了与许广平恋爱,弥补了正常婚恋情感体验的缺失而省察了对弟弟周作人的误解和偏见。与许广平恋爱是兄弟失和之后鲁迅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情感冲击,二者都给鲁迅的情感世界带来了震荡与颠覆,冲突与纠结,但与兄弟失和的破坏性情感体验相比,与许广平恋爱的情感性质是宁静温暖的,这对鲁迅的心理起到了某种修复作用,也使他体尝了一种血缘之外却同样浓厚亲密的特殊情感,并得以平静地回忆与思考。《风筝》写于鲁迅和许广平爱情见证的《两地书》开篇之前四十多天,作品的情调由峻急转为舒缓,笔端流露出脉脉温情。与许广平恋爱的情感体验反衬出鲁迅曾经缺失人性中正常的婚恋之情而导致的情感认知的偏狭,这使他得以调整视角重新审视过往的生活,对周作人的情感表现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从而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感情评价。由此可见,情感体验的缺失是人与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重要因素,但情感体验又是任何人都无法全面获得的,有限的人类始终存在着某些情感体验的缺乏,因而也难以避免不同体验所产生的误解与冲突,在这方面,兄弟失和反映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困惑。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学家巴赫金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都有各自的视域所限,因此主体间需要交往,这种“交往”的形式就是“对话”。对话不仅包括自我与“他人”的,也包括与变动不居的“自我”的;进一步说,世界的本质就是对话。“巴赫金认为,他人利用他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可以看到我所看不到的东西,借助他人的视野可弥补我的视力范围不及所造成的缺憾,可纠正我的误区和盲点。”[6](P24)可以说,《风筝》这篇具有明显内倾趋向的作品,是鲁迅在兄弟失和之后灵魂深处的一种自言自语的对话,鲁迅把“他者”的存在看成“自我”存在的一个前提,把主体间的交往视为一种“应答”活动,在反复的、动态的与“他者”和“自我”的复调对话中拓展了个体生命体验的内在心理空间。
兄弟失和的情感体验使周作人深深感慨“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的[5](P40),这使他开始进一步思考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他首先感到了这一启蒙理想的破灭,认为那些反封建的“主义”“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于是他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3](P2)。他对文学的目的进行了重新定位,从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时期的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转向了对文学个性表现的强调。他说:“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7](P34)。这种立足于自我表现而非启蒙社会的文学观念,不仅维护了文学的本体性,也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新的文化专制的产生。周作人深刻地发现,那些以反专制为目标的时代先觉者们,在以新的、进步的姿态占据时代制高点时,不经意间又对其他不同的思想文化造成了威压,成为了新的专制者。这使他认识到,专制并非仅仅存在于皇权政治和纲常礼教中,乃是普遍渗透于民众的思想意识深处,其原因是“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好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被赋裁判的权威”[7](P5)。这种把个人的或部分群体的见解当作普遍通用的法则而加以“盲从”与“狂信”的态度,是造成专制的主要原因。为此,他强调对个性自由的尊重,认为一切权威,无论是“君师的”还是“民众”的,以及一切以“绝对真理”所进行的“思想的统一”,都是对个性自由的扼杀而应予以批判。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周作人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宽容观,认为个性自由的尊重必须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宽容是个性自由得以生长的土壤。他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中指出:“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当的规则是,当自己求发展时对于迫压的势力,不应取任何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8](P9)这种反叛专制、倡导宽容以维护个性自由的现代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其意义极为深远。
与周作人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相对应,鲁迅通过文学艺术的创作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反省忏悔的时代主题。如果说《狂人日记》开启了一个时代觉醒的序幕,狂人“无意之中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的忏悔象征了时代先觉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省,那么,《一件小事》《我的兄弟》这类作品则是反映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忏悔。与这两种富有整体性群体性代表的忏悔不同的是,《风筝》表现的是极具个人性的灵魂忏悔。《风筝》的创作处于新文化运动落潮时期,此前那种群体的、一致的、必胜的革命阵营已不复存在,作者也不再以“遵命”的态度为时代呐喊,为先觉者代言。兄弟失和标志着最后一位亲密的同路人与之分手,鲁迅步入了一条寂寞独行的探索之路。此时的创作完全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体验中,在对个人灵魂的拷问中抒发独具个性特色的思想情感,因而《风筝》的忏悔不仅具有社会意义更显示出生命哲学的价值。从文化反思到个人反省,从知识分子的忏悔到自我忏悔,鲁迅对忏悔的探索进入到了人性的深处。
兄弟失和无疑是周氏兄弟人生中的不幸事件,但正是这一不幸的经历,使兄弟二人从不同角度体察了个体人性的局限,在人性偏狭的认知基础上对人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是周氏兄弟因失和而获得的奇特共鸣。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的人性善和个人迷信意识的国度,认识人性的偏狭是极其不易和难能可贵的。西方文化对人性局限的认识主要出自于基督教典籍,而周氏兄弟这方面的发现则更多来自于生命的体验。从这一点上看,也是兄弟失和的重大收获。中国自古就有“为尊者讳”的观念,对于有着“民族魂”称号的鲁迅,人们可能不愿看到有损于他伟大形象的评论,这也是兄弟失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屏障。其实,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人性的完全,人性的偏狭是人类共同的特性。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敢于正视自身的偏狭并为之忏悔,这才是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9](P284)《风筝》这篇散文,也可以看作是鲁迅这一独白的生动印证。
参考文献:
[1] 孙郁,黄乔生.周氏兄弟[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2] 止庵.周作人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4] 周作人.知堂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7] 周作人.谈龙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8]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9] 鲁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赵琴]
Kite:Mourning and Repentance of Disputes of Brothers
WANG B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haanxiXueqianNormalUniversity,Xi′an710100,China)
Abstract:Kite was re-written only two years after the disputes of the Zhou Brothers. It possibly represents Lu Xun′s deep feeling of repentance to Zhou Zuoren. The work describes the character from a benefactor to a killer and confessor, which shows Lu Xun′s ideological feature of courage of self analysis, and also reflects that after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 Xu Guangping, which made up his lack of common love and marriage experience and resulted in his deep feeling of repentance to the disputes of brothers. The disputes made the Zhou Brothers experience the parochialism of human, and helped Zhou Zuoren establish a unique literary viewpoint of tolerance. Lu Xun deepened the theme of the times by the literature, namely the self-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Lu Xun;Zhou Zuoren; disputes of brothers; repentance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王兵,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96/.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3-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