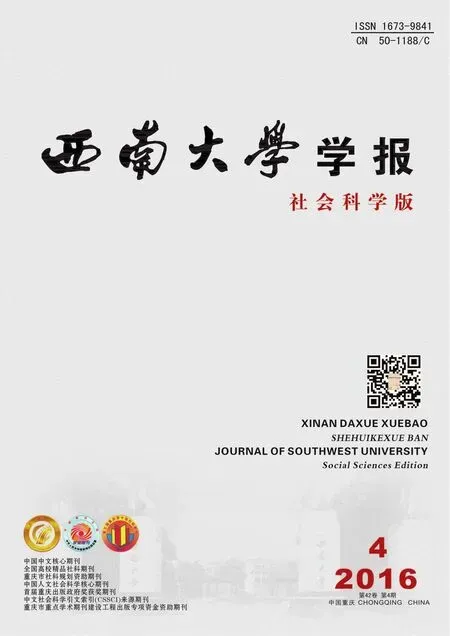对奢侈消费的批判: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
2016-02-20吴琼
吴 琼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对奢侈消费的批判:从马克思到鲍德里亚
吴琼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奢侈消费正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最发达而显著的表现。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有力批判。他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奢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获利机制,而且成功解蔽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在面对奢侈消费问题时似乎是失语的,他主要还是从资本主义一般商品消费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但马克思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面对这一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方法论应该受到批判。
关键词:奢侈消费;意识形态;鲍德里亚;符号消费;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47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左派社会批判理论界曾把这个社会称为消费品堆聚或景观世界。而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已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奢侈品堆积物的世界,这是20世纪法国著名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所指认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如今,奢侈品已经从马克思时期尚没有完全进化成人的“猴体”,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最发达的“人体”。奢侈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统治方式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这就使一些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面对如今这种来势汹涌的新的资本统治方式时是失语的,他的理论对此并无现成答案可寻,反而是鲍德里亚从符号政治经济学层面对奢侈消费的批判才更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在分别梳理了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相关理论体系后,从方法论层面对两者作了一个比较研究,希望提供一个正确面对这一问题的视角。
一、马克思理论视域中的奢侈消费问题
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就穆勒有关奢侈问题的论述进行了如下摘录:“至于加速资本的增长,则立法拥有反奢侈浪费法这一手段,立法可以把节俭提上议事日程而认为浪费是可耻的。”[2]10虽只简单一句话,但却明显表现出马克思对奢侈问题的基本态度,他坚决反对奢侈浪费而主张节俭的必要性。在同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的“需要、生产和分配”一节中,马克思有了大段有关奢侈问题的论述。*这里请忽略《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部著作写作顺序的相关争论问题,本文只是觉得《穆勒摘要》中有关奢侈问题的论述非常少,所以才做了把《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放在前而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放在后的处理。由于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揭示工人的异化问题,所以针对国民经济学一味地盘剥工人劳动而抑制其需求的做法,马克思认为是不可取的。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其原则就是节制需要而对工人的劳动进行剥削,工人就是劳动的奴隶,他们的任何奢侈对于资本家而言都是不可饶恕的,“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2]134-135。工人只要拥有能维持他们生活下去,继续进行劳动的那么一点儿就够了,“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有权要活下去”[2]135。此时,由于马克思还不具备思考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的理论水平,而无法发现生产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张力,就连对“消费”的批判也只是外在的,所以他也只能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咒骂国民经济学导致的工人劳动的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资本家享受奢侈是无耻的。至于国民经济学内部掀起的奢侈与节俭之间的争论,马克思只是指出“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2]136,却再无力攻击。
进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期,马克思已经摸索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条线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所以他也从这一点出发来看待奢侈消费问题。他指出:“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3]489这说明马克思意识到奢侈消费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一段时间内是奢侈的消费物,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有可能不是奢侈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奢侈的东西,在别的国家就有可能是再常见不过的一般商品。在这部著作中,处处显露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的苗头,所以,此时他也能对资本主义享乐哲学大加批判了,这也直接指向马克思对奢侈消费问题的深刻论述。资本主义享乐哲学的虚假性在于“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3]456。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是有着严格界限的,哪个阶级消费什么都有明确规定,直接跟等级相联系,不能僭越,但资本主义以来,这一界限被打破了,以前高等级所能使用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用,只要有钱就行。实际上它给人一种假象:“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在这些情况下,它下降为道德说教,下降为对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或者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把强制的禁欲主义宣布为享乐。”[3]489《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明显显示出马克思对奢侈消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此时,马克思已经完全能够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方面对奢侈消费加以批判了。然而仍不免诸多欠缺之处,主要体现在:他没有把奢侈问题放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来看待。
只有到了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期,这部代表了马克思“在阐明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的著作中,他才能够既从资本生产的自身发展过程出发,又站在阶级立场上来面对奢侈消费问题。普鲁东认为:“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批评道:“如果硬说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4]124好像大家都可以买得起奢侈品了,实则不然,“产品的使用取决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又建立在阶级对抗上”[4]124。在贫困社会,广大群众只能首先满足于对粗劣产品的需求,而进入繁荣时期,阶级本身的性质最先发生了改变,挣脱了身份限制,成为变动的、不稳定的。无产阶级能享用奢侈品只能说明奢侈品本身的性质意义发生了变化,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对立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改变。“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104这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性,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4]129消费活动本身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性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把人的自然需要变成社会的自然,也就是形式的改变,同时还创造出新的需要,包括科学探索、社会交往,也包括了奢侈品的体验等等,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的转化正是资本运行自身所推动的。到这里,虽然马克思对普鲁东从庸俗经济学出发来看待奢侈消费问题的视角进行了批判,显示出他分析这一问题的一定功力。但无论是从阶级立场上彻底批判奢侈消费问题方面还是从整个资本生产逻辑中解构出奢侈消费的一般逻辑方面而言,他都没能深入进去,而这些工作是随着他之后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才逐步解决的。
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时期,涉及从简单再生产出发论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与交换,特别是在论述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时,马克思才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分析。他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来分析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具体而言,奢侈品在马克思那里是由资产阶级消费的,凡是劳动力再生产,从而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充分进行,包括扩大再生产能够充分进行的过程当中,工人阶级需要的都不能叫奢侈品。“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Ⅱ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Ⅰ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5]448奢侈品就是资本家的消费特权,工人是无钱也无权消费奢侈品的,因为成为奢侈品的东西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极为有限的,如果工人也消费奢侈品,那必然就减少了资本家对奢侈品的占有数量。另外,工人要购买得起奢侈品,资本家首先一定要增加工资,而这是资本家最不愿意的。一旦工人有足够的钱能消费得起奢侈品,那工人也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
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奢侈消费的批判至此结束,再无其他深刻论述。所以客观而言,他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达到像其对资本主义一般商品消费的批判一样的科学高度。尽管他也像解决其他问题如对所有权概念、交换价值等的理解一样对奢侈消费的解读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化、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最终也只能说马克思只是为以后的学者涉入对奢侈消费的批判提供了“一种断代史的新素材”[6],而这一点被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批判性地发展了。
二、鲍德里亚理论视域中的奢侈消费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意识到的那样:奢侈消费的发展始终依赖社会经济实力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阶段,奢侈就等同于浪费,是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破坏,因为一旦一些人沉迷于奢侈品的享受中就意味着一些贫苦人获得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遭到了侵占。这时奢侈与权力紧密相连,只有拥有特权的皇权贵族才能毫无非议地享用奢侈品。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得到解放,大多数人已经脱离了温饱忧患年代,从而衍生出对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后,奢侈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受到广泛认可。尤其是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过渡,使得大多数人追求奢侈消费成为可能,以至于奢侈品在今天列斐伏尔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阶段,演变为资本控制、奴役人的方式。鲍德里亚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奢侈消费意识形态化这一问题的揭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他在继承了马克思有关该问题的分析基础上又经过了法国情境主义国际大师德波“景观社会”的理论中介,由此形成了他的完整理论体系。
德波是20世纪闻名于法国的情境主义国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马克思不曾遭遇到的全新阶段。马克思所面对的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标准化、齐一化生产阶段,工业化垄断了商品生产,从而解除了个体性差别和意义,人都成了“官能性”的人而拜倒在物面前。但在德波看来,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大众媒介的广泛普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也因此人们所触及到的世界就成了被景观重新编了码的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这样,他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统治现实而今已变成一个消费景观的王国”[7]。在物化的、笼罩着拜物教气息的圈子中没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高贵,这一自我价值的丧失又引起人们的普遍心理不平衡,人反而迫切地渴望重新确立一种差异、意义,“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8]72。由此,对奢侈品的消费就成为表征人的地位、身份的象征,奢侈消费也具有了被资本家操控的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才得以深入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奢侈消费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分析上来。
对此,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一)贬低奢侈品的使用价值,升华其符号价值
如果单就使用价值而言,奢侈品与一般的商品并无本质性差别,都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具体需要,那为什么它的价格却能高于一般商品几十倍甚至更多?比如,一款经典的LV手袋售价在两万元左右,而普通的皮质包也就五百元左右。面对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奢侈品,似乎价格在奢侈品消费者眼里并不是什么问题。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时期奢侈品除了具有使用性功能之外还有超自然的特质,它跃出了实用范围的功能,成为被符号标识的物。在奢侈品身上有一个来自文化的抽象化过程,面对文化性功能,使用性功能就要隐退。也正是拥有了超越自身功能的可能,才得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这样才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符合系统性的逻辑。奢侈消费在今天并非侧重其使用价值,而是成为人融入整个世界和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全新方式。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奢侈消费根本不是为了寻求其功用性,而是“被当做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奢侈品被赋予的这一含义正是当代消费社会的真正所指。奢侈消费一定要符合一个特点:我的物并不是我固有的消费对象,物主要不是在消费物的功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符号,是差异性系统中的符号,代表一种差异性的功能。“物品的‘功用化’也是一种凌驾并随处取代了客观功能的周密抽象(“功用性”并非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符号)”[8]72。这里把功用化打引号,就是区别于物自身的使用性功能,重新确立了物的功用。它是由主体随意赋予的,变成了跟主体有着某种特定联系,并从功能中抽象出来的东西,用于社会区分逻辑,在社会区分上起作用。变成符号的奢侈品迫使人们在符号系列中间来寻求它的存在,不同的物之间成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直接对应,它们相互指涉,形成一个体系。“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他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8]3单件的物品并没有意义,只有全套商品形成物之体系后才体现出意义,这就是鲍德里亚讲的“物体系”。他的这样一种理论构境,其实不是在研究物的关系,而是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正在被不断再生产的等级性社会关系,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最终落脚点。所以,物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体系。鲍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的奢侈品仅仅成为象征成功人士或有钱人的符号。不同于以往人们对奢侈品的购买,吸引人们去消费的不再是奢侈品本身的功用性,消费过程中再三权衡的也不再是奢侈品的实际用途,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是由大众媒介引导的屈从消费行为,所以人们购买奢侈品从来都是越多越好,丝毫不会满足于对已有物品的使用。
(二)奢侈消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阶级定义法
以往社会等级地位森严,人的出身是命定的,是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阶级构成也相对稳定,像封建社会时期地主与普通百姓之间,或者是古老的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十分严格的等级差别。人们的消费物也与其所在的阶层相符合,丝毫不敢有越界的想法,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来临,这种命定的东西正在被一点一点儿地消解掉。而当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这一地位仪式却仍然保留在人们的心目中,它需要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这就是消费的方式。当消费受到控制,受到广告、媒介等的引导,人们不再以满足基本需要来消费时,原本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动摇,各阶层之间的消费界限也消失了,不再有固定的消费风格,由此才有了阶层与消费之间颠倒的位置对调。“人所缺乏的,总会被投注到物品身上——‘发展落后’者的心目中,在技术产品身上被神化的是威能,拥有技术的‘文明人’心目中,被神化在神话学物品上的,则是出身和真确性。”[9]94通过消费奢侈品,人们重新获得了他们本无法企及的社会认可。“某个体属于某团体,因为他消费某财富;他消费某财富,因为他属于某团体”[8]51,在此复杂的阶级形式被简单地转移到个体与团体的关系上,这就是阶级被资产阶级民主化洗礼以后,围绕奢侈消费而产生的落差、差异而确立的新的区划法。
奢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被打扮成社会等级性身份地位区分的标志,对奢侈品的盲目追崇正是基于确证自我身份的表现,因为只有奢侈品才能彰显出购买者的财力与独特个性。“昂贵物品的消费是值得颂扬的,并且要是该物品的成本所包含的值得称许的元素,超出该物品外观上的机械用途所赋予的实用性时,该物品就具有尊贵性。所以,物品中如具有过度所费不赀的卷标就是颇具价值的卷标——透过对该物品的消费,就能带来高度满足的间接的、且又比出高下目的的功效。”[10]115不含有炫耀性挥霍成分的物品被视为不符等级而被消费者拒绝,不予购买。不顾物品本身的功用性,只是一味地想要占有它,在此,奢侈品不再作为功能物而存在,它只是一个能够满足人欲望的符号。对奢侈品的消费实际上就是在消费一种等级秩序中的符号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消费主体关系这样一种等级秩序,消费奢侈品的人真正关心的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系列中他所处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消费这个平台实现自我完成和自我消解,主体关系已经不再是主体的关系,而是主体特性的消解,变成了一个系统中的符号,主体自己也成为了符号。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所建构起来的奢侈品消费的意识形态性。
(三)对“符号/意义”的追求导致人在真实世界中的自我丧失
奢侈消费表征的是社会上层人士,是人人都向往的社会阶层,通过这一消费行为引起他人的注意,自身的社会地位得以确认,从而获得内心的满足感。鲍氏认为,这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人因为看到白人在地面上布置飞机的模拟物来引导飞机的飞行和降落,而被搅得心醉神迷,于是他们也用树枝和藤条建造了模拟飞机,满心欢喜地期盼着真飞机的着陆,从而获得内心的幸福感。现实正是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被非现实化,一切真实的东西都被缩减为符号,在消费奢侈品的过程中人们获得的并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产生的眩晕”。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8]11。
鲍德里亚为我们展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虚幻的符号世界,到处充斥的图像、声音、媒体使真实的世界发生颠倒,虚拟实为真实。“真实与策划、存在与表象——本来都是哲学一直严格区分的范畴,在媒体世界中却纠葛在一起,甚至含糊不清地彼此转换跳跃”[11]25,这种现实与虚构之间难以区分的状况直接造成人在消费过程中的迷失。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日常行为中物的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变成了对符号本身的消费,在消费中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是“主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一切他想要的,甚至包括他想不到的东西,以此彰显了自身作为成功人士的身份地位,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消费的假象所迷惑。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超真实”存在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拟真”的世界甚至要比“真实”还要真实。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黑白被颠倒。人在消费奢侈品的过程中脱离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一个符号的存在,也因此而成为意识形态秩序中的符号。这就是后现代的一种阴谋策略,它让人忘记了自我的真实存在,而让符号变成了唯一的真实。
三、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奢侈消费理论之比较
相比于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时期一般商品消费而建立起的庞大思想体系,他对奢侈消费的论述确实是极为有限的,这也导致他的相关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方面,不仅缺乏系统性的历史梳理,而且很多学者都以为面对今天奢侈消费的甚嚣尘上,我们无法直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应对策略。笔者以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在其所处的时代做出对资本主义奢侈消费的批判超出其实际地位的高度。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于“匮乏”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人们还基本上处于需要大量购买生活资料的阶段,而不像现在,一旦基本的生活资料得到满足,再增加消费,就必然需要靠文化的力量来打造奢侈品,这样不仅资本家能够从中赚取更多利润,而且由奢侈品所蕴含的新的阶级区划标准以及平等的意识形态更容易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换言之,正是在对奢侈品的消费过程中实现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认同。并且,马克思是为阐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才做出了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5]448这样的假设,所以对于奢侈消费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确实是其尚未充分论及的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此问题就毫无话语可言,其实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依据。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其次是二次方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也就是三次方的交换价值时期[4]99-100。概括而言,交换活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经过了“剩余产品交换——物质产品交换——一切东西都进入交换”[12]这样三个阶段。鲍德里亚正是认识到了这三个发展阶段之间都发生了“断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第二阶段跨入到了第三阶段的交换活动中,由此,他在经由德波的理论中介基础上得以洞悉到当代资本主义奢侈消费的统治现实,并把对当代社会基本生存方式的异化消费之考察带到了意义、符号、景观、媒介等领域,首创从奢侈消费这一特殊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从商品生产转嫁到对差异、意义的生产上,谁来生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意义、差别、个性的体现。我们就追求这样一种意义,而意义又是由整个工业生产体系在定义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就每个角度而言都已经把意义、象征性价值发挥到极致了。它让人们相信一个神话:好像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丰裕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从而转向更高级的奢侈品享受,奢侈品再也不是资本家阶级的享受特权,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以拥有一部苹果手机或者是一辆奥迪汽车。通过消费奢侈品体现出人们迫切凸显等级的欲望,“为了有效地增进消费者的荣誉,就必须从事于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费。要博取好名声,就不能免于浪费”[10]73。奢侈消费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的差异化生产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扮演出来的最新策略,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全新统治方式。奢侈品不再是我们的真正生活、自由发展、个性发展的需要,它本身成了资本生产制造出来的产物,在更归根结底意义上承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言说的商品物化在当代的最新表现形式,换言之,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奢侈品不过是被妖魔化最严重的符号。
鲍德里亚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后由英美所引领的消费社会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揭示,有助于我们在深层逻辑上把握奢侈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的具体情况,从而揭穿了奢侈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获利机制,并成功解蔽其意识形态性。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理论确实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反观当下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我国的诸多奢侈消费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透过鲍德里亚的理论分析,诸如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奢侈品愈发狂热?这种狂热现象何时才能终结?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奢侈品牌?为什么国人更加崇拜、更加迷恋国外的奢侈品牌等一系列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由于他采取了和德波一样的理论程式,并发展了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论而从消费者的心理基础、微观结构层面以及资本逻辑的运作等角度来展开研究,从而放弃了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这就导致其理论存在重大失误。归根结底,鲍德里亚是从资本主义的外部现实层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始终无法深入到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机理层面。
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奢侈消费现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审视今天种种新现象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说:“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包括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13]306这就为我们牢牢掌握马克思的方法论武器来面对一切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提供了有力依据。一切关系在今天万物商品化阶段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就连奢侈品这一原本象征“有品质的生活”的标志物如今也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这个现象在马克思时代没有出现,但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理解它。尽管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形式在不断深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资本生产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它就仍然处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一般逻辑上。而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在于基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来解释奢侈消费问题。今天,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统治的主导性、总体性与颠覆性,更要看到其历史形式的变化性与隐蔽性;不仅要从宏观上批判与反思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更要从微观具体角度来看待其统治的实质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处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无限展开与外在现象的具体把握之中,而不能奢望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是实践形式就一劳永逸了。这个拜物教(物神化)难题的解决,需要非常细致的对日常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等的研究批判,需要无数次微观具体的生活实践特别是通过不断地“去资本化”的新的实践逐渐破解。这是一个需要漫长而反复的修复才能逐渐克服的痛苦的自然历史过程。
所以,马克思有些耐人寻味地告诉我们:“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97马克思的“拜物教”问题之难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或意识形态批判、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的问题,而是漫长的、细致的反复“修复”、“纠正”人类历史生活误区的实践问题。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轻易像鲍德里亚那样,自以为抓住了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述的奢侈消费层面,并运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揭露了它的意识形态性,就可以质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企图颠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唐正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3(5):33-49.
[7]刘怀玉,伍丹.消费主义批判:从大众神话到景观社会——以巴尔特、列斐伏尔、德波为线索[J].江西社会科学,2009(7):47-55.
[8]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10]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布罗耶尔,洛伊施,默施.法意哲学家圆桌[M].叶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姚顺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及其方法论根源[J].现代哲学,2007(2):5-1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4.003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吴琼,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036/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