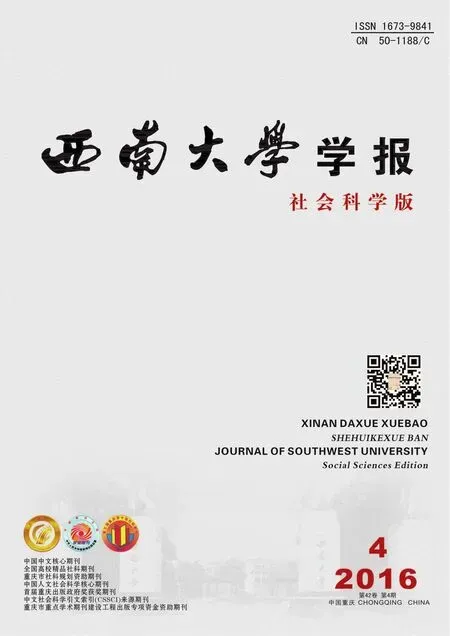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四重前提性澄明
2016-02-20陈雷
陈 雷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市 100872)
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四重前提性澄明
陈雷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市 100872)
摘要: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正义”概念来谈论正义,即使偶尔为之,也是迫于被批判者使用而使用,那么其因由何在呢?当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意指历史在资本主义普世史中终结,被福山继续以之来为现代自由主义正义摇旗呐喊时,无疑需要召唤沉默的马克思正义思想出场来展开正义的对谈。那么马克思用以对谈的正义概念和正义原则又是什么呢?当马克思面对由康德的伦理正义和黑格尔的永恒正义合力形成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正义时,马克思对之予以批判的意旨又是什么呢?当马克思所寻求的共产主义人类正义,之所以不被视为乌托邦而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本性原因又何在呢?这些事关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先验性定在,而是需要加以澄明的前提性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正义思想;匿名的在场;历史的复写;前提的批判;现实的未来
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和现实旨归,是聚焦政治哲学的聚焦点,可以聚焦政治哲学的各种聚讼,成为政治哲学语言所指的在场。正义之于马克思政治哲学亦然。正因如此,它被前见性地视为马克思本有的政治哲学内涵而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定在,以至于错失了审察正义本身之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它是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问题。因为它事关我们研究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然而,在研究马克思正义思想时,当我们面对诸如罗尔斯和诺奇克等人的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以及面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正义理论时,习惯性地会受这些国外正义思想的影响,跟着他们的思想观点走,很少会回到“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什么”的前提性问题上。但这恰是我们不受外来思想支配而独立研究马克思正义思想时,必须要搞清楚的首要问题。
一、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匿名的在场
“正义”概念在马克思文献文本中极难找到,即使是在“正义”概念出现的地方,也多半是马克思在批判被批判者时,迫于被批评者所使用的“正义”概念而又不得不对之批判时所使用。正是因为马克思尽量避谈正义甚至于尽量避免使用“正义”概念的缘故,以至于后来者在“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展开了依据马克思文献文本和各自对马克思文献文本所理解和引用的理据来研究和建构马克思的正义思想的努力。而且可能正是因为马克思尽量避谈正义,使得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论理解力,充分扩展自己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论阐释空间,才使得“马克思与正义”关系在研究者那里更具理论的魅力性和研究的开放性。这或许可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持久研究得到印证,也可从中国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研究的持续升温得到证实。甚至于罗尔斯和诺奇克等人也不得不提及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可见,国内外对马克思与正义关系的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仅恰恰证实了“马克思与正义”论题的理论魅力和开放空间,而且也证实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研究的发散式、多样性研究格局。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是在场的也是匿名的,是匿名的在场。事实诚然如此,问题是何以如此?
事实上,“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1]97,同样契合马克思的哲学旨趣。而且在马克思那里还有不愿谈的自我节制。马克思在不能谈和不愿谈之间沉默的别无其他,正是沉默于言谈正义的事情。然而我们却又分明在马克思的白纸黑字里窥视到了正义的在场和隐匿的行踪。可见正义被马克思以沉默的不谈方式消解为无名,能指为匿名的在场,任由后来者去有所作为,马克思自己则置身事外。
既然“不能谈”成为马克思不谈方式之一种,抛给我们的反思是马克思何以不能谈正义?这正是马克思的大智慧之处。“不能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实指,确实不能谈。意指在语言中给思维划界,界限的那一面属于不能说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之所以沉默不谈,是因为界限那一面的事情无意思。界限那一面的无意思的事情究竟是些什么事情呢?维特根斯坦沉默不谈。他只是以肯定的方式明确肯定了界限这一面的事情是自然科学的命题,除此之外都与哲学毫无关系,不能谈。[1]20显然除了自然科学命题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当是界限那一面的不能谈的事情。与之相反,“不能谈”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虚指,看似不能谈,实则能谈。在黑格尔那里,存在意即思之在。海德格尔则为存在找到了居所,那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的主人,是语言说话,是道说,人不是语言的给出者而是倾听者,是在倾听语言的道说中才说话。[2]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并非缺场,而是由马克思的文字给出正义,即“词语给出:存在”[3]。换言之,正义在马克思的语言中存在,为语言所道说,语言成为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寓所。尽管如此,道说正义的语言并非是“正义”语词,而是除此之外的任何语词。因为道说正义,“马克思语言”可以,马克思不可以。而且,马克思不能谈。*这在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出于批判的目的引用包括“正义”语词在内的施蒂纳文本原话时,只能够运用语言书写功能写出“正义”语词,但在批判时马克思却又拒绝使用“正义”语词来批判之,而是以批判的否证方式在否定施蒂纳思想时连带地否定了施蒂纳的“正义”。因为马克思不能谈正义。一旦马克思谈正义,就会在对谈中处于与对谈者同等的对谈地位,将自己的哲学境界降低到与之对谈的对谈者的哲学水平上。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的第118、210、263、566、619页中都可见到这种“马克思语言”可以写出“正义”语词但马克思却不可以且不能谈的情形。
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将西方传统正义划到“有些精神行为扎根于沉默”[4]的界限那一面去,视为“马克思”不能谈的正义,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正义思想划到语言能够道说的界限这一面中来,视为“马克思语言”能谈的正义,以此将自己的唯物史观正义与西方传统正义区隔开来。这源于马克思对温和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永恒正义的反感。温和政治经济学总是以田园诗的姿态认为“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5]。同时也源于马克思对吉尔巴特的那种天然正义即绝对正义的拒斥。吉尔巴特将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所获得的利息视为天然正义。但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总是历史视域的正义,是生产方式的相对正义,“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6]。相对于这一直接运用“正义”语词道说唯物史观正义的特例,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情则是,马克思让语言道说唯物史观正义,却又避用“正义”语词来道说。这说明它已被他散播到其他语词中去,褶皱于马克思思想的各个层面,匿名于马克思各文本之中,隐秘的在场。
不仅如此,而且马克思还以“不愿谈”的不谈方式拒绝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正义。福山认为正义和政治秩序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7],马克思对此更是了然于胸,理解得透彻,批判得彻底。这可从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著作中得到见证。我们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主义正义论是伦理层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在内的伦理善的最高表达,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高善,是伦理的德性,体现在家庭血缘伦理、市民社会经济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的各个方面,表征为自在自为的意志和自由。“因此,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神,在这些神面前,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8]这种“伦理即永恒正义”的伦理性正义,或者说,这种作为自由主义正义的伦理性正义,既是黑格尔法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以法哲学作为其前提和基础的必然结论。据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正义的拒绝和申斥。因为马克思深知,现代国家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系统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也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9]206。自由主义正义就是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实。更何况资产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将自由主义正义视为他们的阶级意识形态,而且还将其拔高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全民社会价值,甚至于还将其扩张为全球普世价值,充满着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尤其会让马克思深恶痛绝的,“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0]519。黑格尔更是将之视为永恒的正义,意即人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为历史的永恒。这也与马克思的那种通过消灭阶级和国家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解放思想格格不入。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0]38,源自于政治解放的自由主义正义也并不就是人的永恒正义,唯有人类解放本身才是人的解放,源自于人类解放的人类正义才是人的永恒正义。因此,被黑格尔视为永恒的自由主义正义,只是资产阶级的伦理诉求和政治谵妄,只会逐渐僵化为人类解放的思想羁绊和实践障碍,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以至于马克思不愿谈正义。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尽管正义和政治制度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并非不重要,但是相对于人类生存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以及由其构成的经济基础,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和正义是次生的,正义只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而出现的次要问题,以至于马克思更愿意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事业上,而不愿意刻意谈正义,而将他自己的正义思想隐藏在他愿意谈的事情背后,巧妙地处理为匿名的在场。
二、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历史的复写
当身处新世纪新时代的我们面向历史时,我们愈加领会到历史的厚重和忘恩负义,愈加感觉到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需要出场,需要它沿着马克思的语言逃逸线溢出,将它带向我们的语言之中来面向我们,在我们的语言地带绽露显白出来,敞开为无蔽之境,在本己的切近中自我澄明。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如果感受我们的时代,“他会说,消费是人民的鸦片,因而消费也就是宗教”,以至于我们的消费时代已用“无社会能力”翻新了贫穷一词,“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从而也掩盖了剥削,剥削才是贫穷的原因”[11]61-63。而且更是因为当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沉默于他的文本之中深藏不露时,黑格尔的“永恒正义”便会以普世价值的姿态成为西方的正义话语霸权,其在当代的新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正义,为此摇旗呐喊的便是福山紧跟黑格尔的脚步宣称“历史的终结”[12]。这种以肤浅的历史忘恩负义来雕刻厚重的历史真实,迫使我们围观的是历史雕像的反讽,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忘恩负义。“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11]60面对历史的如此现实窘态,我们为此需要召唤马克思正义思想出场,重新复写历史视域的正义,让自由主义正义在马克思正义思想中自行反观到自我镜像的本相来。
正义犹如双子星,眼见的单星并非真实,总有暗星般的非正义隐藏在看不见的远处,相伴而行,彼此不可或缺。可见,与正义最亲近的当属非正义了,可将正义和非正义视为鸳鸯一体,二者的阴阳结合才能够衍生出正义的概念族群。就此,我们认为,正义和非正义一如凸凹,此消彼长,相互周易,盈缺自如。一旦二者之间凸凹削平如镜面,不复为凸凹,也就不复为正义与非正义了,从历史的维度看,应指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非正义消失,正义成为常态。其本真性的意谓就是共产主义已经超越正义,自由人联合体跨入了人类大同的历史,马克思的思想真正实现为现实,马克思的篇章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因此,当我们言谈正义时,非正义总是如暗星般如影随形地成为我们言谈的背景之幕,与正义共同构成我们言谈的境域,历史的、现实的或当下的。反之亦然。
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生产关系,为人类生产方式所规定,又反弹于人类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中成为历史的内容。历史反过来又成为正义的形式,构成正义一般,规范约束着正义的历史内容,使之不至于成为无边界的正义,通行于各生产方式的各个历史阶段,通约于人类总史。正义的这种历史形式,我们称之为正义的历史原则,也视之为正义的总原则或一般原则。正义的历史内容,具体是指由历史的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现实生活。在各生产方式中,依照马克思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及其以此来关注资本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未来的哲学旨趣,我们可以将对正义具体内容的研究置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处于后两者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简洁区分之中进行。其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私有制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公有制生产方式,由此所决定的正义形态也就可以本质性地区分为私有制形态的正义和公有制形态的正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正义就属于前者,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共产主义正义属于后者。马克思就是在批判前者之中立论后者的,其否定性的和肯定性的正义思想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在辩证地批判资本主义时,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二律背反性同构现象,唯有正义的历史原则才能够本质性地解析。在历史地批判私有制社会异化现实时,唯有依据正义的非异化原则才可以反其道批判之。在辩证地审视正义与法权的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法限定了正义的法权形式;只有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自觉劳动才真正实现了无法权正义,也意即它超越了正义。简言之,人类总体历史的生产性存在,在正义的历史原则下证成;人类前史的私有制之恶,在正义的非异化原则下批判;人类正史的个性全面发展,在正义的自由自觉劳动原则下呈现;这三者共同同构为马克思正义思想内容,交织为正义的历史逻辑。历史之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能够成为正义的视域,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516,马克思正义思想就是隶属于历史视域的。
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中,正义的历史形式之所以决定正义的历史内容,是因为历史是人类的劳动生产史。将正义概念置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之上,便是将“正义一般”即正义范畴置于历史的感性根基之上,确认了历史的形式就是正义范畴的普遍性特质和抽象性能指,通约于各生产方式的各个历史阶段,统领正义的各具体历史内容,使得正义历史内容的特殊性统摄于正义历史形式的普遍性之中。也正是在历史形式的抽象性统领下,正义的历史内容才可以沿着历史的轨线,在历史的各节点上呈现为具体,其内容才具有具体性和饱满性,既不至于流俗于无规定又不至于流俗于空疏。反过来,尽管历史的形式作为正义的普遍性能够统摄特殊性,但是由于它又是最单纯最抽象的正义规定形式,不具有任何规定性的内容,不能说明正义的任何意谓,因此它又需要它的特殊性内容来确认和反映其普遍性特质和决定性地位,而离不开具体的特殊性内容,从而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可见,正义的规定性本身是双重的,“即:第一是形式的,第二是内容的”[13]。这样,正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集中于正义概念的个体性之中而共同构成了正义的根据。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正义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它始终是在历史形式和历史内容的双重规定性中历史的在场。非正义也始终以历史的方式敲打着正义前行,凸凹为历史的非镜面波纹和褶皱,直至共产主义的到来,一切方归于历史镜面的澄明和纯净。
三、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前提的批判
马克思和康德同为批判哲学大师,在哲学批判中安放自己的哲学思想。康德意在澄清知性知识前提,为理性信仰安置地盘;马克思意在澄清感性历史前提,为共产主义安置地盘。康德是挤压知性地盘至合理的程度以腾挪出理性的空间来安置信仰,马克思是延长历史终结时间节点至共产主义以破灭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来还历史的清白。因为在康德和马克思之间还穿插着黑格尔,他以绝对精神的名义从哲学的缜密论证中宣称资本主义的永恒正义,即资本主义日不落正义。这就将问题引向了正义的本性上。换言之,就是内蕴于康德实践哲学的伦理性正义和内蕴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永恒正义即伦理性正义,尽管前者是基于内在个体良知的伦理性正义,后者是基于外在共同体规范的伦理性正义,但是二者同是立足于理性自由根基的自由主义正义,是改造精神世界的现实自觉,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哲学呈现,自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启蒙精神的批判神韵和哲学担当,散发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文气息、人道情怀和世界胸襟。这对置身于其中的马克思而言,与内蕴于他的哲学的历史性正义,特别是与内蕴于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人类正义,是从根子上相抵牾的,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拆穿历史谎言,修正历史偏差,喊出改变现实世界的历史最强音,在批判中引导无产阶级革命不断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这场较量是在批判的语言中进行的,并且存档在语言的批判之中显明出来。康德在知性知识领域挤走了上帝,却又在理性信仰领域请回了上帝,使之担保个体伦理正义的自由,试图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黑格尔虽然替哲学报了它作为中世纪神学婢女之仇,但他并未将神学贬低为哲学的婢女,而是在绝对精神和上帝之间的暧昧调情中调和了哲学和宗教,使之担保国家伦理正义的永恒。他们的内在公约数是上帝成为伦理正义的守护神。只不过在康德那里是道德性的上帝,在黑格尔那里是政治性的上帝。他们的外在公约数是语言所指成为伦理正义的表达方式。意在以语言所指的共时性语言在场特权压制作为历时性语言能指的文字沉默。因为“所指的形式本质乃是在场,它靠近作为语言的逻各斯的特权乃是在场的特权。”[14]换言之,一切非资本主义正义的表达都是反资本主义的,都不可视为友善表达资本主义的语言所指,而被视为外在于资本主义共时性的语言能指,或者说,历时性的语言能指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异端,以便从语言上守护资本主义正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譬如,马克思所表达的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够实现的人类正义,是指向资本主义未来的历时性表达,是诞生于语言所指之中的语言能指,是共产主义正义的能指文字书写,自然而然地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异在的语言能指。像“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10]197这类语言能指就极易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异在。因此,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既根源于又脱离于资本主义语言所指的社会现实,是马克思在语言所指中突围出来,予以语言能指反击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它是马克思以时间性的语言能指来对阵空间性的语言所指的战利品。
马克思的语言能指反击,事实上就是历史前提的批判。换言之,就是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私有制社会形态的批判。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集中体现了私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涵,为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提供了解答谜底的钥匙。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与崛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无产阶级,共同构成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随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即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史前时期也就随之而告终。因此,只有理解了资本主义,才能够充分理解前资本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也就基本上批判了人类前史的私有制,也就体现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705的方法论智慧。于是马克思就交织叠加地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等方面的全面批判。批判锋芒直指资本主义永恒正义,其尖锐性和震撼力直插人的心底。
马克思的批判目的是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而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唯有批判了人类前史的私有制制度,才能够为实现人类正史的公有制制度指引历史方向,不至于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语言所指所迷惑,以此认识到历史不会终结于作为前史的资本主义,而会延续到作为人类正史的共产主义。进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永恒正义是矮化历史的历史谎言,共产主义的人类正义才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正义。
诚然,伦理性正义并非不重要。如果经济基础不合法,政治制度不合理,又无力改变现实世界,那么从精神上呼唤伦理正义未尝不可,以精神的改造来认识现实改变的必要性,仍是一种历史责任,在一定的历史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理由。这点并非马克思没有认识到。然而,如果一味沉湎于改变精神世界之中不可自拔,不免有坠入批判的批判之罗网之中,沦为词句对词句的批判,反对的是现实世界的词句,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再好不过的例证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他期待着在“批判的批判”中改变世界,事实上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的只是自己被逐出大学教席[16]的自我命运,世界依然照常如旧。这点尤为马克思所清醒地认识到,并在哲学批判中加以阻止。
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难免被怀疑。置他于尴尬境地的是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它们是在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时提出的,是作为马克思批判论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有力的一部分,以之见出《哥达纲领》分配正义论的幼稚可笑、异想天开和非现实性。而且即使就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本身而论,它们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与马克思所警惕和抵制的那些东西,有阶级性的本质差别。更何况这只是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事件的附带品,相较于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整体性而言,相较于马克思所寻求的生产正义而言,分配正义根本不配成为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根本就没有赢得过马克思的青睐,至多不过是从属性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15]695。只不过后来者根据市场经济或消费社会的需要,将之附会拔高为不应有的突出地位,反而对本应重视的生产正义视而不见。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短视和消费社会的必然反映。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正义和人类正义才是被重视的对象。
事实上,伦理性正义向来是为马克思所警惕和抵制的,甚至是予以坚决批判的[17]。根本原因就在于,包括当代分配正义在内的伦理性正义,是资本主义架构内的正义取向,在当今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其正义的软实力、影响力、扩张力和渗透力,都不遗余力地伸展着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实质。可能它们也不时地相互批判,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各取自由视角,立论自己而驳论对方,然而资本主义的地基却从未离开过,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地平线上相互缠绕着的,从未越资本主义雷池半步。
四、正义之于马克思意味着现实的未来
马克思远要比康德和黑格尔走得更远,是因为立足于现在而视域向前的,关注的是现实的未来。当康德和黑格尔还在“宗教-政治-哲学”的视域中运转哲思时,马克思已经在“宗教-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跨过了“宗教-阶级-国家”而将哲学视域转向了“无-宗教-阶级-国家”的共产主义未来。康德和黑格尔关注的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及其阶级利益和思想理论,马克思关注的则是无产阶级人类革命及其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大同。根本原因就在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立脚点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马克思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
这并非突兀,也并非是无根的浮萍。马克思在他17岁时就已立下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入不幸的行为。”[18]不幸一语成谶。这位在同时代人赫斯看来“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11]65的马克思博士,只要他愿意在体制内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就可拥有不可限量的远大前程和富裕生活。而且他的家境也足够确保他过上富裕的生活而远离贫穷。这一切也决定了他没有理由愤世嫉俗。然而,他为了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坚贞不渝地反对资本主义及其剥削,参加各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过上了宁愿流亡也决不向现实妥协半步的贫困生活,足见马克思未来的共产主义视域是多么地纯粹和高尚。因为他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他的视域是未来的共产主义,他的目标是人类正义。正因如此,马克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19]。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视域及其所呈现的人类正义不是乌托邦,而是立足于现实的未来,是由资本主义现实所决定的未来。
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总体现实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总体现实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在此生产力决定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现实是,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由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总体现实影响是,历史向世界历史方向发展,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一概世界化了,市场经济主导着世界。在世界市场经济的总体环境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矛盾是,资产者占有剩余价值与无产者失去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着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发展。其必然的总体历史冲突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无产者积聚联合成为无产阶级总体创造了时空条件。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势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0]。这种历史趋势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基于资本主义的总体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总体生产力决定了总体生产关系的这种生产方式状况,决定了总体经济状况的社会化矛盾,由此也就决定了阶级斗争的总体政治状况。总体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合力,也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总体现实之中的,并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势归于终结的时候,共产主义也就实现为现实。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理论预设或理论幻想,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未来现实。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认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9]210为此马克思强调,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行动比思想行动更重要,因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9]347。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为实现人类正义而进行的共产主义行动。
另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具体现实决定的。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这就决定了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外在于社会的现实个人,而是内在于社会的现实个人。阶级社会的人是有阶级属性的。可见,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最为具体的现实。资产者和无产者就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个人,分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问题是他们是如何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呢?这就需要根据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来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占有物的生产资料,无产者拥有人的劳动力,资产者购买无产者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就构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劳资关系。由于是资本购买了劳动力,因此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就拥有对雇佣劳动力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以至于资本占有了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失去了剩余价值,造成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资本剥削,体现了生产的非正义性。这种经济异化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现实生活异化。它的政治性就是资本对人的统治,既包括对无产者的统治,也包括对资产者的统治。因为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也要为它的增值奔走于世界各地,受它所驱使。这也说明了无论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还都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21]阶段。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的根源,就在于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存在。要想铲除和扬弃私有财产的非正义性,唯有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正义。“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9]331,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人类正义。
因此,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视域及其视域内的人类正义,是由资本主义总体现实和具体现实共同决定的,决不是马克思无根由的肆意臆断,更不是马克思所预设的历史乌托邦,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未来。只要在人类总体历史的大历史尺度上假以时日,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完全发挥出来以后,共产主义的人类正义就会完全实现。因为那时就会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自由自觉劳动的生产关系完美地结合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彻底地实现为无分工、无剥削、无阶级和无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个性和全方位能力就会于其中充分涌流和发挥。但这可能需要我们人类要有足够的耐力在历史的时间流中耐心地等待,可能我们几代人或几十代人都不能亲眼目睹到。但我们绝不能据此将之视为乌托邦。即使退一万步讲,因我们是向死而生的而不能亲眼目睹到而将之视为乌托邦,那么这种乌托邦也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唯物主义被当代西方世界颓废为唯物质享乐主义的今天,它更是难能可贵的,尤显得稀有和珍贵。
为此,我们要坚决反对生产力至上主义倾向,只重视生产力发展而无视生产关系是否与之相适应。表现在现实中,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比社会主义更充分更有优势,以便为资本主义永恒正义贴上“历史终结”铭牌,戴上“日不落”徽章,以此屏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酷剥削现实,企图以之来一叶障目。其实质是一种右翼实用主义思想在作祟。可能唯一让他们苦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至今还存世,而不是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至今还在现实地上演。我们也要坚决反对生产关系至上主义倾向,只顾及生产关系和谐而根本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左翼冒进主义倾向的生产关系,只是藐视生产关系是决定于生产力的自我虚妄,是试图挣脱生产力束缚的生产关系幻想,最终只会破灭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原罪之中,真正沦为历史的乌托邦。在此双重反对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体认到,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人类正义,是体现既重视生产力发展也重视生产关系和谐的典范历史正义。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9.
[3]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5.
[4]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M].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1.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79.
[7]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0.
[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伯尔.伯尔文论[M].袁志英,李毅,黄凤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2]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10.
[13]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86.
[14]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5.
[17]张文喜.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2014(3):31-43.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04.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4.002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陈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0-0/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