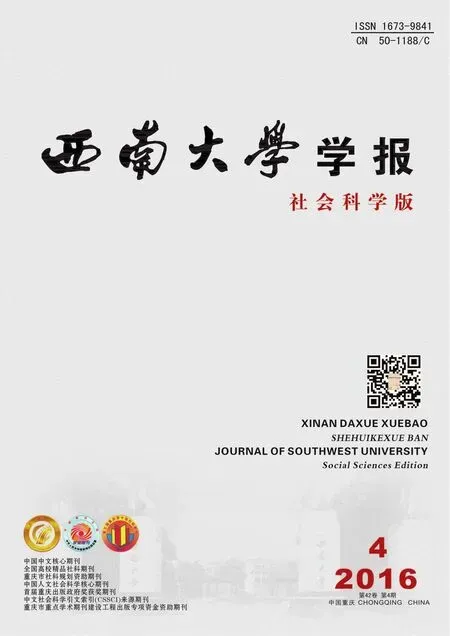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2016-02-20王崇
王 崇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王崇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非制度化互动方式主要指集体抗议、社会运动等政治互动方式;制度化互动方式主要由选举、立法投票等构成。。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关键词:抗争政治;非制度化互动;视角转换;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中国启示
在政治体系运行过程中,抗争行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较为激烈且具有斗争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塞缪尔·P.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利益集团,现在他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1]抗争政治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2]。从广义来讲,其包含了社会运动、集体抗议和革命等形式,由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对于上述行为研究的差异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碎片化”的学术研究模式才得以整合。道格·麦克亚当等人提出融合了集体抗议、社会运动与革命问题的统一分析框架——“抗争政治”研究*其标志性文章为:Doug McAdam,Sidney Tarrow,Charles Tilly.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1996,1(1).,并指出抗争政治需具备如下几个特征:“提出要求者与被诉求者之间发生集体的相互作用;国家或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者;互动结果影响参与者的利益。”[3]
目前,学术界关于抗争政治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研究视角层面对抗争政治研究进程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分析。本文的目的在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梳理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演进脉络基础上,剖析抗争政治研究视角的转换过程,寻找过程背后的深层原因;二是在考察抗争政治研究视角转换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具体启示。
一、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演进
抗争政治研究的理论总结是由西方社会现实环境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发展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整体而言,抗争政治理论研究经历了集体行为论(collective behavior)、资源动员论(resource mobilization)、政治机会结构论(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国家与社会交会论(state and society’s intersection)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这四种理论从整体上反映了抗争政治研究的演进过程。
集体行为论是抗争行为研究的源头,其最早溯源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聚众:一个关于大众心理的研究》一书中关于聚众行为的分析。1921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人将集体行为界定为:“个人在某种共同性的冲动影响下做出的行为。”[4]受到当时社会学主流观点——“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其强调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有机构成的整体,其中每一部分的缺失都会影响整体功能和秩序的实现。思想的影响,集体行为论重点关注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自发和混乱的集体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初级和混乱的集体行为方式如何发展至有序状态。在集体行为论者看来,集体抗议等行为的发生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造成的:首先,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不合理、缺失或崩溃导致了社会紧张;其次,社会紧张带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孤独、愤怒、焦虑、迷茫等心理反应,在此基础上产生非理性、自发性的破坏行为。例如,格尔在研究集体抗议和革命的过程中就发现:“集体暴力的产生源自行动者内心所持有的相对剥夺感,而这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个人期望与个人认为所能够获得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之间的差距造成的。”[5]康豪瑟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社会结构内中间群体(如社会团体、专业组织)缺失,当面临压力或危机时,精英与群众之间很容易受到对方直接的影响和鼓动,导致盲目性集体行动的产生。”[6]
集体行为论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集体抗议、社会运动或革命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但也遭到诸多质疑。一方面,集体抗议、社会运动或革命行为的发生并非完全与社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心理挫败感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查尔斯·蒂利等人在研究基础上发现:“法国集体暴力事件的发生并非与生活状况好坏存在明显相关性。”[7]另一方面,集体行为论关于行动者的非理性假设也难以站得住脚。道格·麦克亚当认为:“如果参与者是出于表达被压抑的冲动或焦虑,那么,这就与社会运动作为推动社会政治变迁的动力这一客观事实不符。”[8]集体抗议行为的发生并不完全是由于人们对于社会系统崩溃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反应。相反,集体抗议者是理性的行为主体,抗议活动是否发生跟抗议者能否动员到足够的资源相关。
资源动员论的提出在于回应和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事件本身所呈现出的理性化、组织化、专业化等特点。倘若运用集体行为论者的非理性假设,很难解释这些政治抗争事件,比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麦卡锡和左尔德在《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不完整理论》一文中指出,在抗争活动中,抗议者要不断“动员支持者、将群众或公众中的精英转变为同情者、争取斗争对象的转化、运用外部的通信传媒、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等资源”[9]。也就是说,在坚持理性人假设前提下,资源动员论者认为组织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通讯资源等对于抗争发起者而言至关重要。但问题是,“由不同人群发起和参与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存在平等的、市场性的资源竞争关系,也一定存在某种不平等的统治性关系。”[10]152作为被主流政治体制排斥在外的政治抗争活动,其发生或发展总会面临特定的政治环境并受其影响,这正是资源动员论者“忽视与制度化政治有稳定联系的正式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与被排斥群体发起的集体行动之间的不同”[10]159,不加区分地谈论资源动员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缺陷。因此,抗争政治研究必须将变化的政治环境因素纳入视野,关注其对抗争活动的具体影响。
在上述观点影响下,政治机会结构论日渐萌发和成型。1973年美国学者艾辛杰在研究美国城市中抗争行为的发生条件时指出:“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与城市政体或政治系统的开放与封闭程度相关联,开放度高的城市为民众表达意见提供了途径,开放度低的城市限制了民众表达诉求的机会,而处于中间程度的城市政体环境为民众发起抗议活动提供了客观条件。”[11]换言之,变化着的政治环境既引导着政治抗争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又影响着抗争活动的整个过程。随后,麦克亚当将政治机会结构界定为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制度化政治体制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二是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或精英同盟的不稳定性;三是运动从精英中获得盟友的可能性;四是国家镇压社会运动的能力和倾向。”[12]事实上,上述几种要素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比如一国是民主政体或威权政体,二者对于抗争活动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威权政体对于政治抗争活动一般倾向于采取排斥性策略,民主政体则倾向于采取包容性策略;二是国家能力*迈克尔·曼认为,国家能力主要受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影响。前者指国家不需要与市民社会进行例行协商而作出决定的能力,后者指国家的制度性能力,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详见(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8-69页。,主要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或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弱,比如国家是否具有科层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官僚,这直接影响了国家与政治抗争者的互动过程;三是国家自主性,“由于国家是由一套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构成的,在维持秩序或面对其他威胁时,国家利益并非一定等同于国内支配阶级或其他成员的利益,国家具有维护物质秩序与政治稳定方面的独特的、根本的利益”[13]。也就是说,政治机会结构论者从整体上关心国家要素(政体的开放与封闭程度、政治精英的团结程度、国家的镇压能力)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影响,但问题在于,某些抗争活动可能并非完全由国家因素决定。在此情形下,研究者对既有解释方式进行了不断反思。
国家与社会交会论认为,对于抗争政治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双重要素,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及发展过程“既非完全由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亦非完全由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决定,而是由二者之间的交会情况决定”[10]184。换言之,政治抗争活动是否会发生、发生之后的走势以及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由社会要素或国家要素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二者相互依赖与互动的具体过程。比如,赵鼎新认为,政治抗争活动发生与发展的特点,取决于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代表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情感与价值诉求。适度发育的异质性中层组织可以带来不同人群利益和诉求的分化,尽管限于部分人群的诉求事件在所难免,但不至于产生大规模抗争活动。国家是否允许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建立并运作,对抗争事件的发生、发展及二者的互动具有重要影响。详见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发育情况以及国家对它的态度。一般而言,“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成熟的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可以有效分散利益和诉求,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抗争活动,但处于兴起阶段的社会中层组织由于分化不足,同时又具有一定动员能力,容易诱发激进的政治抗争活动,而此时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威权或民主)以及国家对于社会中层组织的态度(包容或禁止),对于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10]185。
二、抗争政治研究的视角转换:三种类型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抗争政治研究总体经过了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机会结构论、国家与社会交会论的理论演进过程,上述理论成果为我们认识和解释政治抗争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工具。事实上,不同的理论解释背后,既与理论所要对话的社会现实相互关联,又蕴含着特定的研究视角。整体而言,上述理论演进过程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不同视角的转换。
(一) 社会中心视角
社会中心视角曾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中心视角的产生与发展最早可以溯源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洛克在论述国家和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与目的时就曾指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缺陷,政府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权力,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14]社会中心视角往往从社会结构或社会行动主体层面解释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原因与过程,国家或政府则被视为一个“平台”或“黑箱”,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较为典型的表现便是在西方国家盛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多元主义。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社会被看做是由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某项子系统功能的缺失会导致系统整体价值或运行秩序受到损害”[15]。受其影响,研究者在解释社会发生抗争行为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结为社会系统之间整合不足导致个体的非理性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失范”。集体行为理论将政治抗争行为的产生与发展归因为社会结构紧张所导致的非理性集体反应便体现了上述视角。
除此之外,在社会中心视角下,多元主义成为人们解释政治抗争活动的另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在多元主义理论中,国家或政府被人们视为一个“平台”或中立的“竞技场”,在此“平台”或“竞技场”之上,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相互争斗或彼此影响。罗伯特·达尔曾在《谁统治》这一经典著作中围绕美国纽黑文市的城市重建、公共教育等事件的决策问题,再现了平民、企业主、政府人员等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相互斗争和影响的真实过程。事实上,资源动员论者正是秉持了上述政治观念,在坚持“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强调组织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通讯资源等对于抗争者的重要意义。但是,以社会为主要的观察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抗争活动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因素。
(二) 国家中心视角
在以社会为主要观察视角的抗争政治研究中,政治抗争行为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特点几乎都可以从社会要素中找到答案。然而,随着理论研究的推进与现实社会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国家或政府在政治活动或抗争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研究者发现“在政治活动中,政府机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平台’,反而往往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和行动主体不应该退出研究者的视野。”[16]3-4其次,面对二战以后严峻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义”逐渐兴起,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国家或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主体或制度结构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政治抗争活动本身也产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剧变将一些学者的视野从一个国家内部的改良性运动转移至革命性运动和跨国比较上来,这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拾’国家。”[10]175因此,以西达·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学者不断呼吁“把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 )”[16]1-7。
政治机会结构论也正是伴随上述背景逐渐发展并完善的。如上分析,根据麦克亚当对于政治机会结构四个方面构成要素的界定,政治机会结构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以国家为中心视角观察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过程与特点。事实上,探讨一个国家制度化政治体制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影响,就是要关注一国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结构设计以及选举或政党制度的特点;分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或精英同盟的不稳定性、关心社会运动从精英中获得盟友的可能性、纳入国家镇压社会运动的能力和倾向这一分析维度,从本质上是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问题。为此,研究者需要围绕单个国家进行个案分析,或者收集多国案例开展比较研究。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现实中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可能并非完全由国家因素决定,因为“社会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不断变化的”[17]。
(三) “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鉴于不同国家中不同政治抗争事件的复杂性,对于某些政治抗争活动的分析,基于社会中心或国家中心视角的解释都可能存在适用性不足的问题。为此,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进行了探讨,并逐渐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视角。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与社会交会论认为:“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及发展过程既非完全由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亦非完全由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决定,而是由二者之间的交会情况决定的。”[10]184这实际上将问题的观察视角拓展至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例如,赵鼎新认为,社会异质性中层组织发育情况以及国家对它的态度,共同决定了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特点及走势,“伴随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不断向社会扩展权能,社会民众则通过政治抗争活动实现各自利益。针对抗争活动,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尽相同,这对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具有重要影响。”[18]除此之外,在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反应不是一成不变的。杰克·A.戈德斯通指出:“政府是选择压制社会抗争还是接受其影响,这只是非常广泛的选择中的两个,国家可以采取镇压社会运动并进行机构变革、镇压社会运动但不进行机构变革、容忍社会运动等多种应对方式。比如,如果国家觉察到一个社会运动或许多社会运动是个巨大威胁,或者认识到抗议运动方法的新颖性,国家可能就会发展新的强制机构对付他们。”[19]
“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实质上是对于以社会或者国家为中心观察政治现象的反思和调整,在肯定国家作为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具有其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力量在推进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基础上,其核心意旨是:国家首先是嵌入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国家(尤其是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在与社会组织(组织、宗族、群体、团体、部落)的互动和冲突中得到重新塑造,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现实中的国家(作为一个实体组织)并非是完全理想意义上的马克斯·韦伯眼中的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组织。这事实上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象。在现实中,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与社会之间界限模糊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二者之间并非具有明显而又确定的边界,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乔尔·S.米格达尔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一书中指出:“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可以使研究者注意到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和社会相互影响并且都在发生改变。”[20]24比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及国家能力相对较弱,地方官僚往往与地方强人(地主、酋长、村落领导、放贷者等)联合以维持统治秩序,地方强人则在此过程中强化了中间交易者的地位,最终形成国家领导者、地方官僚与地方强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交往中相互妥协的局面。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影响了国家特征,国家同时也强化了社会的碎片化。”[20]91-97
三、抗争政治研究视角转换的中国启示
在抗争政治理论演进及研究视角转换过程中,研究者事实上是围绕政治抗争这一主题,针对现实中发生的政治抗争事件,分别从三种不同视角进行观察,并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在不同研究视角的交锋过程中,人们对于政治抗争这一政治社会现象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不同研究视角本身的优势、劣势有了更加客观的评判,而不至于走向狭隘。“如同研究者批评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是对政治的‘社会化约’,国家中心视角可能存在对于国家权力和能力过于傲慢的高估等。”[21]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于经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会变得更加真实和理性。
因此,在合理区分中西方国家与社会不同之处的同时,上述理论演进及视角转换过程启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抗争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可以结合三种不同视角加以切入,并提出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解释。目前,既有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在上述三种不同视角下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在侧重于通过社会中心视角分析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过程与特点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首先,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认为,政治抗争活动的发生与中国革命传统相互关联,“中国工人、退休人员及民工等往往通过革命怀旧心理来发起抗议活动,国家的革命怀旧传统并不会随着其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经济体而褪色。”[22]陈峰在研究中也发现:“人们在抗议活动中展示的标语、口号通常表现出较强共产主义原则与色彩。”[23]蔡禾等人在考察利益受损民工的抗争活动时指出:“心理因素如相对剥夺感、怨恨等对于利益受损民工抗争行动的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4]其次,在抗争者的资源动员与行动策略层面,陈曦对“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这一抗争策略进行了研究,“在对待地方政权的态度中,抗争者努力实现忠诚与反抗的有机结合。为此,采用‘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的策略可以引起政府更多关注,避免抗议或请愿活动遭到公务人员的敷衍塞责、推诿扯皮(official stonewalling)。”[25]于建嵘在分析农民政治抗争活动时认为:“现阶段农民抗争活动呈现出‘以法抗争’的特点,这种抗争一般以地方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并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26]赵鼎新认为:“抗议者居住空间分布的集中,有利于培育社会运动中所需的个人关系网络。”[27]
在侧重采用国家中心视角,关注国家在政治抗争活动中的决定性影响方面,研究者也开展了学术观察。首先,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周雪光指出:“在单位制背景下,国家主导并塑造了不同个人之间相似的行为模式,并将个人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给集体行动提供机会的不是社会层面有意识的精心组织,而往往是国家及其政策转变;集体行动中的个人跨越了地域和单位的界限,虽然其个人利益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标指向却都是国家;基于无组织的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行动最终损害了国家的治理能力。”[28]蔡永顺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结构为政府应对政治抗争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政治体系中的多层次权力结构可以帮助政府减少处理抗议活动时的不确定性,因为上级机构可以授权较低层级权力机构有条件的自主性。当通过地方政权处理抗争事件时,中央政权既规避了指责,又有较多精力处理有限的少部分抗争事件,保持了社会稳定。”[29]
在侧重通过观察社会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过程来理解政治抗争现象的研究中,邓燕华等人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在遣散抗议者的过程中,往往依靠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资源,他们调查抗议者的社会关系,派遣工作组并联系抗议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做其思想工作,这有利于抑制抗议活动的规模,为双方协商和谈判提供契机。”[30]陈曦在对湖南、河南两个内陆省份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抗议者采用‘扰乱秩序和制造麻烦’的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互动,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回应以化解各种矛盾。最终,集体请愿与抗议活动不仅没有威胁到反而维系了政治体系的运行。”[25]
综合上述分析,由于不同政治抗争事件所涉及的时间、地域、群体与环境不同,我们对于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也需要具体地区分和甄别。三种不同研究视角的真正分野不在于内容,亦无孰优孰劣,而在于其能否使研究者在运用过程中形成自洽的解释逻辑。因此,影响研究视角选取的关键因素在于,该视角能否让我们更加逼近抗争事件的真相,能否契合抗争事件的情境,能否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四、结语
裴宜理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31]客观而论,对于抗争政治研究,我们一方面要采取长远的历史眼光,因为“历史是在人类事务的时间范围内看到的人类事务”[32]。另一方面,还应具有中西比较借鉴的宏观视角。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并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理论解释,而对于宏观视角与理论旨趣的探讨却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两方面的创新意义或价值:一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抗争政治理论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理论演进背后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转换过程,并在事实上提出了分析抗争政治问题的不同观察维度;另一方面,在批判反思中考察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政治抗争研究的启示,对于政治抗争活动的观察和研究不能陷入机械和僵硬的固定程式,而应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从上述不同视角谨慎地提出研究假设,在充分调研和掌握抗争活动的真实资料基础上进行验证,以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与结论,这也构成了抗争政治研究的客观要求。(感谢殷冬水教授、梁述清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32.
[2]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M].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
[3]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M].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5.
[4]PARK R, BURGESS E W.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1:865.
[5]GURR T R. Why men Rebel[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1-40.
[6]KORNHAUSER W. The politcs of Mass Society[M]. Glencoe:Free Press.1959:1-51.
[7]SNYDER D, TILLY C.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2,37(5):520-532.
[8]MCADAM D.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17-19.
[9]MCCARTHY J D, ZALD M 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J].1977,82(6):1212-1241.
[10]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ESINGER P K.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3,67(1):11-28.
[12]MCADAM D.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s,and Framing Process. Toward a synthetic,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M]. edited by MCADAM M Z.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20.
[13]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30-33.
[14]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78.
[15]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5):52-56.
[16]彼得·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找回国家[M].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7]BURSTEIN P, EINWOHNER R L, HOLLANDER J A. The success of Political Movements:A Bargaining Perspective[M]. i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rotest: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Jenkins and Klandermans.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275-295.
[1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9-50.
[19]杰克·A.戈德斯通.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M].章延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19-24.
[20]乔尔·S.米格达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M].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1]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1(2):217-242.
[22]PERRY E J.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Farewell to Revolution[J]. The China Journal.2007,57(1):1-22.
[23]CHEN F. Subsistence Crise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J]. The China Journal, 2000,44(3):41-63.
[24]蔡禾,李超海,马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09(1):139-161.
[25]DALI L Y, CHEN X. 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15,20(1):87-88.
[26]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8.
[27]ZHAO D. Ecologies of Social Movements: Student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8,103(6):1493-1529.
[28]ZHOU X.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3,58(1):54-73.
[29]CAI Y.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38(3):411-432.
[30]DENG Y, O’BRIENA K J.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J]. China Quarterly.2013,215(215):533-552.
[31]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J].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3):4-8.
[32]阿诺德·J.汤因比,G.R.厄本.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M].胡益民,单坤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
责任编辑刘荣军
网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4.005
收稿日期:2016-04-01
作者简介:王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2/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04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