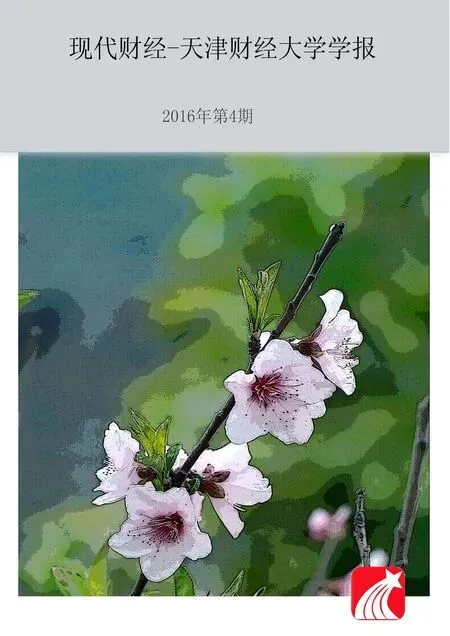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规制
——兼论软法规制与硬法规制的耦合
2016-02-20陈耿华
陈耿华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规制
——兼论软法规制与硬法规制的耦合
陈耿华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重庆401120)
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发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面临挑战与困境,而软法在治理此类行为中的独特作用却未获足够重视。事实上,以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规制效率高,凸显民主性和灵活性,也契合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特性,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行业自律规范可作为非正式的法源而被直接援引并作为发现、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及行为标准的渊源。此外,单一的硬法抑或软法规制皆无法独立完成治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任务,唯有软法和硬法相耦合的规制理路才能满足网络市场竞争秩序的治理需求。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硬法;软法;行业自律规范;商业道德
引言
软法的概念兴起于国际法的研究领域[1],尔后逐渐从国际法发展至国内法的研究领域。一般而言,软法对应于硬法而存在*“硬法”和“软法”两者是在特定语境下作为“对称”概念相伴随而存在。首先,从本质而言,软法乃行为规则,可用于构建秩序、规范秩序。其次,从形成主体看,软法的形成主体具有多元性,可能是国家机关,亦可以是行业自治组织,甚至是私人团体。复次,从载体渊源看,软法的载体渊源形式具有多样性,通常以成文性文件居多,比如纲要、宣言、章程、守则、标准、决议等等,也不排除不成文之渊源,譬如某些交易习惯。再次,从实施方式而言,相比于硬法,软法不具有国家法(硬法)的拘束力,故而其实施并不仰赖于国家强制力,体现着非国家强制性。软法的制裁重点立基于成员的身份,软法拘束力更多来源于一种“自愿”。赵军.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互联网时代竞争法的拓展[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70。。所谓硬法(也称为国家制定法),是正式的、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规范体系,而软法则是游离于国家法之外的,具有相当于(或类似于)法律的约束力之规范体系。*罗豪才教授则从公法角度研究软法现象。其认为:软法是一个概括性词语,被用于指称许多法现象,这些法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作为一种事实上存在的有效约束人们实际行动的行为规则,它们的实施未必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参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姜明安教授认为:软法是非典型意义上的法。(参见罗豪才.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9)宋功德教授认为:软法就是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程信和教授认为:软法是对应于硬法而言的。如果说,硬法是国家法,是正式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软法可概括为国家法之外的,具有相当于或类似于法律的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体系。参见程信和.硬法、软法和经济法[J].甘肃社会科学,2007(4):219-226。本文对软法的理解采取这种观点。虽然对软法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2],然而
即便至今,国内学者对于软法现象仍欠缺系统、综合的研究,对于软法的界定与理解依旧未形成统一的、明确的概念*有的认为应以是否具有国家外在强制力作为区分硬法和软法之根本标准;有的认为不论是软法还是硬法,首先其皆应当是法律规范,而软法则是那些界定不够清晰或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那么明确的法律规范;有的则秉持“软法只是具有法律效力,但并非真正的法律”这种观点。在经济法学界对软法和硬法的研究较少,中山大学程信和教授在《硬法、软法和经济法》一文中首次运用经济法的视角,对软法和硬法的现象进行了界分,并认为:经济法制既包括硬法机制,也包含软法机制。。虽然硬法和软法的划分方法是否合理科学仍有待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理论上如何界定软法并不影响软法本身的存在及其正当性,只是为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和理解软法现象提供选项。本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软法本身的探讨,而重在对它的工具性使用进行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这些不具有外在强制执行力、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但确能对互联网竞争主体及竞争行为产生有效约束力的“软法”。
面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频发且花样迭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虽不乏强制力和威慑力,然而其未能充分彰显应有的规制力度,其调整方法滞后,规制成本较高,过于滞后而回应性不足,而以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却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将公共治理领域的软法*卡多佐将软法这种具有生命的法称为“变动的法”、“动态的法”、“生长的法”、“用或然性逻辑验证的法”、“非国家创造和存在于国家之外的法”、“扎根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和扎根于公平正义信仰中的法”。参见 [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M].刘培峰,刘骁军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1-19。嵌入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法律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之举。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研究多从硬法层面进行探讨,鲜少关注以行业规范为代表的软法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影响,对如何构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治理模式、怎么实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硬法相耦合的实施机制的研究则尚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立足于硬法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面临的困境,探讨软法治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和合理性依据,并聚焦软法适用于此类行为的路径,进而明确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法和硬法相耦合的规制理路。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硬法规制之困
制定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为传统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量体裁衣”而来,其规制对象、调整方法、界定行为正当性的标准等等,无不是建立于传统市场之基础上。尽管作为传统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基本规制模式的硬法,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下,传统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的、单一的硬法规制模式依然显得过于滞后[3],反不正当竞争法未能充分回应时代提出的制度需求,其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回应性不足:欠缺民主性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极具交互性、隐蔽性、专业技术性,利益关系甚为复杂,纯粹依靠反不正当竞争法难以全面遏制。面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频发,要真正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民主价值的考量尤为必要。仅仅依靠有限的政府智力而未寻求公众的广泛参与及互动的平等协商,难以称得上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4]。由于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往往直接依靠国家公权力予以强制施行,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对社会的干预,国家公权与私权欠缺必要的互动,难以保证所制定的规则得以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5]。从某种程度来看,漠视社会团体自治的良性因素与渐进理性的正面效应,也是对社会民主价值的忽视。鉴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集虚拟性、全球性、智能性于一身,行为样态的复杂及多变(已然超出立法可归纳的范畴),导致规制此类行为所仰赖的监督体系也极为庞杂,如纯粹依靠硬法体系的规制显然极不现实。
(二)调整方法滞后:未考虑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特殊性
互联网作为现代通信技术高度发展之产物,互联网空间是经互联网互联而形成的虚拟空间,其从产生、运作到发展无不是依附于信息技术,从而导致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明显带有更多的技术特征[6]。如何借用法律、规则的形式来引导互联网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制互联网空间的行为,从而确保互联网空间的竞争模式适应市场竞争秩序的稳定发展之需求,始终难以得解。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并未考虑:互联网商业经营模式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与传统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区别。为了赶上这个无边界的、全球化技术之发展步伐,硬法的规制始终历经艰难[7]。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互联网生态圈的演变极快,这无不意味着任何具体的规则都容易显得过时。作为规制传统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之初难以考虑到互联网商业模式衍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难以预料互联网独特商业模式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殊属性,其调整方法滞后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三)规制成本较高
一般而言,硬法规制的模式是通过制定、实施法律的形式来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实际上,如此一套相应规范,从制定之初则需要耗费国家、社会巨大的立法资源,在实际的遵守及执行时,也存有不小负担。据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对11种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具体列举式规定,而新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则完全超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畴,给反不正当竞争法提出了全新的巨大难题。然而,面对形形色色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随时、快速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可能有损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频繁地修改法律所耗费的成本也将是法律所难以承受的。总而言之,样态各异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涌现的当下,硬法规制体系不堪重负,呈现较高的规制成本及较低的规制效率。
综上所述,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规制体系,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时,难以独立完成规制此类行为、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的任务,其调整方法落后,未能考虑互联网独特的技术特性,回应性不足,忽视对社会民主价值的考量,在规制成本及规制效率上也面临巨大的难题。作为实证法规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可避免存在的“双重不完整性”*这种“双重不完整性”一方面表现为实证法无法穷尽所有的生活事实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法规中的概念亦无从精确地界定其意义。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77。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入软法治理模式已是必然之举。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法规制的适应性分析
为何关注软法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作用,具体发挥哪一层面的软法来规制此类行为?这首先要追溯至软法的法律渊源。软法的法律渊源具有多样性*法律渊源在立法学中有特定含义,指的是法的效力来源,包括法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69。。具体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层面,软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家制定的互联网市场发展政策。第二,构建互联网市场的“代码”*“代码”一词源于美国著名网络法学者劳伦斯·莱斯格的著述《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代码既从物理上界定了网络市场的构架,又从价值取向上确定了网络市场竞争行为的模式;即确定了网络市场主体竞争行为中可以采取的手段,又包含限制网络市场竞争主体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技术手段。。第三,互联网市场的自律性规范。第四,互联网市场中的技术标准*作为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网络市场具有技术产品的一般特征。正如美国网络法学家理查德·斯皮内洛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法律和规范来控制技术一直是一个徒劳无益的举措,而用技术“校正”技术一直更为有效。因此,在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过程中,必须注重技术的力量,通过制定符合法律规范的技术标准,将作为网络市场竞争行为载体的技术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之内,使技术规范法制化。。司法实践中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规制依据主要是行业自律规范,故本文主要探讨软法中的行业自律规范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功能与角色。
行业自律规范,也称为行业规范、行业自律公约、行业自律公契,意指行业自律组织为谋求行业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捍卫该行业的持续性健康发展而制定的、对行业内部全体成员皆有普遍约束力之行为规范,其是行业自律规范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下文中的行业规范如无特别指明,都特指互联网行业规范。。
在互联网市场中,考虑到虚拟性、信息化、数字化等特征,故而带有技术特征的行业自律规范成为保障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发展、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手段。“信息时代无法容忍死板的规划,灵活上升为最高原则。”[8]相较而言,传统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体系无法将这些内容归入其中。因而,作为软法主要表现形式的行业自律规范,则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提供了全新的规制思路及路径。
1. 行业自律规范的软法规制模式凸显灵活性和民主性
首先,相较于立法者,行业内部从业人员通常掌握该行业前沿技术知识,也具有更高水平的实务专长。立基于此,其对于行业的发展掌握更为精确的数据,对行业变化而带来的问题反应更为灵敏、迅速。其制定的行业规范往往是相关从业人员为保障市场竞争秩序及行业的长远、整体发展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努力。其得以依据信息产业发展进程中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的新问题,快速对自律规范作出及时调整,从而避免了硬法规制的滞后及僵化,因而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其次,行业自律规范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习惯类似,也是特定群体或阶层内部成员所应共同、普遍遵守之行为模式,体现内部成员对社会组织生活的预期,并且其以平等协商、开放对话的方式推行,彰显了相互依存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但有利于弥补国家制定法固有的滞后性及僵化性,而且也是对人民首创精神的尊重及强化制定法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不少部门法在制定过程中已经采取了向习惯开放的积极姿态,如《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这也是对社会民主价值的尊重与回应,凸显了行业自律规范(软法)的民主性*事实上,软法较之硬法最大的优势是一定社会共同体成员对相应软法的形成或制定的广泛和直接参与。,也为其执行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9]。
2. 行业自律规范的软法规制模式契合互联网的商业特性
软法的运用适应互联网市场信息化的特点。互联网市场区别于传统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技术推动。从第一起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诞生至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样态在逐步升级,行为表现更趋高技术性,隐蔽性和复杂性。可以合理预测,未来还会出现更为棘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10]。互联网市场规制模式的构建要求其应当考虑互联网的商业特性,应当融入互联网特定商业模式的因子[11]。而行业自律规范作为一种技术行为规范,将其纳入规制依据,则是治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应对。退一步而言,鉴于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制定于互联网行业共同体,必然考虑互联网行业普遍遵从的行为标准,参考经营者所在行业相关领域的具体做法。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于某种意义而言乃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另一种具体表达。
3. 行业自律规范的软法规制模式规制成本相对较低
针对不一而足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虽然其行为样态各不相同,但丝毫不影响行业自律规范对其规制的效果。当行业自律规范的规制模式与立法规制模式的目标设置一致时,行业自律的模式得以通过较低成本的投入,快速修改不合时宜的自律规范从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新命题。
换言之,行业自律规范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所耗费的成本更低,也更为高效,表现为:首先,相对于独立的机构,自律组织机构在所在领域通常掌握更精专的实务专长及技术知识,因而在具体规制政策的制定上会有更多创新的空间,在解释标准时所耗费的信息成本也相对更低。其次,自律组织机构出于相同理由在监督及执行的成本上也会相对较少,基于互动而产生彼此信任的前提上,自律机构的行业者和管理者在打交道时所损耗的成本亦将得以降低[12]。最后,相对于公共规范制度,自律组织机构对其设置的程序及规则进行修改的成本也较低[13]。而这些,正是硬法所不能承受之轻,不但频繁地修改法律所耗费的成本将是法律所难以承受的,而且频繁地修改法律也是法律的稳定性所不容许的。考虑到互联网领域的监管与审判中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新颖,更应当为行业自律规范留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此外,以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规制模式也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法律多元理论*法律多元理论是西方法律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其最新发展趋势是不对国家法/非国家法作二元对立的分析,而是强调在具体场景中对二者复杂互动关系的具体观察。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经典的国家法/非国家研究中二元论的限制,将中国有关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关系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张钧.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法学评论,2010(4):3-7。表明,任一社会秩序的建构皆不可纯粹依赖单一的正式法律制度。面对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日新月异,粗线条的硬法立法模式显得滞后有余而回应不足,单一的一元治理模式备受挑战,而多元善治*“善治”通俗地讲就是“良好的治理”,它指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其本质特征表现为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9. 在和谐社会协同治理视阈环境下,多元治理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本文指的是社会自治团体等与公权力的多元合作管理。、共同治理的理念才能回应满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治理需求,通过多元管理的模式引入自治团体、行业协会、网站、网络运营商等主体,才能获得有效治理[14]。
总而言之,行业自律规范从制定之初就凸显其鲜明特色,不但制定方式灵活,而且强调对话与沟通,重视共识与认同,充分尊重团体的自我治理,推动社会的自我治理与自我规制。即使在实施过程中其结构也是开放的,规范可以进行反复的修改,并且在不违反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实现利益最大化[15]。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业自律规范不但呈现较低的规制成本及更高的规制效率,而且也凸显其灵活性和民主性,还较好融合了互联网特定商业模式的因子,而这些正是硬法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较为欠缺的,引入行业自律规范的软法规制模式,是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然要求。
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法规制的路径
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特殊性与互联网市场的虚拟性等特征,互联网市场的治理不可能简单地建构于硬法之上,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效规制不可能纯粹依赖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承认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在治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独特作用,发挥行业自律规范的规范效果,构建软法规范体系有助于实现从国家管理向公共治理的转型。那么,作为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行业规范具体包括哪些?如何实现行业规范的软法治理功效?
(一)作为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行业规范有哪些?
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主要是由中国互联网协会负责起草、发表以及组织实施,早在2011年工信部就发布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竞争秩序若干规定》主要从三个层面对互联网竞争行为作了规范: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得干扰他人软件运行;安全软件的评测行为要客观严谨。(也称之为“第20号令”),从性质上看该文件纳入行政规章范畴。此规定乃2009年“3Q大战”爆发以来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文件。而早在2002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就已颁布《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此外,还有2005年颁布的《中国互联网版权自律公约》、2011年公布的《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主要规定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禁止强制捆绑、禁止软件排斥和恶意拦截、反对不正当竞争、安全软件不得滥用其安全服务功能的有关内容。、2012年出台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以及2013年面世的《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等。
以下将着重介绍涉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两个主要文件。
第一,《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颁布于2013年12月3日,该《公约》共计6章27条目,规定了互联网行业成员应遵守的五大原则,分别是遵纪守法、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自主创新以及优化服务,从而捍卫用户的选择权、知情权以及其信息安全等,进而以此提供安全服务。此外,该《公约》还明确授予安全软件对互联网行业公认的木马、蠕虫、病毒等恶意程序享有直接处置权,从而有效保障互联网用户的安全利益。最后,该《公约》为保证非安全类终端服务企业享有平等发展权,明确禁止恶意拦截、恶意排斥、歧视性对待其他经营者的服务、产品的行为,相关软件的评测必须基于客观公正之基础上。
第二,是《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此《公约》颁布于2012年11月1日,共计4章22条目,以诚信、守法、公平、客观、中立为基本原则,倡导开放、协作、分享、平等作为互联网精神,要求企业坚决抵制相关违法行为及不良信息的传播,遵循国际惯常行业惯例及商业规则,遵守robots协议,遵循开放、公平、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理念,鼓励创新的同时也保障公平公正竞争秩序的建立,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共同抵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等。
(二)作为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行业规范如何适用?
1. 前提:非作为正式法源而被直接援引
行业自律规范作为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代表,是一种行为规则,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其实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也仅仅对行业内部成员具有约束力,故其在判决书中并非作为正式法源而被法官直接援引。换言之,行业自律规范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所体现的,并非作为法律规范性文件意义上的依据,法官审理此类行为时,作为最终裁判的依然是依据国家制定法。美国、英国等也采取类似举措,其在判决中也并不直接确认及适用这些行业自律规范17*其实这正是美英两国基于对自由政策传统和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审慎选择。。
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006年审理的阿里巴巴与三际无限关于雅虎助手一案*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二中民初字第16174号民事判决书。,法官就依据行业自律规范对恶意软件之定义,来认定涉诉行为是否具备恶意软件的构成要件,进而对行为进行最终定性。此间,行业自律规范是认定涉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认定依据,但其并非最终的裁判依据,并非作为正式法源而被直接援引,也并非作为规范性文件意义上之依据,法官在该案中最终还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4条予以判决。
2. 路径:作为发现及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及行为标准的渊源
法官审判互联网新型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无具体的条款得以援引,此时,该法第2条即发挥其作为一般条款的功能角色[16],成为此类案件不二的裁判依据。进言之,《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中核心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即成为法官认定涉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之评判标准与裁判准则。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更多的是通过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形式而体现出来[17],故而,公认的商业道德如何界定便成为判断涉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关键。然而,何为公认的商业道德始终是困扰法官的难题。鉴于商业道德这一表述比较空泛、边界模糊,并且难以包含任何带有权利义务性质的法律术语[18]。此外,商业道德所具体包含之要素也可能因地、因时而有所区别,甚至是对商业道德包含的不同要素的不同强调比重,也导致裁判结果的完全不一[19]。总而言之,商业道德不管从内涵,还是外延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为何行业自律规范可作为行业公认商业道德及行为标准的渊源?行业自律规范与行业公认商业道德是何种关系?这首先要追溯两者的源起。行业自律规范(行业惯例)产生于某个具体、特殊的商业共同体中,经由不断地反复实践,最终获得共同体内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共同的遵守,甚至成为人们世代相传、型构之行为准则。故而在明确具体的法律颁布之前,人们通常将行业惯例视为某一特定、具体的商业领域内所普遍依循的“法”。而道德也是在历经人们的反复长期实践而固化、成为人们行为的判断标准。其次,行业自律规范具有正当性和指引性。行业自律规范是其所在行业相关领域经常做法的具体体现,是行业共同体成员普遍、惯常的做法及公认标准之展现,通常也是建构于良善的标准之上,并且其从最初的提出草案,到获得行业内成员的广泛签署,以及到最终的生效,这些事实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该行业自律规范具有正当性,并为业内所公认。此外,行业自律规范反映行业竞争需求及竞争特点,与行业道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行业自律规范一般是由该领域掌握实务专长及高端技术知识的行业专家制定,具有更高的创新可能性,反映了行业的竞争特点及竞争需求,也是以成文规则的形式对该行业竞争现象进行的总结归纳,故而其可作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之标准。从以上这三个层面看,行业自律规范与行业商业道德的核心指向具有内在关联性。当人们在理解“公认的商业道德”时,换言之,在将“道德”这个较为宽泛的上位概念限缩为所谓的“公认的商业道德”之际,作为一般理性人则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与行业惯例相挂钩,即将“公认的商业道德”等同于合法的行业惯例[20]。“自律性规范,则被看作是一种最终的道德诉求。”[21]
那么如何发挥行业规范作为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及行为标准的渊源之作用呢?其实法官在审判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时早已得心应手运用行业规范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与否,如在3Q大战第二轮纠纷——360QQ保镖案中,广东高院则认为:“依照《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和《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禁止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恶意修改或者欺骗、误导、强迫用户修改其他服务者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参数,本案中扣扣保镖破坏了QQ软件及其服务的安全性、完整性,使原告丧失合法增值业务的交易机会及广告、游戏等收入,偏离了安全软件的技术目的和经营目的,主观上具有恶意,构成不正当竞争*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虽然此间没有直接厘清行业规范与行为正当性标准(即行业公认商业道德)的关系,但也表明了行业自律规范作为界定行为正当性的标尺之一,传达了行业自律规范对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所起的作用。而首次真正明晰行业自律规范在认定行业公认商业道德、行业惯常行为标准所起的作用,以及申明如何利用行业自律规范认知行业公认商业道德、行业惯常行为标准的路径则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上诉人提到,一审法院援用工信部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下文简称《若干规定》)及互联网协会的《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自律公约》)来认定涉诉行为是否侵害了诚实信用原则及公认的商业道德,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因是诉争行为发生在2010年10月底到11月初,而《若干规定》与《自律公约》则分别颁布施行于2011年与2012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答复:“在市场经营活动中,相关行业协会或者自律组织为规范特定领域的竞争行为和维护竞争秩序,有时会结合行业特点和竞争需求,在总结归纳其行业内竞争现象的基础上,以自律公约等形式制定行业内的从业规范,以约束行业内的企业行为或者为其提供行为指引。这些行业性规范常常反映和体现行业内的公认商业道德和行为标准,可以成为人民法院发现和认定行业惯常行为标准和公认商业道德的重要渊源之一。”当然,对于这些行业规范的适用,是在审查判断的基础上予以参考,而并非当然地接受或断然地不予采纳。一方面,行业自律规范的适用应当置于法律的审视之下,不可与法律的目的相冲突。另一方面,法官须得对所适用的行业自律规范进行识别、认定与审查,并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予以合理、充分的论证[22]。即言之,行业自律规范得以作为认定行业惯常行为标准及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渊源,其本身必须是客观、公正及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原则及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企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其创新程度高,商业模式更新尤为迅速,相关的行业自律规范也在不断地形成与发展,甚至在某些时候,具有阶段性的特征,故而在将其作为判断行业行为标准及公认的商业道德时,也应当根据互联网行业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现阶段发展的特点,甚至是发展的阶段,考虑其是否有利于构建平等公平的竞争秩序,是否符合消费者的一般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以此加以适用[23]。
总之,“行业性规范常常反映和体现了行业内的公认商业道德和行为标准,可以成为法院发现和认定行业惯常行为标准和公认商业道德的重要渊源之一。”法官对于行业自律规范不可无条件地断然接受,首先,这些行业规范性文件不得违反法律原则及规则,也必须是客观公正的。即言之,法官应当在判断行业规范相关内容是否合法、客观及公正的基础上,参考行业自律规范,将其作为界定互联网行业惯常的行为标准及公认商业道德之参考依据。
四、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法规制局限性的克服:软法和硬法相耦合的规制理路
应当注意的是,重视发挥以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舍弃硬法的规范作用。一方面,软法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不可避免带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作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中的软法不可避免带有散乱性的特点,过度地拓展与利用软法资源都可能引发法律的泛化。又如,软法虽以民主商谈、多元参与及沟通协作做为追求,然而实践中各社会主体在商谈能力上皆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何得以确保各方主体的意见真正纳入软法规范的制定,并且立基于此实现经济法主体的利益,皆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本规制依据,硬法规制(主要指《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捍卫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进程中依然功不可没。硬法始终是社会运行中最基本的原则,应当始终坚持硬法的框架性和基础性功能[24]。正如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所言:“法律是人性中所蕴含的最高理性。”在构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体系过程中,也应当全面发挥硬法在该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首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属性决定应以硬法作为规制基础。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其源头看是一种侵权行为,对其规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脱胎于侵权行为法。即便历经两个世纪的演变,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然成为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但该法保障经营者合法利益的本质未有改变,捍卫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立法目标也未有改变。在互联网市场跌宕下,虽然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模式备受挑战,但并未改变硬法作为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之基础的形态。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仍然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其规制也应当以硬法(即《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基础,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合理配置市场参与者的权利、义务,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市场秩序井然。
其次,硬法乃国家干预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手段。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频繁涌现,乃市场机制失灵之重要体现。为平衡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的干预及调整不可或缺,而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与其他治理手段方式相比,更直接体现国家意志。也正因为此,带有明显国家干预性质的硬法更容易迅速实现国家干预之目的。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实践看,以硬法为重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相关立法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核心法律依据。鉴于此,这些作为硬法的立法文件也应发挥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作用,成为该类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
再次,硬法配置权利义务的模式是捍卫经营者利益及公平竞争秩序的有力保障。从微观层面看,规制侵权行为采取一种衡平配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路径,并以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作为基础。这种侵权责任的承担,务必有强制性规范对其进行确认,也需有强制性规范来清楚界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硬法作为国家制定法葆有评价、指引、预测、教育及强制等功能,得以在最大限度范围内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诞生,从而保障市场经营者的合法利益,捍卫公平竞争秩序。
由此得知,软法治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固有的缺陷需要发挥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代表的硬法的基本规制作用,硬法规制为软法规制功能之发挥提供特定环境,离开该环境也难以保障软法机制功效的实现[25]。任一社会秩序之建构既需要软法,也需要硬法。尽管软法与硬法之间可能存有某些冲突,然而两者将走向交叉、结合、转化甚至是某种程度之混同[26]。一方面,硬法对软法具有指引、肯定及支持的功能,而另一方面,软法对硬法则起着先导、指引、支持及补充的功能[27]。可见,硬法和软法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硬法之长往往乃软法之短,而软法之长通常也是硬法之短,二者耦合并用、相辅相成,通过功能上的互补,软法与硬法共生形成的制度设计已然演变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制度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28]。因此,在法律体系中两者应取长补短,而在法律实践中这两者缺一不可,并行不悖[29]。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软法和硬法正是存有这样的耦合*所谓耦合,最初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经由徐孟洲教授引入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来,意指经济法现象中的不同对象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并且相互影响之关系。关系,应确保硬法与软法的刚柔相济,尽量避免以强凌弱或者是以柔克刚,从而做到各展其长、扬长避短,各得其所、软硬兼施。可见,在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过程中,必须回应互联网市场发展之实际需求,全面发挥硬法与软法各自之特长,依照法律调整的“边际效益原理”,按照所处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可能面临的各异问题,清楚界分硬法与软法的调整对象[30],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硬法规制体系是确保国家有效干预、彰显国家对秩序作出有效规制之必要选择。此外,还应当充分认识、尊重互联网及信息经济发展的外在客观规律,充分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硬法规制作用,还应当重视行业协会的功用,发挥行业自律规范的作用,这就是说,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硬法实施初次控制的前提下由软法开展二次控制[31],从而构筑起一个富有实效、功能齐全、结构匀称、体系完整的法律规制体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软法的品质也需要不断提升,才能据此型构软硬并重的混合法控制模式[32]。
总而言之,“在多元化的制度选择主体中,国家(政府)的选择则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当然,国家(政府)在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并不否认和排除其他主体在制度选择中的作用和地位。”[33]构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体系,一方面应发挥硬法的基础性作用,而另一方面亦不可忽视软法对于此类行为独特的治理作用。一言蔽之,互联网市场的虚拟性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殊性,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治理不可能纯粹地寄希望于硬法之上,还应当着重实现软法特殊的规制理路,只有刚柔相济、软硬兼具,以此构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软法与硬法规制相耦合的规制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法的干预及规范功能,从而推动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朝着规范化目标发展。

[1]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456.
[2]吕中国,强昌文.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8-136.
[3]黄茂钦.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软法之治——以“治理”维度为研究视角[J].现代法学,2015(6):75-85.
[4]姜明安.软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J].求是学刊,2014(5):79-89.
[5][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张志铭译.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80.
[6]叶明,陈耿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关系认定的困境与进路[J].西南政法大学大学学报,2015(1):80-86.
[7][美]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M].李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满达人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45.
[9]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
[10]王艳芳.《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适用[J].法律适用,2014(7):2-7.
[11]朱理.互联网领域竞争行为的法律边界:挑战与司法回应[J].竞争政策研究,2015(1):11-19.
[12][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33-134.
[13][英]戴恩·罗兰德,伊丽莎白·麦克唐纳.宋连斌,林一飞,吕国民译.信息技术法(第2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309.
[14]罗豪才.公共治理的崛起呼唤软法之治[J].政府法制,2009(7):12-13.
[15]蒋坡.国际信息政策法律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43.
[16]郑友德,范长军.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具体化研究[J].法商研究,2005(5):124-134.
[17]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创新性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57.
[18]吴太轩,史欣媛.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中商业道德的认定规则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1):22-30.
[19]蒋舸.关于竞争行为正当性评判泛道德化之反思[J].现代法学,2013(6):85-95.
[20]李生龙.互联网领域公认商业道德研究[J].法律适用,2015(9):57-61.
[21]赵军.网络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互联网时代竞争法的拓展[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83.
[22]范长军.行业惯例与不正当竞争[J].法学家,2015(5):84-94.
[23][德]弗诺克·亨宁·博德维希.黄武双,刘维,陈雅秋译.全球反不正当竞争法指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50.
[24][美]戴维J·格伯尔.冯克利,魏志梅译.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8-39.
[25]罗豪才,周强.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J].中国法学,2013(5):102-111.
[26]朱文龙.软法视角下中国与欧盟社会治理比较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3:24.
[27]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5-36.
[28]徐靖.软法的道德维度——兼论道德软法化[J].法律科学,2011(1):31-41.
[29]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J].中国法学,2006(2): 3-24.
[30]Goldsmith J, Wu T.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1]翟小波.“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J].法律科学,2007(2):3-10.
[32]罗豪才,苗志江.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J].法学杂志,2011(12):1-4.
[33]彭海斌.公平竞争制度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6:261.Soft Law Regulation of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s——Also on the Coupling of Soft Law Regulation and Hard Law Regulation
责任编辑廖筠
CHEN Geng-hua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the hard law which refers to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s faced up with challenges in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que role of soft law in the management of such behaviors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In fact, the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norm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ft law regulation with high efficiency are quite democratic and flexible. They also f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business model and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 governance.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s,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norms, being informal sources, can be used as the origin of discovering and identifying business ethics, which are wide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conduct. Finally, hard law or soft law cannot independently regulate the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s. Only with the coupling of the two can we really regulate the competition order in the network market.
the Internet; unfair competition; hard law; soft law;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norms; business ethics
2016-01-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FX125);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XZYJS2015018)。
陈耿华,女,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竞争法研究。
D92
A
1005-1007(2016)04-0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