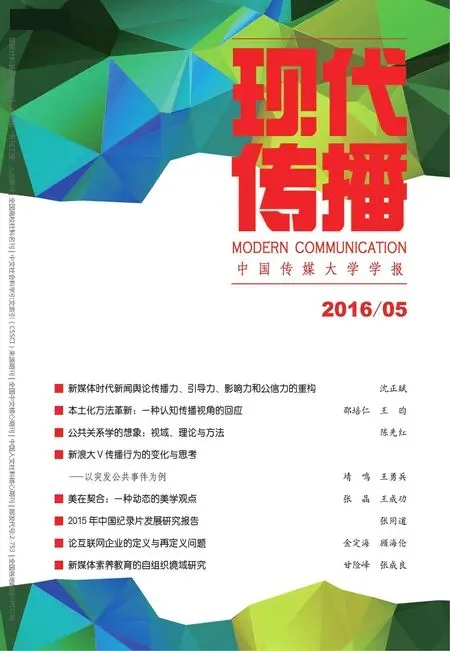现实的抽象与人类的仪式
——亚恩·阿蒂斯·贝特朗的纪录片《人类》解析
2016-02-19■周文周兰
■ 周 文 周 兰
现实的抽象与人类的仪式
——亚恩·阿蒂斯·贝特朗的纪录片《人类》解析
■ 周文周兰
【内容摘要】《人类》是2015年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纪录片作品,以采访和航拍构成全片,探讨了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时,以富有创意的简化形式让影片充满了独特的魅力。通过把惯常的采访提纯到抽象的高度,使影片成为了倾诉与聆听的人类仪式,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世界纪录片对抽象追求的历史为前景,重点探讨了《人类》对现实的抽象和仪式化。
【关键词】《人类》;纪录片;仪式化;抽象
2015年,当今世界最顶级的高空航拍摄影师、法国导演亚恩·阿蒂斯·贝特朗推出了最新作品《人类》(《Human》),一经公映便引发震撼,为世界纪录片历史增添了又一部杰作。犹如片名《人类》所蕴涵的宏大主题一样,该片通过全球几十个国家许许多多普通人向世界讲述自己的经历、感受、爱与恨、痛苦与欢乐等,揭示了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在形式表达上极富创意,导演以极致的简化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抽象,将该片演绎成一场倾诉与聆听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人类仪式,既产生了直刺人心的效果,又创造了高耸云霄的磅礴气势。
一、纪录片与抽象
当导演贝特朗雄心勃勃地要展示宏大的“人类”时,影片的抽象性质便已确定。
抽象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古今中外无数艺术家都曾孜孜不倦地探索,把抽象视作自己艺术达到一定境界的标准。但是,人们大都会认为,拒绝虚构、以客观纪录现实生活为宗旨的纪录片,似乎从根本上就与抽象绝缘。世界上占据主体地位的纪实风格纪录片,以直接电影为代表,追求最大限度的真实和客观性,要求零度情感,摄影机像墙上的苍蝇一样作旁观纪录。对镜头纪录下的现实生活,要求时间和空间的完整性、要求完整的过程、要求原汁原味的全部的场信息。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的确与抽象相去甚远。因为,抽象艺术恰好需要对自然对象加以简约、提炼或重新组合;需要消减对象中次要与偶然的因素,只保留最本质部分,甚至完全舍弃自然对象,只创造纯粹的形式。
不过,这只是我们通常的看法,对真正有创造力的导演来说,直接电影严苛的跟拍手法、甚至流水账似的纪录只能是束缚艺术激情和想象的桎梏。事实上,在世界纪录片刚刚成熟的20世纪20年代,它就有两个重要分支:一是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的人类学式的客观纪实;二是伊文思、维尔托夫等人的先锋纪录片“大都市交响乐”。后者追求的正是对现实的抽象和超越。
20世纪20年代,受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领域盛行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出现了一次实验电影运动。1927年至1930年,该运动进入第三阶段,许多先锋派电影人士转拍纪录片并形成纪录电影流派,被称为“第三先锋派”。“第三先锋派”使先锋派电影往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确立了先锋电影的纪录片方向。
当时的许多先锋纪录片被称为“大都市交响乐”,著名作品有:《柏林:一个大都市的交响乐》(沃尔特·鲁特曼)、《持摄影机的人》(吉加·维尔托夫)、《雨》(尤里斯·伊文思)、《尼斯的景象》(让·维果)、《布鲁克斯的早晨》(简·莱达)、《里斯本传闻逸事编年史》(莱托·德·巴罗斯)等。
先锋纪录片放弃了机械、被动地记录生活,强调创造性地记录现实,其特点是: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追求与生活的疏离和陌生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竭力追求形式感,强调形式即内容,甚至形式大于内容。其目的是:通过生活的陌生化、艺术形式感的创造,将镜头画面的角度、视觉冲击力、运动感、节奏等推向极致,从而创造一个富于联想的、诗意的、象征的、充满幻觉的现实世界。即,镜头虽然全部来自真实拍摄,但创造的却是一个抽象的全新的世界。伊文思的《雨》、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鲁特曼的《柏林:一个大都市的交响乐》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伊文斯的影片《雨》和《桥》分别记录了阿姆斯特丹的一场雨和鹿特丹的一座桥。但是,由于陌生化的追求,现实中真实的雨和桥已经被抽象。
巴拉兹在《电影美学》里曾对此有过精彩的阐述,他指出,伊文斯已不想再给观众表现什么客观现实,《雨》和《桥》所表现的事物原貌,是现实中根本看不到的,观众在伊文斯影片里所看到的雨并不是在某地某时所下的某一场雨。片中的镜头画面并非是通过某一时间和空间概念而联结起来的,伊文思要表现的是下雨时的种种现实,而不是下雨这件事本身。同样,巴拉兹认为,当伊文斯在表现一座桥时,即使他告诉了人们这是鹿特丹的一座铁路桥梁,但他还是把这座巨大的钢铁建筑化成了千百幅从各个角度拍摄的抽象画面,这时,桥的真实感已丧失殆尽,很难叫人相信它上面能走货车。
就是说,在《雨》《桥》《持摄影机的人》等先锋纪录片中,镜头画面只是一系列形象,而不是具体事物的再现。这就像著名电影美学家伊芙特·皮洛在《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评价塔尔科夫斯基影片所说的那样,镜头画面没有像常规事件那样充分展现,但是它们非时间性的存在比它们的展现过程更重要,其目的是抽象,是追求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性。
从上面可以看出,世界纪录片从来就有摆脱平淡无味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其目的是通过世俗与神话的结合,在纪录的世俗物质性里融入神话的抽象和超越性。康德也说过,没有抽象,视觉是盲目的。这对从芜杂的现实世界取材的纪录片尤其重要。
所以,尽管《人类》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纪录片抽象的追求上,它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不过,它的形式感与仪式性更加直接、强烈。
二、形式:现实的提纯与抽象
克莱沃·贝尔指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纪录片《人类》最具创意的就是它的艺术形式,它经典地展示了艺术纯粹形式的力量,具有鲜明的探索性质。
按照现代艺术最经典的理论家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里的论断,抽象艺术最重要的原则是简化。在《人类》里,贝特朗就以对现实充分简化、提纯和抽象为理念,通过简单却极具意味的形式处理,创造了慑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使之摆脱了我们心目中现实类纪录片总是沾着泥土、略显粗糙的偏见,上升为一部精致、干净、带有形而上气质的艺术作品。
除了航拍画面,《人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采访。采访是电视节目、纪录片常用的手段,一点不新鲜,但《人类》却将常见的采访推向了极致,从而使平凡的人物抽象为整个人类的形象。具体方式有以下几方面。
1.对着镜头说话
所有影视作品都有一定的情境,人物在这情境里活动。当人物直接对着镜头说话时,他便从所处的特定情境里脱离出来。在常规影视作品里,只有极少数富有开拓性的导演会让剧中人物在某些特定时刻直接对镜头说话,否则会被认为是穿帮。这少许的对镜头说话、对固有情境的脱离,其实就是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与陌生化手法之一。
同样,影视作品里,除了个别特殊片段,被采访对象一般也不会直接对镜头说话,而是有采访者在旁边提问。不管这个人是出现在画面里,还是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被放置在镜头之外,观众都能感受到被采访者是与一个提问者在交流。这其实也是一种情境。
《人类》的所有采访对象都对着镜头说话,这构成了该片基本的叙事策略,也成为它贯穿始终的风格,在影视史上绝无仅有。这种方式有多方面意义:其一,通过突破人物规定情境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空间,它可以是观者观看的任何时间与空间,是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其二,采访对象对着无人的镜头,犹如面对真实的自己,倾诉就变成了内心独白,是真情流露,增强了亲和性与感染力;其三,这时的镜头,是采访者、是观众、是被采访者,也是看不见的整个世界,是多角色的合一;其四,其目的是直接与观众对话,在直接的对话交流中,引起关注,引发思考。
而本质上,当人物以间离的方式脱离他的具体情境时,他就已经抽象化了。
2.黑色背景
进一步,导演将所有人物的现实信息都遮蔽,统一配置为黑色背景。
法国摄影家JeanloupSieff曾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色彩太多的世界里,彩色只是细节,会让人注意照片里太多的小故事。黑白摄影是一种过滤,能突出精髓,让人一眼进入你的氛围、你的主题。”
《人类》不是黑白影片,但黑色背景在过滤芜杂背景方面所起的作用与黑白摄影的效果一样,而且更彻底。在这里,人物的现实性再次被抽离,只剩下一个个单纯的人。导演如此设计,显然是故意弱化人物的国家、民族、宗教信仰、生存环境等外在属性,目的只想凸显作为单个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在导演看来,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地球,其余都无关紧要。而地球太恢宏,恢宏得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深厚的黑色可以满足关于这个概念的无穷想象。
所以,统一的黑色背景是这些人物抽象化、符号化的重要手段,如此,他们才能更好地担当人类的代表。
此外,黑色背景构成了近乎低调摄影,它加强了严肃、凝重的氛围,突出了影片主题。
3.证件式标准照
接下来,《人类》导演对所有采访人物的拍摄采用了证件标准照形式,这使得拍摄本身成了一个象征行为。
近年来,大学毕业照、婚纱摄影越来越趋向多样化,各种好玩、搞怪的拍摄纷纷出现,很多已经是行为艺术,体现了人们思想的开放与活跃。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如何丰富多样,证件式标准照却始终不可替代。毕业也好,结婚也罢,以及其它等等,最隆重的永远是那张表情稍显严肃的正式标准照。
有一部韩国经典电影《八月照相馆》,主人公开了一家照相馆。有一天来了一家人拍全家福,拍完后,儿子让老母亲单独再拍一张标准照,母亲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拍了。到晚上,老母亲独自一人又来了,穿戴与打扮十分细致,希望主人公重新帮她拍一下。主人公非常认真地拍了,他知道,老太太是在精心为自己拍遗像,其儿子白天也是这个意思。后来,身患绝症的主人公也为自己拍了一张。
我国纪录片《老头》中,也有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照相细节。那些老头都已退休,每天就晒晒太阳、打打牌、下下棋,过着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后来因为办一个证件,所有人需要拍标准照,结果大家非常开心,非常重视,对拍出来的形象也非常在意。
证件式标准照往往是社会成员、公民身份的证明,是很多重要场合的必需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因为拍摄有严格要求,所以拍摄对象也都会郑重对待。纪录片《人类》对人物采取证件标准照形式拍摄,无疑是赋予了人物一种庄严的形式,仿佛是在拍摄地球家园的身份证,为人类建立影像档案。
4.脸孔特写
身份证等证件照上的人物基本接近特写景别,但是由于整体才一寸或两寸大小,其特写的效果几乎显示不出来。但在影视作品里,不管是大银幕还是电视或电脑,任何一张脸的特写都很引人瞩目。
当《人类》把所有人物都拍成特写甚至大特写以后,加上黑色背景、横幅画面的宽度延伸,在那一张张或凝重忧伤或喜悦快乐的脸孔扑面而来时,其视觉冲击力十分强烈。
脸孔与指纹应该是人类识别度最高的部位,所以科学家一直致力于开发以它们为标准的安全识别系统。但指纹太精细太复杂,如同难解的密码,只能依靠机器。脸孔才是一个人的真正标志,因为它包含了喜怒哀乐、人世沧桑,它有情感有思想,既是直观的外在的物质的,又是心灵的隐秘的精神的,它携带着一个人的全部信息。所以,扎克伯格把创建的全球最大社交网络平台取名为“脸书”(Facebook),真是再恰当不过。
所以,导演贝特朗拍摄《人类》,收集人的脸孔特写已经足够。这让人想起吴哥窟著名的四面佛像。古今中外无以计数的佛像雕塑与绘画几乎都是全身像,而吴哥窟只雕刻了佛的脸孔,只做佛脸孔的特写,并无限放大于天地之间,使之具备崇高的形式感,从而演变成了震古烁今的宇宙形象。
《人类》中特写的意义与之相同。当一个完整的人被简化为一张脸孔的特写,当黑色背景彻底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信息,当人物直接对镜头说话,在这多重的抽离与简化后,脸孔虽然依旧生动,但早已经高度抽象化。而只有这样,这一张张脸孔才能担负起“人类”这一宏大叙事。
三、一场仪式
导演亚恩·阿蒂斯·贝特朗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纪录片《人类》做成了一场仪式,把人们司空见惯的采访抽象到了仪式的高度,再与航拍镜头先天的宏伟仪式感巧妙剪辑,仅此,即可彪炳纪录片史册。
对于仪式的感知和体悟,贝特朗胜过许多人。他一生执着于高空航拍,总是高高远远地俯瞰地球,用上帝的视角加上法国人天生的浪漫情怀,逍遥巡礼人间,那本就是一种超然的仪式。他从中获得的最大馈赠应该是:辽阔的视野,浩然的气魄,精神可以一直在天空飞翔,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主要是美丽、整齐、简洁,即使目睹杂乱、污浊、苦难的现实,也始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超越。这一切,也必然导致他的唯美气质和抽象情结,而这正是仪式所必需的。
1.采访——倾诉与聆听的仪式
当贝特朗决定发起全球几十个国家数千人的采访这个宏伟创意时,关于纪录片《人类》的仪式便开始了。尽管这是面对面的近距离拍摄,与居高临下的空中航拍完全不同,但作为这场庞大行动的主持人,贝特朗本能地从仪式中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出于内心审美情结的需要和感召,即使现实苦难深重、千疮百孔,他也要像在高空一样,将目光所及之处,尽皆抽象化、仪式化。
《人类》的仪式性不仅在于采访遍及全球的浩荡规模,更是导演追求作品形而上高度的结果。该片最重要的仪式是倾诉,以及画外观众的聆听。为此,贝特朗与团队营造了一个简洁却强大的仪式场:搭建全球性的舞台,让人们对全世界说话;用一块统一的黑色布景,去掉了时间和空间,取消了这些人现实中的千差万别,使他们抽象为人类的符号;再以标准证件照的形式,用一个个脸孔特写,在庄重的形式感中,赋予他们作为人类的象征。
仪式情境的设计很成功,仪式的主体——采访对象被其强大的氛围所感染,便以最隆重的态度全情投入。仅仅从他们脸孔特写就可以看到,即便最穷困最卑微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面容、头饰打理得干干净净,绝对盛装出场。哪怕不理解《人类》导演的高远理想,但知道这是向全世界说话,所以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了各自的尊严。只需看看那一张张脸孔,不管开心喜悦还是忧郁沉重,都能给人深刻的印象。
《人类》中的人物脸孔使人想起我国著名油画《父亲》。20世纪80年代初,画家罗中立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作品《父亲》,不仅震惊画坛,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该作品借鉴西方现代绘画超级写实主义理念,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民形象。画作虽然极为写实,但整体构图是人物脸部大特写,衬托黄土背景,加之使用伟人画像的大尺幅,因此,这个农民形象极具象征意味,具象化为抽象,成为“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是一座仪式般的纪念碑。
仪式的目的是信仰、文化、价值的共享,是表演者与观看者的心灵交流。纪录片《人类》以仪式的方式,在倾诉和聆听之间,为世界和人类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这场仪式,参加者们感受到了深深的洗礼。影片最后,当着全世界的面,一位受访的中年白人妇女由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你今天为我带来了很多东西,让我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有才可用,我的故事是受欢迎的,你让我感到开心,你让我感到我是有贡献的,对此我非常的感激。”一位满脸沧桑的老黑人说:“非常欢迎你们来我家,来我家吧,我邀请你们所有人。”一位老妇说:“我们听说过人们怎样拍电影,但是现在,每个人都会看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部落,我非常开心。”
而创作团队也用字幕表达了对所有采访对象的谢意:“这部电影奉献给成千上万的人们!那些用诚实、勇敢、善良来回答我们问题的人!”
2.航拍——崇高的仪式
对观众而言,航拍则为该片创造了人类的崇高仪式。
当片中精美的航拍镜头徐徐展开,再辅以天籁般的音乐,观众就像导演贝特朗一样,自由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以上帝的目光俯视巡游地球,那种仪式的超越性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航拍的大远景与采访的脸孔特写交叉剪辑,两极景别造成的强烈冲击力,不仅是视觉的,更是心理与精神的,那就是仪式的崇高感。
作为重要的美学概念,崇高是指审美对象因其峻拔、伟岸的感性形象,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宏阔的气势,使审美主体受到震撼、敬畏,继而为之感召、鼓舞、激越,克服恐惧与痛苦,产生一种超越审美对象的思想与情感,精神境界获得巨大升华,是辉煌壮丽之美。崇高的审美对象,一方面是高山、大海、日月星辰等大自然,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前者主要体现为大自然的宏伟、壮美,后者则表现为人类在追求光明、真理、正义、真善美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九死尤未悔的精神。
皮洛在《世俗神话》中也认为,电影将大自然古朴化、借景抒情也是使日常生活、自然现实仪式化和蒙上神话色彩的重要表现,在大自然的宁静、祥和中,犹如众神的和解、天地人合一,仿佛回归失落的天堂。
在《人类》里,当特写的微观剪辑到航拍的宏观,一张张已经简化与抽象化处理的脸孔泛化成壮阔的高原、广袤的沙漠、汹涌的大海、飞翔的鸟群、奔驰的骏马,或者排山倒海般的人浪、威武的仪仗队、数百人参与的激情昂扬的搭人梯活动等等,这就使一个个具体的人扩大到整个人类,并在大自然的壮丽与人类集体的奋发中,产生出一种跨越天地的恢宏的崇高仪式。
《人类》与纪录片历史上不满足于纯粹现实纪录的其他作品一样,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影响深远。它不仅开拓了纪录片的表现内容,更因其自觉的独特的形式追求,通过把司空见惯的日常现实抽象化、仪式化,使平凡的世界因之而诗意盎然、焕然一新,同时,还使作品具有隽永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些东西正是我国纪录片最欠缺的地方,非常值得学习和进一步研究。
(作者周文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周兰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