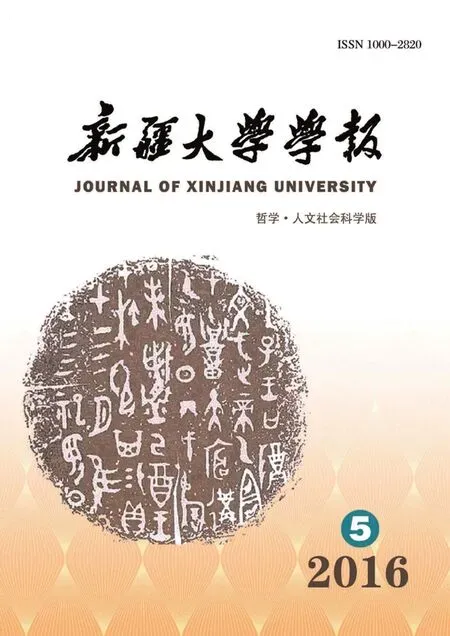以情纬物,藉思成理:论陆云赋的艺术*
2016-02-19邓成林刘运好
邓成林,刘运好
(1.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2.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陆云赋虽数量不多,却个性鲜明。陆云赋题材不及陆机之丰富,但二人都因袭辞赋传统的铺采摛文、写物图貌的手法,并兼有魏晋辞赋情理兼备的艺术特点。如果说,陆机以情境胜,以文辞胜,以诗笔写赋,其格调偏于沉郁[1]673-674;那么,陆云则以理境胜,以结构胜,诗赋界限判然,其格调偏于上扬。以情纬物、藉思成理的圆融统一,创造了具有审美价值的独特理境,是陆云赋最具创新意义的艺术特色。
然而,关于陆云赋的研究,除了文学史专著有所涉及外,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列有“陆云的辞赋”专论,彭鸿程《试论陆云的文学创作》一文论及其辞赋,指出“陆云的赋作浸染着浓郁的悲情和深沉的生命意识。这种用情的创作倾向,正是陆云对自己‘先情后辞’(《与兄平原书》)文学主张的实践”[2],其侧重于情感内容分析,对陆云赋的艺术未作分析。故笔者从表达体式、理境构成、艺术结构三方面分别论述陆云赋审美艺术的特点。
一
陆云赋以抒情说理为主体,“以抒发生命之悲、迁逝之感和隐逸之思为主要内容”[3]370,其中又隐含着难以言说的覆国亡家之痛。然而无论其体物、述行,还是直接抒情说理,皆以物象为载体。从整体上说,陆云赋的艺术表达体式,表现了汉魏状物赋以“铺采摛文”“写物图貌”为手段,以追求“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的审美效果。但是,陆云赋的物象描摹也有自己的艺术特点。无论是平面静态的抑或立体动态的描写,还是大处落笔抑或细处渲染,皆有层叠铺排,却绝少繁缛,用笔清省,又简约有致。
陆云写景状物也有大量平面的静态的描写,从细处渲染,以达到“蔚似雕画”的审美效果。如《逸民赋》:“曾丘翳莽,穹谷重深。丛木振颖,葛藟垂阴。潜鱼泳沚,嘤鸟来吟。仍疏圃于芝薄兮,即兰堂于芳林。靡炎飙以赴节兮,挥天籁而兴音。假乐器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挹迥源于别沼兮,飡秋菊于高岑。蒙玉泉以濯发兮,临浚谷而投簪。”前六句描写隐士所居环境之美,以深山丘谷,草木郁深,状林壑之美;以丛木茂盛,藤荫浓密,状草木之盛;鱼在溪水或游或息,鸟栖山林亦鸣亦吟,状鱼鸟之欢。再四句以就灵芝丛中而艺蔬,即芳蔼之林以筑室,既无狂风炽烈之起,惟有天籁之音而兴,以展现其居处之清幽。后六句以隐士鸣琴音,挹清源,餐秋菊,濯发玉泉,临谷投簪,以叙述式写景,凸显其生活之逍遥,秉性之高洁。虽是采用线型结构,作平面的层层铺排,然又选词精练,写出景物特点,如以“翳莽”写山丘,“重深”状穹谷,“振颖”摹丛木,以及丘之曾,谷之穹,鱼之潜,鸟之嘤等,都能达到“蔚似雕画”的艺术效果。而其叙述式写景,则又从细处反复渲染,在写人中,也凸显了景物的清幽高洁。有铺排而不见铺排,特别是将人物描写融入山林美景之中,用笔清省,简约而有情致。此外,“翼翼黍稷,油油稻粱”(《喜霁赋》),“伫眄瑶轩,满目绮寮。中原方华,绿叶振翘”(《登台赋》)等,亦属于此类。这种表达体式与陆机赋的写景状物比较接近,然而陆云辞赋这种平面的静态的描写,往往穿插在立体动态的描述之中,形成文章起伏有致的描述节奏。
既善于从大处落笔,写出气势,又善于从细处渲染,写出神采,则是陆云赋突出的特点。如《愁霖赋》:“于是天地发挥,阴阳交烈。万物混而同波兮,玄黄浩其无质。”先从大处落笔,铺陈天地、阴阳、万物、玄黄之状,夸饰其雨狂雷激,波涌汗漫,水天相连,写物之势,骇骨惊心。然后从细处渲染,“雷凭虚以振庭兮,电凌牖而辉室。溜鼎沸以骏奔兮,潦风驱而竞疾”。以凭虚振庭,凌牖辉室,鼎沸骏奔,风驱竞疾,渲染雷声之烈,电光之明,檐溜之涌,潦流之疾,写物之貌,昭晰切状。最后又以“岂南山之暴隮兮,将冥海之蹔溢”,收束全文,凸显气势。陆云状物写景基本按照这种描写顺序,既壮阔寥莽,气象宏伟而不局促,又蔚似雕画,细密而不空疏。这类作品一般用笔紧,用调急,给人以五音繁汇、目不暇接的审美感觉。
陆云赋叙述式写景,除《南征赋》大量运用四六言短句,多略去语气助词“兮”以外,大多将舒缓之笔与挺急之调有机融合,造成一种张弛有致的情致。如《登台赋》:“历玉阶而容与兮,憩兰堂以逍遥。蒙紫庭之芳尘兮,骇洞房之回飙。颓向逝而迕物兮,倾冠举而凌霄。曲房萦而窈眇兮,长廊邈而萧条。”大体上说,叙述用笔缓,描写用笔紧。以“容与”描述登台,以“逍遥”描述休憩,充满一种怡然自得的意味。而描述芳尘蒙室,言无人矣;回风骇人,言森然矣,则又笔调趋紧。特别是描述吹风逆物,如崩颓之回响,渐渐逝去;倾斜之冠,风吹飘举而入云霄,以夸张之笔写室内回风之狂,尤其骇人心魄。然而,后二句回风逝去,洞房萦绕而幽深,长廊悠远而寂静,风过幽静,言其冷落,用笔又趋于舒缓。缓与急的有机融合,使其调急而不峻切,笔缓而不拖沓。由张入弛,壮美与优美结合,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以轻淡之笔隐写景物之气势,是陆云写景状物的另一特色。如《登台赋》:“万禽委虵于潜室兮,惊风矫翼而来翔。纷谲谲于有象兮,邈攸忽而无方。”“惊风矫翼”之鸟,纷飞喧嚣而有形,迅疾远逝而无常。以众鸟联翩飞翔,喧嚣纷扰,描述其触目惊心的衰败之象,本是阴森恐怖,气势骇心,却用“委虵”、“谲谲”等轻淡的字眼加以描述,将骇心的气势隐于言象之外。《喜霁赋》以淡笔写雨霁,隐写霖雨之势,特别具有代表性。如“靖屏翳之洪隧兮,戢太山之触石。凌风绝而谧宁兮,归云反而挥霍。改望舒之离毕兮,曜六龙于紫阁。扬天步之剡剡兮,播灵辉之赫奕”,以靖、戢、绝、反,写雨止风静,用笔轻淡,然以太山触石来比拟雷雨之际强烈的闪电,以谧宁挥霍以状风云,仍可给人当初霖雨来时雨急风狂的联想。而月亮离于毕星,日光耀于天庭,也是在轻淡的写景中,让人联想到夏日霖雨磅礴的情景。其写景状物,以轻淡之笔写出气势,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增加了文章的审美张力。
概括地说,陆云赋在表达体式上,铺采摛文,写物图貌,带有明显的因袭传统赋的印记,但是,描写看似繁缛,而用笔清省;在层叠铺排之中,又简约有致,而且淡与浓、缓与急的艺术辩证法,都使陆云赋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而这与陆云以“自然”为审美本体,追求“清”艺术风格的诗学思想,显然是密切相关的[4]。
二
善于创设理境,是陆云赋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以情纬物,藉思成理,是陆云赋设境的基本特点。无论是状物、写景,还是述行、叙事,都以情贯之。即使是直接抒情言志的作品,往往也以连贯的意象为描摹主体,以景带叙,因象寓情,将叙述、写景、抒情、说理有机交融,从而创造出诗意的境界。而藉物言理,叙述说理,因景寓理,则是陆云赋以情纬物、藉思成理的三种基本方式。情、景、理的生生互证,构成了陆云赋独特的理境。
就以情纬物而言,其状物写景之《愁霖赋》的愁瘁之情,《喜霁赋》的雨霁之喜,《寒蝉赋》的悲悯之心,述行叙事之《登台赋》的兴废之感,《南征赋》的美颂之意,既是贯穿全篇的情感元素,也是笼罩全篇的结构元素。其直接抒情言志的赋,基本采用叙述式抒情—写景式抒情—说理式抒情的结构模式。《逸民赋》除了序文以外,开头叙述逸民隐逸之由:因世道险隘,无可措足,故栖迟丘壑,息影山林,超然尘网,恬淡浩然,养气怡性,与道逍遥。叙述中既隐含着对陋世的批判,也浸润着诗人对隐士的赞美、欣羡之情。然后,描写隐逸之处山林之美,所居境界清幽。即使是叙述隐士濯发玉泉,临谷投簪,写生活之逍遥;挹清源,餐秋菊,掬芳露,玩幽兰,拟秉性之高洁;放志怡颜,望灵岳,想佳人,写精神之高远自由;尸居山立,遵渚在林,写其韬晦避世,万物不扰其心等等,也仍然以写景为主体。如:“假乐器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挹迥源于别沼兮,飡秋菊于高岑……明发悟歌,有怀在昔。宾濮水之清渊兮,仪磻溪之一壑。毒万物之喧哗兮,聊渔钓于此泽。”以丰富的意象,在叙述中又将写景、抒情有机结合,创造出幽美的隐逸之境。《岁暮赋》在结构上与上赋微有不同,此赋用序文叙述抒情,一入正文即写景抒情,然后以说理抒情为收束。正文思路则逆接序文而展开,时序更替,时光流逝之迅疾;老之将至,学业无成之感慨;故乡之思,姑姊沦亡之苦痛;生命有限,欲归不能之忧伤:使诗人百感交集。最后借道家之观点,晏子之达言,自宽自慰。赋虽短小,抒情却类似《离骚》,忧端无绪,反复凌乱;结构有序,而层次之间种种情感又互相包融:折射了诗人创作时极为复杂的心境。赋之抒情说理,也始终以写景为主体,如开篇多层次地铺陈渲染时光的流逝,而后以“变棘心之柔风兮,滋丰草之湛露。玄晖邈以峻服兮,黄裳皓而振素”,“天庙既底,日月贞观。沦重阳于潜户兮,严积阴于司寒”,具体描摹时序更替,点染时光流逝的迅疾。其抒情说理也多采取寓情于景的方法,使景物成为抒情说理的主要构成元素。如“时凛戾其可悲兮,气萧索而伤心。凄风怆其鸣条兮,落叶翻而洒林。兽藏丘而绝迹兮,鸟攀木而栖音。山振枯于曾岭兮,民怀惨于重襟”,借助凄风鸣条,落叶乱飞,鸟兽栖音匿迹等景物,极写严冬的寒冷萧索,以悲伤、凄怆、怀惨等语词,渲染心境的落寞忧伤。陆云通过以情纬物的艺术表现手法,化叙述为描写,化抽象为具象,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就藉思成理而言,陆云赋无论是写景、状物、抒情,或寓哲理于意象,或因意象而达理。仔细考察,陆云赋创设的理境大约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藉物言理,即传统所说的托物言志。然其所言之志既以哲理为核心,又浸润深厚的情感。其《寒蝉赋》最为典型。序言蝉外有容仪,内有五德,君子效法之,则可以立身事君。然蝉缘木凄鸣,于侨居异乡的诗人之心有戚戚焉,故作赋言志。正文部分先言蝉之德,再言蝉之悲,次言蝉之用,最后言由蝉所引发的感慨。写蝉之德,首先总写蝉之美,突出其“清”;再写蝉德音之美而远闻,突出其“廉”;次写蝉音声之美,突出其“文”;其次写蝉操守之美,突出其“信”;再写蝉志存高远,凤居其处,然惟求一枝,适性而已,突出其“俭”。写蝉之悲,或写其忧伤征人不归,鳏寡无依;或写其叹息原宪之贫,孤竹之隐;或写其巢于枯枝,而思琼林远条,其志不达,哀鸣于风雪。写蝉之用,先言朝衣画蝉以为美,冠冕缀蝉以为饰,取其华美而明德。写由蝉所引发的感慨,先写由蝉的悲鸣,悟时光之流逝,从而产生仕不得志、王业艰难的感叹,再表达天光临照、皇室清静的希冀。通篇写蝉,句句言理,且情寓其中。二是叙述说理,由叙述最后升华到普遍的哲理。如《逸民赋》乃是在叙事写景中,歌颂隐士超然的情怀,高洁的节操。而其文结尾则又升华出普遍哲理,“是故夫形瑰者征咎,体壮者为牺。虽明文而龙藻兮,终俯首而受羁……荣在此而贵身兮,神居形而忘我。钦妙古之达言兮,信怀庄而悦贾。曾既明于天爵兮,何惙悲于人祸。陋国风之皇恤,同明哲于大雅”。以道家思想为基点,阐述外形奇伟、体格健壮、立德修名、建立不世之业者,必然自取其祸;唯有顺乎自然,等同生死,身藏治国之器而不用于世,方为达人之玄鉴。然后进一步申述庄子“齐物”之理:守无可无不可之道,泯是非,齐万物,同荣辱,进入忘我之境。怀思庄子之隐,敬其妙古之言,方可高蹈山林,怡养德性,避祸全身。三是因景悟理,也即由眼前之景生发开去,表达其哲思。如《登台赋》“仰凌眄于天庭兮,俛旁观乎万类”,由人事而感悟庄子相对主义式的哲理:“于是忽焉俛仰,天地既必。宇宙同区,万物为一。原千变之常钧兮,齐亿载于今日。彼区中之侧陋兮,非吾党之一室。本达观于无形兮,今何求而有质。”言俯仰宇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推究天地万物之变,一寿夭,同大小,此种达观之见本于无形之道,不可求之有形之象。此外,《愁霖赋》由天气之变而引发“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的人生哲思;《喜霁赋》由阴阳通泰、万物茂盛而产生超然世外的联想等等,都属于因景悟理的类型。
以情纬物、藉思成理的圆融统一,构成了陆云独特的理境,是除《南征赋》之外陆云所有赋的特点。这与陆机《浮云赋》《白云赋》《瓜赋》《鳖赋》等纯粹描摹物态是大不相同的[1]671-675,比陆机赋有更加浓郁的说理倾向。陆云赋由屈原开创的“以创作主体情感为表现对象的”的“情境”[5],而拓展为以创作主体由形下而形上的理性抽象的“理境”,带着鲜明的哲学思理形态,这显然与魏晋玄学的浸染密切相关。
三
程章灿先生认为,“叙述结构的经营”是两晋赋家的自觉努力[6],而陆云的这种自觉更为强烈。其《与兄平原书》强调文章布局,提出文章必贵“经纬”的理论。而注意“转句”与“结”的起承关合;文句之间的“流泽”“无间”,即文气流畅而不隔;杜绝“言语流行断绝”等等,则是对文贵“经纬”的具体要求。显然,陆云赋完整地体现了这一文章美学观念,主旨突出而严谨有序是其艺术结构的突出特点。
内在意脉连贯,文气流畅不隔,使陆云赋内在结构上承转自然。陆云赋都是前有小序,叙述作赋缘起,揭示文情之旨。正文围绕序言展开,不枝不蔓,主旨突出。郭建勋指出:“(陆云赋)各篇皆有明确的情志流贯其中,渐次展开,犹如长江清秋,千里一道,毫无阻滞蹇塞之感。”[3]375或以叙述引入说理,如《逸民赋》之序将世俗之人与古之逸民对比,揭示古之逸民,弃世贵身,甘隐丘壑;天地不改其乐,万物不扰其心;妙悟人生之臻境,享受自然之欢乐。正文围绕这一主旨,由叙述引入,以描写为核心,最后升华说理。或状物以理贯之,如《寒蝉赋》序言蝉外有容仪,内有五德,君子法之,可以立身事君,故作赋以美之。正文部分先述蝉之德,再言蝉之悲,次说蝉之用,最后抒发感慨,升华哲理。以所取之象(蝉)为线索,以蝉之“德”为核心,展开描述与议论,不枝不蔓。或因情设体,如《登台赋》以登台、入室、归去之行迹为线索,以所见之物象为描写核心。这一类采用的是线型的递进式结构,其叙事、抒情、说理往往是在同一维度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意脉尤为连贯,形之于文,则充盈着一往必达的流畅文气,从而构成自然严谨的内在结构。
陆云赋的结构虽也有转折跳跃,然其内在意脉似断而实连。由于有些赋表达主旨比较复杂,其结构就必然有所转折跳跃,如:《愁霖赋》由霖雨愁人而转入抒写“结南枝之旧思兮,咏庄舄之遗音”,渲染思乡之情;“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无期”,感慨人生短暂。《岁暮赋》在感慨岁月流逝,人生苦短之后,中间插入“蒙时来之嘉运兮,游上京而凯入。委乘辂于紫宫兮,剖金虎而底邑。凭台光之发晖兮,荷宠灵而来集”,抒写宦游上京,得其恩宠殊荣的人生际遇。仔细考察这类赋的文意与结构的转折跳跃,仍可见其严密的情感逻辑。陆云家在东吴水乡,故见霖雨而忧虑家乡,因忧虑家乡而产生乡关之思,由乡关之思而感叹人生,又由己而推及众生,最后回归主题。在表达上由近及远,由景及情,由己及人,其内在意脉仍然斑斑可见。而《岁暮赋》插入宦游上京,表面上破坏了抒情的统一性和结构的完整性,而在深层中又与浓烈的思乡之情形成反衬,强化了乡情的浓度。这种深层意脉的一致性与表层意义的跳跃性,恰恰使抒情写景得以化绵密为疏宕,化质实为空灵。这一类赋采用的是交错的递进结构,其叙事、抒情、说理往往在不同维度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眼前与想象的交错闪回,造成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宕与拓展,不仅形成结构的跳跃转折,而且给人更为广阔的时空之感。
注意意群与意群之间的连贯,“转句”与“结”(结语)的起承关合,则又使陆云赋在形式上强化了外结构的严密逻辑性。陆云赋主要以线型结构为基本形式,往往特别注重意群与意群之间的意义连贯性。如《逸民赋》抒写古代逸民隐逸之由时,以“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作结,然后自然转入对逸民居处幽美环境的描述,最后以道家思想收束;《登台赋》以登邺中三台的行踪为结构线索,先言登阁之缘由,再写登台入室之所见、所感,最后抒发现实人生之感慨。始终抓住自然与人事、现实与历史的盛衰形成对比,意群与意群之间的连贯也非常紧密。在外结构上,陆云还特别注意“转句”的起承关系,如《登台赋》在交代登阁缘由之后,先用“尔乃”转接,叙写登台所望,入室所闻、所见、所感;再用“于是”转接,描写三台之荒凉冷落;又以“于时”转入写时光与感慨;此后连用三个“于是”,分别阐释由时光、宇宙之变化,而引发“齐物”之理的思考,天命历数的体悟,兴废无常的感慨。在《南征赋》中,这种结构方式表现的尤为典型。此赋以谀颂成都王司马颖,叙述起兵的原因与目的为总起,然后连用四个“尔乃”承接,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渲染描述军威之雄壮,最后用“乃有”收束,以熊罴、虎啸之喻,概述其锐不可摧的气势,构成了总—分—总的结构形式。这类文章有鲜明的起承关系,主旨突出而结构整饬。而且转折连词的运用,有意识地将两组意群隔开,不仅造成语音上的停顿,增强了文章叙述的节奏性,而且也有效地消解了辞赋意象绵密的弊端。这种结构的整饬还表现在“结”(结语)的关合上。如《愁霖赋》与《岁暮赋》均以“于是”承接,然《愁霖赋》以“考幽明于人神兮,妙万物以达观”而总言人神物理作结,《岁暮赋》以“考大德于天地兮,知斯言之益矫”而概论自然之理、前哲之言作结,关合文情,收束全篇,使结构在跳跃中复归于整饬严密,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概括言之,陆云赋在情与物的二元关系上,多模拟而少创新,然其以情纬物,藉思成理,所构成的理境,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独特的主体性。自玄学勃兴以后,魏晋赋都浸染了大量的说理。从阮籍、嵇康、向秀到张华、潘岳、陆机等,其作品无不充满了玄学思辨色彩。“由于受《周易》‘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晋辞赋创作有明显的‘因情设象’的模式化倾向。”[3]375但是,由于陆云有更为自觉的文体美学意识和超越的人生态度,使其笔下的景物、情思、哲理三者圆融统一,摆脱了当时流行的繁缛华丽之风,而以超逸清拔的意象取胜,这就使其说理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境界——理境,从而开启了东晋以降辞赋理境的风气。由屈原创造的“情境”,到西晋创造的“理境”,再到东晋受佛教浸染而产生的“意境”,不惟是辞赋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诗歌发展的基本趋势[7]。在这一文学发展进程中,陆云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徐公持曰:“在西晋主流文风中,陆云既有入乎其中的基本一面,又有出乎其外的个人特色一面。”[8]这一评价可谓平实而中肯。
由于“二陆”在理论上切磋文艺,在创作上互相润色,使二人辞赋的风格较为接近。但陆机诗赋文体错位,诗繁缛而赋清简;陆云恪守诗赋文体本位,诗清简而赋丰赡——繁而不缛,故《文心雕龙·熔裁》曰:“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在西晋文坛上,陆云之具有相互补充的美学风格,其诗赋之别皆在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