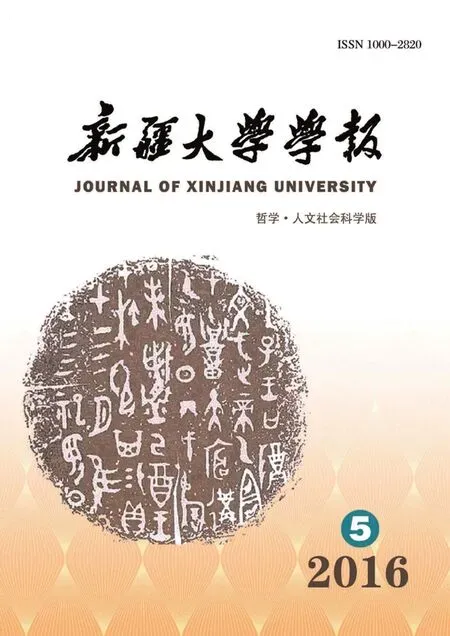清代比兴传统的重拾与宋大樽的学李诗风*
2016-09-29周游
周 游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宋大樽是清代乾嘉诗坛上较为另类的一家,但历来研究者寥寥。原因有二:其一,他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诗坛领袖,故在习惯以诗派流变为框架的诗史叙事中易沦为附庸;其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史学实证主义大潮下,受历史学的影响人们对于清代思想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汉学的考证学转变上,对考证学外的思想潜流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漠视。
宋大樽并非达官显宦,与当时控制学术话语的考据学亦保持疏离,故与时代主流又显得格格不入。但宋大樽在诗坛的缺席并非由于他的诗学理念与当时的诗学发展相断裂,而仅仅是与后代的关注点相错开,正如宋学从未消除它的影响力,具有宋学倾向的宋大樽也从未脱离清诗发展的概念环境。当外在的考据学学风有了内转的需要,当诗学上要求重拾比兴的传统,宋大樽等人的理论就十分值得注意了,倏忽之间,作为诗坛潜流的他们已然成为了时代先鞭者。
一、“始始而终终”——退回到本体的诗论建构
对于事物起源的求索,或许是出自人的本能。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心理大概来源于人们认为通过最初的一点就可以辨别出事物的本质,并且通过这最初的一点可以慢慢推衍出该事物之后的发展路径。但黑格尔认为这种简单的起源“单就它本身来看,在内容意义上却是很不重要的,因而对于哲学思考显得是完全偶然的”[1]。在这样的表述下,思考起源问题变得十分尴尬,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偶然的开端,那么以很大精力去讨论它就显得十分可笑。并且我们依据已经发展多时、蔚为大观的事物去回溯这样的起源,最终或许只能得到一个人为设定的始点——偶然的事物既然不具备内容意义,又如何能作为一个可以追寻的生生之道而被我们发现呢?
中国的思想和文学领域同样不能摆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但和西方具有创世意味的起源与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的开端不同。中国哲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基本在一元论的立场上①如张载是气一元论,于万象后面建立一个太虚作为本体,但太虚即气,本质上仍然是气化的万象,所以此处太虚并不是一个符号式的原点。二程是理一元论,这个理也不是创世性质的起源,有点类似万象的一种客观规律,他们也并不于万象后面再立一个符号式的原点。除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未有天地说起外,大抵宋代理学都是就既有天地说起。,将此问题聚焦在“已发”和“未发”上。与西方相比,中国思想上“未发”似可看作某种意义上的“起源”,其与作为“已发”的“开端”的距离并没有西方那么遥远,“已发”“未发”的分野是模糊的,打破分野也只在“一动”。钱穆先生曾言:“已发未发,是宋儒极爱讨论的话题。荆公濂溪,皆不免划分已发未发作两截看,故皆看重未发看重前一截。”[2]以上是就哲学领域来谈,那么这与文学有什么关系?陈世骧先生观察到“中国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特征,此一特征源于中国文化表达的普遍的同质性”,“简言之,由于这种同质性,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往往与伦理的、政治的、宇宙论的观点未曾互相分化”[3]。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宋代以后的文学批评自然与理学模式具有相似的结构。看重前一截在哲学理论的本体建构上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涉及到文学领域前一截的“未发”状态就常常被人忽视。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诗论,尤其是从宋代以来的诗话,其表现方式多是简短、偶然、非正式的评论,虽然很多评论敏锐深刻,富有暗示性,但是并不成系统,本来也就并不着意于建立一个完备的批评体系。
那么宋以来大量诗话所关注的诗歌实践技巧,其实多是外在的“工夫”问题。但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是从琐碎到系统,一种理论的完整也要求本体与工夫都能具备,传统诗论忽视了“未发”一层,在理论上并不完整。宋大樽的《茗香诗论》的出现就是对这一缺失进行补完。诗论以客问的形式开始:
客问曰:“曩观王文简所编唐贤三昧集,信而好之矣。谓三昧之旨,非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无之际者也。顾学之久,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4]102
这段话虽然是从王士禛所编的《唐贤三昧集》说起,但语言却袭用扬雄《解难》而略有不同。《解难》中类似的表述来自另一个“客问”:
今吾子乃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聘于有亡之际,而陶冶大炉,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5]
“客”在这里是责难扬雄为文过于高深,旨意宏大微妙,读者费时良多仍然不能明白。这就如同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对读者来说有“亶费精神”之慨,就是在作者那里,亦是劳而少功。与扬雄寄意深远的辞说不同,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所提倡的乃是严羽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表现效果,重视直观体验。宋大樽的“客”是以一个“非”字将这段话的前提引向了另一端,但相对于扬雄的“客”的观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反题。既然宋大樽的“客”引述了《解难》的原文,可以认为这个“非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骋于有无之际者也”是承认了扬雄的“客”的观点后作出的一个合题。可是这种作为合题的文学实践所导致的结果为何仍是“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殆不可乎?”那么可以想象的诗学实践已然末路穷途。此时宋大樽要建立自己的诗学,要去回应客的疑问,只能暂时放弃在“工夫”上的开辟,而转向“本体”。
答曰:“诚若所讯者,岂蒙之克辨也。虽然,试言之:学三昧集见终矣,若原始,抑犹未也。列子之言曰:‘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始何事,厥中惟灵,厥外惟无。此吾向者未作诗之说也。终何底?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此昔王文简既作诗之说也。始始而终终,取天下之合而连之者也。”客憬然曰:“曩者之于诗,譬画者、弦者之靳其手也。”余复开动端萌,客请缀之以其类。爰摭古言而证之、而广之、而或反之,表左[4]102。
此处宋大樽强调“原始”引述的“四气”之说,本原于《周易》。而汉代以来中国人对“气”的概念基本不出此框架。宋明理学之本体亦渊源自《周易》,牟宗三先生曾判宋明理学为三系:“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伊川朱子系”[6],其中前两系“以《论》《孟》《易》《庸》为标准可会通而为一大宗,当视为一圆圈之两往来:自《论》《孟》渗透至《易》《庸》,圆满起来,是一圆圈,自《易》《庸》回归于《论》《孟》,圆满起来,仍是此同一圆圈,故可会通为一大宗。此一大系,吾名之曰纵贯系统。伊川朱子所成者,吾名之曰横摄系统。”①钱穆也赞同伊川、朱子系与濂溪、横渠甚至明道存在体系的不同。简言之,《论》《孟》的出发点在主观地讲心体,《易》《庸》则从客观的性体讲起,从主观的心体到客观的性体形成一个贯通,这个系统便圆满起来了,从理论上说天人之隔就消解了。宋大樽希望“始始而终终,取天下之合而连之”也就是希望达到一个圆融的通路,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纵贯系统。他虽然从宇宙观的“气”说起,但作为诗论不可能不回归到主观的心体,他所说的“厥中惟灵”的“厥中”必然是合人心、道心而言的。宋大樽的诗论既然建立的“未发”的前一截,那么对于具体的诗歌形式与诗歌表现技巧,就总会有所看低。《茗香诗话》中多有如此的论述:
知始则知本,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本也[4]102。
不伫兴而就,皆迹也;轨仪可范,思识可该者也。有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太虚无为之风,无终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风,登空汎云,一举万里,尚何有迹哉?[4]105
在这里宋大樽表现了一种对于“未发”之始的执念,一但形于“已发”便很容易有迹,有了痕迹便可以用理性去模仿去把握,即所谓“轨仪可范,思识可该者”,这在宋大樽看来是不可取的。除非“伫兴而就”,如同陆、王系统中的“一心之遍润,一心之朗现”,凭借一心之感兴才能做到虽有待而无迹。宋大樽强调“伫兴”而发以达到“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的境界。从“已发”的角度看,宋大樽的诗论与王士禛倡导的“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出一辙。但在宋氏眼中,王士禛终究忽略了“未发”的部分,则王氏所谓的“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便丧失了本体,真的成为空中之音、水中之月,成了孤悬在外、虚张声势的梦幻泡影。宋氏自己的诗论则从“未发”而来,是有根坻的。如果单纯从理论的建构上看,宋大樽的诗论堪称完整,但由于他一方面过于强调“未发”的前一截,陷入一种形而上的理想中,另一方面在“已发”的后一截上也是推崇“莫知所以然”,故而实践性非常弱。所以后代的学者对此诗论的态度分成两派,知者多就体系的完整而称许,以为是妙道之行①指陈斌、姚椿、潘德舆等。,而不知者则就其陈义过高,以为是孟浪之言。
所谓的“不知者”以陈衍(1856—1937年)和胡玉缙(1859—1940年)为代表,二人批评的重点都集中在诗论中的一句话:
感变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也,则又不必言者也[4]104。
陈衍针对此句曰:“夫可以不言,而亦有不能言者,则不言固矣。若可以言,而又不必言,不几于无言矣乎。当云其可以言言者,又有其不必言者也。”[7]陈衍此处有一个误读,宋大樽所说的“有可以不言言者”不是陈衍理解的“可以不言”,宋的意思是以“不言”来“言”,重点还是落在“言”上,即不通过直言明言来描绘事物,而是以不直接表现来让读者获得一种直观体验。对于很多情感没法很准确地用直接的准确的言语表现的时候,只能“以不言言之。”宋大樽的下一句“其可以言言者也,则又不必言者也”意思是说那些可以用言语直接描写的,往往又没有必要写出来。在宋大樽看来,好的诗应该不是那种平铺直叙,它要传递的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要能感动人,这就并非简单的语言描写所能胜任。陈衍认为“则又不必言也”等于“无言”,显得过于绝对,于是改成了“又有其不必言者也”。但这样改违背了宋大樽自己的想法,宋追求的诗的语言之工乃是“莫知所以然”,如果语言和所要描写的事物完全对应,则诗意索然。所以在宋大樽看来“可以言言者”皆是“不必言”的,不需要留有余地。如果留有了余地,则是留下了痕迹。
胡玉缙则认为此言“殆又欲返之始始,则是编之落语言文字迹者,当亦自笑其多事。前有德清陈斌序,称其于道有见,殆为所欺欤”[8]793。他的解读更加囫囵,宋大樽此句的侧重点并非“返之始始”,而是在“已发”的时候如何做到“绝迹”。宋大樽在此处显然不是为了消解自己整个诗论,不是如佛家的“随说随泯”。胡玉缙和陈衍一样只注意到了“无言”而忽视了宋大樽真正想表达的“言”。陈斌并没有被宋所欺骗,反倒是胡玉缙对此没能理解透彻。
宋大樽诗学虽然重心在本体,但也有涉及“工夫”的内容,上面引起误解的句子就是其中一部分。在这里先将其谈“工夫”的内容完整展现:
今问以何能而至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诗之铸炼云何?曰:善读书,纵游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养心气,其本乎!感变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也,则又不必言者也[4]104。
铸炼的方式是由外而内的,是一种顺取之路。而感变则是由内而外的,形式上是逆觉之路②逆觉即返诸本心的体察,顺取与逆觉的说法均来源于牟宗三。。宋大樽整个诗论的本体形式是纵贯的而并非横摄的,与之对应的工夫是“逆觉”的③伊川、朱子系是横摄的,所以他们重视《大学》,工夫路径是由外而内的。。宋氏诗论在工夫上兼顾了顺取与逆觉,但他认为由外而内的铸炼才是“本”,可能是因为方便实践。但这样就会有一种不和谐感:如同以象山、阳明系的本体配上了伊川、朱子系的工夫。这是其诗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宋大樽的工夫的目的和理学的工夫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于个体如何通过这样的实践来打通天人之隔。宋大樽过分注重理学与诗学的同质性而忽视了诗学的独特性,所以在诗论中完全不注重具体的技巧的讲授①当然,宋氏自己的诗歌创作并非不注重技巧。,这样的“工夫”无论其得与失都是理学的得失而非仅诗学的得失。
二、比兴传统的重拾——宋大樽的“学古”内涵
以上是从一种理论内在发展的完整性上来考察何以宋大樽的诗论会转向本体的建构。一种理论追求其结构的完整虽有其内在必然性,但这种回归“始始”的理论何以出现在宋大樽的时代则不能单从理论内部来考量,还需要联系学术传统与诗坛现状这两大面向。
清代学术对晚明游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进行了矫枉,儒家大体上沿着智识主义的道路前进②余英时虽然认为这一发展并非思想史上的唯一动力,但毕竟是主要趋势。。然而从理论角度看,王学的弊端在于将“一心之遍润,一心之朗现”中的“一心”泛化:“心”渐渐丧失普遍性,每个单独的个体之“心”都可以成为衡量世界的标尺。于是人心遂虚悬而荡,提撕不住了。补救的正途应该是重新确立“心”之普遍性,若以博学事功来补救,则为离题③此处亦可参考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48页。牟宗三的意思是应强调道德之形而上的“天”,笔者认为依照王学自身理路,从心的角度展开更妥当。。但纵使有所离题,清初诸儒多采汉宋兼治,以道问学来辅助尊德性,尚未完全贬低义理之学。然而随着考据学话语居于学术主流地位,在乾隆时期汉学家已经忽略乃至否认宋明理学对他们的影响[9]。至此学者的眼光从内转向外,彻底偏向另一边:“以具体史识、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学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论证。”[8]3在考据学话语的影响下,一方面学问化成了清诗的重要特征之一,乾嘉时期的主流学人如钱大昕、王鸣盛、翁方纲等人更是创作了为数众多的金石诗和考证诗,但这类诗多平铺直叙,诗人以理性出之,很难直指人心,摇荡性情。另一方面,从学问的完整性上看,内外之学均不可偏废。
既然博学事功对于义理之学的补救尚且属于离题,于内在之学并没能很好地修正,学者们又如何能满足于完全将义理之学束之高阁的考据话语呢?于是汉学内部已有不少人开始了重建义理之学的尝试④戴震、段玉裁以及后来的阮元、焦循等都有这样的尝试,乾嘉时期常州今文学派的兴起,也与学术的内在转向有关。。这种重新内转学风发展趋势也一定于诗学有所启示,因为几乎同时(乾隆中期以后),诗学领域不少人开始关注比兴传统的丧失,兹举两例:
瀛以乾隆甲午应顺天试,出诸城窦东皋先生门。尝问诗于先生。先生诏之曰:诗之为道,渊源三百篇,有赋焉,有比兴焉。近今之诗,有赋无比兴,此诗所以衰也。(《东皋先生诗钞序》,秦瀛《小岘山人文集》卷三)
唐诗去古未远,尚多比兴……降及宋元,直陈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兴体微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既然认识到近今之诗与古之别在于“比兴”的丧失,那么重拾比兴就成为诗学复兴的必由之路。袁枚(1716—1797年)“性灵说”的提倡已开此先声,宋大樽(1746—1804年)、黄仲则(1749—1783年)的诗学李白⑤宋大樽与秦瀛交谊匪浅,其子宋咸熙《耐冷谭》中亦载秦有关比兴的言论。洪亮吉与黄仲则亦为挚友。,陈沆(1785—1826)作《诗比兴笺》,乃至后来的魏源(1794—1857年)作《诗古微》,龚自珍(1792—1841年)诗歌注重抒情性⑥陈广宏指出龚自珍对于“情”的理解,与晚明李贽、袁宏道一致,而与清代以“学问”涵养的“性情”崭然有异。参考陈广宏著《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变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244页。,应该都是对这一“比兴”传统的回应。这种回应突破了一家一派的诗学范围,成为了一种日益显露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诸人的学术立场都与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考据学有或多或少的背离,既然主流的考据学对于主流的诗坛有深刻的影响,那么上述诸人在学术上的内转趋势应该也带动了诗学上的内转,走向了重拾比兴的道路。章学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诗学风气的转向,他在论诗话时指出:“前人诗话之弊,不过失是非好恶之公;今人诗话之弊,乃至为世道人心之害。”这两句话虽然是针对袁枚而发,但是无疑亦点出了“前人”转向“近人”的趋势乃是从外在的得失到内在的人心。
宋大樽诗学的“学古”内涵也就在于此转向之流,他与袁枚不同之处在于一偏重师古,一偏重师心。袁枚之弊端类似晚明心学之弊端,宋大樽则从普遍的心性出发,强调心性之正,算是真正补救了“情肆”的危险,这是其理论上更完善之处。宋大樽的《茗香诗论》和稍后陈沆的《诗比兴笺》可以看作是提倡比兴的代表著作①其他人如黄仲则、魏源、龚自珍皆未有如此系统的诗学著作。晚清的陈衍就将二者相比较。。先来对比姚椿所作的《〈茗香诗论〉跋》和魏源所作的《〈诗比兴笺〉序》:
诗之有说自韩婴始也,子贡诗传,伪书也。然外传引诗与左氏同。虽间存古说而不得为定论。汉魏而后,则有钟记室之论人,司空处士之论境,有味乎其言之也。两宋论愈多,诗愈晦。说经者废小序弗用,而讲音律者,推求于字句之间,虽有沧浪之专主妙悟,为本朝王文简公开其先,然流弊亦往往而有矣。夫诗者性情之事,才与学皆后起者也。文简说诗,标举神韵,天下翕然宗之。数十年来,其敝也流于蹇弱而貌似,于是有志之士,务以才力相胜,而通儒钜公又以其学问之余溢为诗歌,至于推原本始则犹有阙焉。左彝宋先生患人之知作诗而不知诗之所以作也,乃为诗论,引世之忧愤、悲怨、淫泆、诡谲者,而一轨于正。予读之曰:“是诗教也,论云乎哉,有是书而先生之诗可知矣,而先生之人可知矣。”(《〈茗香诗论〉跋》)
……视中唐以下纯乎赋体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自昭明《文选》专取藻翰,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敝;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诗教再敝。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10]
姚椿、魏源都指出了诗学的两大弊端。对于诗话之学兴起后导致的讲求音律、推求字句导致的弊端二人都提到了。但另一弊端二者说法有所不同,姚椿针对的是当下:在汉学影响下“通儒钜公又以其学问之余溢为诗歌”;魏源针对的是六朝注重藻翰的诗风。
魏源此论还引出了比兴之诗与赋体之诗的对立,以为“中唐以后纯乎赋体”,这和秦瀛、洪亮吉近今无比兴的观点是同气的。中唐以后纯为赋体,那中唐以前呢?其实亦不是纯为比兴的时代,至少六朝文学重藻翰就被排除在外。从先秦汉魏到六朝到初盛唐,再到中唐以降,诗体语言(比兴)与赋体语言一直是此消彼长地变化着的。一旦一种诗体语言的形式固定之后,经过强调与不断实践所衍发出来对于此形式的重视会让之后的诗学发展慢慢偏向一种新的赋体语言,这时候诗体语言又会为了保持诗学的本质抒情性而重新试图瓦解这种赋体语言,如此不断变动演进就形成了流动的诗学史,也造就了纷繁的诗歌形式。清代考据学的重点也在于训诂名物,这点和李善作注专诂名象并无大异。无论是六朝的藻翰还是清人的以学入诗,都会造成饾饤其词的后果,这其实只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赋体语言而已。所以姚椿与魏源所指出的其实都是赋体诗学之弊。因为姚椿与宋大樽的时代更接近汉学如日中天的时代,故其论述救时之气重,而魏源则更像是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谈此弊端。
既然中唐以后的诗学“纯乎赋体”,而六朝亦以赋体为主,故而比兴的时代仅剩先秦汉魏与初盛唐了,所以宋大樽的学古之路即是从盛唐而入以上溯汉魏。
盛唐的代表则是李白、杜甫,杜甫的诗学对于中唐以后影响更大,他“晚节渐于诗律细”,将格律的精妙发展到极致。但也正因为如此,沿着杜甫的路子走很容易忽视其诗歌的比兴特色,而慢慢沉浸于字句的推敲与格律的钻研,落入已经固定并渐渐失去生命的纯赋体语言。李白的诗歌更多地继承了前代的风格[11],他的诗歌体现了古体向近体转变的轨迹。一方面,其诗歌创作慢慢从六朝的翰藻中挣脱出来[12],宋大樽要对治当时的清诗学问化之弊,学习李白的经验显然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李白又不为日益固定的近体诗格律所束缚,更多地具有一种自由的精神面貌。朝鲜学者金万重曾言:“邵子曰:‘看花须看未开时’,李如花之始开,杜如尽开,夔后则不无离披意。”[13]宋大樽诗学本来就重视未发的一截,而李白诗歌的这种始发的状态自然会深入其心。
叙述至此,我们就很能理解宋大樽为什么在诗歌创作中选择李白作为模仿的标杆。
三、宋大樽的学李诗歌实践
宋大樽现存两部诗集。一部是其生前手订的《学古集》,收诗133首,分四卷:卷一杂言27首;卷二五言古诗60首;卷三七言古诗19首;卷四五言今体诗27首。另一部是《牧牛村舍外集》,由其子宋咸熙褎集其所删者而成,存诗216首。该集未按诗体分类,今重新整理如下(见表1),以便于和《学古集》做一个对应比较。

表1 《牧牛村舍外集》诗体分类
既然《牧牛村舍外集》所存的是被宋大樽删弃的诗作,那么对比《牧牛村舍外集》和《学古集》我们能很清楚地了解宋大樽的取舍标准。这两个集子所收诗作在诗体上最明显的变化:一是今体诗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二是七言律诗的完全消失。
宋大樽的这种诗体的取舍,与李白诗表现形式的倾向是一致的[14]212,这是宋大樽从形式上追求比兴效果、师法太白的最主要特点。孟棨《本事诗》尝言:
白才逸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律俳优哉。”[15]
为何抛弃七言律诗能够增强诗歌“兴寄深微”的效果?
依据松浦友久先生的观点,律诗在形式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彻底地以‘对偶’的形式把握和表现一切事物。与此相对,在绝句中,对句并非不可欠缺”[16]242。单在律诗中,“如果说五律代表了中国古典诗诸形式中正统、典雅的表现感觉,则应该说七言律诗既代表着壮丽、典丽的感觉,又更明确地代表着对偶性本身。进一步当然可以认为,七律从诗型本身看正象征着对偶化→整齐化→完结化的极限”[16]250。由此可以判断,七律的消失表明了宋大樽对“对偶性”的抛弃,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其背后所反映的是诗内在心象的转变:诗一旦抛弃对偶性就丧失了均衡性的结构,诗的意象就偏于一方,随着诗歌中上下句的衔接而流动,并在曲终流露出余情。李白诗之所以有灵动(尤侗《曹子闲南村诗序》:“李似动,杜似静”,《西堂杂俎一集》卷四)的气质,之所以“一气不断,自然入化”(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正在于此。
由于《学古集》中没有七律,这种去对偶性的倾向可通过对比两个诗集中的五律来考察:
怀归
捧檄平生愿,如何欲挂冠。
只缘慈母望,不觉宦情阑。
草隔江乡绿,风连海国寒。
忍教添白发,为我忆长安。
(《牧牛村舍外集》卷一)
怀楚中故人
美人如明镜,知我双眉愁。
河汉渺无际,芙蓉忽已秋。
梦随今夜月,飞渡岳阳楼。
对尔鼓瑶瑟,相思楚水流。
(《学古集》卷四)
前一首诗中间两联对仗工整。颔联中“宦情阑”的原因是“慈母望”,于是这句话因果完整,怀归的目的不再被指向其它可能(官场凶险或自身年迈体衰)。颈联中“江乡”与“海国”交代了目的地与身处之地。“绿”也因为与“寒”相对,就不仅仅是指向一种颜色,亦不仅仅为表现了自然山水之生机勃勃,而成为了具有“暖”的意味的词。这两联亦可互为补充:“江乡”、“慈母”、“绿”是处于一个聚合层面中,来与“海国”、“宦情”、“寒”的聚合相组合,诗人的怀归即是以前一个聚合代替后一个。后一首诗由于抛弃了对偶,则无法拆解成类似相对而互相补足的意象聚合,其意象是偏在的、流动的。由美人知我愁指向何所愁:与故人地理位置的远(无际),到时间因素的晚(秋)。由于迫切地想见到故人,而现实中无法实现,便借助梦境,随着今夜的月,飞渡到楚中的岳阳楼,接着就可以对着所思之人鼓瑟来抒发相思之情。由于没有对偶所造成的句意的停顿与回环,加上“忽”、“随”、“飞渡”等词的使用加快了意象移动速度,整首诗的意象一气贯下,使人应接不暇。
除了“去对偶化”外,李白诗风的另一个特点则是诗的描写具有很高的普遍性与抽象性。袁枚曾认为“杜甫长于言情,而太白不能”(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袁枚论诗看重个体化的私情,他认为杜甫所长而太白不能言之“情”当亦是具体描写下的私情。以离别诗的创作为例,松浦友久也认为杜甫、韩愈所善于描写的是对送别对方进行的细致描写[14]58,而李白诗则由于“扬弃了个别人物、个别特点的描写,离别本身的印象倒更加强烈”[14]54。伤逝、怀人之类的主题在魏晋以来的诗歌中就非常普遍,李白诗中对于人类普遍之情的描写可以说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宋大樽的诗歌创作就继承了李白诗的这一特色,这也使他的诗学实践能更接近汉魏诗歌的堂庑。先举下面三首为例:
望洞庭山
怀周山人允中三首
风送渔歌响,年年绕洞庭。
吴王消夏后,余此风泠泠。
余亦钓船至,留看山色青。
翻怜湖畔客,犹著种鱼经。
闻有林屋洞,洞中何所之。
秋来看明月,此去通峨嵋。
石室银房杳,花飞神女祠。
仙之人不见,万古长相思。
仙乐依然在,听君焦尾琴。
从来弹古调,未必索知音。
我有水仙曲,相将答所钦。
春风一为别,渺渺数峰深。
(《学古集》卷四)
这是一组怀人诗。第一首诗叙述诗人行船至洞庭山,见悠悠青山而生发出思古之幽情:吴王曾在此消夏,时运交移,繁华落尽,如今只剩下泠泠清风。此处亦是当年范蠡的肥遁之所,诗人用“怜”字来形容他应是兼有爱与惜之意。此处的范蠡或即指代周山人,又或许只是沿着吴王的思绪而谈起。总之面向现实的怀旧蓄念并不明确,它和面向过去的思古幽情纠缠不断。第二首诗中,诗人的思绪飘散得更远,仿佛置身于神仙之境,然而遗憾的是终究未能见到仙人,而留下了万古之相思。这里仙人是谁?亦未明确交代,或许亦包括古之贤圣与后之来者,一切跨越时空而能与诗人为知己者。我们能从中感受到诗人的一种超脱尘俗的愿望,这种愿望需要打破人在现世中占有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去感受一种永恒。第三首诗的开头所说的“仙乐”,似乎依然是从第二首诗的仙境中传出的,但这种仙乐又和现世的周山人联系了起来。周山人弹奏的是古调,古人弹奏的是古调,甚至仙人亦弹奏的是古调,而从来弹奏古调都未必能得知音,这种遗憾是亘古不变的。诗人亦准备了《水仙曲》,将要回应知己。但他有没有弹奏呢?我们不得而知。现世的周山人不在身边,仙之人不见,古之人又难觅,他只能在春风中作别渺渺青山。第三首最后一联“春风一为别,渺渺数峰深”融合了李白的两首诗中的句子:“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人轻描淡写地留下了类似“此地一为别”和“江上数峰青”的句子,而其实要表达的则是“曲终人不见”,“孤蓬万里征”的遗憾。
这三首诗中都并非具体描写诗人与周山人的交往细节,而是将自己的感怀放大到天地之间。诗人不见的不仅仅是周山人,亦有古人与仙人。而知己难觅又不仅仅诗人才有体会,这种寂寞是跨越三界,无论古今的。李白的“曲终人不见”所思所念的亦不是具体的某个人,在这一点上,宋大樽与之有着相同的情感观照。再看一首诗:
怀山塘酒家
美人安在哉?尤在姑苏台。
一片五湖月,香魂独自回。
春风忽吹散,化作桃花开。
笑劝当垆女,如何不举杯。
(《学古集》卷四)
诗中的美人指代西施,相对于永恒的月亮,美人的形象是无法常驻的,其幻化亦是忽然而至的。香魂化作了尘世间美好而脆弱的桃花,桃花的无常比起美人的香魂更让人有直观的体会,目的是让人感慨欢愁有涯,人生短暂。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美人、月色还是桃花都并非具体的描写,这些景象的组合完成于诗人的脑海中,是作为抒情的载体而抽象存在的。诗中唯一具体的人物是或许曾与诗人有接触的“当垆女”,而她此时亦必不在诗人面前,不然何谈“怀”呢?诗人劝她举杯消愁,无非是自勉及时行乐罢了。这种抽象的描写在宋大樽《学古集》中多有,下面两首亦反映相同的主题:
招叶青焕以照之天台
索君笑,赠君言,我能使君再少年。铜山只合尽沽酒,一朝饿死夫何有?少年如花春风吹,古之少年安在哉?望天台,散我怀,笑口且共桃花开。
(《学古集》卷三)
贻城中游好
昨自天台回,逢人劝放怀。惜哉天上瀑,未得酿绿醅。吴山半酒楼,江湖抱我杯。楼头乌啼花乱开,美人不来明月来,有酒不醉将如何?
(《学古集》卷三)
美人、桃花代指一种美好而易逝的事物,明月则代表永恒不变的时间。酒是沟通二者的媒介:在酒精的作用下人可以坐驰,能突破时空限制与友人相聚,与古人神游,同时忘却生命的短暂。这里的美人、桃花、明月、美酒与李白诗中相同的意象都是抽象的,它们在表达的功能性上也是相同的。与之相反,《牧牛村舍外集》中的送别、怀人、怀古诗则多就具体的事情而描写,兹举一例以明之:
送张八丈雪涛从军台湾
援手旧缝掖,孤查老客星。
飓风吹剑冷,海色上眉青。
喻檄惊三岛,杨帆效百灵。
宁同下帷者,寂寞守遗经。
(《牧牛村舍外集》卷二)
单从诗题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出人物、地点与事件的完整,这与之前几首诗模糊的怀人有很大的不同。诗中亦是紧贴“从军台湾”来实写,描绘了此行的艰辛。诗人最后一联表达了对张雪涛远行的不舍与不解,反用了初唐杨炯《从军行》中的句子“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宁愿皓首穷经,也不愿投笔请缨的表达正反映了乾隆时期智识阶层重视考据学,而相对轻视事功的心理。与宋大樽同时代的赵文哲因参与征讨大小金川之役而殒命西南,其好友钱大昕亦对其选择事功而放弃学术表示惋惜。所以这首诗无论从描述的事件,乃至表达的思想都是当下的,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这种类型的诗在《牧牛村舍外集》中绝非孤例,对比之前《学古集》中的诗,能明显发现二者的区别。
形式上的“去对偶化”和描写上的抽象化是宋大樽学习李白诗风的两大重要法宝。前者使得宋氏之诗能更接近李白诗所具有一种追求非完整性、非固定性的嗜好。后者则使宋氏之诗在对世界人生的关怀上和李白一致。这两个方向的一致就使得宋大樽诗与李白诗的渊源不只是停留在意象的雷同和单独句子的化用,而是体现了二者诗歌在内在心象上的一致。因此,宋大樽在当时几乎有了当世李白的美誉,秦瀛诗曰:“乌虖李白今不死,开元以还见吾子。”(秦瀛《小岘山人集》詩集卷十一)汪远孙诗曰:“白眼看余子,青莲有替人。”(汪远孙《借闲生诗》卷二)宋大樽自己亦“自以为太白复生也”(《学古集》序)。然而做李白之“替人”谈何容易,幼承庭训,学诗亦师李白的宋咸熙尝言:“诗家之有李杜,如黄河泰山之有世间,千古不能有两。”“自唐以来学杜者多,学李者少,盖无太白之天资怀抱,欲求其似,惟恐画虎不成。”(宋咸熙《耐冷谭》卷一)李白千古不能有两,既然世人很难有李白之“天资怀抱”,那么宋大樽是否具有呢?在此宋咸熙自然须为尊者讳,但笔者则不能不深究。玩味二人生平,联系其诗作,笔者归纳出三点不同,其核心是二人对人生及诗歌的控制力有差异,现表之如下:
1.李白有极强的客寓意识,没有一个明确的家的概念,因此他漂泊天地间,有“生世如转蓬”的印象。宋大樽则有明确的故乡,有家中年迈的母亲。这类意象一直会出现在其诗中,制约着他去纵横四海,所以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诗歌中,宋大樽都无法如李白般落拓不羁。
2.李白一生都在追求事功,但这种努力的结果并非自己所能预期。李白人生的许多不幸也源于此,但他有着傲岸倔强的性格,能够在人生的谷底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这又是宋大樽远不能及的。宋大樽晚年好佛,不欲闻世事,他的人生是简单而能够自己把握的。
3.就人生的最终归宿死亡来说,李白的死留下了“捞月”的传说,不管真实性如何,至少暗示了一种不确定性。这正暗合李白一生的漂泊不定与诗歌中常有的不完整与不稳定的感觉。而宋大樽的去世则完全在自己的计划之中:他精通占卜,并在生前准确地预知了自己的离世(朱骏声《记宋助教遗事》,《传经室文集》卷六,民国刘氏刻求恕斋丛书本)。
正是因为这三点不同,使得宋大樽无论在人生还是诗歌创作上都比李白的控制力强,但控制力愈强则生命愈稳定而文学格局愈受限制。因此宋大樽的诗歌虽然形神都和李白诗有共通处,但是毕竟输在了格局上。宋大樽终究无法做李白的“替人”,这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原因。李白诗歌善于描写抽象与普遍的事物,则所能描写的事物毕竟有限。形式逻辑上有一个法则,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其内涵就越小。如李白这个具体的个别的人就有着很丰富的内容,而抽象的“人”却贫乏得多,它甚至会缩小到只是李白的一个面。故而一旦李白这样的天纵之才出现并致力于以诗来表达这些普遍的抽象的事物,很快就能覆盖这一领域。再有千百人来开垦,也只能是不断地重复生产。因此宋大樽的学李诗风的成就以笔者来看并不在诗本身好不好,能否超越李白,而在于:其一,他能较早地参与重拾比兴传统的诗风转向,并对后来的龚自珍诗歌提倡抒情性有重要的影响。其二,是他能准确地把握李白诗的特性,他的师法李白在形神上都非常到位,这给后世研究李白诗歌亦提供了一个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