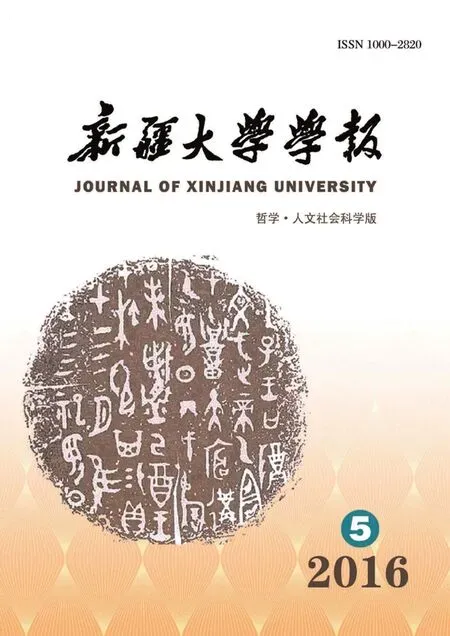明代古诗选本中的“谐隐”与博雅思潮*
2016-02-19岳进
岳 进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064)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谐隐”的论述可追溯到六朝时期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追溯谐隐的文体渊源,也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史书记载的典故,得出“(隐者)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1]271的结论。在六朝文学发展的思潮中,文学自觉意识逐渐增强,文体分类观念日趋成熟,文、笔之争就是文学观念深化的反映。刘勰持一种“泛文类”观念,《文心雕龙》收入文体81种,包括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谐隐》则属于“文笔杂”,范文澜认为“杂文谐隐,笔文杂用,故列在文笔二类之间”[1]5。而谐辞、隐语,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收录标准不符,未被收录,可见当时对谐隐的定位就存有不同看法。而后人心中的“古诗”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流传久远的《文选》塑造、定型的,明人编选古诗有意破除《文选》长久以来形成的习见。钟惺《诗归序》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反“选体”的意识:“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为古诗,因而名古诗为‘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2]卷首臧懋循《诗所序》亦云:“繇斯以降,作者无虑百千万言,而揆寔之家冣着者无如萧徳施、左克明、郭茂倩,或摘小疵而掩全璧,或综乐府而遗声诗,安以称得所,犹未也。”[3]卷首他认为从萧统《文选》到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集中体现了前代古诗选集类型单一、观念片面的弊端。元人左克明的《古乐府》中已开始收录“古歌谣辞”,而真正大规模地收录谐隐类古诗,直到明代古诗选本中的古逸诗才出现。
一、复古与“古逸杂篇”中的“谐隐”
明初,杨慎最早开始辑录古逸、民谣和古谚,编集《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和《古今谚》。关于杨慎的编选动因,《古今谚》“古谚不可忽”援引《文心雕龙·书记》云:“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此者,可忽乎哉。”[4]147藉由圣贤诗书的采纳,证明粗鄙俚俗的民间谚语亦有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又“谚语有文理”云:“贾人之铎,可以谐黄钟;田夫之谚,而契周公之诗。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籁;五性之文,发于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强者,此非自然之诗乎?”[4]147从古谚本身立论,认为发乎自然是古谚与生俱来的诗学属性。最为重要的是,古谚、逸诗等原初上古先秦文献,可为复原古道提供鲜活丰富的素材,为儒家诗教呈现生动的实例,《风雅逸篇》自序云:“以此其存,概彼其余,岂必无主文谲谏之旨,民彝物理之训哉。”[4]3韩奕作《风雅逸篇后序》更充分地阐述:“要之皆至理所寓。人不皆圣贤,至其言或喜或乐,或愤迅,或感慨悲歌,或激烈,或贞静,或幽隐,玄微灵怪,奇可异,惊可讶,及其归,皆不越乎彝伦日用,是亦圣贤之徒,而选风雅者所不弃也。是编既出,则风雅当有所补,而典籍亦全矣……升庵复古之志广且勤,又虞夫文体靡下而用其意者也。业诗者试并观焉。”[4]85作为《诗经》的补遗,圣贤至理的寄寓,实现复古理想的重要方式,逸诗、谣谚已获得多重话语功能和意义。故而,“凡先秦以上歌谣声诗,其巨细短长欢呼悲怨之类,悉以收录不遗。下逮谚语,亦在采获。”[4]85
在杨慎看来,逸诗、谣谚都是风雅的补充,是建构和传播儒家经学的有效方式,最看重的就是其诗教功能。它们往往来自现世的人生经验和历史镜鉴,兼具泛概时世的哲理意义和日常实用的劝诫教化功能,更易于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尤其是民谣、古谚等民间俗语,语言表面看来俚俗、朴质,甚至滑稽可笑,却隐含至理,深入浅出,表现出谐隐类话语的语言特点。臧懋循《古诗所》云:“古谚、古语本不属诗,但语涉褒刺者,已入杂歌谣辞,余难概废,别为一卷,仍附其次。”[3]凡例之所以收录不具有诗歌属性的古谚,正是看重其直刺事物本质、揭破普适性事理的独特功能,“杂歌谣辞”卷外,特设“古语古谚”一卷。此亦是受到此前选家的影响,如冯惟讷编《古诗纪》古逸一目下设“古谚”类,收录174首;张之象编《古诗类苑》以《古诗纪》为蓝本,遵其分类,专设古谚部(古谚),录古谚188条。此后,崇祯年间付梓的唐汝谔《古诗解》录古逸杂篇76首,其中“语谚”33首;陆时雍《古诗镜》录《谐语》106首。
《古诗归》选古逸124首,虽未设立谚语之类属,但以评点的方式,“苦口婆心”,为读者指明学习路径,至于古逸中的隐语、箴铭等,更是频频评议,阐发其中的处世哲理,提点读者深思明辨。如钟惺认为黄帝《兵法》是奇妙的“防微慎渐之语”,《金人铭》以“慎言”为题旨,实为“免于刑戮身世之学”,“柔密恭慎,持身涉世之学”[5]卷一。又评《方回山经引相冢书》:“语太尽情,然有至理。”[5]卷二评《古谚古语》:“‘将文者且朴’,至理也。”[5]卷二
此后,陆时雍《古诗镜》专门于歌谣乐府中析出此类具有警策性质的谐语,将乐府与歌谣、乐章(即郊祀乐府)、谐语明确区别开来,置后三者于八代之末,收录《歌谣》三卷,选先秦歌、谣、诵、操41首;《乐章》三卷;《谐语》一卷,录《谐语》106首,观其评语:
歌兴到即流,措辅成响,稍涉拟议,即非矣,故歌言无文不委。歌所贵者二,一欲其逸宕而多风,一欲其郁屈而多感[6]337。(总评“歌谣”)
《房中歌》不沿《雅》、《颂》典则,靡丽相杂而成,以之视《封禅颂》则庄,视《郊祀歌》则轨矣[6]375。(评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
《诗镜总论》云:“诗有六义,《颂》简而奥”,“《大雅》宏远”,“《小雅》婉娈”,“《风》体优柔,近人可仿。然体裁各别,欲以汉、魏之词,复兴古道,难以翼矣。”[6]卷首风、雅、颂,是陆时雍心中设定的诗歌最高标准,是复兴古道的终极理想,而其多元的题材主旨、艺术风格,远非汉、魏古诗所能满足,故而,必须从多种取向上扩大选录的古诗范围,强调不同的体类功用:“歌谣”委婉多讽,抒情意味深厚;郊祀歌应肃穆庄重,和洽雍容,摒弃一般诗歌的骈偶、藻饰和繁缛。对于谐语,陆氏未加评议,但别自为卷,在与歌谣、乐章的对照中,反衬出其心中早已形成稳固的观念:谐语应揣度议论,阐发事理,观点鲜明。此种观念正是积淀、生成于此前大量出现的古诗选本《古诗归》、《古诗解》等。
谐隐类古诗在明代古诗选本中的出现和备受推重,与晚明体系严紧、分类细密的辨体思维构成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诗体辨析严密,体式分明,制定规范,不容逾越;另一方面,却又广泛收入本不合诗体的边缘性古诗。个中缘由,颇令人深思。
二、谐辞、隐语与博雅、宗经之风
若追溯思想渊源,《文心雕龙》应是其中之一。《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和肯定,呈现出一种兼收并蓄、多元融合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和文体分类观念又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明人认为:“刘勰之评,议论精凿。”[7]不但《升庵诗话》《艺苑卮言》《诗薮》《诗源辨体》等诗学论著皆引录之,杨慎、曹学佺、梅庆生、钟惺等名家还专门评点《文心雕龙》。明人对古逸的重视,可以说正是继承了六朝《文心雕龙》《文选》中的文体分类观念,广泛吸纳歌、谣、谚、箴、铭等多种诗歌产生初期的文体,作为古诗发轫之源。《古诗纪》《古诗解》等明代古诗选本普遍引用《文心雕龙》的《铭箴》《诔碑》等篇作注解。《古诗归》中大量采用“隐语”为批评用语,《古诗镜》还特设《谐语》一目,都不能不令人想到《谐隐》篇关于谐辞、隐语的论述。
除《文心雕龙》的传统沿袭外,明代选家对谐隐类古诗的关注,还与当时博洽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晚明时期,出现一股读书好古、以经术为源的博洽学风,大批文人博通经史,以兴复古学、经世致用为务。这样的风气是接续了何良俊、杨慎、王世贞等开创的学术传统。龚鹏程撰《晚明思潮》,第十章《经学、复古、博雅及其他》论何良俊主博雅、重经学、倡复古,实为反时义俗学、宋明理学的一种策略,亦是吴中地域自身的学术传统[8]。
杨慎可以说是博雅一派的肈始者,以博学名冠一时,著述丰富达百余种,主要目的便是复古、宗经。张素嘉靖庚寅年(1530年)为杨慎《丹铅余录》作序云:“今知君子所以贵博且精者,非以掩众譁誉,欲以诩道而正辞也。”[9]治学宏博所欲弘扬之道,乃为六经。杨慎嘉靖丙辰年(1556年)编注《绝句衍义》,即有仿孔子注六经之义,作序曰:“近日多为禅梵绝学之说,或以六经为糟粕而薄之,又以为尘埃而拂之,又以为赘疣而去之,又以为障翳而洗之。不畏天命,狎大人,侮贤言,六经且然,何有于诸子百氏乎?”[10]他批评时人薄弃六经、热衷禅学,故以注诗的方式倡导儒家经学。
但杨慎谨守六经的体制界定,《升庵诗话·诗史》云:“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11]他认为诗与经史判然有别,不可通观。而王世贞更强调《书》《易》与《诗》的共通性,“《易》奇而法,《诗》正而葩。韩子之言固然。然《诗》中有《书》,《书》中有《诗》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诗也”[12]965。不仅《尚书》《易经》中的有韵之作可以当作诗歌,亦可以从历史、政治的不同角度去解读《诗经》。对此,唐汝谔在《古诗解》中表达异议:“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复佚乎?夫业已列于经矣,奚其佚。”[13]凡例在此,似对王世贞之说持有保留态度。
另一方面,这种兼容经史、数术等多向来源的诗性认同,开拓选家的采集视角,导引选家从纯粹的诗体转向关注其它“文笔杂”性质的文字,选家中不乏赞同、接受王世贞的说法,运用到古诗选本中。王世贞认为《易》中有诗,《易林》《参同契》都可被视为《诗经》的一种外延。“延寿《易林》、伯阳《参同》,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12]976《古诗归》《古诗镜》“谐语”中都大量吸取《易林》的短句作为诗作。此外,在《古诗归》的评点中还鲜明表现出以诗为经、以诗为史的特点,关于这一点下一节详述。
明代古诗选本中,若以数量的多寡和类型的丰富而论,《古诗纪》可以说是最典型地体现了以复古、宗经为旨归的博雅传统。冯惟讷编选《古诗纪》,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搜集、编录古诗,自认为此书已达到“著诗体之兴革,观政俗之升降,资文园之博综,罗古什之散亡”的功用,紧接着又自谦云:“若必云本道德之旨,叶风雅之音,校论叙成一家之书,尚有望于大雅君子焉。”[14]凡例在此,体现出明确的价值等级意识,即将编选的价值层次分为两个等级:初级,网罗散佚、博综无遗;高级,弘扬风雅精神、实现道德教化。而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选本价值观,张四维为《古诗纪》撰序就是集中从两方面评价该选本的意义,序云:
先生以俊才大雅,高步一时。见世之为诗者多根柢于唐,鲜能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治,乃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辞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鸩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焉[14]卷首。
张氏从两个层面肯定《古诗纪》的无所不收、了无孑遗:首先,古诗的类型得以拓展,突破传统的诗词歌赋,历来不受重视的残缺文献、边缘作品及原生态的民间俗语,皆为《古诗纪》悉数收录;其次,选录古诗的来源突破传统的诗集、乐府集、别集,扩大到经史子集、博物志怪、稗官小说等。显然,张氏并非是从辑佚类书的角度赞誉《古诗纪》的广收博取、兼容并包,也不仅仅是从追溯诗家渊源的意义上,肯定古诗之为“穷本”,其关注的焦点是“以窥风雅之治”,以人性教化为根本。这一点在序末再次得到强调:“使艺林之士,因诗考人,因人论世,得以绎祖述之渊源,第古今之优劣,猎皇王之菁华,而穷性术之变化也,岂不伟哉?”[14]卷首对当时诗坛一味宗唐之风的反拨,也正是由此展开:
明兴,诗人承宋元余习,颇乏远调。弘治间,北地李先生献吉始以唐风为天下倡,一时人士宗之,文体一振焉。及其敝也,株守名家,矜其学步,千金享帚,斯不远览之过尔。余故谓先生是编之集大有功于雅道[14]卷首。
张氏认为,相较而言,唐诗的盛行仅是有益于文体的振兴,学诗者局限于亦步亦趋的模仿,不能“远览”其根本,而古诗的学习,“有功于雅道”,此与上引序文开端指出的冯惟讷“俊才大雅”“风雅之治”,构成前后呼应的内在逻辑关系。由此可见,明代古诗选本编撰的价值和意义,已超越单纯的诗学层面,“博”只是手段,“雅”方为目的,由“博”以致“雅”,即由复原古诗全貌以达到复兴古道的目的,复古与博雅,二者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此后,嘉靖至万历时期,出现一系列重要的古诗、唐诗选本,如李攀龙《古今诗删》、臧懋循《古诗所》《唐诗所》及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唐诗归》,唐汝谔《古诗解》和唐汝询《唐诗解》,陆时雍《古诗镜》《唐诗镜》,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等,皆兼顾古诗与唐诗的编选,且并举而置,地位相当,可见博雅、复古观念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尤其是身处晚明末世,古诗的编选承载了文人士子更多的政治期待。崇祯年间钱龙锡作《唐士雅古诗解叙》云:“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13]卷首唐汝谔也在“凡例”中强调以雅正为选录原则:“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13]凡例博雅复古在这里不止是针对时义俗学的文化策略,其真正意义是与盛世太平景象构成一种潜在对应关系,甚至就是国家中兴的先兆预示,“史不云乎: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吾明正嘉之际,文惟师古,而世庙见龙飞之盛。今(原缺)圣天子将挽世俗,登诸唐虞。士雅是编,《卿云》、《南风》而下,读其解者,爛焉。古圣王之化一新,庸非中兴之先兆与?”[13]卷首古诗选本成为一种镜像,映射出晚明士人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昌隆盛世的渴望。
三、谐隐、小品与博雅、性灵思潮
从明代小品文的创作潮流来看,杨慎编集逸诗、谣谚的行为并非独立的个体现象,与之交往的何景明就编有《四箴杂言》,批点过《唐诗正声》的敖英编有《慎言集训》。敖英自叙编集动因:“余平居应酬,往往不当言者言之,不必言者言之。甚或招尤起羞,悔莫能追。每览载籍于慎言有涉者,辄掇节焉,汇以抄之以自警。”[15]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戒”,下卷为“贵”,采古今规戒之词以自警,与杨慎“主文谲谏之旨,民彝物理之训”追求相比,是将古籍箴言更加日常化、个体化的经世致用。其中对人生哲理、道德准则的普遍关注和思考,都彰显了一种理性思维和自我批评精神,与宋明理学对于义理的精研有密切关系。
明代古诗选本中普遍选入大量铭语、箴言,亦与箴言体小品的编选桴鼓相应。如《古诗类苑》“人部”立有“规戒”一目,收上古箴铭45首,其中《武王书铭二十章》《武王铭十七章》。“铭者,书于器以自警也。”“武王诸铭,可谓钦明文思。”[5]卷一周武王铭语精警入微,《古诗纪》《古诗归》和《古诗解》皆收录。《古诗归》评《盥盘铭》云:“溺于人,三字,警甚!谗色俱在内。”[5]卷一评《带铭》“火灭修容”云:“四字奥而确,慎独人语。”[5]卷一注重从细碎小物中体察感悟、时刻警戒,防微杜渐,克己慎行。铭箴之作与谐隐谣谚,体类风格不同,雅俗有别,但时时自省、克制警戒的宗旨是完全相同的。
从思想渊源和体制形式两方面,明人又未尝不是受到宋人题跋小品的影响。钟惺推崇黄庭坚的题跋文字,谓“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不合,所以为妙。”[16]565特摘录数条作《摘黄山谷题跋语记》,其文字篇幅短小,体式灵活,主要涉及治学治经与心性修养。如题语中有《书赠韩秀才》曰:“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礼仪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16]565《书旧诗于洪龟父》曰:“须要尽心于克己,不见人物臧否,全用其辉光以照本心。”[16]565于此提出治经之法的根本是“养心治性”、务求“克己”,与《古诗归》评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嘉靖、万历时期,撰写箴言体小品渐成风气,出现田艺蘅《玉笑零音》、陆树声《清暑笔谈》和曹臣《舌华录》、徐学谟《归有园麈谈》、吕坤《呻吟语》等箴言体小品集。它们往往好奇嗜古、独标新见,呈现出另一种审美取向,与晚明古诗选本的评选遥相应和。
田艺蘅的《玉笑零音》,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认为属于箴言体小品①详见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第八章“逸韵闲情”,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除劝诫警世的道德箴言之外,最能突显个人观点的部分实为泛议经史、品评人物,这也是其小品文中一以贯之的突出特点。《玉笑零音》被编入田著《留青日札》,谢国桢“以是书为朱明一代杂家之冠”,赞其“高瞻远瞩,不为俗囿,颇有新知,世多称之”[17]760。蒋灼《序》中所引田艺蘅自述:“凡其可喜可愕、可哂可疑、可怪可奇之事,得之于心评,断之以臆见,皆得以并存而兼取之。”[17]764可见田氏取舍最为看重的也是书中的心评、臆见部分。黄汝亨《重刻〈留青日札〉序》云:“田子艺先生嗜奇博古闻于世……盖读其《留青日札》所载,博物通雅,抚时悼俗,或徵或谑,或经或怪,或质已闻,或标独解。”[17]761其中评说经史、臧否人物,往往独行其意,别出己见,颇与正统儒家观念不符,时人不乏质疑之词。万历元年(1573年)刘绍恤《留青日札序》云:
田子艺以博雅闻名,所著外家言皆有叙述,业已信于世者亡论已;乃其所为《留青日札》,则命之曰吊诡之役,非耶?夫士之负奇者,每自托于师心之谓,而不轨于古。始或一溺于古,则其词无复蔓衍摹拟,无所取衷。之两者钧之覆瓯哉。子艺之言俱在,事系稗家、《世说》,纤细蝟举,犹云抵掌之资尔。若上自圣则,下及艺苑,陆海繁露,何所不有。世儒率以多为解,子艺独手之,禔衡百氏,郁郁乎无遗文焉。又,其著者则阐说时事,引当否,稗实用,即人所讳言,子艺慷慨悲愤,擢发直指儳焉,有击筑弹剑之风。当其宣鬯性灵,时时脱颖,朝而胠箧以出,暮而投箧以入,吹万不同,贤于比竹。凡是者,文学其天性也。综核组织,日以成趣,裦然一代外史云[17]卷首。
明代嘉靖以来的诗坛,风云变幻,潮流涌动,或溺古摹拟,或师心负奇,均未能处理好古与心的平衡关系。书中同时收录隆庆六年庞嵩等著《书一通》也提出:“然拟古者滞于仿模,呈己者沦于肤浅,塞耳填目,无可传者。”[17]765在这样的诗坛语境中,刘绍恤认为,田著备受质疑的“吊诡”,正是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尊古、复古,博取古籍杂家,无所不有;同时,又独抒性灵、别出心裁,激情慷慨地阐说议论,兼具文学之性与外史之趣。针对文坛时弊,田氏笔记小品所具有的博雅嗜古又独标心评的特点,就成为兼取复古、性灵之利而避其害的最佳模范,标示着文学发展的重要取向。
这种取向落实到诗学批评方面,即是将诗与经、史打通,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破除藩篱,通达而观。崇祯十三年(1640年),王锡琛为《诗归》所作序文中就旗帜鲜明地弘扬“以诗为经”、“以诗为史”。序云:
钟、谭两先生取三百以前之诗,以迄于唐,为卷五十一,秉笔而出入之,直则归经,断则归史。一字褒贬,其难范类《春秋》。眼明手捷,古人隐怀,一笔刺入。虽马、郑传笺,子夏《诗小序》,其严峭或过之。钟、谭之《诗归》,诗而经矣。论诗必论情与事,及其时代,风会高下,纸上悲嬉,颜面若接。钟、谭之《诗归》,诗而史矣。今学士家,类能读经史诸书,而置诗学不问,则知钟、谭之为诗,不知钟、谭之为经史也。吾度其不能读钟、谭之诗,不知钟、谭之为经史也……吾愿读诗者以钟、谭为归,而读钟、谭者,以经史为归[2]卷首。
可见明末诗家对古诗的理解和接受,已经完全持一种开放性态度,不拘限于诗学批评的视角。融通经史的批评视点,不仅代表着博达通阔的学术视野,更是复古思潮与性灵思潮合流的产物。
关于《玉笑零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是书皆采取新奇故事,纬以俪语,凡一百二十八条。其中如以尧舜之让天下为爱身,不与朱均以天下为爱子,舜禹之受天下为不知害;铸鼎为镇厌之术,金縢为诅咒之媒,皆纰缪之甚者。”[18]以其非议圣贤、批评典制为谬,而这一点恰是晚明古诗评选的一大特点。《古诗归》以诗为经史,臧否历史人物,评说是非善恶,注重剖析圣贤、豪杰的所作所为,刺中隐怀,如最早见于杨慎《风雅逸篇》的《贾子引黄帝语》,《古诗纪》更名为《太公兵法引黄帝语》,《古诗归》又更名为《兵法》,《古诗类苑》《古诗解》皆依循和《古诗纪》的题名和体例,列为“谚语”类第一条,而唐汝询对钟惺评语存有异议,释云:“此言事贵慎于早,防之于微,一失其时,必将为人所制;几微不察,后将无可奈何。理有固然,故特揭以为戒。或疑圣人藏杀机,误矣!”[13]卷三末句正是针对钟评“防微慎渐之语却藏杀机。古圣贤如黄帝、太公皆是狠人。”[5]卷一又引用钟氏评语:“钟伯敬曰,语语是先发制人。黄帝用先着,老氏用后着,作用机权则一。”[13]卷一
钟氏并非意在颠覆圣贤的经典形象,揭示普世性的慎戒之理外,引导读者向“真圣贤”的境界提升。评唐尧《戒》:“要知真圣贤忧勤语,与黄帝语同旨异。”[5]卷一评虞舜《帝载歌》中“迁于贤善”云:“大圣贤作奇事,未有不顺人情者。四字便是揖让、征诛之本。所以异于操、懿、温、莽者以此。”[5]卷一圣贤之“忧勤”“贤善”等种种作为,代表着个体心性修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作为小品文和选本共同关注的焦点,不仅承载着钟惺经世、出世的人生理想,也投射出晚明士人共同的心理情结。如钟惺《告雷何思先生文》篇中云:“先生负盖代之才,与志、与格、与识、与气骨,以圣贤豪杰自任。其于经世、出世、度世,处处着脚,无不以为立可就。”[16]548叙其座师雷思霈便以圣贤豪杰自期。注重慧业修持的袁中道也表示:“狂者,是资质洒脱。若严密得去,可以作圣。”[19]早在正德戊寅(1518年)韩奕为杨慎《风雅逸篇》作《后序》就提出:“人不皆圣贤,至其言或喜或乐……及其归,皆不越乎彝伦日用,是亦圣贤之徒,而选风雅者所不弃也。”[4]85先秦歌谣与谚语皆寄寓至理,教人知行,虽然言者不是皆为圣贤,所言者却符合圣贤之道。逸诗谣谚的编集、阅读和接受,实际上就是一种朝圣的行为,一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洗礼,表现明人对成圣的向往。如果说,治学博雅,以复兴古道、宗经为旨归,是明代学术经世致用的路径之一,于个体心性而言,实现成圣、征圣的人生修为,则是一体两面的另一治学理想。《古诗归》以诗为经、史,对谐隐类话语的评点,正是兼具这两种期许。
综上所述,博雅风气之下,明人复古、宗经又博洽渊通、个性飞扬,并未固守学究式的解经,或一味追求大而全。立足于跨界流通、多元交叉的学术视角,以经世实用、修心成圣为鹄的。中、晚明选家突破前代古诗选集的固定模式,扩大古诗来源,广泛收罗谣谚、箴铭等谐隐类诗作,并以诗为经史,宣畅性灵、独标心解,与箴言体小品交互影响、融通,构建出鲜活生动的文学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