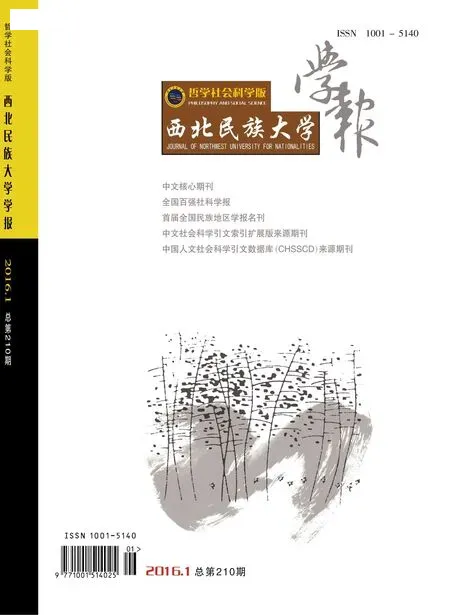蒙元时期蒙古文应用文翻译述要
2016-02-19金玲
金 玲
(西北民族大学 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蒙元时期蒙古文应用文翻译述要
金玲
(西北民族大学 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蒙古文翻译实践活动中应用文书翻译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为促进不同历史时期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译史的研究多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入手,鲜少涉及应用文体。本文分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章节,总结概述了蒙古文应用文翻译在这两个时期的历史沿革及硬译体形成的具体原因等,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致使专家学者加强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蒙元;应用文翻译;述要
应用文体是社会大众在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中为处理公私事务所常用的具有直接使用价值和某种固定程式的各类文章的总称。是操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进行思想交流、情报互通、问题解决和事务处理的实用性工具。我国应用文体的使用由来已久,和文字同步,大概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了。据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具有了原始应用文的雏形。经过了春秋战国的萌芽期、秦汉的初步成形期、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唐宋的成熟期等,到了元明清时期趋于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应用文体的实际社会使用价值,曾多次进行改革和规范,为应用文体种类的完善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国内应用文体的外汉翻译研究涉及面广,论著颇丰,成绩喜人,已基本形成体系,可为民族语文翻译提供有益的借鉴。下面以蒙元时期蒙古文应用文体翻译历史沿革综述与探析为例,以期揭开蒙古文应用文翻译的原始面纱。
一、大蒙古国时期
蒙古族很早就熟悉并掌握了各类应用文体的写作与翻译技巧。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在蒙古诸部就已经存在口授的命令,为了便于记忆和传递,多由押韵的韵文形式构成,可将其视作蒙古文应用文体的雏形。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结束了长期混战的社会动荡局面,建立了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为了巩固统治采取推行千户制、分封子弟贵戚、推广怯薛、建立也可扎鲁忽赤、编订大扎撒、创制蒙古文字等措施,初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的各项政治和军事制度,为大蒙古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族源、生产发展水平、语言等各异的不同部落统一在汗权的统治下,逐步形成了具有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蒙古民族共同体。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蒙古族与多元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蒙古族统治者为推动蒙古族社会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进行有效交流,保障各类信息和政令的畅通无阻,文字的创造和翻译活动的展开是首当其冲,势在必行的第一要务。1206年成吉思汗下令以畏兀儿字为官方文字,借以译写一切异族典籍,打破了宋人徐霆所说:“鞑人本无字,然今之所用……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则用汉字”的局面。在此背景之下曾两次颁布成吉思汗的《大扎撒》,即法令,可视作开启了用畏兀儿字译写法律类应用文书的先河。据《世界征服者史》载,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儿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1]。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2]。《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3]。
此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经过长期的东征西讨灭掉金国,征服了吐蕃和大理,又通过数次的西征吞并了中亚细亚以及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州的蒙古帝国,下设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犁等四大汗国分别统治着所征服的地区,又同时受制于中央政府。在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内有不计其数的东方,中亚,包括俄罗斯以及东欧在内的风俗迥异的民族,操着特点各异的民族语言,往来穿梭于各地,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畅通无阻的碰撞与交流。大蒙古国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等四位大汗,历时53年。在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历程中,应用文书翻译的存在为上传下达和沟通交流的有效进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桥梁媒介作用。同时应用文书翻译活动自身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褪去雏形的稚嫩,逐步形成最初格局。据史料记载,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有些口授的命令和大扎撒是用波斯语译介的。此外,这期间可考的应用文体翻译主要涉及公文和书信文件,换句话讲就是官方文书和个人书信等,多涉及外交政策、法律或经济方面的内容。如,蒙古族最早的外交信函是贵由大汗于1246年致罗马教皇的两封答书。公元1241年,蒙古铁蹄挺进至西烈西亚和匈牙利境内,因大汗窝阔台的死讯传来,蒙古军返,西方基督教国家得以喘息。公元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携带国书前来,请求蒙古人在欧洲境内停止杀戮。柏朗·嘉宾于公元1246年,即定宗元年二月到达,十月带回定宗贵由大汗的复信[4]。此复信由镇海、哈答和八剌等三位大臣译为“回回”语,即波斯语。
二、元朝时期
忽必烈于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结束了诸多政权分裂并存的局面,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空前统一的国家,史称“大元”。大一统的局面促进了横跨欧亚的统治版图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碰撞。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无可避免的与中原汉文化和西藏吐蕃佛教文化等有了接触、了解甚至相互利用以巩固政权。这给元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为了使幅员辽阔的国土内上传下达的顺利进行和保障各类信息和政令的畅通无阻,元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们通过长期而卓绝的努力采取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来完成大量的翻译工作。
(一)促进翻译事业发展的措施
首先,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定为国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降旨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并同时命:“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应出给札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5]意即一切官方文书,含奏章和奏表等必须以巴思巴文为原文,另附汉文或其他语言文字为译文。
其次,设立译史和通事,为满足翻译之所需。译史为笔译者,分为蒙古译史和回回译史。蒙古译史负责将中央下达的或由地方和某些部门向中央和皇帝呈报的公文、奏章、材料等应用文书译成蒙古文字,以供皇帝审阅或蒙古官员执行。回回译史则是专门为色目官员服务的。其职责是将公文、表章、报告、表册等应用文书译成“回回”语,即波斯文字,供色目官员照办。设置情况与蒙古译史同,但名额少于后者。此外,还设有从事口译的通事,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而进行口舌通传。由于通事常伴各级各类各地区官员左右,其作用便大于译史。有时,通事还常作为官府代表办理公事,或出职当官,地位较译史高。
再次,在中央设立专为皇帝服务的翻译机构和官职。分别为蒙古翰林院、内八府宰相、艺文监等翻译机构和经筵译文官、扎尔里赤等官职。其中蒙古翰林院的职责范围是负责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内八府宰相掌诸王朝觐傧介之事,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同译写而润之。内八府宰相和蒙古翰林院的任务有所交叉,互为帮衬。艺文监设于天历二年(1329年)。专司以国语敷译儒书,及儒书之合校、镂刻和印刷等工作。经筵译文官,负责为帝王翻译和讲解儒家和佛家经典,特别是对安邦定国有助益的政书类经典的翻译。扎尔里赤,又称扎鲁忽赤,例如“谙都剌……通经史,兼习诸国语,成宗时为翰林院扎尔赤里,职书制诏”[6],是大断事官。这些专门为皇帝服务的翻译机构同时也是管理机构,翻译机构内的官员同时也具有译史或通事的双重身份。这种客观事实,使得元代的翻译活动处处以皇权的巩固为出发点及归宿点,也是元代一些公文文书翻译出现硬译体的直接诱因。
最后,多途径、不拘一格地培养选拔和招纳翻译人才。元代翻译人才来源的首选途径是设专门学校进行培养选拔。在秉持推行蒙古化,同时加深汉化的双重教育政策下,设立了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和汉文国子学等一系列蒙古本民族的中央和地方官学等。元代提倡尊孔崇儒,因而儒家经典成为学校课程及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不仅重视中原文化的教育,也非常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教育模式。这一特殊教育模式的形成,无形中为蒙古文翻译培养了通晓蒙古文、汉文、波斯文、藏文等多语人才,从而推动了蒙古文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各类官员,为中央集权统治力量的加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招纳,是元代翻译人才来源的次要途径。即从民间隐士、自学成才人士或被占领地区的语言人才中进行招纳等。
(二)应用文书翻译范例
元代所译应用文书分为下行文书,上行文书和平行文书三类。下行文书涉及诏书、制诰,令,符等。上行文书有表,奏,启等。平行文书则涉及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公务的各类官方文书,信函等。这对于中央政府,四大汗国和各类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保障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不二法门。此外,元代所译应用文书还涉及适应社会生活需求的书,记、规、志、序、跋、铭、谥、碑文、祭文和各类契约等多种文本。现选其要者分述如下。
1.诏敕
在元代这个君主高度专制的王朝,皇帝发布的命令属于国家最高决策,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凡遇如重大典礼,赦宥、政治兴革、大征伐、人事任命和大诛罚等国家大事时,必有圣令的下达。以皇帝名义颁行的名目繁多的此类命令被专称为诏敕。元诏敕类文书内容涵盖较广泛,大致由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等四类组成。其中,诏书和圣旨是比较重要的两种形式。关于诏书和圣旨《经世大典序录》云:古者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时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润,其来尚矣。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谨列著于篇[7]。可见,圣旨是以蒙古文记录皇帝的命令,诏书则由翰林国史院的文士用汉文起草并修润的。现存元代诏书主要散见于《元史》本纪,《元典章》卷一及新集《诏令》;《元文类》卷九《诏赦》;《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五《诏》、卷六《诏赦》[8]等。由于当时“国字”八思巴蒙古文在官方文书中的大范围应用,元代诏敕普遍用至少两种文字颁行。从翻译角度分析,要么先撰写汉文原文,再译成八思巴蒙古文;要么先起草八思巴蒙古文原文,再译以汉字或其他文字等。用八思巴蒙古文翻译汉文时,又存在音译、意译等两种不同翻译形式。这都致使诏敕颁发过程变得极其复杂,因而分别以蒙古翰林院为主,以内八府宰相和扎尔里赤为辅,同时负责诏敕的翻译事务。此后,元朝历代皇帝凡遇诏敕颁降,都必用“国字”八思巴,再以汉字等其他民族语言文字作为译文而附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定例,这侧面反映出蒙古族统治者不愿循规蹈矩地简单承袭汉法、强烈寻求自成一派的气魄。从而也为我国古代诏敕制度的历史演变乃至于诏敕多文种互译的研究增添了新气象。
2.奏章、公文和信件
元代在处理朝政的公私事务过程中,凡遇圣意下达时需翻译诏书和制诰等诏敕类文书。而遇有下情上达圣听时则需翻译奏章、官方文书和信件等。
首先,由于元朝历代皇帝及蒙古大臣多不识汉文,如遇有中原汉地政务亟待处理者汉族大臣必有表奏。因此汉族大臣所上奏的表奏等必须经过翻译,再呈御览。这对于下意的上达具有积极的桥梁媒介作用。据《元史》卷102《刑法志·职制》载: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应出给札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9]。由此可见元代对其翻译重视之程度。
其次,公文和书信文件的翻译,换句话讲就是官方文书和个人书信的互译,多涉及外交政策、法律或经济方面的内容。元代公文翻译可考之例甚多。如,《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为《尚书》,意为上代之书。据载《尚书》为孔子所汇编的上古时期的历史文件。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细究其所录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更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如其所录“典”为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记录了君臣谋略;“训”为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和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影响深远。既如此,元代统治者也晓其价值,乐于借鉴。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忽必烈问徐世隆尧舜禹汤的故事,他据《尚书》所载内容作答。世祖要他将《尚书》直接进读。书成,由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徐世隆传》)。这是《尚书》改写本的翻译。其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曾诏令元明善节译《尚书》中有关政要的部分。元明善集贤直学士文升一同译润。译毕,每上奏一篇,仁宗都称好不已。此外,有些元代公文翻译的史料是以碑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的。如,照那斯图先生在其《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10]第二册中搜集了元代文献包括皇帝圣旨、皇后懿旨、太子令旨、帝师法旨、碑刻、书页等40种。其中公文类有27件,与宗教有关的3件、牌子类4件、书籍类2件、其他散类有4件。27件公文中19件被刻在碑上,其中12件被译为元代白话文,未经刻印保持原貌的有8件,其中2件面向汉地、6件是面向藏区颁发。这些公文被译成汉文时,内容形式和年代基本上忠于原文。再如,蔡美彪先生在其《元代白话碑集录》[11]中收录有近百个碑文。按年代先后顺序来看,这些碑文自1223年至1366年,时间绵延143年之久。主要是元朝历代蒙古统治者们向北京、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云南、江苏和湖北等十几个省市以及它们的下属地区和寺庙颁布的各种指令。从行文上来说,这些碑文均自蒙古语原文硬译而来,文字拗口很难通读。这些碑文上的纪年法的翻译说明蒙古族人在统治中原后的一百多年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向所有的属民、特别是向人口众多的汉族人民下达政令时,不得不考虑对方的文化与风俗习惯,进而进行翻译,以保障政令的顺利贯彻。
信函翻译方面,最早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曾派景教徒带着书信、礼品、钱币,去耶路撒冷朝拜圣地,途中又受伊利汗国国王之托,首先到达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后又见到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信函方面可考者元代另有两封外交信函,即1289年和1305年致法兰西国王子菲利普四世的信。这些信中含有关于联合远征近东和建立友好关系方面的内容。1290年和1302年给罗马的两封信中提到征服吉尔吉斯坦及要求跟教皇联军对付他们的敌人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之事。这说明了蒙古统治者强有力的外交关系。
3.政论典籍
所谓政论典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论文书。元朝统治者为求统治中原地区的“御民”之术,命人译写了不少古代帝王安邦治国的方略。如,《贞观政要》《帝范》《忠经》《帝戒》和《帝训》等政治文献。《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曾命察汉译《贞观政要》进献,仁宗非常高兴,诏令缮写若干份,遍赐大臣。文宗图帖睦尔时期又诏令奎章阁学士院以国字译《贞观政要》,锓版模印,赐以百官。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时,曹元用又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帝范》系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论述人君之道的一部政治文献。也就是现代的政论文。该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分上、下两卷,收文12篇。文章言简意赅,论证有据,凡“帝王之细,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命察汉译《帝范》和《忠经》。《帝诫》是但泽和许敬忠二人编写以备经筵进讲的。泰定帝命译此书以进。《帝训》本是汉文本《经世大典》的第二部分,辑录了元代文宗以前诸帝的言论教诫。泰定帝命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和许敬忠合译此书,改名《皇图大训》,“敕授皇太子。”[12]此外,泰定帝三年(1326年),诏令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世祖圣训》,以备经筵进讲(《泰定帝纪》)。
4.法令文书
元代应用文体翻译中还涉及法律、法令类文书的翻译,这对于保障政令畅通和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元典章》。《元典章》全名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共60卷,另附《新集至治条例》,作者佚名。是一部政书类的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下迄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二年(1322年)。内容包括皇帝圣旨、诸王及后妃令旨、元廷庙议记录、朝廷条画、省台文件和各种具体案例。其所涉及的范围,涵盖元代政治、制度、监察、法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生活、农民起义以及中古汉语史、翻译史等诸多方面。《元典章》内所录公文都是当时人记录的原始文献,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说都是第一手的极其珍贵的档案史料。所收文件时间,从蒙古蒙哥汗(元宪宗)时到元英宗朝。《元典章》全书所收公文数量共2 637条*《圣元名贤播芳续集》是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一部元文选集,共六卷,洪武六年高丽刻本,国内未见流传。参阅周清澍,元代汉籍在日本的流传与翻刻[M].;载氏,元蒙史札[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元典章》文体独特,是使用元代白话口语硬译蒙古语的一种特殊硬译文体。此特点在其所收录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等的翻译方面尤为突出。如,存在像“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等这样语法怪异的词语或句子,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产物。这种奇特文体是由于元朝翻译活动之初译者对于蒙汉双语的掌握程度低,驾驭能力有限导致的。加之被翻译的文本大多是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等官方文书,译者不敢有半点疏忽,翻译时诚惶诚恐。为了避免出现纰漏而采取这样的极端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度屈从于蒙古文原语,机械地记录蒙古文的词、词义、词法、句式以及语法等,几乎完全打破了译语,即汉语的语言规范,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到的硬译体形式[13]。此外,元代统治者为使政令畅通无阻,在被统治地区传达皇帝,后妃,太子皇子和国师等的旨令时有时会采取立碑刻文的形式。这有利于各类令旨的悠久保存,以期其威慑力永驻。元代碑铭有蒙古畏兀字碑和八思巴蒙古字碑两类。如,蒙古畏兀字碑有内蒙古翁牛特旗的1335年《张氏先茔碑》及1338年《竹温台碑》、甘肃武威1362年《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等,均为蒙汉文对照,蒙文系据汉文原文意译而来。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额尔德尼昭的1342年《兴元阁碑》断石,全刊蒙古畏兀字蒙文,也自汉文译出。八思巴蒙古字碑现存约有30余种,内容均为保护佛寺道观产业及减免僧道赋税差发等事宜[14]。碑文多为八思巴蒙古字与汉字合刻,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系文书原文,汉字据蒙文译出,以汉语元代白话体直译原文文义,多属硬译体。此外,据西北黑水城遗址出土蒙汉文献来看,元代应用文书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还涉及契约,条据,婚书,合同,讼词,状,符牌,印章和钱币等众多内容。相信随着文献研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证明这些方面是否存在双语互译情况,将为蒙古文应用文书翻译提供一手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世界征服者史[M].汉译本上册,28.
[2]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M].柯九思《宫词》注.
[3]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1929.(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C].第1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218,210.
[5]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395.
[7]宋濂,元史·本传[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3747.
[8]元典章(大元圣政国朝典章)[M].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11.
[9]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395.
[10]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平成2年.
[11][14]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4.
[12]苏天爵,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帝制[M].
[13]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70-73.
(责任编辑包宝泉责任校对包宝泉)
RSummary of 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Mongolian Writings in Periods of Mongolia and Yuan Dynasty
Jin Ling
(School of Mongolian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writings is very important in Mongolian translation. It ha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society in different periods. However, translation history usually starts wit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seldom covers practical writings. Focusing on the two periods of Great Mongolia and Yuan Dynast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d the reasons why literal translation came into being so as to gain the attention of academy, and hope top scholars will enhance and perfect the study of this very field.
[Key words]Mongolia and Yuan Dynasty; translation of practical writing; summary
[作者简介]金玲(1979—),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蒙汉翻译。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蒙汉应用文翻译研究”(项目编号:31920130071);西北民族大学本科教学建设精品课“应用文翻译”(项目编号:BJPKC-1060320302)
[收稿日期]2015-09-16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1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