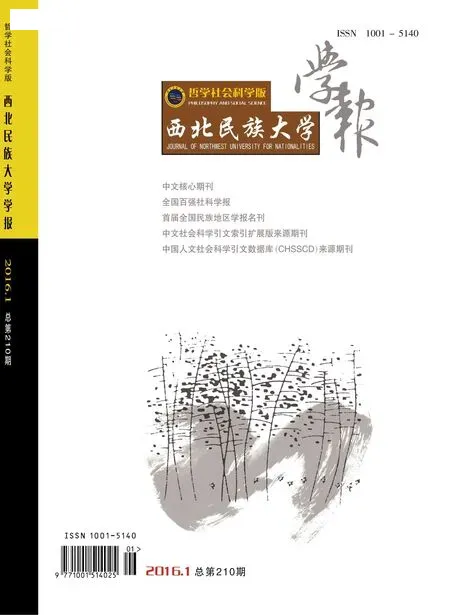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016-02-19张平
张 平
(西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张平
(西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摘要]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贫困变动;减贫成效;扶贫
一、引言
中国的扶贫事业是在强烈的发展愿望与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其力图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时实现后工业化和共同富裕的双重跨越,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道路。这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探索时期,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目前的扶贫模式多为自上而下的行为,即政府主导在先,贫困人口参与在后,在实践过程中扶贫目标定位于区域性反贫困(如“整村推进”),且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近年来西部多数省区的年均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以上,但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减贫速度落后于增长速度、脱贫人口再度返贫等问题仍然存在。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还受到民族文化、习俗、传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减贫成效更是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贫困认定标准的提高(2011年新定标准为2 536元)和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基数不断加大(根据国家民委统计,2011年西部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总数约为3 917万人,占全国比重的32%;贫困发生率为26.5%,高于全国水平13.8个百分点),扶贫开发的成本和难度也将日益增加。在新的扶贫形式下,需要对扶贫的模式和措施展开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近期,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否有减贫成效,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Dollar & Krarry,2002[1];Ferreira,2003[2])。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哪些因素发生作用?是否需要尽可能做更多的工作?随着单一因素的影响被确定下来,其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如何?什么是关键组合?此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
二、增长部门构成的减贫成效
大量的跨国分析认为减贫成效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Loayza & Raddatz,2006[3];Christiaensen & Demery,2007[4])。
Ravallion & Datt (2002)[5]利用印度跨时期的地区数据,按照不同的经济增长与初始条件的部门组合,考察了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影响。研究认为贫困对农业产出的弹性在各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非农业产出有显著差异,其差异对于整体贫困率的下降尤其重要。在较高的人口素质、较多的农业产出、较好的农村生活水平、较低婴儿死亡率地区,非农业增长进程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
Suryahadi et al.(2009)[6]利用印尼的数据研究发现,农村服务业的增长降低了所有部门和场所的贫困。然而,城市服务业的增长在大多数行业对减贫影响最大。农业增长大大地降低了农村地区贫困。在农村地区农业增长在减少贫困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服务领域的增长,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会加速消除贫困。
Ferreira et al.(2010)[2]考察了巴西1985年至2004年期间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情况。研究发现减贫效果存在跨部门、区域和时期的显著性差异。服务部门增长的减贫效果大于农业或工业。工业增长的地区间差异来自于人口发展和工人权利初始状况的不同。由此,经济增长在巴西减贫中扮演着很小的角色,而恶性通货膨胀的治理(1994年)、社会保障和援助的扩大、1988年宪法的大部分授权是贫困全面减少的主要原因。
Montalvo & Ravallion(2010)[7]使用一种新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认为这一过程在各部门和地区间是很不平衡的;初级产业(主要是农业经济)是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点与印度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外, 大量的研究围绕农业发展的减贫成效展开:
Datt & Ravallion(1998)[8]利用一组1957到1991年的国家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业技术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状况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Dercon(2006)[10]分析了1989年-1995年间埃塞俄比亚实施经济改革后村庄的贫穷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贫困显著下降,但在不同村庄的经验有所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是相对价格的变化,还包括土地、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地理位置。这种观点被理论研究(Loayza & Raddatz,2006)[3]以及实证研究结果(Thorbecke & Jung,1996[10];Sumarto & Suryahadi,2007[11];Christiansen & Demery,2007[4])所支持。
Quizon & Binswanger (1986[12],1989[13])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利用局部均衡市场模型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农业增长带来的绿色革命对减少农村贫困没有好处。进而,他们认为减贫的主要方式是提高非农收入。同时,Warr & Wang (1999)[14]的研究也认为台湾的农村减贫成果也主要来源于工业增长的贡献。
也有研究认为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减贫效应是相同的。Foster & Rosenzweig (2005)[15]使用印度1982年-1999年期间农村家庭面板数据,用于实证评估农业生产力改进和乡村工厂扩张对农村收入增长、减少贫困和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农业技术变革和工厂就业增长增加了农村收入和工资,并因此减少贫困。Warr (2006)[16]认为增长的服务和农业部门对东南亚四国减少贫困的影响最大,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
三、多种因素初始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一)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
在给定的平均消费水平下,消费构成决定了贫困状况。但是是否初次分配也关系到随后的减贫率?大量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不平等可以阻碍增长(Aghion et al.,1999)[17]。一种有争议的解释是:信贷市场失灵,意味着穷人无法捕捉投资机会。贫困人口的比例越高,增加了信贷的紧张,经济增长率越低。除了对增长率的影响,高的初始不平等也用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经济增长率在一个地区的减贫效果不如另一个地区有效。通常,任何对于由平均分配引起的贫困弹性的测量,取决于其他要素的分布情况。这些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很难去定义。然而,可以预计在经济平等情况下,贫困人口往往会获得较高份额的增长收益。跨国数据分析也支持较高的初始收入不平等会导致较低减贫效果(Timmer,1997[18];World Bank,2000[19])。财富分配可能影响到穷人分享经济增长的程度。事实上,信贷市场失灵的论点可以用于解释由初次分配问题关联的穷人资产的增长前景。初始财富的数量越小,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越小。
(二)基础教育水平
低的基础教育水平经常被定义为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来源。教育也会影响到穷人参与非农收益增长分配的多少。近年来,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改革的协同效应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研究主题,典型的例子包括Dre`ze & Sen (1995)[20]对印度,以及Thorbecke & Hong-Sang (1996)[10]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世界银行在减贫中的做法也强调了结合人力资源开发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World Bank,1990[21],2000[19])。
(三)城乡差异
在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和农村部门收入之间差距的程度(Bourguignon & Morrison,1998)[22]。Ravallion & Datt (1999)[23]构造了一个简化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这一模型中,贫困的减少采取了将贫困农业部门人口吸收到非贫困的非农业部门。该模型假定任何农业工人如果有意愿参与非农业部门将产生一个成本。这个成本决定了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均衡收入差别。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成本降低了总产出。但是这一成本也降低了劳动力吸收到非农业部门,从而意味着更高的贫困率。此外,部门间的工资差距也使得减贫效果较差。较高的初始工资差距(反过来意味着较高的初始贫困率),在给定非农业经济增长率下,减贫的比率更低。可以说,二元经济限制了减贫的前景。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不发达制约产业化前景。要素市场扭曲也需要通过非农经济增长来减少城乡不平等对减贫的阻碍。例如,在Harris & Todaro (1970)[24]的经典模型中,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固定于市场出清水平,虽然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存在着流动性,但是转向城市的农业工人不是都能找到新工作,于是他们将面临失业,或转向相对较低收入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市场二元程度越高(通过跨部门的工资差异衡量)意味着更低的增长和穷人的受益更少。
最初在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的人口分布同样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通常,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生活份额的变化将使洛伦兹曲线变动。这一影响在理论上含糊不清。例如,在库兹涅茨假设条件下,在或低或高的城市化水平下,不平等都会很低(Anand & Kanbur,1993)[25]。
(四)城市化水平
利用市场扩张,城市化经常被视为一种促进农村非农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企业很可能被吸引到这些地区,因为较大的地方产品市场、熟练的劳动力、更广泛品种的生产投入、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以及更好的基础设施(Lanjouw & Lanjouw 1997)[26]。可以认为,在平均产出增长条件下,这些因素也会影响贫困问题。合理的解释是,穷人在市场准入和基础设施方面,比富人有更多的限制,穷人更倾向于宽松的条件。假设城市化水平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市场准入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可以预见,穷人生活在一个更加城市化的地区将会在非农业增长时受益更多。而另一种争议是,更高的初级城市化水平可能导致已经富裕的城市中心非农业增长的进一步集中,因此可能抑制减贫成效(相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分布更加均匀)。初步城市化的整体影响,对于减贫平均产出的弹性,可以是正的或负的。
(五)非收入因素
减少收入层面贫困并不能保证减少非收入层面的贫困,如教育或健康等。因为贫困是个多方面现象,只使用单一指标实施扶贫是不正确的(Kakwani & Pernia,2000)[27]。Grosse et al.(2008)[28]利用1989年至1998年玻利维亚的数据,以增长发生率曲线、Ravallion-chen减贫率和财富均衡增长率作为研究工具,研究了个人和综合性的非收入成就,如教育、死亡率、疫苗接种、发育迟缓、和多层面的福利措施等非收入指标的改善是否有绝对或相对减贫的意义,以及它们是否更有利于贫困人口。
四、减贫的非均衡性与测度
Ravallion & Chen (1997)[29]通过对67个国家的考查发现,1981至1994年间减贫效应非平衡的变化与增长率无关,意味着贫困下降与平均收入高度相关。他们估计了贫困发生率(按每天一美元计算)对于平均家庭收益的弹性是-3。Ravallion(2001)[30]进一步在误差纠正后,重新计算出的弹性为-2.1。
Dollar & Kraay (2002)[1]通过对4年、92个国家构成的样本分析,发现20%的最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率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利用较大范围的样本,Worldbank(2005)[31]发现52%的差异可以归结于增长。利用对于穷困测量差别和范围的分析,Kraay (2006)[32]发现总体上46%至70%的人口能够分享到增长收益,在长期将处于71%~97%之间。
Richard & Adams(2004)[33]利用来自60个发展中国家的126个时期的数据分析了贫困的增长弹性,即在给定比例的经济增长中,究竟有多少百分比的贫困下降。减贫的比率取决于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定义。当控制了收入不平等因素后,经济增长以平均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增长弹性是2.79(包括东欧和中亚),即10%的平均收入增长将减少27.9%的贫困人口(按人均每天1美元)。但是当经济增长按人均GDP测算的话,贫困的增长弹性是2.27,低于之前的预测。
Machiko & Erik(2006)[34]研究了全球化进程对穷人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成长”渠道,即开放、增长的不平等与贫困的因果链。在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从区分生产要素流动、技术变革和扩散、全球化对波动性和脆弱性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全球性通货紧缩,以及政府机构角度的研究,认为全球化将带来一个因果链,即“开放—增长—非均衡—贫困”。
Edward(2006)[35]分析了从1993年到2001年全球消费分布。认为增长的一半在全球消费发达国家人口中受益,其他的主要受益人是中国。在其他地区,贫困人口人均消费的增长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经济增长有助于穷人,但它对富人更有利。分析表明,依托经济增长速度来消除贫困是相当低效率的;更直接的国家介入似乎更有效。
大量的研究认为:在不同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单位增长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是非均衡的。虽然穷人通常能够从增长中受益,但是其收益与平均收益仍然有所差别。贫困变化差异分析取决于测度选择的样本情况和分解方法。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能够从总体富裕中获益,从总体收缩中损失。但是有从多少贫困人口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在国家间有很大的不同,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也有所差异。由于跨国间数据的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微观实证研究(Ravallion,2001)[30]。
五、简评与启示
关于发展与公平、增长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始终充满争议。其实质在于对库兹涅茨倒“U”假说成立条件的满足:其一,经济体的自发调整是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其二,政府是否有能力对经济进行有效调控;第三,经济增长是否在一个长周期中衡量?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贫困变动总是基于上述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
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也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以上理论综述为中国减贫事业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第一,贫困人口多居住在偏远地区,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缺土、缺水、生产生活极其艰难。大多数地方以“农本经济”或“粮食经济”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二、三产业比重低,传统产业、传统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缺乏竞争力,经济效益差,增收途径少、难度大。多数贫困地区资源贫乏,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的科技文化水平低,就业机会少,剩余劳动力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此外,还受到宗教、民族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区域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等诸多要素共同制约着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中国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以来,贫困人口快速减少,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脱贫人口数量的逐年减少和扶贫投入的不断加大,扶贫成本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还一度出现贫困人口总量不降反升的现象。回顾反贫困历程,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将扶贫目标定位于区域性反贫困。这一举措,在大面积“普贫”的背景下,确实能够提高扶贫效率、减少扶贫成本,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区域内减贫的非均衡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第三,由于贫困人口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同,其经济增长和贫困群体状况也具有异质性,需要结合各贫困县区的具体情况展开针对性研究。从大量的研究实践看,这种针对性研究不仅对于国别研究是适用的,而且对于一国(或地区)内部不同区域分析也同样是适用的。只有将贫困问题置于具体环境之下,才能得出合理、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Dollar & Kra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Journal of Economic Gowth,2002,7 (3):195-225.
[2]Ferreira, Leite & Ravallion.Poverty reduction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Explaining Brazil's poverty dynamics, 1985-2004[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3 (1):20-36.
[3]Loayza & Raddatz.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matte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07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6.
[4]Christiansen & Demery.Down to Earth: Agricultur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Z].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7.
[5]Ravallion & Datt.Why has economic growth been more pro-poor in some states of India than oth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 68),PP: 381-400.
[6]Suryahad, Suryadarma & Sumarto.The effects of location and sectoral componen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pover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89(1): 109-117.
[7]Montalvo & Ravallion.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0, 38(1): 2-16.
[8]Datt & Ravallion.Why have some Indian states done better than others at reducing rural poverty[J]. Economica,1998, 65(257): 17-38.
[9]Dercon, S. Economic reform, growth and the poor: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81(1): 1-24.
[10]Thorbecke & Hong-Sang.multiplier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analyze poverty allevi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 48 (2): 279-300.
[11]Sumarto & Suryahadi.Indonesia country case study[Z].In: Bresciani & Valdés (Eds.), Beyond Food Production: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Edward Elgar, Cheltenham.2007.
[12]Quizon & Binswanger.Model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growth and government policy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Indi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1986,PP: 103-148.
[13]Quizon & Binswanger.What can agriculture do for the poorest rural groups?[Z]. In: Adelman & Lane(Eds.), The Balanc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Effects 4.1989.
[14]Warr & Wang.Poverty,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Z]. In: Ranis & Hu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Develop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 Essays in Memory of John & Elgar, London.1999.
[15]Foster & Rosenzweig.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inequality[Z].Brow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mimeo.2005.
[16]Warr, P.G. Poverty and growth in southeast Asia[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3,2006,PP: 279-302.
[17]Aghion, Caroli, & Garcia-Penalosa.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 37 (4): 1615-1660.
[18]Timmer, P. How well do the poor connect to the growth process? [Z].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imeo.1997.
[19]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ttacking Poverty[M].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2000.
[20]Dre`ze & Sen.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M].Delhi: Oxford Univ. Press.1995.
[2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overty[M].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1990.
[22]Bourguignon & Morrison.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ualism[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 57 (2): 233-257.
[23]Ravallion & Datt.When is growth pro-poor?Evidence from the diverse experience of India’s states[Z].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 2263.1999.
[24]Harris & Todaro.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 60(1): 126-142.
[25]Anand & Kanbur.The Kuznets process and the inequality-development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 40(1): 25-52.
[26]Lanjouw & Lanjouw.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An Update[Z].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1997.
[27]Kakwani & Pernia.What is pro-poor growth?[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0,18(1): 1-16.
[28]Grosse, Harttgen & KLASEN.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in Non-Income Dimensions[J].World Development, 2008,36(6): 1021-1047.
[29]Ravallion & Chen.What can new survey data tell us about recent changes in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Z].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7,11 (2): 357-382.
[30]Ravallion, M.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J].World Development, 2001,29(11): 1803-1815.
[3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Equity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2005.
[32]Kraay, A.When is growth pro-poor?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0, 2006,PP:198-227.
[33]Richard & Adams.Economic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stimating the Growth Elasticity of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2004, 32(12): 1989-2014.
[34]Machiko & Erik. Channels and policy debate in the globalization-inequality-poverty nexus[J].World Development, 2006,34(8): 1338-1360.
[35]Edward, P. Examining Inequality: Who Really Benefits from Global Growth?[J].World Development,2006, 34(10): 1667-1695.
(责任编辑戴正责任校对戴正)
[作者简介]张平(1977—),男,四川仪陇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研究”(项目编号:71363048)
[收稿日期]2015-11-07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1-01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