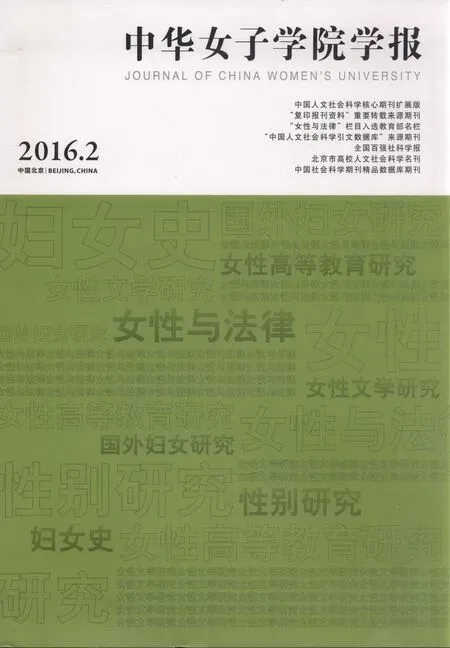从性别视角考察端木蕻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16-02-15陈娇华
陈娇华
从性别视角考察端木蕻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陈娇华
摘要: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重要代表作家,也是一位擅长刻画女性形象的男作家,他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神态生动的女性形象。但由于作者男性中心意识的潜在影响和拘囿,这些女性不是被理想化和神圣化为女神/地母形象,就是被扭曲、变形为尤物形象,或者沦为承载意识形态观念的符码。这既与作者自幼的生活环境及其母亲、萨满教文化及现实复杂斗争形势的影响分不开,也给创作的艺术审美带来了一定的遗憾。
关键词:端木蕻良;女性形象;男性中心意识;萨满教文化
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重要代表作家,以《鴜鹭湖的忧郁》登场中国现代文坛。随后发表的《科尔沁旗草原》《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激流》及《大地的海》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形成了其创作风格的粗犷浑厚与磅礴气势。事实上,端木也是一位擅长刻画女性形象的男作家,王富仁指出:《可塑性的》和《三月夜曲》两个短篇,“充分展示了端木蕻良在女性心理描写方面的不同寻常的才能。”[1]9端木笔下涌现了许多性格各异、神态如生的女性形象,如《科尔沁旗草原》中泼辣好强、伶牙俐齿的三十三婶,《新都花絮》中美丽端庄、冷傲自私的宓君,《早春》中温柔美丽、“像森林中的女王似的”金枝姐,《可塑性的》中娇美哀伤、沉沦迷惘的凤子及《初吻》中温柔漂亮、像画中“古装美女”的灵姨等。她们承载着作者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的情绪体验与审美理想,体现了其对女性生活情感和命运遭遇的深切关注与思考。尤为可贵的是,由于端木受自幼生活环境及其母亲的影响①据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回忆:端木“小时候爱和妹妹在一起玩,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小妹没有了,表妹来了,就和表妹在一起玩。他特别喜欢和女孩在一起,因为从小在女孩子堆中长大,有点像个女的那样文气。他妈妈想女儿,也把他当成女儿一样来养、来打扮。你看他在武汉照的那张相,长头发,长筒靴,他像男,也像女。这个阶段的生活,使他更了解女性,了解了女孩儿,为他写小说中的女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参见钟耀群口述、孙一寒整理:《钟耀群谈端木蕻良家事》,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这些女性身上流露了其难能可贵的性别倒错意识②这里的“性别倒错意识”指男作家具有女性意识,即站在女性角度对女性主体关注、书写和尊重的意识。和女性关怀意识,如《早春》对姑嫂“姊妹情谊”的书写;《雕鹗堡》中代代无视全村人的偏见、歧视,公开向石龙表达好感的大胆与勇敢,以及《新都花絮》中宓君对爱情的主动选择与追求等。但正如埃莱娜·西苏所指出的“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2],端木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其身为男性作家的性别印记。而历来对于端木创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地域文化、创作风格、《红楼梦》的影响及其与萧红创作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相反,从性别视角进行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迄今为止,在“中国知网”上输入主题词“性别意识”所能查询到的论文仅有三篇。这里,笔者拟以端木新中国成立前的小说作品作为案例,从以下三类女性形象身上,考察作者不自觉流露的男性中心意识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
一、审美理想的载体:善良驯顺的女神形象
端木出生于科尔沁旗草原一个贵族大家庭,自幼生活在母亲和使女的关爱与呵护下,喜欢跟女孩子一起玩,而且爱读《红楼梦》,“生就一副女人心”,对女性充满了同情与怜爱,对女性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自然相当熟悉和了解。正如《早春》的叙述者所言:“因为我天生日长在女人堆里,她们有什么事我都知道了。她们有什么都不避讳我,我从她们的话里知道多少平常想像不到的,我从她们的动作里,看见许多别的动物所从来没有过的动作。”[1]219因此,端木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善良、温顺和无私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又可分为三类:一是美丽、羞怯,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形象。这主要出自改编的神话故事,如《女神》中的女神、《琴》中的达芬妮、《蝴蝶梦》中的菠茜珂等。她们美丽非凡,菠茜珂“有蝴蝶般的美丽,灵魂一样的飘逸”,“美丽的名声到处传播着”;琴的“眼睛像春天的星子”,“唇红得像一块红玉”,手臂则“闪着诱人的光”;女神更是“比一切的月亮都美”,是“开了花枝的月亮,笼了轻纱的月亮”。她们飘忽梦幻、美丽迷人,充满诱惑力,引起了许多年轻人的爱慕、追求与渴望。更重要的是,她们有着天使般的纯洁、羞怯和顺从,在她们身上,寄托了男性的审美理想,但“她们只是一种对象性存在,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真实人的生活,她们只是一个美好但没有生命的对象”。[3]66因而只能存在于男性虚幻的想象世界,或者只能活在缥缈的仙界,不食人间烟火。二是纯真、善良,充满母性情怀的大姐姐/小母亲形象。如《初吻》中的灵姨、《早春》中的金枝姐及《雕鹗堡》中的代代都是这类女性。灵姨美丽温柔,像小母亲一样照看和呵护“我”,同“我”一起玩闹。一次起床时,“我”错认她为妈妈,向她歪缠、撒娇,她“用头顶门儿顶着我的头顶门儿,腾出手来给我穿衣服。我便和她打呀、闹呀、揉呀、搓呀……”[1]95一幅生动的母子嬉戏图跃然纸上。《早春》中的金枝姐则像大姐姐般对“我”关爱且呵护备至,以至“我心里想,能够和金枝姐永远在一起玩该多好”。[3]107她帮我挖野菜,为“我”采摘喜爱的黄花,特别是送我回家那一幕,俨然就是一个小母亲形象:“快到家了,她把我的衣服整理了一下,然后把一篮子娇绿的莴菜递到我的手里,然后俯下身来,她的头发热烘烘的蓬松在我的脸上,她要和我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仿佛要和我贴脸,也终于没有贴,便把嘴唇在我拿着黄花的小手里作了一个嘴,便说:‘我看着你进去!’……”[1]114-115三是宽厚、无私,富有牺牲精神的地母形象。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湘灵和二十三婶,《早春》中的母亲和姑姑等。她们善良、无私,有大地般的博大胸怀和牺牲精神,愿意为所爱的人奉献一切乃至生命。湘灵是丁府使女,全身心地照看和爱恋着丁宁,与他偷吃禁果。丁宁走后,她常看他留下的书,想“从书里和丁宁更加接近”。[4]328即便因怀孕被逼自尽,她对丁宁仍无怨言,依然不愿做“不为丁宁所愿意的行为”。[5]336这是一个完全为了爱情没有自我的女性,只知奉献不知索取。二十三婶也是如此,善良软弱,与世无争,“永远是腼腆地驯顺地绝不想在别人身上取得什么,她觉着她是要在妨害着别人的利益了,她就羞怯了,自叹了。她觉得做了一桩极大的罪恶”。唯一希望能有个人真心爱她,为此她“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虔诚的大胆的贡献在他的面前”[4]140,然而丈夫不爱她,周围的人冷落她,最后她孤独的死去。
上述三类女性要么纯真、羞怯,具有天使般的温柔和美丽;要么善良、无私,富有地母般的牺牲精神;要么两者兼具。她们都是作者审美创造的结晶,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这既是作者自幼的生活环境和母亲对其影响的结果,也与东北萨满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关,体现了作者对女性欣赏爱悦的美好情怀。端木自幼生活在女人堆里,母亲和使女对他很疼爱、照顾,他与妹妹们的感情也很好,这些无疑都会潜在地影响着端木日后的创作,影响其对于笔下女性的情感态度与形象塑造。端木曾谈道:托尔斯泰“描写了他的带着爱力的母亲和他的为着爱别人而生活的使女”,他在母亲和使女身上“看见了真正的人类,他走向了她们。而且为她们这一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而成为她们中间的一个”。[5]312某种意义上,端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也可作如是观。同时,据论者考证:满人的“萨满”就是大地的意思。在远古时期,“母亲是一切的开始,所有的生命都需要她的呵护”,她“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就像那生养与哺育万物的大地一样”,她“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是整个家族的支柱”。[6]73萨满教这种崇拜和敬仰女性的母性思维必然也会影响到端木对于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使得她们温柔善良、宽厚博大,具有母性情怀。①有论者指出:“东北作家群就是生长在这样一片充满野性和神奇的大地上,他们在幼年时代大多都目睹多次萨满教跳神的表演盛况,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自然也受到萨满教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千百年来,萨满教精神逐渐沉淀在人们的心理的底层,萨满式的激昂和沉迷的情绪状态也随之延续和泛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参见阎秋红:《“越轨的笔致”》,《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此外,作为一位红学专家,《红楼梦》女性观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应当看到,端木笔下这些善良、驯顺的女性形象与其说反映了女性现实生存的内外两面真实,不如说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及其对于理想女性的想象与期待,是作者潜意识中男性中心意识渗透与影响的结果。作者多次提到要为自己的母亲写本书,1932年曾写有名为《母亲》的短篇小说,而《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也写到母亲的情感和故事等。可以说,对母亲的依恋和崇敬情感导致端木不自觉地对笔下女性的塑造趋向理想化和神圣化,对此,波伏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在纯精神上对母亲表示尊重的年轻男人,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希望女人能享有母亲那种纯洁。”[7]230因而,他不可能真实地写出这些女性隐秘的复杂心理与情感体验。而且端木创作的审美追求也决定其女性形象更接近京派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将女性形象抽象化、概念化为自己审美理想和某种情感情绪的载体。端木谈到,《红楼梦》的立意是要为半世纪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写“真传”,结果却“写的是多愁多恨,发挥的是自家的如痴如狂”。[5]344又说歌子的好,是因为出自生命和灵魂;赞赏年轻女人为沉在河里的丈夫而悲歌,远嫁的公主用歌声传达自己心事,已嫁少妇以词句来感发新的情怀等。[5]310某种意义上,端木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浇灌的,也是自家的审美理想和现实哀情。事实上,《早春》里的金枝姐就类似于《边城》中的翠翠,是作者潜意识中的一个纯真幻影,她美丽清纯却又虚无缥缈,以至于最后竟无从找寻。而《初吻》《女神》《蝴蝶梦》及《琴》等创作于萧红逝世后的爱情小说,也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梦幻般美好却无从把握的爱情理想。《初吻》写的是一种“理想中的美的爱情”,主人公爱的不是灵姨的本体,“而是一个镜像中的存在”。[1]16“在他的意识中,母亲—画像—灵姨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灵姨并不是活生生的独立个体。他对灵姨的爱……主要是纯精神性的,神性的,它纯净、美”。[1]17因此,在灵姨及金枝姐等女性身上“寄予了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怀念之情”,作者“把对萧红的深深的眷念融入笔下那些细腻饱满的美好形象中,以此来祭奠爱妻的亡灵”。[8]至于《女神》《蝴蝶梦》《琴》等取材于神话故事的爱情小说,更是讴歌优美、神性的理想爱情,充满了梦幻、浪漫的神秘色彩,“传达着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怀念和歌颂”。[1]18这些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并非现实女性生存境况和生命形态的写实,而更多是为了承载作者对于亡妻的爱恋和思念情感。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女性理想化和神圣化,即虚构女性神话的倾向泄露了端木潜意识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因为男性作者“通过把女人塑造成天使,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并将这一理想化的歪曲表现以话语的压抑形式加诸现实中的妇女,压制妇女的自由意志,在他们把女人引入艺术品的同时,一种话语的形式压抑着日常生活中的女人,让女人自己也变成了没有自由意志的艺术品。”[3]67波伏娃曾批评这种女性神话倾向,是以把女性放置于概念化的、超自然的观念世界里,来掩盖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女人的真实面貌。而每个女人必须要面对的却是自己的真实存在。因此,“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它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诅咒也显得权威起来。”[9]214这样一来,端木所塑造的温柔美丽、驯顺无私的女神/地母形象显然有可能堵死通往一个个具体真实的女人之路,相反,却强固了男性权威和男权统治,其男性中心意识不言自明。同时,这种对女性理想化和神圣化的倾向也使得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写意化倾向,思想性格比较单薄、抽象,缺乏丰富、立体的情感心理内涵,在形象美学方面不免存在一些遗憾,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二、男性中心意识的载体:妩媚妖冶的尤物形象
端木蕻良小说中还有一类出现得比较多的女性形象——妩媚妖冶的尤物。所谓“尤物”,《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指优异的人或物品(多指美女)。”[10]1521论者也界定为:“‘尤物’更多的是用来指称美丽的女性,特别是给国家带来‘灾害’的美女。”[11]这里的“尤物”,主要指漂亮、性感,敢于突破传统礼教观念,自由地支配或利用自己身体的女性形象。她们既有生活在都市里的新式女性,如《新都花絮》中的宓君、《可塑性的》中的小凤、《三月夜曲》中的波兰女子等;也有生活在大家庭里的少奶奶,如《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三十三婶;还有生活在贫困乡间的底层女性,如《鴜鹭湖的忧郁》中的小女孩妈、《憎恨》中的周磨官媳妇等。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或是情感欲望匮乏,被所爱的人背叛或者抛弃,心有不甘,不能忍受情感的孤寂或情欲的缺失,在情感和欲望的追逐中挣扎、沉沦,如宓君、凤子、三十三婶等;或是物质生活贫困,悲惨地挣扎在死亡线上,无法忍受贫困、饥饿折磨,不惜以出卖色相、身体来换取生存的权利,如小女孩妈、周磨官媳妇及波兰女子等。
西方女性主义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类:天使和妖妇,认为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而妖妇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4]65如果说前面所述的“善良驯顺的女神形象”属于天使类女性;那么这里的“妩媚妖冶的尤物形象”则属于妖妇类女性。这类女性不愿顺从传统观念和男性意志,她们有欲望、有主见、有心计、敢反抗及不愿意放弃自我念头,因而遭到男性作家的扭曲和诅咒。一方面将她们丑化、贬抑为“妖妇”或“恶魔”,另一方面则诅咒她们,认为她们不配有好的命运和结局。某种意义上,端木蕻良笔下的“尤物”形象也未能逃脱此种被诅咒的命运。不可否认,作者在书写这些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悲惨遭遇时,满怀同情、怜悯的情感,且投注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和关怀思考。但也应看到,作者在情节故事、叙述语气及女性形象描写方面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男性中心的文化偏见和性别意识,从而使得这些“尤物”形象身上也隐现着一丝被“诅咒”的痕迹。
首先,作品情节层面不自觉地流露了男性中心意识。这点主要体现在对女性情爱故事结局的安排上,纵观上述尤物型女性,她们的情爱/性爱故事没有一个结局圆满,而是大多以失败的恋情或是堕入虚空的人生告终。《新都花絮》中,宓君与恋人路分手后,情感极度空虚、无聊,来到陪都重庆,希望以抗战救亡来充实自己,忘却昔日情感创痛。但在新的恋情面前,她很快暴露自私、虚伪的本性,因此恋爱再次受挫,沉入到悲痛、落寞中。《可塑性的》中的小凤,本是没落贵族少女,由于家道中落,沦落风尘,靠出卖色相和身体维持生存,受骗上当却懵懂无觉,把自己命运完全寄托于他人身上,最后绝望自杀。《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三十三婶也是如此,丈夫长期在外,她内心情欲无法得到满足,便突破伦理道德底线,以病态形式发泄内心的情欲意念,最终落得遭人厌弃,堕入人生的虚空中。而《鴜鹭湖的忧郁》中的小女孩妈和《憎恨》中的周磨官媳妇也分别依旧挣扎在死亡线上和被愤怒之火烧死。可见,这些不满情感和现实生活现状,企图以色相、身体来挣扎、反抗的女性,最后无不以失败、落寞告终。
其次,男主人公和叙述语气也明显流露出男性中心意识。尽管作者对笔下女性的不幸命运和悲惨遭遇充满人道主义同情与怜悯,但作品的男主人公和叙述语气无不流露出对于这些“尤物”的鄙视与厌弃。《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就一直讨厌三十三婶,躲避和嫌弃她,称其为“无耻的苍蝇”。叙述者也在叙述层面经常流露对三十三婶的厌恶和嘲讽。如叙述丁宁不得不去三奶府上借钱,面对三十三婶的献媚,作者写道:“丁宁对于这种拙笨的献词,感到奇异的好笑,他又勾起了方才三十三婶所给予他的丑恶的印象,他想,我真的就能容这样的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吗?分明的,三年前,那更丑恶的一幕,使他更感到恚愤的一幕,又在他的眼前一闪。”[4]134类似的带有厌弃和鄙视感情色彩的段落、句子几乎始终伴随着三十三婶,读者很容易陷入这种无处不在的情感和道德判断中,而无法获得对于这类女性复杂心理情感的丰富和深入了解。《可塑性的》中表哥辛人也是居高临下地以侮藐和鄙视态度看待凤子的受骗堕落和卖弄风情,而叙述者的叙述也流露其不无责难和鄙视的情感态度。“一个平凡的女人,有着可塑性的胚胎,任着别人的暗示或社会的偏见来支持她的意志。专在必然里选择了偶然听信它的作伪,任凭它欺骗自己,巧妙地感到满足……”[1]128一种掺杂着冷漠、痛惜、恚愤和鄙弃的复杂情感尽显其中。而《三月夜曲》中的“我”更是时刻警惕波兰女子的色诱和骗术,最后终于“让她明明白白地滚蛋”。尽管我们不能把男主人公和叙述者的情感态度完全等同于作者的态度,但两者合谋的这种厌弃和鄙视情感多少泄露了作者潜意识中鄙视此类尤物型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识。
最后,对女性魅惑力的凸显更体现了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识。尽管作者并没有明确地将此类女性称作尤物,但在描写她们形貌、体态和神情时过于凸显其魅惑力,则泄露了其物化女性,视女性为尤物的倾向。有论者指出:“把女性称‘尤物’本身就有对女性不尊重的意思”,因为它过于强调“‘尤’即美貌的一面”,“更多的是强调‘物’即不把她们当成人看的一面”。[11]某种程度上,端木小说便存在这种物化女性的倾向。端木喜欢用女人来形容景物和意象,这是中国传统充满性别歧视意识的“香草美人”比兴滥调的重现,在古往今来的许多男性文人、作家笔下不难看到。端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如,“黄河的河面就如一个受污的乡女一样,今天在脸颊上冲洗着两道耻辱的泪痕。”(《风陵渡》)[5]77“草芽都像白色的流苏似的踏出来,娇嫩的像刚洗过的少女的皮肤似的。”(《早春》)[5]104“喜鹊畅快的发出丰艳的少妇被膈肢样的笑声”(《早春》)[5]107等。更重要的是,端木还喜欢将这类尤物型女性描写得妩媚、娇艳,善于在异性面前施展自己的魅惑力。三十三婶使出浑身解数、撒娇作痴吸引丁宁的注意力,她把“自认为足够刺激丁宁的话语,安排在每一个空隙里”,“眸子是多么激动呵,机灵的眼角是蕴蓄着怎样的过多的笑呵”,而这笑也是“更形娇艳”。[4]126凤子在辛人面前也是扭捏作态,极尽风情,她“风姿绰约地把腰肢扭转,然后回眸有情地注视以后,陷在迷惑的娇痴里”。[1]125而波兰女子在戏院对“我”更是极尽魅惑之能事,先是装作整理丝袜吊带,“偏着脸,眼光由发际翻转上来,微笑着,又像是称赞着自己的腿,‘丰富而有生命’,后来竟将头搭在我肩上,抽搐起来。”[1]142-143总之,作者将这些女性刻画得毫无尊严,她们屈从于异性情爱,彻底丧失自我,自甘降格为物。这种将女性物化的书写显然折射了作者潜意识中物化女性,视女性为尤物的男性中心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给作品艺术审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它导致女性形象刻画失真,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欠合理。如宓君后来的性格发展便不符合情理与逻辑。她到重庆是决心投入抗战洪流中,彻底改变自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因此工作热情、积极,对孩子们充满爱心,特别是对小小更是爱护有加。但后来她拒绝去看病危的小小,显得有些突兀,不符合性格发展逻辑。显然有为了凸显她的自私、虚伪本性,或是为了制造其恋爱悲剧而有意为之的嫌疑。另一方面,也导致女性形象刻画失却人性深度,使女性形象不如男性形象深刻、丰满。《遥远的风砂》对土匪煤黑子的刻画极富人性深度,它“破除了传统小说的人物二分法,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反之,在煤黑子身上既有原始的恶又有原始的善;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生命”。[1]5然而,端木在刻画尤物型女性时却过于强调她们的“尤”,即魅惑力,导致这些女性形象失却人性的深刻与丰满,显得有些概念化和平面化。如前所述的三十三婶便是一个显例。相对来说,凤子这个形象的刻画比较丰满、成功,作者生动地写出了她对辛人由最初的希望到后来的失望,再到最后绝望的过程,从而使其最后的自杀悲剧显得合乎情理。
三、意识形态的符码:倔强反抗的女性形象
有论者指出:端木蕻良的作品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原始强力,而“顽强的生命力、大胆的反抗精神、强烈的求生意志”构成了这种原始强力的精神内涵。[12]端木在1936年《致鲁迅》中也谈道:“怎样的向东北草原的农民的生活的深处去发掘呢,这个问题深深的苦恼着我。以怎样的原始的岸傲的雄健,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斗力合流呢?”[5]357可见,塑造倔强的反抗者形象,表现他们的反抗与斗争是端木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受五四新文化思想、东北地域文化及现实复杂的矛盾斗争形势等影响,端木笔下涌现了许多反抗者形象,如反叛传统观念、追求婚恋自由的女性形象:《雕鹗堡》中的代代、《红夜》中的玛璇及《大地的海》中杏子等;反抗强权、暴力及沉重的阶级压迫的复仇者形象,如《朱刀子》中的朱老五、《大地的海》中的虎头、《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宁姑兄妹及《憎恨》中的圆子等。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前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东北大地上的不断肆虐蹂躏,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席卷整个黑土地,端木笔下更是涌现了大量不屈的抗击侵略者血腥暴虐的反抗者形象,如《风陵渡》中的马老汉、《遥远的风砂》中的煤黑子及《浑河的激流》中的猎户们等。受这股强劲的反抗精神的影响,以及出于对侵略者残暴罪行的强烈愤恨及其激发出的爱国精神也必然会影响到这些反抗者身边的女性,于是,一些抗击侵略者暴行的女性反抗者形象随之涌现,如《浑河的激流》中的水芹子、《大江》中的卓雅等。水芹子本来是一个沉浸于爱情憧憬和躺在父亲怀里撒娇的快乐女孩,但在父亲被逼与猎户们一起决心起事反抗的情势下,她也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反抗女性,大胆地喊出“给我枪!给我枪!”的反抗斗争心声。卓雅则出身于富裕的华侨商人家庭,本来可以过上快乐无忧的生活,但出于爱国激情,她还是勇敢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前线,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可以说,这些女性已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情感圈子,献身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抗战,体现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
事实上,这些女性反抗者形象的涌现除了上述现实战争形势的激发及男性反抗者的影响外,东北萨满教文化及端木母亲性格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东北“原始萨满教文化,鼓舞着人们去与一切生存厄运做斗争,特定的地域文化塑造了女性形象的顽强坚韧的性格精神,很难想象在这里会产生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形象,因为这里的文化和水土只能诞生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这些女性在性格上都是那么刚烈和倔强,在国仇家恨交聚的历史背景下,她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一种不可抑制的野性生命力喻示了我们民族潜藏着不可战胜的精神能量”。[13]而端木母亲也是一位性情刚烈,极具反抗性的女性。端木在《科尔沁前史》中谈道:母亲为了阻止父亲娶妾,亲自闯到那个姑娘家与她撕扯,使她断了做小妾的想头。后来还有几次类似的娶小妾事情,都被母亲闹翻了。端木母亲在端木十三四岁时给他讲述自己身世,要端木记着,长大后替她把这些苦记下来。这些无疑都会潜在地影响着端木对于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
然而,即使在这些倔强、反抗的女性形象身上,依然不难发现作者身为男性的性别印记。其一,这类女性反抗者形象不是很多,且大多不是作为作品主角出现,而是作为男性反抗者的配角来写的。相对说来,活跃在端木小说中的反抗者形象更多的还是男性,除前面所举例证外,还有《大地的海》中的艾老爹和来头、《萝卜窖》中的莲子、《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义勇军们、《万岁钱》中的小五以及《大江》中的铁岭、李三麻子和他们的战友们等。可见,作者更多的是把顽强的反抗精神寄予在男性形象身上,而非女性。即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倔强反抗的女性形象,她们也更多地表现在反抗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争取婚恋自由上,相反,在疾风骤雨式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中,反抗的女性形象则是寥寥无几。这或许与作者潜意识中“男主外,女主内”及“男强女弱”等传统观念的拘囿不无关系。其二,这些女性反抗者没有明确的性别自觉意识,她们不是为了性别意义上的解放而反抗,而是为了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或者民族的解放而反抗,也就是说,她们反抗的目的不是出于对性别歧视的抗争,而是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观念意识,沦为作者表达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等意识形态的符码。《红夜》中玛璇勇敢追求自由爱情,反叛宗教禁忌,因为有恋人龙宝与她同道。在反抗宗教神秘禁忌、争取自由爱情上,俩人是盟友。《雕鹗堡》中代代敢于在全村人面前喊出:“只要你下来,我永远跟你好。”体现出反抗传统观念、追求和表达自由爱情的勇敢精神。但这既是受石龙特立独行思想的影响,也出于救护和帮助石龙的人道主义情感。《浑河的激流》中水芹子的勇敢反抗是受到父辈反抗精神的激发,当她看到父辈们决心起事反抗,“自个救活自个”,“自个做自个的主人”时,她不仅劝说恋人金声加入反抗者行列,而且自己面对强敌入侵,也大胆喊出:“给我枪!给我枪!”体现出坚决反抗的斗争精神和意志。因而,这些倔强、反抗的女性形象身上依然隐现着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男性中心意识的存在给女性反抗者形象的塑造也带来一定的遗憾。最明显的是,导致这些女性形象失真。如《浑河的激流》中的水芹子,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最后面对强敌入侵,勇敢地喊出:“给我枪!给我枪!”体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但在前面部分,她却显得很幼稚、娇痴,甚至躺在父亲怀里撒娇、睡着,由父亲抱到床上去睡。这不仅容易使读者质疑水芹子的年纪,而且与后面成长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反抗者也不太协调。《雕鹗堡》中的代代也是如此。在前面部分,她与石龙几乎没有交集,与她相好的是村里另一勤快的小伙子东来。石龙只是偶然一次帮助过代代。但在后面情节中,代代竟当着全村人的面对石龙喊出:“只要你下来,我永远喜欢你!”代代性格的这种转变显得有些突兀,仿佛只是为了传达作者的人道主义观念而有意为之。当然,短篇小说体式的拘囿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作者男性观念所致。
综上所述,端木满怀爱悦和怜悯的情感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神态如生的女性形象,但由于其男性身份所携带的性别本能意识——男性中心意识的潜在影响和拘囿,他不可能像女性作家那样能真正了解和理解笔下女性,并感同身受去体验和书写她们,导致这些女性不是被理想化和神圣化为女神/地母形象,就是被扭曲、变形为尤物形象,或者沦为承载作者意识形态观念的符码,而没有也不可能真实反映现实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状,这一定程度地也给创作的艺术审美带来了一定的遗憾。这是端木创作中值得深究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王富仁.端木蕻良小说[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2](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4]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5]孔海立.端木蕻良作品新编[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6]席慕蓉.大雁之歌[Z].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韩传喜,吴楠.断裂与转换——论端木蕻良1942年的三部爱情题材小说[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5).
[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性的秘密[M].晓萱,张亚莉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撰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周妍.“美女”为何称为“尤物”[J].咬文嚼字,2009,(4).
[12]张华.野性、顽强、火爆——论端木蕻良小说的原始强力[J].吉首大学学报,2007,(3).
[13]阎秋红.论端木蕻良抗战小说的萨满教文化因子——从长篇小说《大江》《大地的海》谈起[J].满族研究,2005,(3).
责任编辑:杨春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Duanmua Hongliang’s Novels from Gender Perspective
CHENJiaohua
Abstract:Duanmua Hongliang w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Northeast Writers Group known for portraying the female image. But with the potential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ale centered consciousness, such images became either idealized as that of a sacred Goddess or mother image, distorted for YuWu, or symbolized as part of the author’s ideology. This was not on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but also by Shamanistic culture and the realities ofdailystruggle.
Key words:Duanmua Hongliang; female image; male centered consciousness; Shamanistic culture
作者简介:陈娇华,女,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21500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2-0079-07
DOI:10.13277/j.cnki.jcwu.2016.02.011
收稿日期:2016-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