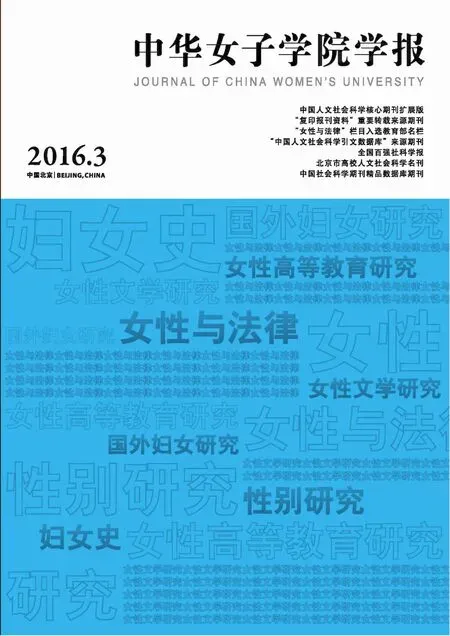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轻刑化量刑的思考
2016-02-15于晓丽
于晓丽
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轻刑化量刑的思考
于晓丽
摘要:研究发现,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制约束缚、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容忍与冷漠以及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帮助的漏洞所致,而且,我国当前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定罪量刑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现状也颇引人担忧,因此,有必要从“受虐妇女综合征”、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期待可能性、社会危害性等理论及实践问题入手,对广泛关注的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从而提出对此类犯罪轻刑化的法理依据。
关键词:以暴制暴;轻刑化量刑;受虐妇女综合征;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
当前,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的犯罪案频发,从“刘栓霞毒杀丈夫案”[1]、“谈玉红杀夫案”[2]到如今的“李彦杀夫案”[3]及“姚荣香杀夫案”[4],关于此类案件的争论越来越多地浮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目前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的争论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暴制暴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其中一种主张认为,此类行为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并且有的案件存在分尸、抛尸等恶劣情节,应当作为一般的故意杀人案件进行处理,长期遭受的家庭暴力并不能成为其抗辩理由,只能作为一种酌情量刑情节。另一种主张认为,此类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但是因为其长期遭受严重家庭暴力,在愤怒恐惧下杀害其丈夫,考虑行为人受暴情况及其本身社会危害性小、期待可能性不大、被害人存在过错等情况,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或者将其归为“情节较轻”的犯罪。二是以暴制暴行为成立正当防卫,因此无罪。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因为长期遭受严重的家庭暴力,符合“受虐妇女综合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英美法系很多国家已经将“受虐妇女综合征”归为正当防卫,并且将其作为专家证据为以暴制暴行为做无罪辩护。
笔者认为:受暴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在量刑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成因
(一)中国传统观念的制约及束缚
根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10月21日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①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在“夫权”、“男尊女卑”等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往往选择隐忍、包容的态度,希望借此感化自己的丈夫并挽回家庭。这样不仅没有使施暴者受到感化,反而使其变本加厉,造成恶性循环,使得受暴妇女慢慢走向崩溃的状态。
(二)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容忍与冷漠
一般来说,在社会现实中,当受暴妇女无法忍受配偶的长期严重家庭暴力时,往往最先求助于自己最值得信赖或者最邻近的人或单位,比如家人、邻居、朋友、单位、社区组织等等。而此时,社会往往抱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观念,面对受暴妇女的求助,往往当作普通家庭纠纷,不予及时干预与帮助并实施女性权益的保护,或者往往劝解受暴妇女选择容忍与原谅,使得受暴妇女自感更无依赖。除此之外,非社会系统作为民间个人或者组织,其干预能力往往也是有限的,通常只能起到临时制止及调解作用,并不能使施暴者受到警示,也不能使家庭暴力得到真正的解决。
(三)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帮助的漏洞
所谓“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指警察、医疗、社会及专业服务机构等”。[5]276在我国,家庭暴力处理的司法途径有两种,一是按照故意伤害罪和遗弃罪进行处理,二是按照虐待罪处理。但是往往从这两种途径很难收集到有效的证据,因此保护受暴妇女的力度十分有限。当妇女遭受到家庭暴力而报案时,警察往往当作家庭纠纷,极少对施暴者采用强制措施甚至行政处罚;医疗机构遇到此类情况时,并不会引起太多重视,不会在医疗记录中记载妇女受到伤害的原因;也没有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如心理疏导机构对受暴妇女进行心理上的救助。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妇女得不到公力的救助,在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走上了以暴制暴的“私力自救”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有关正式或者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在家暴预防和处置救济中将依法发挥作用,期待受暴妇女从中得到较好的救济和帮助,从而减少以暴制暴犯罪案件的发生。
二、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的轻刑化量刑探究
当前,我国对于受暴妇女以暴制暴犯罪争议集中在量刑上。在量刑过程中,即使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此类犯罪的妇女存在长期遭受严重家庭暴力的情况,却仍然改变不了此类案件在量刑时并不过多考虑家暴这一情节的现状。其次,我国各地法院对以暴制暴相似案件的量刑差异也很大,从死刑到有期徒刑或缓刑,情节相似的判决却跨越了极大的量刑幅度,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对以暴制暴案件没有明确的量刑法律依据。令人欣喜的是,2015年3月我国两高两部发布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其第二十条规定:“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6]这一规定表明:首先,从以暴制暴行为人角度看,在法律认定的几种情形下,如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有防卫因素,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次,从以暴制暴受害人(家暴施暴人)角度看,以暴制暴受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对以暴制暴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罚。基于这一新规定,笔者将在下文中,对此类案件在防卫因素、被害人过错、犯罪主观要件、期待可能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在量刑时的作用进行分析,找出对以暴制暴行为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论依据。
(一)“受虐妇女综合征”专家证词在量刑上的作用
受暴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的心理特征,笔者认为是符合“受虐妇女综合征”特点的。“受虐妇女综合征”指的是长期遭受丈夫或男友暴力虐待的妇女表现出的一系列特殊的心理状况及行为模式。“婚姻肯定不是对虐待的特许状。”[7]453-455没有哪位妇女会持续地容忍(即使是轻微的)使她遭受耻辱和成为丈夫专制对象的虐待,受暴妇女在长期受到家暴后就开始反抗,但由于家庭暴力的“周期性”①家庭暴力的“周期性”是指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呈周期性模式。模式的形成,一般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暴力周期。每个周期通常包括关系紧张的积聚期(口角、轻微推搡等)、暴力爆发期(暴力发生、受害人受伤等)、平静期(亦称蜜月期,加害人通过口头或行为表示道歉求饶获得原谅,双方和好直到下个暴力周期到来)。,受暴妇女基于对家庭的依赖以及对其配偶的信赖,一次次原谅施暴者,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加之施暴者对受暴者家人的威胁恐吓、社会对家暴的冷漠无视以及一次次受暴后无法得到公力的救助,以致受暴者对自己的生活现状逐步产生了“习得性无助感”①习得性无助感是指个体经历了失败与挫折后,面临问题时产生的无能为力、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与行为。,最终走向心理崩溃的边缘,导致以暴力手段终结这段亲密的暴力关系。
因此,从以暴制暴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笔者认为:处于“受虐妇女综合征”表征期间的当事人,其刑事责任能力类似间歇性精神病发作期,期间受暴妇女长期积累的几近崩溃的精神和心理状况,导致对自己行为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明显降低,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从而不能完全承担刑事责任,量刑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也规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这里可以用“专家证词”作为判断依据。
(二)防卫因素在量刑上的作用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第十九条规定:“准确认定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制度要求行为人应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限度条件等等。笔者认为,以暴制暴行为人在一定的情况下其行为是符合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的。
1.以暴制暴受害者的长期家暴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以暴制暴案件的发生具有特定性,即行为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虽然此时受害人没有实施家暴,属于如睡觉、醉酒状态等,不属于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但传统的正当防卫制度是在双方力量基本差别不大且以男性视角的合理反应来适用的,因此是缺乏性别视角的。如果在以暴制暴案件中,此时仍然要求女性当事人必须恪守“存在有不法侵害”这一起因条件,就无法体现对特定情况的区别对待,违背了实质性公平原则,同时也势必影响法官对以暴制暴行为的合理性做出准确判断,从而失去正当防卫制度本身的意义。因此,“长期家暴”应是以暴制暴案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2.长期家暴对受暴妇女的身体、精神的威胁恐吓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制度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即李彦、姚荣香们只能在她的丈夫对她施以家庭暴力的同时进行以暴制暴行为。然而实际上,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一方面在生理上根本无法在遭受暴力的同时进行抗衡,否则会遭受更加严重的暴力;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长期遭受控制,使其不敢反抗也不知反抗,有一种自我放弃的无助感,因而恪守这种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显然是不公平的。从法理上讲,“不法侵害不仅包括单一的、一次性侵害行为,而且也包括连续性、经常性的不法侵害,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和判断家庭暴力是否正在进行,而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判断。”[8]“对于在时间上间隔较近的两次殴打,仍以认定为一次侵害行为为宜。”[9]由此判断,此时尽管家庭暴力行为暂时停止,但对于在家庭暴力的长期紧张控制环境中生存的受暴妇女的心理而言,仍然处在“正在进行”之中。在现实的以暴制暴案件中,受暴妇女往往是在受暴之后进行的杀夫或者伤害的行为,因此以暴制暴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3.以暴制暴行为结果符合正当防卫中超过必要的限度条件。在李彦、姚荣香两个案件中,都有杀死丈夫的严重后果,但在对以暴制暴案件进行量刑的时候,笔者认为,不应完全采用事后判断的方式。因为受暴妇女往往在实施杀夫行为时,她们对自己将要遭受到的死亡威胁或者严重伤害的心理预期是肯定的并且是合理的,这符合“受虐妇女综合征”的心理特征。可目前,我国往往采用事后判断的方式,忽略了受暴妇女长期积累的几近崩溃的心理状况,所以很难认定以暴制暴女性当事人符合限度条件。
我国《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对于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的规定有所突破,在认定制止家暴的防卫行为中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方面已经考虑到防卫者长期受到家暴的情节,“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6]这一规定对于受暴妇女以暴制暴行为适用正当防卫的合理限度条件可以有所放宽,在对其量刑时可以适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期待可能性在量刑上的作用
期待可能性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脆弱的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10]240-241的法律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法律只能要求人们做其有可能去做的事,不能强迫他人做其不可能做的事。”[9]该理论核心为“法律不强人所难”。由于家暴行为具有空间的隐蔽性、时间的持续性和手段的残忍性,所以,依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则家庭暴力应属于此类暴力犯罪,家庭暴力不仅有“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受暴妇女家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如“你要敢提出离婚,就杀死你全家”等的恐吓语言以及实际暴力及破坏行为的威胁预告,导致受暴妇女理所当然认为自身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正面临危险,因此奋起反击,如果一定要受暴妇女切实受到不法侵害才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就会造成“法律强人所难”,并且不利于惩恶扬善。所以对受暴妇女以暴制暴行为的可谴责性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当随之减小。
(四)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上的作用
被害人过错,即被害人故意或者过失的错误行为而诱发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产生,进而引起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造成犯罪侵害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的这种错误行为即被害人过错。[11]《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规定:“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说明在处理以暴制暴案件时,被害人过错已经开始进入到司法量刑的视野中。
受暴妇女之所以以暴制暴终结施暴者的生命,与其他一般故意杀人案件并不相同。在此类案件的发展过程中,被害人与受暴妇女始终处于一个互动过程,被害人往往对受暴妇女施暴行为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是通过施暴者一次次的施暴进行的,也可以说,被害人对受暴妇女一次次的侵害造就了受暴妇女由被害到犯罪的“恶逆变”。这一点可以从以暴制暴行为的特点中体现出来,即“犯罪的被动性、对象的针对性”,她们主要是因为一次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且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通过杀夫来寻求一种解脱的途径。
此外,笔者认为,被害人的过错程度应与以暴制暴犯罪人的量刑轻重构成反比关系。被害人之前的施暴行为时间越长、手段越残忍、对受暴妇女造成的身心伤害越严重,则对以暴制暴行为人的量刑就应当越轻,以体现实质公平。
(五)社会危害性在量刑上的作用
刑法惩罚行为的实质是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在以暴制暴案件中,如李彦杀夫案,虽然客观上看,李彦采用了分尸等情节恶劣的手段,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较为严重,但受暴妇女的行为均具有绝对的对象性和起因性,受暴妇女一开始充当的是家暴被害人的角色,她们实施杀夫行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结束丈夫对她们的进一步伤害,一旦杀夫行为结束,她们的犯罪行为也便结束,对社会的危害性也随之结束。由此可见,以暴制暴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都较小。因此,秉承刑法的目的和刑罚想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言,应当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相吻合,展现“法官对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问”,彰显隐于“法律规则之后的力量”。[12]处理此类案件应当丢掉“杀人偿命”的一般理念,并认识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从而做出轻刑化的量刑。
此外,以暴制暴案件的诱因是被害人之前的家暴行为,所以被害人对以暴制暴案件的发生有过错,由此也可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对行为人的道德谴责性较轻,而且容易得到邻居群众以及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同情与宽容。“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6]
三、结语
受暴妇女因以暴制暴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和施暴者长期虐待受暴者导致死亡(董珊珊案)而被法院以虐待罪判了有期徒刑6年半相比,两者的量刑极不对等,太不公平。假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长期受父亲虐待、性侵而无法解脱,在其父熟睡时将其砍死,其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因为行为人女孩不到14岁,不具有刑事责任年龄,而并非是因为以暴制暴案件中的被害人是长期施暴者、性侵害者,这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和保护极为不利。
因此,在对此类案件进行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被害人在案件中起到的作用,考虑受暴者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是否“强人所难”,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处罚情节”,将无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对于以暴制暴犯罪的量刑采取从宽、减轻或者缓刑量刑,使以暴制暴行为人(受暴妇女)尽早回归社会和家庭,履行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义务。
【参考文献】
[1]陈敏.女人无需沉默[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9/153614415192.shtml,2015-08-06.
[2]贾芳芳.谈玉红杀夫案今日宣判[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dfjzz/content/2010-08/12/content_2238768.htm?node=6309, 2015-08-06.
[3]刘春华.四川女子杀夫分尸改判死缓,最高法院核准为死刑[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5-04-24/100331755772.shtml?t= 1429851070667, 2015-08-06.
[4]范跃红.浙江温州一不堪家暴杀夫的妻子获5年轻刑[EB/OL].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503/t20150306_ 1483691.html, 2015-08-06.
[5]高小贤.防止家庭暴力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处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EB/OL]. http://www.court.gov.cn/ fabu-xiangqing-13616.html, 2015-08-06.
[7]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8]赵秉志,郭雅婷.中国内地家暴犯罪的罪与罚——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十起家暴刑事典型案件为主要视角[J].法学杂志,2015,(4).
[9]王新.受虐妇女杀夫案的认定问题[J].法学杂志,2015,(7).
[10](日)大眆仁.刑法论集[M].东京:有斐阁,1978.
[11]任志忠,汪敏.被害人过错与死刑适用[J].法律适用,2009,(1).
[12]杜月秋.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为视角[J].法律适用,2007,(3).
责任编辑:蔡锋
Lenient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Woman Responding Retributively to Violent Crimes
YU Xiaoli
Abstract:It 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women’s retributive actions to violence against them includ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intolerance and indifference of non-form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and loopholes of form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It is worrisome that China’s current laws and judicial explanations and regulations on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women who took violent actions against abusers are not satisfactor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more on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justifiable defense, victims’faults, expectation and social harm so as to give justification for lenient 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against such women criminals.
Key words:retributive violence crime; lenient sentencing;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justifiable defense; victims’faults
DOI:10.13277/j.cnki.jcwu.2016.03.003
收稿日期:2016-03-16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023-05
作者简介:于晓丽,女,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等。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