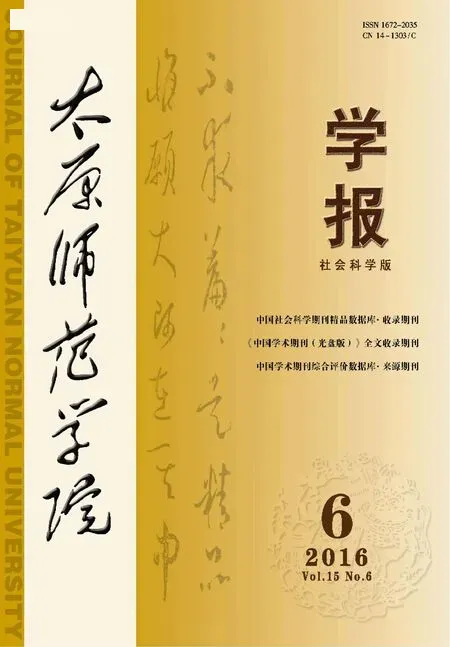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2016-02-13谢薇
谢 薇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法律学】
法治视野下的“真实”
谢 薇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所代表的不同价值对我国的司法和法治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我国立法对“真实”的基本定位为贴近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和西方法治倡导的法律真实有不同之处,这不仅源于诉讼模式的差异,更是由于司法环境的不同。尽管如此,我国在追求“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中,仍存在一定困境。如何达成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努力,更需要在全社会中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法治
依法裁判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普遍原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或阻碍。但一个公正的裁判必然建立在准确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上。但何为事实?历来存在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
一、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概念及作用
客观,“谓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与‘主观’相对。”[1]客观真实,是指事实真实的发生过程。客观真实注重事件的真相,认为这种真实是案件本应具有的状态。但法律真实,是指司法过程中通过证据所构建的案件事实。这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下的实际事实。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同时人的认识程度会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客观真实实际上几乎难以达到。这也就有了两者的区分。
对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标准、价值导向等方面。但对具体案件来说,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设置的初衷也是使法律真实尽可能地贴近客观真实。因此,两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对司法和法治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发现客观真实有利于解决纠纷,打击犯罪。因此,它代表着一种实体上的正义。而法律真实注重证据构建的事实,对证据的重视使得一系列非法证据得以排除,人权得以保障。同时,它也减少了发现客观真实的人力物力,提高了诉讼效率,所以更偏重程序上的正义。两者不仅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要求。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和文化,首先应使每个人感受到法律在解决纠纷、保障人权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有益的。所以,据以裁判的这种“真实”尤为重要。
二、中西方司法中对“真实”的追求
程序的正义观念起源于西方,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于英国普通法制度之中,并在美国得到发展。因此,西方人对程序的重视有其历史渊源。这也反映到他们对司法程序的尊重上。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是其追求“法律真实”的典型体现。凶案现场的若干证据都将嫌疑指向辛普森。然而法庭上,其律师提出证据证明警察在现场发现的带血的手套大小不符合辛普森的手;几名证人有种族歧视倾向并说了谎。这说服了陪审团,最终辛普森被无罪释放。但在辛普森被释放后,他公开承认了自己谋杀前妻的事实。虽然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但还是尊重了法院的审理,没有对法官和陪审团进行攻击,也没有游行示威。
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事实”的概念加以明晰。三大诉讼法仅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我国的诉讼法中无不贯彻了一种“证据裁判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还规定了证据的收集、非法证据排除等一系列规则。但这种证据不是一非法就排除,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并未将“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明确包含在内,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许可,反而体现了司法在具体案件中对“真实”的一种裁量。这种对法律真实的追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在使用以证明构成要件的有效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的情况下,即不能达到法律真实的程度,就不能认定案件事实。所以说,我国司法中的这种“真实”是一种法律真实,而刑事诉讼法尤其体现了一种追求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但这种追求是否能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还只是一个理想性的目标,此处还不得而知。如2001年的莫兆军案中,原告手持借条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还钱,而被告却以借条是被胁迫写下的为由拒绝还钱,但并没有证据。法官莫兆军根据“优势证据”判决被告败诉,结果被告在法院门口自杀身亡。后查明,此案确实是原告诬告。莫兆军也因“玩忽职守”而被起诉,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他却被调离法官的职位。
上述两个案子中,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事实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有罪无罪、胜诉败诉。不同的是,辛普森案中对法律真实的追求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而莫兆军案中对法律真实的坚持却造成了惨剧。在笔者看来,法官莫兆军的行为显然不存在过错,如果他罔顾庭审,罔顾法律,为了事情的真相判决被告胜诉,那么是否就实现了正义?似乎并没有。我们暂不讨论莫兆军审案是否存在瑕疵,但中西方诉讼模式和司法环境的差异确实影响着案件的“真实”。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
西方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案件事实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下形成,所以法律真实有其形成的基础。虽然中国现在正在由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过渡,但很多时候法官并不像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那样仅仅消极地推动程序的前进,职权主义色彩依然浓厚,庭审前法官去实地调查案件真相的情况并不罕见。于是法官用以判案的依据往往是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掺杂着自己对案件的了解。这种方式确实可能有利于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实质的公正。就像著名法官宋鱼水在办疑难案件时,在双方认可的条件下主动调查,这会导致法律真实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也可以尽可能地在事实层面上解决问题。但并非所有的法官都可以在实地调查时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而法律对法院主动调查取证的规定仅限于有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或者程序事项。除此情形外,法院调查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因此,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这种实质合理的结果未必形式合理。离开形式合理的机制保障,追求实质合理就会没有标准,就会走向片面,就会导致“权”大于“法”的人治,使实质合理成为一句空话。[2]
(二)司法环境的差异
美国对程序公正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寻求案件真相,司法独立也使得人们尊重法院所作的判决。但在中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更多的注重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他们所期望法官认识到的事实是一种客观真实,当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真实时,法官建构起的法律真实很可能和他们的愿景相冲突,就像莫兆军案中败诉的被告。他们也缺少一种程序意识,面对不服的判决只能以死明志,却不知可通过上诉得到救济。莫兆军虽然最后无罪,但对他的批捕起诉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一个按法律规定、以证据裁判规则认定法律真实的法官何罪之有?还是说因当事人的原因造成的社会影响应由法官承担?这对法院独立断案的影响又怎么消除?莫兆军案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当事人扬言法官必须作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否则就死在法院门口;许多法官在面对一些简单案件时也不敢自行断案,为保险起见,将案子交由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样不仅司法威严大打折扣,司法的独立性也受到影响。
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基础与困境
如上所述,客观真实注重对案件本来面目的探求。这种探求本身有利于纠纷的解决或对犯罪的打击。尤其是在社会秩序较为混乱或犯罪率高时,追求客观真实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但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若没有一系列手段规制,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过其正面影响。对于民事诉讼,当人们将纠纷诉至法院,往往是要求法院给他们一个“说法”。除非继续沿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否则法官主动地调查取证既不符合中立立场也不合法。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说,如果追求客观真实而忽略了形式价值,那么就会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这种对客观真实的追求虽然可能符合群众的心理期望,却不符合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法治的要求。
而法律真实却恰恰相反。当人们内心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真实时,尤其是当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相冲突的时候,基于法律真实的判决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反感,甚至心理失衡。其中,刑事案件可能表现尤为突出。所以,理想的法律真实须向客观真实看齐,尽可能地靠近客观真实。这就要求法律真实要有坚实的基础作支撑、完备的制度作保障。这种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须完备。法律真实的构建以证据为基础,其认定以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和实体法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因此法律为法律真实的构建提供大前提。如果法律不完善,即使人们严格遵守法律,也无法最大限度地还原客观事实。其次,对于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侦破案件能力的提高,侦查人员法律意识、职业素养的强化,都可使得破案所获取的证据合法且更符合客观真实。对于民事纠纷,原被告双方举证能力较强,不至于因举证能力的问题而使证据构建的事实远远偏离于客观真实。最后,公众注重程序的独立价值,尊重司法。公正的程序可以吸收不满。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正确的和正当的。[3]只有人们逐步认识到程序的意义时,才能将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的差异引发的不满降到最低。显然,我国现在还不能为法律真实提供肥沃的发展土壤。虽然莫兆军案发生在十四年前,近些年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但这种关于“真实”的追问一直在继续——如何弥补我国现在法律真实的基础的缺陷?又如何能使法律真实更贴近客观真实?
四、落实“真实”的几点想法
基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各有的困境,“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不能仅仅成为一句口号,如何形成二者的统一,笔者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民事案件
在我国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要尽可能规制法院主动调查取证的行为。对于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实地调查的,法官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证据作出裁判。同时,要防止法官过于强调程序的对抗性——认为只要当事人在法庭上对抗,自己只需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裁判即可,完全不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文化水平等因素,这就可能导致上述欠款纠纷案的重演。因此,这种平衡就要求法官正确履行释明权。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并没有规定,而是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中,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别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自认、变更诉讼请求、证据的采纳、回避以及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诉讼请求后果的释明权进行了规定。可见,释明权在我国立法中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释明权的不规范、不统一,若使用不当很可能导致法官参与法律真实的构建,这样不仅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还破坏了司法公正。因此,立法上合理规范释明权的范围、时间、方式是解决实践中法官释明权问题的前提。
(二)刑事案件
笔者虽然认同辛普森案件的审判,但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结果,因为凶手完全可以被定罪量刑——只要执法人员通过正当程序来收集、保存证据。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其意义为: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因此,审判程序中,陪审团有理由相信,如果证据是伪造的或非法取得的(一只臭虫),则将导致指控被否决(面条被倒掉)。[3]虽然,我国司法排除的对象仅限于非法证据,对合法证据予以保留,不可能使被告仅因一条非法证据即予无罪释放,但这可能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客观真实。所以,应该严格依法进行侦查,同时提升侦查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尽可能地使贴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不被排除。这样,既能打击犯罪又能保障人权,从而达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相辅相成、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相统一的效果。
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对公众来说,都应尊重司法的程序及其判决。但这种“程序意识”在我国没有传统。即使在我国的程序法律相对完善的今天,这种程序意识的观念仍没有根植于公众的心目之中。树立公众对司法的尊重及信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法治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此外,司法权威也应当被逐步树立起来。笔者认为,公众对司法的信仰和司法的权威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只有权威才值得信仰;司法只有被人们信仰才有权威。因此,公众逐步接受法律真实的过程,也是逐步尊重司法的过程,更是法治普遍实现的过程。
五、小结
在“以客观真实为目标,以法律真实为底线”的目标追寻中,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基础,导致其实现面临一定的困境。但在立法和司法上如何匹配相适应的制度,如何平衡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以构建恰当的标准,还需要针对我国现实作进一步深入探讨。另外,该目标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使其被大众所认可。这种恰当的建构与公众的认同有助于实现和法治的互相促进,在不断完善司法的同时,推动法治的不断前进。
[1]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 阮国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辨析: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J].行政法学研究,2007(2).
[3] 王伟,等.法治:自由与秩序的平衡[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张 琴】
The Truth under the Scope of Rule of Law
XIE Wei
(FacultyofHumanities,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The values represented by objective truth and legal truth have different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judiciary and rule of law. According to our legislative system, the word “truth” is usually defined as the legal truth which is as close to the objective truth as possible. However, as the presence of the goal—— “objective truth is our final goal, while legal truth is our bottom line”, how can we balance between objective truth and legal truth to achieve that goal? What problems are we encountering if we have not achieved the goal? How can we get out the dilemmas that we are facing now? In this study, we will be discussing these questions above and hope to inspire further studies regarding the objective truth and legal truth.
objective truth; legal truth; rule of law
2016-06-20
谢 薇(1993-),女,山东东营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1672-2035(2016)06-0044-04
DF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