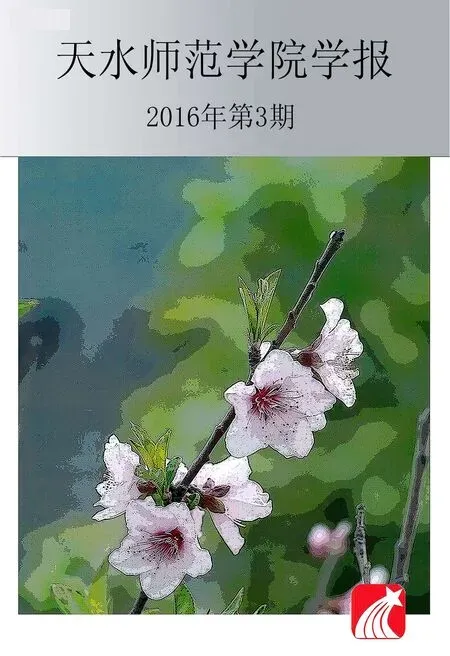这只理想主义的小波尔羊:论赵丽华的爱情诗
2016-02-13薛世昌
薛世昌,马 超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这只理想主义的小波尔羊:论赵丽华的爱情诗
薛世昌,马超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赵丽华以其零度风格的抒情让人们觉得她的深刻可能更甚于她的柔情,其实她的女人之心终归还是“感觉到了被剥开时的疼痛”。赵丽华的爱情诗实在、朴素而不矫情,写出了虚伪时世里难得一见的爱情真感受;赵丽华的爱情诗通脱、透彻,却经由通脱、透彻而形成一种虚无与悲观。她的这种悲观有着深远的来历——对存在本身不幸和无奈的宿命认识。赵丽华的诗歌是去魅、自然、本真、生活化的,她的爱情诗同样深具去魅、自然、本真、生活化的特色。
赵丽华;爱情诗;零度抒情;去魅
布罗茨基论及阿赫马托娃时说:“在人的一生中,时间与人的对话借助了不同的语言,如天真、爱情、信仰、经验、犬儒哲学等。在这一切之中,爱情语言显然是一种混合的语言,它从其他所有的语言中汲取词汇,它的声音能使无生气的对象感到满足。”[1]诗歌无疑是“爱情语言”中最为美好的语言。赵丽华,这位“恣意放纵现代人的情绪”且又“怜爱、悲悯自然中存在的一切生命”[2]276-284的当代女诗人,曾以其零度风格的抒情让人们觉得:她的深刻可能更甚于她的柔情,她的目光应该像柳叶小刀,随风而敏锐,“……当雨滴在它们的身体上滑过/我看到了它们的颤栗/要是叶片与叶片在相互梦见/我会相信那是真的”(《树叶》),但是,她的女人之心终归还是像《一只橙子》之所云,不时“感觉到了被剥开时的疼痛”。赵丽华自称:“我的写作面是很宽泛的,纯粹的爱情诗歌少之又少。”[3]但她毕竟写下了为数不少的爱情诗。虽然它们也许并不“纯粹”。为什么一定要“纯粹”呢?当“对象”和“情人”这样的词语在我们的现实语境里失去了它们的所指,那么所谓“爱情”,连同对它的咏唱为何定要“纯粹”呢?
一、赵丽华的爱情诗:实在、朴素而不矫情
赵丽华是一个对世俗行为极其反感的世俗之人。当世俗的大众与世俗的诗人按照他们世俗的爱情观与世俗的爱情想象把爱情诗写得那么优美、圣洁、缠绵、矫情,那么不口语、不生活,不实在(好像是在彰显爱情的所谓正能量),赵丽华即在自己的写作中,一反那些优美和缠绵的所谓爱情,抒写出自己鲜明的风格:实在而不矫情、朴素而不做作。
曾有一个题为《爱的四个境界》的诗歌文本在微信圈广为传播,这个文本通过诗歌的例举,言说了人间爱情的不同境界。第一个境界之例诗为泰戈尔《世界上最远的距离》,第二个境界之例诗为舒婷《致橡树》,第三个境界之例诗为仓央嘉措活佛的《见与不见》,第四个境界的例诗为叶芝的《当你老了》。它们无疑都是优秀的爱情诗,如果一定要以它们来例示爱的境界并以叶芝《当你老了》为最高,可能是因为叶芝所写的爱情,生死两别,最为悲摧,且暗含了爱的长久、爱的难忘、爱的美好等等爱的基本元素吧,但是,赵丽华却对叶芝的那首《当你老了》进行过无情的解构(就像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之于杨炼的《大雁塔》)。赵丽华的《当你老了》是:“当你老了,亲爱的/那时候我也老了/我还能给你什么呢?/如果到现在都没能够给你的话”。作为解构之作,即作为一种离不开“上下文”的写作,赵丽华曾自述此诗写作的互文背景:“网络时代的快节奏下,我省略了叶芝的铺陈、絮叨和矫情,改含蓄为显性,改试探为确凿,改洋洋洒洒为简捷和直接。”[4]86也就是说,赵丽华的《当你老了》看似是对叶芝《当你老了》去其铺陈还其直接、去其絮叨还其简捷、去其矫情还其实在的题对题之改写,其实却是愤世嫉俗的赵丽华对大众阅读所喜欢的吞吞吐吐与含含糊糊以及缠缠绵绵等等诗歌语言所实施的面对面反击。
赵丽华自己并非就不铺陈不絮叨,如她的《风遇到树叶》:“风只有在遇到树叶的时候/它才是轻快的、絮叨的/它说了很多可有可无的话/做了很多毫无意义的事/它是那么不厌其烦地掀动着树叶/一片又一片/一遍又一遍/漏下来的光挤着斑驳陆离的影子/叶片偏转着身子/……在这种乐此不疲的游戏中/我仿佛看到了另外的快乐”。在这首正所谓“不纯”的爱情诗里,赵丽华絮絮叨叨地写出了自己真实得几乎于虚伪时世里难得一见的爱情感受。这是一种长期以来被那些爱情的优美取向与激情取向所遮蔽了的爱情感受。所以,赵丽华的这种爱情诗,固然不无絮絮叨叨的爱情腔,但其中更有孤绝的真情感与真体验。其实,只要直面生命,就能说出本真,问题在于我们更多的时候做得不够诚实——我们只学会了絮叨却没有学会诚实的絮叨!而不诚实的絮叨,就是无病呻吟,就是装腔作势。再比如她的《想着我的爱人》也十分铺陈:“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我坐下来吃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东篱说:这首诗“直接、简单、日常而轻松地呈现了一个人想一个人的彼在状态及内心活动——多么实在、朴素而又确为真理的俗世俗人之爱呀!不矫情,不做作,坦然而豁达,一切看似平常,结尾却陡显智慧——多么出人意料!”[4]83是的,这首同样絮絮叨叨的诗结尾确乎是有些“出人意料”,出什么人的意料呢?出的是那些习惯了在结尾的时候来一个升华的旧文人的意料!可是赵丽华却在结尾的时候用了一个平平静静的降调。这种平静与安闲,甚至也会让韩东感到意外,因为他在《你的手》里是这么写的:“你的手搭在我身上/安心睡去”,写得多么小鸟依人——写得多么矫情!
平平淡淡才是真,赵丽华这种“拒绝矫情”的爱情观,在她作品中的表现是普遍而直接的,比如她在《爱情》一诗中如此直陈:“当我不写爱情诗的时候/我的爱情已经熟透了//当我不再矫情、抱怨或假装清高地炫耀拒绝/当我从来不提‘爱情’这两个字,只当它根本不存在//实际上它已经像度过漫长雨季的葡萄/躲在不为人知的绿荫中,脱却了酸涩”。这首诗写出了“赵丽华的葡萄”,也说出了“赵丽华的爱情”。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曾经以“愤怒的葡萄”描述过自己的庄园感受,现在,赵丽华也通过葡萄意象陈述出自己的爱情理解:口口声声的爱情其实是爱情的酸涩!这一种爱情体会,非过来人,实难说出。这是一种真感受!它的陈述和它的证明,都在这首诗里,明明白白:有多少女性的诗人到达爱情后不是“香消玉殒”?有多少不是诗人的女性进入爱情后不是如入沼泽,进退两难?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她们,这好像是上帝有意的安排:女性是聪颖而又敏感的,要不用一个什么好看的东西把她们迷惑住,如果她们一往而前,她们岂不把世界人生的秘密悉数洞穿一一抖露?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却是对爱情的告别;而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也是对爱情诗的告别。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诗人的爱情诗,应该从“亮光型”,走向“亚光型”。
其实赵丽华的爱情诗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实在”。她也写过一些“矫情的”爱情诗——她毕竟是一个女人。比如她的《或许真有爱情》:“柳树一直以为和不远处的杨树/是纯粹的同志关系/但那天柳树做梦/梦到杨树抱了抱她/再看到杨树/她就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仿佛什么事/真的发生过”。这种爱情的体验极具边缘性,一般的爱情诗写不到这样的边界地带。再比如她的《干干净净》:“亲爱的,你说就是在死的时候/你也会垫在我身下/好使我不至于弄脏受潮/所以我就一直这么干干净净的了”。赵丽华说:“必须承认,诗歌也有时效性。现在读这首很久以前的诗,我牙都酸倒了。赵丽华你曾经这么矫情啊!不仅矫情,而且盲目,而且弱智,而且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缺乏起码的认知……”[5]同样被她认为“矫情”的还有她的《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醒着》:“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醒着/我不能在夜晚的深处想你/我不能再向你身边移动半步/我再也撑不下去的冰壳/只消轻轻一碰,就都碎了/一片一片的冰/一片一片的裸体/一片一片压痛了夜晚”。她说:“这也是我年轻时最初练笔的诗歌。强烈而稍嫌稚嫩的情感,为了加强效果而采用夸张的排比递进手法,有一些造作和夸大其辞的嫌疑。现在读来,微微脸红。”[5]她把这两首诗的“矫情”与“稚嫩”都推给了“年轻时”与“很久以前”,是不应该的。有些人永远都是矫情和稚嫩的。这说明决定一个人矫情与不矫情的,除了时间,还有其他。
二、赵丽华的爱情诗:通脱、透彻但是有些悲观
赵丽华的爱情诗,实实在在而不矫情,不遮不掩而不欺骗,却潜藏着一个危险:它容易经由通脱、透彻而形成一种虚无与悲观。她的《我爱你爱到一半》就从树叶上发现了爱情的一种“不应该”:“其实,树叶的翻动/只需很小的力//你非要看看白杨叶子的背面/不错/它是银色的”。这首诗,通脱中隐含着无奈,无奈的同意中隐含着内心的不快。毫无疑问,赵丽华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深味:爱,除了爱,再无别的意义。如果还有别的意义,则爱当中,也就掺入了非爱;爱,也应该是没有条件的,如果有了条件,则这种爱当中,也就掺了外在。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条件”的爱是那么普遍,普遍得让“无条件”的爱变得无比凄凉。
赵丽华的《朵拉·玛尔》表达的就是这种凄凉:“她平躺着/手就能摸到微凸的乳房/有妊娠纹的洼陷的小腹/又瘦了,她想:‘我瘦起来总是从小腹开始’/再往下是耻骨/微凸的,像是一个缓缓的山坡/这里青草啊、泉水啊/都是寂寞的”。赵丽华说:“写这首诗时,我脑子里同时出现这几个人:朵拉·玛尔、蒙特、张爱玲、卡米尔·克罗岱尔。这几个是分别被毕加索、康定斯基、胡兰成、罗丹疯狂追求,最后又分别丢在人生中途的女人,又都是艺术感觉不在追求和抛弃他们的男人之下的出类拔萃的作家艺术家、几个有境界、有修为,并一直倔强而孤单地活到老死的绝世才女。我为她们集体献上这首诗。越是才华卓绝的女人性格往往越是决绝、孤傲、执拗、不善妥协,在爱情上越是容易被伤得彻底。”[4]26这样的诗和这样的道白,表明赵丽华是一个人生的悲观主义者,她对爱情的态度也同样悲观甚至悲怆。在《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中她说:“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就象一只/张开嘴的河蚌//这样的缝隙恰好能被鹬鸟/尖而硬的长嘴侵入”。但是女人却又不能不渴望爱情,并且唯恐错过生命的花期。赵丽华的《馒头》一诗,看似调侃,实则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她对爱情同样透彻的理解……她感慨女人的命运——那是多么悲剧的命运,但分明是人生的真实,也分明是人生的荒诞。她的《埃兹拉·庞德认为艺术涉及到确定性》即让我们对爱情的虚无深深叹息:“而我恰恰总想写出事物的不确定性/比如我刚刚遇到的一对情侣/不久前还如影随形、如胶似漆/现在他们擦身而过,形同陌路,互不搭理”。赵丽华这种对人生的通透之见与她透彻如水的爱情观,让她对自己诗歌中那些理想化的爱情始终保持着“抒情的控制力”。而这种抒情的控制力长期的存在,却会渐渐形成一种诗歌发现的“冷眼”与“冷口”——那种让人“只感到脊背发凉”[4]105的语气,而这样的冷眼与冷口合起来,又会不会形成她的“诗冷漠”?即如她的《埃兹拉·庞德认为艺术涉及到确定性》,我老是在疑惑:这是诗吗?和她充满画面感的《热水瓶》比起来,这其实更像是一个逻辑的三段论。在这一三段论中,她证明了事物的不确定性,而她用此事物的不确定性又要证明什么呢?是要证明爱情的不可相信吗?
对爱情的警惕与怀疑于是出现——赵丽华有时候甚至还要对它进行戏谑。比如她的《时机成熟,可以试一次》:“我要这样/持续地/专注地/不眨眼地/意味深长地/或者傻乎乎地/色迷迷地/盯你三分钟/如果你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状/我的脸就会/首先红起来”。她描述了一种爱的实验与戏拟。她似乎是触及到了一个脸皮薄厚的问题,其实是触及到了一个爱的坚持与爱的放弃问题,也是一个爱的试探与爱的防守问题。再比如她的《当一只喜鹊爱上另一只喜鹊》,对“爱的装饰化”进行了反感至极的戏谑,却表现为开玩笑般的诗写。这是一首充满了形式探索意味的“跨界、混搭、互文”[4]121的诗歌文本。李以亮说:“这首诗采取了后现代的戏拟、拼贴、反诗的形式,显示了诗人的博学、幽默、反抒情的一面。”[4]121赵丽华的反抒情,在这首诗里,几乎体现为反爱情!她在两只喜鹊热烈的爱情对白之后,却导演并毁灭了这种热烈。所以,赵丽华的爱情诗,要么不说(因为她知道说了反而不好,但是,人们却因此以为她“简单”、“浅显”),要么就开开玩笑。她知道,她也只能这么说(但是,人们却也因此而说她“随意”、“不严肃”)。总之,在对人生的种种并不看好中,赵丽华对人间的爱情尤其持有虚无态度,她的《广寒宫》就是她用黑色幽默般的口气写出了爱情的虚无及其淡淡的苦涩。
三、赵丽华的爱情诗:她的悲观有一种深远的来历
赵丽华是一个女人,拿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女人。一个还算美丽、还不讨人厌、还比较懒惰、还知道自己穿什么衣服最漂亮、还有爱、绝望和脆弱的女人,仅此而已。”[6]赵丽华也是一个内心孤独的女人,如她的《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这首颇堪玩味的诗分明传达着赵丽华至少在写作这一首诗时的内心寂寞。赵丽华也同样是一个向往着爱情并思考着爱情的女人。她对爱情有过一段可谓通透的阐释:“爱情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最低道德和最高智慧。爱情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善与恶。爱情有的时候是义无反顾,是不算计,是疼爱对方超过自己,是无原则的妥协。是堕落,你的爱人是你的鸦片;是飞翔,你的爱人是你的翅膀;是浪费,你们愿意共同消磨所有的时光……”[7]但是,有一天,赵丽华看到了诗人周公度的《好运气的人》:“古代的书上,/有许多好运气的人。/他们爱一个人/就爱到死。//古代的坟墓里,/有许多好运气的人。/他们爱一个人,/就埋在一起。”赵丽华说她看到这首诗,“喜欢的不行”,认为“更加的简单(玩到极简也是拽),更加的朴素(有时朴素到极致也是一种时尚),更加心无旁骛(爱至此,心至此,写作至此,都是一种境界)。爱一个人,就爱到死。爱一个人,就埋在一起。这不仅是好运气,这简直就是我们的大理想(虽然有一些不合时宜)。”[8]原来她向往的是这样一种“古典”的死活都要“在一起”的爱情!原来她向往的是这样一种“真心”的爱情——比如她的《约翰逊和玛丽亚》,赵丽华说:“(那只小波尔羊)即便要去屠宰场了,也仍在意爱情是否真心的问题!所以我极其喜爱这只理想主义的小波尔羊,同时也极其喜爱这首诗歌。并把它作为我的代表作品之一。”[4]72原来赵丽华向往的仍然是理想主义的与浪漫主义的爱情!
其实,对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赵丽华一直在她的诗中反复地表达着自己的理解,如她的《浪漫主义灌木》、《一个农民的浪漫生活》、《雪》等,但是,这一思考的结果,却是她对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绝望及其绝望的表达。这让她的诗歌总体上成为一种比“零度抒情”更为冰凉的“零下抒情”: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巨大的冰冷与绝望。但是赵丽华的这一种冰冷与绝望既与时代无关,也与现实无关。论时代,她总要比北岛顾城他们那一代人幸运得多吧?论现实,赵丽华衣食无愁,且社会地位不低,应该仍然是幸福的,然而,从她的诗来看,她却是不高兴的。然则她的痛苦就可能有着一种更为深远的来历。这一点,恰被牧野看到并指出:“诗人流露出对存在本身的‘人’的不幸和无奈的宿命认识”。[2]276-284
现实中的赵丽华是一个“社会人”——被装饰的人被伪装的人,而诗歌中的赵丽华则是一个“自然人”——真实的人本色的人。真实的人与本色的人其实也就成了抽象的人、超越的人,于是,赵丽华的不幸与无奈因此也就是一种超越的不幸与抽象的痛苦,是一种根性的佛陀式的不幸与痛苦。“一直以来,我感觉我们的诗都太滞重了。我们让诗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历史的,现实的,命运的,道德的,民族传统的,个人信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等等。我很想在我的诗中卸下这些负累,让诗轻松一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轻松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幽默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日常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沉重的生活轻松化,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一些呢?”[9]我能理解赵丽华的这一态度,因为我觉得赵丽华有时候真像一个和事佬、一个人生的劝架者,她所有的话语里似乎都隐藏着三个字:“算了吧”!所以我总是觉得,她的诗不只是“有效地抵消了口语写作浅表型书写的粗浮劣和知识分子的虚伪”,[10]更是对整个民族当下共同语中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放弃责任”的语言倾向一种带有冒险性的诗歌接引。
然而,她的这种爱情表达,却最不能让大众接受,甚至不能让那些自己的爱情本就破碎的大众接受——不只是不能接受,他们甚至对赵丽华这样“无足轻重”的表达有些失望与恼火。赵丽华有一首诗《张无忌(二)》:“张无忌和赵敏接吻/赵敏把张无忌的嘴唇/给咬破了/有关这一吻/电视上处理的比较草率。”大众是多么迷醉于“接吻”的优雅,但是赵丽华却偏要指出“嘴唇/给咬破了”这样的难堪。大众的阅读与接受从来都是“认不同”而不“认同”的。比如大众之所以更喜欢李白,是因为自己不够潇洒,而李白却十分潇洒;比如大众之所以不太喜欢杜甫,也是因为自己窝囊,可是杜甫竟然也窝囊!这当然是幼稚的——只有小孩子才眼馋自己没有的东西。但幼稚恰恰是愤怒的根源,当赵丽华不能满足他们的浪漫想象与爱情想象,大众于是恼火,矛盾于是产生。唐翰存在评论娜夜时说得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资源里缺乏的恰恰就是‘爱’,甚至丧失了爱的能力。在仇恨和残酷的现实里,我们多么渴望那温暖的、柔性的、爱的话语!”[11]可是老唐对娜夜的这种期望,在赵丽华这儿是不存在的。赵丽华至少会从她的诗歌逃往她的哲学(一如她还会逃往绘画)。赵丽华曾写过一首《吸引》,这首诗一开始还是诗的:“像铁钉和铁屑奔赴磁石/我迷醉和惊叹于这种吸引/无法拒绝,身不由己,被拽住,被拽走/被‘啪’地一下粘贴牢/正极遇到负极……”,但是接下来她却陷入了哲学与说教:“你听到的多是些半真半假的语言/顾及面子,或掩饰某种真实/而肉体和思想并行不悖的话语才是由衷的/俗世规则和传统观念把你拽开,拽走/灵与肉搏斗,挣扎,走开/然后更快地弹回来/将肉身撞破/没有人这样告诉你:/‘在你不由自主的时候让思想听凭肉体’/你收拾着碎片,若有所悟/你思考的不会是绝对的真理”。就在我对她这样放肆的哲学皱起眉头时,她却又回到了诗:“就像屋檐上的水,它硬要滴下来/就像春雨过后的幼笋,它硬要拱出地面/就像闪电,它硬要将黑夜撕开/就像这个女人,她忍不住要给你/拒绝如此艰难,因为她需要……”。赵丽华对此“总结”说:“偶尔,哲学能够写出诗,但诗远比哲学美妙。如果你仅仅把诗写到哲学层面你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可以说:哲学的某些偏颇、造作、故做惊人之语等等毛病恰好是诗歌所要着力一刀一刀剔除的。”[4]148那么,谁来接受这样的手术治疗呢?赵丽华已经不写诗了,这把刀子,迟早应该落在我们身上。
四、结 语
赵丽华“原生态”的诗写方向既异于传统又异于常人,尤其异于已渐呈八股之势的中国现代诗,事实上赵丽华曾这样表述过自己的诗歌观:“我认为好的诗歌就是要不拘泥、不造作、不牵强、不说教、不高蹈、不无病呻吟、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不故做清高也不故做下流。就是要在平俗的、被大家惯性的眼睛和感官忽略的事物中找出它所蕴涵的诗性。”[12]是的,赵丽华不只是在诗歌的去魅、自然、本真、生活化的道路上曾经奋勇地前进过,她也在中国爱情的去魅、自然、本真、生活化的道路上奋勇地前进过!
[1]约·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M].刘文飞,唐烈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25.
[2]牧野.浅者不觉深,深者不觉浅——赵丽华诗歌批判[J].诗探索,2002,(3-4).
[3]赵丽华.我的几首爱情诗[J/OL].赵丽华的新浪博客.[2016 -05-14].http://blog.sina.com.cn/zhaolihua.
[4]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诗/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
[5]赵丽华.爱情诗[J/OL].赵丽华的新浪博客.[2016-05-14]. http://blog.sina.com.cn/zhaolihua.
[6]罗晖.赵丽华答罗晖问[J/OL].东方网.2004-06-26.http:// cul.sohu.com/20061001/n245626681.shtml.
[7]赵丽华.情人节写爱情诗[J/OL].赵丽华的搜狐博客.[2016-05 -14].http://zhaolihua1107.blog.sohu.com/.
[8]赵丽华.一首短诗,无比喜欢[J/OL].赵丽华的搜狐博客.[2016 -05-14].http://zhaolihua1107.blog.sohu.com/.
[9]赵丽华.我曾多次写到雨[J/OL].赵丽华的新浪博客.[2016 -05-14].http://blog.sina.com.cn/zhaolihua.
[10]丑石.轻松地玩一会儿——赵丽华的诗歌“策略”[J].诗潮,2003,(2).
[11]唐翰存.玫瑰花开,恰到好处[J/OL].唐翰存的新浪博客.[2016-04-1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d55ce0100 02h1.html.
[12]赵丽华.孤单(诗十首)(网络点评版)[J/OL].赵丽华的新浪博客.[2016-05-14].http://blog.sina.com.cn/zhaolihua.
〔责任编辑 艾小刚〕
An Idealistic Bohr Goat:Zhao Lihua’s Love Poems
Xue Shichang,Ma Chao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Zhao Lihua’s zero style lyrics make people believe that she is more profound than tender.Her love poems,solid and simple,depict the rare true feelings of love in this false world.Her love poems,free and penetrating,develop into nihility and pessimism,and this pessimism has far-reaching origin--unfortunate and helpless destiny understanding of the being itself.Zhao’s poems,and also her love poems,are featured as de-evil,natural,real and down-to earth.
Zhao Lihua;zero style;love poems;de-evil
I227
A
1671-1351(2016)03-0073-05
2016-03-09
薛世昌(1965-),男,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项目“现代诗歌内形式研究”(15XJA751003)及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女性文学视域——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路径与困惑”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