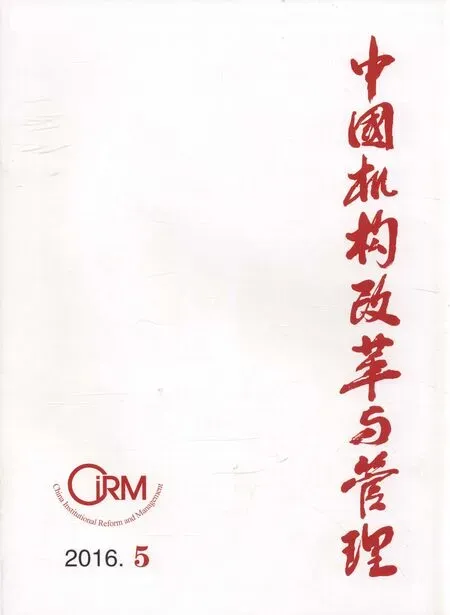论点摘编
2016-02-13
论点摘编
公权力在公益慈善中的作用
2016年4月1日《学习时报》刊登了王名解读慈善法的文章。文章认为,公益慈善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慈善法把公益慈善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社会过程与公权力做了区分。公权力不能强制介入公益慈善过程,不能强制分配公益慈善资源。公权力在公益慈善中如何发挥作用?首先是法治,对公益慈善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一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慈善权);二是建立使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在阳光下运行的机制;三是保障这些资源有效地用于社会的过程。其次是登记、税收等行政权力的运行。再次是出现问题以后的执法和监督。还有培育和支持。公权力是慈善活动很重要的一种支持力量。公权力从税收、购买服务等各种政策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最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不仅要保障慈善行为者,也要保障慈善受益人。具体到慈善法,过程体现为三个环节。一是登记、认定和相应资质的赋予。建立了慈善组织的统一直接登记体制。相对于过去的混合登记体制,这是建立了一种新的体制。与登记相配合的是认定机制,这也是一个新制度。二是监管。此前的监管基本上是入口管理,这次明确实行过程监管,门槛较低,但在登记注册后,要建立一个全社会参与的过程监管。三是支持。这是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慈善法明确的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旨在建立起包括民政、税收以及其他各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多方协调的监管体系。
慈善法具有前瞻性
石国亮在2016年3月31日《中国社会报》撰文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尤其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复杂化、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等因素的推动下,慈善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从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扶贫济困仍然是慈善最主要的功能。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慈善对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精准扶贫、打赢扶贫攻坚战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将传统的以扶贫济困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扩展到科教文卫体、环境保护等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中,体现出慈善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丰富和发展的,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大局。慈善法对慈善活动作出的规定,既能够引导和规范当前我国慈善力量更好地参与扶贫济困,又能够指引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还要把目光投向全球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慈善法对慈善的界定,充分体现了对现代慈善理念的认可,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准确判断。因此,在对慈善法的概念、理念和内容等进行解读时,应更好地凸显慈善法对“现代慈善”的理解。
慈善法将促进慈善组织蓬勃发展
刘忠祥在2016年3月21日《中国社会报》撰文指出,慈善法明确了慈善组织的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和程序,降低了慈善组织成立的门槛。从逻辑关系上分析,首先,慈善组织是非营利组织;其次,慈善组织是以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再次,在组织形态上,慈善组织可以是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组织与一般非营利组织的根本区别是以慈善活动为宗旨,基金会以公益事业为目的,全部属于慈善组织;部分以慈善活动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属于慈善组织范畴,当然是否登记为以慈善活动为宗旨是发起人的自主选择。慈善法没有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做出规定。已颁布实施多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部行政法规都在总则里界定了业务主管单位,并在其后的章节里规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对比慈善法与三部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可以推定,对慈善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审批,改变了实施多年的社会组织“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直接登记使成立慈善组织更容易,慈善组织将会大量涌现。当然,还需要行政法规与之相衔接。
抓紧完善慈善法实施后续工作
2016年3月17日《京华时报》刊登了朱恒顺的解读文章。文章认为,慈善法是我国慈善领域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全面系统地确立起国家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规范。不过,要想实现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仅有一部慈善法是不够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尽快完善相关的税收法律。税收和慈善的关系极为密切,在部分国家,甚至主要通过税法来规范慈善事业。我国慈善领域的相关税收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慈善法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还只是原则性的,这就对税收法律的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对与慈善服务密切相关的志愿服务立法,也有待提速。其次,要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比如,法律中规定了慈善组织认定制度,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但对于不同类型、在不同层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慈善组织,认定程序和制度都有待细化。对于登记和认定之间如何衔接,如何更好地方便慈善组织,也亟待民政部门出台具体的操作细则。与慈善组织登记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也有待修改完善,若没有这些行政法规的完善,慈善组织“设立难”的老问题或许也还会在一些地方出现。最后,执法力量和执法水平也都有待进一步加强。慈善法出台后,大量的慈善组织可能雨后春笋般出现,慈善活动也将更加丰富多样,目前的执法力量能否应对,执法手段和水平能否满足需求,也值得关注。
慈善信托是用许可制还是备案制
2016年4月1日《慈善公益报》刊登了杨思斌的解读文章。文章认为,慈善法专章规定了慈善信托,明确了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有观点认为慈善信托的设立应实行许可制,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慈善信托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委托人、受益人较难监督受托人,因此需要严格的审查;二是税收优惠政策是慈善信托制度激活的重要因素,慈善信托要想获得税收优惠或者其他政策优惠,主管部门的监管至关重要。设立慈善信托不受监管,会给某些人利用设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牟取私人利益以可乘之机;三是在我国慈善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更应对设立慈善信托采取谨慎态度。但是,许可制会大大限制慈善信托的设立和运行,客观上不利于鼓励社会公众发展慈善信托,且许可制不符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慈善法没有采用许可制,也没有全面采用备案制,而是采取了选择性的备案制度,其四十五条规定:“设立慈善信托、确定受托人和监察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受托人应当在慈善信托文件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相关文件向受托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文件报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该项规定,将慈善信托分为需要备案和不需要备案两种类型,前者的设立需要依法向民政部门备案,依法接受监管,享受税收优惠;后者则可以不报民政部门备案,主要适用于小型慈善信托,不享受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