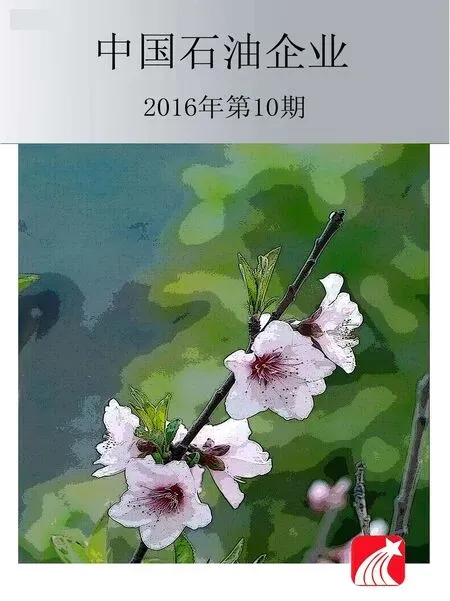“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2016-02-13
“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化解过剩产能绝非简单的物理减量,其要旨在于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产能区域调整和产业资本布局的全面改革。
在中央政府“壮士断腕”去产能决心下,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企业最容易选择“大家一起去产能”,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开始“一刀切”核减产能,这些做法都是对“发力供给侧改革,推进结构性升级”的误读。事实上,供给侧改革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这种“一刀切”去产能做法,实际上是“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化解过剩产能绝非简单的物理减量,其要旨在于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产能区域调整和产业资本布局的全面改革。
去产能,首先要厘清什么是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所谓过剩产能,是指企业成本最低产量与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之差。而企业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污染物排放、能耗、水耗等技术指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该生产能力就是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是个市场判断,落后产能是个技术判断,两者不能简单化等号。一般性产能过剩不是坏事,适度盈余不仅对平抑经济波动有正面作用,而且还是引发企业竞争的动因。而我们要淘汰的是落后产能,也就是哪些技术水平包括设备、工艺等达不到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所规定标准的生产能力。这部分产能不管过剩不过剩,都应该淘汰,否则产业转型升级无法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一些人将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供给结构以实现与需求结构对接。这确实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若局限于此,就忽略了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性改革,没有抓住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推进供给侧改革一定要改革制度,并非有些人理解的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那么简单。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在于从源头上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于提高效率和有效供给能力。实践中,可分为针对主体的改革、针对要素的改革和针对结构的改革。”
就石油石化企业而言,是讲求规模效应的产业,以炼化为例,企业规模和单套装置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世界大型石化公司和国内三大公司所属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印度贾姆纳加尔炼厂能力已达6200万吨,茂名石化炼油能力由1350万吨扩至2000万吨以上,在近40年时间,镇海炼化规模扩大10倍,成为“最赚钱的炼厂”。世界大型石化公司单套炼油装置能力一般超过1000万吨,最大常减压装置规模已达1800万吨,国内三大公司正在实施将其250万-500万吨的装置改造至1000万吨,新建和规划建设的炼油装置单套能力都超过1000万吨。但与国际大型石化公司和国内三大公司所属企业相比,我们的地方炼化在企业规模、单套装置能力等方面差距较大。
根据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截至2015年底,国内年产能200万吨及以上的主要地炼企业145家,总炼油能力为23640万吨/年,同比增长1550万吨,累计产能占地炼总产能的83.6%;年产能在200万吨以下的地炼企业42家,累计产能占总产能的16.4%。前40家地炼平均规模超过400万吨。剩下的上百家产能低于200万吨/年、甚至低于50万吨/年的地炼装置,既没有规模优势又没有质量保障,应该是本轮供给侧改革缩减、淘汰产能的主体。除了规模小,民营炼化企业普遍还面临装置复杂性低、产业链延展度不够的问题,相当多的“茶壶炼厂”纳尔逊复杂性系数普遍在7-8级,这意味着其在产品转化能力上要远远落后于主营炼厂,在未来市场发展中的抗压性也偏弱。客观地讲,民营炼油化工行业属于能源生产和加工制造业,基本特征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统一体,总体技术还处在“通用产品”生产阶段,很少涉及产业链高端,加之生产线分散度高,产品质量档次低;缺乏稳定的物流通道,物流压力较大;生产计划性差,严重依赖订单排产;自主研发投入不足,新产品开发速度慢,多以模仿国外产品为主;分销商层级多,市场信息反馈速度慢,且缺乏信息处理分析系统等问题,已经成为整个行业转型升级的抑制力量。
目前我国炼油市场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主体日益多元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集团市场份额逐年下降,由2005年占比87%降至2015年的64%。二是成品油产量增长较快,消费增幅缓慢,产能过剩明显。2015年我国成品油表观消费量3.16亿吨,同比增长4.3%,低于产量增速1.1个百分点,供大于求不断扩大。随着国家向地方炼厂放开原油进口权和使用权,成品油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三是成品油市场价格扭曲,合规经营企业效益差。随着成品油消费税的提高,偷逃税现象日趋严重,调和油、不合格油品、走私油充斥市场,使成品油市场批发价格已严重低于国家发改委定价,幅度远大于炼厂合理利润。从原油到成品油生产、销售整个链条中,只有加油站环节盈利,而合规经营炼厂则陷入亏损,逆淘汰引发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正在上演。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毛家祥认为:“淘汰落后产能是炼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炼化产业要努力从制造型产业发展模式转变为创造型产业发展模式,避免在数量上‘水大漫灌’,要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行业集中度和竞争力为核心,优化配置资源和市场,积极向集约化方式转变,推进炼化一体化和基地化建设。”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炼油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发展重心加速向具有市场潜在优势的亚洲和中东地区转移。从规模上看,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014年全球共有炼厂651座,平均规模达689万吨,较2003年的572万吨增长19.7%。排名前25的炼油厂总能力达26.28亿吨,占世界总炼油能力的58.9%。从一体化上看,炼化一体化在合理利用石油资源,提高投资收益,降低运行成本等方面优势明显,一般大型炼油企业都配套了相应规模的乙烯装置,并且炼制加工越来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是,我国虽已形成24个千万吨级大炼油基地,总产能占比48.5%,但仍有总产能占比30%的500万-1000万吨/年的中型炼厂,以及总产能占比20%的500万吨/年以下、甚至200万吨/年以下的众多小炼厂。从单套装置规模看,地炼单套装置规模平均仅为300万吨/年,甚至还有10万吨-30万吨/年落后装置。
从整体上看,我国石油化工产业布局多而散,平均规模小,小型炼油企业由于单套装置规模小,作为副产品的化工原料例如烯烃、石脑油、液态烃资源量较少,难以形成炼油化工一体化格局。化工行业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小型企业数量占86%。即使是化工行业龙头企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也存在着产品单系列规模偏小、市场竞争力不强问题。2014年,我国规模以上化肥企业1814家(含复混肥),平均年产量3.8万吨;规模以上农药原药企业713家,平均年产量为0.5万吨;无机化肥原料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多达1857家,平均主营收入只有2.9亿元。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约有60%-70%产品领域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其过剩程度30%-50%不等。其中,尿素产能过剩1800万吨;磷肥产能超过国内需求1000多万吨;氯碱行业全年装置利用率仅70%,聚氯乙烯装置利用率低于%;甲醇装置开工率小于50%;电石行业新增产能400万吨,远超全年淘汰的127万吨产能,装置利用率70%。
产业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较小,不仅制约了行业竞争力提升,还增加了去产能的难度。
“所以说仅仅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完成结构性落后产能出清工作,即便规模很小,市场需求不景气,企业也宁愿在亏损中煎熬,而不愿意主动去产能。因为一旦被淘汰出局,就意味着所有的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更希望行业内其他企业主动去产能,自己能够搭便车等待行业回暖之后带来的市场和利润。”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表示,在炼化去产能战役中,至少有1亿吨落后产能出局。怎样界定落后产能,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去产能模式,将供给侧改革成本降至最低。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结束高速增长期,国内供需矛盾恶化,产能结构性过剩。日本政府结合供需等多方因素制定14大结构性萧条行业名单,主要集中在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等生产资料基础工业部门。不过,日本去产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74-1977年,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加码、税收减免等刺激需求,但收效甚微,结构性萧条依然存在。1978-1983年,政策转向供给侧:一是出台《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处置过剩设备,整体废弃20%落后设备;二是加快企业兼并重组,行业企业数量下降30%以上;三是通过“雁阵模式”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过剩产能。为了防止“把洗澡盆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政府专门出台相关政策保护高端产能。以两次石油危机为标志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结束之后,美国对钢材需求大幅下降,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政府最初也提供包括补贴在内的诸多保护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保护落后产能的最终结果,是拖垮了整个行业,使得美国钢铁业在1998年末开始出现危机,先后共有31家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或倒闭,占全国钢铁企业45%。痛定思痛的美国政府在减税和关税配额配合下,开始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由企业和投资者按市场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最终不仅使美国钢铁业走出低谷,还获得了全球钢铁产业链中高端位置。
“美日在去产能的同时升级了本国产业体系,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姜鑫民表示,我国也应明确划定关停退出范围,设置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资源规模、经营情况、税费缴纳情况等多个红线,凡是有一项不达标的相关产能必须退出。而对于先进工艺和产能予以保护,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如果说“失衡”是当前我国石油化工产业结构性过剩最主要标签的话,那么“均衡”就是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主攻方向。
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关键要实现一系列均衡—这包括体制机制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有效供给程度、工艺技术水平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而提高生产效率,则需要从影响企业运行效率的“洼地”入手,将薄弱环节放在价值链上观察分析,找到影响利润池蓄水功能的短板,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修补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