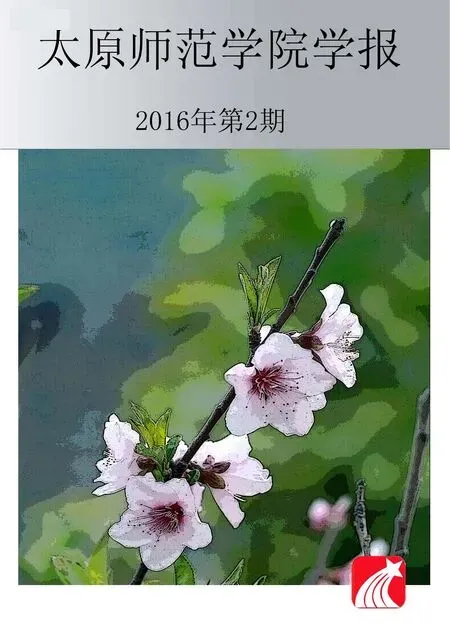论西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创造性疯狂
2016-02-13程艳琴
程艳琴,彭 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论西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创造性疯狂
程艳琴,彭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91)
[摘要]创造性疯狂是西方文学艺术领域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它既源于真正的疯狂,也是对生活中疯狂的模仿。其目的是突破人的有限性和对外在规定性与现实的反叛,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也带有很大的破坏性。结合国内外部分相关研究成果,从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出发,探讨创造性疯狂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表现和意义,并结合现实对创造性疯狂的消极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西方文学艺术;创造性疯狂;精神障碍;模仿
西方关于创造性疯狂的观念早已有之,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等人就提出了“神性的疯狂”一说,此后,不少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都将自己的创造力归因于神灵相助或代神说话。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艺术形式,诗歌及其创作者更是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诗人曾被荷马视为神的代言人,被亚里士多德和雪莱称为先知和预言家,又被西德尼和雪莱分别视为君王和“立法者”。但就是这样曾经被神秘化和神圣化的“诗性的疯狂”如今却常被与现代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障碍相提并论,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被贴上了“疯狂”的标签。曾经被视为人类情感和精神最高表现的文学艺术一下子沦为了精神障碍的表征。本文结合国内外部分相关研究成果,从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出发,探讨创造性疯狂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表现和意义,并结合现实对创造性疯狂的消极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
所谓创造性疯狂,是指作家、诗人或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暂时性地抛开理性和传统的束缚,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原发性体验、想象、幻觉等无理性因素创作出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实现的特殊文学艺术体验或产品的做法。
创造性疯狂与真正的疯狂,即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精神障碍症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创作为动机,一般仅存于创作期间和创作前后,通常在创作完成后通过自觉调整可恢复常态;而精神障碍症为精神性疾病,病因复杂,既有环境因素,也有遗传方面的原因,此外还跟患者的年龄、性别、身体和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相关,发病时间、症状也不尽相同,通常需要专业医生有针对性的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第10版(ICD-10),精神障碍共分为器质性(包括症状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型和妄想性障碍、心境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成人人格障碍和童年与青少年情绪障碍等。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症之间的联系多产生于前者与部分类型精神障碍所导致的心境、情感、知觉等方面的变态反应的相似性,如丰富的联想或想象、紧绷的神经、狂放的激情、幻觉、错觉、分裂的人格、与周围人群和环境的格格不入、对死亡的痴迷等。
鉴于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之间的相似,现代精神病学常将其与真正的精神障碍混为一谈。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有大量研究表明诗人、作家、艺术家中心境障碍、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以此证明“疯狂天才”这一古老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安德里亚森通过对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30位作家的研究发现,有80%的作家经历过情感障碍。而在各种情感障碍中,作家患躁狂抑郁症的比率最高,占到被调查作家人数的43%。安德里亚森因此认为,精神障碍,尤其是躁狂抑郁症与创作有着密切联系。贾米森也通过对历史上著名音乐家、作家、艺术家的传记、信札、作品等的考察发现,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即躁狂抑郁症。贾米森还发现,出生于1705年至1805年一百年间的英国和爱尔兰重要诗人中心境障碍、自杀和因精神问题住院治疗的发生率非常高,这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等。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作家、诗人、艺术家中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发生率也非常高,在安德里亚森的研究中,30%的作家有酒精依赖问题。贾米森在《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以下简称《疯狂天才》)中指出,“在躁狂抑郁症患者中,酗酒和滥用药物的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各种各样无节制的行为都是躁狂的表现特征……”[1]37-38更有甚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维丁、埃默里大学心理学系的凯瑟琳·M·托马斯与马歇尔·杜克等人发现,很多抑郁症患者常出现的认知扭曲都能在诗歌中找到对应,即贝克提出的“跳跃式推理”、“选择性断章取义”、“过度概括”、“夸大”、“缩小”、“归己化”、“非黑即白”,尤其是在诗人患有抑郁症的情况下。[2],[3]维丁等人因此希望文本能够为判断诗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尤其是是否有自杀倾向提供重要信息。
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症之间的联系远非仅仅有些相似的表征而已,在现实中二者的关系还要更加复杂。对于部分创作者来说,创造性疯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后果。为了达到创造性疯狂的效果,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需要跳出常规的情感和认知模式,让自己处于相对陌生甚至扭曲的知觉和极端的情感作用之下,给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心智和情感以巨大的考验,久而久之可能会造成病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和精神错乱,或加重原有的精神障碍症状。罗森伯格认为,即使一般的创作者也都会经历两个重要的隐性思考过程。前者他称为雅努斯思维(the Janusian process)。雅努斯为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有前后两张脸,罗森伯格以之代表同时考虑两种相互对立或矛盾的观念或意象的做法,如黑与白、生与死、起与落、真与假、人与非人等,这些观念或意象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往往同时出现,又因它们之间的对立或矛盾而形成相互撕扯的力量,即张力;后者被罗森伯格称为置换同构思维(the homospatial process),即创作过程中在头脑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形象、声音或文字等叠置、融合以产生新的视觉或听觉等的形象或效果。罗森伯格认为置换同构思维在诗歌、音乐、绘画、雕塑中都有广泛应用。他以“the branches were handles of stars”一句诗为例,说明这里的branches(树枝)被比作handles(手柄)的根本原因是两个词语都含有“an”这个音,二者代表的事物又有着相似的形状,并且都是由木头制成,因此诗人会想到把它们叠置并融合在一起,同时通过这两个词共有的字母“a”诗人又想到了联系二者的纽带——夜晚的星星(star)。[4]14-36罗森伯格的说法是不是具有普遍性还值得商榷,但创作本身涉及超出常规的复杂思维过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雅努斯思维和置换同构思维都不似人们日常以逻辑性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不跳出常规思维的套路是难以做到的。由之产生的观念、想法和景象既有违逻辑,又不合情理,很容易被看作是精神障碍症的表现。但作为创造性思维的体现,创作者在运用这两种思维时是完全清醒和理智的,这从根本上体现了创作者创造性地驾驭个人的思维、情感、素材和艺术形式的能力,也成为创作者与精神障碍症患者的根本区别所在。以充满奇思怪想和不合逻辑的画作而著称的20世纪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就曾说过,“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是我没有疯”。[5]216但不可否认,任何超越常规的思维都会给创作者增加额外的心智与情感负荷,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或加重精神障碍。
反过来,部分精神障碍症也会导致与创造性疯狂类似的体验和感受,对创作起到推动作用。在《疯狂天才》一书中贾米森详尽探讨了心境障碍与艺术气质间的联系,说明作家如何能在轻度或者躁狂状态下进行创作,而躁狂抑郁症的周期性发作有利于作家在“自然发生的、相对立的情感及认知状态之间”感受到“张力和调和”,从而维持创作和生命的继续。朱立安·李布与D·杰布罗·赫士曼也在《狂躁抑郁多才俊》中指出:“躁狂抑郁对天才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6]8与贾米森等人的心境障碍说不同,塞斯则发现,精神分裂患者“过度的自我意识、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反社会性”等症状使他们有可能突破社会禁忌,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7]757部分患精神障碍症的作家或诗人对于治疗的怀疑和抵触似乎也在验证了“疯狂”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贾米森指出,“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相信,混乱、痛苦和极端的情感体验不仅是人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们艺术能力的重要部分。”她援引爱德华·托马斯的话说:“我怀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创作激情最为澎湃之时恰逢情绪低落的时刻——来说,消除忧郁的治疗方案难道不会扑灭我的艺术创作激情吗?”[1]224将精神障碍症的表现与创作直接联系起来的做法固然欠妥,但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在精神障碍症的作用下确实可以获得某些有助于创作的思维方式或视角。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用意识流手法完成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中就根据自己在患病期间产生的幻听及治疗经历成功地刻画了塞普蒂默斯·史密斯这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受战友牺牲刺激而精神失常的人物形象。画家梵高最著名的作品大多完成于其生命的最后两年,而这两年恰巧又是其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两年。同时,精神障碍症的患病经历也可以为作家的创作提供关于疯狂的第一手素材。美国自白派诗人的“精神病院”诗就是源自诗人自身的精神病院经历,如罗伯特·罗威尔的《在蓝色中惊醒》和安妮·塞克斯顿的诗集《去精神病院半途而归》。可见,真正的疯狂可以为创造性疯狂提供素材和养分,但创造性疯狂却未必由真正的疯狂直接导致。除了垮掉派的诗人和作家直接在药物作用下从事写作及超现实主义作家所倡导的“自动写作”外,大多患有精神疾病的诗人和作家并不是在精神疾病发作时完成创作的。即使他们的精神疾病或他们在精神疾病作用下获得的“灵感”得以进入作品的话,这些因素也是在作家或诗人意识清醒情况下有意识地艺术处理过的,是对疯狂的再次体验,也可以说是对疯狂的创造性利用,表现了艺术家对个人经验的控制。彭予认为,书写和表现疯狂对于精神障碍症患者来说不无益处,这有利于“匡正被自我、投射、假象和自我毁灭的无形世界严重扭曲的一切”,从而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9]139-140
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创造性疯狂主要源于人类对自身和现实世界的有限性、文化传统对人的规定性和社会对人的约束性的认识和不满或不满足,是对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疯狂的模仿。南通大学陆永平教授将人的有限性归纳为三点,即“人的个体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人的个体认识的有限性”和“人的自我需求满足的有限性”。[10]91-93正是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激发了人类对于无限性的渴望和憧憬,主要体现在人类掌控生死和命运、超越凡身肉体及充满战争、苦难、失望的现实进入永享快乐与祥和的“彼岸”世界的愿望和人类认识不断向未知领域开拓的决心和勇气。古希腊悲剧中人与命运的抗争、埃及的木乃伊、基督教对于天国的描绘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一不体现了人类对无限性的追求。作为“人类以感情和想象作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这种超越与追求。不同于文学艺术作品中形式技法和思想上的一般性创新与变革,创造性疯狂体现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超常规的体验、感受和认识,它以人作为一切经验、知识的出发点,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无理性特征。这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因此常被当作真正疯狂的表现。
基于针对的对象不同,创造性疯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作为有限存在的个体的人,另一类则是针对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外部因素对人的存在的外部规定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换句话说,前者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超越,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尤其是在情感和知觉方面,通常表现出异常敏感或错乱的神经、有违逻辑的思维、极端的情绪和对现实的扭曲认识,甚至包括超常的想象。爱伦坡作品中异常恐怖的气氛和人物的变态心理、浪漫主义诗歌对于痛苦和死亡的痴迷都可以归为此类。后者则是对现存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化传统以及乏味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本身的抗议,表现出一定的反传统、反社会性。而后者往往被视为现代派和后现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共性。在实际的创作中,一部作品既可以反映对个体的超越,又能同时表现出对社会和传统的不满和抗争。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最能直接表现诗人的情感、知觉以及理想,也是把创造性疯狂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种艺术形式。早在古希腊,人们就意识到仅凭技艺和寻常理智创造不出真正好的诗歌作品。柏拉图指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和代神说话。”[11]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诗是伟大天才的产物,也是‘病人’的事业;一个是非常机敏的人,另一个是‘疯子’。”[8]47然而,最终对“疯狂的诗人”这个观念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当属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浪漫主义之前,古典主义重理性、轻情感,强调优雅、对称、节制和诗歌的教化作用;浪漫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转而推崇大自然、灵感、想象力,强调个人情感和主观感受的表达。华兹华斯就主张“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果说华兹华斯所倡导的情感仍在理性、健康的情感范围之内,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却在抒发人类自然情感与感受的同时开始了向人类理智与情感极限的挑战。柯勒律治靠鸦片乘上了想象的翅膀,完成了充满幻象、绮丽无比的梦境诗《忽必烈汗》。雪莱的《朱利安和马达洛》成为以疯狂为主题和形式的诗歌的早期尝试。而拜伦更是在人类情感的探索中体验到了“疯狂”的味道,一句“我们艺术家全都疯癫”向世人宣告了诗人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职业。[1]2在探索人类感性与情感表达中,诗人常常将自身的理智与情感推到极致,从而置身于精神错乱的边缘。亚里斯多德曾说过,“一个自己处于激情中的人,能够制造出最真实的激动和愤怒”。[8]47
如果说浪漫主义的疯狂更多地体现诗人对个人理性、情感与知觉极限的挑战与超越,那么在浪漫主义之后,创造性疯狂却更多地成为用以突破现行社会制度、道德规范、艺术创作的解放力量。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理性主义受到空前追捧。理性主义无孔不入,从科学到技术、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学艺术到教育,无一不打上了理性的烙印,这一方面促成了人类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的扩展和延伸以及人类物质生活品质的极大提高,但同时也严重贬低了人的情感、感觉经验的价值,成为导致人“物化”的罪魁祸首。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世界看到了单纯追求理性并不能确保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安宁,战争、环境污染等无时无刻不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创造性疯狂成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运动倡导者和支持者抗议泯灭人性的战争的有力手段,一大批画家、诗人以创作表现了现代社会和战争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的幻灭以及人性的压抑与扭曲,从而以疯狂的手段展示了疯狂的世界。金斯伯格的《嚎叫》可以说是这类诗歌的典型代表,当然他的《卡第绪》既描写了真正的疯狂——其母亲的精神病,更细致描写了各种致幻剂毒品——笑气、麦司卡林、麦角酸——令诗人所产生的幻觉。
最后将创造性疯狂与真正的疯狂完美结合的当属美国自白派诗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罗威尔、普拉斯、塞克斯顿为主要代表的美国自白派诗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诗歌作品演绎了现代版的“疯狂诗人”。这些诗人自身多患有相当程度的精神障碍症,并都因此有过自杀未遂或自杀经历。他们不仅毫不掩饰地描写个人的精神病经历、对死亡和自杀的痴迷,还在诗歌中探讨个人对疯狂的体会和认识。他们或应用弗洛伊德关于记忆、创伤等的心理学理论探究个人患病的家族或家庭原因,或通过对现实和文化传统的观照挖掘个人疯狂背后的社会根源。自白派诗人因此也成为当代对“疯狂”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研究新的导火索,人们似乎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疯狂诗人”、“疯狂天才”的直接明证,但他们同时也将研究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了创作与真正疯狂之间的联系,而忽略了创造性疯狂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现象的真实存在。
如上所述,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疯狂是一种特殊的疯狂,它可以源于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正的精神障碍,也可以是对之的模仿,其目的在于实现对个人和社会各种规定性的超越,体现人的终极自由和潜力;创作创造性疯狂与精神障碍症不可等同,艺术并非机械地反映现实,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非可简单量化和衡量。现代精神病学关于“疯狂诗人”的研究无视文学艺术创作自身的特性、不同派别诗人的诗学主张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等而将作品视为个人精神状态的直接写照,带有明显的简单化特征。
创造性疯狂确实带来了西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不少创新和成果,并在批判社会现实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其破坏性和消极的一面。首先,诗人和艺术家在试图实现对经验主体的超越的同时往往容易脱离现实,表现出逃避主义倾向,从而进一步拉大艺术与现实间的距离;而当这种超越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时,有些诗人和艺术家就会铤而走险,借助酒精、药物等有害物质,尤其是当他们的创作关涉个人的生存、声誉和身份地位时,从而不仅使他们自身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同时他们也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其次,创造性疯狂虽然有时带有积极的反叛作用,但它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引起社会变革,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反传统运动最终也只是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文学艺术与公共事务的渐行渐远,导致文学艺术作品的进一步被边缘化。再者,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创造性疯狂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的反映。当个人无法在自己与周围的各种环境因素之间求得平衡时便转而向自身寻找出路,最终将自己逼到崩溃的边缘。因此,对于西方的创造性疯狂,我们要采取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既不能一味提倡和颂扬,也不能完全否定其意义。近年来,国内不断有艺人因吸毒被媒体曝光,我们不清楚他们吸毒的具体原因,但如果认为毒品所导致的暂时性幻觉能够有助于创作的话,那就是颠倒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一种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有违法律,也有违道德,这种创作也就没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M].刘建周,诸逢佳,付慧,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Wedding,Danny.Cognitive Distortions in the Poetry of Anne Sexton[J].Suicide &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2000(2).
[3]Thomas,Katherine M.,Duke,Marshall.Depressed Writing:Cognitive Distortions in the Works of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Poets and Writers [J].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and the Arts,2007(4).
[4]Rothenberg, Albert. Creativity and Madness: New Findings and Old Stereotypes[M].Maryland: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
[5]Rattray,Jacqueline.Analyzing Surrealist Madness Through the Poetry of Salvador Dalí[J].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2008(2-3).
[6]朱立安·李布,D·杰布罗·赫士曼.狂躁抑郁多才俊[M].郭永茂,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Glazer,Emilie.Rephrasing the madness and creativity debate:What is the nature[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9(8).
[8]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郝久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彭予.美国自白诗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陆永平.论人的有限存在的价值规定[J].求索,2005(7).
[11]曾繁仁.试论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EB/OL].http://www.krilta.sdu.edu.cn/getNewsDetail.site?newsId=f9ece2d1-03f4-4bcf-9f51-b81b3f15c694.
【责任编辑冯自变】
On Cultivated Madness in Western Arts and Literature
CHENG Yan-qin, PENG Yu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Beiha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China)
Abstract:Cultivated madness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western arts and literature. It could originate in real madness and be an imitation of it. The purpose is to transcend the finiteness of being human and rebel against external limitations and social realities. It carri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lications. A discussion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theories and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starting wi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ivated madness and real madness, about the features, representation and implication of cultivated madness in western arts and literature. A few comments are also offered on the negative side of cultivated madness.
Key words:western arts and literature; cultivated madness; mental disorder; imitation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2-0074-05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幻觉型诗人研究》(13BWW052)
[作者简介]程艳琴(1974-),女,吉林通化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在读博士。
[收稿日期]2015-10-19
彭予(1956-),男,河南信阳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