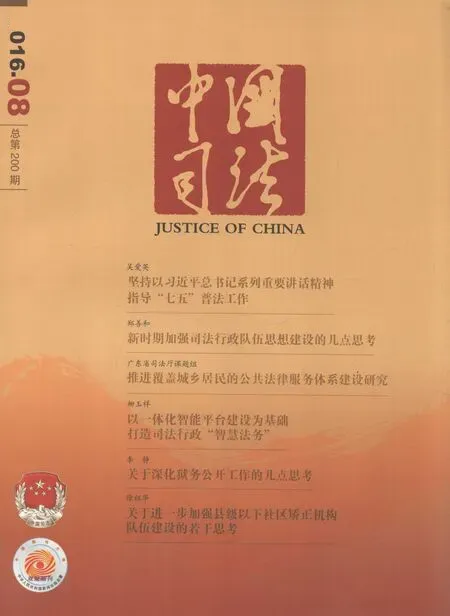言论广角
2016-02-12
言论广角
陈卫东:司法改革应遵循法治理念
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对司法改革来说尤为重要。以法治理念推进司法改革,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依宪改革。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也是司法改革的根本遵循。司法改革规划应在宪法框架内制定,司法改革举措应符合宪法要求。其次是依法改革。改革难免要突破一些法律,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改革不能任性,突破法律就需要获得授权,符合修改法律条件的再修改法律。再次是依程序改革。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司法改革主要是对程序的改革,更需要以合法正当的程序平衡各种利益、吸纳不同意见、规范权力行使,使司法改革的过程成为可参与、可预见、可控制的科学过程。多方参与理念。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多方参与、民主决策有助于汇聚智慧、凝聚共识。多方参与就是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改革中来,进而形成改革合力。多方参与的前提是改革透明、信息公开、广开言路,通过不同渠道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分析专业人士建议和社会公众建议的不同价值。多方参与还要发挥好地方政法机关尤其是基层单位的作用,充分发挥一线司法人员的积极性。多方参与还须正视多元利益关系,防止部门本位主义,避免借改革强化部门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如是说,《人民日报》,2016年7月13日)
张泽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扭转庭前会议实体化倾向,实现由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权责机制。具体而言,应明确将庭前会议的事项限定为程序性事项,并且可以尝试庭前会议主持者与法庭审判者分离,庭前会议的召集、主持由庭前审查法官负责,而法庭审判则由庭审法官负责。其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由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切实有效的辩护,是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重要保障。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展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将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向后延伸至死刑复核和执行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范围仅限于无期徒刑、死刑案件,对于其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重罪案件则不适用,这在实践中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考虑到我国法律援助资源还不充分的现状,可以将法律援助范围扩大至被告人可能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最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以审判为中心要求把定案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并质证,这恰是直接言词原则的要义所在。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如是说,《人民日报》,2016月7月13 日)
朱 勇:彰显法治的力量
法律完成制定、公布程序,发生效力以后,即进入执行阶段。对于公民、法人而言,正在生效的每一部法律都具有严肃的权威,必须严格遵守。而对于法律内容中的瑕疵,可以在严格执行的基础上,通过正常程序向立法机构提出,推动立法机构进行修改、完善。为了树立法律权威、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司法机关就应当发挥好自己的功能,提升自身的“法治定力”。司法机关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者,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形成对法律的遵守与敬畏,与司法机关能否正当履行职责、公正实施法律密切相关。所谓“法治定力”是要求司法机关做到两个自信,即法律自信和功能自信。首先,司法机关必须忠于法律,对于立法机构通过合法程序制定、颁布的法律严格适用。司法机关应向社会表明一种态度,即在司法程序中,生效法律必须获得严格遵守。其次,司法机关还必须对自身功能充满自信,对于进入司法程序的事项,司法机关拥有最终裁决的权威。利害关系人可以发表意见,媒体可以进行评论,但对于事实的认定、法律的运用、行为性质的判定与处理,只能由司法机关主持,其他任何人或机构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的法律自信、功能自信,可以向社会传递一种信息,就是司法机关忠于职守,有能力维护法律权威,并通过司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正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勇如是说,《人民日报》,2016年7月12日)
危浪平:推进律师执业保障制度改革,需要处理好赋权与规范行权的关系
一方面,赋权是执业保障改革的关键。第一,落实三大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赋予律师的各项诉讼权利,严格落实律师在诉讼中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举证、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权利,保障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代理权。第二,完善便利律师行使权利的各项机制,方便律师进入法院、办理立案、会见、阅卷、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事务。例如前段时间出台的法庭规则即已赋予律师与出庭履职检察人员安检同等对待;有的地方已经建立网上律师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立案等。第三,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对阻碍律师行权的,应依法依程序追责;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有关部门要及时处理并作出书面答复;对于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伤害律师的,有关机关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保护措施。另一方面,规范行权是执业保障改革的重要方面。第一,健全完善执业行为规范,特别是要划出律师行权底线,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督。第二,通过不良执业信息公开、诉讼收费标准规范,引导律师自觉遵守行为规范等举措,守护行权底线。
(危浪平如是说,《学习时报》,2016年6月24日)
方工 邢杰:强化司法者职业尊荣感需要多方努力
树立和巩固司法权威,不仅是司法职业自身的任务,也应作为社会建设的内容。通过全社会总动员,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使各类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民众都尊重法治、遵守法律;尊重司法队伍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需要;尊重司法职业中立性、终局性、权威性特点;尊重司法活动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重视程序等要求;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服从依法作出的生效司法决定。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并因此使司法者产生职业尊荣感,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司法环境等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应该在全社会营造弘扬法治精神,遵守宪法和法律,支持司法体制改革,尊重司法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的社会氛围;营造维护司法者正当权利,使司法者不必顾虑依法审理案件、作出司法裁断可能使自己遭到不利境遇,因而能够公正司法的司法环境。树立和巩固司法权威,促进司法职业尊荣感所需要的良好客观条件,不会自然而然自发产生,需要各有关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创造。对此,司法者也是能动的创造主体。尤其是在减损司法职业尊荣感的诸多因素中,也有司法者自身的原因,如履职能力不强导致司法质量不高,道德修养不良出现司法行为不端,滥用司法权力形成司法腐败,等等,这就要求司法者本身负起责任,积极作为,兴利除弊。司法权威、客观环境与职业尊荣感一旦进入良性循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对提高司法者精神境界,保证司法公正,意义重大。
(方工、邢杰如是说,《检察日报》,2016年6月28日)
傅达林:打开法治大厦的每一扇门
法治社会的成长,离不开法律职业人的通力合作。在法治大厦的复杂系统中,立法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等,或许扮演着彼此不同甚至互相制约的角色,但在点亮法治灯塔的大方向上,他们是同路人。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来源,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部活力影响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开法律人职业转换的大门,不仅能优化法治工作队伍的人才结构,还能起到阻滞部分法律职业僵化的作用。事实上,让不同法律职业者从抽象的换位思考变成具体的职业转换,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这种切身体会,就是法治共同体的黏合剂。司法系统实行员额制改革后,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检察官,总体上还只是一种补充方式,但它依然具有很强的破冰意义。当然,人的职业选择有非常复杂的考量。过去法官、检察官向律师的单向流动,固然是因为有职业“玻璃门”存在,也不可否认和个人待遇尤其是经济地位的差别有关。吸引更多优秀的律师和法学专家进入立法和司法的职业序列,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革,通过制度性安排提高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尊荣,增强司法职业环境的吸引力。
(傅达林如是说,《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