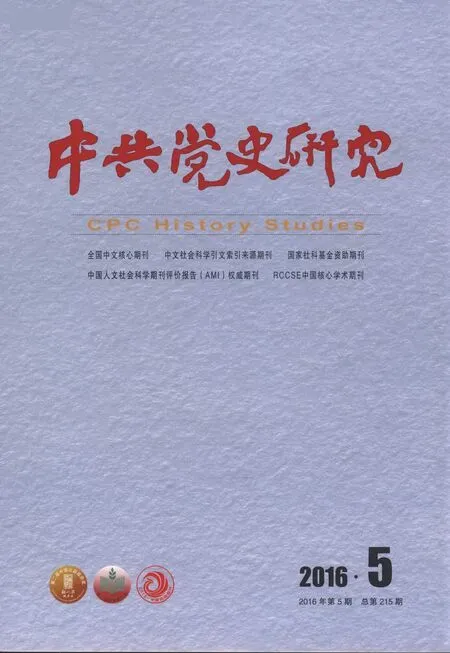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内政权思想的分歧与整合
2016-02-12周家彬
周 家 彬
·探索与争鸣·
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
——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内政权思想的分歧与整合
周 家 彬
自中共二大通过民主革命纲领,中共内部围绕未来政权设计问题出现了瞿秋白的平民本位与陈独秀的国民本位两种逻辑的争论。随着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中共逐渐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政权主体之外,在政权的阶级属性上肯定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在政权发展上强调政权向共产主义革命过渡中的作用。最终,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在“革命民众政权”的名义下整合了党内的分歧。
平民主义;平民政权;分歧;整合
“平民”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目前学界多认为“平民”就是指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这四大阶级,未意识到“平民”的含义不止一个。因此许多研究者视瞿秋白提出的“平民政权”为四大阶级联合执政,并将瞿秋白的“平民政权”等同于中共三大提倡的“平民的民权”*于化民:《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平民政权”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瞿秋白在提出此概念时并未包括资产阶级,但视此为“平民政权”思想的缺陷,并认为瞿秋白随后又将资产阶级列入,强调“平民政权”最终还应该包括四大阶级*参见赵崇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思想研究1920—1927》,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实际上,中共三大提出的“平民的民权”与瞿秋白的“平民政权”完全不同,前者是陈独秀支持的四阶级联合执政,后者则是瞿秋白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
一、分歧:平民本位与国民本位
中共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革命目标。此后,中共内部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形成了平民本位与国民本位两种政权思想。
在中共内部,“平民”主要有两种含义,即“平民主义”之“平民”与“平民政权”之“平民”。“平民主义”是由李大钊较早提出的一个概念,针对的是国内的特权贵族、军阀政治,意在将西方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扩展到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平民”的主体是全体国民,所提倡的核心观念是“自由”与“民主”的精神。*《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但在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中,“平民”的概念已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的阶级主体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是这三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并非学者们认为的所有革命阶级联合掌权*于化民:《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平民政权”思想的演进轨迹》,《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1923年9月,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瞿秋白将资产阶级与平民对立起来,认为“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权主义”,必将压制工人、农民等平民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将“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视为“民权革命中最近的目标”以及“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3—208页。。
在未来政权的设计上,陈独秀最初更倾向于全体国民共同奋斗,提倡政权以全体国民为本位,建立一个涵盖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工人等各阶级的民主政治,通过法律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对于革命胜利后政权的阶级属性,陈独秀并不确定,他认为既可能是资产阶级掌权,也可能是无产阶级执政,但更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比“消极的中立态度”的小资产阶级更革命。总的来看,在陈独秀眼中,国民革命更接近“平民主义”,带有全民运动的特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未来的政权中都有一席之地,其所追求的是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发展。*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33—37、85—90页。陈独秀的主张获得了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中,李大钊对“国民革命”表示了赞同,并号召工人、学生、农民、商人等各阶级“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中,周恩来也表示了对全民性国民革命的支持;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与毛泽东等人联名致孙中山的信件也提倡“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进行全国民的革命。参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70页;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71—75、81—86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95页。。
在大革命初期,陈独秀与瞿秋白在国内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在阶级关系上,陈独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抱有很高期望,瞿秋白则认为资产阶级必将脱离革命;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上,陈独秀强调民族革命是主要任务,瞿秋白则希望两种革命同时进行,逐渐向阶级革命发展。在这两点分歧的基础上,二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权思想,而陈独秀对这两点认识的变化又构成中共政权思想整合的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瞿秋白与陈独秀的政权思想有三点明显的区别:在政权主体上,前者认为主体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限制的对象,后者则坚持资产阶级也是重要的主体;在政权阶级属性上,前者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后者则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担任领袖;在发展方向上,平民本位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奋斗压制资产阶级,建立更有利于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体,而国民本位则并未过多考虑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问题,倡导的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遍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陈独秀与瞿秋白思想的上述分歧,源于二人参照物的不同。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定位的评估与未来政权的构想,源于对俄国革命的实践以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认识。在俄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于二月革命后掌权,这个事实使得陈独秀在思考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时,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随后,他又指出“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足见其政权思想充分参考了俄国革命实践。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53—161页。同时,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渐兴起的国民革命,特别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胜利,也为陈独秀提供了重要参考*黄志高:《1921—1925年中国共产党对凯末尔革命的观察与反应》,《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瞿秋白对“平民”的定义借鉴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当时并未发行中文翻译本,瞿秋白可能看到了俄文版并自行翻译、引用了部分内容,当时被瞿秋白称为“两个策略”。中有关1905年革命动力的描述,即“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其压制资产阶级、准备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设想也源于列宁此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05页。。陈独秀与瞿秋白政治思想来源上的差异,反映出二者在革命探索方式上的区别:前者接触马列原著少,理论水平不高,但很务实,相关认识的形成主要以实践为导向;后者由于理论水平较高,偏重革命理论的推演,用中国革命对接列宁相关理论,以列宁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
中共政权思想中的分歧,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有关中国阶级状况以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等争论的影响。马林一直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阶级革命持消极态度,认为中国社会分化不明显,“现代工业工人的人数仍然很少”,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推进中国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12、20—21页。。维经斯基则指出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巩固和扩大共产主义组织”,虽同意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但要注意“揭露资产阶级在争取各省自决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坚定性和观望态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7—120页。。维经斯基还反对马林有关中国阶级分化尚不明显的论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地分化”,并且“在组织上因而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为国内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1919—1927)》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国共合作的条件应是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52页。。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尚未提出遏制资产阶级的问题。
共产国际起初非常支持马林的主张,指示中共迁往广州,配合马林准备国共合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21页。。但随着1922年秋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大会被驱散,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更加强调共产党自身的壮大。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拉狄克代表俄国共产党在会上提醒中共要注意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建立“牢固的根据地”,扩大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中的影响,防止悲剧重演*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84—93页。。共产国际四大认可了拉狄克的观点,《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组织自己的力量,为实现工农“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第584页。。1923年1月,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虽然认可各阶级联合革命的主张,但同时要求中共保持自身严密的组织机构,“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1923年2月马林离开俄国后,共产国际内部发展工人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有可能投向国际资本主义的怀抱,主张“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撤销马林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身份,消除马林观点的消极影响,增加对中共的物质援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39—241页。。另外,东方部还委任与马林意见相左的维经斯基起草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重申无产阶级要壮大自己,掌握领导权,将自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8—80页。。身在中国的马林坚决反对共产国际决议,他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将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须将工人运动置于联合其他阶级的民族革命中,服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9—460页。。
1923年6月,在上述分歧的影响下,中共三大召开。会间,代表们围绕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争论,特别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更引发了激烈争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80页。。马林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要求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不再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认为中共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先学习民族自觉再谈共产主义。陈独秀支持马林的观点,指出“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86—296页。瞿秋白虽然承认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也赞同加入国民党,但仍旧希望减少甚至消除资产阶级的势力,提出以无产阶级改造国民党,防止资产阶级控制革命。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支持瞿秋白对阶级问题的分析,反对资产阶级掌权,认为革命动力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会上,蔡和森还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指责陈独秀放弃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68—481页。
结果,马林和陈独秀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意见。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承认“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共产党无法建立成群众性政党,应当加入国民党,携手其他革命阶级共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页。。同时,新党纲明确指出目前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无产阶级要“唤醒农民”,“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觉醒,“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这里所谓的“平民的民权”,即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政权,是面向各个阶级的政权,其主要政治主张如取消不平等条约、实行普遍选举、保障自由权、推行地方自治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范畴,与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并非一个概念*许多学者认为中共三大的“平民的民权”等于瞿秋白提出的“平民政权”,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5—143页;赵崇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政权问题的探索》,《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7月1日,陈独秀致信萨法罗夫,告知中共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农民难以发动,而资产阶级既有力量也有意愿反帝反军阀,因此目前“只能进行国民革命”,并应收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1—262页。。
1922年至1923年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内部围绕中国阶级状况、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以及未来政权规划,形成了两种观点: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还不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资产阶级推行民族革命是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因而未来的政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政权;瞿秋白、维经斯基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无产阶级终将与资产阶级决战,反对在民族革命中忽视阶级斗争,反对抬高资产阶级的地位,主张大力发展工人运动。瞿秋白更进一步主张在未来的政权中,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压制资产阶级。马林、陈独秀的意见在中共三大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争议并未消除,分歧仍在继续。
二、转变:中共对资产阶级的失望与反感
中共三大后,中共内部的争论仍在延续。陈独秀继续反对过多地强调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1—262页。。瞿秋白则于1923年9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详细阐释以限制民族资产阶级为特点的“平民政权”思想*《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93—224页。。但总的来说,受到关余事件、学潮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日趋反感。受此影响,中共有关国内阶级关系以及民族革命与共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为随后政权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在关余事件中,中共意识到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消极态度。1923年12月初,孙中山着手准备从外国人手中收取粤海关关税盈余。对此,陈独秀积极支持,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受关税问题侵扰,对于此次孙中山的行动“当十分热心”*《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74—175页。。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应却出乎陈独秀意料,《银行周报》和《钱业月报》共同刊登了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积案业公会联名反对孙中山截留关余的申明,声称关税本应用于偿还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截留关税会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希望孙中山放弃此举*《请孙中山保全关税以裕基金》同时载于《钱业月报》1923年第3卷第12期和《银行周报》1923年第7卷第47期。。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反应十分不解,表示“不懂得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种什么特别心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74—175页。。
国共合作中的摩擦加剧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1923年11月,中共广州团地委希望通过改组广州学生联合会整合学生运动,遇到民权社的反对,中共对此非常反感,认为它已经被国民党右派收买,并斥之为“反动派”。1924年5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因校方禁止组织学生会向国民党求助,中共希望借此从教会学校中收回教育权,指示学生发起退学风潮。但国民党对此态度比较消极,例如孙中山认为学生既然已经选择在外国人的学校学习,就“应该牺牲一切自由”,对于学生退学的举动,孙中山仅表示“亦属可嘉”。*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年—1924年)》,内部出版,1982年,第214—215、398—399、477页。中共创建广东工人联合会,希望以此统一广东工人运动,却遭到与国民党渊源较深的广东机器工会的竞争与挑战,导致中共在广东兵工厂中“受机器会派之攻击”,无法在上层发展势力;在电灯局、自来水厂内“因与机器(会)对抗关系,皆不能活动”*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广东区委文件(1921年—1926年)》,内部出版,1982年,第76页。。农民运动也遇到广东许多地方政府的限制甚至压制。另外,国民党人办的《香江晨报》和商人办的《香江晚报》经常发表非难中共的言论。*《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年—1924年)》,第491—492、362页。对于上述事件,中共理解为“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认为他们“趋于妥协”,“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很难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页。。此时国民党认为“商人实为本党之主力军”,视资产阶级为革命之主力*《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中共将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看作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消极态度也在所难免。但无论中共将国民党右派视为资产阶级代表的看法正确与否,右派的进攻确实增加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失望。
此时,中共内部对资产阶级的失望与不信任十分普遍。邓中夏认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资产阶级“总不免为了身家,赡顾却虑”*《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41页。。恽代英更指责资产阶级的“福利便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夺别的国民”,要求“革命政府必须侧重农工游民乃至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唤起多数国民的参加革命行动”,为此应该对资产阶级“稍加裁抑”*《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6—471、497—506页。。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在中共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尚不明显时,陈独秀仍旧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运动要重视资产阶级,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要配合资产阶级。国民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在关余事件以及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后,陈独秀意识到资产阶级并非如他之前所想对国民革命采取积极态度,开始对其产生失望情绪,转而呼吁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并一改以往的观点,认为学生、小农、小商等小生产者比资本家更有力量,远离劳动阶级将使国民党战斗力逐渐衰弱。*《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156、161、300—301页。
资产阶级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表现,加之维经斯基取代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导致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开始转变。虽然中共中央也承认,自“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发展并不理想,“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4页。。但在1924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中共彻底否定了此前马林提出的先学习民族自觉再谈阶级斗争的观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86—296页。,转而认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人民普通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不需要专门学习,“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澈底”,因此要“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同时这就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的方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3—244页。。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改变了三大对国内阶级状况以及民族革命同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更加强调资产阶级妥协性,提出以阶级斗争推进民族革命。
扩大会议后,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持续恶化。8月上旬,粤海关查获广东商团走私入境的大量军火。商团随后实行罢市,最终发生了叛乱。在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下,10月15日,商团投降,叛乱平息。中共党内大多数人将此视为买办阶级的进攻,如瞿秋白表示商团事变“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640页。,蔡和森将商团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58页。。彭述之则将批判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商业资产阶级,认为“商业资产阶级即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分子”*《彭述之选集》第1卷,十月出版社,1983年,第148—154页。。陈独秀更对整个资产阶级表达了失望之情。1924年8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79期上发表《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和《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两篇文章。前者并未明确谴责买办阶级,批评的对象是一个更为模糊、含义更广的概念——“商人”,认为商业资产阶级向来拥护陈炯明,是革命的重要敌人;后者则直接批评工业资产阶级,认为“中国实业家不赞助国民革命运动,真是自灭的蠢物”*《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345页。。在一期刊物上同时批评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可见陈独秀此时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失望与反感。此后,陈独秀在文章中曾一度不再明确区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渐以“商人”“资本家”“富商”等词统称资产阶级,并将资本家置于共产党的对立面*《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343—344、360、391—392、406页。。作为此时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称商团为“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认为中国人民深受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要注意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这两方面的斗争*《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21页。。
1924年10月,广东商团事变刚结束,北京又发生政变,中共借孙中山北上逐步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虽然中共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一起促成国民会议,但又区别对待各阶级,标榜维护“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的特殊利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05—306页。。陈独秀视工农小资产阶级等下层群众为运动主力*《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409页。。彭述之更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成分居多”,“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资产阶级“必然还是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184页。。
在国民革命之初,陈独秀曾对资产阶级革命性抱有极大期望,但实践结果让陈独秀乃至全党逐渐对资产阶级丧失了信心。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革命——可能革命但有妥协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转变,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先民族革命再阶级革命——以阶级革命促民族革命”的变化。中共这两个认识上的转变为后来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整合: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提出
1925年1月,在对资产阶级普遍失望和反感的情绪中,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开始强调国民革命向阶级革命过渡的问题。五卅运动后,中共更加明确政权的主体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并于1925年10月正式提出“革命民众政权”思想,完成了党内政权思想的整合。
中共四大改变了三大关于阶级的判断。中共三大对资产阶级革命性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0页。。在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中共虽然意识到资产阶级具有严重的妥协倾向,但并未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只提出“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对其参加革命尚抱有一丝希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3—244页。。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中共四大除指责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属性外,还指出工业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形成,处于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工业资产阶级的过渡之中,因而“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认为真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主、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阶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2—333页。。中共四大的阶级判断还体现在对国民党的认识上,明确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阶级属性:左派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激进分子;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右派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8页。。将资产阶级划入右派,足见资产阶级已逐渐被中共视为反革命。此后,中共在策略上虽不时提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甚至呼吁其加入“国民的联合战线”,但在革命性的判断上,始终坚持资产阶级有“出卖群众运动”“抛弃全民族利益”的趋势,警惕其反革命的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148页。。
在此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中共更加重视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以及国民革命向共产革命的过渡问题。中共四大认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要在民族革命中为阶级革命做准备。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既要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将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此外,在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中共不再以国民运动为中心,看重工人运动对国民革命的推动作用,而是强调二者共同发展,既以阶级斗争促进国民运动,更以国民运动“增厉阶级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7、336—338页。从中共三大认定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到1924年扩大执委会重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再到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共产革命做准备,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剧变,越来越接近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工人阶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引起了中共对于政权问题的强烈关注。五卅运动以工人的阶级斗争为起点,吸引了各阶级共同参与。这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用实践证明了四大关于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共同发展的论述,增强了中共依靠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赢得革命的信心。瞿秋白就曾断言,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同时,五卅运动中发生的屠杀惨案引起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重视。陈独秀认为“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因此呼吁建立全国性机构统一协调运动,武装民众,组织自卫团,以此对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屠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第488、500页。。
1925年10月,中共召开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提出组建“革命民众政权”是当时的紧要问题。扩大执委会继承了中共四大关于阶级问题的判断,即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日益反动并背叛民族革命。因此,所谓革命的民众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排除在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0—468页。。“革命民众政权”以“革命”这一界定词,鲜明而巧妙地将资产阶级排除在未来政权之外,表明中共正式放弃了陈独秀以国民为本位的政权主张,接受了瞿秋白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思想*部分学者根据瞿秋白《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建立“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的政府”的呼吁,认为瞿秋白改变了对资产阶级的排斥态度,并将其纳入“平民政权”的范畴。实则此时瞿秋白并未对“平民政权”思想作出上述修正。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瞿秋白就已经明确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只剩得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全国的小农,小商人,客观上十分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革命。”此后,瞿秋白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判断。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瞿秋白虽然呼吁建立“国民会议的政府”,但此中的革命势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识界及一般被压迫平民”,所指仍旧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并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所设想的未来是“创造劳农平民自己的国家”。可见,瞿秋白并未将资产阶级纳入其“平民政权”思想中。参见赵崇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思想研究1920—1927》,第192页;《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90、403—411页。。此外,由于中共自四大开始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向共产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革命民众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发展前途与瞿秋白提倡的“平民政权”并无二致。这表明,中共实质上认可了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但在形式上以“革命民众政权”思想这一新的名称整合了党内的分歧。
对于中共日益激进的政权主张,共产国际并未立即认可,反而认为中共过于乐观。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维经斯基大力支持发展工人运动,但反对中共与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表示虽然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的行为,但“资产阶级脱离过程很复杂”,“不能认为这种脱离是最终的脱离”,资产阶级“还是很革命的”。瓦西里耶夫甚至直接指出,中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以及中共自身地位等问题的认识“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54、678页。1926年2月至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赞成中共四大以来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判断,认为五卅运动显示工人阶级“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但对于资产阶级的评价,决议延续了维经斯基、瓦西里耶夫的看法,即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某些阶层退出了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资产阶级都是敌人,指示中国革命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未来政权也要建立在此联盟基础上。这里所谓的城市民主派,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136页。共产国际此时并未改变联合资产阶级推进民族解放运动的策略,因而并未将其排除在政权之外。
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权问题。北伐军迅速占领两湖地区,让共产国际领导人眼前为之一亮。布哈林感慨道:“中国革命越来越成为吸引东方殖民地日益觉醒的群众的伟大中心。”胜利在望,未来政权的规划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共产国际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担心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一系列让步,“使中国今后走上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处于外国资本主义集团的友善保护之下”。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民主专政”,预防资产阶级出现“脱离革命或企图反对革命”的情况,保证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146、279、283页。共产国际正式认可中共“革命民众政权”思想。
由于陈独秀转变了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中共四大改变三大以来的阶级判断,否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强调国民革命对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更加重视向共产革命过渡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的扩大执委会提出“革命民众政权”,为党内关于政权问题形成的两种逻辑间的争论划上了句号。这一思想也最终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四、总 结
中共二大以后,中共在国内阶级关系以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上的认识经历了重要转变。起初,马林、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力量也大于无产阶级,因而希望中共以民族革命为主要任务,使阶级斗争让位于民族革命。维经斯基与瞿秋白等人则对资产阶级持以谨慎的态度,更加重视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瞿秋白甚至提出在革命中压制资产阶级。但关余事件、学潮事件使得陈独秀等人对资产阶级日益失望,中共遂提出以阶级斗争推动民族革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消极态度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中共逐步否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提出以民族革命推动阶级革命。总的来看,中共对资产阶级的评价经历了“革命——可能革命但具有妥协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变化,在两种革命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先民族革命再阶级革命——以阶级革命促民族革命——以民族革命发展阶级革命”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党内关于政权问题形成的两种逻辑——国民本位与平民本位,逐渐走向一致。最后,中共中央在“革命民众政权”思想的名义下整合了党内关于政权问题的分歧。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吴志军)
From Class-Oriented Regime to Revolutionary People Regime——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the Theory of Regime inside CPC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Zhou Jiabin
Since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approved their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ogram, about the future regime, controversy was aroused by Qu Qiubai’s class-oriented political theory and Chen Duxiu’s nation-oriented political proposal. As it changed the understanding of class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class revolution, CPC gradually excluded national bourgeoisie from the future regime, confirmed the leadership of proletariat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to communism on the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ime. At length, Qu Qiubai’s class-oriented political theory obtained the predomination inside CPC and two different theories of regime were converg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Regime of People”.
D231;K26
A
1003-3815(2016)-05-0093-09
*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