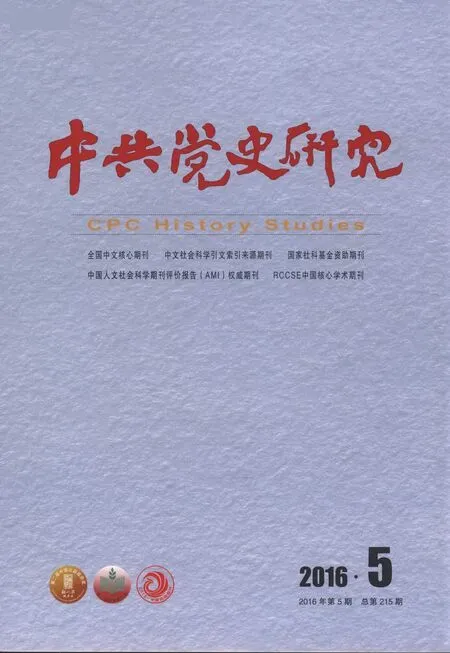国家与都市之间:上海劳模形象建构与流变的个案研究(1949—1963)
2016-02-12刘亚娟
刘 亚 娟
国家与都市之间:上海劳模形象建构与流变的个案研究(1949—1963)
刘 亚 娟
黄宝妹最初以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但她积极引领潮流、打扮入时,极大地区别于传统纺织女工的形象。尽管有关方面一度纠正青年女工中存在的“消费主义,向往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之倾向,但黄宝妹享有国家设置的政治正确性与阶级优越性,一方面迎合了当时上海隐而不彰的灰色情调,回应了其都市文化中有关时尚的记忆;另一方面,她成为上海显示城市地位的标志和中共暗示工人阶级优越性的样板,更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代言人。阶级出身、政治身份、女性特质是摩登劳模形成的关键,中共塑造“工人阶级”在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是其存在的空间,而国家性与上海地方性之间的共谋共生则推动了这一形象的流行。
劳动模范;摩登;新国家;老上海
在现当代中国劳工政治的议题中,“女劳工”因兼具“性别”与“阶级”等多重符号格外引人关注。学界一般认为女劳工的女性身份往往让位于政治身份,性别意识形态被阶级意识形态所取代。与之相适应,大量的学术成果聚焦于“铁姑娘”等农村女劳动者,并以此为主体建立起毛泽东时代女劳工的经典形象。这种“去性别化”的女性形象与新中国前十七年间的主流叙述对于生产者须“革命化”的鼓励相适应,因而被普遍接受,而与之存在差异甚至相悖的劳工形象则遭屏蔽,以致在诸如上海等大城市生活的女劳工至今仍面相模糊。
鉴于此,本文将注意力聚焦于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上海纺织女工黄宝妹*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电影《黄宝妹》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徐大慰对于“大跃进”时期女劳模影像的研究,但其研究侧重于劳模的革命意识形态,与本文旨趣多有不同(徐大慰:《上海女劳模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953年8月,22岁的黄宝妹被纺织工业部评为劳动模范,此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五次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她三次出访苏联,曾是多个国际会议的座上宾客,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青年工人的标志性人物。尽管她最初以劳模身份走进人们的视野,却以美丽时髦的形象大放异彩。她外表光鲜,活跃于艺术舞台,得到国家媒体的大力宣传,在新上海引领着一种合法的时尚。
从纺织女工、劳动模范到工人影星、工人大学生,看似相互矛盾的诸多形象在黄宝妹身上得到了统一。她的个人历程不仅有助于讲述一段鲜活的一个人的故事,更有利于放大性地展示1949年后新国家与老上海基层社会在多个层面的纠葛。本文冀望以此个案为视角,以1949年后的上海为空间背景,以关于黄宝妹的口述访谈、个人照片与自传、开放档案、中外报纸等多种史料配合,更新学界在相关议题中的既有认知。
一、劳动竞赛的展开与劳模黄宝妹的出炉
黄宝妹193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东镇川沙县麦家宅。母亲来自山东,父亲是盐城人,全家以卖豆腐为生,收入微薄。家中有兄弟姐妹三人,黄宝妹是家中大姐,并未接受过任何教育。1944年,黄宝妹进入日本裕丰纱厂从事细砂挡车。她继承了母亲的外向性格,聪明灵巧,很快就成为车间的生产小能手。1948年,裕丰纱厂改为中纺十七厂,黄宝妹重回车间。同年,她与弄堂里的邻居、十七厂钢丝车间工人吴华芳结婚。次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黄宝妹继续在上海市国棉十七厂二纺细纱车间做挡车工人,延续着一个普通纺织女工的日常生活轨迹。*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
1951年8月,纺织工业部、中国纺织工会发出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通知。10月,上海派出21人参加在天津召开的织布工作法会议,回沪后相继在各棉纺织厂组织工人学习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与“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掀起了改进操作法、提高生产效率的热潮,并在各厂普遍开展劳动竞赛。*施颐馨等编:《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64页。“郝建秀工作法”为解决当时纺织业普遍存在的难题提供了一剂药方,适应了黄宝妹所在的国棉十七厂“提高产品质量与降低成本,节约用棉、用纱量”*《国棉十七厂党委会关于完成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与任务的初步总结及一九五三年工作的计划大纲》(1953年1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2-41。的需要。黄宝妹因在厂里生产成绩优秀,作为工人代表被派去学习。在回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过程中,她不仅创造少出皮轧花的纪录,还带头在三线罗拉细纱机上安装能提高质量的红芯子,并进行一般性的小检修。1952年11月,黄宝妹被评为“车间一级郝建秀工作法先进工作者”。同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历表(黄宝妹)》(1954年2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52-2-95-157;《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登记表(黄宝妹)》(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658-10。
1953年3月18日,纺织工业部和纺织工会发布《关于总结、评选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模范及其他部门创造与推广先进经验的模范的联合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纺织工业劳动模范。4月2日,中国纺织工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开展以“减少断头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开展以减少断头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工人日报》1953年4月15日。会议对评模条件等进行了规定,除突出“认真执行郝建秀工作法、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等要求外,还特别指出候选人应是“一贯积极学习政治、文化、技术,积极学习苏联经验,接受新鲜事物,进步最快者”*《中国纺织工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评选纺织工业全国劳动模范》,《工人日报》1953年4月29日。。黄宝妹经历了从生产小组到市里的层层评选,最终以积极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创造出看650锭的全厂细纱看锭新纪录、比车间平均白花率降低44.43%的生产成绩*《青年团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黄宝妹的优秀事迹的介绍》(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578-1。、“没有读过书,却能看《劳动报》”以及积极学习政治文化等事迹,被评为1953年全国纺织工业部劳动模范*《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登记表(黄宝妹)》(195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658-10。黄宝妹印象最深刻的先进事迹是“没上过学,却能看《劳动报》”这一条。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
基层工厂虽在评模过程中表现积极,但劳模当选后却是另外一幅生态。当选后劳模的社会活动激增,不少青年劳模就坦言“吃不消”*《三天里面就有一天不能学习 金秀兰吃不消这些额外负担》,《青年报》1953年4月17日。。“被部分落后群众打击”“受了委屈”“情绪低落,因此生产稍有下降”等情况也屡见不鲜。除被动陷入“无法劳动”的窘境外,也有不少劳模“自满起来,看不起人,严重脱离群众”。*《三年来上海市劳动模范工作情况报告》(1953年4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1-114-3;《上海市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情况和今后培养劳动模范的意见》(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1-15-62。而与上述劳模不同,评模后的黄宝妹的表现颇令国棉十七厂满意,该厂党委多次提到“黄宝妹成为劳模还虚心向群众学习”,“不仅自己学好工作法还发动大家学会”*《中共上海市国棉十七厂委员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工作简报》(1953年11月16日—11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2-41。,甚至“外出开会,即使很晚回来,也要到小组里去看一下”*《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
黄宝妹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成为工厂的标志性人物,尽管在国棉十七厂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顺利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但在1953年全国纺织工业部评选的106个劳动模范中,黄宝妹只是其中平凡的一个。即使在上海纺织女界,黄宝妹既没有杭佩兰的资深履历,也不及裔式娟领导的小组负有盛名,甚至没有张秀珍等私营工厂工人的特殊符号*《时时把人民的需要记在心上,张秀珍钻研技术提高质量》,《劳动报》1953年8月7日。。按照一般的规律,全国劳模的光环会在数年间消退,黄宝妹也将很快被后起之秀超越并取代。然而,一个并不特殊的机遇使黄宝妹显示了自己的独到之处,从而在庞大的女劳模群体中脱颖而出,产生出超越普通劳动模范的另一种象征意义。
二、“学习苏联”与摩登初现
1954年4月底,黄宝妹作为劳模代表赴苏联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临行前,她特地做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缎子长旗袍。到了莫斯科,她看到苏联女工们都穿着花衣服、花裙子,头上扎着花头巾,“美丽极了”,相比之下,自己的服装黯然失色。*黄宝妹:《我决心带头穿起漂亮的服装》,《新民晚报》1956年3月5日。她还注意到苏联人喜欢唱歌,特别喜欢跳交谊舞。苏联之行是黄宝妹首次走出国门,在异国的见闻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她开始学习跳交谊舞,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她烫了头发,又立刻做了两件布拉吉(连衫裙)。*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
劳动模范既是劳动明星,更是政治正确性的样板,不仅需要在生产上发挥先进作用,还“需要在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教育”*《劳模工作情况》(1953年4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C1-1-114-3。。回国后的黄宝妹被派往各地作报告,内容是宣传苏联。在报告中,她开始以全新的美丽形象出现,而最常穿着的就是颜色鲜艳的旗袍和在当时颇为时髦的布拉吉。起初,黄宝妹小心翼翼,习惯在花裙子之外披上暗色的长款大衣或蓝布衫加以遮盖。但观众的积极反馈给了她信心,她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黄宝妹的形象有别于传统纺织女工,在女劳模之中也属另类。但这一形象的产生并不偶然,它脱胎于新中国的政治宣传与老上海基层社会的空间之中。
近代上海以“崇洋”为特征,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崇洋趋新主要以“西洋”为参照、以欧美为标杆,那些人高马大的白俄人常被剔除出“外国人”的范畴之外,有些人甚至沦为所谓“罗宋瘪三”*程乃珊著,贺友直图:《上海FASHION》,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32—133页。。1949年后,中国逐渐确立了政治上一边倒的模式,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群众运动。电影、音乐、文学、展览、派遣专家、讲演报告以及互访形式,都成为进一步宣传苏联先进性的途径,其中又以苏联的文化输入效果最为明显。万紫千红的苏联花布成为“新鲜”事物,苏联鱼子酱也成了洋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对于上海人而言,总比《小二黑结婚》等乡村爱情故事更能产生共鸣,上海青年群体开始热衷于唱俄罗斯民歌,很多人还追起了苏联明星*程乃珊著,贺友直图:《上海FASHION》,第138页。。“摩登女郎”作为近代上海的代名词,与“洋”构成了上海都市性最明显的特征。1949年后,女工在工资待遇等方面逐渐得到改善,稍有了一些追逐时尚的资本。但工人长期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朴素的工作服在政治宣传中的合法性与标志性都构成了一种束缚。有女工刚进厂时,打扮得比较漂亮,还烫了头发,就被人斥责为“小阿飞”“作风不正派”。只要“穿得漂亮一些”,便有人说“跟资产阶级学样”。*吴秀莲:《穿花衣服不该受责难》,《解放日报》1956年3月7日。在追逐时尚的弄潮儿中间,青年女工成为最为积极又尴尬的支持者,她们有心追逐摩登却无力摆脱束缚。在此背景下,黄宝妹的出现显得恰到好处。
黄宝妹的形象既迎合了“学习苏联”的政治宣传,又满足了上海基层社会的文化需要。依托于这一摩登女工的形象,上海将近代以来以西洋为标杆建立起来的“崇洋趋新”加以改造,并与新中国“向苏联学习”的思路相结合,将学习苏联转化为崇另一种“洋”,从而在文化心态上找到了另一个支点,黄宝妹的摩登形象因此迅速流行起来。党报记者努力捕捉黄宝妹的身影,有时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华东工业青年先进生产者会议在本市开幕》,《文汇报》1954年10月19日;《更正》,《文汇报》1954年10月20日。。伴随新闻报道而来的是众多青年男读者的青睐,求爱信纷至沓来,黄宝妹一时成为大众情人。厂党委及工会不得不派专人负责回信拒绝,《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报道,介绍黄宝妹一家讨论宪法的情景,借此暗示黄宝妹已结婚生子,帮助其解除困扰*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169页。该书系黄宝妹口述的自传。另参见陈瑞枫:《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记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黄宝妹家讨论宪法草案》,《人民日报》1954年8月19日。。
除了在报告时以新形象示人,卷发与布拉吉也逐渐成为黄宝妹的日常装扮。她穿着布拉吉到厂里,小姐妹起初看了也都很奇怪,问她“怎么穿这样的衣服?”但黄宝妹则以“一定要向苏联人民学习,穿得美丽一些”为武器捍卫自己的形象*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后来厂里一些青年女工看她穿着漂亮,也做了布拉吉穿在身上*汪求实:《百姓生活记忆:上海故事》,学林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与“见了毛主席之后,连工服也不穿了,换上了笔挺的中山装”而被认为已经开始腐化变质的男劳模受到不同的待遇*《三年来上海市劳动模范工作情况报告》(1953年4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1-114-3。,基层工厂对于黄宝妹则表现得相当宽容。黄宝妹的劳模身份为其形象提供了合法的外衣,这种合法的摩登在工厂中引领了一股潮流,并在上海市委的鼓励下进一步发酵。
1955年5月17日,上海团市委机关报《青年报》发表文章,号召“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称“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启新:《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青年报》1955年5月17日。。次年妇女节前后,团市委又专门讨论了妇女的服装问题,要求从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像花一般地漂亮美满的新气象”这一目的出发,改进本市妇女的服装工作*《关于改进妇女和儿童服装问题的宣传材料》(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845-5。。配合团市委的要求,上海《青年报》再次发出号召,《解放日报》也大力驳斥“好像凡是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的人,都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这一“奇怪的论调”*《勇敢地穿起来!》,《解放日报》1956年3月7日。。黄宝妹则与之积极互动,她带头穿起漂亮衣服,并呼吁“大家把所有漂亮衣服都拿出来穿”*黄宝妹:《我决心带头穿起漂亮的服装》,《新民晚报》1956年3月5日。。
不久,上海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筹备处的一个工作组携带新服装式样,亲自前往黄宝妹所在的国棉十七厂,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展览会。黄宝妹在上班以前,和其他工人一起参观了新服装。《新民晚报》的记者还特别关注到黄宝妹当天的穿着,称“她身上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短大衣,面子虽然是黑色的呢料,但灰背皮的大领子和金黄色的大纽子,恰当地改变了这一件新装的单纯的色彩”。在参观展览会之后,黄宝妹还“准备在上海做一件新式样的连衫裙”,预备带到北京等到开会时穿。*朱叶:《新服装送到了国棉十七厂》,《新民晚报》1956年3月21日。
除了“带头穿上漂亮的服装”,黄宝妹还积极利用劳模身份为女工谋福利。在市人大会上,黄宝妹等人联名要求在杨浦区新设一批大中型商店,以满足女工的消费需要。根据她的建议,1956年10月,杨浦区计划建立新的商业中心,配有出售西餐咖啡和酒菜点心的饮食商店、大型服装公司、大型理发店、洗染店、女子浴室、卷烟店、照相馆,出售脚踏车、无线电等交电商店也应有尽有*《杨浦区将建立新的商业中心》,《新民晚报》1956年10月15日。。市福利公司还根据黄宝妹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杨浦区的美兰理发店加以扩充,并从市区抽调技术较好的理发师为女工服务*方壮潮、王永年:《杨浦区一家理发店扩充 接受黄宝妹等意见》,《新民晚报》1956年12月28日。。
黄宝妹并非唯一走出国门的女劳模。在她之前,上海劳模杭佩兰就曾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归国之后也一度受到追捧。劳模个人的社会活动与基层工厂本身的利益经常背道而驰,当杭佩兰作为国家人与工厂人的两种身份产生冲突之时,她很快从形象代言人这一角色中抽身出来,在基层工厂的扶植下恢复了劳动模范的角色*《上海市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情况和今后培养劳动模范的意见》(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1-15-62。。与之相比,黄宝妹则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她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展示”的巨大效应,并以出访苏联为契机,为自己开拓新的局面*笔者在访谈过程中,曾问到为什么几次都派她出访,她说大概是因为她形象比较好。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后来国棉十七厂党委曾批评黄宝妹,称她常对别人说:“我想,到外面去的作用比在厂里挡两台车的作用大得多。”《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1956年5月,根据上海市委的意见,黄宝妹被提拔为国棉十七厂工会副主席*1956年5月,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在国棉十七厂检查工作时曾提到黄宝妹可提拔为干部。《关于劳模黄宝妹脱产担任工会副主席工作问题的报告》(1956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6-2-122-83;《关于同意上海市国棉十七厂张生娣、应五妹、黄金(宝)妹、沈金秀等同志提升的批复》(1956年5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6-1-36-69。。尽管她陷入了“不劳动”的窘境,对于这一市委提拔的劳动模范,国棉十七厂仍十分礼遇*据黄宝妹回忆,“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厂里开始下放部分干部回厂里做工。黄宝妹主动要求回到车间,但厂领导坦言,她是市委指定担任职务的,称“不敢”让她回车间。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也正是考虑到党内外的“影响”,热衷于社会活动而脱产时间较长的黄宝妹仍在1956年获得“上海市青年生产突击手”称号*《关于劳模黄宝妹脱产担任工会副主席工作问题的报告》(1956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6-2-122-83。。
如果说1956年政府对黄宝妹摩登形象的公开支持是大环境的产物。那么伴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与政治气候日趋严峻,对于女性消费的鼓励也戛然而止。上海《青年报》在一片批评声中进行了自我检讨*《关于如何掌握青年跳交谊舞问题的请示报告(草稿)》(1957年7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527-51。。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也开始纠正青年女工中存在的不良倾向,以配合日益紧张的政治运动*《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乘“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运动之风,进一步保证青年工人思想大跃进的调查材料(草稿)》(1958年9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600-7。。上海青年女工中“向往奢侈、享受的风气”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从潮流转为暗流,但仍在工厂内外涌动。据总工会的报告反映,“青年女工在生产时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平时互相讲究谁漂亮。发了工资都买新式的衣服”*《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关于新工人、青年工人会议收集的青年工人某些不良现象的材料》(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1819-154。。团市委的调查还显示,从1957年起,工厂里开始盛行金链条,有女工追求“大衣、钻戒、收音机,四季衣服毛绸丝”*《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乘“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运动之风,进一步保证青年工人思想大跃进的调查材料(草稿)》(1958年9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1-600-7。,更出现了“到处打听什么服装式样最时新,什么店理发式样最漂亮,什么服装要梳什么样的头,配什么样的裙子、袜子、皮鞋”的“时髦小姐”*《上海电表厂一位“时髦小姐”的转变》(1960年9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469-1。。至于“爱漂亮”的劳模黄宝妹,团市委干部虽也表示过担忧,但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着缄默*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与受到批评的普通女工不同,提干后的黄宝妹将更多的时间投身于社会活动,延续着摩登形象,依然保留着相当的曝光率*《各国青年六千人大联欢》,《文汇报》1957年11月6日。。
除了具有与众多劳模不同的光鲜外表,黄宝妹还有一个“摩登”的爱好——表演越剧。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曾在上海滩大放异彩。女子越剧的布景、行头非常考究*煌莺:《女子越剧红的理由》,《绍兴戏报》1941年1月13日。。女演员的服装漂亮时尚,上海女性争相模仿,老上海的照相馆还推出以越剧人物为造型的戏装照,颇受欢迎*参见罗苏文:《论近代戏曲与都市居民》,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年幼时的黄宝妹就是越剧迷,但为生活所迫,看越剧的次数屈指可数。1953年当选劳模之后,纺织工业部奖励给她一台收音机。之后,她就常在家里收听越剧节目,有时一面听,一面就拿出唱本跟着哼。只要越剧有新戏演出,她也总是抽空去看。渐渐地,她从看越剧发展为自己扮相、表演。黄宝妹的文艺爱好拉近了她与艺术界的距离,她开始成为一系列文艺作品的原型。上海市越剧团特地排了新戏《黄宝妹》,话剧《红蕊子》也是改编自黄宝妹的故事。越剧迷的她也开始在文艺舞台上初露锋芒,许多单位都邀请她前去表演,连市里召开共青团干部大会,也点名要她唱一段越剧。*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61、62页。她给领导干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逐渐为文艺界所青睐,而这种趋势在1958年到达了顶峰。
三、“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人影星
在1957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柯庆施提出了十二项奋斗目标,要求“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人民日报》1958年1月25日。。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上海发展纺织工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出现了干部下放与参加劳动生产的高潮。在此背景下,黄宝妹主动要求重回工厂,并以纺织工人的身份参与到“大跃进”运动中,她的表态得到了市委领导的肯定*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恢复了工人角色的黄宝妹积极投入生产,配合了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在关键时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为劳模的示范作用,而这一选择也依托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再次为她赢得了机遇。
1958年5月底,文化部发布《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根据“增加反映工农业跃进题材的影片”的创作要求和“新艺术片”的创作思路*《反映伟大时代 大办电影事业 文化部发出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人民日报》1958年6月3日;《上影举行创作思想跃进大会》,《大众电影》1958年第12期。,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劳模的电影,由谢晋担任导演。团市委召开座谈会,干部着重介绍了黄宝妹,称“在这次大跃进中,黄宝妹小组又创造了四小时半消灭细纱上接头白点的神话般的奇迹”,报纸上也能经常看到她的事迹*谢晋:《深刻的教育,愉快的协作——拍摄“黄宝妹”工作散记》,陈荒煤等:《论纪录性艺术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41页。。
除了黄宝妹的各项事迹,令谢晋心动的还有天马电影厂副厂长的介绍。据他说,黄宝妹“人很活跃,非常喜欢看电影,据说还会唱越剧”。谢晋很快想到,若是把黄宝妹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让她自己来演自己,对观众会更有说服力。*谢晋:《深刻的教育,愉快的协作——拍摄“黄宝妹”工作散记》,陈荒煤等:《论纪录性艺术片》,第41页。后来谢晋到黄宝妹家中和她见面聊了几次,最终决定让黄宝妹演自己*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
1958年夏,电影《黄宝妹》开拍,黄宝妹在剧中出演自己。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电影《黄宝妹》主要刻画了黄宝妹不畏困难的生产模范形象。在当时严苛的氛围下,上影四面楚歌,屡次被公开点名。尤其是在朴素而年轻漂亮的“护士小姐”和讲原则、有事业心、有人情味的“上海姑娘”均被认为是“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而遭到批判之后*受到批判的电影包括《护士日记》(江南电影制片厂,1957年)和《上海姑娘》(北京电影制片厂,1957年)等。参见陈荒煤:《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陈荒煤文集·第7卷·电影评论(上)》,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电影人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唯恐与“资产阶级”有任何瓜葛。但对于黄宝妹而言,出演电影却意义非常。在老上海的女性看来,电影明星往往代表着最摩登的女性,以至于一谈到“摩登”就会联想到明星*许美埙:《一个摩登演员》,《现代电影》1933年第5期。。尽管出演“劳模”的角色,黄宝妹却渴望得到与演员一样的“待遇”。双方在塑造形象方面还因此产生过一些分歧,如黄宝妹服装穿得稍微漂亮一点,就被电影人认为不像工人,而像机关干部或学生。在得到摄影师“拍漂亮小姐才要加砂……加了砂就不象工人了”的答复后,黄宝妹批评到:“他们对我们工人是存在不正确看法的,认为工人就是不漂亮的……今天我们拿自己的劳动来建设社会主义,过着社会主义的生活,为什么不能穿得漂亮一些呢?”*朱修勤、邢祖文:《访工人电影演员》,陈荒煤等:《论纪录性艺术片》,第72页。相较于胆怯的电影人,工人模范黄宝妹凭借自己的阶级与政治保护伞表现得更加“勇敢”。
1958年底,电影《黄宝妹》在全国放映。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联合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评选活动中,《黄宝妹》成为得票最多的一部艺术纪录片*《“党的女儿”“英雄赞”等11部得票最多》,《文汇报》1959年2月4日。。更多的积极评价则主要源于其政治正确性,有观众认为其获得的成功正是“正确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而获得的成就”*朱军:《新的时代,新的电影》,《大众电影》1958年第21期。。也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它抨击了“大跃进”中的“观潮派”*王云缦:《〈黄宝妹〉和“观潮派”》,《大众电影》1958年第21期。。而在更多人眼中,与其说电影本身受到关注,不如说“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影片中黄宝妹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就是黄宝妹本人”*石方禹:《喜逢〈黄宝妹〉》,《大众电影》1958年第19期。。当黄宝妹手拿纺纱的海报出现在各个电影院门口之时,她也成为一个美丽而醒目的标签,从而在各个领域均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另参见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98页。。“照相馆报广告照,要请黄宝妹,元旦广播节目,人民电台一定要请黄宝妹唱一段越剧”,有些单位“指明要黄宝妹,调一个也不行。电话里打交道,请不到黄宝妹电话不挂,也有干脆派人到厂里坐等,请不到黄宝妹,人就不走”,“有些报馆,只要记载黄宝妹的事迹的稿件就刊登”,还有的单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也有的地方摆宴会,送礼物,衣料,围巾,洋伞,照相机,馒头糕、土特产”*《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这一年,黄宝妹作为唯一的普通工人和邓颖超、康克清等女领导人及领导夫人一起出席了世界妇女理事会。她还登上了妇联主办的外文杂志的封面,杂志专门讲述了她带领小组迎接劳动竞赛和挑战、解决纺织难题的片段。*Yang Po, A Knotty Problem Solved, Women of China, No.4, 1959, pp.20-24.
出演电影《黄宝妹》之后,黄宝妹在劳动模范之外又有了“工人影星”的头衔。1959年11月2日,黄宝妹出席由文化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举行的宴会,共同庆贺1959年国产新片展览月的成功*《周总理出席招待会祝贺新片展览月的成功 文化部负责人谈大跃进以来电影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1月3日。。此后,黄宝妹虽没能转型成为专业演员,但“电影明星”所蕴含的“派头”和光鲜外表,还是将她推上了风口浪尖,附加于她身上的诸多角色也开始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黄宝妹“成名”后,社会各界对黄宝妹发出的热情邀请纷至沓来。国棉十七厂出于培养劳动模范、希望其发挥生产带头作用的考虑,多次出面拒绝。但市委层面的施压与黄宝妹个人的积极互动常冲破基层工厂设置的屏障,双方摩擦不断。*1956年,毛泽东视察上海,并在中苏友好大厦进行座谈,上海市委曾指定黄宝妹参加。但国棉十七厂一直未通知她,会议开始后才急匆匆通知黄宝妹前往。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国棉十七厂党委在另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厂里曾出于真心爱护与支持她的态度出发,主动为她挡掉一些不必要的活动”,“但黄宝妹同志却常常因此而不高兴”。《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棉十七厂还是展示出保护劳模的姿态,对于黄宝妹的一些负面信息也尽可能加以掩盖*《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这或许是因为事故频发的国棉十七厂急需正面典型所带来的“红利”加以挽救*1955年11月,国棉十七厂发生了黄白布的严重事故,上海市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点名批评了厂长。此事本应进行通报批评,并转发给各厂党委,但最终仅作为材料上报国营工业部与市检查委员会。《关于十七棉几件生产情况的检查报告》(1955年12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2-661-10;《通知》(1956年2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47-2-661-32。。不过,伴随着黄宝妹的“问题”增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诉使工厂招架不住,厂党委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在1959年9月给市委工业部的报告中,厂党委严肃指出黄宝妹“自满骄傲”“脱离群众和生产”等问题,并将矛头指向不客观的报纸宣传,特别批评了电影《黄宝妹》,认为影片“把黄宝妹讲得太好,把别人讲得太差”,甚至个别镜头“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从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群众指指点点”*《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引号中的文字在草稿中均被删去。。
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厂党委几易其稿、反复斟酌,部分相对直白的表述均在后面的陈述中进行了删改,表现了他们的犹豫与担忧。在是否继续扶植黄宝妹的问题上,他们权衡利弊,最终作出了“今后只要继续加强对她的教育,仍然可以发挥先进旗帜作用”的结论*《关于黄宝妹同志几个问题的报告(草稿)》(1959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6-2-237-88。。
尽管对于黄宝妹颇有微词,也一改主动保护与积极宣传的姿态,但这种来自基层工厂的微弱声音成为黄宝妹风光背后的一点小插曲,黄宝妹继续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工人的典范受到各级党媒的青睐。1959年,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再次授予黄宝妹“上海市红旗青年突击手”称号。在其先进事迹材料中,组织部还特别提到:“近年来,黄宝妹的社会活动特别多……但是她在生产上并没有掉队,永远保持先进。”*《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黄宝妹同志先进事迹的材料》(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373-143。同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读物,配合了市委对黄宝妹的宣传*唐克新著,朱然绘图:《永远向前的黄宝妹》,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李白英改编,胡祖清图:《黄宝妹夜战白点》,上海美术出版社,1959年。。凭借在全国范围内的辐射作用,黄宝妹成为上海工人先进性的代言人,对于其形象的建构仍在继续进行中。
四、被观看的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中国
1958年,苏联白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展出了著名艺术家谢里汉诺夫的一套新作品,即他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创作的人物雕塑,“劳动模范黄宝妹”位列其中*《苏联著名雕塑艺术家谢里汉诺夫的杰作》,《新民晚报》1958年3月4日。。黄宝妹进入苏联艺术家的视野并不意外。据称,苏联领导人来华访问时,就曾对中国女性过于朴素的穿着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形象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面貌*许星:《论20世纪五十年代苏式服装在中国的兴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黄宝妹自1954年出访苏联以来逐渐形成的美丽时髦形象,构成了其作为被解放的妇女、领导阶级的工人以及社会主义的中国等代言人的资本。经过包装后的黄宝妹及其住所几乎成为苏联代表团参观上海的“景点”之一。*据黄宝妹回忆,在1956年前后,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陪同一个苏联代表到黄宝妹家里参观。苏联代表见到她三代人同住在一间老房子中,激动地说:“黄宝妹是劳动模范,又是人民代表,怎么住在这么差的地方?”后来为了外事活动需要,在市领导的要求下,厂里将两间宿舍分配给黄宝妹。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51页。1959年6月,市纺织工会设宴招待苏联纺织轻工业工会,劳动模范黄宝妹也是座上宾客。《苏轻纺工业工会代表在上海进行参观访问》,《文汇报》1959年6月10日。
1959年7月26日至8月4日,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维也纳举行,由上海团市委上报,经团中央组织部批准同意,黄宝妹作为工人代表列席代表团*《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1959年出席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海代表的名单》(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2866-6。。世青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国际集会,对于在外交上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而言,也是为数不多的与西方接触的途径之一,成为难得的展示社会主义中国风采的舞台。团中央以“宣传我国各方面的成就,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为目的,要求各行业代表充分准备材料,以反映“工农业生产,交通水利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人们愉快美好的生活以及新的社会风尚”这一主题*《团中央、共青团上海市委有关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通知、往来文书》(1959年5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21-2-1264。。
到达维也纳后,黄宝妹和其他女团员身着统一的白底花旗袍,她们的亮相使新中国“名声大震”*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代表团中的黄宝妹格外引人注目,邀请跳舞之人络绎不绝*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59页。。她还回忆,参加世青节的外国人对于“上海”印象深刻,得知她是上海来的代表都翘起大拇指,这令她感到非常骄傲*黄宝妹访谈(1),2015年5月8日。。也正是在维也纳,黄宝妹拍摄了她认为一生中最美丽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宝妹烫着卷发,一缕碎发梢置于额头前。她身穿花旗袍,手上戴着一块手表,低头摆弄手中的照相机,露出甜美笑容。据她回忆,这张照片实际上是一种被观看下的摆拍。一个外国记者将照相机借给她,让她摆出这个动作后完成了拍摄。她的形象似乎与旧上海的摩登女郎存在相似之处。这样一个光鲜美丽且被物质文明裹挟的工人形象,代表了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工人阶级的理想设计,黄宝妹很好地完成了被观看的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的任务。这张照片后来未在国内刊登,而是刊登在捷克的主要报纸《青年阵线》上。黄宝妹的影像也受到多家外国媒体的青睐,苏联记者拍摄黄宝妹身穿格子衬衫手拿鲜花的照片并予以刊登,黄宝妹与朝鲜等国妇女的合影还被刊登在奥地利的报纸上。*黄宝妹访谈(2),2015年7月20日。照片与相关外文报纸均从黄宝妹家中获得,2015年10月24日。颇值得玩味的是,黄宝妹参加世青节的新闻虽受到了国内一些新闻媒体的关注,但相关报道聚焦于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青年联欢的主题之上。《新民晚报》选择了古巴代表团萨卢多团长与黄宝妹的合影*《听卡斯特罗的战友 讲古巴革命的故事》,《新民晚报》1959年7月31日。。《解放日报》则刊登了黄宝妹和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亲切交谈的照片*《本市纺织女工黄宝妹在维也纳联欢节上和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亲切交谈》,《解放日报》1959年7月31日。。对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国内读者而言,黄宝妹个人的美丽形象与大幅照片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却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经过报道之后的“黄宝妹”在国内外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而她个人也在此次世青节的舞台上遭遇了内冷外热的尴尬境遇。
联欢节结束后,黄宝妹又受邀前往捷克参加世界青联第五届全体代表大会*此次全体代表大会主要商讨有关世界青年团结、和平,以及世青会的发展问题。Miroslav Vecker, Prague Greets World Youth, World Youth, published by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 1959.8, pp.1-2.。回国后的黄宝妹继续履行她作为上海乃至中国形象代表的义务。1959年12月,黄宝妹当选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次年2月又当选上海市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参选“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先进事迹中,黄宝妹的生产成绩仍然作为当选的必要条件被复制,尽管她已经与“劳动模范”渐行渐远。*《全国三八红旗手预选人》(1960年12月30日),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藏,档案号43-2-78。
1960年,上海市委研究决定让黄宝妹脱产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9月20日,黄宝妹正式成为纺织工学院纺织工程专业干部班的学生。在读书的日子里,黄宝妹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她常在宿舍里教同学唱越剧,应邀在“大学生之家”和文化宫里表演越剧,同时继续以工人大学生的身份参与留学生交流等外事工作。*张自强:《七百五十多个中的几个》,《文汇报》1961年10月7日;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123页;《上海归侨学生举行暑期联欢会》,《文汇报》1962年8月26日。
然而,就在黄宝妹逐渐适应了新角色的同时,基层工厂与上海市委层面在对其继续扶植还是弃之不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再现。在连续八年获得各级劳动模范的称号之后,黄宝妹没能通过国棉十七厂的推荐,在1960—1961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生产者”评选中落选了。在随后进行的四次复评中,国棉十七厂抵制了来自区委、市委、总工会等单位的压力,厂领导在复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群众的意见表明,基层工厂对于这一无法在厂里发挥先进带头作用的劳模决定搁置不用。*黄宝妹落选之初,区委就督促厂工会进行复查。此后,市评选办公室又收集了厂工会、生产小组、普通群众座谈等各方面的意见。1962年初,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前往市评选办公室了解有关情况,并撰写说明刊登于党刊。10月,市总工会再次进行复查,特别针对厂领导在评模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调查。《“黄宝妹落选原因复查”的复查》(1963年3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3979-17;《关于评选黄宝妹同志先进生产者情况的复查报告》(1962年10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3979-29。自此,一个失去了“先进生产者”称号的黄宝妹正式告别了“劳模”的光环,但她仍以全新的身份继续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上海市委与各级机关虽在“挽救”劳模黄宝妹的过程中失败,却仍未放弃这一“著名的先进生产者”和“纺织工人当中较为突出的标兵”,而是转而从其他角色入手继续对黄宝妹加以培养与扶植*《“黄宝妹落选原因复查”的复查》(1963年3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1-2-3979-17。
黄宝妹曾因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而当选全国劳模,进校后的她与郝建秀成为同学。在《文汇报》的要求下,黄宝妹开始与郝建秀通信,并以姐妹信件的方式刊登在报头。党报不失时机地捕捉两人的信息,有意构建了一系列劳模姐妹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形象。*黄宝妹、郝建秀:《姐妹书简》,《文汇报》1962年10月21日。照片中的郝建秀两条大辫子的朴素形象与黄宝妹身穿布拉吉、头烫卷发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在毛泽东时代被国家赋予了相似政治身份的女劳模也无意中展示了其迥然不同的地方性。
1963年8月,黄宝妹大学毕业回到国棉十七厂担任技术员,同时担任该厂的形象代言人,每年纺织系统沪东块对口检查互助组均由她引领*朱金大、韩兆云主编:《踏遍青山人未老——劳动模范黄宝妹》,第124页。。同以前一样,党报在捕捉其美丽形象的同时仍竭力维护黄宝妹作为“工人”的身份与气质。有关报道称:“每次下车间,工人们看到黄宝妹的行为和穿戴同没有上大学时一个样子,都亲切地说:‘黄宝妹还是我们的黄宝妹’。”*张煦棠:《社会主义的新型劳动者》,《文汇报》1964年10月5日。1964年7月,34岁的黄宝妹再次回忆起童年时的贫苦生活,感慨“如今,苦难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黄宝妹:《听蝉歌 忆童年》,《新民晚报》1964年7月19日。。对自己的现状,她无疑感到非常满意。作为原本生活在上海却被定义为乡下人的产业工人,黄宝妹在1949年后才正式开启了成为“城市人”的过程,新政权不仅赋予了她作为工人的尊严,还给予了她曾经遥不可及的“摩登”。
五、余 论
黄宝妹最初以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与其他穿着朴素、老实憨厚的典型劳模相比,黄宝妹无疑是个另类。然而,来自党和政府的认可与扶植、党媒的持续跟踪报道、中外艺术家的青睐以及民间的效仿追随,都证实了这一形象适应了当时中共宣传与基层社会实践的需要,黄宝妹因此成为既代表新中国又代表老上海的“双面人”。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宝妹的某些行为无疑也受到了相当的责备,但这些可疑的举止又为她赢得了一种被观看的资本。从摩登劳模这一复杂且不乏冲突的形象之生产与传播着手,本文尝试在下述问题的讨论上有所推进。
第一,在以往关于女劳工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习惯将阶级意识形态与性别意识形态对立,因而有意识地构建出一系列“去性别化”的劳模形象,但既有结论无法解释黄宝妹形象的生成。一方面,黄宝妹出身工人,后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此后无论角色如何嬗变,工人模范的身份始终是其形象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摩登劳模又脱胎于老上海“摩登女郎”“洋”的灰色文化与新中国红色文化的夹缝中,呈现出一种上海基层社会的连续性及其对新国家的适应性。在此个案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性别特征构成了摩登劳模产生的关键因素,缺一不可。
第二,执政党在塑造工人阶级作为城市领导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克服多重屏障。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载体,工人物质生活与外在形象的丰裕对内对外均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然而,新中国在发展生产与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劳动光荣”经常压倒“消费合理”,一种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由此生成。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快速铺展、收缩与前后替代,“合法”与“非法”往往失去了清晰的界限。正是在上述模糊的空间中,摩登劳模的形象才能生存并流行。
第三,既有关于毛泽东时代城市史的研究多以“接管”与“改造”为主题,或讳言“都市”,或不自觉地隐藏着一种“去都市化”的悲观情绪。近年来部分学者证实了50年代的上海在文化消费上呈现出“摩登犹在”的姿态*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有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年第3期;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等等。。在此基础上,本个案引入“都市人”这一维度,以揭示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上海作为曾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城市之一,在1949年之后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代言人被观看。上海在全国政治棋盘上始终模糊,既是批判的对象,又是生产力的依靠;既代表着改造不尽的资本主义残余,也展示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改造资本主义老上海的同时,新国家也在与之开展着合作。正是在现实主义的考虑下,黄宝妹这一另类的劳模形象才具有了持续流行的土壤。这种个人、地方、国家有意识地结盟并彼此推动的事实,提示我们必须以另一种思路重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研究。
1963年,“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的故事在上海广泛传播。军区组织观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有指战员听说要讲“一分钱,穿草鞋”,表态“不看!”然而,很快就有看过的人前来透露,这部讲述上海解放之初的影片“里面什么都有啊!”*崔永元制作:纪录片《电影传奇》之《霓虹灯下的哨兵——考验》,北京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6年。于是,借助“好八连”的故事,以接受共产主义洗礼为名目,他们重新回顾了刚刚解放而“什么都有”的上海。那一天,上海人仿佛重回到充满了危险与诱惑的“东方巴黎”。中共建政后,时尚的电影明星逐渐演变为人民演员,所谓“资产阶级”学习着如何低调求生,而黄宝妹的大幅照片与美丽图像就如“什么都有”的电影。透过这个还算时髦的上海劳模,老上海人追忆着曾经的摩登女郎,新中国的产业工人们也做起了“上海梦”。而当黄宝妹代表中国走出国门接受赞誉之时,“上海”曾经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优越感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产生了新的走向。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吴志军)
Amid the State and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s of Shanghai Model Labors’ Images (1949—1963)
Liu Yajuan
Huang Baomei was known as the national model labor initially, but she was active and fashionable,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mages of textile female labors. Altho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ce rectified the tendency of “consumerism and life style of capitalism” among the female workers, Huang enjoyed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class superiority. On the one hand, she legally reflected the unclear and illegal taste, recalling the memory of “modern lady” and “western style” inside the urban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she was the symbol of Shanghai, the model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celebrity to show the advantage of communist China. In this case, the class backgrou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gender features main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er imag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arrative and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al images of the working class provided the space of its existence, and it was the conspirac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Shanghai locality that made it popular through the 1950s to 1960s.
K271
A
1003-3815(2016)-05-00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