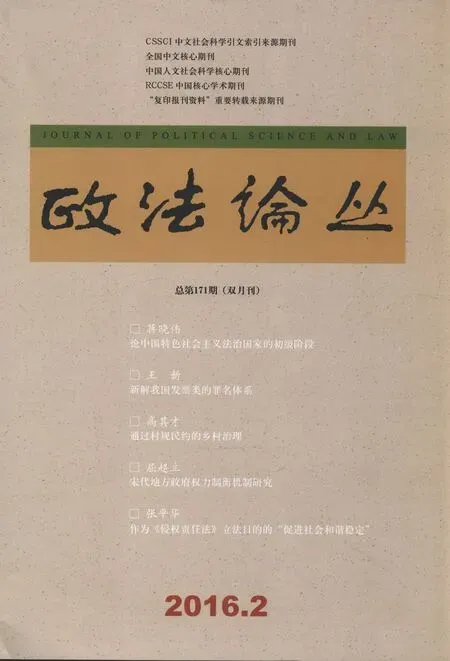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2016-02-12吕建武
李 丽 吕建武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李丽吕建武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摘要】逻辑虽然不能提供给法律人完美的规则体系,但却是实现法律人理性判断的技术性保障。肯定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逻辑作用的无限夸大,更多的只是强调逻辑对法律思维的指导与规范。法律思维活动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现逻辑的规范,通过规则的约束实现思维领域中的合理推理与论证。逻辑一旦内化为法律适用中的技术性规范,则始终会影响着法律思维模式的构建,进而保障法律思维合法性的理性实现。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应当是简单的并具有可接受性的。
【关 键 词】法律适用逻辑规范形式分析理性判断
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与人们正确的思维表达尤其是推理论证的正确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逻辑是实现法律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和推理有效的工具,同时也是实现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与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但是,自从霍姆斯提出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观点之后,逻辑便成为了法学研究批判的靶子。虽然法律适用依然离不开逻辑的规范,但逻辑已难以再获得法律人的重视。法律思维实践中,高举“逻辑万能论”的旗子固然不可取,但因正视了逻辑的不足便全盘否定了它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则是走入了另一极端。逻辑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法律适用中没有逻辑是断然不能的。
一、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及其争论
(一)关于法律与逻辑
在人类逻辑思想形成的初期,法律便与逻辑结下了不解之缘。被尊称为“逻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1]P169。法律是理性的产物,而逻辑则是理性的基础。实现法律的理性,离不开逻辑的指导和规范。人们发现,无论是法庭的辩论,还是司法文书的制作,都可以借助于逻辑不同程度地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西方逻辑学家黑尔蒙说过,“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美亚的判决书中早已使用了三段论推理形式。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也使用了逻辑命题形式和推理形式进行了法律的制定和宣示”[2]P3。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了“法治优于人治”的理论时,也进一步确立了逻辑在法治化实现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依赖于人们正确的思维活动,而要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则离不开逻辑的指导与规范。逻辑与法律的天然联系,促使了逻辑研究在法学领域的蓬勃兴起,并使得其研究成果与法治秩序之建构紧密结合。人们普遍认识到逻辑在法律思维实践中的应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研究法律与逻辑相结合的新的学科领域。以德国克鲁格、波兰齐姆宾斯基、奥地利塔曼鲁和魏因伯格、美国图尔敏、德国阿列克西、英国麦考密克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了法律思维领域中的思维规律的总结与探索,先后建立了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等传统逻辑内容为基础的法律逻辑体系,以及以一阶逻辑等现代逻辑内容为基础的法律逻辑体系”[3]。
我国关于法律与逻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吴家麟、雍琦、王洪、梁庆寅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始了法律逻辑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及其内容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对于法律逻辑的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推动学科前进方面功不可没。学者们认识到,要正确地阐述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适用,必须解决法律思维的三个关键领域,即法学家布赫瓦尔德所指出的“法律概念和体系的建构、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3]。法律思维实践中,需要通过对思维本身规律的总结,概括出法律思维表达应遵守的逻辑规律和规则,当然也包括正确思维表达应掌握的逻辑方法和技巧。在质疑和反思中,我国法律逻辑学的研究从“法律+逻辑”的简单原理加案例式的传统逻辑方法研究阶段,转向了法理视角中的逻辑规律规则及其方法的研究,继而又转向了与论证、批判等日常思维密切相关的非形式法律逻辑的研究……。法律逻辑问题受到了逻辑学家与法学家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于法律逻辑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为法律逻辑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开启了法学与逻辑学在应用领域中的广泛交流。作为一个新开辟的学科领域,法律逻辑问题尚存在若干的争论与困惑。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不过,如何最大化地发挥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应是每个研究阶段都需考虑的问题。正确地认识与实现逻辑在法律思维实践中的作用,有助于法律逻辑相关争议问题的合理解释和解决,有助于法律逻辑学科体系与学科内容的科学构建。
(二)法治实现中对逻辑作用的质疑与评价
法治的实现依赖三个法律台柱,即“一个自治的法律制度、普遍的规则和适用法律的推理过程”[4]P162。逻辑一度被认为是法治实现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性手段。无论是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还是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朗·富勒,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都一致认可了法治实现所需要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为了实现这种稳定性与确定性,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法律概念、法律判断与法律推理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逻辑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法律适用中的公平与正义。德国学者伯恩·魏德士认为形式逻辑对于法学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法律思维实践中首先应当遵守逻辑思维法则,否则便会导致思维表达的混乱或者错误。[5]P309
法律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在复杂的思维过程中实现逻辑的规范,很难通过简单的套用即能完成。大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指出:“在司法过程中,不但要发现法律而且要创造法律——澄清法律的疑义、平衡法律的冲突、填补法律的漏洞。”[6]P105法律现象是千变万化的,谁也无法如“自动售货机”式地机械地断案。当分析法学家们高举逻辑的大旗,倡导通过严密的逻辑去理解与分析法律概念与法律命题时,社会法学家们则对逻辑的应用提出了质疑与批判。社会法学派中的法律现实主义更是走向了极端。从霍姆斯开始,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者就开始反对过度地强调逻辑的作用,他们更倾向于把法律的规范性降到最低,认为法院的判决也是极为不确定和无法预见的,而且认为这应当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人们不应加以外在的力量对此进行扼杀。“法治只有凭靠各不相同且相互冲突的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协调共存,才能更好地维持下去”[7]P169。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法律适用中“直觉也优先于逻辑”。在他们眼中,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人为地设置一个“逻辑天堂”,并无助于法治的实现。霍姆斯的一句“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更是彻底动摇了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如何应对这种危机,学术界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从逻辑学科入手,试图通过对逻辑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避免法律适用中“逻辑无用论”的尴尬;另一种则是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法律因素的充分考量,实现法律思维的逻辑理性。
形式化的逻辑公理系统,的确显现出准确、严密和系统性的特性,借助它,人们可以对诸多法律问题进行理性剖析,通过技术性的手段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公正。然而,过度地追求形式理论的完整与严密,有时未必会达到预期效果。逻辑理论本就抽象枯燥,再加上繁琐复杂的公式符号,其结果往往让人望而却步而不愿接受。逻辑是西方科学发展的源泉,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体的,而我国则恰好相反。由于自古缺乏对思维科学的系统研究,也自然缺乏对思维科学的重视与实践。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人分析问题时,往往更习惯于“不追求对感性材料的深层思考和对事物的精确分析,仅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及对事物粗浅和笼统的描述”[8]P29。法律思维实践中的逻辑研究若把形式分析过于专业化、复杂化,逻辑法则便会如枷锁一般束缚法律人的思维,其结果自然会使得法律人极力排斥逻辑法则的重压与束缚。形式化的思维训练固然可以达到规范思维的目的,但若逻辑强大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抽象、复杂的逻辑理论知识的掌握,其功能的实现自然会大打折扣。
同样,站在法理的角度研究特定思维领域中的逻辑应用,同样受到了阻力。逻辑关注的主要是思维的形式问题,它只能确保判断结论实现形式上的正确性,但却无法保证判断结果与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的契合。美国学者莫里斯·R·科恩说过,试图把法律变成一个“完全地演绎制度”[7]P478,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当面对个案的复杂多变、法律的模糊不清等不确定因素时,要达致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必须综合考量所有的不确定因素,正确地处理法律规范之外的价值判断、道德因素与法律漏洞等因素的干扰。虽说法律与逻辑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此时逻辑的作用似乎不再凸显,判断的得出更多依赖的是法律允许下的各种利益因素的考量。逻辑解释的更多的是形式的有效性,它无法解释法律思维实践中的所有问题,更无法实现法律人一直追求的实质正义。逻辑左右不了法律人的“先入之见”,解释不了审判者的自由裁量,更探及不到法律原则与精神。人们开始质疑乃至批判逻辑的应用。霍姆斯的一句“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影响并误导着几代律师、法官及其法学家们,也彻底摧毁了人们曾经对逻辑的依赖。
对法律适用中的逻辑的理解和认识实则存在着若干的误解与偏见。首先,霍姆斯对逻辑的批判之语不能简单地演绎为对逻辑的全盘否定。因为,霍姆斯不但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他还说过“法律人的训练,就是逻辑的训练”[9]P465。霍姆斯并不是不重视逻辑,而是反对人们把逻辑的作用绝对化。法律问题的解释不能仅仅依靠逻辑是不争的事实,强调逻辑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无限夸大逻辑的作用。其次,历史上对逻辑的质疑和批判,更多的是把“逻辑”等同于“三段论逻辑”,或者是“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形式化”。三段论理论是应用非常广泛的逻辑理论,这也使得在法律适用和研究中三段论成了逻辑的代名词。“逻辑形式多样并非仅一种三段论”[10]。从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到后来法学界掀起的反逻辑思潮,实则是建立在对逻辑这个概念的误解基础之上的。逻辑作为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学科,无论是采用自然语言表述的传统形式逻辑,还是以人工语言为标志的现代形式逻辑,都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概括正确思维表达应当遵循的规律规则。逻辑不仅仅以三段论的形式适用于法律思维实践中,法律思维实践中的概念明确、判断分析、推理论证等都需要逻辑的分析。对于逻辑在法律思维领域中的作用应当客观评价,它虽然无法解释法律思维实践中的所有问题,但它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逻辑是正确思维表达的工具。无论是逻辑规律规则的遵守,还是逻辑形式的刻画,都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法律人的思维,进而使之达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的目的。作为指导思维实践的工具性学科,逻辑不但可以约束法律思维主体的任性与肆意,而且还能促使法律思维活动忠于法律、服从法律目标的最终实现。逻辑是一种理性,更是人们正确思维的法则。
二、法律思维实践中逻辑的功用及其表现
法律思维是指按照法律的逻辑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思维实践活动中的特殊领域,法律思维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规律和规则。根据法律进行思维是法律思维的首要特征。法律思维实践中,对于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应当“与法律文字和精神保持一致,应经由实在法建构和推导而来,要为实在法所支持和证成”[11]。根据法律做出判断时,可以无视法律之外的因素,即便受到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也必然建立在法律授予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应“尽力从法律上回答所有的法律问题,尽可能通过法律思想去填堵实证法中的种种漏洞”[11]。法律思维的法律性的实现需要正确地理解和分析法律的适用,也需要理性地反省与论证法律的适用。逻辑是实现正确的法律思维和理性反省的法律思维的技术性保障。
(一)实现法律思维正确性的技术性保障
法律思维合法性的实现首先需要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法律本身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与适用需要严格地遵循正确思维的规律规则。无论是立法中法律规范的制定与解释,还是司法实践中法律规范的寻找与确定等,都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准确运用,都要受到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规则的约束。法律思维主体要将繁杂的社会现象纳入法律的框架下做出评判,首先需要遵循正确思维表达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进而实现正确地理解法律概念,恰当地做出法律判断与合乎逻辑地进行推导的目的。
逻辑学作为一门研究思维规律规则的学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现已发展成一门有若干分支的庞大的基础学科。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最早创建而经后人不断发展完善的传统形式逻辑,还是莱布尼茨开启的现代形式逻辑,都从不同的视角对正确思维的规律规则做了系统而又严密的阐述。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形式逻辑的创始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人类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等一系列问题。由“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和“辨谬篇”组成的《工具论》,从人类最小的思维细胞概念开始,系统地介绍了人类正确判断、推理与论辩应当遵守的规律规则。另外,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与充足理由律等逻辑基本规律在法律思维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从不同侧面保证着思维的确定性。同一律从正面表述思想的自身同一;矛盾律断定了两个相互否定的思想不能同时肯定,避免思想表达的前后矛盾;排中律则要求相互否定的思想不能同时否定,拒绝判断的模棱两可;充足理由律则指出法律判断的得出必须有真实而充分的理由。逻辑基本规律对人类思维活动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法律思维实践中,只有自觉遵循逻辑基本规律,才能避免法律概念的歧义和含混,避免法律判断的模棱两可和冲突矛盾。虽然人类思维形式规律无法被一门学科所涵盖和解释,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传统逻辑的理论本身却也是科学严谨的,“在这个系统中,任何的定义、规则、公式等内容,都有自己严格的界说,无不体现着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严谨与科学”[12]。严谨而科学的逻辑学理论在具体思维实践中发挥着指导与规范的作用。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理论,尤其是三段论部分,在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维表达方面至今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逻辑规律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对思维活动规律的总结,也是人们正确思维首先应当遵守的规律规则。要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必须自觉地遵守正确思维的规律规则。因为,如果没有了这种客观的、理性的规则约束,当面对着个人嗜好、利益诱惑、直觉、习性等因素的干扰时,主观性、非理性的因素便成为理性判断的障碍,思维活动则由此缺乏了理性对待法律问题的自觉性。“大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会像在法的领域那样,由于违背逻辑规律、造成不正确的推理,导致虚假的结论而引起如此重大的危害”[13]P58。法律人的思维表达是否准确严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正义的实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这是霍姆斯在过度地夸大逻辑作用的背景下所做的言论。法律适用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逻辑。因为如布鲁尔所言,经验最终也离不开逻辑的检验与约束。逻辑是明确法律概念、合理做出法律判断不可或缺的技术性保障。
(二)实现法律思维理性反省的技术性保障
法律思维合法性的实现也面临着若干障碍。因为法律规范并不是都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理解和解释的,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解释性含义或者规范适用中的冲突等规则适用的困惑。就学科自身的特点而言,逻辑更多的是实现形式上的正确性,但并不能确保推理结论是否符合法律的原则与精神。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逻辑功用的质疑。库的里亚夫采夫在《定罪通论》中指出:“如果不顾法律的目的,过分追求法律之逻辑一贯性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司法裁判就会重蹈概念法学的覆辙。”[14]P37
逻辑究竟是不是仅在法律规定明确、事实清楚的时候才发挥作用,而在法律规范不明确、事实模糊的情形下不发挥作用呢?其实,在法律规范明确、事实清楚的法律适用中逻辑的作用不容置疑,在法律规范不明确、事实模糊的情形下,法律判断的得出同样离不开逻辑的规范。只是,人们更习惯在确定的框架下适用逻辑,而“没有认识到法律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也应当而且能够从逻辑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3]。面对着法律规范的明确、事实的确定或者价值伦理的选择时,固然无法简单地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对号入座,然而,在左右为难之际,又何尝不是对另一概念的明确与判断得出的论证,只是考虑的因素多了,衡量的关系复杂了而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对思维规律的探索过程是长期的、没有终点的。作为总结人类思维规律的学科,逻辑学虽然已建立了体系庞大的学科体系,积累了若干规范人类正确思维表达的理论,但是,逻辑学并未穷尽所有的思维领域的规律。法律思维领域中尚存在若干问题需要人们进一步地探讨与提炼。
一般的法律思维活动需要逻辑的指导和规范,复杂的法律思维活动同样离不开逻辑的指导和规范。逻辑作为正确思维表达的工具,在复杂的思维活动中仍然发挥着指导和规范的作用。此时,逻辑的最终目的是借助规则的运用,最大地实现多种因素干扰下判断的可预测性与稳定性,最终实现判断结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法律思维领域中,当“作出主张的同时提出应当承认的要求。假如这个主张受到了怀疑,那它就必须要进行证立”[15]P106。人们需要从逻辑上寻求准确刻画法律推理及其法律论证的结构与模式。演绎逻辑系统可以更好地阐释法治实现的形式正义,也可以有效地约束司法权力的滥用。三段论演绎模式或者蕴涵模式的建立,成就了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形式理性”。法律思维过程因具备严密的逻辑系统性成就了理性的法律判断,因为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演绎系统,才能排除干扰,进而得出令人信服的法律判断。
法律思维实践中,法律的确定性可以通过逻辑实现,法律的不确定性同样离不开逻辑的指导与规范。简单案件中的判断经常会基于法律感而较容易地得出,而复杂案件中的判断则需要通过逻辑的推导演绎判断结论的必然得出。法律感或许的确存在于法律思维主体的判断之中,法律判断的得出凭借法律感即可获得,根本无需经过繁琐的推导演绎。然而,当法律思维主体需要论证这种由法律感获得的判断时,他也必须借助逻辑的工具进行审慎的思考,并且刻画出判断得出的具体过程。无论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最佳法律规范的寻求,法律理解和适用的复杂性导致了法律判断形成的复杂性。在法律判断的形成过程中,必须通过不同判断间的比较和权衡,实现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批判、反省与论证。也就是说,复杂案件中的判断更需要逻辑的检验与论证。由于法律规范的寻找、法律事实的确定中存在若干不稳定的干扰因素,因而,法律规范的解读及其法律判断的推导路径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式进行呈现的。
逻辑在法律思维实践中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规则的约束实现思维领域中的合理推理与论证,进而从技术上保障法律思维合法性原则的理性实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离不开逻辑的指导与规范。对于法律思维实践中逻辑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传统逻辑的角度,还是从经典逻辑及其扩充为框架的其他逻辑理论的角度,都应当致力于对法律规范、案件事实等问题的逻辑分析,“以逻辑力量为依托来实现对案件事实的理性认知”[16]P240。法律思维活动可以通过逻辑工具的运用,实现根据法律思考所必需的思维理性。法律与事实彰显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确导致了逻辑适用的复杂与困惑,当面对着若干的不确定性因素时,法律思维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拿起逻辑的武器排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实现法律判断的理性认知。法律思维活动应当被置于理性的范围之内,遵守逻辑规则是思维理性实现的根本保障。
三、逻辑规范的实现与逻辑适用的司法化面向
(一)逻辑规范的实现
思维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法律思维主体受到自身思维活动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影响,在期待做出合乎法律规范的判断时经常会事与愿违。为了克服这种主观性和随意性,法律思维活动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现逻辑的规范,从而使法律判断的形成排除思维主体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干扰。法律适用中的逻辑规范首先强调的是运用逻辑的意识与自觉性。“剖析任何一种思维模式会发现,模式内存在着一种抑制或限定性机制”[17]P139-140。对于法律思维主体而言,逻辑的适用一旦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条件反射,则会在思维实践中影响着思维主体的认识活动和心理活动。法律思维实践中自觉地适用逻辑,不但影响着法律思维主体的合法判断的形成,而且还能够通过可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实现法律的权威。实践中,所有的规范都集中在对思维活动的限定上,这种限定实质上是对思维主体主观性、随意性倾向的约束。思维活动中各种干扰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冲突,营造出一个纷繁复杂的局面。设立一个分析、解决问题的规范限定,使得法律思维活动中所有的判断都始终落在合法性之上,会使原本复杂的局面变得更科学有序。
当然,思维主体逻辑思维能力的具备对法律适用中逻辑规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思维主体只有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素养,法律思维实践中逻辑规范的效果才更明显。受过全面系统的逻辑思维训练或者长期从事逻辑研究的人,在逻辑规范的实现方面往往会更得心应手。法律思维主体的逻辑思维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不断训练和积累的结果。通过系统地逻辑理论学习和思维训练,可以帮助法律人正确地论证与表达思想,科学理性地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融传授知识、培育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18]钱伟长教授曾经说过:“不是学好一门课就能像这门课所教的那样工作就是了。因为这门课的知识隔几年或几十年就可能没用。如果我们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学生通过这门课所学到的逻辑思维能力永远有用。”[19]P189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应是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
逻辑学是从思维的形式结构方面研究人类思维的规律规则的,逻辑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而只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和规则。学科的特点使得逻辑学的理论知识抽象又枯燥,许多人由此认为逻辑离人们实际思维太远,并提出了“逻辑无用论”的错误主张。“对逻辑理论学习重视不够,缺乏对逻辑形式的准确把握,因而在对实际思维进行逻辑分析时缺乏深度,方法也显得落后,直接影响了逻辑应用的水平”[20]P195。逻辑知识的欠缺是法律思维实践中逻辑适用的障碍之一。毕竟,无论理论的应用,还是能力的获取,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作为前提的。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理论的应用及其能力的提高都会成为妄言。培养法律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首先要重视法律人逻辑理论的学习与逻辑思维训练的合理设计。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涉法性抽象思维,本身具备着抽象性的特点,法律思维主体应当熟练掌握正确思维表达的逻辑理论知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逻辑理论素养,从而获得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理性方法和手段。“学习逻辑确实能使我们熟悉正确推理必须符合哪些规则,并提醒我们推理过程中可能遭遇那些常见的谬误和陷阱”[21]P5。当然,法律思维主体对于逻辑知识的掌握不必拘泥于内容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不必过于强调逻辑规则的推导、形式演算,更不需纠结于深奥难懂、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内容上。逻辑学只有实现由“纸上的逻辑”转变为“行动中的逻辑”,才能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法律人的逻辑理论学习和思维训练,应当在研究法律思维的逻辑规律与规则的基础上,侧重于引导人们自觉运用逻辑工具分析法律适用中的问题,培养和提高人们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如何合理设计与组织逻辑思维训练,提高人们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实现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逻辑思维训练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思维训练能否顺利实施,案例的选取与应用至关重要。思维训练案例如果选取的不合适,那么,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无法达到预期的训练效果。只有来源于法律实践,具有真实性的教学案例,才能更具有说服力,才能从根本上转变“逻辑无用论”的错误认识,充分调动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陈旧老套、耳熟能详的故事笑话,虽说能够活跃气氛,但是,因为远离了思维实践而不具有分析价值。其次,应当精心地设计训练问题,合理地使用思维训练案例。如果仅仅为了纯粹地理论学习而特意设计训练题目,采用简单的套用方式分析案例,则会陷入备受批评的“逻辑原理+法学案例”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思维训练,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分析都是预设好的,运用逻辑手段解决法律问题总有生搬硬套之嫌。人们无法从案例分析中切实体会到逻辑的实际指导价值,训练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摆脱上述尴尬,选取恰当的、典型的教学案例是关键,同时,正确地使用思维训练案例也同样重要。逻辑思维训练中的案例分析与专业角度的案例分析是有区别的。专业角度的案例分析更侧重于法律知识的运用、法律规定的援引与遵守,而逻辑思维训练中的案例分析,侧重的是从逻辑角度分析法律问题,即通过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帮助人们掌握一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思路及其方法。也就是说,逻辑思维训练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案例的,它注重的是分析的逻辑过程,而并不是分析的最终结果。
法律思维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法律思维主体的认知活动必须受到理性的指导和规范,遵循正确思维表达应当遵守的规律和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判断过程的顺畅,确保判断结论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从而实现司法的公正性和思维理性。逻辑知识的具备与逻辑素养的形成,是对法律思维主体正确思维表达的基本要求。法律思维主体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和经验总结,不断强化逻辑思维的训练,才能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素养。逻辑规范的限定是法律思维实践活动中对“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思想体系”[22]P300。实现思维活动的规范限定,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探索和总结。对于法律思维主体而言,这种规范的限定就是要保障思维主体的思维理性,当然也是实现正确思维和理性思维的重要基础。
(二)逻辑适用的司法化面向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研究有助于法律思维活动的指导与规范。只不过是,只有符合法律人的实际所需的理论研究,才能为法律人所接受。形式逻辑对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规则做了系统而严密的论证,形成了科学严谨的符号理论体系。但是,法律适用中的逻辑研究,如果过多地致力于现代形式逻辑的符号推演与论证,则会远离法律思维主体的实际所需,在具体操作中也会因“失去普适性,从而弱化理论解释实践的能力”[23]。“理论和实践之间永远都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24]逻辑理论研究若与司法脱节,则根本无法获得法律适用主体的认同。亚狄瑟曾指出:“逻辑学家们的教科书似乎陷入了奇异公式,符号逻辑、量化理论、图表技术与几率计算之中。”[21]P4现代逻辑通过特制的表意符号实现了对人类思维形式的形式化研究,同时,现代逻辑追求演算的准确性特点,也促使其在数学、计算机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在狄亚瑟看来,那些符号逻辑和奇异的公式是难以吸引法学院的学生们或者法官与律师的”[25]。而且,这些符号公式的适用也“与自然形态的自然普通思维却格格不入”[26]。适用法律思维实践中的逻辑研究不能局限于空泛的理论抽象与符号推演,而应当着眼于法律思维实践本身,充分考虑逻辑适用的法理学依据,在不逾越法律的前提下实现逻辑的理性规范,关注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高度符号化、抽象化的逻辑理论固然促使逻辑的研究更向前了一步,但同时也为法律思维主体间的交流设定了诸多的障碍,影响了逻辑方法的实际操作,这非但无助于实现判断结论的正确性、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而且还使得判断形成的过程更为复杂。在法律思维领域的适用过程中,更多地基于符号推演而形成的对思维活动的指导与规范,由于含有太多的专业的成分,当法律思维主体按照既定的逻辑公式推演、适用法律时,会面对若干的困惑与不解。况且,缺乏数理符号功底的法律思维主体在专业抽象的符号化公式面前,往往会失去学习和接受这些符号公式的动力。抽象的逻辑理论、繁琐的公式推演让法律思维主体对逻辑的适用望而却步,法律思维主体的思维活动无法按照逻辑的规则有条不紊地进行。
逻辑适用的司法化面向,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符号公式的运用,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也决定了法律适用中的逻辑根本无法排除命题、推理的形式化的分析。因为抛弃了形式化分析的逻辑已然不是逻辑,“形式不论脱离还是不脱离内容,总还算做逻辑;但内容脱离了形式,那它无论如何不能算做逻辑”[10],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逻辑的推导与分析,“当逻辑的形式和结构成为法律分析的标准时,这些逻辑结构和形式便成了现代法学派进行法律分析的工具或目的”[27]。在法律判断的形成中,人们需要通过逻辑规则检验判断结论的可成立性,同时需要借助形式化的方法分析、还原判断形成的过程。拒绝复杂繁琐的公式符号及其推演,并不意味着对命题、推理进行形式化分析的否定。比如,“所有S都是(或者不是)P”,“有的S是(不是)P”,“如果p,那么q”( p→q),“只有p,才q”( p←q)等,诸如此类的命题形式刻画可以更好地实现逻辑形式分析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律思维主体在平时已接受过此类命题形式及其符号公式,也便更容易地为法律思维主体所认同。由此进行的逻辑推演能够更好地发挥逻辑工具性学科的作用,进而能够更好地通过指导、规范法律思维而达到论证思想的目的。只不过,倘若使用的符号公式过于专业,或者说非经系统学习难以掌握的知识,则恐怕只有面临被否定的局面了。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分析应当是简单的并具有可接受性的。
法律思维的理性实现需要逻辑的规范,掌握逻辑规则是法律思维主体排除主观因素干扰的技术性保障。为了更好地实现逻辑对法律思维的理性规范,法律适用中的逻辑研究必须紧密结合法律思维实践,实现由理论研究的抽象复杂到实践指导中的简单操作的转变。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只有面向司法,符合法律人的实际思维所需,才能通过对具体个案的严谨的逻辑审视,概括出适用于法律分析中的逻辑规律规则。法律适用中的逻辑应当是简单化的,并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如波斯纳所言,“当法官和律师确定使用逻辑时,他们使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28]P68。逻辑规则的概括与应用,无论是在抽象程度,还是在呈现方式方面,都应当协调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最大化地避免理论在操作层面上的尴尬。
逻辑一旦内化为法律适用中的技术性规范,则始终会影响着法律思维模式的构建。当思维主体所做的判断受到外在干扰增多时,逻辑对思维模式的引导与限定则会表现得尤为明显。逻辑虽然不能提供给法律人完美的规则体系,但却是实现法律思维主体理性判断的技术性保障。肯定逻辑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逻辑作用的无限夸大,更多的只是强调逻辑对法律思维的指导与规范。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王洪.法律逻辑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3]王洪.法律逻辑:回顾与展望[J].政法论丛,2009,6.
[4][美]安·塞德曼等.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M].时宜人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德]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9]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0,1897.
[10]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J].齐鲁学刊,2012,1.
[11]王洪.司法的不法与司法的不正义[J].政法论丛,2014,6.
[12]孙培福.传统逻辑功用再思考[J].理论学刊,1999,5.
[13][苏]B·H·库的里亚夫采夫.定罪通论[M].李益前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6]胡建萍.从一起案例看逻辑推理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运用及启示[A].梁庆寅主编.法律逻辑研究(第1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7]林喆.法律思维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18]周远清.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00,3.
[19]张静焕.法律逻辑方法与个案评价[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20]吴家国.从传统逻辑到普通逻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1][美]鲁格罗·亚狄瑟.法律的逻辑[M].唐欣伟译.台北:台湾商周出版社,2005.
[22]王纳新.法官的思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3]陈金钊.从法律感到法律论证——法律方法的转向[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1.
[24]周祯祥.理性、规范和面向司法实践的法律论证[J].政法论丛,2015,2.
[25]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5.
[26]孙培福.逻辑现代化:从天然渐变为人造[J].山东社会科学,2005,5.
[27]印大双.如何刻画法律推理中的事实与规范[J].政法论丛,2014,6.
[28]苏力.法理学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2.
(责任编辑:唐艳秋)
Function of Logic and Its Realization in Legal Thinking Practice
LiLiLvJian-wu
( Media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Although logic can not provide a perfect rule system for lawyers, it offer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m to judge rationally. To affirm the role of logic in legal application is not to overstate its function infinitely, but to emphasize its instructive and regulative role for legal thinking. Legal thinking activities ought to realize logic norms within the scope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to realize reasonable inference and argument in thinking practice through rule constraint. Once logic is internalized a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legal application, it will ha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thinking mode and then guarantee the rational realization of legal thinking legitimacy. It is believed that logic analysis applicable in legal application should be uncomplicated and acceptable.
【Key words】legal application;logic norms;form analysis;rational judgment
【中图分类号】DF0-05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 丽(1976-),女,山东即墨人,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律逻辑;吕建武(1981-),男,河北冀州人,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逻辑、逻辑应用。
【文章编号】1002—6274(2016)02—1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