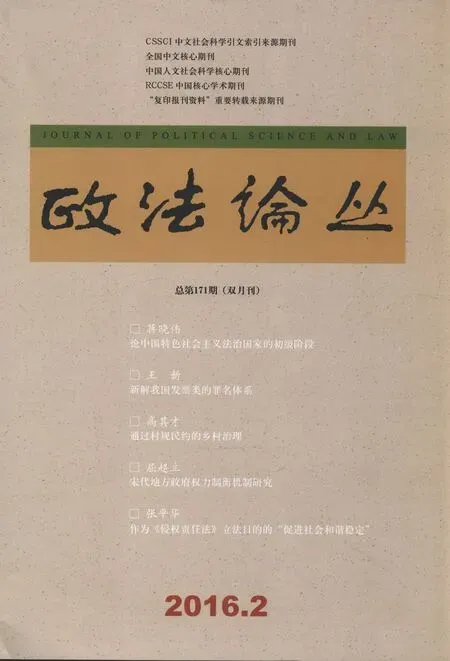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在防控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
2016-02-12魏红
魏 红
如何发挥社会控制在防控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作用
魏红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内容摘要】西南地区地处偏远,部分区域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具有社会关系松散、流动性大,受教育水平低、自我控制弱化等特征,这些地域性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高发、频发态势。在当前法律保持高压打击的情况下,犯罪上涨趋势仍然不减,在这种困境下,可从社会控制角度出发,强化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建立社区、村寨预防制度;注重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个体自我控制形成的影响,使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能够共同发挥作用,达到防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关 键 词】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控制社会关系纽带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强调了从严惩治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为性侵害未成年人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权利保护机制。但是,近几年,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然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根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发布的《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显示:“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媒体曝光的案件高达503起,平均0.73天就曝光1起,也就是每天曝光1.38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1]。一方面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另一方面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却呈现持续高发态势。为什么在当前我国司法体系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的情况下,犯罪发生率仍居高不下,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社会控制作为社会学范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01年,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首次在论文集《社会控制》中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控制概念及其理论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到现今主要有社会纽带理论、自我控制理论、控制平衡理论以及强制性控制与社会支持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从社会性约束机制角度研究犯罪,认为当社会控制出现弱化时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为从犯罪社会学角度研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西南地区地处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
一、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具有区域性特征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之所以有些人没有出现犯罪行为,主要源于两种类型控制的制约: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的控制涉及诸如个体意识、守法和积极的自我概念等;社会的控制涉及对诸如家庭、学校和宗教等传统社会制度的依恋和卷入,弱化的个人控制源于弱化的社会控制”[2]P235。因此,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行为人的社会特征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从对行为人社会控制所涉及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犯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而在以往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与严重的危害后果,以及被害人的年龄、在校学生以及留守儿童的身份,对犯罪行为人所呈现的社会特征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人们深受社会环境影响,其行为选择都被深深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迹。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犯罪行为人显现出来的行为特征背后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虽然惩治性侵害犯罪的法律规定一直在不断修改与完善,但在严峻的犯罪现实面前,法律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处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本文下面将通过对西南地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数据分析,从中发现犯罪行为人特征,以此探求犯罪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分析的案件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布的,近五年来西南地区(不含西藏)五省市、自治区发生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收集到的共计288个案例、296个犯罪行为人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四川省88个案例、重庆直辖市59个案例、贵州省55个案例、广西壮族自治区47个案例、云南省39个案例。虽然从2013年7月起,最高人民法院开设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裁判文书,但由于性侵害犯罪本身具有高犯罪黑数特性,加之性侵害案件的隐私性与敏感性,在我国目前所有公开的数据库与案例库中所占比例不高,因此,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性侵害犯罪具有一定的困难与局限性。由于本文所涉及样本规模范围与收集途径有限,呈现出来的西南地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偏差。在保证案件数据统计分析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本文分析认为,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经济收入低
对于犯罪行为人的职业,在本文收集的案例中,对其中101个行为人职业有效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民所占比例占57.4%、无业人员占16.8%、教师占6.9%、务工人员占5.9%、退休职工占4.0%、其他占8.9%,真实地反映了犯罪行为人中农民比例居高的特点。通过分析2013年西南地区(不含西藏)五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数据得知,该地区当年从业人员总计为14059.39万人,其中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分别为48.4%、20.5%、31.0%①。很明显,该地区将近一半的人口依然从事着第一产业。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自2008年至2013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40%下降至接近30%②。西南地区(不含西藏)五省市、自治区除重庆以外,在2008年至2010年间,其比例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从业人员比例甚至一直处于60%以上③。虽然后三年的数据有所缺失,但是从总体来看,西南地区大部分人口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此外,从非农业人口统计情况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自2008年至2013年一直处于15%到20%的较低比例状况④。
在现今社会崇尚金钱与物质享受等畸形价值观的影响下,欠发达区域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婚姻对象的选择与家庭关系的稳固,造成一些适婚年龄男性单身或者已婚男性离婚,由于其性需求无法从正常的伴侣关系中得到满足,有可能通过采取一些非正当手段来解决与释放性焦虑和性压力。此外,如果社会成员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生存状况恶劣,长期压抑性生理需求有可能累积演变而导致性心理变态,从而加大诱发性侵害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二)社会关系松散,流动性大
对收集案件中犯罪行为人职业的有效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犯罪行为人的职业分布情况为,无业所占比重为16.8%,务工人员和退休职工分别占5.9%和4.0%,而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员(包括教师、保安、个体户、协警等)仅占15%。由此可见,犯罪行为人的职业大多不固定,表现为社会关系松散,社会流动性大。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往往选择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寻找务工机会,由此大量的进城劳务人员增加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人们,时常面临着失业和另谋就业的风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广西五省市、自治区城镇失业总人口为104.8万人⑤。为了维持生计,人们不得不常常四处流动寻找务工机会,这种状况使得外出劳务人员群体的家庭婚姻关系较为松散,正常夫妻关系的稳固性也会受到影响。此外,由于社会流动性加大,社会成员对家庭、族群的依附程度降低,极易导致个人情感纽带松弛,对其行为后果的负向后果顾虑大大降低,如在犯罪冲动刺激强化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三)受教育水平低,自我控制弱化
上述案件中,有关行为人文化程度的有效数据181个,分析比较发现,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犯罪行为人所占比例高达40.9%,初中文化程度的犯罪行为人所占比例为29.3%,几乎接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高中或中专文化的只占12.7%,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仅有8.3%,甚至还有8.8%的文盲存在。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文化程度低这一显著特点,可以说,10个犯罪行为人中就有8个人仅接受过基础教育甚至以下教育水平。据2013年西南地区(不含西藏)五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显示,该地区小学、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人口数分别为1898.6万人、1344.38万人、376.41万人。此外,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3年西南地区文盲人口在15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云、贵、川远远高于全国比例,其中贵州省甚至高达10%以上⑥。
西南地区地处偏远,相比较东部及沿海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低,高等教育高素质人才尤为缺乏。很多家庭由于经济条件恶劣,为了维持生活生计,许多青少年不得不早早地离开学校外出打工挣钱,在本应该接受学校教育的黄金时期却过早地踏入了社会,于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多元化价值观和各种文化思潮代替了来自学校正规的、主流社会的教育,青少年极易受到身边的群体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缺乏社会主流向上的价值观熏陶,而很多被主流社会核心思想文化所谴责与批判的行为却渐渐习得和接受,来自道德信仰的约束力日渐式微,自我控制和约束力逐渐弱化,在面临犯罪的诱惑时,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面对不断上涨的犯罪趋势,当前偏重于惩罚的法律力不从心
(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不断上涨趋势
近几年,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态势不减,2010至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猥亵儿童罪7963件,8069人,平均每天5.5件;起诉嫖宿幼女罪150件,255人;起诉引诱幼女卖淫罪68件,121人⑦。2012至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猥亵儿童罪案件共计7145件,平均每天6.5件,三年间,每年案件总数呈逐年上升趋势⑧。仅2014年,全国审结涉黄犯罪案件1.2万件,同比上升15.7%,其中,涉及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犯罪1.1万件,上升19.9%⑨。
(二)西南地区性侵害犯罪频发的原因
犯罪控制理论是基于不同的人性观,即假定人们生性自私并有包括实施犯罪在内的反社会性行为,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因此,该理论试图解答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人们会犯罪,而是为什么人们不去犯罪。其中,最为著名的犯罪学控制理论当属美国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纽带理论。社会纽带理论包括四个要素:依恋、投入、卷入和信念,该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形成了人们对社会强烈的契约意识,从而保证其个人行为与社会的一致性;只有当约束人们不去破坏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纽带弱化时,才容易出现越轨行为和犯罪现象。因为犯罪行为会破坏甚至导致其与家人、族群和工作单位关系纽带的断裂,而往往正是基于维护这种社会关系的心理,以及对关系破裂后的恐惧,人们才会发自内心地抑制违法越轨行为。一旦社会成员失去了与这些社会纽带的紧密联系,将会丧失对社会的依附感与归属感,内在自我控制出现弱化,实施犯罪行为的随意性开始增强。因此,分析犯罪行为人背后的社会控制原因,是构建犯罪社会预防体系的前提与基础。
1.“熟人关系”社会解体。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典型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人际交互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自然、自发及自觉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在“熟人社会”中,各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形成共同认可的社会共同规范并维系着传统的礼制道德秩序。因此,“‘熟人社会’的优势是,可以通过伦理道德来有效约束其成员行为达到自我秩序安定的效果;并且更深层次的是成员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感及社会认同”[3]。“熟人社会”中成员之间彼此熟识,由此形成的复杂微妙的熟人关系,使得人们在认知与行为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并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因此,一旦社会成员中有人出现越轨行为,会很快被周围的熟人知道,进而受到已经形成共识的社会共同规范与社会舆论的谴责与批评,以此约束人们越轨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保持社会成员个人行为与社会的一致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步伐不断深入与加快,传统“熟人社会”已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城镇里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联络。随着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承载着熟人社会的大量自然村寨在慢慢消亡。一方面是部分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传统与现代法治社会文明发生冲突,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认同一致性;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生活日益功利化而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熟人社会”中传统的道德秩序逐渐被异质化,社会成员原有的安全感与社会认同感渐渐消失,传统的道德规范被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共同规范尚未形成并得到认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越轨行为、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几率将大大增加。特别是在西南地区,伴随着传统民族村寨、族群等社会结构的解体,人们对家庭、族群的依附程度明显降低,参与传统群体活动、行为减少,往往不再追求群体的认同感和一致性;而且心理上对于群体组织的奉献与投入也大不如从前,与社会联接的纽带在无形中慢慢松弛,这更易导致犯罪行为实施可能性的增大。
2.内在自我控制弱化。就社会控制理论而言,行为人内在控制弱化是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本文收集案件情况来看,西南地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人大多文化程度低、缺乏固定职业、经济收入不高、社会流动性大。而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环境中,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低意味着个人对事物认知能力不足以及知识技能的欠缺,而这些因素都将直接影响着行为人道德意识水平与法治认知能力的水平。在性侵害犯罪中,行为人往往为了满足一时的性欲需求而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可谓是丧失了个人最基本道德底线的行为。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一方面表现出行为人缺乏对法律责任的认识与了解,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了其道德自我约束力的不强。由此可见,行为人内在控制的弱化极易引发性侵害犯罪行为的发生。
3.人口性别比失衡。本文通过对2008年到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与西南地区(不含西藏)五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发现,该区域2008年至2013年的总人口性别比(以超出女性100%的百分比数为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0%以上⑩,西南地区的总人口明显呈现出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本文统计分析上述五省市、自治区男女性别比得知,2008年男女性别比为1.082,2009年为1.078,2010年为1.076,2011年为1.077,2012年、2013年分别为1.079与1.076,表现为每年男性人口都要比女性人口多出数百万人。
男女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每年新增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找不到配偶,而男性未婚人口数量的增多,将加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发生的风险。一方面,性别比失衡会导致婚姻市场供需失调,大量年轻男性无法找到适婚对象,从而被动单身,如果再受教育水平低、生活技能缺乏、经济收入来源有限等条件的限制,该类人群将直接处于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相对恶劣,使得他们组建家庭的几率更低,在性心理方面将长期处于压抑与焦虑状态;同时,男性参与社会活动相对于女性而言更为频繁,自我控制与行为顾虑较少。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由于思想单纯幼稚,社会经验不足,更容易成为受性侵害的对象。多重因素的叠加,加剧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三)单纯刑罚惩治效果有限
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我国法律一直秉持严厉打击、从重处罚的态势。2007 年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明确提到了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现行刑法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等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于办理此类案件的政策把握与法律适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并着重强调: “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并规定“对于强奸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一般不适用缓刑”、“对于判处刑罚同时宣告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告禁止令”;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在刑法体系上进一步完善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可见,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法律规定一直在不断完善;同时,刑法量刑等级关系简表也显示性侵害犯罪中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量刑均衡[4]P280,在司法实务中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加重情节处罚也相对较重。
由此可见,法律对于此类犯罪的惩处不可谓不严、罪名不可谓不多,照此发展趋势,将形成刑罚威慑功能不断放大,社会重刑观念凸显,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也会陷入越来越依赖刑罚处罚的困境之中。但从目前刑事司法惩治犯罪现状来看,过于依靠刑事惩罚的犯罪控制效果十分有限;同时,刑事惩罚具有事后性,犯罪行为人往往在实施犯罪之后已经对其行为触犯法律后悔不已,在严刑峻法之下,很容易造成犯罪行为人内心仇恨,滋生报复社会念头。正如人们认识到的:刑罚是把双刃剑,过度的惩罚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有资料显示,性分割犯罪行为往往具有反复性,许多犯罪行为人在实施该类犯罪受到处罚之后,回到社会中还会重新实施犯罪。在对性侵害再次犯罪预防方面,国外曾进行过为期20年的对性侵害犯罪人定罪执行后的跟踪追溯研究,发现,60%的高风险犯罪人被重新定罪[5]P92。就此情况分析,该类犯罪行为人更需要有对身体进行调适、心理疏导的社会帮助,矫正治疗的意义可能大于刑罚意义的处罚。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系来看,如此个体化、针对性强的犯罪预防措施还非常缺失,因此,刑罚惩处的有限性,在对性侵害再次犯罪的预防效果上也显现出局限性。
三、强化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的社会控制是解决困境的关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要解决当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所存在问题的关键,应该从犯罪背后存在的社会原因分析入手,发现并尽快形成新的社会共同规范,以加强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来应对“熟人社会”解体后社会纽带弱化带来的问题,从而探索一条以犯罪社会预防与刑事惩治并重的社会控制新路径。
(一)建立社会共同规范是预防犯罪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全球化的主要影响是出现了一个“全球化都市社会”,在那里,“传统的东西终结了”[5]P13,自然的世界被人造的世界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所信奉的真理和传统的行为都受到了挑战;失去了传统的生活也对自我的认同提出了挑战;自我意识不断地受到不同观点的挑战,也受到了社会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挑战。同样,“传统的终结即发现的开始”[5]P13,传统契约的消弱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人生的旅程不再具有可预知性,也就加大了犯罪发生的风险性与可能性。由于城镇化进程对西南地区传统社会的冲击与影响,原有道德、风俗习惯的解体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已成为近年来性侵害犯罪大量发生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因此,新的道德、信仰的培育与尽快建立,社会共同规范的重新形成与普遍遵守,应该是预防犯罪的土壤和重要基础。
(二)加强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是应对“熟人社会”解体的核心
在当今传统“熟人社会”解体的背景下,在非官方的社会领域中,自由意味着社会秩序将建立在自我控制的基础之上,而非国家机构的控制。如今社会犯罪率高居不下的情势与社会自我控制弱化、社会共同规范的缺失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弱化与缺失导致社会失去了一种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能够不断再生并维持,一种能有效地实现人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相互克制的社会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共同社会责任存在于社会习俗、社会传统、一般性认知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习性之中。如果说,社会共同规范的缺失是理解犯罪的关键所在,那么,犯罪预防的关键就是社会组织性与凝聚力的加强,以及社区、族群观念的形成,才能突显这种能力持续性的作用,最终达到约束社会成员、增强个人归属感、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三)良好的家庭、学校教育是培养个人自我控制的摇篮
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纽带已逐渐成为个人情感的一部分,当其出现偏差行为并可能触犯法律时,这种情感纽带的约束作用便被激发出来,以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特拉维斯·赫希强调,形成自我控制机能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在个体的儿童时期能享受到家庭、学校的培育,所以,控制理论的倡导者将家庭、学校视为实施有效干预的关键场所,用一个贴切的比喻来说,“家庭是避免孩子参与犯罪的‘保育箱’和‘免疫药’”[6]P67。
四、以多维度、融合式社会控制防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美国犯罪预防模式的主流观点和要义是‘寓防于控,以控达防’,突出控制在防治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7]P88,形成了一般预防、提前预防和防止再犯的三个层次的犯罪预防模式;英国则是“在兼顾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同时,将犯罪预防的重点转向情景预防,对犯罪实行由多机构参与、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综合治理”[8]P33,这些犯罪预防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建立犯罪预防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树立犯罪预防与刑罚惩治并重的刑事司法理念
我国犯罪预防的基本理论与指导方针注重“综合治理理论”,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过于依赖刑罚的作用,导致与高投入的司法成本相比,犯罪控制效果不明显。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由于侵害行为隐蔽性高、犯罪黑数大,性侵害案件立案难、取证难,刑罚的惩罚作用难以全面实现;同时,未成年性侵受害人身心受到的侵害,很难仅仅因为犯罪行为人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而得到修复和弥补。对被害人而言,阻止与预防性侵害的发生远远重要于对犯罪人事后的惩罚。因此,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对策略上,预防的意义要大于单纯的惩罚,在司法政策上应体现为强调与重视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与此同时,以预防此类犯罪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更要注重社会预防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不同维度融合式社会控制的作用,真正树立起犯罪预防与刑罚惩治并重的理念。
(二)发挥内在控制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1.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注重家庭与学校教育对个人内在控制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犯罪率的增加和破坏法律及秩序的行为不能简单、一味地归责于贫困和失业。相反,犯罪率不断上升的根源在于丢弃了关于婚姻家庭的正确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对孩子进行抚育和培养的行为[6]P155。
在西南地区要尤为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所带来的附属产物。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并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重庆直辖市、四川省的比例已超过50%,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的比例超过40%[9]。据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严重的则会导致心理畸形发展并在行为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范和越轨现象[10]。农村留守儿童与城镇流动儿童,普遍存在学业成就感弱、辍学现象严重,性格形成偏差、心理问题普遍,情感交流缺失、品行操守不良等问题,是未成年人中最容易越轨、犯罪的群体,也是最易遭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人群。
在西南地区留守儿童中,通过强化家庭教育,增加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的交流、沟通,增强家庭的亲密度,可以使儿童获得充分的爱并能够培养自我价值感;学校教育中,注重心理辅导、信念培育,培养未成年人对主流社会价值观与信念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具备正向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能够促使个人自我控制的良好形成,达到从根源上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预防的目的。
2.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与道德水平,强化个人自我控制约束力。从本文对西南地区性侵害犯罪人情况的分析来看,大部分罪犯受教育程度低,个人素质不高。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犯罪行为的发生,不仅受到社会环境外部控制的影响,而且个人内在自我控制能力的强弱,往往成为影响犯罪发生与否的直接因素。因此,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除了强调法律制度体系的正式控制外,还需要充分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价值观教育同基础知识技能的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强化社会成员的内在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将外在的强制约束力内化为自觉抵制犯罪的行为。
(三)建立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相融合的预防机制
正式控制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法律直接赋予的强制性,制约那些偏离社会秩序以及与社会秩序相冲突的行为,其往往以国家法律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非正式控制往往是以风俗习惯、社会规则与舆论的形式应对越轨与偏离社会的行为,非正式控制对正式控制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尤其是对那些潜在存在的风险,以及在正式控制不便于直接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1.建立民族乡镇、村寨预防制度,发挥非正式控制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社区作为城市主要的群体联络单位,是实现犯罪预防的重要载体。而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乡镇、村寨等组织是当地民众之间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以民族乡镇、村寨为单位建立预防制度,对于预防性侵害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从该类犯罪的行为特征来看,行为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熟人为侵害对象,而在村寨生活中的熟人关系不外乎是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或族群关系。民族乡镇、村寨预防制度通过利用乡镇、村寨中的族群组织来强化个体对家庭、族群的依附度,是传统社会熟人关系在现代化生活中的变通,既可以加强个体成员在家庭、邻里和族群中的依附性与归属感,又可以适应城镇化进程的发展,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疏远陌生关系,建立起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
西南地区各乡镇、村寨族群组织调控社会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如通过讲理、摆古等活动教化少数民族同胞,增强民族内聚力;还可以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传统议榔制、侗款制与石牌制在新时期的积极作用,将朴素的是非善恶判断标准、自然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共同规范相结合,以乡规民约的形式上升成为整个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通过乡镇、村寨社会舆论的褒奖、谴责甚至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奖善惩恶,达到积极预防的效果。
2.完善司法体系,强化正式控制。从我国目前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情况来看,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着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之处,如对未成年性侵被害人保护的年龄应该扩展至18周岁以下的所有未成年人,并且不论男女,以实现对所有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由于未成年人在不同的成长发育阶段,其身心发育成熟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建议按照性侵害人、性侵受害人年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相应细化量刑幅度档次,深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对性侵害行为方式的认定上,建议扩大行为范围,将非自然性交方式也纳入刑法规制之中。
对于如何预防性侵害犯罪人再次犯罪,虽然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采用了禁止令作为预防的手段,但是该禁止令只能限制有犯罪前科之人,不包括因猥亵等其他性侵害方式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分子,其预防效力还具有较大局限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参考、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采取特殊备案方式,对于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违法记录的人,根据危险程度和典型意义实行一定范围程度公开或可查询的备案登记制度,在可能接触到未成年人的工作环境中特别是学校、幼儿园等单位,要加强对应聘者的备案审查制度,在审查中若发现具有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违法犯罪记录史一概不予录用,预防其接触易犯罪环境而再次实施犯罪。
(四)加强性教育,培养未成年人的性自卫能力
根据《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显示, 在受访的1346名男生和2136名女生中,仅有20.0%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48.3%“不知道”何为性教育,31.7%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知道一点点)”;在接受访问的394名中小学教师中,49.7%从来没有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而在337名受访家长中,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也未超过半数[1]。可见,我国儿童的性教育普遍性不强。由于未成年人在性侵害实施者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地位,故而加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知识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防范意识,增强性自卫能力,可以大大减少犯罪行为人实施性侵害的机会,这也是多维度社会控制的预防措施之一。
五、结论
近年来,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该类犯罪行为、情节越来越恶劣,更重要的是当被侵害人是未成年人时,人们内心的良知被深深地唤醒。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刑法的本质使然,但是,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才是目的所在。社会控制理论从犯罪行为人的角度出发,分析犯罪行为产生的社会原因,认为社会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的削弱,以及犯罪行为人内在自我控制的弱化,是导致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最终原因。笔者认为,近年来西南地区性侵害犯罪率的上升,与该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原有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对此类犯罪的防控不能仅仅着眼于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刑罚惩治力度的加大,还需要从修复与强化社会纽带关系出发,通过发挥社会纽带对社会成员在认知、行为规范形成方面的影响与作用,将社会正式控制的外在约束力逐渐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体自我的控制力,从根源上起到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积极预防与控制作用,从而达到全面防控犯罪的目的。
注释:
①该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广西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以及重庆统计年鉴。
②该数据是通过整理分析2008-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农业人口数量得出。
③该数据是通过整理分析2008-2010年广西、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统计年鉴中农业人口数量得出。
④该数据是通过整理分析2009-2014年广西、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统计年鉴中非农业人口数量得出。
⑤该数据来源于2013年中国分地区城镇失业登记人员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2015-12-22.
⑥该数据是通过整理分析2009-2013年广西、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统计年鉴中人口文化程度得出。
⑦本数据来源于政府门户网站:检察机关3年起诉猥亵儿童罪7963件8069人,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29/content_2690264.htm, 2015-12-6.
⑧本数据来源于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5/id/1637974.shtml, 2015-12-6.
⑨本数据来源于中国法院网: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守护国家法治生态——2014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分析”,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5/id/1612546.shtml,载《人民法院报》第五版, 2015-12-08.
⑩该数据是通过整理分析2008-2013年广西、贵州、四川以及重庆统计年鉴中有关人口性别的数据得出。
参考文献:
[1]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会“女童保护”项目.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EB/OL]. http://edu.163.com/15/0302/17/AJNGBVCM00294N01.html, 2015-12-22.
[2][美]斯蒂芬·E·巴坎.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第四版)[M].秦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吕承文,田东东.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J].重庆社会科学.2011,11.
[4]白建军.量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英]海泽尔·肯绍尔.解读刑事司法中的风险[M].李明琪,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6][英]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7]董士昙.犯罪预防模式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4,1.
[8]董士昙,刘琪.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3.
[9]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妇运.2013,6.
[10]卜范龙.教育评论:莫让留守儿童成为时代的孤儿[EB/OL].http://edu.ifeng.com/a/20141203/40890240_0.shtml,2016-01-08.
(责任编辑:唐艳秋)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Control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ime of Sexual Offense for Minors in China’s Southwest Regions
WeiHong
(Law School of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China’s southwest regions are remote, and there are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 and a poor education in some areas.In these regions, the offenders who commit sexual assaults on minors have som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their social relations are incompact, and they have a high degree of mobility, as well as having a low educational level and a weak self-control ability.The crime of sexual offense for minors presents a situation that it has a high incidence and happens frequently because of thes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currently there is a lasting high-pressure attack of law against such crimes, the rising tendency of this kind of crime is still maintained. While facing this dilemma,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im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rime of sexual offense for minors,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control,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cohesive force of our society, as well as building up the system of prevention of village and community; in the meanwhil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emanating from the education received in family and school upon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let formal control and informal control work together.
【Key words】China’s southwest regions;crime of sexual offense for minors;social control; the ties of social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DF52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魏 红(1969-),女,山东阳谷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司法。 在前期案例收集、数据分析、资料整理过程中,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耿琳琳参与了相关实证分析研究活动,在此表示感谢。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法学会重点调研课题“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调查研究”[KT201401(Z)]、贵州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教学重点课题“贵州高层次刑事法律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黔教研合JG字(2013)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编号】1002—6274(2016)02—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