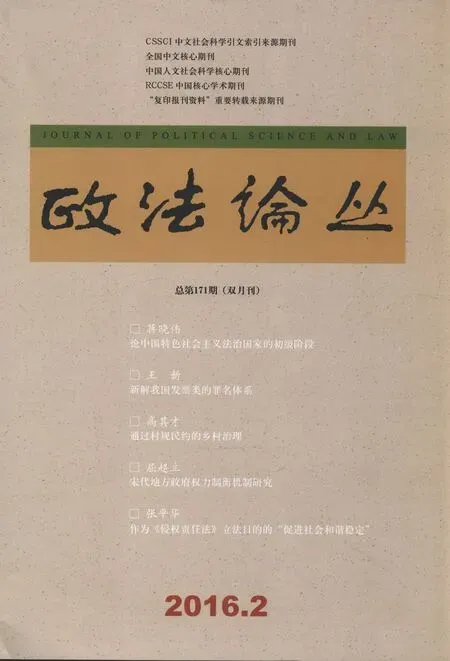关于交易习惯的几点思考*
2016-02-12米新丽
米新丽
关于交易习惯的几点思考*
米新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70)
【内容摘要】交易习惯作为交易中人们反复使用、普遍接纳的做法,其性质为事实习惯,在民法上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立法者在制定法中宜吸纳合理、合法的交易习惯,使立法更能反映社会需求和交易规律,从而更能得到普遍遵行。在民法典编纂工作已启动的背景下,重提制定法对交易习惯的吸纳有更重要的意义。司法者在实践中也需要重视交易习惯的认定和适用,并根据一般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以及消费者合同的不同特点,适用交易习惯时采取相适宜的对待规则,以更有利于化解纠纷。
【关 键 词】交易习惯立法吸纳司法适用
交易习惯乃各国民法学界与实务界均非常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之一。就学界而言,虽然对交易习惯的解释存在不同表达,但基本都认同交易习惯的反复实践性和普遍接受性。就中外立法实践而言,对交易习惯亦不乏规定。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5条第2 项规定: “行业惯例指进行交易的任何做法或方法,只要该做法或方法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一类贸易中已得到经常遵守,以至使人有理由相信它在现行业中也会得到遵守。此种惯例是否存在及其适用范围,应作为事实问题加以证明。如果可以证明此种惯例已载入成文的贸易规范或类似的书面文件中,该规范或书面文件应由法院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我国《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对交易习惯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7条把交易习惯解释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以及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综合学者观点以及中外立法之规定,笔者认为,交易习惯是指在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反复使用、普遍接纳的做法或者当事人之间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这些做法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其有如下特点:其一,交易习惯是长期、客观存在的做法或规范,经由长期反复实践而形成。故当事人主张适用时,必须举证证明其存在,法官依职权主动适用时,须予以充分的解释。其二,交易习惯为交易双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一个交易惯例,既指一个特定交易或特定地区的习惯,又指对一个文句或短语的含义在特定交易或特定地区都普遍知晓这样一种情形。”[1]P365。其三,交易习惯有的具有一般性,有的具有特殊性。交易习惯的一般性不仅指其在地域上通行于全国,而且指根据一般人的通常理解予以认可。交易习惯的特殊性一方面指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的交易习惯;另一方面指具有行业或特定交易的特殊性。其四,交易习惯具有合法性。指交易习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否则,即使当事人自愿适用,也不得据以解释合同、填补漏洞。
从司法实践来看,有不少法官依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合理运用交易习惯进行司法裁决,化解了合同纠纷。由此可见,交易习惯在民事立法和司法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正因如此,有关交易习惯的讨论比较热烈。本文希望在对交易习惯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强调制定法对交易习惯的吸纳,以使制定法更为科学、更能得到普遍遵行。并对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提出一种新的思路:根据合同种类的不同确定交易习惯的适用规则,使交易习惯在促成交易、解释合同以及化解纠纷等方面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
一、交易习惯的性质
尽管对交易习惯的概念学界认识比较统一,但对交易习惯的性质,却存在一些争论。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事实习惯说、习惯法说、兼具事实习惯与习惯法说。事实习惯说认为,“所谓习惯,是指当事人所熟悉或者实践的惯行表意方式,它是指事实习惯而非习惯法。”[2]P147习惯法说认为,“习惯法是一定社会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惯行的,为一定群体的人们在心理上所接受的,能够象法一样规制约束人们行为的,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合同法所说的交易习惯即指习惯法”。[3]兼具事实习惯与习惯法说认为,“在《合同法》上,‘交易习惯’既可能是指‘事实上的习惯’,也可能是指‘习惯法’,应当根据解释前提的不同,做不同的区分。可以认为,在合同法上某种事实的确定时,‘交易习惯’应作为‘事实上的习惯’来理解,在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目的解释上,‘交易习惯’应作为‘习惯法’来理解。”[4]。那么,对于交易习惯究竟应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关乎交易习惯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
有关习惯和交易习惯的定义前文已有述及,那么,何谓习惯法?有学者认为,“所谓习惯法,系指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反复惯行之事项,经国家承认而具有法的效力之规范,英美法称Common Law或Customary Law。”[5]P21有学者认为,“唯习惯须经国家承认时,方成为习惯法。民事采用之习惯法,必须具备以下要件:其一,须有习惯之存在;其二,须为人人确认其有法之效力;其三,须系法规所未规定之事项;其四,须不背于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其五,须经国家(法院)明示或默示承认。”[6]P302亦有学者对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其一,习惯为“事实”,依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张该习惯之人负有举证责任。习惯法则为法律,其为法院所知者,应依职权径行适用,若为法院所不知,依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其适用为有利益之当事人,负陈述并举证之责任;其二,习惯为社会之惯行,习惯法则为法院所承认;其三,习惯须当事人援用,法官是否以之为裁判之大前提,仍有斟酌裁量之余地。习惯法则法官有适用之义务,设不予适用,其判决当然违背法令。[7]P270-271由此可见,习惯与习惯法并非同一概念,交易习惯作为习惯的一种,不宜理解为习惯法。
笔者认为,交易习惯,应理解为事实习惯,因为:其一,习惯法必须经过国家认可,事实习惯是一种客观的做法或规则,不必经过国家认可。而交易习惯不以国家认可为前提,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符合事实习惯的特点;其二,习惯法因经过了国家认可从而具备了法律效力。但事实习惯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交易习惯正是如此;其三,习惯法因具备当然的法律效力而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适用,但交易习惯须经法官的判断和释明,方可在司法裁决中加以适用。比如我国《合同法》第61条:“……,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此处的“交易习惯”法官无法直接引用,必须对其内容予以审查和合理解释,方可载于判决书中。此外,我国《合同法解释(二)》)第7条也把“交易习惯”解释为“做法”,而且需要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这也就把“交易习惯”定位到了事实习惯中。至于“兼具事实习惯与习惯法说”的观点,出发点很好,希望藉此对交易习惯的理解提供更开阔的思维,从而给法官适用交易习惯提供新的视角。但其也存在不足:首先,从逻辑关系上讲,事实习惯与习惯法分属不同范畴,所以,交易习惯不可既做事实习惯又做习惯法;其次,这种理解可能会使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变得更为复杂,同一个概念在适用上并不同一,给法官的审判实践带来困惑。
由于对交易习惯认识上的差异,使有学者在界定交易习惯范围时存在误区。比如,有学者认为,“商业惯例不是交易习惯因而不具有补充合同内容、解释合同条款的效力,司法中应予以甄别”。[8] P295从作者的分析来看,其商业惯例不是交易习惯结论的前提是:认为交易习惯是习惯法。但是,如果把商业惯例排除在交易习惯之外的话,那么在商事合同中,用以补充、解释合同条款的交易习惯又是什么呢?而事实上,商业惯例恰恰是一类很重要的交易习惯。对于交易习惯的分类,学者们有这样的表述:“习惯有社会全部之一般习惯与行于一地方之地方习惯,有行于一般人民间者,有仅行于特定阶级或职业者。”[9]P466“其通行于全国者,谓之一般习惯。通行于一地方者,谓之地方习惯。至一般人所信行者,谓之普通习惯。适用于特种身份或职业及地位者,谓之特别习惯。”[10]P28“交易习惯可以分为:一般的交易习惯,即通行于全国的习惯;特定区域的交易习惯,即所谓的地区习惯;特殊行业的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长期从事某种交易所形成的习惯。”[11]P426虽然学者们的分类标准和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都认为交易习惯有一般习惯(全国习惯)、地区习惯(地方习惯)和行业习惯(特殊习惯)之分。看来,行业习惯属于一类重要的交易习惯已毋庸置疑,那么,商业惯例恰是属于行业习惯的重要内。
二、交易习惯的立法吸纳
前文已述,交易习惯在民法上占据重要地位,对合同法而言尤其重要。更有学者把交易习惯之于合同法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交易习惯是合同订立的方式根据、合同成立的时间根据、合同义务的发生根据、合同内容的确定根据、合同条款的解释根据等,[12]笔者深以为然。既然如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如何对待交易习惯?
从立法者角度来讲,对业已存在的交易习惯进行梳理、分类和深入研究,将其中合理的部分纳入到制定法中来,将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吸纳交易习惯将有利于立法的科学性,并使之富有生命力。交易习惯系一定领域、一定行业或一类交易中反复使用而形成,反映了一定的客观规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首创精神。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的生命力来自于符合社会需要,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深厚的实践基础,法律的科学性来自于尊重客观规律。”[13]“在制定法上注意研究并及时采纳习惯,不仅可以弥补制定法必定会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疏忽,以及由于社会变化而带来的过于严密细致的法律而可能带来的僵化;更重要的是,吸纳习惯也是保持制定法富有生命力,使之与社会保持‘地气’,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渠道。”[14]所以,立法对交易习惯的尊重将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吸纳交易习惯有利于制定法的可实施性,并使其得到普遍遵行。“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15]P25虽然“肯定会失败”的表述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因为法律的实施既要靠国家强制力,更要靠民众内心的认同和遵从。而习惯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民众的内心认同。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将法律分为四种:政治法、民法、刑法以及风尚、习俗。对于其称之为第四种法律的风尚、习俗,他这样写道:“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16]P70卢梭这段经典的论述,将习惯置于公民“心中之法”的地位,突显了习惯的力量。制定法中若将公民的“心中之法”进行合理吸纳,将有利于获得公民的认同,从而获得普遍遵行。
第三,有利于法官直接援引,并且更能够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在我国,制定法占绝对主导地位,法官审理案件时当然首先要从制定法中寻找裁判依据。那么,合理吸纳了交易习惯的制定法,便有利于法官在审理相关案件时直接援引,省去了当事人对交易习惯的举证、法官对交易习惯的审查和认定等繁琐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通过这种做法,更能够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因为交易习惯是一种为交易各方所熟知的普遍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交易各方的共识。“许多通行习惯中关于利益分配、损害分担的种种规定,乃经过长时期利益冲突而逐步形成,因此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民众关于应然的某些共识。”[17]P57人们对于形成共识的东西更容易接受,因此,对合理吸纳了交易习惯的制定法也更能够接受。
当然,将合理、合法的交易习惯纳入到制定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是一项永远的工程。需要对各类交易习惯进行分类、筛选,剔除其“陋习”部分,吸收其合理、合法部分,经过严谨的立法程序,方可纳入到制定法中来。但立法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系统论述,其通过对2500件制定法进行检索、分析后得出了结论:中国当代的制定法,除了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和对外关系的问题上,一般是轻视习惯的。[14]当然,这一现象在近十几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根据有学者在2014年的研究,我国立法对于习惯尤其是民事习惯转变为更为尊重和认可的态度,开启了从“为立法而立法”到“为生活立法”的这一转变。即便如此,该学者仍然认为,在中国立法和法治建设中应当重视当代习惯的积极功能,在国家法律发展中广泛吸纳习惯的内容。[13]目前,民法典编纂的启动给习惯进入制定法提供了契机,所以,重提制定法对习惯的重视有重要意义。亦有学者对民法典编纂中启动民事习惯调查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认为,发现民事习惯这种客观事实、编纂民法典以及民事习惯司法适用等均需要民事习惯调查。而且从近代以来欧陆民法典制定历史来看,尊重民事习惯也是一项重要经验。并对民事习惯调查的方案设计给出了不错的建议。比如,在中央和地方设置民事习惯调查机构、制定调查规范和章程、遴选调查人员、确定调查内容、程序和期限等。[18]P52-54期待立法者能够对此类建议给予重视,使制定出来的民法典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更有利于促成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更能够得到普遍遵行。当然,即便这项工作得以开展,由于制定法总是落后于社会实践的特点,使得制定法无法穷尽各类合理、合法的交易习惯,也无法及时吸纳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而新形成的交易习惯,这就使得实践中法官对交易习惯的正确理解和运用显得尤为重要。
三、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
关于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适用交易习惯,已有学者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如学者认为,交易习惯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在当事人未能证明时,法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某种习惯来填补合同漏洞。如果双方当事人举证的交易习惯彼此矛盾,法官应考虑采用如下规则确定优先适用的交易习惯:如地区习惯与一般的习惯冲突,应以一般的习惯为准;如地区习惯与行业习惯冲突,应确定行业习惯优先;如地区习惯、行业习惯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冲突,应以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准。遵循的总思路为:在交易习惯彼此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最接近于当事人双方意志、最能够为当事人双方所理解和适用的交易习惯。[11]P426-428这些建议对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理解和适用交易习惯无疑使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实践中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交易习惯在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的适用中是否应予以区别的问题;一方认为是“交易习惯”,另一方则认为是“不公平条款”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遵循前述学者提出的适用规则的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根据合同种类确立有差异的交易习惯的适用原则,具体为:区分交易习惯在民事合同、商事合同①以及消费者合同中的适用,确立相适应的对待规则。
(一)交易习惯在民事合同中的适用
对于民事合同中的交易习惯,法官可以根据一般的社会知识、经验,根据一般人通常的理解来进行阐明和适用。事实上,有些法官在处理合同纠纷的时候,即运用了这种一般性来解释合同、处理纠纷。如在“丁昌学与熊合群民间借贷纠纷”②一案中,被告熊合群于2011年农历2月2日向原告丁昌学借款4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利息为1分,农历5月15日前还清。原告于2014年5月12日,以被告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还本付息。被告提出了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该抗辩意见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对借条中“农历5月15日前还清”的理解。“农历5月15日”是指哪年的5月15日呢?这是确定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关键所在。对此,法官在判决书中认定,依照交易习惯,还款日应视为2011年5月15日。又因为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故该抗辩意见成立。在这一案件中,法官对这种方式记载的还款期限,以交易习惯进行了认定:确定为出具借条的当年。这种释明和认定方式,即是依据一般性的理解来进行的。这种一般性的理解是社会成员一般性的共识,或者说是“理性人”的理解。此时甚至不必由主张适用交易习惯的一方来承担举证责任。
当然,对于较为复杂的案件(比如对交易习惯是否存在有争议),则需基于当事人的举证或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进行判断和适用。如原告甲某诉被告乙房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案。[19]该案中,被告交付的商品房未安装铝合金窗,原告认为按照交易习惯,被告交付的商品房应安装铝合金窗。但被告提出抗辩,认为对此双方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做约定,故其无此义务。本案的关键点在于:当地是否存在交付的商品房应安装铝合金窗这样一个交易习惯。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认可存在这一交易习惯,但认定过程太过简单,未论证其认定是基于原告的举证还是依职权调查,原告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该地存在这一交易习惯。二审判决否定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合同未做规定。在这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直接遵循一般性的理解做出认定较为困难,所以要在当事人的举证的基础上进行确认,根据《民事诉讼法》符合依职权调取证据情况的,可依职权调取证据。如果证明存在这一交易习惯,则应作为合同的默示条款,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如果证据不足以支持该交易习惯的存在,则应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无论是否存在这一交易习惯,均应给出充分的说明。
(二)交易习惯在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我国在学说上采“民商合一”观点,在立法上采“民商合一”体例,所以并不严格区分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但由于商事活动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商事合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相比还是有自身特点的,主要表现为:其一,相较于普通的民事主体,商事主体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而且缔约双方信息地位平等,一般不需要强制规定的介入保护;其二,因商业运作面对瞬息万变的大环境,合同的复杂度更髙,所以需考虑未来可能发生之风险而事先加以规划;其三,因为拥有更多工具可协助于事前评估风险、并在事后也更有承担风险的能力。[20]P80而一般的民事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未必占有充分的商业信息,也未必对收益和风险有较强的预测能力,对合同的条款也不一定进行细致的推敲,合同往往表现为一次性交易的特点。基于这样的差别,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中的交易习惯,在理解和适用上宜有所区别。
对于商事合同中的交易习惯,不妨采取充分尊重的原则。商事合同中的交易习惯往往体现为商业惯例(或称商事惯例),是在长期的商事交易活动中经过反复实践逐步形成的,多数符合交易规律。所以,在商事审判实践中充分运用交易习惯很有必要。如“康玉德与杜振霞、潍坊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买卖合同纠纷”③一案中,原告康玉德诉称,原、被告是水泥购销业务关系,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水泥款并收到了被告出具的收款条,原告向被告催要水泥和水泥款未果,故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水泥款以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逾期损失。被告对原告所持收款条没有异议,但辩称该收款条是原告收到水泥后偿付的货款。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收款条载明的水泥款的性质,究竟是原告所主张的预付款?还是被告所坚持的偿付款?对此,法院在判决中进行了认定:原被告作为商事交易的主体,其交易应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水泥服务公司(因水泥服务公司已被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其主办单位潍坊市散装水泥办公室承担,故案由中被告之一为潍坊市散装水泥办公室)收到原告的货款并向原告出具了收到条,根据交易方式相对等的商事惯例,被告在向原告交付水泥或出具水泥提单时,也应该要求原告出具相应的凭证,以达到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而本案被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故应当认定水泥服务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被告应当承担交货不能的违约责任。本案中,对于争议焦点法院即采用商事惯例进行了分析,此处商事惯例的内容为:商事主体双方在向对方履行义务时应获取对方出具的凭证,未获凭证将可能会被认为义务未履行。对于此惯例,从事商事交易的双方均应有足够的认知,毋需法院再进行过多地论证,予以充分地尊重即可。
同时,又因为商事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活动,其复杂性、专业性程度较高,在商事实践中形成的商业惯例也因此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仅凭法官一般性的理解尚不足以解决对商业习惯的运用问题,而且不能苛刻地要求法官熟谙各类商业惯例。此时,可由主张适用交易习惯的当事人举证,法官主要从程序上审查其在行业中是否存在,内容上审查其有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即可。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交易习惯彼此冲突,除了遵循适用最接近于当事人双方意志、最能够为当事人双方所理解和适用的交易习惯的理念外,在方法上,可以采取专家证人的方式。充分的专家证据以普通人能明白的方式把问题向裁判者深入浅出的解释清楚,有助于法官对交易习惯的理解、释明和运用,并进而做出令双方当事人信服的裁判。在美国,主张存在一种行业惯例的当事人负有证实其主张的举证责任。证明的方法通常是由熟悉特定行业的商业活动的专家出具证实这一行业内存在某种行业惯例的证明。[21]P201
(三)交易习惯在消费者合同中的适用
消费者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消费者、另一方当事人为经营者的合同,其与一般的民事合同、商事合同又有所区别,既要重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又要注意利益平衡。所以,在适用交易习惯尤其行业惯例的问题上,亦需更契合的对待规则。
在消费者合同中,对交易习惯的适用与否及理由应予以更加充分的释明。在消费者合同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消费者,在知识、经验等诸多方面均远逊于作为商人的经营者,双方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地位。当经营者主张适用交易习惯时,法官应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合同的这一特点。如“酒店业12:00退房”在酒店业看来,是一项国际惯例,是一种交易习惯,自然适用于交易双方。但在消费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看来,该条款属于“霸王条款”,对消费者不公平。中国消费者协会于2009年把挑战酒店业12:00退房行业习惯作为十大维权举措之一。酒店业中午12点退房行业习惯肇始于欧洲,后传到美洲、亚洲,成为酒店业的一项行业规范。我国的酒店业也采取了这一行业规范。酒店业和消费者之所以在这一行业规范产生争执,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对结算时间的理解上不一致。消费者通常是以入住酒店小时为其结算的时间,支付一天的房费意味着理应住24小时,这是消费者一般性的理解。而酒店业认为消费者入住的主要目的在于过夜,客人住一个“间/夜”计收一天房费。在首例“旅客状告宾馆结算时间案”④中,被告方即以12点退房为交易习惯进行了抗辩。从法院的判决来看,没有对该条款本身的合理与否进行释明,但从格式条款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认定,认为其不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故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旅客状告宾馆结算时间案”中,法官显然没有采取对“一天”的一般性理解,虽然也没有明确认同12点退房的交易习惯,但从判决结果看,还是间接认可了这种做法。该案件虽涉及到了消费者合同中交易习惯的认定与适用,但遗憾的是没有对是否认可交易习惯进行释明。笔者认为,在消费者合同中,如果法官对一方(尤其是经营者一方)主张的交易习惯进行了认可和适用,有必要对其合理性进行释明,这有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也有利于减少今后的类似诉讼。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同纠纷,有些是因为经营者的不法行为所致,有些是因为合同条款本身不公平所致,还有些是因为消费者对经营者相关行业规范的不了解或不理解所致。所以,如果在判决中对所认可的交易习惯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使消费者能够理解其合理性,那么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如果法官对一方(尤其是经营者一方)主张的交易习惯不予认可、不予采用,亦应说明原因。通过裁判文书对于不合理的交易习惯予以否定,既能够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又能促使经营者进行改进,提高其商品或服务质量。此外,法院还可以向经营者发出司法建议敦促其进行改进。在“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⑤中,受理本案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不但在判决中对机场只用专用代号标明的行业习惯不予认可,还且还向中国民航总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对同一城市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民用机场,航空公司及航空客运销售代理商填开机票标明出发地点、使用机场专用代号时,应使用我国通用文字附注或以其它适当方式说明,以保证客运合同的正确履行,提升我国民用航空行业良好的服务形象”。民航总局接受了这一司法建议,并进行了改进。所以,在消费者合同中,法官对于交易习惯是否认可及其理由应进行充分论证,这有利于做出让双方均信服的裁判。
总而言之,交易习惯作为一种事实习惯,有别于习惯法,其在民法上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立法者对此需加以更多地关注,使立法更贴近生活、更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更具有可实施性,从而更充分发挥鼓励交易、促进交易的作用,并能够得到普遍遵行。但由于制定法总是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原因,使司法者在实践中高度重视交易习惯成为必要。司法者宜根据民事合同、商事合同以及消费者合同的不同种类采用相适宜的运用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与一般的法律适用相比,交易习惯的适用需要更透彻、更周延的论证。笔者认为可以此为基础,探索建立交易习惯的案例指导制度,将实践中法官运用交易习惯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汇编,对以后的案件审理起到启发、指引作用。
注释:
①本文所称的商事合同,是指双方均为商事主体的合同,也即学说上的双方商事合同。
②参见“丁昌学与熊合群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content/content?DocID=af5951f3-0d7a-41d2-bb7e-a1c57e0e20dc.
③参见“康玉德与杜振霞、潍坊市散装水泥办公室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载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content/content?DocID=0dbbfc19-9117-4329-a7dc-428161a2d368.
④2008年3月17日16时, 王先生入住北京广安门宾馆。房价:148元/日。3月18日下午2点王先生退房时, 广安门宾馆依据双方的旅客服务合同的约定,要求加收其半日房费。王先生认为宾馆加收半日房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属于霸王规定, 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等价交换的原理, 故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要求宾馆退还多收的半日房费74元等诉讼请求。被告方在抗辩中即运用了交易习惯。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条、第25条、第26条、第40条、第44条、第60条第1款、第114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先生的诉讼请求。参见“首例旅客状告宾馆结算时间案”,http://tulawyer.findlaw.cn/lawyer/jdal/d3469.html.
⑤原告杨艳辉购买被告南航公司的上海至厦门九折机票一张。机票载明:出发地是上海PVG,杨艳辉到上海虹桥机场出示机票时,机场工作人员告知其应到上海浦东机场乘坐该航班。因已来不及赶赴浦东机场,造成误机和退票损失。故起诉要求退还票款、赔偿损失,并在机票上注明机场名称。被告南航公司辩称:按照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南航公司的机票都是使用自动打票机填开。自动打票机无法在机票上打印中文机场名称,故用机场代码PVG标明。南航公司已尽到自己的义务,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上海有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确实为上海公民皆知。但这两个机场的专用代号SHA、PVG,却并非上海公民均能通晓。作为承运人的被告南航公司,应当根据这一具体情况,在出售的机票上以我国通用文字清晰明白地标明机场名称,或以其他足以使旅客通晓的方式作出说明。参见“杨艳辉诉南方航空公司、民惠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http://www.110.com/panli/panli_61420.html.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合同法(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余延满.合同法原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罗筱琦,陈界融.交易习惯研究[J].法学家,2003,5.
[4]白晓东. 论交易习惯的功能与解释——“交易习惯”作为“情理”因素的解读[J].科技和产业,2011,11.
[5]林诚二.民法总则(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王云五.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7]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8]王利萍,郭平.国内商事审判中交易习惯的认定及适用[A].王保树.中国商法年刊[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9]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0]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1]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2]李绍章.商事合同视域下交易习惯的规范功能及其裁判技术[J].新疆社会科学,2012,2.
[13]高其才.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J].政法论丛,2014,2.
[14]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J].法学评论,2001,3.
[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8]陈寒非.民法典编纂中的民事习惯调查:历史、现实与方案[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3.
[19]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直面民俗习惯的司法之难[J].法律适用,2008,5.
[20]王文宇.商法新思维——商事合同、商事组织与商事交易的视角[A].王保树.中国商法年刊[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1]王军.美国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唐艳秋)
Several Thoughts About Transaction Habits
MiXin-li
(Law Schoo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Abstract】As the widely acknowledged and rapidly use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actions, transaction habits should be essentially regarded as de facto habits, which is currently playing an important and valuable role in civil law. The legislator is supposed to absorb and adopt legitimate and reasonable transaction habits in statute law, to make sure tha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transaction rules can be fully reflected in legislation, and also be generally followed. Bringing up absorbing transaction habits in statute law again is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our country has started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Law Code. It is necessary for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put emphasi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nsaction habits, and design suitable rules to sui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civil contracts, commercial contracts and consumer contracts respectively, thereby settling disputes effectively.
【Key words】transaction habits; legislative absorbability;judicial applicability
【中图分类号】DF52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米新丽(1969-),女,山东平邑人,法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民法总则重大疑难问题研究”(14JJD82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编号】1002—6274(2016)02—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