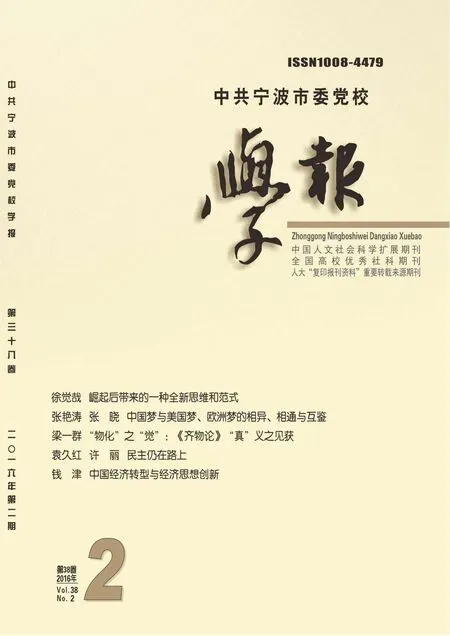非物质劳动及其解放潜能
2016-02-12吴宁王璐冯琼
吴宁王璐冯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非物质劳动及其解放潜能
吴宁王璐冯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马克思预见了作为生产要素的“一般智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构作用,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发掘了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力量,安德烈·高兹挖掘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一般智力;生态
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党建理论;
王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冯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马克思认为,当人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上得到充分保证时,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马克思从劳动出发论证人的解放,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了劳动解放的条件。在当代社会,信息革命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主体要素(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的智力因素相对于客体要素(生产资料)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人类的价值创造已由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转变为主要依靠脑力劳动,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得以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非物质劳动越来越重要,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被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所取代,物质劳动的价值贡献日益下降,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兴起,非物质劳动的比重越来越多。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试图在劳动领域之外探寻解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变化没有太多关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焦点重聚劳动领域,针对当代非物质劳动的兴起,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地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挖掘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对其解放潜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劳动中的“一般智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阐述了工业经济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劳动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增值活动,其主要形式是生产商品的物质劳动。尽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但也曾论及非物质劳动。马克思曾明确地把“服务”作为一个生产性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2](p149)他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2](p435)马克思在阐释“服务”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类非物质生产劳动:劳动过程中“一般智力”的应用和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服务”。在马克思看来,非物质劳动以“一般智力”应用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过程中,成为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生产形式。马克思不否认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但认为它“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2](p443)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物质生产劳动无疑是财富的直接源泉,而作为非物质劳动成果的“一般智力”是“由积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智力”[3](p343),是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并不轻视非物质劳动,但认为非物质劳动不能与物质劳动截然分开。他预言,随着“一般智力”逐渐融入机器化大生产中,自动化机器系统将取代活劳动成为生产的主体,脑力劳动将不断超越直接的体力劳动成为主要劳动形式,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下降,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显著提高。马克思指出,虽然“一般智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强制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成为可能,但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吸纳“一般智力”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一方面创造出愈来愈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又把这些自由时间变成剩余劳动的时间,促使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走向崩溃。[4]随着矛盾日益激化,工人自己占有剩余劳动的呼声日益高涨,突破资本逻辑的劳动才能获得自由,阶级革命是实现劳动解放的必经路径。
马克思通过“一般智力”发现了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预言“一般智力”会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时爆发出革命的能量。在物质劳动主导的机器化大生产中,“一般智力”对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潜能的激发作用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物质规定性与社会规定性的结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p207~208)也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6](p925)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始终建立在资本批判的基础上,“一般智力”由物质变换关系中的生产要素转化为资本中的要素,其解放潜能就在于促成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激发劳动者自我占有剩余价值的需要,在危机频发的背景下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劳动解放。随着机器化大生产一路高歌猛进,人类社会迅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被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所取代,物质、资本、传统劳动形式的价值贡献日益下降,知识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呼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归,非物质劳动所包含的人类解放潜能使之成为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旨归。
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非物质形态;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生产非物质产品;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在生产场所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经打破了生活与生产的界限,延伸到整个社会中并成为人类生命的全部。[7]
二、非物质劳动中的“集体生命”
“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概念是意大利左翼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多在马克思阐述的“一般智力”的启发下提出的。拉扎拉多认为非物质劳动是当代的主要劳动形式,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拉扎拉多指称的非物质劳动是在后工业时代不仅生产非物质商品也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的劳动,而马克思指称的非物质生产劳动(nonphysical productive labor)主要是在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领域中非物质要素的应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帝国》的合著者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劳动物化于商品中,其解放潜能日益消逝,而非物质劳动蕴含解放的潜能。在他们看来,非物质劳动是知识的生产、信息的传播、符号的解释、情感的交流等活动,是创造非物质性产品如知识、信息、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3](p279)哈特和奈格里在《大众》中将非物质劳动概括为两类:第一类非物质劳动是生产象征、符号、语言、文本或观念等非物质商品的劳动,通常凭借有形的物质载体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第二类非物质劳动是涉及感情的劳动,是激发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潜能的劳动,有促使劳动者合作的内在动力,孕育出各种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中的合作不像以前的劳动是由外界强加或组织的,而是内在于劳动自身的。[3](p279)在他们看来,随着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信息时代,在工业社会中仅发挥过渡与辅助作用的非物质劳动逐渐凸显,比重日益增加的非物质资本并没能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安然渡过了各类危机,并实现了资本的全球扩张。以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具有以下特征:首先,非物质劳动融合了生产与生活。与物质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生产的是诸如知识、观念、形象、情感、社会关系等,因而劳动者与其成果不容易分离开来,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步进行,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侵占了劳动者的私人生活时间。随着劳动时间的变化,劳动地点也延伸至私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在非物质劳动中无法区分导致非物质劳动成果的价值无法依据劳动时间来计量。其次,非物质劳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非物质劳动表现为再生产主体的过程,人在生产的同时也被生产出来。非物质劳动的人是各种生产和操作中的能动主体,而不是服从简单指令的奴隶。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提升人的主体性,是主体人的生命确证,能扩展劳动者的知识、丰富其情感、全面发展其能力并通过合作丰富人与人的关系。最后,非物质劳动是蕴含合作关系的劳动。工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合作是资本组织规划的结果,其目的是资本增值,是一种外在强制。非物质劳动中的合作不依赖于资本,而是由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觉生成的。非物质劳动包含主体间互动的情感劳动,“感情的劳动所产生的是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物能量”[3](p279),在提升主体性的同时开启了新的合作关系。非物质劳动要求集体合作与协作,要求人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是工作团队的积极参与者。“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合作关系的生产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8](p147),这种内在于劳动的合作孕育一种集体生命。
哈特与奈格里试图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上重构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理论。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的价值不取决于劳动时间而是直接由主体力量显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在生产商品的同时也生产了社会关系,人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于人的结果;虽然非物质劳动并没能在数量上压倒物质劳动,但其领导地位已日益显现。不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生产的信息化、智能化与合作化程度越来越高。哈特和奈格里没有将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所指的物质生产劳动区别开来,强调劳动的非物质特性主要是就产品而言的,意识到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非物质产品而且生产社会关系甚至社会生活本身。[8](p109)哈特与奈格里宣称了非物质劳动的领导地位,认为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非物质劳动深入所有生产部门、使得所有劳动者都受到资本的剥削。非物质劳动还渗透到劳动者的私人生活中,使得资本剥削无处不在。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有限约束,非物质劳动的普遍化导致资本对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在全球的普遍展开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和一种全新的革命力量——多众,它们作为世界新秩序的两极呈现出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一方面,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促成了资本形式的多样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非物质资本的“去中心化”①特征使得资本的扩张演化为资本之间的权力博弈,全球化使得资本剥削由国内转向全球,发展壮大的全球资本建构了帝国(Empire)。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主宰这个帝国,帝国是权力博弈的产物。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促使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孕育出新的对抗主体即多众(Multitude)。哈特与奈格里依据非物质劳动重新界定阶级,“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3](p58)资本已经渗透到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资本剥削范围的扩大和力度的加重必将激起更强大的反抗,工人阶级扩展成为多众。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拓展到包括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作与沟通以及劳动外的情感交流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生产出广泛的、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多众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多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8](p14)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蕴含着的巨大能量通过内在于非物质劳动的合作迸发出来,“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似乎为一种自发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3](p280)非物质劳动带来的劳动过程的均质化使得生产的公共性明显提高。非物质劳动生产的观念、意识、情感和社会关系都具有公共性,能生产出更多的“共同点”(诸如公共知识和集体生命),这些“共同点”具有解构私有制的能量,使多众摆脱资本控制成为可能。随着“共同点”的扩展和帝国的不断强大,多众也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所有的差异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表达”。[8](p14)多众成为建构全球民主的主体,是生成于帝国中的革命力量,抵抗帝国生命权力的扩张成为多众的主要任务。非物质劳动建构了新型的革命主体,使多众的民主自治成为可能,多众民主革命成为非物质劳动条件下人类解放的最佳途径。哈特与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解放寄托于民主自治的设想,哈特与奈格里建立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上的解放理论完成了革命主体的建构,重新论述了当代世界秩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他们指出,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日益彰显,劳动与资本日益分离。他们分析了劳动与资本分离后的资本统治逻辑,认为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剥削对象发生了变化,由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转向获取劳动力的价值。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型,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化为全球化背景下帝国与多众的对抗。
在我们看来,哈特与奈格里试图将工人阶级扩大为逐渐脱离资本统治的自治主体——多众,形成与帝国的直接对抗力量,在帝国与多众的二元对立中上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使自己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的另一版本。但是,非物质劳动并没能将劳动者从资本统治的牢笼中真正解放出来,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仍牢牢掌控着劳动者,资本剥削无处不在;多众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并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自治主体。哈特与奈格里倡导的多众民主自治只是资本主义民主体系中资本统治形式的变种。他们虽然也提到多众革命的具体策略,却将之集中于全球公民权、最低收入限制和对新的生产工具的重新配置(如得到和控制教育、信息与交流的资源的权利)这三项无法兑现的全球权利上。他们粉饰非物质劳动中的内在协作与集体生命营建的公共性,却不重视劳动者主体性的提升,主体的不成熟使其多众革命陷入困境。
三、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
虽然哈特与奈格里在非物质劳动中建构革命主体的理想最终落空,但并没有泯灭人们对非物质劳动解放潜能的憧憬。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对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义及其解放潜能做了有益的探讨,是对哈特和奈格里相关研究的逻辑推进。高兹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必将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度,最终因资源耗尽和环境破坏而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对人和自然实行双重剥削。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建立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只有深入挖掘非物质劳动中的生态意蕴,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彻底解放。
高兹关注知识经济中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随着知识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力,物质劳动逐渐降到产品生产过程的边缘或成为简单的产品外部包装”[9](p9),物质劳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的次要环节,“价值创造的核心是非物质劳动”[9] (p9)。“从亚当·斯密那时起就被视为价值源泉的简单抽象劳动向复杂劳动转变;可以有每单位时间的单位产量衡量的物质生劳动向无法用古典的标准衡量的所谓的非物质劳动的转变。”[9](p1~2)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在高兹那里就是精神劳动,它包括智力、想象、交往、感情交流等等。他认为,非物质劳动的一系列特征使主要包含个人精神的人力资本难以测量和量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真正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依赖于劳动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力,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劳动者的适应性、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导致“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想法不再适用”[9](p8),在“工作就是生产自身”的情况下劳动不能被预先的预定和严格地控制。在高兹看来,知识经济代表资本主义及其测量和交换体系、平等关系和增值过程的根本危机。高兹认为,一方面,“劳动评价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价值评价的危机”[9](p36),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在不可对价值进行定量分析的非物质劳动中无法体现。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激发了劳动者提升自身品质与技能的需要,非物质劳动主要依靠的不是共享的正式知识而是个体的经验知识,非物质劳动是主体的自我生产活动,“主体与公司、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区别必须被消除。”[9](p19)劳动者必须成为自己的企业家,即成为知本家,知识资本创造出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技术精英。
高兹认为,工业经济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逐渐泯灭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非物质劳动把劳动者的能力、个人性情同自由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等同起来,孕育出以自主权利为目的的个体意识而不是被资本引导的无限膨胀的物质需求。高兹指出,“未来是属于自主创业者的”[9] (p21),“随着自主创业的逐步确立,所有人及其生活的全部最终都会被工作占据和被剥削。”[9](p22)如果劳动者“拒绝资本为自身目的去占用和使用他们”[9](p29),知本主义就会朝向相反的发展方向。高兹主张,实现普遍的自主创业必须取消付薪就业,提升劳动者自主创业的意识和能力,“每个人都必须在弹性工作中负责健康、流动性和工作能力,确保知识更新。终生必须以管理好自己的人力资本为己任,以培训的方式不断增加投入。”[9](p20)“发展中的‘后雇佣社会’的基本构想是:没有付薪就业也没有失业。如果仍然有人失业,仅仅标志着他们的‘就业能力不足’。”[9](p25)只有普遍实现自主创业,才能使知识技术作为生产力节约出来的直接劳动时间成为真正的自由时间,使不能用利益衡量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发展成为可能。非物质劳动中的知识资本不再专属于少数人,而是由每个个体的自我生产创造并集合为人类的共享成果。
高兹认为,非物质劳动打破了传统的劳动-闲暇的二分,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逐渐融合,个人劳动的直接社会化使劳动不再缺乏自由而成为寻获意义、追寻幸福的源泉。高兹指出,非物质劳动使劳动成为人的内在需要,并能以“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将经济理性整合于生态理性中,解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高兹从非物质劳动出发论证“更少但更好”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根本路径。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体不再是与资本相对的无产阶级,而是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新工人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新工人阶级采取“控制公共领域”的非暴力方式,通过否定和超越“交换”来改良资本主义,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10]高兹认为新工人阶级的自治联盟是一种学习型组织,对这种组织而言,“有关集体生活的宪法、法律与原则将被设计为能使每个公民通过实践来学习,并使社会在不断改善‘国民幸福指数’的分布上便于操作”。[9](p109)在高兹看来,非物质劳动不仅孕育了主体而且开辟了解放的道路,为生态理性约束经济理性提供了可能。但是高兹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并没有溢出资本的逻辑,而试图以非物质劳动同化资本与劳动,将与资本对立的工人阶级打造为自己的“知本家”,形成一个普遍自主创业的太平盛世。高兹指出,“这至少是未来工作的新自由主义的愿景:废除付薪就业、普遍自主创业、整个人类和生活都被资本吸纳,每个人都完全认同这些。”[9](p29)他试图将资本掩饰为一种自发的伦理合作,没有意识到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以解决,这种改良主义思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命运,工人自治不可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
四、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
不论是马克思对未来的预见还是哈特、奈格里和高兹对现实的感悟,都凸显了知识、技术、情感、人际等非物质要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成熟的非物质劳动,马克思只能在分析这些非物质生产资料(特别是“一般智力”)的基础上预见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存在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虽然具有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能,但作为生产资料的“一般智力”只能通过机器对劳动者发挥作用,掌控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通过这个中介将节约出来的直接劳动时间据为己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一般智力”不可能冲破资本的逻辑、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哈特与奈格里则立足于资本逻辑之外寻获非物质劳动的解放潜能,认为非物质劳动孕育出的“集体生命”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但他们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没有真正跳出资本的逻辑,资本在非物质劳动中扩张,以垄断方式占有非物质劳动的成果,通过这种占有将剥削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甚至教育这一提升主体素质的领域,“集体生命”只存在于乌托邦中。高兹挖掘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蕴,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思考资本与非物质劳动的对立和非物质劳动者成为自己的资本家等问题。资本主义体制不可能培育劳动者的主体性,资本家也不可能让渡出操控资本的权力。高兹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个人多样化能力的付出,体现了劳动者的个性,打上了个人的智力和情感的烙印。“非物质劳动不是主要依赖于劳动者所用的‘形式知识’。非劳动者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是依赖无法被教授的表达和协调合作的能力,依靠的是利用作为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的那些知识的能力。”[9](p9)这样的劳动就是自我的生产,这种生产不能被形式化也不能被否定。非物质劳动是指以劳动者的脑力消耗为主,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强调劳动者的创造性、知识的应用性、劳动者之间的协作性,以知识、文化、服务和社会关系为成果的劳动形式,主要包括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情感劳动和服务劳动。非物质劳动开拓了劳动领域,拓展了人类交往范围,导致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发生巨大变革,导致个人增进自由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奴役,带给落后国家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其解放潜能不容忽视。
非物质劳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由于时代所限,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价值,区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
源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随着劳动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价值理论,以把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推到剥削机制的核心。”[3](p29)一些学者认为,知识、信息和智力劳动已经成为生产领域价值和利益的主要来源,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已不现实,劳动不再是预先设定的规范和标准可以衡量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其实,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丰富了劳动价值论的内涵。第一,非物质劳动证实了马克思对“服务劳动等非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预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对象化过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12],包括体力和脑力的耗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包括精神生产领域里的劳动,是基于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抽象,并被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所证实是一个科学的概念。[13]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创造出特殊的使用价值并以人们可感知的形式进入交换领域,成为价值的源泉。第二,非物质劳动丰富和发展了价值的评定标准。高兹认为,知识经济使得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社会劳动的产品是知识的凝聚,产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蕴含的知识、信息的量,非物质产品的价值无法按劳动时间准确估量。虽然以非物质产品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对价值的定量分析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由凝结在产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的价值并不受定量分析的影响,仍然表现为劳动力的消耗。非物质劳动凸显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价值创造,脑力劳动的消耗并非仅物化在机器和产品中、随着劳动时间的流逝而减损,而是对象化于人自身,随着劳动者能动性和创新程度的提升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量。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真正财富的创造对劳动时间和劳动份额的依赖变少,而对劳动时间内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依赖程度变大——这种高效的能力跟花费的劳动时间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取决于科学的整体水平和技术的进步,也就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在这种演变中,生产和财富的最主要的支柱既非劳动者的直接劳动,也非他的劳动时间,而是他自己整体生产力的获得、他的理解力和他作为社会的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一句话,是社会个体的发展程度。自此,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并且交换价值也不再是衡量剩余价值的尺度。”[14]脑力劳动的特点决定了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者的能动性和创新程度。第三,非物质劳动拓宽了价值创造的领域、丰富了价值的内涵。马克思在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中定义了商品的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随着非物质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地位的日益提升,劳动已经突破经济关系的范围进入其他社会关系中,人时刻都在劳动中。非物质劳动在创造出交换价值的同时,也创造出象征价值、美学价值等非物质价值,以人的发展为直接目的的非物质劳动相对于物质劳动具有更大的价值拓展空间,逐渐成为新时代价值创造的中心。第四,非物质劳动预演了未来人类自由劳动的价值创造图景。马克思指出,“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15]非物质劳动创造了实现人类自由的活动领域,在那里个人可以与他人可以实现完满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共享途径的增多,更多的非物质产品以便利的、免费的方式被大众获得并消费。非物质产品具有非消耗性和非稀缺性,产品应用的次数越多、范围越广,价值就越高,这使得产品的价值不需要在交换中确定而直接以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评定。非物质劳动以直接社会化的成果预演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对非物质劳动的价值评定将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奠定基础。
非物质劳动将一部分资本变为社会共享的财产,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基础。非物质劳动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共享性并通过消费而不断增殖的特征,直接与私有财产对抗。随着非物质劳动与公共财产趋向于重叠,私有财产的概念日益变得荒谬,私有化的基础被解体,“公共财产乃是大众的化身、生产和解放,善即公共的所有”。[3](p287)非物质劳动打通了生产与生活的界限,以直接社会化的成果营建了更多的人类共享空间,更多人在资本的逻辑之外、从非物质劳动中获得自由。虽然资本仍通过垄断方式占有非物质产品或切断非物质生产过程,但并不能遏制非物质劳动创造社会共享的无限潜能。一方面,非物质劳动创造出大量的共享知识,为推动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和公共知识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非物质劳动蕴含人类新的相互关系和主体自由的积极条件,使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渗入交往领域和主体生产领域,变为一种由主体能力决定的掌握、处理信息的劳动,通过提高与丰富劳动者的知识、能力及情感来生产主体自身。知识经济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表现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发了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劳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不可能被资本完全掌控,非物质劳动营建的共享空间不会被资本操控而成为革命的前沿阵地。非物质劳动以内生的合作营造了社会生活的公共性,情感劳动将激发这种自发的合作中的自觉意识、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的人际关系和更多地参与决策、自我实现以及宽容、友爱、温柔的情感等将成为非物质劳动的价值旨归。非物质劳动将促使这种“潜在的、自发的和基本的共产主义”[16]变成现实。
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大规模扩张带来的恶果,生态危机的解决有赖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渐意识到以文化、精神因素为价值依归重新安排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非物质劳动的发展正好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充盈人的观念世界,使物质需求合理化,把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导向精神超越和境界提升的方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形式的转型使得自由时间增多,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解决与幸福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态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幸福时,生态文明才能实现。非物质产品的非消耗性使得非物质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可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发展非物质经济必须要有生态思想的指导,只有当人们有了生态意识时,才能实现生产与生态的双赢。
非物质劳动将以物质劳动为依托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非物质劳动并不排斥物质劳动,而是与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非物质劳动往往要回归物质,其产品往往要以物质为载体,劳动的能量也源于物质的生命构造——人们的身体和头脑。物质劳动中有非物质的因素,“所有的物质劳动都有非物质劳动的一面,因为物质劳动不仅改造了直接作用的物质对象,也改造了主体和社会关系。在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之间不存在清晰的差别”。[17]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不仅不会取代物质劳动,反而会促进物质劳动的发展。劳动不限于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也是劳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都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全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充分涌流,也才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8]。
非物质劳动虽然开辟了劳动解放理论的新视野,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质,而且使资本以榨取劳动时间以外的生活时间的方式更全面地剥削了劳动者。人类要想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单凭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能实现自由或劳动解放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劳动的转型只是资本统治形式的变换。非物质劳动及其解放潜能的当代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注释]
①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网状社会关系形态。哈特与奈格里认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知识、信息等非物质资本具有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更有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成就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和去领土化的统治机器——帝国,促使帝国在开放的、不断扩张的边界内整合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唐正东.“一般智力”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的解读视角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7~208.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孙乐强.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与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3).
[8]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M].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9] André Gorz, The Immaterial: Knowledge, Value, Capital [M]. London: Seagull Press, 2010.
[9]André Gorz, The Immaterial: Knowledge, Value, Capital [M]. London: Seagull Press, 2010.
[9]André Gorz,The Immaterial: Knowledge, Value, Capital [M]. London: Seagull Press, 2010.
[10]吴宁.高兹的生态政治学[J].国外社会科学,2007,(2).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
[13]程恩富、顾钰民.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价值理论的当代拓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1,(11).
[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2~193.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26~927.
[16]Alberto Toscano, From Pin Factories to Gold Farmer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Stream on Cognitive Capitalism, Immaterial Labor, and the General Intelle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2007).
[17]Sean Sayers, The Concept of Labor: Marx and His Critics, Science & Society, Vol.71(2007).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责任编辑:刘华安
[作者简介]吴宁(1966-),女,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项目(批号2015JJ01)的阶段性成果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资助项目(31541111812);湖北省教育厅高校专项科研资助项目(325121180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11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2-00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