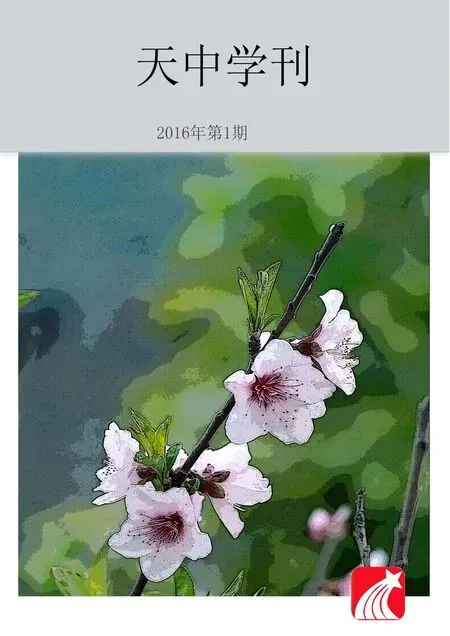小说史的叙述体例、理论命题及研究视角——刘勇强教授小说史研究方法评介
2016-02-12蓝勇辉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蓝勇辉(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小说史的叙述体例、理论命题及研究视角——刘勇强教授小说史研究方法评介
蓝勇辉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刘勇强在小说史研究上有精当的见解与较大的突破,总结来说,主要有几个特色:第一是将小说家作为探究小说史演变的内容,采用“一书兼二体”的小说史叙述体例;第二是从小说文本及小说史的角度归纳总结出一系列理论命题;第三是运用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及超拔的鉴赏构建个性化的小说史。
关键词:刘勇强;小说史;叙述体例;理论命题;研究视角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小说史叙论》《西游记论要》《幻想的魅力》《中国神话与小说》等著作以及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的学术文章上。《中国小说史叙论》是刘勇强小说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主要以此书为对象,旁及历年来他在刊物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综合介绍其学术研究的贡献与特色所在。
一、从心理状态观照小说与独特的叙述体例
小说史的撰写,自20世纪以来,业已历经百年。其中小说史著作层出不穷,要想在其中脱颖而出殊非易事。30年以来影响较大的几部小说史,往往在叙述体例上有所突破。如齐裕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引入类型学,“从体例上突破了《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却又未背离撰写一般通史的原则”[1]1;颇受好评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则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体例,建构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型”[2]序言。然而,《明代小说史》在叙述体例上的新创也带来了相应的缺点,“由于作者淡化了具体文本在小说史中的呈现,小说史一定程度上成了小说出版的历史,而文体由于没有更多地与具体小说文本相联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史的价值”[3]。《中国小说史叙论》(以下简称《叙论》)是刘勇强小说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所采取的叙述体例卓尔不群,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一书兼二体”,且动态地把握小说文体演变与文本的内在关系,从而构建了独特的小说史叙述体例。中国古代小说从萌蘖、发展、衰退、消亡以及过渡到近现代小说,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而研究者要想抽绎出契合古代小说发展的叙述体例殊非易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以作家作品式为代表的叙述体例,其后学界形成了注重小说“外部研究”的写作格局。当然,也有着眼于小说“内部研究”的小说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与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4]265。小说史的叙述体例,自可不拘一格,如古人所说的因事立篇,文无定法。事实上,任何一种叙述体例自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哪一种更切中古代小说发展规律之肯綮。《叙论》采用“一书兼二体”,最大化地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平衡。《叙论》认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民间与文人的合作、语言的演变及相关文学要素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小说发展的四大主要动力,这四者在明中叶前后促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全面繁荣,并成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因此,它将小说史分为两个大的段落,“上编‘从肇始到成熟:两种体式及其演进’,着眼于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从时间上说,大致从汉魏到明初。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不同体式,基本上都已形成。这意味着小说在题材、叙述方式、艺术功能等几个方面,都在长时间的演变中,逐步形成了与其他文体或艺术门类不同的目的与表现特点。下编‘文人独立创作普遍时代的小说世界’突出了小说文体成熟后,以小说家为中心的小说创作特点”[5]16。如前所述,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以文体为中心,着重条分缕析了古典小说在文体上独立的过程。稍稍可以补充的是,囿于篇幅及论述重点,董著主要论述对象为宋前文言小说的文体演变,而对于唐后的小说文体特别是白话小说的演变情况涉及较少。而《叙论》则文言与白话兼论,从题材、语言、叙事、艺术、体制等文体构成要素,全面地透视古代小说文体的肇始与成熟过程,并将成熟时间定位在明中叶,这就在时哲前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了小说史的文体研究。
然而,小说文体成熟后的古典小说创作特色及发展动力业已发生重大变化。与传统诗文有所不同,小说的创作主体变化较大,这在明中叶以后的通俗小说创作上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综观早期文言小说,其创作者大都是上层文士。而宋代的白话小说创作者大都为民间艺人,他们的小说创作特色从题材、艺术、思想等已迥异于唐代作者。即便经过文人再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金瓶梅》,仍残存着早期说书艺术的痕迹。不过,随着创作主体的变化,明中叶后的小说创作呈现了全新的风貌,而以明末清初为最。有人以为这是时代环境、朝代更迭的结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固然不错,然而试想一下,哪一种社会意识,譬如道德、哲学、宗教不受时代与朝代更迭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社会的政治、哲学、道德、经济等大的宏观条件影响特定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大背景又影响到作家的心理,从而形成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是作家心理的直接反映。小说亦如此,明末至清代中叶,小说创作与小说家之心理特征的关系日益密切。钱钟书曾说:“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此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6]99这也是说,政治与社会、哲学、文学是平行的,它们“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6]100。其实哲人加赛德也曾说:“一个时代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ideology),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6]281因此,与其从政治、经济、社会中把握小说的发展,倒不如从小说家的心理状态把握时代的脉搏。笔者以为,这正是刘勇强《叙论》下编中十分突出的特点,将文人的思想与心灵作为观照小说创作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小说史撰写上的一大点睛之笔。
小说史介绍小说家的生平经历是必要的,所谓知人方能论世。但是如果能将小说家的生平经历与文本勾连起来,这种介绍才不会与文本欣赏相疏离。一般的小说史囿于篇幅,往往未能体察小说家的精神世界,遑论将小说家视为小说发展的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叙论》表现出不同流俗的眼光,它将文人小说家的精神品格、心灵历程、创作心态与小说文本紧密结合,并提炼为重要的叙述内容。观念一变天地宽,在书中,随处可见这类精彩纷呈的论述。如下编第五章,《叙论》从时代的共性与作家的个性指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固然与其家境败落的特殊经历有关,但从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上看,与清代作家自我意识在叙事文学中的新体现关系密切,《叙论》列举了李渔、吴敬梓、夏敬渠等小说家的这种特性。难能可贵的是,《叙论》并未止步于从同时代的小说阐述曹雪芹将自我形象融入《红楼梦》的特性,而是从更广阔的文化血脉与文学土壤,指出曹雪芹创作中流露出怀旧气质与追忆闺阁女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叙论》认为:“对往事的回忆使《红楼梦》拥有了一种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起点……曹雪芹对过去的记忆与其说是对自己家族辉煌历史的怀恋,不如说是对一种生命体验的追索。”[5]427
那么,小说家心灵世界的变化与小说创作有何关联呢?如果说,从列鼎而食而变成食粥赊酒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成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理由的话,那么箪瓢屡空的困顿则成为明中叶后许多寒儒创作小说的动机。《叙论》指出作者的心态变化是小说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明中叶后小说创作素材与小说家的生平经历与情感世界的前所未有的联系”[5]264,这也可以解释抒愤、逞才与自怜等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何屡屡见诸小说家的笔端。《叙论》说:“对明清小说家来说,娱乐则不仅是小说取悦听众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他们自我遣兴逞才的方式。说到底,他们从事小说创作是在失去了诗文经典写作和淡化了史的意识后的一种良心游戏。”[5]267对小说家心态与小说创作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洞见,使《叙论》在相关问题上能超越前人。勃兰兑斯说得好:“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2小说家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气质、遭遇、思想、心灵等因素往往在小说作品中有深刻的投影,无疑启示研究者:小说创作及发展,与小说家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
《叙论》正是秉承探讨作家心灵与作品关系的理念,因而能得出令人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结论。在下编的第三章,《叙论》着眼于文人精神与世俗载体的矛盾,从二者的互动中重新评价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的价值及消亡的历史原因。在小说史上,甚至小说断代史里,历来轻视甚至抹杀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价值。有鉴于此,《叙论》指出,清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精神上更多地向文人的思想、情趣靠拢,应从短篇白话小说自身的创作特点出发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叙论》自始至终围绕着世俗文化与文人精神的双向互动,从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编撰与传播的方式、散发出的新的思想意识、文体的新变及局限等方面重新评价了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在小说史上,每个时期推动小说发展的各种动力是不平衡的,而研究者往往对这种不平衡习焉不察或失于揭橥,明代是其中最突出的转折点。明中叶后,最重要的动力便是小说创作主体从说书人向文人的转变,是文人的参与使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叙论》敏锐地捕捉文人参与对小说发展的关键作用。因而在下编里,将更多篇幅留给了文人小说家。
然而,古代小说的演变发展,无不是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结果。既受文人思想、其他文学体裁、小说体制等的影响,也受政治的、哲学的、经济的等综合因素的掣肘,这对研究造成了挑战。但《叙论》驾轻就熟,并未孤立地阐发文人参与对于小说发展的作用,而是同时将小说的发展规律与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统治者政策、文体特点等关联起来,因而避免了偏照一隅而可能导致谨毛失貌的缺陷。
刘勇强《叙论》所创建的“一书兼二体”的叙述体例,内容并非前后脱节。事实上,《叙论》以明中叶为界限,分上下两编,二者内容如草蛇灰线,左右映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二、从小说现象着眼和高屋建瓴的理论命题
刘勇强注重从文本的各种蛛丝马迹中去总结小说史现象,从相类的情节、故事、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其所归纳出的相关理论命题,大都见微知著,高屋建瓴。例如他提出的从传统文化归纳的“超情节人物”“西湖小说”“万里寻亲型”“水贼占妻型”“美人黄土的哀思”“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等理论,对于研究者诠释小说史现象、发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均大有裨益。这些针对古典小说现象的命题,具有鲜明的学术品格。例如他提出“超情节人物”概念:“明清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一些僧、道、术士的形象,常常超越于基本情节之上,以简约的形式、近乎雷同地出现于不同的小说中……他们并不是完全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甚至引导了这一(指故事)结局的出现。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不是作为情节冲突的一方介入其中;如果他们制约或引导了情节发展的走向,那也是作为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存在的……超情节人物通常是一种‘定型人物’,它反映的是人们对某一群体或类型的人的基本看法,是在部分的基础上对全体进行的概括。”[8]
中国古代人物谱系中,一僧一道一术士的身份很特殊,与历史及传统文化密切关联,从根本上说,可视为宗教世俗化在小说中的生动注脚。这一点与西方小说理论中的人物差异很大,如果套用叙事学理论命题,便削足适履,隔靴搔痒。众所周知,佛道二教在明清时期的教理已无多少创获,而其古奥深邃的理论逐渐衰微。为了扩大生存空间,努力吸引下层民众支持,二者均踏上世俗化之旅。正如陈洪指出的:“佛教各宗派都向最近世俗的净土宗靠拢,道教则背离了全真保和、清心寡欲的原旨,而完全倒向了画符禁咒、斋醮祈祷的一面。世俗化虽使二教苟延一时,却极大地降低了威信。”[9]288于是乎,本庄严肃穆的宗教,渐渐降低姿态,以迎合世俗。僧道术士穿闺入户,游荡市井,乃至混迹青楼。他们诵经修行、参禅打坐的神圣色彩业已褪色,转而热衷于算卦堪舆、打醮消灾等民间迷信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文人嘲讽与抨击,投射在古代小说中,他们大都以猥琐邋遢、好色狡诈、道德败坏的面目出现。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指出:“这种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中的对和尚、尼姑的轻视,不是出自对宗教的不敬,而是出自一种势利之心……他们因为社会地位低微,自然会受到猜疑。”[10]186不过,这类人物在小说中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士人为了迎合市民对僧道的印象设计的,正如刘勇强说的,这代表了一类人对他们的看法。而明清僧、道、术在古代小说中大量出现,总结一僧一道一术士具有典范性意义的“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功能与意义,无疑给我们很多启示。他指出:“从明清小说的超情节人物来看,他们既不同于叙述者,因而不直接承担叙述任务;又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行为者),因而也不直接参与行动。然而他们可以规定叙述、引导行动,并由此起到某种聚焦的作用……虽然僧、道、术士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的背景,但作为超情节人物形象,他们又是小说家的一种叙事手段,这种手段能以显豁的方式揭示出小说的基本命意和作者的态度;同时,也能以简捷的方式增强情节的张力、突出人物的品性。”[8]
这就鞭辟入里地从共性与个性的角度,肯定了这类人物认识在理解小说主题、情节、叙事等方面的作用。古代小说人物谱系庞大,三教九流,帝王将相、医卜星相、贩夫走卒等星云密布,“超情节人物”为研究者打开认识古代小说人物特殊性的一扇窗口,无疑具有很强的研究示范意义。譬如,笔者也曾注意到明清小说“一渔一樵”联袂出现的情况,追流溯源,他们与古代的隐逸文化密不可分,容当拟文讨论。
刘勇强所建构的理论命题,十分注重小说的细节印证,并从相类的细节中总结归纳出小说的艺术。他曾说:“我一直以为,只有悉心勾勒古代小说艺术创造中的这些细节,才能产生出与中国古代小说实际符合的理论命题,也才能为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叙事学提供必要的基础。”[8]在《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中,刘勇强指出:“场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或结构上的要素,它是地域文化在小说叙述中的一个凝结。近十几年,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运用得较为普遍,由于其基本术语都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而过于形式化的思路,也阉割了小说的丰富性,不足以揭示小说叙述的真正成就。西湖作为小说场景的广泛出现,也许给我们又一个启发,即我们可以从古代小说中提炼相关的命题,使之与形象构成、情节类型等研究相呼应,探讨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点及其理论表述。”[11]近年来,小说与地域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大热点,此文不无肇始之功。事实上,西湖小说的艺术成就很有限,其意义更多的如此文所说:“西湖小说在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性不只在于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如何深广、艺术水平如何的精湛……最值得重视的也许是,为什么杭州和西湖能造就如此广泛的创作群?而这些作品又以怎样的姿态折射出小说家们对区域文化以及特定城市生活的体认?”[11]
姑且不论其结论是否成立,这篇文章拨云见日,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会给研究者这样一些启示:如何认识西湖小说的文本价值、小说史规律及文化意义,西湖小说折射出文人何种创作心理,西湖小说所蕴含的叙事意义又是什么,等等。
如果说从小说创作中提升出理论命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古典小说的叙事学成就的话,那么从传统文化血脉中寻找诠释小说的理论命题也是破除陈腐之见的有效途径。刘勇强《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文化底蕴与文学传统》是近几年来诠释《红楼梦》主题的力作。曹雪芹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其血液里流淌,投射到小说作品里,则有待研究者破译人物及情节所携带的遗传基因。就小说部分情节的渊源而言,诸多研究者已撰文指出。笔者以为,最难破译的是作者在众多女性性格及命运设定上所蕴含的、难以言诠的哲思。刘勇强指出:“曹雪芹在追忆往事(闺阁女子)的愧悔中,书写着对女性的纯美想象,成为展开心路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感情基础。”[12]688而孳乳小说这一层情思,其渊源有自,那便是“美人黄土”这一诗词意象。文章缕述了两汉至清代诗词等作品中这一意象在语汇、意蕴、情感上与《红楼梦》的逻辑联系,不容置辩地说明,《红楼梦》的“美人黄土”意象与文学传统的血脉之亲,而总结为:“《红楼梦》的‘美人黄土’意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哀艳的悲伤情绪,或者说是一种创作的心理动机,而不是正面描写。但它浸淫于全书中,弥漫于情节里,因此对小说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12]704这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题无疑大有裨益。
三、独特的研究视角与个性化的小说史
刘勇强在小说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极大地受益于其超拔的小说鉴赏与诠释能力,不拾余唾的追求使其研究表现出极强的个性化特色。他在《叙论》中说:“小说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大家和名著不断发现与诠释,对小说史现象进行的分析、归纳与描述。”[5]580因此,他的小说史研究,既不“消解大家”,也不“悬置名著”,不仅对《红楼梦》等名著做了颇见功力的诠释,同时对一些长期被打入冷宫、遭误读、受轻视的作品重新磨光刮垢,使其在小说史的舞台上找到自身的位置。如在小说史上,裴铏《传奇》中的《封陟》篇是不大受注意的作品,《叙论》认为此作在描写爱情及人物的心灵冲突方面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而对于突出女性悍妒的作品《醋葫芦》,刘勇强却精辟地将其主题归为“男性自虐的戏谑与说教”[13],并肯定此作擅长制造戏谑的阅读效果。又如,《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鲜为人所提,但刘勇强却将其视为历史题材世俗化的典范,用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对其可圈可点的艺术成就做了精彩的分析[14];对于《金鳗记》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度方面,刘勇强指出其成就足以逾越《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宋代话本小说[15]。明末的短篇白话小说,整体艺术水平低下,似无足称道,然而刘勇强在《叙论》里秉持公心,披沙拣金,努力撷取小说作品思想的吉光片羽。如对于《石点头》中的《王孺人离合团鱼梦》及《瞿凤奴情愆死盖》流露的复杂思想给予首肯,对于《型世言》在描写农村生活上的新开拓也给予赞赏。而对在小说史上默默无闻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巧妓佐夫成名》《长须国》《定婚店》等作品,《叙论》均一语中的地诠释作品在细节上的贡献,从而确定它们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意义。
进一步而言,刘勇强超拔的小说鉴赏与诠释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例如,从形象构成和情节类型的角度探析小说史的演变是当前小说史较少涉及的,而他则谙熟于此。在《中国神话与小说》一书中,他多次从形象构成切入,分析不同作品在形象构成上的差异,并以此确立经典作品在形象上的小说史地位[16]。循着这一思路,《叙论》指出:“《柳毅传》与《西游记》在题材、文体、语言等似无关联,但在龙宫、龙王、龙女等非现实形象方面不乏相通,而这正是审视小说史应该注意之处。”[5]17又比如,《叙论》在评价《柳氏传》时,就以柳氏狐狸精形象的源与流为切入点,从而确立其在历代同类题材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情节类型的演变也是刘勇强小说研究的独特视角。在《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一文中,他通过对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两个情节类型的分析,探讨了白话小说及戏曲创作中本事、情节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我们示范了如何给予非经典作品正确的小说史地位。譬如“三言”中的《蔡瑞虹忍辱报仇》是鲜有人提及的作品,而他认为:“作者深刻地描写了蔡瑞虹在背负传统道德压力下面对复杂生活境遇的内心世界。例如她对朱源态度的转变,就很细致地反映了一个经历了许多欺侮的女性矛盾的情感。作品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通过蔡瑞虹曲折经历,串连了诸多阶层人物,从而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显示出水贼占妻(女)型具有极大可拓性。”[17]又比如《型世言》卷三的《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屡遭道德说教之讥,刘勇强指出:“在《西湖二集》中,王原寻亲的描写是重点;在《石点头》中,王询的离家出走与王原的寻亲在篇幅上基本相当;而在本篇当中,王喜(即王原父)的被迫出走及流离失所的痛苦,却是情节最突出的地方……作品对贫苦农民生活困境的生动表现,不只在《型世言》中极为突出,就是放在整个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看,也是值得称道的。寻亲故事往往还与佛教相关联,不外借佛法以显示孝子的虔诚,唯独此篇描写王喜皈依佛门,乃是饱经磨难、求生无路后的心灵追求,比之那些着意宣扬佛教的,更为深刻。”[17]显然,刘勇强通过对比烛照作品在水贼占妻(女)型与万里寻亲型小说中的新贡献,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非经典作品小说史地位的途径。
如前所述,刘勇强注重细节印证,而他的细节印证,往往从动态着眼,从小说史的演绎着眼,沿波探源,为所谓的“二三流”作品翻案,从而重新确立它们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前所述的《醋葫芦》与《醒世姻缘传》《狮吼记》《妒疗羹》等作品都是以悍妇为题材,它们有共同的创作倾向,单篇而论,其历史地位微乎其微,但是将它们作为一个作品群来看,这些作品无疑是小说演变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叙论》颇有见地地指出:“即使一个小说家不具备对某种生活现象的审美判断,他也会在时代风气的裹挟下,从中找到自己创作的位置。”[5]335这种评骘小说文本,从细节考量小说文体的演变,在刘勇强从地域、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研究视角观照古代小说的文章中也有精彩的呈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要之,刘勇强卓尔不群的学术追求赋予了小说史研究鲜明的个性化品格。有个性的学术才是有生命力的学术。刘勇强一直提倡与呼吁个性化学术,他说:“我认为具有独立思维与个性意识的学术研究,才是学术发展的真正动力。目前看来,自主性的、创新性的、有个性的研究论题在古代小说研究中还不是非常充分。”[18]在《文学没有“史”》一文中,他认为应建设个性化的文学史,又说“个性化不是一种目标,而是一个现实。我们要做的只是使它得到真正的、合理的凸现。同时,个性化也并不反对客观性。相反,它是对纯主观的挑战……而真正有参考作用的,难道不就是个性的眼光吗?”[19]另外,他对吴组缃小说创作及文学研究的个性化击节称叹,推崇备至[20]。缘乎此,其研究亦足以称为一家之言。
在“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背景下,探索古代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努力建构起属于中国的小说叙事学理论,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刘勇强在古代小说史的叙述体例、理论命题及研究视角上的贡献,以及他务去陈言、不囿权威的学术胆识和超拔的学术洞见,给学术界以诸多启迪。
参考文献:
[1] 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史略[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
[2]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3] 刘勇强.小说史叙述的文本策略[J].北京大学学报,2007(3).
[4] 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5] 刘勇强.中国小说史叙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钱钟书.人生边上的边上[M].北京:三联书店,2002. [7]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 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J].文学遗产,2009(2).
[9] 陈洪.结缘:文学与宗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1]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J].文学遗产,2001(5).
[12] 刘勇强.美人黄土的哀思——《红楼梦》的情感意蕴与文化传统[C]//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言及文学系.重读经典:中国传统小说与戏曲的多重透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13] 刘勇强.醋葫芦:自虐的戏谑与说教[G]//古代小说研究: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 刘勇强.虚拟的历史公共空间——谈《拗相公饮恨半山堂》[J].文史知识,2004(11).
[15] 刘勇强.话本小说情节艺术的范本——谈《计押番金鳗产祸》[J].文史知识,2004(2).
[16] 刘勇强.中国神话与小说[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17] 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J].文学遗产,2000(3).
[18] 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J].中国文学研究,2013(3).
[19] 刘勇强.文学没有“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谈片[G]//北京大学中文系.缀玉二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0] 刘勇强.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J].文学评论,2006(1).〔责任编辑 刘小兵〕
The Narrative Sty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Novel History—— On Pro. LIU Yong-qiang’s Research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
LAN Yong-hu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Professor LIU Yong-qiang’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novel has three identical features: 1) put the novelist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novel history; 2) conclude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from the aspect of text and novel history; and 3) use the unique perspective and high taste to construct the identical novel history.
Key words:LIU Yong-qiang; novel history; narrative sty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蓝勇辉(1988-),男,畲族,福建漳州人,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1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