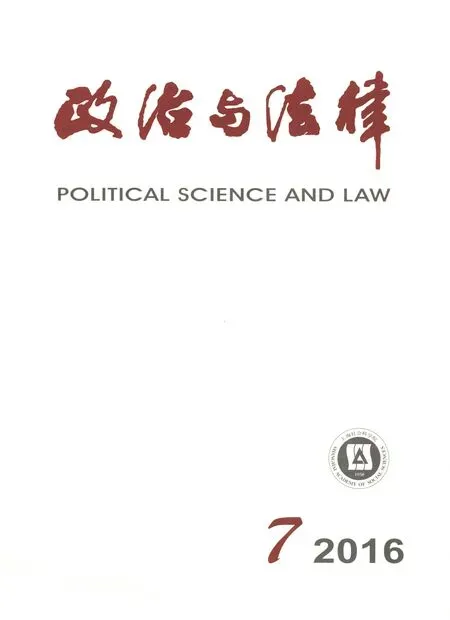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法律调整论批判*
——兼论人体移植器官来源困境之立法应对
2016-02-11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法律调整论批判*
——兼论人体移植器官来源困境之立法应对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
人体移植器官并不是一种产品,将其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范围的做法既缺乏法理基础,也不具备伦理基础,甚至也不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法律禁而不止是一种正常的法律现象,并不能成为足以支撑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理由。“改堵为疏,允许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做法不是应对人体器官来源短缺的一种有效路径。医学技术的发展不足以支撑人体移植器官的产品化。在扩大人体移植器官来源方面,法律应当保护人们捐献器官或遗体的权利,通过制度激励来激发和保障人们捐献器官尤其是身后捐献器官的热情,并应当严厉禁止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杜绝人体器官买卖。
器官移植;人体器官;产品责任法;生命伦理
人体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人类医学发展的最重要成就之一,被称为“21世纪医学之巅”,①管文贤、李开宗:《开展活体器官移植的伦理学思考》,《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6期。其成功及在医疗临床上的日益广泛应用为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②薛培、彭涛:《人体器官移植及其刑法学分析》,《东方法学》2011年第1期。为众多身患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带来了重生的希望。然而,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短缺也成为日益困扰器官移植技术深入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从技术上来说,没有器官就没有器官移植,而没有器官移植,很多能够借助于这一技术重获新生的人就会失去重生的希望。在此背景下,探讨扩大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的路径,并谋求立法上的支持与推动,成为不少法学家乃至伦理学家及广大从事器官移植临床的医务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之一。有学者提出,应当考虑将人体器官纳入产品的范围,通过市场交易来扩大人体移植器官的来源。陈云良教授在《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上发表的《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法律调整》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作为努力探索扩大人体移植器官来源以缓解当前我国器官移植临床上移植器官来源短缺窘境的一篇论文,该文勇于突破常规,提出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这一为绝大多数伦理学家与法学家们都颇为讳言的方法作为解决我国人体器官严重短缺问题的途径,其勇气难能可贵。然而,通读陈文,笔者认为,陈教授在论证过程中不但存在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理论瑕疵,而且不乏一些生命科学上的常识性错误。③如陈文认为“若移植的人体器官为单一的器官,如心、肝,只能取自非活体”,但实际上,肝移植的肝来源既可以是尸体也可以是活体,因为从医学上说,人只需要半个肝脏就足以维持其生命,所以活体肝移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大行其道,在我国亦然。为此,笔者特撰文与之商榷。
一、人体移植器官不应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范围
陈文在分析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现状以及困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短缺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应该认真反思过去的‘绝对否定说’,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结合伦理、法律、科技、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提出‘严格限制肯定说’,即在肯定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基础上,将移植器官纳入《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严格限制器官产品的准入和交易。”④陈云良:《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法律调整》,《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以下引文如非特别注明均出自陈文)其言下之意,是要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一种产品(亦即物)而准许其交易。但实际上,人体移植器官根本就难以被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因为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伦理上看,这一做法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障碍。
(一)人体器官不是一种产品
产品作为一个经济学和法学上的概念,有着严格的范围界定。而各国立法对产品范围的界定不仅要考虑产品质量的监管范围,更要考虑其伦理、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国际组织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产品范围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如1973年关于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的《海牙公约》第2条规定:“‘产品’一词应包括天然产品和工业产品,而不论是未加工还是加工过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欧盟《产品责任指令》规定:“产品是指初级农产品和狩猎物以外的所有动产,即使已被组合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内。初级农产品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产品,不包括经过加工的这类产品。产品也包括电。”1989年德国《产品责任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任何动产,即使已被装配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内,还包括电。但未经初步加工的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养蜂业、渔业产品在内的农业产品(初级农产品)除外,狩猎产品亦然。”日本《产品责任法》规定,产品是指被制造或加工的动产。根据该法,产品不包括不动产、初级农产品、狩猎品以及血液和人体组织。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规定:“产品是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具有组装整件或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产品责任法中都未明确将人体器官、组织与血液等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⑤当然,也有个别国家的司法判例中出现了将血液作为产品的做法(参见[英]厄莱斯代尔·麦克林:《医疗法简明案例》(影印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但这一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一些国家的立法甚至还明确将人体器官、组织或血液排除于产品的范围之外。
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产品有着清晰明确的范围界定,即“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⑥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据此,判断一种物品是否属于产品而应当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应当是看其是否经过加工、制作。因为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目的是针对现代化的批量生产、批量销售,⑦黄靓:《刍议输血感染案件的法律责任》,《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所以,这里的“加工、制作”应当理解为连续性、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而人体移植器官尽管在移植入受体之前会做些技术上的处理,但却完全达不到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加工、制作之程度,更谈不上连续性、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而且,在各国伦理与法律一致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背景下,人体移植器官也根本无法用于销售。显然,人体移植器官不是一种产品,至少不是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下的产品。既不是产品,则其客观上就不具备将之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基础、条件甚至是必要性。
(二)人体移植器官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缺乏法理基础
陈文主张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范围的理由之一在于,“在人体器官移植手术之后,部分接受者因植入了存在质量问题的器官,受到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伤害,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责任主体与归责原则,导致这部分受害者的权益无法保障”。其言下之意是,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范围就可以在缺陷(或瑕疵)器官移植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上适用我国《产品责任法》的规定,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器官接受者的利益。但实际上,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由我国《产品质量法》加以调整,其需要具备的首要前提就是器官是一种产品。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即人体器官移植中所形成法律关系符合产品质量法所要调整的产品质量关系。而实际上,不仅人体移植器官不满足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概念,而且人体移植器官的提供者、医疗机构与接受者之间也绝不是产品质量法调整下的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从法理上来说,人体移植器官的提供者并不是器官的生产者,而只是人体器官天然的所有者;而医疗机构也不是人体移植器官的销售者,而只是使用者,其依法并不能从人体移植器官中获得类似于产品销售者那样应当获得的经济利益;⑧其通过器官移植获得的收益属于提供器官移植这一技术服务所获取的服务收益,而不是依靠出卖人体移植器官所获取的差价。至于人体移植器官的接受者即受体,也完全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语境下的消费者的概念,因为在器官来源的选择问题上,其完全不可能具有消费者所应当享有的自主权。而在人体移植器官不是一种产品,而器官捐献者不是生产者,从事移植的医疗机构也不是销售者,甚至人体移植器官的接受者都不是消费者而无法形成产品质量关系的前提下,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由我国《产品质量法》加以调整的做法无疑于缘木求鱼,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后果。而这显然意味着,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范围以更好地保护人体移植器官接受者合法权益的做法存在先天的法理瑕疵,是一种不可行的路径选择。
(三)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不具备伦理基础
在伦理学上,自然界中实体可以被划分为三类,即人、物以及介于人与物之间的其他实体,而尸体、器官、人体组织乃至胚胎等则属于第三类实体。而这三类实体各有自己的伦理格位,人有人格,在自然界具有最高的、能够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伦理格位;物有物格,具有只能作为人类活动客体的、比较低的伦理格位;而人物之间的包括器官在内的第三类实体在伦理格位上处于人与物之间,即具有高于物格但却又低于人格的伦理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体器官买卖在伦理上是被绝对禁止的。世界卫生组织第WHA 40.13号决议就明确指出,人体器官交易违背了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是对《世界人权宣言》和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精神的践踏和侵犯。在各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尽管没有像伦理学上那样明确器官这类实体的伦理地位,但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却通常都将其作为一种具有人格性特征而不同于物的实体对待,即承认其人格性,严格禁止将其物化,如作为大陆法系民法典之蓝本的《法国民法典》就对此有明确规定。陈文所主张的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人体移植器官等同为了一种物,使人体器官的伦理格位直接降格为物。这不仅会诱发将人一步步降格为物的道德风险,使人的整体性社会价值遭到贬损,而且明显是将捐献者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而非他/她的目的,⑨See Deryck Beyleveld and Roger Brow sword,Human Dignity in Bioethcs and Biolaw,Oxford University,2011,p.192-193.从而损害人性尊严,并最终导致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的紊乱。就此而言,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不但不具备伦理基础,而且会冲击现行的生命伦理秩序,是为伦理所不容的。
值得指出的是,陈文对此并不以为然,相反,陈文认为,“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不会使人降格为物”,“不会降低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不会因为少了某个器官而减弱”。但实际上,尊严作为一个来自伦理学上的概念,是建立在人格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和享有的,没有人格就谈不上所谓的尊严。正是在此意义上,尊严是只有人才享有的,物——不论是有生命的物还是无生命的物,甚至包括动物——都谈不上所谓的尊严。而人体器官、尸体、胚胎等之所以被认为关涉人性尊严,就在于其具有人格性,是一种人格体,⑩刘长秋:《生命科技犯罪及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与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而绝非一些学者(也包括一些法学家)主张的那样,是一种物——无论其是否已经与人体相脱离。①有学者认为,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应当被界定为物(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体器官无论是否与人体脱离都不构成物(参见邾立军:《论脱离人体的器官的法律属性——与“二元区分说”商榷及对“人身之外”的理解》,《法学论坛》2011年第5期)。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作为抹杀人体移植器官人格性而将其降格为物的一种做法,已经包含了对人性尊严的蔑视和侵犯。因为当一种具有人格性而具有更高位格的实体被作为产品而降为物时,寄寓其人格内容之上而体现出来的人性尊严早已因为该人格体人格的被漠视而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还包含了将人物化的道德风险,因为既然来自人体而作为人格体的器官能够被产品化,则同样来自人体的新生婴儿也没有理由不可以被产品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代孕出生的婴儿。在此意义上,人的尊严一定会因为某个器官的产品化而降低。②从伦理上来说,人体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必须有所牺牲的医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并为各国法律所认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器官无偿捐献所显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他与互助,在于通过器官无偿捐献所显现出来的大爱。人体器官买卖作为一种“沾上了铜臭”的现象,则从根本上损害了这种利他与互助,从而使器官移植不再具有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正当性以及应当为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性。而失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器官移植,更多情况下会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不再是帮助。
(四)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不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不具有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其原因在于,人体器官移植是一种直接关涉人生命健康的专门医疗活动,对这一活动,更适合由器官移植法或医疗法这类专门立法来加以调整。也正因为如此,各国几乎都出台了专门的法律(即器官移植法),将有关移植器官的质量、来源以及移植活动的审批、监管等问题纳入器官移植法调整的范围之内。在此背景下,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而由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做法,根本就没有必要。而且,从产品质量法的内容来看,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也完全无法适用于人体移植器官,如产品抽检制度、投诉制度、认证制度完全不适合调整人体移植器官,甚至有关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也几乎与人体器官这类所谓的“产品”没有关系。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一种产品而置于我国《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之下的做法不具备可行性,只会增加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负担。
综上所述,陈文所谓的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结合伦理、法律、科技、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提出的所谓“严格限制肯定说”,即将人体移植器官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加以调整的做法,尽管很具有挑战传统观念的勇气和魄力,也不乏新颖性,但却是一种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法理上都站不住脚的学说,不具备可行性。
二、法律禁而不止难以成为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理由
陈文认为:“虽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禁止人体器官产品化,但由于移植器官供体数量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等犯罪行为并没有因为法律禁止而减少,人体器官黑市交易不仅大量存在,甚至日益猖獗。”以此为基点,陈文进而认为,“立法禁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其如此,不如改堵为疏,允许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将其纳入法律规制与国家管控之下”,以“扩大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但实际上,这一结论作为陈文用来论证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不乏仓促和武断之处。
首先,“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等犯罪行为并没有因为法律禁止而减少,人体器官黑市交易不仅大量存在,甚至日益猖獗”的说法,完全没有认真考察各国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交易的实际效果,而只是从人体器官交易禁而不止的表面现象出发得出的一个不严谨的结论。实际上,各国法律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禁止在防范人体器官买卖泛滥方面发挥了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以我国为例,人体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过去一直都在我国医疗临床上存在并日益严重,而我国司法机关也以“非法经营罪”或“故意伤害罪”审理和裁判了大量人体器官交易的犯罪行为。然而,自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通过而令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事责任制度生效以来,这类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已经受到了显著遏制。显然,法律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禁止是起到了预防相关违反犯罪行为之巨大作用的。所谓“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等犯罪行为并没有因为法律禁止而减少,人体器官黑市交易不仅大量存在,甚至日益猖獗”的现象至少在我国未见踪迹。这从某个侧面表明,所谓“立法禁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其次,“立法禁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并不能成为法律认可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而准允人体移植器官买卖的理由。其原因在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只是众多社会治理手段中的一种,而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包括伦理、法律、政策、教育甚至是宗教等在内的各种手段共同发挥作用,任何一种手段都有其内在的缺陷与不足,都不足以成为实现社会治理的完全依赖。而且,受人性先天存在的各种缺陷等其他因素的制约,任何社会治理手段都是不可能做到禁而即止的,伦理如此,政策如此,甚至连对人们更具心理威慑的宗教也如此。至于法律,显然也无法摆脱这一局限。这是法律治理在任何社会问题的治理上都必然且必须要直面的一个客观现实,而绝非法律禁止模式不足而需要反思和改变的理由。实际上,法律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禁止都是禁而不止的,即便是杀人、抢劫、拐卖人口这类在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犯罪甚至在一些国家还被认为是重罪的行为也都是禁而不止的。假如仅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法律禁止模式的意义而主张“改堵为疏”,则杀人、抢劫、拐卖人口这样的犯罪也完全可以依同样的逻辑而“改堵为疏”。这显然是荒谬的。笔者以为,假如真的如陈文所说,出现并存在着“立法禁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客观现象,则人们需要做的显然更应当是在理性、科学地看待法律调整功能局限的同时,反思法律禁止的力度是否到位以及禁止的措施是否完备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如陈文所说的反思法律绝对否定模式之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改堵为疏”。例如,人们更应当考虑增设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加大对人体器官买卖的刑罚力度,或者加大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经济处罚,加重人体器官买卖的成本,等等。
再次,退一步来讲,即便是真如陈文所言,“立法禁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也不意味着“改堵为疏,允许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就是应对人体器官来源短缺的一种有效路径。其原因在于,表面上看,人体移植器官的产品化的确可以起到通过市场来建立一个看上去似乎更合理的器官获取体系之作用,但实际上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短缺的问题。因为在人体器官交易模式下所进行的器官移植,只会有利于那些具有经济能力的人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人体移植器官的产品化尽管可以通过市场建立一个新的人体移植器官获取体系,却会冲击原先建立在利他性基础之上的人体移植器官获取体系,并致其最终崩溃。③毕竟,在法律允许人体器官作为产品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再愿意无偿地捐献器官,这会导致以利他性为基础的人体器官无偿捐赠体系最终崩溃。因为将人体器官置于自由市场之中“破坏了稀缺卫生资源应当被依据需要分配而不是依支付能力分配的原则”。④Emi ly Jackson,Medical Law:Text,Cases and Mater ial 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746对于不具有经济能力的人而言,其不但被剥夺了过去在人体器官无偿捐赠模式下可能享有的获得他人捐赠器官而接受器官移植从而重获新生的机会,而且还可能会基于经济上的贫穷与生活上的困顿而被迫出卖自己的器官,从而令其陷入更为艰难的处境之中。换言之,在“改堵为疏,允许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情况下,具有经济能力的人的确具有了通过给付一定金钱而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的确缓解了困扰富人的器官来源短缺问题,但不具有经济能力的人却并未从中受益,反而成为受害者。⑤需要指出的是,陈文在指出伊朗是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国家和论证其实践可行性的时候指出,“在伊朗,有偿捐献制度受益更多的主要是穷人,原因在于富人更有条件和能力照顾自己的饮食和健康,因而其身体或者其他器官病症的发病率比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要低一些,富人对肾脏移植的需求反而没有穷人高”,并指出,“伊朗的器官有偿捐献制度把为了经济目的而出卖器官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伊朗透析与移植患者联合会(the Dialysis and Transplant Patients Association)的设立取代了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器官中介’,并基本杜绝了人体器官黑市交易”。陈文为此专门注明以上资料引自王荣平、付媛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上的《人体器官商业化之合法性探讨》一文,但遗憾的是笔者认真地看遍了《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并没能发现有这样一篇论文,反倒是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看到了这样一篇论文。但依然遗憾的是,笔者看完了该文,却并未发现该文中有上述论证。至于陈文所援用的以上资料究竟出自何处以及其真实性如何等等,恐怕有待其进一步严格考证。显然,法律“改堵为疏,允许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做法不但无法真正改变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短缺的问题,于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无益,而且会加剧人们的不平等。而这显然背离了法律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在论证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法律调整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时候,陈文不止一次地提及了伊朗的经验,认为“伊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存在移植器官短缺的国家”、“伊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伊朗,有偿捐献制度受益更多的是穷人”。但实际上,这一点并不确实,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人体移植器官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伊朗而言也不例外。伊朗并不是一个不存在移植器官短缺的国家,尽管有数据表明,这种有偿的器官捐献制度基本消除了等待进行活体肾脏移植的名单。一些研究伊朗器官获取模式的西方学者就指出,在伊朗,很多来自农村地区的患者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诊断和透析的机会,因而未被放入等待移植的名单中;而也有些人则承受不起活体捐献移植的高额费用(尽管有各种补助)而选择等待其成本要小得多但等待时间也要久得多的尸体器官捐献;⑥在伊朗,捐献尸体器官除了可以给捐献者家属必要的丧葬费之外,是不允许提供任何其他补偿的。而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女性以及失业者根本就没有被放进等待(活体)移植的名单中。⑦Alastai r V.Campbel l,The Body in Bioethics,Rout ledge,2009,p.50.而且,即便是活体器官捐献移植,其在伊朗的供需比也只是7 6:1 0 0而已;⑧Alastair V.Campbel l,The Body in Bioethics,Rout ledge,2009,p.50-51.其移植器官的缺口尽管比较小,却依旧是存在的。其二,伊朗并不是一个对人体器官进行产品化的成功的例子。原因在于,伊朗这一有偿捐献的制度已经妨害了其他潜在的捐献来源,即来自家庭成员间以及尸体的具有利他性的器官来源。其中,在尸体器官移植方面,与世界平均捐献率(每百万人有1.8人捐献)和美国(每百万人有2 6.9捐献)以及英国(每百万人中有1 0.5捐献)的捐献率相比,伊朗尸体器官捐献率依旧明显较低。⑨Alastair V.Campbel l,The Body in Bioethics,Rout ledge,2009,p.50-51.这说明,所谓的“伊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并没有确实的数据和证据支撑,现有的数据和证据反而表明伊朗的人体器官有偿获取模式并不成功。其三,伊朗有偿捐献器官制度的受益者也并不主要是穷人。因为法律允许受体向捐献提供一定补偿的做法,使得富人更容易找到有意愿捐献的供体,富人依旧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偿器官捐献的最大受益人。就其本质而言,伊朗实行的有偿器官捐献模式作为一种会对穷人形成歧视的制度,⑨See Alastai r V.Campbel l,The Body in Bioethics,Rout ledge,2009,p.51.其主要受益者不可能是穷人。
三、医学技术发展更不足以支撑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
医学技术发展也是陈文主张应当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一个重要理由。陈文认为,“医学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出现了大量器官移植的成功案例,也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手术更有信心”。其言下之意在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越来越高,而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也已经有能力对移植器官进行筛选,能够将移植器官像产品那样进行质量检疫、检测,从而防止将存在问题的器官植入受体体内。但陈文对于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治病救人方面的效用显然有所高估。
实际上,医学技术发展与其他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所适用的对象是人。这使得医学成为各类自然科学中最复杂的学科之一。现代医学的进步使得器官移植日益成为一种医学常规手术,也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受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医学工作者可以很轻易地就能检测移植器官质量从而保证移植效果的程度,更不意味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足以支撑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的程度。实际上,由于人体自身的复杂性,适用于人体的器官移植技术远不像其他自然科学技术一样易于为人们所掌握和控制。器官移植成功与否,其效果如何,很多时候并不是器官本身的质量就能决定的。以尸体器官移植为例,决定尸体器官移植能否成功的临床因素就包括:受体与供体间组织与血液的相容性、有效的免疫抑制、缺血的限制和器官的大小,⑩蔡昱:《器官移植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 7 7页。而器官摘取及移植的时机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摘取时间过晚就会影响器官的活性而致移植失败等)。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远没有使器官移植技术像其他自然科学技术甚至其他医学技术那样发达和易于操作,其在对待人体移植器官这一“产品”上也还远没有像一般工业技术对待产品那样准确。这一点,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无论其技术有多高超或其经验有多丰富——无法像普通生产者或销售者对待其产品那样自信,更不敢对借助其“加工、制作”之“产品”(即器官)而维持生命的受体的生命健康作出保证,尤其是在当前很多器官移植后的三年存活率尚不足50%的情况下(如小肠移植后,其三年存活率仅有30%)。也就是说,即便器官这一“产品”经检验是完全合格的,也不意味着移植过程中或移植后就不会因为这一“产品”而致接受移植的患者生命健康出现问题(毕竟还有排异反应的问题),更遑论器官移植还会受到窗口期及病毒检测试剂灵敏性问题的限制而无法提供百分百准确的检测结果。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则显然意味着需要对人体移植器官适用严格责任,一旦受体因为器官移植而出现了死亡等情况,则在医疗机构无法证明自身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就适用严格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而且,从医学上来说,人体器官移植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其原因在于,器官移植尽管能够挽救很多身患器质性病变者的生命,但这种挽救其实是以牺牲另外一个人的利益的方式来实现的;在活体移植的情况下,供体至少需要面临以下牺牲(即健康风险或损害):手术创伤及痛苦;手术并发症;器官储备功能的损失,防御疾病能力的减低;围手术期内终止工作所致的经济损失;几率极少,但仍然无法彻底避免的死亡率。②同前注①,管文贤、李开宗文。就此而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还远没有令器官移植成为一种对供体完全无伤害、无负面影响的技术。人体器官移植——尤其是活体器官移植——对于人体器官供体生活与生命质量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它不是救治人类生命健康的最优方法和手段,而只是一种次优越方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③实际上,即便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也不会有多少人——除非是基于不得以的苦衷或困顿——轻易出卖自己的器官。所谓的“通过市场的力量对供体方进行筛选受体有机会对移植器官产品进行选择”,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臆测。而对于受体而言,器官移植后的生活一般并不若浴火凤凰般的重生,受赠者必须极大地依赖抗排斥药物,而抗排斥药物又会降低免疫系统能力,易导致致命的伺机性感染或患恶性肿瘤。一定意义上,器官移植只是把受体承受的一种致命疾病转变成了慢性疾病而已。所谓“器官植入者生活质量较好”,只是相比于其接受移植前的生活状态而言的,相比于正常人,接受移植后的患者依旧面临器官功能储备不足、免疫力弱于常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是不可能象陈文所说的那样“一如常人”的。此外,就移植后的存活率来看,器官移植技术尽管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移植后的存活率方面有了显著提高,但对于很多类目器官移植来说,移植后的存活率并不像很多人预想得那样高。以肺叶移植为例,研究表明,目前活体肺叶移植一年与三年的存活率仅为6 5%和5 3%。④Austen Garwood-Gowers,Living Donor Organ Transplantation:Key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9,p.220-220.就是说,很多时候,活体肺叶移植其实只是牺牲了很多健康人的利益而帮助接受了肺叶移植的65%及53%的人延长了一年或三年的生命而已。这其实意味着,现代医学发展所带来的器官移植技术的降生及其进步只是人类救死扶伤的一棵救命稻草。该技术的进步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和必要性让更多人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为代价,通过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的方式来救助那些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人。
四、我国人体器官来源困境的立法对策
当前,伴随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快速发展及其在医疗临床上的日益广泛应用,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不足的问题已经在我国医疗临床上充分显露,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从法律的角度上探讨扩展器官供体来源,以最大可能地增加器官捐献,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以为,就其原因而言,导致我国移植器官供体来源不足的因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的制约,二是现行法上的不足。就观念因素而言,在我国奉行了数千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必然形成的人们对自己身前或死后身体完整性的过分看重成为制约人们自愿捐献器官的最大障碍。就现行法的不足来说,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立法激励措施的欠缺。从伦理上来说,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即供体)利益的方式来拯救另外一个个体(即受体)生命的医学救助手段,其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的接受并进而得到法律的许可,主要是源自于通过器官无偿捐献所显现出来的利他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在伦理上,器官捐献属于美德的范畴,也就是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而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其所维系的只能是“义务的道德”。这一点决定了作为一种美德的器官捐献不宜以义务设置的形式被确立在法律中,而只能以权利设置或精神激励的方式为法律所倡导和保障。正如倪正茂教授所指出的,“在法的大家族中,生命法尤其是非传统的生命法,对法的激励功能是情有独钟的。器官移植法就是对器官移植的激励。献血法是对无偿献血的激励。1907年美国颁布的《优生法》,1948年日本颁布的《优生保护法》等,都是对‘优生’的激励。充分重视生命法的激励性特点,对促进生命科技的发展从而对保护人的孕育、生产、生存、健康起巨大的作用。”⑤倪正茂:《生命法学探析》,法律出版社2 0 0 5年版,第1 4 0页。遗憾地是,现行的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尽管规定了“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但并没有规定鼓励人们身后捐献遗体或器官这样一项基本原则,而在具体制度上也没有设置多少激励措施。这导致人们身后器官捐献无法在制度上得到更有效的激励和保障,人们身后捐献器官的热情不高。⑥实际上,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自2 0 1 0年3月以来在全国十个省市(后扩大到十六个)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旨在推动以遗体器官捐献为主的器官捐献事业。该工作开展四年多后,已经在推进遗体器官捐献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比较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激励机制在推进我国移植器官捐献工作方面的可行性。但这一有效并需要为我国器官移植法所肯定和推广的做法迄今还未被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吸收。
二是立法防范和惩治措施的不足。就目前来看,我国法律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禁止力度显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刑法方面。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尽管将人体器官移植纳入了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却仅设置了三个罪名,而有关人体器官买卖的罪名仅“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这一个罪名。实际上,涉及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还是很多的,如制作、发送和刊登人体器官买卖讯息的行为。实际上,对于人体器官买卖这类犯罪,很多国家的法律都给予了严厉的禁止。如在韩国,其《有关脏器等移植的法律》(最新修订于2009年)第6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得给付、收受或者约定给付、收受金钱、财产性利益以及其他反对给付而实施下列各项规定的行为:1.将他人的器官提供给第三者或者为了提供给第三者而收受的行为,或者对此做出约定的行为。2.将自己的器官提供给第三者,或者为了给自己移植他人的器官而收受的行为,或者对此做出约定的行为。3.教唆、斡旋、帮助第1项以及第2项行为的行为。”其第6条第2款则规定:“任何人不得教唆、斡旋、帮助违反第1款第1项以及第2项的行为。”在英国,其2004年新修订的《人体组织法》第32条明确规定,行为人的下列行为构成犯罪:(1)因提供或者要约提供任何受限制人体材料而给付或接受报酬的;(2)寻找图谋报酬而提供受限制的人体材料的;(3)为报酬而要约提供受限制的人体材料的;(4)发起或协商签订任何有关提供或要约提供人体材料而给予报酬的协议的;(5)参与安排或控制那些包含或包括了发起或协商发起这类协议的法人或非法人社团之活动的。在我国香港地区,“谋求寻觅愿意为获取付款而提供该器官的人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器官”、“提出或商议作出任何安排,而该等安排涉及为该器官的提供或提供该器官的要约而作出付款”、“拟于香港或外地移植于另一人体内的器官的广告,或为获取付款而要约提供该等器官的广告”以及进出口移植器官等这类关联行为也都构成犯罪。在我国澳门地区,不仅人体器官买卖的行为将被处以刑罚,未遂犯亦被处罚。至于日本、法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范围也都远远大于我国刑法规定的范围。我国刑法上的缺憾直接导致我国立法打击人体器官买卖的力度不足,使得人体器官买卖尤其是变相人体器官买卖依旧时有发生。而这些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损害了人们对器官捐献的信任,使得很多人担心自己捐献的器官会被医疗机构或医生用来牟利而不愿捐献器官。
观念的形成和改变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不可能奢望通过立法的推动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观念。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可能通过立法去解决导致我国器官供体不足的观念根源,移植器官供体来源的短缺依旧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器官移植不得不面对的瓶颈。但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在增进我国器官捐献方面会无所作为,也不应有所作为。笔者认为,这种作为显然应建立在其对人类生命伦理规则之尊重和维护的基础之上,而绝不是背离人类生命伦理的底线,将人体移植器官作为产品,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来实现。
基于此,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围绕自愿同意捐献制度来建构,其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基于现行法所显现出的不足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具体而言,一方面,法律应当尽可能地增强对身后器官捐献权的保障以及对人们主动行使这一权利的激励,使器官捐献者不仅能够顺利行使自己的身后器官捐献权,而且能够通过身后器官捐献而令其自身与其家属获得更多的荣誉感。例如,法律可以规定由相关政府部门或组织出资为身后器官捐献者建立纪念碑、纪念林;可以规定由政府部门对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捐献者家属给予特定救济;可以规定由国家设立器官捐献者纪念日,通过举办大型的缅怀活动,褒扬捐赠者的善行及其家属的大度;可以考虑规定酌情减少甚或免除那些生前主动要求身后器官捐献的患者因其器官捐献所需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或将这部分费用纳入医保;可以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对身后器官捐献给予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建立各省市人体器官捐献基金,专门用于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困难救助、缅怀纪念、表彰奖励、机构运行及信息平台建设、维护等工作。应该说,这些都是激发人们身后捐献遗体或器官之热情,从而自觉、主动捐献遗体或器官,以增加移植器官供体来源的有效举措。另一方面,针对医疗实践中人体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所给器官捐献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在法律上加大对人体器官买卖的处罚力度,尽可能地减少器官捐献的机会成本,保护好人们对器官捐献的好感与热情。
五、结语
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而纳入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谋求通过市场来解决困扰人体移植器官来源短缺的问题,将毁损人体器官移植正当性所赖以构建的利他性基础,加剧人们的不平等,使法律背离其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
法律应当而且也理所当然地能够在扩大人体移植器官来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法律尊重并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倡导、鼓励和保障人们自愿捐献器官来进行的,而不是违背和忽视人类生命伦理,通过将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来推进的。在扩大人体移植器官来源方面,法律应当保护人们捐献器官或遗体的权利,通过制度激励来激发和保障人们捐献器官尤其是身后捐献器官的热情;不仅如此,法律还应当严厉禁止人体移植器官产品化,以防范人体器官交易对以利他性为基础的器官获取体系带来毁灭性冲击。这是保障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维护人类生命伦理秩序稳定,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程维荣)
D F0-052
A
1005-9512(2016)07-0106-10
刘长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重点实验室兼职教授。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2014年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重点实验室(山东政法学院)开放基金资助课题“我国器官移植法修改完善的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K FK T(SU PL)-2014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