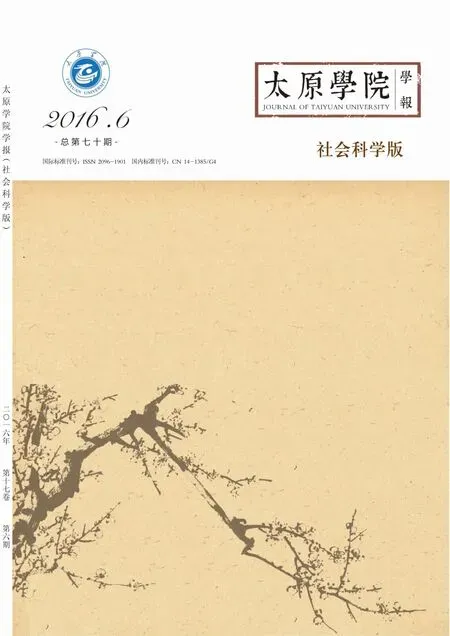论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2016-02-11周衡
周 衡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论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周 衡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县居是姚合重要的政治生存和文学创作的空间,姚合在从政早期先后任武功、万年等地的县吏,创作了大量县居诗。我们通过对其县居诗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到姚合在县吏阶段面对仕途和隐逸的内心矛盾,从而产生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上的仕隐冲突。这种心灵冲突的生成不仅与吴兴姚氏家族、个体本性、时代精神有关,也与其内在的儒道矛盾有密切关系。
姚合;县居诗;仕隐;儒道
姚合元和十五年(820),任京兆武功主簿,长庆三年(823)任万年尉,宝历元年(825)调富平尉,至宝历二年(826),始授监察御史。在县吏时期,姚合创作了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闲居遣怀》十首为代表的五十八首县吏诗歌(按,本文所引姚合诗全出自吴河清《姚合诗集校注》[1])。县居诗是姚合诗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对象,在宋元以后成为中国传统县吏文人的创作范式。作为姚合诗歌创作的典型代表,县居诗承载着其县吏时期特定的政治情怀、精神动态。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其县居诗,来观察姚合的政治行为、心理流变乃至文化精神,从而更为全面地描述姚合在县居阶段的精神形象。
一、姚合早期政治心理与其县吏认识
(一)士有经世筹:姚合早期政治行为与心理
姚合元和八年(813)始入贡举,胸有远志,其《过张邯郸庄》云:“时清士人闲,耕作唯文词。岂独乡里荐,当取四海知。”此时正是唐宪宗政治管理的上升时期,无论是朝中融洽的君臣关系,还是面对藩镇的皇权威严,都呈现出一派中兴格局,姚合面对如此“时清士人闲”的时代,自然生成出“当取四海知”的功名梦想和政治欲望。他在《送王求》中说:“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士人之所以没有“活身策”,正是因有“经世筹”,这种思想与孟子所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相似,具有视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怀。
正是这种身处中兴时代的政治梦想,姚合进士及第不久便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幕府。姚合在《寄狄拾遗时魏州从事》写道:“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愚虽乏智谋,愿陈一夫力。”可见其入幕的雄心野望。元和十三年七月,宪宗诏削夺淄青李师道在身官爵,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姚合在《从军行》中感慨自己身在魏博幕中却未能参战,“昨来发兵师,各各赴战场。顾我同老弱,不得随戎行。”但是姚合认为“从军不出门,岂异病在床。谁不恋其家,其家无风霜。鹰鹘念搏击,岂贵食蒲肠”。诗人在朴直劲峭的语言里包裹着满腔热情和无尽焦灼,蕴含着诗人对个体声名建立的渴望。
(二)荒城僻县:姚合县居诗对县居环境的叙述
数年的从军并未给姚合带来理想的政治前景。元和十五年田弘正移镇,姚合罢幕职,不久出任武功主簿。在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姚合对此职务的不满,这种心理直接反映在他对县居环境的叙述上。姚合对武功县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县僻”和“荒城”两个语汇之上。如其十一:“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回。””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然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载,武功县“东至(京兆)府一百四十里”[2]32。又卷一载京兆府府境“东西三百一十里,南北四百七十里”[2]2,故无论从武功县畿县的行政地位,还是从它在京兆府的区域方位来说,都非荒城僻县。柳宗元《武功县丞厅壁记》云:“武功为甸内大县,……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坟衍之大;其植物丰畅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树艺,其俗有礼让,宜乎其大雅之遗烈焉。”[3]6616在柳宗元描述中,武功县因其行政地域成为京畿大县,因其土疆丘陵、植物物产而成为高厚富饶之所,同时因其风俗礼让,具有宗周遗风。因此,姚合县居诗对武功县环境的评价具有个人色彩,是源自其政治理想落空之后的心理反抗。《武功县中作》一直提到其任武功主簿的年限,如其六云:“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其十二云:“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其二十七云:“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从中我们大略可知《武功县中作》诸诗当作于姚合任武功主簿的后期,长达三年的县吏生涯,似乎看不到未来的政治前景,正如其二十三说:“一官无限日,愁闷欲何如。……白发谁能镊,年来四十余。”这里流露了姚合深居县吏的苦闷以及在苦闷中对人生改变的期待和焦虑。同时,姚合在其十四中说:“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我们从“故人多得路”中能看到姚合对故人前途似锦的艳羡以及自己仕途寂寞的失落。可以说,姚合称其县吏环境是荒城僻县,其真实内涵并非是对政治本身的放弃和否定,而只是对政治失意、仕途无望的哀伤和自愤。
(三)微官杂务:姚合对县吏职务的认识
唐代县级行政常分赤、畿、望、紧、上、中、下等七等。其中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姚合所任的武功县、富平县和万年县分别为畿县、次赤县和赤县,欧阳詹《同州韩城县西尉厅记》云:“赤县仅二十,万年为之最。畿县仅于百,渭南为之最。”[3]6790从此,可见姚合所任万年、富平、武功的重要性。唐代政府对京畿之县的人事任命较为慎重。唐玄宗《赐京畿县令敕》云:“亲百姓之官,莫先于邑宰。……卿等列在三畿,各知人务,宜用心处置,以副朕怀。”[3]414在此敕令中,唐玄宗要求京畿县令勤勉吏治,并允诺“凡著贤能,必无旷职,即宜好去”。可见中央政府对京畿县职的重视。又欧阳詹《同州韩城县厅壁记》认为唐代重要之县,其簿尉之职,“虽一命之官,其为人尚也如此,则主司慎择才地精美。”[3]6790可见唐代政府多选“才地精美”者担任京畿望紧等重要县的吏职。
然姚合在其县居诗中对其所任的县吏职务常用“微官”“官卑”等相同内涵的语汇来展露其对所任职务的不满。如《武功县中作》其三的“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其十二的“官卑食肉僭,才短字人非”、《游春》其二的“卑官长少事,僻县又无城”等。就姚合所任的武功主簿、万年尉、富平尉等地方县吏来看,若与京城豪门贵族、达官显宦相比,确为卑官冷职。然正如前文所述,三县之职皆非平常。之所以姚合会有如此认识,一方面是因其本有的政治期待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龃龉而导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姚合早期从政行为的浮躁焦虑之心。姚合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及第时已三十九岁,其初任主簿时已四十三岁,此后六年皆任地方县吏。年岁渐老,暮年初生,漫长的县吏生涯和逼仄的生命光阴之间必然产生对立,从而在姚合心灵上投射出焦虑和恐慌,最终形成对政治理想实现的怀疑和对当下政治状态的否定。
唐代主簿是辅佐县令管理吏务的总务属吏,李林甫《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载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4]753县尉也是县令的主要僚佐。“县尉亲理庶务,分判诸曹,隔断追催,收率课调”。[4]753可见无论是主簿还是县尉,其在县吏体系中身居辅助要职。姚合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中常记载其职务行为,如《武功县中作》其三的“簿书销眼力”、其四的“簿书多不会”、其十七的“簿籍谁能问”,可知其任主簿需勾稽县衙出入的各种文书,承担唐县级政府的勾检职能。这些繁琐的日常职务对于姚合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从传统文人的教育发展来看,从汉代到唐代的儒学教育并未引导文人培养经世致用的吏治素养,其主要还是以礼乐文词等方式参与政治管理,这种以专业的文词能力从事业余的政治管理最终导致文人无法真正融入吏治领域,繁琐的政务也就必然会减低其对政治的热情,从而产生厌倦游离之心。和所有身怀政治梦想而乏吏治能力的文人一样,姚合在早期从政生涯中同样表现出对具体吏务的抗拒,这也是其隐仕冲突的心灵结构产生的重要前提。
二、意象、行为与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一)野客与朝客:姚合县居诗人物意象所蕴含的仕隐冲突
诗歌创作是一场精神狂野的演示,阅读者只有拥有意象这一把钥匙,才能把握作者精神的译文。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基本单位,其成为创作主体现实情感、精神观念等文化意识的重要载体。诗歌创作者与阐释者的印证对话也须通过意象的疏解来达成相对的共识。在姚合县居诗的意象群中,人物意象出现有十三处,频率虽不高,但其存在为我们了解姚合此时的心灵趋向有一定意义。
姚合县居诗人物意象有两类。第一类是作为典故符号的人物意象。姚合在《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云:“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其五云:“长羡刘伶辈,高眠出世间。”这其一中所用典出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体现嵇康对世俗酬酢的拒绝和反抗,其五所用典出自刘伶《酒德颂》,反映刘伶超越名教、潇洒自得的心灵。典故“作为携带文化涵量与生命体验的遗传信息单位,被诗人常常用来沟通历史精神与现实生活。”[5]姚合借用嵇康、刘伶典故,一方面出于崇古知音心理,另一方面也是用典寄寓其县居时期对县吏职务的反抗和对自由姿态的渴求。
姚合县居诗人物意象的第二类是作为社会身份的人物意象。这类人物意象在姚合县居诗中出现了十八次,他们没有被明确其具体人名,而是以模糊的社会身份或精神形象出现。这些社会身份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隐逸形象,如《武功县中作》其八的“野客嫌知印”、其十二的“野客教长醉”、其十八的“野客嫌杯小”等。第二种是宗教形象,如《武功县中作》其十二的“高僧劝却归”、《游春》其十二的“山僧见亦狂”等。第三种是亲朋形象,如《武功县中作》其八的“家人笑买琴”、《闲居遣怀十首》其二的“亲朋笑我疏”等。第四种是功名形象,如《武功县中作》其三十的“拜别登朝客”、《游春》其十二的“朝客闻应羡”等。在四种人物意象中,以“野客”为中心的隐逸形象其心理功能在于引导姚合归依于自然本性,超脱县吏俗物,如“野客嫌知印”“野客教长醉”等都是呈现出远离功名浮华而心灵舒展的山林隐者对县吏职务和现实状态的游离,姚合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也必然生成与之相应的归隐之思。同时,以“朝客”为中心的功名形象则以对照方式显现出姚合对功名仕途的否定,如“拜别登朝客,归依炼药翁”鲜明表达了诗人对“登朝客”的排斥,而选择“归依炼药翁”作为县居人生的方向。野客和朝客这两种人物意象在姚合县居诗中构成一种文化张力,隐喻着姚合内心精神的困境状态。
如果说“野客”只是从社会交游角度来塑造姚合的内心趋向,那么“东山客”就是姚合在县居诗中直接的自我认定。在姚合《武功县中作》其十五中云:“谁念东山客,栖栖守印床。”“东山客”用谢安典,多突出高蹈隐逸之义。姚合自认为“东山客”,其内涵正与“野客”相呼应,意味姚合亦以“野客”自称。在其县居诗中,姚合多有“青山”这一意象,如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绿衣”、其二十“旧国萧条思,青山隔几重”、其二十八“长忆青山下,深居遂性情”等。在这里,“青山”成为姚合处于县吏困境的人生之思,它是姚合对过去应举之前人生状态的概括。但随着姚合进入县居生涯,被繁杂政务所缠绕的的不自由感更为强烈,所以他一遍遍说“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其七)、“何年得事尽,终日逐人忙……人间长检束,与此其相当”(其十五)。一边是内心对自由性情的回顾与渴望,一边是身处县吏的检束苦闷,从而最终构成诗人仕隐冲突的心灵结构。
(二)骑马与杖藜:姚合县居诗主体行为中的仕隐冲突
姚合仕隐冲突的心灵结构还表现在其县居诗中所呈现的主体行为。行为是人类情感的外在姿势,苏姗·朗格在《情感与形式》中说:“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6]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可见的具体化的行为来寻找行为者内心的变化轨迹。
在姚合县居诗的诗人行为中,我们首先注意到“骑马”和“杖藜”这两个行为。《武功县中作》其十八云:“闭门风雨里,落叶与阶齐。野客嫌杯小,山翁喜枕低。听琴知道性,寻药得诗题。谁更能骑马,闲行只杖藜。”在这首诗中,“闭门”“落叶”“野客”“山翁”“听琴”“寻药”和“杖藜”等意象和行为对诗歌的塑造具有相同的推动方向,从而统一经营出一个清淡闲雅的生存环境。然而“骑马”这一行为成为这首诗的杂音,从而被诗人以“谁更能骑马”的方式对其进行排斥,但最终在文本中形成“骑马”和“杖藜”的行为对抗。骑马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人物行为,其在政治语境常常与政治雄心、功业梦想相关。《宋书·刘义庆传》:“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世路艰难”无疑是一隐含着政治风刀霜剑的隐晦词语。刘义庆为了避祸远害而“不复骑马”,其实就是对政治追求的放弃。此刻姚合言“谁更能骑马”,意味对政治仕途的消沉乃至放弃,选择“杖藜”作为人生未来的行为,所以姚合在《武功县中作》其一写道:“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将蕴涵政治色彩的马放置于象征自由的山鹿旁,这也就鲜明体现了姚合内心因仕隐冲突而对未来人生的设计。
为了消解内心的仕隐冲突,姚合在县居诗中强化了那些代表隐逸闲适精神的行为。我们可以梳理出众多具有相似功能的人物行为,如其四的“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其九的“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其二十一的“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等等,在这些行为中,诗人寻药种莎、移花买石、携枕醉卧、闲行钓鱼,竭力塑造一个内心平和、精神萧散的高人形象。但现实生活中,姚合又必须承担县吏具体职务,还是需要“终日逐人忙”(其十五),还是需要“端坐吏人旁”(其二十一),还是需要“青衫迎驿使”(其二十六),还是需要“焚香开敕库,踏月上城楼”(其二十七),真实的职务行为和内心的自由姿态在这里构成了仕隐冲突的声响。因此从根本上说,诗人试图用这些外在行为来消解政治前途暗淡带来的苦闷,它们依旧是姚合身处卑官而心事寥落的精神表现。
三、儒道思想与姚合县居诗中的仕隐冲突
自魏晋以来,儒道互补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常见的精神结构,至唐宋,又有向三教融合发展的趋势。然就个体的生命成长和精神发展来说,儒道互补并非其最初的精神结构。在传统文人的青少年教育中,儒家文化的系统教育和思想浸润成为文人在家庭成长乃至初入社会时期最为主要的内容,儒家精神构成了传统文人在发展初期最为主导的思想力量。只有到文人进入社会深处,心神与社会、政治、国家产生密切关联时,道家或其他流派思想则有可能成为其思想的新生力量,并和儒家思想构成一种精神张力,影响文人的行为趋向。因此,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从儒道冲突向儒道互补是传统文人塑造精神世界常见的路径。毋庸置疑,姚合的精神发展也具有这样一条路径。
(一)多元力量与姚合的儒学素质
姚合初入社会时期,正是中唐儒学复兴之时。安史之乱的发生促使唐代文人真正以务实的精神去观察社会、阐释国运,以啖助、陆质为中心的春秋学派的崛起及其对世风、士风的影响成为贞元、元和时期儒家复兴的关键符号。姚合身处如此卓荦腾跃的时代,自然受其熏染。从姚合的诗歌表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姚合的应举、入幕等行为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趋向。姚合在此时有自觉的“士”意识。在《送王求》诗中云:“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送张宗原》诗云:“士人甚商贾,终日须东西。”《过张邯郸庄》诗云:“时清士人闲,耕作唯文词。”士人作为春秋以来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建设者和传播者,其所具有的天下观念、家国情怀和生民意识成为儒家文人的主要精神表征。姚合以“士”自居,蕴藏的正是其渴望经世治国、参与社会的政治追求。且其政治行为在此时表现出来的行为目的也具有儒家所标举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在《从军行》中写道:“鹰鹘念搏击,岂贵食蒲肠。”诗人以“鹰鹘”为象,表现其不以个人私欲的满足为政治目标,而心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杜甫《画鹰》)的政治抱负。
传统儒家思想在国家层面主张尊王权、强一统,这种思想也在姚合身上有所体现。唐代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王权渐有衰微之象,地方强藩颇有割据之心。唐德宗因奉天之难,调整中央政府对藩镇的政策,从此施行姑息之政。而至宪宗始欲制僭平叛,复振王权。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中,姚合亦当受其影响。姚合在《寄狄拾遗时魏州从事》诗中云:“主人树勋名,欲灭天下贼。”又在《从军行》中说:“又无远筹略,坐使虏灭亡。”《剑器词》其三:“破虏行千里,三军意气粗。”在诗中,姚合称那些背离中央、意欲割据的藩镇为“贼”和“虏”,又在其《剑器词》其一中以“积尸川没岸,流血野无尘”的战争场面来写中央政府对藩镇的用兵,而在《剑器词》其三结句云:“元和太平乐,自古恐应无。”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姚合赞颂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并认为在削弱和打击藩镇的基础上,元和时代才迎来“太平乐”。元和十四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被杀,淄青平,姚合作《闻魏州贼破》诗云:“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烟雾扫开尊北岳,蛟龙斩断净南河。旗迥海眼军容壮,兵合天心杀气多。从此四方无一事,朝朝雨露是恩波。”在此诗中,姚合认为这场战争是“兵合天下”,魏州破从而“尊北岳”,正是体现其尊王权、强一统的儒家思想。
姚合的儒家意识除了受儒学复兴、政治格局变迁等因素影响之外,还与其家族文化有密切关系。姚合出身吴兴姚氏,这一家族崛起于初盛唐之际,自姚懿至姚崇,家世渐显,姚合即为姚元景曾孙,名相姚崇曾侄孙。姚崇作为姚氏最为关键的家族领导者,其生命禀赋和政治精神对其家族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云:“公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真率径直,而应变无穷。”[3]2601可见儒家礼法德行成为姚氏家族重要文化标准。姚崇著《五诫》,其虽围绕吏治强调从政为官之道,亦可见吴兴姚氏崇尚务实、立主公平廉洁的家族文化。姚合在其文章中多有呼应其家族文化之处,姚崇在《冰壶诫》中云:“玉本无瑕,冰亦至洁,方圆相映,表里皆澈:喻彼贞廉,能守其节。……故君子让荣不忧,辞满为珍,以备其德,以全其真。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冰壶是对,炯诫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3]2365在这里姚崇认为君子当表里清澈,不求浊富,当安贫守道,这种观念无疑具有浓厚的儒家富贵观念和政治思想。姚合《新昌里》诗云:“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近贫日益廉,近富日益贪。以此当自警,慎勿信邪谗。”姚合亦以比兴之法表达其对贪富的批评,主张安贫廉洁,这种思想正是和姚崇观念一脉相通。
(二)个体本性与姚合的道家精神
儒家思想多强化个体的社会价值和群体意义,从而要求个体生存克己复礼、舍身成义,这就往往促使文人以社会意义和国家使命为个体追求,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损害其个体本性的自由表达,加重其生存的沉重感和悲剧性。姚合在县居诗中经常提及其本性,常用“疏”“拙”“僻”等字言其性情。如《闲居遣怀》其二:“情性僻难改,愁怀酒为赊。”其十:“拙直难和洽,从人笑掩关。”又如《武功县中作》其六:“性疏常爱卧,亲故笑悠悠。”《游春》其十一:“自知疏懒性,得事亦应稀。”等等。姚合不仅界定自身本性为疏懒野僻,同时认为这种疏懒野僻之性与政治事务管理之间矛盾,如《武功县中作》其二云:“方拙天然性,为官是事疏。”其二十九云:“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确实,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疏懒、拙直、野僻等性格并非政治管理所需的人文素质,复杂多变的吏治不仅需要责任心、胆量,还需要灵活性、忍耐心等等。正是自我认定的疏直本性与繁杂吏治之间的对立,导致姚合在县吏时期的精神开始由儒家务实向道家无为嬗变。在县居诗中,姚合开始反省其应举入仕的人生选择,并常有否定性的评价。在《武功县中作》其八中云:“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所谓“道心”,当指自由独立的心灵,正是因应举入仕的人生判断,从而导致自由的衰减。后又言:“只应随分过,已是错弥深。”更是直接认为入仕从政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种人生反省其深沉本质是对自身儒家意识的意义否定,从而逐渐显露其对道家文化的接近。其道家意识首先表现在姚合强调生存行为以实现性情为目标,从而保持精神的自适从容,如《闲居遣怀》其四云:“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他认为宁愿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要实现本性的舒展。其次,在县居吏治中,姚合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勤于吏治的儒家官员形象,更多采取疏懒无为的政治参与姿态。但这种疏懒并非弃职不管,而是以一种“斋心调笔砚,唯写五千言”(《武功县中作》其十)的方式追求“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章五十七)的吏治效果。
因此,我们在姚合的县居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姚合一方面在感慨政治仕途的不顺利,另一方面又对当下的政治选择有否定认识,从而渴望重返青山,这种因儒道思想在个体意识中的矛盾也就造成了姚合在行为、心理上的仕隐冲突。直至姚合出任金州、杭州刺史,随着政治仕途的平顺,社会地位的提升,姚合才从仕隐冲突中走出,真正生成了儒道互补、仕隐相契的圆融状态。
[1]姚合.姚合诗集校注[M].吴河清,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3.
[3]周绍良.全唐文新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4]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5]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46.
[6]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09.
[责任编辑:岳林海]
Conflict between Career and Seclusion in County Life Poems of Yao He
ZHOU Heng
(School of Literary Art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China)
County life was an important space of political survival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Yao He. In the earlier time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Yao He served as the county magistrate of Wugong, Wanli, and other counties, and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county life po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oems, we can watch his inner contradiction about career and seclusion at his county magistrate stage thus produ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career and seclusion in hi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mental state. The generation of this spiritual conflict not only related to Wuxing Yao’s family, the individual nature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Yao He;county life poem;career and seclusion;Confucianism and Taoism
2016-08-3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姚合题材诗与大和文学研究”(2016SJB750005)
周衡(1975-),男,江西吉安人,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2096-1901(2016)06-0027-06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