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更路簿》的“更”
2016-02-08逄文昱
逄文昱
(大连海事大学 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6)
试说《更路簿》的“更”
逄文昱
(大连海事大学 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6)
“更数”是计量航海时代标示航线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其准确与否关乎远洋航海的成败。“更”是计时单位,被用于推算航程,在“标准航速”下,一更约可航行六十里。“更”的概念萌芽于南宋,元代经民间火长使用、推广,至明代普遍应用于远洋航海。《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应是在“标准航速”下从甲地航达乙地所用时间。不同的海道针经所载更数存在差异。每次航行,火长均需根据实测航速重新推算更数。南海《更路簿》与《海道针经》一脉所出,但有自己的特点。
更路簿;海道针经;更;定更法;计量航海
我国古代的航海史,按其导航技术,可分为模糊航海时代与计量航海时代,两个时代以航海罗盘的应用为分野,时间大约在北宋末至南宋。模糊航海时代,“船师”凭经验和天文、水文等知识引领航船,做近岸或短距离的越洋航行。计量航海时代,火长掌管罗盘,用航海图定位,以海道针经导航,大大降低了对可视航标的依赖,长时间长距离的远洋航行有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从而使我国古代的航海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所谓海道针经,即计量航海时代的航路指南,航路由针位和更数两大基本要素标示,古代航海家普遍习惯以针言之,称为“针经”,而海南渔民则习惯以更言之,称为更路簿。针经与更路簿实为一脉,只是称谓有别。
针位表示航向殆无异议,而关于“更”,学界曾进行过颇多探讨,至今争讼不断。朱鉴秋[1-2]、向达[3]6认为“更”是里程单位;王振华、范中义[4],南炳文、何孝荣[5]以及孙光圻、王莉[6]等认为“更”既是时间单位也是距离单位。陈希育[7]认为更既表示时间,又表示速度,还表示里程。各种意见既有相同,又有不同。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而古代航海为什么要以“更”做为计量单位?火长为什么要在航行前进行“定更”?笔者试图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研讨,以向方家求教。
一、“更”对于计量航海的重要性
指南针应用于海船导航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末年。朱彧记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8]徐兢记曰:“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9]130至南宋时期,海船上出现了针盘(见图1)及专门掌管针盘的重要角色——火长,“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之命所系也”[10]。
火长如何应用针盘进行导航?曾随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记载得十分清楚:“皆斲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必达其所。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11]可见,火长是从民间选取的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舵公,运用其所掌管的罗盘、“针经”与“图式”为航船导航。“图式”即航海图,为标绘有可航水域的水文、岛屿、航标和沿岸地形地物等要素,供目标定位使用的地图。据刘义杰考证,能够真正用于导航定位的航海图即《顺风相送》等文献提到的“山形水势”图[12],见图3。“针经”即“海道针经”,又有“针路簿”“针本”“针谱”等诸多称谓,海南渔民称之为“更路簿”,为航海罗盘应用于导航之后以针位和更数记录的航线集合,见图2、图4。针位即以航海罗盘上的方位字指示的航向,有“单针”(如“单乙针”)和“缝针”(如“甲寅针”)两种形式;更数用于计量两地之间航行时间和距离。从某地起航时,火长按照海道针经标明的针位,用罗盘确定从甲地航往乙地的航向,然后即取直线航行,以针经上记载的“更数”计量航行时间,推算航行距离,到乙地后,还需要参照“山形水势图”来加以确定,看山屿形状和水文状况是否与图上描述一致。如此即完成了一个航程的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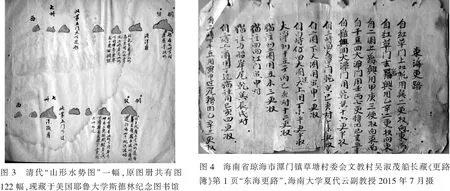
二、“更”是用于推算航程的计时单位
那么,“更”作为计量航海时代一个如此重要的计量单位,它究竟是计量什么的?远洋航海为何要引入“更”作为计量单位呢?
关于“更”与“里程”和“时间”的关系,明清文献多有类似记载。明代海道针经《顺风相送》记曰:“每一更二点半约有—站,每站者计六十里。”[3]25清周煌引《指南广义》记曰:“一更六十里,以沙漏定之。”[14]655清陈伦炯记曰:“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毎更约水程六十里。”[15]14正是“一更六十里”的记载,让明清以来的许多文人学者弄不清楚“更”到底是里程单位还是时间单位。清徐葆光的困惑颇具代表性:“海中船行里数皆以更计,或云百里为一更,或云六十里为一更,或云分昼夜为十更,今问海舶伙长,皆云六十里之说为近。”[16]432
那么,“更”到底是个什么单位?我们不妨从“计更”方法进行考察。徐葆光记:“今西洋舶用玻璃漏定更,简而易晓,细口大腹玻璃瓶两枚,一枚盛沙满之,两口上下对合,通一线以过沙,悬针盘上,沙过尽为一漏,即倒转悬之,计一昼一夜约二十四漏,每更船六十里,约二漏半有零。”[16]432周煌引《指南广义》也有类似的记载:“(更)以沙漏定之,漏用玻璃瓶两枚,细口大腹,一枚盛沙满之,两口对合,中通一线以过沙,倒悬针盘上,沙尽为一漏,复转悬之,计一昼夜约二十四漏,每二漏半有零为一更。”[14]655可见,至清代康乾时期,船上普遍以沙漏计时,一昼夜二十四漏,约二漏半为一更。刻漏计时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使用的是“水漏”,大约在明代,西方“沙漏”传入后,因更适合海上环境,逐渐被我国海船普遍采用。而在沙漏计更之前,远洋海船曾以焚香计更。郑若曾说:“一日一夜定为十更,以焚香几枝为度。”[17]很明显,“更”是一个时间单位。黄叔璥明确反对将“更”作为里程单位:“志约六十里为一更,亦无所据。”[18]872来集之说得更加清楚:“老于海道者,其所凭在针、舵、更三者而已。盖火掌(注:原文如此)视针,长年运舵,香公计时,三者缺一不可,必三人专心协力而行……一日一夜定为十更,以焚香几枝为度。”[19]由此我们知道,香公除负责日常奉祀海神外,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船员,担负焚香计时之责,“更”无疑是时间单位。
“更”作为时间单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国古代很早就用“五更”来计量夜晚的时间。船行海上,自然也需要计时。而航海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为统一、方便计,舟子便将一昼夜定为十更,“夜五更,昼五更”[20]。然而,我们知道,我国古代惯以时辰计时,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算下来“每更约一时辰之久”[21]408,既然如此,远洋航海为何不直接以时辰为计时单位呢?这是因为,在“标准航速”下,一更六十里与陆上驿站里距相同,便于计量水程。
总之,不管以刻漏还是焚香为计,“更”首先是时间单位,但“更”与航程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换算关系,而这种换算关系的确立乃是出于远洋航海以时计程的需要,而“更”只有与航程联系起来才更有实用意义。
由此,“更”可做如下定义:“更”是计量航海时代远洋航行的计时单位,通常一昼夜分为十更,在“标准航速”下,每更约可航行六十里。《更路簿》上所载更数,理论上应是在“标准航速”下的从甲地航达乙地所用时间,但往往存在误差。
三、“更”是如何引入计量航海的
关于为什么要引进“更”这样一个计量单位,清康熙年间曾任南澳总兵的陈良弼说得十分清楚:
大凡陆地往来,有里数有程站,可以按程计日,分毫不谬。惟洋船则不然。盖大海之中,全凭风力,若风信不顺,则船势渐退,此不可以日期定也。汪洋所在,杳无山影,非同内洋,有涯岸按泊者,彼此不可以程站计也,故设为更数以定水程。[13]372
可见,因为海船的越洋航程既“不可以日期定”,也“不可以程站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引进“更”作为计量单位。陈良弼进一步阐述:
今虽泛泛言及更数者,亦皆因愚以诱愚,何曾深知其微奥耳!而有甚者,以按边之船,亦询及更数。夫既有可泊有程可考,举眼见之,不问又安用此无稽之形影乎?[13]372
“更”用于计量深入大洋的远洋航行,是因为航程中没有可靠的航标和驿站里程可供参考,而近岸航行也以“更”计,则为“因愚以诱愚”,多此一举了。清人李增阶也说,“外国水程论更数驶船”[21]408。所谓的“外国水程”,即通往外国的远洋航海。在海道针经确定普遍应用于导航后,近岸航线还是惯用日、月或里数计程,如元代北洋漕运航线[22]和清代的“海疆道里表”[23]。
那么,“更”是如何被引入计量远洋航海的呢?
在针盘应用于导航之前的模糊航海时代,历代航海家已经开辟出诸多航线,其中甚至有长达万里的远洋航线,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汉使纪程”和《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唐人贾耽所述“广州通海夷道”。模糊航海时代,海师(或称舟师)凭借所掌握的地文、水文、天文、气象等知识以及多年航海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为船舶导航。由于毕竟缺乏可靠的导航工具,海师无法长时间脱离陆域航标进行导航,所以这一时期的航线大多是近岸航线。但是,在无数次的航海实践中,一些海师为了能缩短航程,勇敢地进行了跨洋航行的尝试并获得了成功,或者仅是由于遭遇狂风等不测天气而意外走通了一条便捷航线,于是,一些跨洋航线在罗盘应用于导航之前就已经被有经验的海师掌握了。如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在海师何蛮的带领下,朱宽率隋朝官方船队第一次航达台湾。但是当时的海师无法将这样的跨洋航线准确纪录下来,原因有二:其一,难以描述方位;其二,难以计量航程。无法记录也就不能为他人导航所用,因而该航线只能由开辟它的海师亲自导航。
针盘应用于航海导航之后,首先解决的是精确指示航向的问题。原本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位被细分为至少四十八个方位,航向准确不再成为问题。但航线的记录只有针位是不行的,航程的准确计量亟需解决。
其实在模糊航海时代,人们已经对航程进行记录。最初以日、月计量,如“汉使纪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24]晋法显东归,也是以日、月计海程:“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而今已过其多日,将无僻耶?”[25]宋代航海,从文献看,以日、月和里数计程兼有,如《武经总要》记载的广州出海航路,“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蠉州国界】,又南三百里至陵东山【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26]在针盘确定应用于航海的南宋,还是惯以日、月计程,如“南毗国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27]29;“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真腊国)”[27]7。
但是,深入远洋的航行无法以驿站为参照,因而不能像近岸航线那样以里数计程;又由于帆船航行受风力、洋流等影响,航速不可控,也不能简单地以时间计程,且月、日作为计程单位太不精确。远洋航海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方便使用而又更为精确的计量单位,聪明火长们经过探索,对传统的计时单位“更”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只是作为“舟子秘本”,很长时间不见于文献记载而已。
在明代流传下来的众多海道针经中,“更”已经作为计量单位被广泛使用。《顺风相送》说,“每一更二点半约有—站,每站者计六十里”[3]25,明确表明“更”与“站”之间的关系,而每站六十里是参照了陆上驿站之间的距离。我国的驿传制度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商代,唐宋以降,更为完善,“唐代二驿之间里距为三十里,宋驿增加到六十里”[28]。可见,“一站六十里”的概念当形成于宋代。然而宋之前,我国的递运机构有“驿”、有“亭”、有“铺”,而“站”则出现在元代。站赤,来源于蒙古语jamuci的音译,即驿传,《元史·兵志》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29]元代站赤里距相对于宋制发生较大变化,近者二三十里,远者三十五里至四十五里[30]。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即大力整顿全国驿站,并将元代习称的“站”一律改回为“驿”。
由此,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更”作为计时单位,是在针盘应用于远洋航海后,为满足精确计程的需要,参照宋驿里距,以传统的“日月计程”为基础,被创造性地加以利用,经过元代民间火长的使用、推广,约定成俗,至明代普遍应用于远洋航海。
四、定更法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知道,“一更六十里”,是在“标准航速”下实现的。那么这个“标准航速”是如何确定的?这就需要火长了解和掌握“定更法”,即行船之前对航速的测定。
关于“定更法”,很多文献都有记述,且以黄叔璥的记载为例:“船在大洋,风潮有顺逆,行使有迟速,水程难辨,以木片于船首投海中,人从船首速行至尾,木片与人行齐至,则更数方准;若人行至船尾而木片未至,则为不上更,或木片反先人至船尾则为过更,皆不合更也。”[18]872
此种方法是通过船、人、木片的相对位置来确定船行速度。将木片从船头投入海中,船向前行,人往船尾快走,木片亦与船作相对运动,漂向船尾。如果人与木片同时抵达船尾,即为“标准航速”;如果人先于木片到达船尾,表明船行或遇逆风逆流,航速偏慢,称为“不上更”(亦称为“不及更”);如果木片比人先到船尾,则表明航船或遇顺风顺流,航速偏快,称为“过更”。“不及更”和“过更”都“不合更”,即不符合标准航速。
可见,所谓定更法,即以实测得到的航速推算航行时间的方法。一条航线的里程是恒定的,航速发生变化,航行时间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根据航速推算实际航行时间。“定更”正说明“更”是个变量,定更法进一步证明了“更”是时间单位。
《海道针经》上所载两地之间的更数,应是标准更数,即在“标准航速”下从起航地到达目标地所用的时间。而在“标准航速”下,一更可航六十里,很容易得出两地之间的里程。然而,海上航行,风力、水流等因素并非恒定不变,因而并不能保证始终以“标准航速”航行,于是,海道针经上的更数——两地之间的标准航行时间就一定会出现或大或小的误差。这就需要火长在行船之前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定更”,即“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15]14。如果测定的结果为“不及更”,则要根据船、人、木片的具体位置,在《更路簿》所载更数上加上若干更;如果测定结果为“过更”,则要减去几更。当然,需要火长凭经验来确定增减的更数。
在航行实践中,一次“定更”显然难以确定全程航速,因为水流、风力等因素时时在发生变化。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多次测定、修改更数,以尽量达到准确。“定更”需要一个前提——“利风”,除逆风外均可称为“利风”。远洋帆船靠风作为自然动力,由于中国古代海员高超的驶帆技术,“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9]130,逆风不行船,自然也不能定更。一般来讲,“利风”则顺流,但有例外情况。比如在地转偏向力作用下,虽然“利风”,则可能是逆流,《顺风相送》特别指出这种情况:“如遇风船走潮水却向潮头涨来,此系是逆流。柴片虽丢顺水流向,后来必紧,不可使作船走议论。”船虽顺风,而遇逆流,木片随海流向后漂流速度越来越快,但这不能反映真实的航速,所以一再强调:“凡行船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古云先著风汛急慢,流水顺逆。不可不明其法。”[3]25
五、海南《更路簿》的特点及结语
海南渔民传承下来的《更路簿》与习称的海道针经,其实质别无二致,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海南《更路簿》针位的表述与《海道针经》略有区别:针经的“单针”,《更路簿》习惯用通过罗盘轴心的直线上的两个方位字表述,比如针经的“单乙针”,《更路簿》则表述为“辛乙针”;针经的“缝针”,《更路簿》习惯用一对相邻的“单针”表述,比如针经的“庚酉针”,《更路簿》表述为“甲庚卯酉”。有的《更路簿》习惯于在针位前加一个“向”字,如“向巽辰”“向午”等。其二,由于海南《更路簿》主要用于出海捕鱼,涉及海域远比远洋贸易为小,航程和时间也短,因而有条件在针位和更数上进一步精确:针位方面,每个方位字(7.5°)再加4线,即将该方位5等分,每线表1.5°,如“自老牛老至六门驶壬丙兼二线巳亥五更收对东南”[31];更数方面,常有“半更”之数,甚至划分更细,如“一更二”“三更一”等。此外,或许由于海南渔民对南海海域岛礁及水文状况了然于胸,所以并不需要用航海图来辅助定位。
中华民族的航海史,同时也是一部航海技术的发展史。以针盘导航为标志的计量航海时代,在“不可以里计”的茫茫海道上,火长们经过实践探索,另辟蹊径,运用计时单位“更”来计量航程,巧妙地解决了远洋航行精确计程定位的难题,使远洋航行更具效率也更加安全,从而推动航海事业迅猛发展,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体现了中国古代航海家非凡的智慧,为中华民族航海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
[1] 朱鉴秋.我国古代海上计程单位“更”的长度考证[J].中华文史论丛,1980(3):202-204.
[2] 朱鉴秋.海上计程单位和深度单位[J].航海,1981(1):10.
[3]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 王振华,范中义.对我国古代航海史料中“更”的几点认识[J].海交史研究,1984(总6):68-73.
[5] 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4.
[6] 孙光圻,王莉.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技术文明比较研究[G]∥王天有.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6.
[7]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166.
[8] 朱彧.萍洲可谈:卷2[M].李伟国,点校∥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49.
[9]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G].虞云国,孙旭,整理∥全宋笔记:第3编第8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0] 吴自牧.梦粱录:卷12[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112.
[11] 巩珍.西洋番国志[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5-6.
[12] 刘义杰.山形水势图说[J].国家航海,2015年(1):88-111.
[13] 陈良弼.水师辑要[G]∥续修四库全书:8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 周煌.琉球国志略:卷5[G]∥续修四库全书:7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上卷[G]∥厦门海疆文献辑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16]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1[G]∥续修四库全书:7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 郑若曾.江南经略:卷8上[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4.
[18]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1[G]∥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 来集之.倘湖樵书·樵书二编:卷9[G]∥慎俭堂刊本,1788:22.
[20] 谢杰.虔台倭纂·倭利附倭针:上卷[G]∥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240.
[21] 李增阶.外海纪要[G]∥续修四库全书:8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 赵世延,揭傒斯.大元海运记·漕运水程:卷下[G]胡敬,辑.∥续修四库全书:8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3] 赵文运,匡超.山东省胶志·疆域志·道里·海疆道里表:卷4[G]∥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6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24] 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71.
[25] 章巽.法显传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1.
[26] 曾公亮.武经总要·广南东路:前集卷20 [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
[27]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志国: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8]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
[29] 宋濂.元史·兵四·站赤:卷101 [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83.
[30] A.J.H.Charignon. 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393-394.
[31] 夏代云,卢业发,吴淑茂,等.《更路簿》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221.
[责任编辑:孙绍先]
A Brief Account of “Geng” in Geng Lu Bu
PANG Wen-yu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
“The number of Geng” is one of two basic elements to indicate sea routes in the era of measure navigation and its accuracy affects the success of ocean voyage. As a time-measuring unit, “geng” is used to calculate sailing distance, which amounts to around 30 kilometers within one geng at a “standard speed”. “Geng” as an idea appear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used and promoted by the folk pilot in the Yuan Dynasty till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to the ocean voyag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geng mentioned in Guide to Sailing Directions is supposed to be the time duration sailing from the location of A to that of B at a “standard speed” while that number varies in the different Guides to Sailing Directions. The pilot must re-calculate the number of geng each voyage according to the sailing speed measured on the spot. WhileGengLuBu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shares the same origin with Guide to Sailing Directions, they have their own properties.
GengLuBu; Guide to Sailing Direction; Geng; geng-determining method; measure navigation
2016-11-07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3132016363) [作者简介] 逄文昱(1971-),男,辽宁岫岩人,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航海历史研究。
K 12
A
1004-1710(2016)06-00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