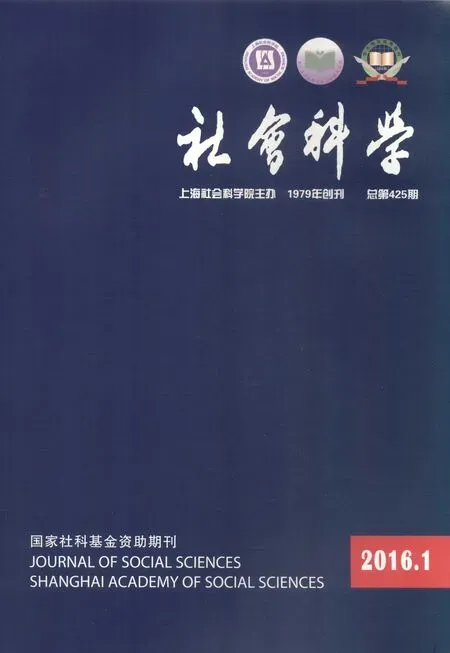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
2016-02-05李向平
李向平
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
李向平
亚洲秩序与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目前执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最值得面对的问题。亚洲社会数十个国家大多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及信仰方式,缺乏主导的价值体系或信仰结构,这无疑构成了建立当代亚洲文明秩序及命运共同体要谨慎面对的问题。超国家命运共同体或亚洲文明秩序的建立,最终要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国际社会的交往规则、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这种秩序既要包含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传统,同时又要超越这些宗教信仰传统,建构一种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共享的普适价值观。为此,建构亚洲秩序中不同宗教交往之间的信仰共识与共同平台实为重中之重。
亚洲秩序;国际社会;宗教交往;共同信仰;价值共识
一、 亚洲秩序是否可能
1970年前后,伴随着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亚洲地区呈现了“儒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致力于一种新型亚洲秩序及其价值观的建构;同时还有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东亚佛教文化圈等不同提法,讨论亚洲秩序及其主导价值体系的问题。如今,“一带一路”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则又把这一具有历史时代意义的问题重新提出,值得深入研究与讨论。
亚洲社会具有多神教、泛神论与无神论的信仰传统,虽然不像历史上一神教的欧洲和中东,为了一己信仰而大打出手,甚至发生直接的宗教战争,但亚洲各国不同的宗教背景及其信仰方式,却是建立亚洲文明秩序及其命运共同体应该谨慎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亚洲各民族国家本身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信仰特征,这就促使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是否有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既要包含亚洲各国的宗教信仰传统,同时又要超越这些宗教信仰传统,建构一种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宗教信仰都能够共享的普适价值观。
当代“国际社会”大多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构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对现实(尤其是权力和领土上的现状)的判断,代表了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诉求。”*[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76页。换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圭臬,一方面,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则是构成了世界性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该体系也开启了近代以来各个国家先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大门,在由地域、人口与主权整合为一体而形成的国家之中,不同社会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民族”,开始把国家与民族、乃至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由此便在国家政治与民族宗教信仰之间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张力,促使那些在近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成立的国家,几乎都处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式的尴尬处境。
如果说国际政治具有国际规范,民族宗教文化则难以一体化。*关凯:《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就亚洲而言,宗教多种多样。亚洲与欧洲不同,历史上就没有一个类似罗马帝国那样的共同帝国,也没有基督宗教那样的统一宗教。今日的亚洲各国,存在着各种宗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东亚大乘佛教,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还有韩国的基督教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在不同的时代之中,不同宗教各领风骚。
亚洲各国的民族宗教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局限于宗教交往及其信仰认同,还会有宗教外的交往关系渗透于其中。而这种形式的宗教交往,往往不会局限在一两个宗教体系之内或之间的交往。它们不得不在宗教交往关系之外,寻找一种能够使宗教交往得以顺利展开的非宗教性社会、文化基础。
在这种宗教交往结构中,宗教交往的目的不是简单的理论对话,亦不是基于信仰本位主义而强化自己的信仰认同,进而期待交往的对方皈依自己信奉的崇拜对象。这种宗教交往关系,其实并不在乎交往的对方能否成为自己的信仰同道。双方可以在充分保持自己的原初信仰基础上进行宗教交往或信仰互动,因此更加需要一个超越了民族、宗教乃至国家的价值体系,公认的普适性价值。
这就是说,不同宗教的信徒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的挑战是,他们需要在更大共同体中寻找和发展他们的共同身份。无论基督徒还是印度教徒,一个人一定是这个更宽广的宗教共同体的一部分。*[美]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而非在宗教交往之中去寻找一个貌似力量更加强势的宗教信仰,亦不是一个人在参与宗教交往的同时,一定要成为另外一个宗教信徒,发生信仰改宗的现象。“如果每一个参加宗教对话的人都能牢记:每一个正统的教徒在与其他人巧遇时,都有一个把真正的超越引入自己生活的机会,那么这种对话就会成为一种手段或途径,借此可以打破那种狭隘的、受文化局限的思想格局。……对话的作用绝不是要把所有不同的信念与宗教观念全都归结为一个立场,或一种观点,而是要让不同的神学与不同的哲学竞相吐艳。”*[美]斯特伦:《人与神》,金泽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交往结构,或当下的多民族与多宗教间的交往结构中,最好不要渗透来自任何一方的权力关系,否则就会影响了宗教交往结构中的公共与普适的意义,影响了民族、宗教交往结构中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呈现。
二、 信仰认同的制度模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宗教的公共性再次得到强调,宗教伦理的公共功能也再次得到突出,甚至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对宗教交往也赋予了特别的伦理期待,而各类宗教也希望通过各种宗教公益活动、参与各种事务来影响社会。
由于宗教与其他社会系统一样,属于一个社会子系统,所以,凡是宗教要体现自己的价值系统以及对于社会的伦理影响、道德功能的时候,它就必然要越出宗教的固有框架,对非信教公民、非宗教社会形式发生影响,由此凸现了宗教的公共合法性问题。
根据韦伯的“理性化”命题*[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宗教在现代社会之中作为个人社会意义的价值体系本身,乃是与公共领域无关的事情*宗教的私人化,使现代社会摆脱了传统宗教及其组织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使传统宗教具有了新的崇拜性质,宗教成为了私人的崇拜,被理解为私人精神和自我情感的事情。。因此,宗教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是宗教返回自身的过程。因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已不需要宗教为其提供合法性了,社会本身能够自行提供其所需要的合法性。整合现代社会的规范秩序已经与超越性的神圣世界日益疏离,其价值基础甚至已经不在于价值世界,更不用说宗教世界观及其价值体系了。
所以,就宗教与社会的交往关系、个人信仰认同与社会结构而言,仅仅是宗教交往、信仰认同本身,就难以成为一个核心分析概念。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宗教及其伦理价值系统,都难以自动实现自己,而是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机制”,尤其是在各种宗教及其伦理遭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将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基点是制度化”*[美]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张明德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要求,促使现代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道德,而是制度与结构。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这个结构就是整合在一起的规则和资源。规则是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是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资源则是权威性资源与分配性资源的结合。*[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页。它们的不同组合与不同的分配,制约着不同结构的形成。
基于这一论述,宗教及其对社会的道德影响甚至是伦理制约,并非由个人伦理责任简单地产生或构成,而是由一群具有特殊资格的行动者制造,并在建构意义过程的资源里被组织,通过仪式化、归正及传承而得以维护,是各种宗教关系在时空状态中的稳定形态。这就决定了宗教伦理的局限,即其必须通过其相应的制度程序来加以表达,或者说,这需要一种现代社会中的“制度主义的宗教”。而宗教交往关系、信仰认同方法,似乎也应该借助于制度主义的宗教交往结构。
这里的“制度主义”概念,主要是指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中,应该予以特别关注的是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不仅塑造人的行为,而且也构建社会结构本身,应关心一个制度是如何形塑社会行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的过程。*谢立中:《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为此,新制度主义高度重视制度意义的宗教,就既存的仪式意义与制度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不少论著,大体以为,社会组织通过各种仪式,使某些价值观念或经济行为制度化、立法化,以确立或固定组织的某些重要事物,并促使它们得以长期维系。*Meyer J.W., Roman B.,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 83(2),1977.pp.340-363.就当代中国宗教信仰而言,比较内在于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义的信仰”来说,“制度主义宗教”则具有外在于或独立于个人或群体意识的“社会事实”的特征。所以,制度主义宗教又被认为是包括了既需要物质资源、又影响资源分配的行动者和组织,更加强调了社会生活建构文化的观点。*Wuthnow, Robert,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 Explorations in Cultural Analysi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7. p.15.
实际上,这种对制度意义的宗教的强调,比较其他宗教定义来说,它更加属于一个形构的概念。比较而言,宗教作为一种制度性的传统、文化、伦理,其社会交往功能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同,其社会化、公共性更容易得到体现。所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结构或宗教(社会)团体,其社会合法性的体现就非经制度化程序不可。这既是宗教交往关系影响社会交往结构的基本机制,同时也是对宗教、信仰认同方法影响社会传统方式的一个基本挑战。
三、 局部秩序与整体文明
现代社会的宗教组织,大都作为一个法人团体或社会组织而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宗教团体就是一种宗教行动领域,就是对一种行动领域的界定,乃至一种局部秩序(local orders)。宗教在现代社会之中作为个人社会意义的价值体系,其本身与公共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社会,实际上是由许多社会集团这样的局部秩序来组成的,宗教制度或宗教组织仅仅是其中的局部秩序之一而已。宗教交往仅仅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构成而已。
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之中,构成这些局部秩序的社会集团、团体组织,各有其权利主张。它们的权利主张,有些可以在其制度空间里通过博弈而构成协调,有些则有可能相互对立。为此,一个国家、社会中的社会团体,必须承担一个超局部的、对于社会整体的效忠责任。在它们追求的目标和运用的手段方面,都必须承受这一限制。它们都被镶嵌在国家共同体里,被保持在一个制度界限之内,形塑了社会秩序的多元性、重叠性等重要特征。
所以,在国内社会的存在形式之中,社会正义的问题是在两个层次上提出来的。一个层次是整个社会共同信奉的一般原则;另一层次是特定集团提出的特别要求。在一般原则的层次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不会出现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些原则。特别是像民主、平等、社会正义、言论自由这样的原则,只要它们仍然停留在社会集体奋斗的最终目标的抽象范围里,就不会引起危及国家稳定或社会和平的冲突。可是,一旦这些抽象概念被各社会集团利用,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这些原则就会成为社会冲突中的强大武器,构成对社会的极大挑战。*[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5页。
一名公民,可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多个社会集团,这些集团都会要求他对该集团效忠。但作为一位社会公民,他的社会行动也会促使他同时考虑对于所属的若干个集团的责任与义务。相应的是,一个宗教体系也可以作为某个社会中的社会团体之一,而一个宗教体系的宗教信徒也同样分属于不同的宗教体系。这些宗教集团、宗教体系,无疑都会要求该宗教的信徒表达他对该团体的责任或效忠。
但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要求,则希望社会团体成员或宗教团体信徒的社会行动,能同时考虑对于几个社会团体乃至一个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所以,某一宗教伦理的社会功能仅能够建构局部社会的道德秩序,难以抽象成为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原则。否则,亦将构成对一个社会的整体价值原则的挑战。
宗教交往及其信仰认同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只能作为国家、社会的局部社会秩序之一,才能发挥它对社会的影响。然而,这些局部秩序还要承受超局部的效忠原则的约束,这就是垂直维度层面对国家、社会的整体效忠,乃至于水平层面对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多层责任,以此来实现对于局部责任的超越。其中的垂直维度的效忠,易于养成封闭结构性的权力专制,多为传统社会;水平层面的多层责任,则大多体现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水平层面的多层责任的发展与成熟,一般而言能够冲淡或制约垂直维度的效忠。
正是在这个纵横交错、彼此制约的社会结构之中,“国家内部的所有冲突,在它们追求的目标和运用的手段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它们仿佛都被嵌入国家共同体这块细密的织物里,从而被保持在界限之内。与局部效忠的多元性、重叠性一起,国家效忠的限制与抑制作用,构成了造成国内和平的三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4页。。
因此,类似于宗教制度、宗教团体这样的局部交往结构及其交往秩序,至少可以包含如下三种特征:
1. 一个社会中的团体或组织,总是受到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社会宏观结构的影响,但宏观社会结构难以决定一个组织的具体特征,在同样的社会结构之下,不同的组织表现出各自不同特点,每个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组织是具体的、局部的社会秩序。所以,对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认识不能代替对具体组织的认识。
2. 组织中的人的活动是围绕着具体问题而展开的具体行动,问题不同,人的具体行动也自然不同。对于团体或组织的认识,必须结合具体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具体行动。
3. 由于每个行动都具有一定的“自由余地”,其行动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并由此导致了团体或组织行动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同一个具体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之中,在不同的行动者身上,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不同的具体行动。*Erhard Friedberg, Local Orders,Dynamics of Organized Action, 1997。另请参见翁定军《超越正式与非正式的界限——当代组织社会学对组织的理解》,《社会》2004年第2期。
处于这些局部秩序之中的信教公民,既属于一个宗教团体,同时又分属于其他不同的社会集团。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既可能冲突亦可能合作。然而,既是宗教信徒又是社会公民的多元化角色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这就决定了宗教的功能不能无限扩大,宗教伦理的制约就是一种局部的秩序。作为宗教团体或者信教公民,他们必须有所兼顾,在多元角色互不相碍的制度架构之中进行交往。“所以,社会不同成员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重叠倾向于缓和冲突,并把冲突限制在能够使社会成员同时扮演不同角色的限度内。”*[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3页。
因此,作为现代社会之中制度宗教及其信仰认同方法,就应当在一种秩序之中承受局限,意识到本宗教的特殊意义而非普遍价值,从作为国内一个社会子系统的组合及其冲突的多元化构成中,常常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组织效忠的相对性,进而充分了解不同组织或集团之间的本来就存有的冲突。
所以,“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并且必定具有法律的要素——确切地说有两种法律要素:一种与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之群体的社会程序有关,另一种则关系到宗教群体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体的社会程序”。而当代宗教的生命力,就不仅仅体现在将宗教的法律方面纳入其关于神圣事务的观念中,同时还要将当代社会的总体经验体现于法律的组织与程序中。这个秩序,不仅是指宗教团体内的组织和程序,也是指这些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更大社会中的组织与程序。*[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7、124—125页。
基于这一局部的与超局部的秩序,宗教交往及其伦理表达的社会交往结构,就当是一种社会交往局部秩序的建构,而非纵向的普遍价值制约和社会秩序。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之中,去寻求一种制度主义宗教行动的“合法性”。换言之,某一宗教交往的伦理表达形式,更多的是在寻求一种宗教交往行动的“合法性”,以发挥保护自己、制约信教公民的社会规约作用,进而避免宗教内部以及宗教之间的交往冲突,同时亦避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与其它社会集团或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冲突。
四、 宗教交往及其合法性
宗教交往所建构的社会资本及其合法性问题,乃是宗教交往得以进行的主要基础。
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的实际含义,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评价,也是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被治理者那里具有正当的或自愿承认的特性。它的表现将涉及某一社会秩序的运转以及该社会成员的忠诚。自从卢梭提出政治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上之后,马克斯·韦伯从三个方面区别了合法性的三大类别,即神圣的传统、人民对于领导者个人魅力的忠心,以及因为对于法律的至高无上普遍信仰而对于“合法权威”的承认。现代西方政治学界则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其一,合法性导源于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些与神意紧密联系的传统;其二,合法性建立在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契约的基础上;其三,合法性的基础是一致同意的价值标准。*庞元正、丁冬红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宗教合法性是现代社会及其制度分化的产物。传统社会之中,由于宗教对于一个社会价值道德体系乃至政治法律观念的普遍影响,宗教的合法性问题在中世纪之前并不存在。*[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只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信仰体系成为社会次级制度之后,才会导致宗教合法性问题的产生。宗教合法性既是现代社会中宗教与法治的基本内容,同时亦是现代宗教能够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所以,当代社会中宗教合法性的获得形式及其表达方法,制约着宗教交往、信仰认同的社会意义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从宗教与政治的本质关系而言,制度宗教的合法性问题无疑是以政教关系及其处理方式作为主要内涵。政教关系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宗教与国家;二是宗教与国民社会;三是宗教取向与历史文化行为模式。同时,也可以将上述这些种关系理解为意识形态方面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权力主体层次上宗教团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张训谋:《欧美政教关系研究·绪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因此,宗教合法性一个最基本的体现形式,就是建立在政教关系合法分离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宗教与国家权力、宗教团体与社会组织、信教公民与非信教公民以及宗教团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并且相应地表现为宗教团体及宗教信徒对自己宗教在社会上所处地位、社会功能发挥空间的基本认同。它的基本意义,就是政教关系、宗教与社会、宗教之间各类关系的处理方法或基本原则。
所以,宗教组织的社会定位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本身就是一个宗教合法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事务的管理。它涉及政教关系尤其是宗教合法性的体现及其社会形式等问题,即宗教组织及其成员如何理解来自国家权力的管理,如何服从这种出自于国家权力的各种法规及其制约。从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关系而言,宗教组织的合法形式及其登记或认证形式,仅仅是一种法律的确认形式,是合法律性,同时也是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政教关系的一种方法。虽然这个方法并非唯一的方法。但是,这种合法律性却构成了合法性的主要内涵,并且制约了宗教合法性的各种表达形式。
宗教的合法律性概念以宗教立法为核心。一般来说,宗教立法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宗教机构当局为本宗教的组织和管理制定的一套法律、法规和制度;二是国家立法机构为处理涉及宗教的公共事务而制定的涉及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三是宗教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协议等。它主要是指因为信仰关系而产生的对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产生的具有约束力量的法律、法规和协议等,还包括具有合法地位的宗教团体的法规中约束成员社会行为的一些条款、法规等内容。*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
这种“合法律性”,近似于合法性,并以一种具体的方式界定了宗教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了宗教所难以逾越的制度界限,既能支配统治者又能支配被统治者。它可以和个体的赞同、社会的根本规范一起分享这种法律地位,证明自己的独立的、制度的合法性。所以,赞同、社会规范和法律这三个基本概念,共同界定了合法性理念的真实内涵*[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亦为我们考察现代社会宗教的社会定位及其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富有实际效果的分析工具。
就宗教交往、信仰认同的表现规则而言,合法性的表达形式与其它社会组织的结构类似。它的解释逻辑是这样的,宗教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强烈地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为了获得制度或组织的合法性,宗教的制度或组织必须顺从法律规范以利于组织的生存与延续。所以宗教组织与其它社会组织间在结构和行为上具有相似性,这也就是因为合法性机制的作用而促使组织趋同。*[美]W.理查特·斯格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因为合法性机制,往往会在外部环境中迫使宗教组织采纳那种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运行机制。
宗教曾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合理化论证工具,而现代社会中宗教失去了这一功能。一方面,是宗教的合法性问题被逼了出来,另一方面,则要求宗教交往的功能表达方式,必须是一种多元的交往层次以及共识重叠的信仰认同方法。因此,各个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原则”及各个宗教在公共领域前的“自我约束”,进入公共领域的“准入机制”等等,均以体系化的宗教信仰作为现代宗教的合法性内涵及其表达形式。
从国家、社会、宗教的三元分析架构来看,国家对于宗教合法性的要求在于国家权力对宗教的法律控制;社会对于宗教合法性的要求,在于社会对宗教的认可及其社会控制;而宗教团体本身对于宗教合法性的要求,则是在于宗教与国家、社会及现有法律之间的良性交往——既有活动空间,亦能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之中不受来自国家、社会的非法干扰。所以,宗教交往关系的公共性、合法性表达形式,实际上就是宗教伦理在现代社会之中如何得以实践、交往、认同的问题。只有将此问题的处理方法,置于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空间之内,宗教与宗教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才可能取得协调,宗教交往、信仰认同的社会功能,才可能正常发挥。
在本质上来说,宗教合法性,就是在宗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给出了一个合乎法律的解决基础,进而充分地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宗教交往的合法性要求。因为,现代社会中政教关系合法分离的原则,乃是宗教交往关系得以表现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宗教交往关系之合法性体现,主要是对宗教团体的“宗教事务”,即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从而保留了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的神圣资源及其传统。 为此,宗教自由必须受到政府行政各个部门之尊重,各行政部门除了维护公共秩序、将非法行为限定在最小限度之外,必须尊重宗教交往、信仰认同的特殊性和宗教习惯,特别注意不得妨碍信教自由。
基于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行政仅仅是对宗教事务的层面进行规范,而对宗教团体的宗教事务及其活动,则无更多的干涉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最基本的就是基于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给予宗教及宗教团体以法定的活动空间,同时也设定了国家权力对于宗教活动不得随意干涉的法律界限。
所以,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相关规定,对于宪法应当是一个极好的补充。 这明确保障了国民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也规定了作为其依据的国家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宗教信仰成为了每一个国民自己支配的私事;政治上则宣告国家政权的无宗教性,以充分保障前者的实现。
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及依据宗教信仰所进行的宗教活动,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是个人的权利,所以既不能派生一切特权,也不能允许国家公共权力保护、支持、优待某一宗教或管制、监督、指导宗教。这就在充分界定权力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基础上,既保证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范围,亦同时保证了作为宗教信徒和宗教团体的被统治者的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而言,这个法律规定,乃是宗教合法性最最基本的构成,是以宗教合法律性体现宗教合法性的最基本方式,同时也为现代宗教交往结构朝着真正自律化方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平台。
因此,宗教交往合法性的社会特性,就在于法律及其制度对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认定。认定某个宗教团体或者宗教组织只能接受来自法律的支配,而不接受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权力的制约。这样,宗教合法性就将以一种具有组织形态的、制度化的宗教行动方式,进而体现了宗教合法性的制度化。而宗教团体本身所具有的自律自治功能,如它作为宗教团体所应当具有的正规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公共性、代表性、参与性等等社会特征,则以社会团体、法人组织形式及其制度要求,在社会规范的形式上,为宗教合法性的真实呈现提供了它本身所要求的社会赞同特征,最终支持了宗教合法律性与宗教合法性的有机结合。
正如法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法律的宗教将失去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为纯属于个人的神秘体验。法律(解决纷争和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和宗教(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乃是人类经验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各自又都是对方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5页。这一观点指明了当代宗教与法律之间那种独特的亲和力,更进一步则是说明了当代社会中宗教交往对现代社会发挥功能的基本路径,说明了把信仰与法律相对立的做法,既会低估了宗教交往的社会性,也低估了宗教交往结构的法律性,进而减弱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五、 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合法性
在合法性短缺的前提之下,宗教交往关系正日益成为个人试图摆脱其孤独,追求个人心志安宁的私人事务,只有个体自我的身份之感,而无社会特性之表达。如果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具有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宗教信仰的话*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6—157页。,那么,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发挥宗教与法律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至于国家行政则应通过法律制度这个中介提供合作,运用宪法的权限提供一个宗教能够于其中合法存在乃至发展的合理架构。
虽然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教模式并没有对“宗教团体”这个新兴的社会团体法人形态予以更多的说明和界定,但是,它以社团法人或场所法人的社会形式,提出了“宗教合法性”这个问题,就已经促使现代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获得了一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制度形式,导致现代宗教、宗教团体、信教公民能够以一种合法的身份存在并活动在现代社会之中,尤其是其“团体法人”的身份更能体现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独立获得方式。
无论哪个方面,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体现,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表现。从这个方面来说,宗教交往关系的平等以及宗教自主权的设立,应当是现代社会之中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表达形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人为地制造了宗教交往间的不平等现象,为国家监督、操弄宗教提供了不平等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传统社会中宗教合法性难以体现的一大政治缘由。
由于法人是一个社会组织而不是单个的自然人,因此宗教交往关系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法人的团体意志总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产生,并且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才能具体实现。没有这样的机构,社会组织就不能作为有意志的独立主体进行活动,也不可能独立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宗教团体、宗教场所能够获得另一种“法人”形式,以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获得了现代法律的认可,也就是现代法律对于当代宗教的行动界限、信仰自由的界定,进而在国家—宗教—社会的三元结构中,以“法人”组织的形式将宗教的合法性奠基在“社会”这个层面,促使宗教在某种层面呈现了韦伯所说的“祛魅”现象,从上层建筑的高处落脚在社会民间,从政治的合法性到社会的合法性,以至于体现出宗教制度、宗教组织本身的合法性,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渐渐地社会化、获得了自己本应具有的社会形式。
上述这种宗教的合法性建构形式,促使各个宗教团体之上不再存在一个近似于国家宗教,国家对宗教团体的“认可制”转变为“登记制”,凡依法申请者均可以成为宗教团体或者宗教场所的法人组织,享受相应的社会优惠权利。国家也不再拥有对于宗教团体的教义、仪式或其他内部事务进行监督或干涉的权力,在行政权力主导的基础之上,宗教的自主权获得了一定的承认。
正是这一宗教合法性的法律基础,促使各个宗教、宗教派别之间获得了平等交往的机会与空间。宗教间交往关系的平等,保证了政教之间的真正分离,在法律设定上实现了宗教自由。宗教间的公私平等,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国家权力不再行使自己的权力,各个宗教之间也不再划分高下、公私,均以法人的形式保证了政教之间的真实分离。为此,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及宗教自主原则得到了最初的肯定,为解决各类宗教纠纷和各类宗教诉讼提供了法律的准绳。各个宗教均能以法人团体的社会形式,具有了自己的法定空间。
然而,宗教之间的平等并不排除宗教合法性的呈现形式当中缺乏相对强制性的表现程序。因为,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合法性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权力的基础,这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它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对这种统治权利予以某种认可。”与此相应的是,人们也可以将此合法性类型分成程序的、强制的、警告的、学术论证的和大众的五种类型,或者是把它分为符号的和现实的两种。*参见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特别是那种出自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形式,往往就会带有程度不一的强制性内容。
宗教合法性的社会形式得以确立,就有了一道防止政治干预宗教、宗教染指政治的坚固的屏障。但是,这个制度的法律效应,实际上就呈现了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程序意义,并且还强制性地将宗教与国家的冲突从政治层面转移到了行政层面。这是在宗教合法性方面,宗教的合法律性对于政教关系制度性设定的法律底限,谁也不得逾越。这就体现了宗教合法性制度设施上宗教他律的刚性特征。
无论是宗教介入政治,抑或是政治干涉宗教,都是对宗教合法性及其原则的最大破坏。而宗教合法性的最基本的价值底线,就存在于这个二元相分的法律架构之中。否则,双方皆会产生政教合一的冲动,企图吞并、利用对方。
在历史上,宗教多半被政治所包含,但是这种包含往往付出了很大的政治成本。现代社会依据宗教立法来管理宗教,宗教则成为一个行政管理、社会控制领域的事情,从而能够将宗教与政治的冲突转移成为行政问题,而不会直接地成为政治危机。依照宗教合法性的制度设计,它能够将宗教团体乃至宗教活动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法定的领域之中,难以直接构成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促使行政监督、社会控制成为宗教合法性的最好补充。当然,这个补充既有法律程序的自律,同时也包含了法律制度的他律。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当代亚洲社会政治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代社会之中宗教势力的膨胀或国家主义的扩展,往往首先会冲击固有的政教关系及其合法性底线。国家权力很容易被宗教化,成为信仰的对象。
在这个方面,新兴宗教与宗教介入政治活动,可能是宗教法人合法性中最重要的变化形式。在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中,政治力量已经日益关注各类宗教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势力参与宗教”或“民族国家借力于宗教”的双重倾向,反映出当代宗教在现代社会政治事务中的特殊功能以及现代政治行动的特别倾向。尤其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促使政治家和政党越发需要宗教团体的支持,增大了宗教对政治事务的间接影响和发言权。至于各个宗教团体也常常采用直接建立政党、推举自己团体的人参加选举、与某个政党达成一致意见等方法来介入政治活动,所以具有社会实体形式、人数众多、财力殷实的新兴宗教团体,往往成为许多政党觊觎的目标和借助的对象。对于宗教团体而言,政党政治对宗教的支持实在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因为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政党政治或宗教团体的组织动员力量,使政党或宗教在全国范围内参加政党选举活动。
这些现象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到当代宗教交往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的政教分离,并非断除政治与宗教的一切关系,而是使两者处于一种正常的关系之中。因此,只要宗教团体还想恢复它们在社会教化方面的功能,适应社会的变迁而重建教团组织,那么,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就不得不成为需要正面对待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宗教的合法性的最后得以构成往往就是源自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构成,说明了国家权力不再出自于宗教的信仰特征。
这就从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提出了宗教交往合法性问题的变化形态,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上再度逼出了宗教与政治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如果已经成为一股潮流,那么,宗教的合法性问题就更加显得重要。它不仅仅关系到宗教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将与世界各国各个宗教文明体系之间的共生共存的命运问题。
总之,宗教合法性的取得方式,实际上是一定社会之中宗教型社会群体的行动在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理性化、制度化的形式表达。它存在于宗教与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习俗等等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些社会交往的关系之中,它们才能构成现代社会中宗教交往关系的合法性。
然而,“宗教和政治之间的真正关系是非二元的,这种关系符合基于人类本质的因而归根结底基于实在结构的本质。现实问题也即宗教问题,关于人类终极的思考也是政治性的,政治与宗教不能彼此分离,没有一种宗教行为不同时属于政治行为。当今人类所有重大问题都既有政治性又有宗教性:饥饿、正义、生活方式、泛经济文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和平构成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这一论断的真实性。依此观念,宗教的要素必须和超越者、超自然者、神圣者、超然者、涅槃、终极实在、永恒之物以及不可理解的内在之物有关”*[西]雷蒙·潘尼卡:《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王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这说明宗教交往的社会—经验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以及处理这一特殊关系的特殊方法。应当指出的是,在亚洲秩序与宗教交往方式之复杂关系中,上述问题与现象也难以避免。
六、 宗教交往与亚洲命运共同体
宗教在理论意义上始终是个迷,在伦理的意义上也始终是个迷。它充满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也充满了伦理上的自相矛盾。它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则恰恰相反: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宗教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却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却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是太人间化了。*[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3页。
这要求当今世界在不同宗教之间的交往关系层面上,必须寻求一个超越不同宗教却又能够包含不同宗教信仰特征的共同标准、普适的公正平台。每一个宗教都有它自己内在的标准,不容许其堕落变质、继续腐化,宗教内部有一种力量要自我净化。每一个宗教无疑都可以诉之于自己的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它自己的宝典如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佛典、四书五经之类,每一个传统都会致力于建立一个本宗教所极端推崇的普适价值标准。但问题也在这里,经由这些宝典树立起来的普适价值标准至多能够约束一个宗教体系内部的信众,而不能够拥有跨宗教的普遍效力。面对着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宗教,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标准,好像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一样。
宗教家或神学家们都十分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普遍性的伦理道德标准。宗教虽然向往绝对的超越,但与现实的人间世界却没法切断干系,像基督教十诫所颁布的道德律令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往今来宗教之间的交往,如我们所知,却成了一种宗教的竞争。所以在宗教的邻居关系中,做好邻居的第一步,将不是拆除篱笆并试图建造一个宗教的公共用地,而是尽可能真正表明我们是谁,并让我们的邻居在我们对着篱笆谈论时看到我们是谁。*[美]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234页。
自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译介到中国知识界之后,影响所及,遂有从宗教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精神动力的各种议论发生,亦有如半个多世纪之前那样的思想观念——中国无宗教或无基督教,于是现代化难以建成。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出现之后,中国学人也包括海外知识界积极地寻找东亚经济起飞的精神渊薮,大都也是在回应马克斯·韦伯的论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教资本主义、东方儒教是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奇迹出现的文化因缘。
另一部分知识学人则苦于中国现代化的步履困顿、举步维艰,承继着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向西方寻觅解决中国现代化难题的钥匙或妙方。韦伯的思想,正巧与此不谋而合。问题被理解得如此简单:中国缺乏象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文化传统,故而现代化难以顺利实现;如欲中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亟当引入基督教新教的文化理念或建设类似的文化价值秩序。岁月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问题仿佛又在重复。在经历了东方的儒家资本主义思潮之后,或许站在今日的历史高度,时人当比前人看得更深更透。但是,如此之思想方法及认识途径,恰好是忽略了亚洲社会缺乏欧洲基督教那样的主导宗教,难以从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之中寻求亚洲社会的普适价值精神,而能够主导亚洲社会各个宗教信仰体系的往往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力量。
这恰好是以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历史演进到了今天,东西方文化或东方佛教(乃至儒教、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必须进行真实对话、真实交往,这一点显得更加迫切,同时现代社会也为东西方宗教的真实对话与真实交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得以沟通交流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面,也是最迫切的需要。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学人对于佛教传统的时代性与创造性的诠释,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于基督教所作的批判,在某种程序上,正为今日佛教与基督教的真实对话、真实交往,提供了富有启迪的历史经验或时代教训。虽然这次对话与交往未能展开双方教义的真实沟通与互相理解,诸如原罪与本苦、拯救与觉悟、罪与业、自我与无我等等,大都局限在民族文化的情感立场。然而,二十世纪已经把宗教交往、信仰认同的相关问题给提了出来。
从今日亚洲的时代要求出发,从东西文化、亚洲各个民族宗教的深层对话、东西宗教交往的真实关系出发,人们可以对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学人的佛教信念进行再认识、再阐释;同样,人们也可以对基督教的东渐过程予以更好的梳理。如同侧重于经国济世的佛教思想,难以给中国学人提供超越俗世、真实觉悟的方法和境界一样;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不重视民族平等、信仰自由的基督教哲学,也难以让亚洲社会中非基督教民族心平气和地接纳与理解。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政治军事冲突,难以为东西文化、乃至亚洲各国的民族宗教的真实对话与实际交往,提供一个理性、宽容、公平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这一历史的遗憾,又正好构成了当今世界东西对话、信仰认同、宗教交往的社会必然性,构成了东西双方交相互补、两得益彰的双重可能性,同时也凸显了亚洲秩序建构中的不同宗教信仰平等而公共交往的重要性。其共同的文化信仰指向,当以西方文化对于东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亚洲宗教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接受与理解,作为互为辩证的两个层面,从而为日后的人类文化、世界信仰认同的重新建成,提供一个多元的、多层面的、人类学性质的价值秩序与精神关怀。
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为世界性宗教,同时也是亚洲各国的地方民族宗教,承受着它们深厚影响的各国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应当因此而具备世界性的心灵胸襟? 若每个宗教皆能积极面向时代之挑战,反省自身之不足,也许更能促成一个契机,使亚洲秩序得以重建过程中的宗教交往达到另一高潮,不单使普世的宗教交往获得丰富的社会性与公共性,更可能为亚洲秩序、亚洲社会的国际特性的建设提供神圣资源。
正如世界诸宗教、亚洲各国宗教必须走在一起,应当形成一个对话的共同体,而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单一的宗教那样,人类宗教未来最适合的图像或许也不是在教会、会堂、庙宇、清真寺的繁荣图景中找到,而是在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以及1999年开普敦世界宗教会议上,全世界见证的、数千人体验的内容中找到。世界主要宗教共同体的代表会聚一堂,彼此会谈和倾听。*[美]保罗·尼特:《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而这样一个能够使全世界不同宗教人士倾听与会谈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认同与理解、交往与合作的国际公民社会。亚洲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宗教交往同时就是社会交往,而不同社会层次、不同肤色之间的社会交往、及其建构与这些交往中的公共理性与公共规范,同时就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能够构成最基本认同的基础。
当代中国各大宗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果,致力于为此经济社会提供价值观念及其文化认同的神圣基础。在此过程之中,各种宗教都曾经希望以己之信仰教化或影响国民,构成全民性宗教信仰体系。殊不知,如果缺乏一个超越看各个宗教的普适性价值共识,各个宗教信仰体系如果同处于一个空间或场所,会不会、能不能平等共处、协调各方,形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交往规则?或者是构成不同程度上的冲突?
传统中国虽然有三教合一之说,但儒家经典及其信仰体系显然就是国民信仰的核心,成为国民价值认同的核心;当代中国社会,一教独大以整合国民价值观念,似乎已不可能。一个民主的社会,必定宗教多元、信仰平等,亚洲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此。尽管不同宗教的信仰共同体,始终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由此改变他们自身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符号世界;但是,一个信仰世界的设置背景,由此赋予社会民众以特定的意义及其构成的意义、规则、传统、符号和价值网络,都会构成一个共同体运作于其中的结构系统,进而会构成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身份标识、地位认同层面上的重大差别。
虽然宗教信仰及其“群体认同,并不会成为一种党派性的阶级意识,而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支撑。这种认同使他们成为有别于他人的一个群体”。但是,基于不同的地位与身份所导致的宗教冲突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身份”,宗教信仰共同体或宗教群体会赋予他们一种身份,并且可能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道凤书社2001年版,第361—362页。
因此,宗教与宗教、信仰与信仰之间往往就会具有这样的矛盾,单一的信仰能够构成信仰的虔诚与委身,但又往往会构成单一信仰的独尊,构成宗教的不宽容;多神的信仰方式常常无法形成一神论信仰方式那种单一与虔诚,呈现一种宽容现象。然而,单一独尊与多元宽容,往往会形成如下一种非常矛盾的信仰现象——“信仰的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同时也消弱了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更加宽容的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与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他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祗”*[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至于当代亚洲秩序及其与不同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似已建立了各种多边宗教集团和多边信仰认同机制,而其信仰方式与认同差异却明显不一、令人目眩。加上亚洲国家组成的各个宗教团体性质常常是模糊不清,同时又由于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影响超越了国家与地理的分界线,尤其是亚洲各国之印度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超越了国家界限,促使亚洲各国与各宗教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格外的模糊。这就增加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困难。
亚洲秩序之中各个宗教信仰体系的力量非常明显,但是历史上亚洲建构的地区秩序大多不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有关国际社会的主张为基础的。欧洲的秩序支持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边界清晰、彼此承认的主权国家;但历史上亚洲的政治强国所依照的标准却边界模糊,而宗教信仰的力量却又超越了这些国家界限,会把国家权力的诉求置之于宗教信仰层面,使国家间的秩序构成显得异常困难。正如基辛格所言,亚洲国家最广泛的特点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新兴的”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都努力通过突出自己国家的特点来克服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核心利益的时候,借鉴的却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向往的也是不同的黄金时代。每个国家都坚信自己拥有特定的内在发展动力,自己在崛起。*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277页。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制度、近代历史中的“一个亚细亚”、1970年代以来的“儒家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及其社会思潮,大都反映了亚洲秩序的上述特点。
因此,就亚洲民族、宗教之间的交往与互动的问题来说,关键是在不同宗教的交往之间,国家权力能否提供处理多宗教交往与互动的公共平台,而不同宗教的交往与互动能否自觉建构其交往之公共理性与公共领域,建构一个既包含了民族宗教绝对价值关系,同时又能够超越了这些绝对性价值体系的国际公共领域,共享公共理性,彼此尊重独立。
如果说,当代国际社会的“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而现代政治秩序的基本特点是,将绝对的道德观和国家政治区分开来“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断,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XI页。那么,亚洲秩序之重建也同时意味着把国家权力之间的均势与民族、宗教及其信仰之间的伙伴关系等概念予以有机地整合,进而在宗教信仰所体现的有限秩序与国家权力之整全秩序之间,运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与公共交往理性来寻找、建构当代亚洲秩序及其命运共同体中的平衡支点。
(责任编辑:薛立勇 潇湘子)
Asian Order and the Interaction of Religions
Li Xiangp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BeltandRoa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n Order and “InternationalCommunity” is the most essential issue to face with. The tens of nations in Asian community mostly maintain various religious backgrounds and forms of beliefs, as well as lack the predominant value system and belief structure, which has doubtlessly become an issue to be prudently faced with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order and common destiny of Asia. Thus whether or not a supra-national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an be established will be eventually determined by the existence of rule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of modern nation. A kind of universal value shared by various nation states and religious beliefs should be constructed, which both contains and surpasses the traditions of religious beliefs of each Asian country. For this purpose, it’s a priority for all to construct belief consensus and common platform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various religion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Asian order.
Asian Or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ligious Interaction; Common Belief; Value Consensus
2015-09-2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2&ZD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信仰研究”(项目编号:10&ZD113)的阶段性成果。
B920; C912.66
A
0257-5833(2016)01-0060-13
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