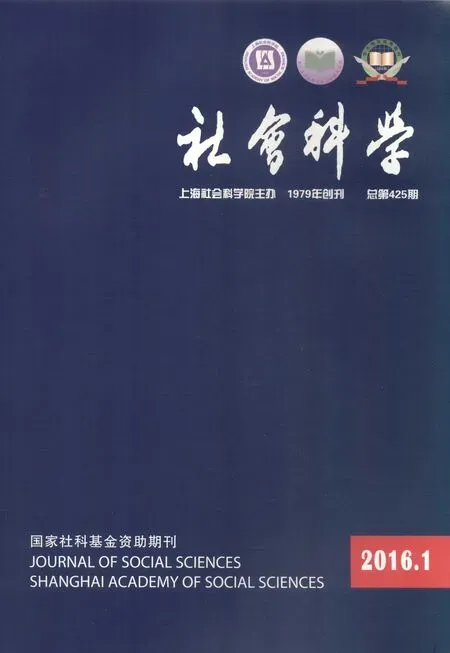论抗战时期文学英雄形象的建构困境*
2016-02-05张谦芬
张谦芬
论抗战时期文学英雄形象的建构困境*
张谦芬
在民族战争的时代危机中,英雄书写成为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但数量众多的英雄形象因主体性、人文性等方面的缺失呈现出模糊的面影。这跟时代政治的掣肘有关,也暴露了当时知识分子自我建设与把握民族精神的种种困境。剖析抗战时期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有助于进一步审视中国抗战文学的特质、成因及后世影响。
抗战时期;英雄形象;精神内核;建构困境
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特别是战争时代,人们很自然地希望有英雄来改变现实、拯救危难,这时期的文学也会承担起对英雄形象寻觅和塑造的任务。中国抗战时期就是这样。艰难世事催生了大量的英雄叙事,也塑造了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然而,纵观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这些英雄形象中极少成功的艺术典型,他们大都缺乏独立的精神主体、鲜明的个性特征,也难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文学是一种时代想象,抗战时期对英雄形象的塑造透露着时代氛围、创作主体和文化传统的丰富信息,折射了作家们在民族战争背景下创作调整的努力和遭遇的种种困境。检视抗战时期文学的英雄形象,对于我们进一步审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甚至对于我们认识整个新文学历史,都有着别样的意义。
一
抗战时期对英雄的吁求极为强烈,可以说,遍布不同政治区域,也贯穿于整个抗战背景中。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国共两党都将宣传英雄事迹作为时代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沦陷区文人也将“新英雄主义”与“健康的文学”紧密联系起来*① 上官筝:《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之健康的要求》,《中国公论》第8卷第5期。。抗战时期杂志上随处可见各类英雄事迹的报道、历史名人的纪念、国外英雄理论的译介,等等。文人普遍认识到:“再没有比这个大时代——更正确地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大时代——更需要英雄的了。”*② 孙晋武:《论英雄主义》,《新意识》1938年第5期。
抗战时期英雄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多方开掘的态势。在题材选择上,有现实感极强的战地英雄书写,如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张恨水的《虎贲万岁》、老舍的《张自忠》以及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有暗喻现实的历史剧、电影,如《海国英雄》(阿英)、《屈原》(郭沫若)、《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等作品借历史人物表现抗敌御侮、誓不屈服的呼号。在人物系列上,有来自底层的农民英雄形象,《差半车麦秸》(姚雪垠)、《鸭嘴涝》(吴组缃)等小说展示了农民从不了解抗战到逐步参与抗战、成长为英雄的历程;有执着于精神追寻的知识流浪者,《伍子胥》(冯至)、《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等小说表达了对战争的思考。在创作风格上,写实与传奇兼有,就传奇而言,既有对民间强力的探索,如端木蕻良的《大江》《风陵渡》、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以及师陀的《马兰》、沈寂的《盗马贼》等;也有谷斯范的《新水浒》、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革命英雄传奇,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开启了英雄书写的新范式。
从这些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英雄形象可以看到作家们对这一题材的关注,然而,这些英雄形象是否真的具备了英雄的实质,真的传达出了时代对英雄的期待?答案显然并不乐观。虽然关于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英雄的精神实质,存在着复杂的解读。但大体而言,正如黑格尔指出英雄“内在的‘精神’”“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9页。,卡莱尔将英雄的本质概括为“‘真实’、‘神圣’和‘永恒’”*[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何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英雄形象必然是时代性与普遍性的结合。英雄人物不仅以其丰功伟绩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且以其强大的精神主体表达出人们超越各种客观限制的渴求。因此,在战争叙事中,英雄形象既要表达对勇气、希望的鼓舞,也要启发对战争、对人性的思索。鲜明的主体性和强烈的人文性是英雄形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内核。然而,审视抗战时期文学英雄形象,在这些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不足。
(一)主体性的匮乏
黑格尔认为:“只有在个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交融中才有真正的独立自足性”,这样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0、303页。英雄形象的重要特征就是其主体性,即在鲜明而独立的“个体的独立自足性”中,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抗战时期英雄书写着重于表达保家卫国的时代主题,对英雄形象的个人独立精神、鲜明个性凸显不够,因此造成英雄主体性不足的缺憾。
这首先表现在一些英雄书写重“事”轻“人”。由于过强的现实目的性,抗战时期部分英雄形象的塑造着重于外部行动的叙述和传奇故事的编撰,很少探索英雄形象的内在主体精神。作家们纷纷着眼于“描写壮烈事件”,或“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或写人却重点在形象的寓意而忽略了人本身,企图通过英雄故事来激发民众、表达决心。抗战初期的《刘粹刚之死》就是如此。作品内容属于实录,但写作上始终围绕爱国尽忠的主题进行,人物本身的特征和个性,特别是内心情感被完全忽略了。《刘粹刚之死》的这一缺陷也引起了当时文坛的关注,但此后的情形并无多大改观。不少作品已经完全将英雄塑造当成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将英雄形象等同于政治的图解,“先有了固定的故事的框子,然后填进人物去,而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之确信等观念,则又分配填在人物身上”*茅盾:《八月的感想》,载《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这样的英雄形象自然是不可能有主体的精神个性。
其次,英雄叙事的群化现象也难以显示其主体性。即使是一些并非概念先行的英雄书写,也不是竭力对英雄的个人能力进行张扬,对个体意识予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英雄的主体性会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与消弭,取而代之的是英雄的集体属性。一些作品以“我们”代替“我”,是一个集中的表征,如“我们的吹号手”(《吹号手》)、“我们的射手”(《自由射手之歌》)、“我们的喇叭”(《我们的喇叭》)等;叙述英雄故事也往往有殊途同归的相似模式,都是表现从小家走向大家,从小我进步为大我,写落后农民成长为抗日的英雄。特别是敌后根据地文学,更是明确区分个人主义的英雄和集体主义的英雄,旗帜鲜明地批评前者,褒扬后者。《地雷阵》(邵子南)和《吕梁英雄传》等作品有意对个人主义英雄进行教育和改造,作品着意表现的不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个”,而是民族集体意志的“这一类”。
群化英雄的叙事不是塑造特立独行的英雄个体,而是展示反抗侵略的民族群像。从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到孙犁等作家的创作,书写对象都是平民化的英雄群体。这些底层英雄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姓名,有的只有个外号或代称,如二里半、小红脸、水生嫂等,在行动方式、思想意识上也都体现着他们所属阶层的共性特征。如《生死场》中“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盟誓一段,喊出了整个时代的心声,但这种时代主题的表达是模糊的,也造成了文本表意上的前后断裂。另一些英雄书写虽写的不是群化英雄,但由于过于追求民族的象征意义,也失去了个人的主体特征。如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从黄河、图腾、艄公写起,显然是要把民族文化中古已有之的英雄气概与饱经沧桑的马老汉联结到一起,但小说的寓意色彩过于强烈,形象的塑造明显缺乏血肉和个性。
最后,英雄主体性的匮乏还表现在对英雄精神力量的彰显不够。英雄人物的独立个性应该在主客体“对立、冲突和抗争”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考验愈严重,困苦愈艰巨,斗争愈激烈,也就愈能表现出崇高”*李泽厚:《关于崇高与滑稽》,载《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只有尖锐的冲突才能显示出英雄的崇高气质,而没有崇高也就无所谓英雄。因此,展示复杂历史情境下的矛盾冲突,才能塑造出真实可感的英雄形象。但是,抗战时期一些英雄书写从二元对立的军事思维出发,采用忠奸对立的情节模式、善恶分明的人物格局、爱憎相对的情感逻辑,将复杂的矛盾、艰苦的斗争肤浅化。这在当时的历史剧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屈原》一剧在人物忠奸对立的情节之外,甚至以张仪小人作祟、南后争风吃醋作为屈原的主要反对面,显然在对历史真实的“失事求似”中削减了屈原的精神感染力。作者也许达到了隐射现实的创作目的,但英雄形象却没有真正站立起来。
(二)人文性的不足
与主体性紧密相连,人文性也是英雄形象的重要内涵,对人本身、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英雄想象的出发点。这其中包括把英雄当作人,写出战争中、生活中英雄光辉的正面和复杂的背面,同时对他们的生命个体、对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和困惑给予必要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彰示出英雄的实质,突出英雄书写的精神内涵。
这些方面,在抗战时期文学中有不同程度的匮乏。这首先表现在对英雄的人性世界没有充分的展现和挖掘。英雄既是特殊的人,又同时是普通人,他有七情六欲,有痛苦,有犹豫和困惑。而抗战时期文学大多着力于表现英雄的英武完美,很少展现人物的普通人性世界。抗战初期,英雄形象塑造从外表到性格都呈现显著的类型化特点,描写“前线的英勇将士,一定把他写成高大的身材,坚强的体魄,严肃而沉毅的面孔,几乎个个都是中世纪的骑士英雄一样”*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伦》,《文艺阵地》1938年第一卷第四期。。对于这样单纯标本似的英雄形象,丘东平有所警觉。他说:“战争使我们的生命单纯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以为最标本的战士应该……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丘东平:《1938年10月10日致胡风的信》,引自《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书屋》2003年第3期。他的创作对此也有所克服,他塑造的英雄形象不是政治进步、道德完善的理想化英雄,而是有着不同个性特征的普通军人。如《第七连》中的青年连长始终对战争的恐怖有着难以克服的复杂想象;《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英勇的战士们身体里盛炽着“狭窄、私有、独占的根性”。这些不完美的英雄形象映现了战争的残酷,给人更为真实的印象。与丘东平的创作差不多同时,姚雪垠在《差半车麦秸》中塑造了王哑巴这样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形象,邋遢的举止、庄稼汉的土气、农民式的狡黠与朴实,充分显示其真实和个性。
不过遗憾的是,丘东平早逝,这种突进到英雄灵魂深处的杂色化创作未能继续,这种带着鲜活战地体验的独特战争书写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在丘东平评价中人与文的分裂,一方面与左翼文坛内部的宗派主义纠葛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其对野蛮战争与脆弱人性的另类化叙事,挑战着英雄书写的陈规,而《差半车麦秸》则一发表就引起了争议和批评。批评者认为作品的重心应该写出主人公从农民到英雄的转变,称转变过程中“内心的痛苦的矛盾斗争,是特征的东西”,而对转变揭示不透是作品的“大醇小疵”。*黄绳:《抗战文艺的典型创造问题》,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51页。显然,这种批评意见并非偶然,而是代表着时代政治的要求——政治所要求的是英雄的激励作用而不是英雄的个性,因此,它期待的英雄是没有缺点或已经摆脱了缺点的英雄,英雄成长小说应该写他们如何脱胎换骨,如何从复杂个性蜕化成单一英雄性的过程。这一潮流的影响是巨大的,姚雪垠稍后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就从《差半车麦秸》中有所撤退和改变。作品书写的是牛全德从旧的江湖义气向革命责任感的进步,最后成长为“一个为革命和同志而牺牲的民族英雄”。牛全德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正符合时代潮流提纯的要求。此后,英雄的不断提纯、不断神化就成为抗战文学的显著走向,无缺陷和进步性几乎囊括了所有英雄形象的特征。特别是根据地及之后的解放区文学,无论是丁玲《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的小战士,还是《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新儿女英雄传》中的黑老蔡、牛大水,无一例外。
人文性的匮乏之二,是缺乏对英雄真实遭遇的直面,特别是缺乏对他们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关爱。当然,抗战时期部分作品也有突破这一缺陷的描写。如丘东平执笔的《给予者》写在战争残酷的对峙中,黄伯祥无奈向自己家的方向开炮,结果,自己家人都被炸伤炸死。作品写黄伯祥在瓦砾中抱起奄奄一息的女儿,看到孩子深陷的眼睛、听到微弱的呼唤,英雄全身遭了猛击似的沉重颤抖。但短暂的二十秒后,黄伯祥踉跄地、寂寞地继续提枪前行。这里既写出了英雄人物坚韧不屈的精神特质,又对他内心的儿女情长给予了深刻的体悟。但这样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学中微乎其微。在绝大多数抗战时期文学作品中,似乎英雄生来就是英雄,他们没有普通人的苦痛、烦恼,也不需要得到普通人的关怀。如《四世同堂》中的瑞全是作家表彰的理想市民形象,其舍弃小家为国尽忠、秘密锄奸不徇私情的形象堪称英雄。然而,瑞全杀招弟、爱高娣,全然出乎政治的立场,他在小家与大家、私情与大义之间的毅然决然多少折损了他的感人力量。
与之相应的是,抗战时期文学对英雄死亡的书写很少呈现较强的悲剧色彩。抗战初期曾一度流行浅薄的“喜剧型的英雄”,之后,文学风格由亢奋转而沉郁,偶尔可以看到悲剧化的结尾。但大部分作品仍很少对英雄的死亡给予必要的关怀,极为克制悲伤情绪的渲染,也少写这些死亡所带来的苦痛,而是普遍以民族大义的悲壮感进行了遮蔽和升华。
正如陈思和所说:“如果创作者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状态”,就无法“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揭示它的美感”。*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这种对英雄缺乏关爱的简单书写,内在蕴含的是人文精神的丧失。与此相关联的是,抗战时期文学往往把日军作妖魔化、简笔化的处理,少见个性化的敌人形象。包括对战争场景的书写,只见敌人的血肉横飞,却少悲悯情怀和感人泪下的悲伤细节。如《地雷阵》中以欢快的笔调写地雷爆炸带来的报复快感,在热闹之中消解了对杀戮的恐惧、对战争的憎恶。然而事实上,缺少了对人的尊重,缺少对人的关爱,也是失去了英雄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也降低了塑造英雄形象背后的精神高度。
二
斯宾格勒说,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抗战时期英雄形象建构的缺憾与战时时代政治的掣肘有关,也关乎知识分子主体的自身建设以及文化传统的反思。
(一)时代政治的限制
抗战时期的英雄书写受到现实环境极大的局限,纠结了复杂的民族救亡情绪。在沦陷区的异族统治下,英雄叙事只能隐晦地寄托于对“隐士”与“强盗”的虚构,叙事上总体陷入飘忽;而国统区、根据地文学则在英雄书写中寄托了民族国家自救复兴的种种想象,典型的如东北作家群对民间强力的寻找、战国策派对尚力英雄的崇拜以及根据地文学对新政权形态的展示。作家们塑造英雄具有较明确的现实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急切的功利性,必然会与文学的人文性和非功利性构成冲突,影响文学的深度和高度。
其一,时代政治要求以抗战为最高道德,排斥文学的自我特征和要求。在抗战高于一切的舆论氛围下,抗战救亡改变了文艺的功能,也窄化了文艺的范围。“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不同意这定义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大众眼中也判定了是汉奸的一种了。”*夏衍等:《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载《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一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这一过于强烈的现实要求,极大地牵制了文学艺术的自由生长,造成了抗战初期根深蒂固的抗战八股。“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的结果”,也使英雄形象的塑造往往只是一味强调“英勇”,“难看到过程底曲折和个性底矛盾”。*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载《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当时,文协同仁对梁实秋“抗战无关论”的批评,与其说是一次抗战题材问题的论争,不如说是一种集体表态式的强调。他们在激烈批判梁实秋的同时,也更严厉地批评着抗战文艺“差不多”的问题。率先发难的孔罗荪和积极论战的茅盾、郭沫若等都对当时的创作“固执”于“抗战”“死做”、“划地为狱”提出了批评,指出不仅要写大英雄,也要写小人物,歌颂将士的英勇时,也可“掀露出”“泥腿”来。*参见孔罗荪《强调现实主义》、茅盾《第二阶段》、郭沫若《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等文。这些充分显示抗战救亡的狭隘观念已将创作束缚在了无力自拔的泥淖之中。抗战文艺统一战线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和反思,成为当时文艺论争难以挣脱的怪圈。老舍创作上的不断调试、茅盾未竟稿的频频出现,都是抗战时代要求所形成的藩篱。这造成了作家把握、表现英雄形象多层意蕴时的犹疑含混。
其二,民族内部的党派争斗也影响到英雄形象的客观塑造。国共两党分别以书刊审查和政治规训等方式鼓励英雄书写的“歌颂”作用、控制其对现实的“暴露”。如邵荃麟的《英雄》因写负伤抗日战士回乡后受到种种轻蔑和利用而被加上“妨碍役政”的罪名;而根据地文坛批评《乌兰不浪的夜祭》不够“真确”是旨在引导传奇题材服务于时代宣传。*江华:《创作上的一种倾向》,载《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同时,英雄书写的不足也与意识形态的阻隔有关,如由于国民党“防共排共的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拨,妨碍了更多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倾力表现”*秦弓:《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5期。,国军英雄形象(特别是以高级将领为原型的)数量不多,而根据地为反对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封锁兴起了以各类模范为蓝本的新英雄传奇。至于像张自忠这样的英雄形象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因素。真实的张自忠曾被蔑为“华北最大的汉奸”,引起很多批评。老舍在创作《张自忠》时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虽然他也意识到“这时代的英雄无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人。假若我沿着这条路走,也许能使剧本更生动深刻一些”。但囿于政治困惑,许多“真的材料”为抗战现实所忌而“未能采用”*老舍:《写给导演者》,载《老舍剧作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123页。。
更严重的是,政治斗争还会直接干预英雄的塑造和传播,英雄形象的生产往往成了政治斗争的载体。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共两党文艺政策的冲突使《屈原》与《野玫瑰》(陈铨)的公演演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手戏。英雄形象的塑造、阐释及流传都受到非文学因素的极大冲击,至今迷雾重重。其中,不仅两剧上演始末的背后因素需要分别清理,两个英雄形象的成败特色也需要重新认识,且需避免政治拨乱反正带来的逆向褒贬。屈原形象中改头换面的忠良思想、“野玫瑰”中民族意识的直接灌注,都暴露了抗战戏剧重功利轻审美的弱点。
(二)知识分子立场的虚弱
在时代政治的强力影响下创作主体的独立自由受到空前的考验,知识分子立场的虚弱是造成英雄形象不足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成为超越一切的情绪状态。如何自处于历史的大变动中,作为大是大非的名节问题拷问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不尽单纯的创作动机下,英雄的塑造往往成了知识分子自我立场的一种表白。因此,抗战时期的不少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并非着意于精神的探讨,而是立足于知识分子道路的现实指引。如巴金的“抗战三部曲”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浴火重生的主题,曹禺的《蜕变》展示知识分子心态在抗战中“蜕”旧“变”新的过程,而老舍的《人同此心》则是通过大学生在“英雄与汉奸”之间的抉择,表达为国捐躯、“人同此心”的时代心声。由于知识分子立场的缺乏,这些作品只是发抒了一种未经沉淀的激情,没有生活实感的英雄形象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刘西渭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旋涡里。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刘西渭:《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36页。
作家们自觉为抗战服务,以民族情感代替理性批判,也限制了英雄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对英雄的缺点不忍批判,神化英雄的壮举,即使写英雄的缺点也是无关轻重的小缺陷;另一方面不能真实再现英雄所面对的现实环境,也就无法体现出英雄内在的精神意志。如吴奚如的《萧连长》结尾写勇敢的萧连长险遭昏聩的上司枪杀,但最后被放走改名换姓再当新兵。作者战后补记萧连长的原型实际是被正法了,小说的虚构是“为了不给日本帝国主义拿去作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宣传,所以在结尾处留给他了一条生路”*吴奚如:《萧连长》,载《吴奚如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显然,作家完全把英雄书写局限于鼓动作用了,实际上没有对民族痼疾的无情鞭挞便陷入了浅薄的功利主义。
知识分子立场的失守与外在强大的时代氛围有关,更与抗战后日益加深的知识分子认同危机有关。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不再是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精神导师,一者由于文弱的知识分子不能杀敌卫国,不是看得见的战斗力;二者颠沛流离的战争生活使知识者离开了熟悉的文化环境,加速了知识者与底层民众的结合。这些促进了知识分子对武力英雄、对工农英雄的崇拜,为文学主体从知识者向大众位移提供了心理基础。丁玲的《入伍》极有代表性地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红军小战士的对比,暴露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也严峻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入伍”的话题。
如小说中的新闻记一样,大部分知识分子未能找到参与民族战争的自我方式,陷入自我认同的虚无之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出版机构倒闭搬迁、文学消费群体缩减、纸张价格飞涨,作家们卖文为生的商业生态几近崩溃,连战前稿酬量极受艳羡的张恨水也称抗战时期是最艰苦的一段。在战时特有的脑体倒挂和通货膨胀情形下,文化人生活水平下降更为明显。大知识分子贫病交加、生活窘迫司空见惯,普通文人无力养家、苦闷自杀的也偶有发生。抗战生活在改变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在艰难生存中,大大小小各方政治力量通过政府拨款、文学评奖、个人交情等对作家的资助和庇护,都导致了抗战时期文学的社会介入性高于其他时期。这本身对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时文艺宣传、组织大众被认为是战时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在大众化的急迫要求下,知识分子的生活、语言、趣味在文学表现中受到极大限制。民族形式的倡导、新文艺腔的批判,都昭示着抗战生活要求文艺的随之变化。五四新文学的文艺体式有机地契合着国民性启蒙、个人主义的五四话语,而抗日救国与大众化、民族化的时代潮流也呼唤属于抗战的文艺形式。显然,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立场的失守与知识分子话语权、话语内容、话语方式的丢失直接关联着。
在模糊的知识分子立场下,除了作为工农英雄的陪衬之外,漂泊、流浪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行动方式。当然,这本身代表了追寻真理的一种姿态,但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模棱两可却也透露出知识分子主体立场的虚弱。这在《伍子胥》(冯至)中呈现为迷惘的逃亡,在《风萧萧》(徐讦)中呈现为轻逸的浪漫。“伍子胥”带着冯至抗战生活体验的深深印痕,反复切近英雄人物在回归自我与承担使命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冯至:《〈伍子胥〉后记》,载《冯至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但小说立场的飘忽带来了叙事的曲笔,局限了对英雄主题的深刻挖掘。唐湜指出,“诗人的彩笔”没有“把那逃亡者的颤动的灵魂细细分析、重重锤炼”,因而整个小说“没有重量,只有美的幻象”*唐湜:《冯至的〈伍子胥〉》,载《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9页。。同样地,《风萧萧》对战争的思考走得更远。小说通过三个女性形象试图打开关于战争、人道、宗教等人文话题的讨论,但是在绚丽的色彩、扑朔的情节、传奇的故事中,这些哲理思考浪漫有余、厚重不足,叙事上的模棱两可正好成为了战乱虚无人生的轻轻喟叹和暂时逃避。
(三)把握民族精神的艰难
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危机还与对民族精神的隔膜有关。战争的烽火促使作家们对民族文化、民间大众进行重新评价。英雄的书写也表现为向文化传统、民间世界深处寻找民族力量的努力,但其中的突破和误区同时存在。
英雄书写中对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不再是一味地否定、批判,而是通过古典英雄形象的借鉴、传统叙事方式的沿用,有效地推动了文学的大众化。但是,对文化传统的弊端习而不察和功利化利用,使抗战时期英雄形象受到局限。如吸收旧小说技巧时,其中所包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思想在英雄的塑造上是需特别警惕的。同时,大量继承改装民间侠客的革命英雄传奇中强调忠、忽略侠,以家国忠义代替江湖义气,是对民间侠文化小传统的政治化篡改。过于倚重古典传奇技巧,制造以少敌多、出奇制胜的抗战神化英雄,过于轻巧地简化了八年抗战的民族苦难。国家立场下的快意恩仇以正义战胜邪恶的名义渲染暴力,顺应并推助了血腥复仇的传统心理,对人缺少温暖细致的关怀。
文学对民族精神的把握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套用,作家对民间的融入也不是空间上的位移。就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多意味着对于民族品格优劣的正视,对民间鱼龙混杂的直面。抗战时期出现了很多表现民族强力的作品,是对民族尚柔传统的反思,表现出对民族复兴的企盼。其中东北作家在白山黑水的地域书写中表现出民族的阳刚之气。但也有作品刻意强调女性英雄的雄化、野性,使民族精神的表达趋于浮泛。
对民间的融入,需要深入表现民间英雄的善恶并存、尊重民间趣味的土俗兼具。不少作家塑造的英雄形象是穿着工农兵服装的知识分子,抽象的精神探寻造成英雄形象单面化、谐谑化的问题。一些作家对于农民英雄“不是照着自己的样子,把他们写成了婆婆妈妈的知识分子;就是凭着幻想,把他们描写得奇形怪状”,“歪戴的帽,斜睨的眼睛,三句不离‘他妈的’”。要写农民就要了解农民,“不但熟悉他们的外形,而且深知他们的灵魂,不但知道他们的生活,而且理解他们的思想”*林默涵:《关于描写工农》,载《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1—1173页。。也有不少作家借用民间英雄灌注集体主义革命理论,殊不知自由自在恰是江湖侠客的最大特征。民间英雄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武侠精神体现的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民间小传统,它对正统思想的偏离恰恰是其生命力之所在。革命化的英雄形象洗去了民间英雄的草莽气、江湖气,增加了政治信仰、阶级立场、革命理想。革命英雄传奇对民间伦理、民间趣味的净化增强了政治宣传鼓动效果,但远离了民间的原生状态,也就难以在大众中产生情感上的深层认同。
不能深入民间,加剧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艰难。路翎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是带有作家自况色彩的英雄形象。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在南京出逃、参加演剧等经历中日渐丰满,但是写到石桥场的生活,由于对农村世界的陌生,英雄人物与乡村保守势力的斗争没有得到清晰的展示。现实矛盾冲突转变成了英雄人物狂热的内心独白,英雄形象在神经质的压抑与人为的夸张中陷入混乱的迷失。在晦涩难懂、精芜杂陈的文字中,游荡于旷野的蒋纯祖成了一个漂浮于民间之外的个人主义者,因而他的失败也缺少了时代的概括性。
在民族战争语境下,知识分子话语主体地位严重弱化,对民间与传统的精神力量把握不够明晰,以至于大部分英雄形象成了民族救亡、时代政治的代言。“非主体的东西占据着话语主体的位置,就决定了这种话语主体的非人格主体性。”*文贵良:《话语与生存》,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36页。。这诸种因素的合力也暗示了战后英雄书写单面化、政治化的流变方向。
三
抗战时期英雄书写的困境在战后因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的强化进一步加深,从解放区时期到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的书写独霸文坛、进入全盛时期。在“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中,英雄形象的革命性、政治性不断加强,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借助英雄传奇的古典形式,英雄形象有力地弘扬了政治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文化。然而,随着传统英雄传奇中富含的民间文化基因逐步脱落,革命英雄形象从人性论走向阶级论、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慢慢剔除了生活化、私人化的特征,直至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
新时期以后的英雄书写明显地是对革命英雄叙事的反拨。从《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开始,关注有缺点的英雄、生活中的英雄。主体化、人文化的叙事态度,催生了各种新的英雄形象。立意上,对民族国家立场有极大突破;叙事上,战争的宏大史诗逐步让位于历史细节的打捞。另类土匪英雄形象的大量出现,是对革命英雄传奇神圣化历史叙事的彻底颠覆。以《红高粱》为代表,作家将个体生命价值与民间意志相融合表达出血腥战争中生命美学的极致,使英雄形象在抗战历史、民间生活背景中熠熠生辉。
随着战争历史的远逝,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非英雄的时代再一次遭遇英雄书写的困境。对理想主义的拒绝,对崇高神圣的躲避,都是对革命英雄主义巨大影响的努力挣脱。这在最初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然而,一味以卑琐代替崇高、以虚无取代理想,英雄叙事走向了非英雄化的极端。
这种非英雄化的趋势体现为对英雄神性和历史感的消解。首先,英雄人物序列下移,草莽盗寇大张旗鼓地进入英雄的行列。叙事的重点也转移为对这些另类英雄非英雄化行径的肯定和夸饰,他们大都“具有形象丑、语言粗、行为怪、不守纪等特点”*江胜清:《论新世纪“新革命英雄传奇”的新突破》,《小说评论》2011年第6期。,甚至有人以“马上有酒有女人”作为这一类欲望化英雄的简单概括。对英雄人物世俗面无节制的渲染,在突破以往革命英雄书写内在规定的同时,陷入另一种精神审丑的泥潭。
其次,遁入历史之外的戏说,使抗日英雄的书写远离战争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1937年的爱情》这篇小说单从题目看,私人生活与重要历史关头的相遇显然是题中之义。但如大部分战争题材的新解,小说除结尾外并没有将重点放在个人爱情与时代风云的交织上。战争成为叙事的远景和背景,是大部分未经历战争的作家的选择。这直接导致新的书写对战争的残酷性描写不够,轻慢的叙事也缺少了亲历者的厚重。对历史现场还原的逃避,是对政治意识形态长期干预的反抗,但也成为新英雄叙事的一个误区。生活无法跳出历史,文学无法屏蔽政治,“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极端化体验,恰恰是我们理解、进入战争本质最有效的切入点”*孟繁华:《抗战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还欠深度》,《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7日。。
这种非英雄化的趋势,是对革命英雄叙事的反弹,二者看似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二者都忽略了英雄最根本的精神意义。政治化英雄忽略了英雄基本的人性,卑琐化英雄则是模糊了英雄本身应有的品质,二者都未能在神性与人性的双重维度下展开英雄内在精神特质的探寻。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崇高精神的引领,在这个意义上,英雄情结永存。在传统价值体系崩塌、人文精神失落的当今,重塑真正的英雄主义更有必要。“任何国家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页。抗战时期文学的英雄书写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源,凝结着民族自救的渴望和民族自新的艰难,其中所昭示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底层的密切关系仍然沉重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文学。
(责任编辑:李亦婷)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s of Hero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Zhang Qianfen
In the critical times of the national war, the writing about hero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terature.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he images of heroes in the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but they are faceles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and humanity. This was related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olitics of the age, and revealed that intellectuals were in the dilemma about the self construc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spirit. Analy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very helpful to re-examine the traits, causes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Images of Heroes; the Spiritual Core; the Dilemma of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2015-09-30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抗战时期小说”(项目编号:13BZW111)、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异质空间与抗战时期小说的民族化思潮”(项目编号:2014M551538)的阶段性成果。
I206.6
A
0257-5833(2016)01-0183-09
张谦芬,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江苏 南京 21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