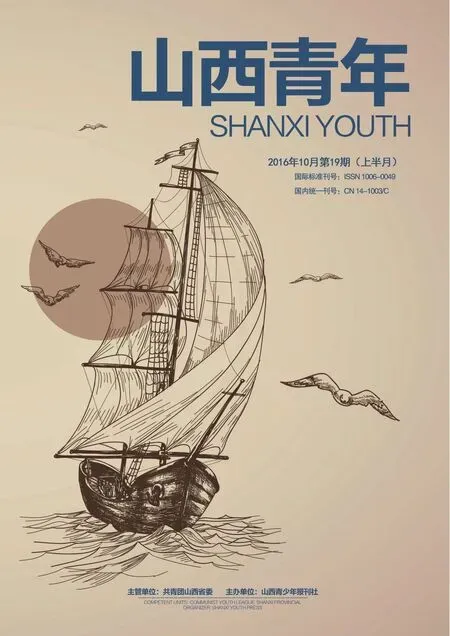基于知识形态变革的大学管理创新
2016-02-04谢瀑
谢 瀑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基于知识形态变革的大学管理创新
谢瀑*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大学是以知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组织,知识活动和知识创新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所在,知识活动形态和知识组织形态的变革,要求大学重新审视管理的“合法性”,紧紧抓住知识创造价值这一关键因素,加强管理创新,不断提高知识创新的有效性。
管理创新;知识形态;组织形态
大学是以知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组织,知识活动和知识创新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知识形态的变革,唯有知识的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协调统一,才能够有效促进知识活动与知识创新,唯有通过管理层面的组织结构创新,才能够为知识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协调统一提供有效保障。正是由于我国大学长期存在的金字塔形的科层管理,不能够适应知识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从而影响了知识创新活动的有效性,基于组织结构层面的大学管理创新才显得尤为迫切。
一、知识活动形态变革要求大学管理创新
大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禀性,决定了“教学—知识的传播或获得,科研—知识生产,社会服务—知识的应用与转化,文化传承—知识的继承与传播”的基本功能,而在这种基本功能的实现过程中,“知识—人—组织”的知识活动形态的变化,决定了大学功能实现的成色。
大学知识的获取是在一定知识形态内进行的,这些知识既包括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学相关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知识等信息,即包含了对外显知识的获取和对诸如教学经验、科研方式与思维等默会知识,传统意义上是围绕静态学科知识核心而呈现的知识活动形态。
知识活动形态是以知识为活动基础,以人为活动核心,以组织为活动载体的,“知识本身要经过保存、传播、创新、转化、生产等基本活动,这是知识的活动形态;知识的活动离不开人的活动,即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等基本活动,这是人的活动形态;当人的知识活动日益复杂化后,就要依附于学科、专业、产业等组织,即形成知识的组织活动形态”。[1]人作为知识活动的核心,首先应当紧紧把握知识形态发展变化趋势,才能不囿于知识保存、传播的狭隘活动,才能够贡献于知识创新、生产、转化等活动之中。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是一种静态的、局部的、受学科分类严格限制的知识,而这种静态的学科知识,从本质上讲是最适宜保存和传播的,所以在传统大学教育中,其知识流动的表现形态一直是以保存、传播为主的。然而,在当今社会,“正在从一个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一个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2],“知识是唯一有意义的资源”[3],知识作为一种无形要素,其经济价值越来越体现出生产性,而生产性知识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知识的静态性相比,其动态、活跃的特质,决定了知识的生产性愈明显,其活动方式愈易于发生变化;由于生产性知识重在应用,重在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利润,必然要求加快理解、传播、创新、转化、固化、更新的速度。知识形态的变化,需要大学的知识活动形态与之相适应。
以静态学科知识为基础,以保存、传播静态知识为主要知识活动形态,自然形成了与之对应的金字塔形的垂直集权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结构主要体现为科层建制、行政集权,以学科为基础的组织依附于科层行政集权,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集权掌握对于学科组织的资源分配,大学的知识活动便局限在对静态学科知识的保存和传播之中,长期形成了固守象牙塔式的“闲逸好奇”,在束缚教师、科研人员跨学科开展教学、研究、创新的积极性,也束缚了知识生产、创新活动与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发展的密切结合。因此,大学的管理体制必须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紧跟知识活动形态的发展趋势,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形成适于知识形态变化的服务化、网络化、扁平化管理结构。
二、知识组织形态变革要求大学管理创新
大学的知识活动形态不仅体现为保存、传播、创新、转化等关系之中,而且也体现为知识的存在方式上。知识的存在方式主要依附于人的基本活动方式,大学的知识存在方式所依附的是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教与学的活动方式,教与学的活动方式包含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联结的中介是知识,如果只是为了保存、传播静态的学科知识,教与学的活动自然依靠于以学科划分的专业及其教学组织,如果以知识的生产性为追求,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就难以适应跨学科生产知识的需要,不仅知识的保存、传播方式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而且知识的组织形态也必然随之而改变。
大学作为以知识为核心资源的知识组织,其传统的知识组织形态主要以学科、专业为依托,知识的组织边界以学科知识与方法、专业领域与方向的划分为依据,其边界十分清晰,人员、资金、物质条件等配置习惯,都是围绕学科、专业展开的,很难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组织,即便遇到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项目,也是通过行政手段调配资源、组成临时团队,知识的组织形态并没有脱离学科、专业的匡扶。
问题在于,这样的大学知识组织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一方面培养出的人才由于缺乏多学科融合的视野,难以成为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学科象牙塔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缺乏与产业的融合,直接影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快速实现最大利润。社会的各个产业并不是以学科、专业进行划分和建设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技术升级,往往需要跨学科跨专业解决,无论是调整产业结构或提升技术水平,都需要同时考虑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选择。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的生产性特征不仅决定诸如政府、企业、科研等组织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而且要求大学在追求知识的生产性价值的过程中,也应当随之模糊知识组织边界。
就大学而言,模糊组织边界,首先要打破学科、专业等组织壁垒,促进知识组织之间的有效融合和组织、活动、人员的相互渗透,建立保证知识信息共享、交流的平台和机制。21世纪是平台创造价值的世纪,[4]围绕知识的生产性特征及其需要,建立与产业企业合作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孵化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创业中心、技术转化交易中心等平台,跨学科跨专业组建团队,形成新的知识组织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由于组织边界模糊的知识组织及其平台的建立,要求大学管理体制必须创新。新的知识组织打破了原有的学科、专业壁垒,以学科、专业为依据所进行的大学资源配置和科层制垂直管理体制,无论选择增加管理层次缩小管理幅度,或者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都难以适应自下而上的新型知识组织结构的发展需要,要求大学管理随着知识组织形态变革不断创新,以有力促进生产性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顺利转化。
三、大学管理的合法性与创新
合法性存在于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系统之中,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5]意味着某种秩序被认可的价值[6]。大学管理的合法性,其实也就是指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系统中构成的管理的意义所被认可的价值,当这种被认可的价值在管理关系中建立起了被认同的普遍信念,大学管理便被认为具有合法性。
大学管理系统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大学的“行政权力”是根据管理者的目的去影响教职工行为的能力,其作用方式是强制推行管理规范和措施。学术权力则是因“学术”而产生的“权力”,其作用方式是通过拥有系统性高深知识和探索高深知识而影响他人,体现为一种学术影响力。大学行政权力的合法性,一方面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延伸,形成与教育行政机构相衔接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通过操纵与分配通过特定的强制手段,在进行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管理时,以内部制度规范为表征的管理职能所形成的正当性。大学学术权力的合法性之所以被确认为正当性而得到普遍认同,是通过探索与传播高深知识、扮演着知识权威的角色而形成的。
当然,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法性还在于其价值“有效性”,无论是存在于“命令—服从”关系中的行政权力的“正当性”,还是存在于“影响—服从”关系中的学术权力的“正当性”,只有被认同为价值“有效性”,才能够成为大学的普遍信念。在知识的存在形态、活动形态、组织形态,都简单依托学科、专业进行结构和管理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管理系统中,由于学术协调机构和行政决策咨询结构的叠加,虽然协调了知识资源及其其他资源的分配关系,但却制约了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知识探索、传播的资源整合,尤其不能适应创造生产性知识的需要,其管理“正当性”的价值“有效性”不能得到更好发挥。
按照系统论的原理,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由此延展的系统组织管理理论认为,一定的功能需要特定的管理结构来实现。我国大学目前的内部管理系统结构模式大多都采取的是矩阵式,纵向是由校长、职能处室构成的,横向是由学术协调机构、行政科层结构、院系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学术协调机构共同与下层的各个项目组和院系形成交叉。在这种管理结构中,虽然加强了各个项目组和院系的横向联系,但项目组织的临时性和院系划分的学科化及其资源分配的集权垂直化,仍然不能适应知识组织形态的变革。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在对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部门、高新技术组织、医院等在知识创新、转换和使用等各个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中发现,大学在各个方面的效益都处在较低程度,匮乏知识管理却使大学成为知识型组织的“软肋”。[7]不仅由于缺乏对知识的系统、有效管理,直接影响了大学真正成为知识型组织的成色,而且在大学管理系统中,由于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弹性”关系的断裂和新的知识组织独立性的“缺位”,直接影响着建立在管理“正当性”和秩序的“有效性”基础上的大学权力的合法性。
大学不同于企业组织、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性机构,高等教育是围绕特殊的理智材料—知识组织起来的,学术工作是围绕知识资源展开的,知识是大学创造价值的关键所在,学术工作不仅需要寻找方式方法扩大和传播知识,而且需要寻找方式方法生产、创造、转化直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性知识。大学的管理创新必须回到以知识资源这个关键点上来,在分权管理已成为普遍趋势的当今时代,不仅大学各层级之间的联系应当相对减少,各基层组织之间应相对独立,而且新形态的知识组织之间及其与各基层组织之间,更应当建立一种紧凑的横向关系,强化知识信息共享,强化知识组织与产业、企业等在创造生产性知识过程中的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在破除知识资源、科研项目资源等自上而下集权分配的束缚同时,加强知识资源、科研项目资源的横向联系,提高知识管理的有效性,促进大学管理全面创新。
[1]胡赤弟,黄志兵.知识形态视角下高校学科—专业—产业链的组织化治理[J].教育研究,2013(1).
[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152.
[3]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5.
[4]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01.
[5]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9.
[6]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7]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lnnovation:Knowledge managenent in learning society chpt2,OECD,2000.
谢瀑(1986-),女,河南洛阳人,管理学硕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规、家庭文化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G647.1
A
1006-0049-(2016)19-01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