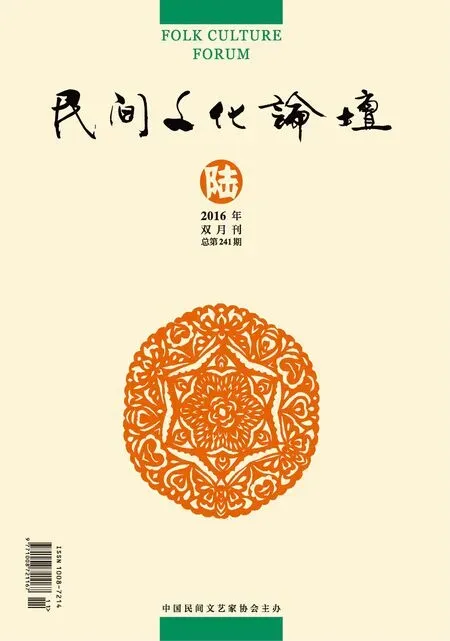民俗的影像记录:从概念到实践的日常化—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专题导言
2016-02-02张举文
张举文
民俗研究·影像民俗学田野方法与个案研究
民俗的影像记录:从概念到实践的日常化—中美民俗影像记录田野工作坊专题导言
张举文
主持人语
本专栏是基于中国民俗学会与美国民俗学会的交流项目,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与美国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承办的“中美民俗影像纪录田野工作坊” (下简称“工作坊”)的阶段性成果。
近十年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田野方法与影像技术。民俗现象的记录与认知,民俗变迁的观察与理解,民俗交流的跨文化解释,在影像田野的支撑下,激励着民俗学理论的生长与民俗学转型。全面呈现民俗现象的活态过程,在镜头叙事中,寻找民俗与社会、民俗与个体、民俗与信仰之间生动而深刻的内在关联。这些民俗影像,既是我们从生活现场捕捉的立体性民俗生活,也是多维呈现民俗世界的纪录片素材,还是融化民俗学理论与民俗文献的“民间召唤者”。正因为如此,尝试以影像田野为关键方法来记录当代民俗文化,以期研究民俗影像的工具性与学科本位价值,成为工作坊朝向影像民俗学的基本思路。专栏刊发的五篇文章,均为工作坊讲员与学员在三期民俗影像实践中的经验和理论思考,这些成果在影像民俗学的建构中具有一定的探索性。
首先,对影像民俗学田野实践的基本问题的探索。
民俗学田野中影像记录实践虽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从影像民俗学学科的角度考量,则算得上全新的学术命题。从2005年开始,美籍华人学者张举文教授即开始影像民俗学的思考,从概念辨析,到田野实践,先后发表多篇论著,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以下问题:
民与俗的融合研究;民与俗的一体记录;记录的目的与功用;记录的技术与模式,以及如何应对影像记录成为民俗生活与研究的常态。
《民俗的影像记录:从概念到实践的日常化》一文是他立足于工作坊影像田野实践回答上述问题的最新成果。论文认为,除了设备和拍摄技巧问题外,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将一个民俗事项讲述出来,体现出制作者或某学科角度的叙事特点,同时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这些展示给特定的观众。此外,影像田野的伦理问题始终是工作坊的一个核心。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海岚以影像田野的学员视角,就自己的切身实践,回答了从“事实”到“事件”再到“故事”的影像记录逻辑。这一从田野实践中升华得来的结论,不仅可以作为影像民俗学的理论观念,关键是在田野实践中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其次,对海外民俗学实践的影像表达之于中国学术的实在性价值的探索。
海外民俗学实践有两个前提,一是工作坊机制具有海外民俗学背景;二是民俗文化交流的语境已成为可以相互理解的学术共同体知识。这两个前提也是工作坊海外民俗学实践的合法性依据。在2015年12月美国俄勒冈州圣诞节的影像田野实践与2016年7月日本名古屋与大阪夏祭的影像田野实践中,工作坊学员们真正感受到了海外民俗学实践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学术魅力。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张多、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朱婧薇、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游红霞关于海外民俗学实践的相关论文和调查报告,从跨文化影像记录的民俗学视角,建构了中国学术对全球化宗教节日圣诞节的新的观察点,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种通过影像表达的海外民俗学实践的中国学术价值。
当然,工作坊仅仅开展三年,其影像民俗学学科意识、海外民俗学实践理想以及跨学科跨文化的项目团队机制,都决定了工作坊整体的探索性质与实践的诸多困难,从实践出发的理论思考固然有着新奇、鲜活的思想火花,但却因学科理论的缺失常常面临失去方向的危机。
——主持人 孙正国
一
这个工作坊的发端离不开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适当的学科知识准备;应时的实践需要;搭建该平台的动机与契机。2005年之前,民俗学界对影像记录的关注非常有限。之后,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会(如,2006年我与谢尔曼一同参加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民俗学会议,也正是从那时我萌生了翻译《记录我们自己》和举办工作坊的想法)和出版物(如,《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6期所载“民俗影视”与“影视民俗”的概念辨析和谢尔曼的“聚焦:电影与21世纪民俗研究的生存”论文;《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发表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2011年出版的《记录我们自己》①[美] 莎伦·谢尔曼著:《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张举文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译著),以及相关学科和媒体的贡献,加上民俗学者对各地非遗申报的介入,民俗学者对影视与民俗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开始改变传统的“田野”记录概念与方法。新一代的民俗学者和学生愈发感到需要系统地掌握有关影像记录民俗的理论和技术,以便有效地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至2013年,作为美国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会有关非遗的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工作坊”得到了经费,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一批民俗学家(如,黄永林博士、陈建宪博士、孙正国博士等有关学者)的大力支持。这三个条件的具备也是多方诚挚合作的结果,使得首期工作坊于2014年端午节成功举办,随后在2015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二期以“美国圣诞节”为主题的工作坊。
第一期工作坊于2014年5月28日至6月6日举办,由来自7个院校的10多名学员参加。在华中师范大学黄永林副校长和陈建宪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顺利实施。工作坊期间,除了从早到晚的讲座、观摩和讨论外,讲员和学员分组记录了世界非遗四地的端午节习俗(包括湖北宜昌和黄石、湖南汨罗、江苏苏州),作为影视记录实践作业。第二期工作坊于2015年12月14日至2016年1月2日举办。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一周理论学习,然后部分学员到美国俄勒冈州继续进行两周的理论讨论与影像记录实践。第二期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由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担任主任委员,陈建宪教授和笔者任副主任委员。整个组织工作由孙正国教授协调,并领队到美国访问调查。参加第二期工作坊的学员有来自20多个院校的50多名学员,其中18人参与了美国的圣诞节的实地记录。第三期工作坊于2016年7月14日至8月1日举办,国内20多所高校的30多名学员参加了工作坊。与前两期相比,第三期工作坊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实行了学术平台合作制度,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博士生论坛联合,共同推进理论研习水平;二是增加了国内影像记录部分,对广西百色平果县的凤梧师公戏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影像记录,共有26名学员参与国内部分的影像实践。7月22日至8月1日,工作坊的8名师生对日本名古屋、大阪、东京的夏祭习俗作了影像记录。
作为工作坊的设计者,我首先要感谢来自多方的讲员与学员以及组织者和志愿者们。三期工作坊的成功举办不仅使每个参与者都有收获感,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合作努力为学科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以跨学科的角度,将民俗的影像记录作为民俗学研究的新日常。
三期工作坊,讲员的专长和背景,当然也包括学员的学业背景,充分体现了这个新领域的构成与生机。讲员包括: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民俗学界研究和从事影像记录的陈建宪教授、田兆元教授、蒋明智教授和谢尔曼教授;代表中国视觉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邓启耀教授和熊迅教授;代表人类学、民族学有关民族志与影视研究的周星教授、秦红增教授、田阡教授、周建新教授、刘谦副教授和张霞博士,以及代表电视台纪录片制作人的王光艳导演、代表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的谭勇导演。当然,还有那些在实地指导记录的具有丰富当地知识的文化馆站的老师们和传统的传承人们,他们代表的是“实践”中的学科力量。学员的背景从只有兴趣到曾经独立完成过纪录片的制作、从非民俗学到民俗学专业、从人类学到传媒学。学员们的互学互助无疑是工作坊成功的最基本前提。
在这三期工作坊的实践中,讲员们突出强调的是,除了设备和拍摄技巧问题外,如何以叙事的方式将一个民俗事项讲述出来,也就是记录下来;如何体现制作者或某学科角度的叙事特点,以及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这些展示给特定的观众。此外,伦理问题始终是工作坊的一个核心:从项目的设计、执行,到后期编辑和展示。毕竟,在目前国内的学术界,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不论是在实地调查还是在教学研究中,都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些,在三期工作坊中都得到很好的实践体验。
二
关于民俗与影像记录,或者说民俗的影像记录,对民俗学来说还是个新课题。这里提出的“从概念到实践的新日常”还需要走很长的实践之路。笔者曾呼吁“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的研究”,并在《记录我们自己》的“代译序”中强调,“记录民俗是民俗学研究的前提”,“记录我们自己”的民俗是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将 “民”与“俗”融为一体的前提。①[美] 莎伦·谢尔曼著:《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张举文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因为那是有关影像记录的讨论,所以“记录”指的是“影像记录”)现在,可以进一步说,民俗的影像记录,不仅是民俗研究的必要部分,也是民俗传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记录者也是民俗实践者,而不只是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要将民俗的影像记录从概念走向实践,要将摄影技术日常化,要将记录民俗实践与记录我们自己日常化。
民俗的影像记录不仅是民俗学的学科基础,也是有关文化研究的各个学科的基础。在数字化时代,利用影视技术对文化活动或民俗事项的记录将成为民俗学者和其他文化研究学者的常态工作方法。因此,利用技术设备,了解影视与生活实践的学科视角,并将影像记录有机地与文字记录结合起来,这是当代民俗学者与人类学者必须应对的现实。
民俗的影像记录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研究民俗事件本身,更好地保护那些正在消失的传统以便将来复兴,以及认识传统的变异机制,而绝不是“固化”某些民俗事项或使其具有“权威”或“标准”。民俗事项是活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多样的,不是单一的。民俗是人与传统行为的共同体,不可以把“人”与“传统行为”分隔开来研究。因此,民俗影像记录突出的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
作为影像记录者,必须明确对民俗的记录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拍摄包含核心符号的有价值的资料片;第二是拍摄在此基础上可用于研究或教学的专题片;第三是拍摄为了多元文化理解通过公众媒体展示的纪录片。但是,这些目的的前提是:影像记录永远是对民俗传统的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记录,是对传统传承的进程的记录。试图将某民俗传统作为“结果”而将其“固化”的记录是违背影像记录的目的的。只有明确了这些目的关系,记录者才能处理好素材资料与公共展演作品之间的关系。
这些目的也决定着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好设备,如何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记录下最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何时使用特写,何时使用远景,如果通过景别的变化体现不同观点与内容价值等。换句话说,这需要我们处理好“主题”与“背景”、“文本”与“语境”以及(民俗事项的)“小语境”与(社会和文化的)“大语境”的关系。这也是纪录片风格模式问题。谢尔曼从纪录片5种模式中发现它们是历时性的,与民俗学的学科发展所关注的焦点是对应的,即,展述式(expository)、观察式(observational)、互动式(interactive)、反思式(reflexive)、表演式(performative)①[美] 莎伦·谢尔曼著:《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张举文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2页。。这对发展民俗学特有的视觉研究非常有意义。
因为民俗传统是由每一民俗事件构成的,所以,对每个民俗事件要弄懂其核心符号是什么,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记录到有价值的东西。将一个事件从头到尾的记录似乎是全面的,但如果没有将核心符号(可能是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词语等)有效记录下来,这样的“全面”只是给外行看个热闹,并不是在记录民俗的根本所在。为此,第一要有充分的背景知识;第二要聚焦于核心符号;第三要有恰当的景别。
记录民俗,经过了采风、下田野、实地考察、现场记录、实地体验与现场记录等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取向(民俗学和人类学现在都需要反思这些词语所反映的“态度”和“角度”问题)。现在,我们更关注的是实地体验与现场记录,即“参与-观察-记录”的“三合一”式的记录方式,但还要强调作为记录者的“我”在记录与展示记录材料中的角色与观点问题。
作为对工作坊的总结,也是对民俗影像记录的希望,我曾提出:要把我看与他观的关系处理好;要把倾听与记录和研究的关系处理好;要记录传统的核心符号;要把摄影技术作为日常;要把记录民俗实践与记录我们自己作为日常。以下是来自学员的反思,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工作坊的实践结果。希望这三届工作坊的实践能为后来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丁红美]
K890
A
1008-7214(2016)06-0063-04
张举文,美国威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