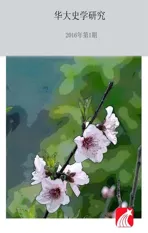帝国法律与两性关系
——评Matthew H.Sommer,Sex,Law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
2016-02-02许龙生
帝国法律与两性关系
——评Matthew H.Sommer,Sex,Lawand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
许龙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起来,但在西方中心论视角下的很多研究成果多是对中国的传统法律给予批判和诟病,而法律史则作为中国学范围内的“边缘学科”,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黄宗智为开创者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研究群体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使美国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苏成捷(Matthew H.Sommer)作为黄宗智的博士生,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已出版,以下简称本书)可以看做美国“新法律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共分七章,作者分别从强奸罪、同性相奸、贞节崇拜、妓女等方面来分析从唐代到清初国家法律对于两性及身体的法律规制的演变过程,重点关注政府、社会和个人之间多方互动。全书的主题,则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强奸罪的定义与处罚的演变
作者首先分析了“奸”、“私”、“乱”字在汉语中的广泛应用,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身体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观,君臣之间的从属关系也可以按照男女关系去进行比附。而回归到大众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色情文学的流行以及底层叛乱中所出现的对于正统性道德的悖离,可以看出民间出现的对于正统性秩序的反动与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更加证明了政治与性秩序之间的紧密联系。
想分析性犯罪,就必须先从性自身的道德和界限入手,即本书说的“礼”(ritual)与“义”(morality)入手。婚礼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使性关系合法化的仪式。“对于两性关系而言,要确保其合乎道德,它就必须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内;若在之外,它就会被认为是一种犯罪。”*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34.但即使是在婚姻关系内,也存在着对于婚内性关系的管制因素。传统文化对于“礼”的看重,使得其能凌驾于夫妇的本能欲望之上,即“礼”是高于“欲”的。
中华帝国的晚期是否存在“婚内强奸”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同西方婚礼多在教堂举行,以宗教赋予婚姻以神圣性所不同,中国人的婚姻关系的促成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郎新娘直接被赋予了抚育孩子的角色和孝敬父母的义务。婚礼不仅是两性结合的合法仪式,也是双方社会意义上的成人礼,男女双方在一天之间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换,哪怕在生理上来看他们都未成熟。在家族血缘传递的绝对主导下,婚姻更多的被看做男女双方对于男方家族的一种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高于感情的优先选择使得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性犯罪具有三个特征:1.发生在男女之间;2.它发生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之外;3.它被认为是第三者的介入,并会对另外一方的男性家族的血缘产生威胁,并最终认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p.35-36.但是并非所有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两种例外:一种是嫖客与妓女之间,另一种则是主人与女性仆人或奴隶之间。主人和婢女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家庭关系的一种延伸,我们在《刑案汇览》中对于奴仆犯罪比照五服内晚辈伤害长辈进行判决就可以看出。作者分析了从唐代到清代法令中对于男性主人与女性仆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的规定,可以看出这种法律上的管制是越来越严格,但是法律并非是一种惩罚的方式来表现统治者希望主人与婢女各安其分的意志,而是以作为被侵害者的一方享有了分享主人部分权利的方式来进行侧面的规制。“与她同寝之后,主人自动提升婢女成为他家族中的法律成员,不管主人是否承认。”*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50.而且即使是安分守己的主人,也有义务为婢女进行婚配。从婢女权利得到法律保障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华帝国晚期的法律是希望将“良民”的婚姻和家庭秩序(特别是贞节观念)推广到全社会阶层的*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54.。
判断一个强奸行为“成”(consummated)或是“未成”(unconsummated),这直接关系到对于强奸者的处罚以及受害人的贞节是否受损。而判断的依据,可以用“器官主义”来归纳,即官方最为关注的是双方的性器官是否有实质的接触。而在关于女性是“自愿”(consent)还是“被强迫”(coercion)的判断上,各个朝代的判断依据也有所差异。汉代法律的认定中存在着女性本位的倾向,即只要没有女性主动的意愿,即被认定为被强迫的。明清时期的法律则对于女性是否是被强迫做出了细致的规定,强奸行为只要不满足这些条件,则会被认为是女性自愿的。因此,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显示了一种视角的转变,或者也可以看作对强奸行为观察焦点的转移。
对于那些强奸施行者来说,他们作为一种对正常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的潜在破坏者,历代都会被社会所关注和监控,以致形成了一种对于“光棍”的恐惧情绪。在清代的法律中,光棍是那群“游离于(也许是反对)家族本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的人”*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96.,“他破坏了家庭的边界,对内部的女性和年轻男孩构成了威胁”*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97.。他们缺少家族体系的束缚,也缺少恒产(故无恒心),是一批在家庭和事业上的失败者,因而强奸者更多出现在他们这一批社会群体中,也使得“光棍”被污名化,甚至成为整个帝国的敌人。通过对清朝三个皇帝在位时期记录下来的49件案例进行分析,作者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强奸行为的模型,这其中涉及了强奸施行者,被害人的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甚至是行为发生地点、时间等等细节。作者对司法档案中建立一个典型的强奸罪行模型的尝试,也可以看做“新法律史”研究中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一种倾向。
如果丈夫允许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呢?这个问题直接动摇了婚姻关系的基础,甚至是挑战了人类延续已久的生存伦理,自然也受到了法律的规制。不管是女方与他人的通奸还是丈夫的“卖妻”行为,法律界定其破坏了夫妻之间的道德连接(义绝),审判方不仅会给予涉事的男方以肉体惩罚,还会宣判夫妻双方强行离婚。若是女方背叛了男方,则男方有权力将其妻子卖掉。因此在“买妻卖妻”的事件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商业化过程中自然人的商品化倾向。苏成捷于2015年9月出版的新书《清代的一夫多妻与卖妻行为》(PolyandryandWife—SellinginQingDynastyChina*Matthew H.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则可以看做作者对于本书相关研究的一个延伸。
二、同性相奸
中西古代文明的背景中,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一直作为一种禁忌性的存在隐没在历史个体的生活中。在清代,男性相奸则正式被纳入法律的话语体系之中。许多学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对清朝廷对于男性相奸的禁止做出了多面向的解释。虽然现代社会对同性恋已经报以越来越宽容的态度,但是抛开同性恋与现代性这个复杂问题不谈,传统社会中的同性之恋,特别是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自愿或是被迫),无疑是对其社会伦理和道德体系的一种挑战。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不仅给其他的社会个体带来了困惑,更使得帝国政府感觉其所代表的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正统性受到了威胁。朝廷因此通过法律来制裁,社会则通过巨大的道德压力和施加给当事人(特别是被侵犯的一方)巨大的耻辱感来禁止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因为正常的性行为中,处于“被插入”这一角色都是由女性所担任的,如果男性担当了此角色,则对其自身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巨大的疑问和损耗。这种“男性气质”的巨大流动则是苏成捷在本书中所反复强调的。
雍正帝之前的法律实践对于同性相奸的罪行大多是比附异性相奸之罪行来进行的。就如同雍正帝之后“贞”与“良”逐渐画上等号一样,法律对于同性相奸犯罪行为中的受害者一方,也比照女性为其构建了一个“贞洁”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方便司法实践)。判断一个男性是否“贞洁”(良家子弟),在于他是否有过被性侵的经历,这与判断一个未婚女性的“贞洁”的标准相类似。在清代对于同性相奸罪行的判例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被害者年龄的关注。案例中罪犯对于被害人的叙述多呈现出一种女性化的倾向,低龄、瘦弱等带来的一种双方男性气质的不平衡,使得被侵害一方相对显示出一种“女性气质”。性特征的不突出以及未婚导致的社会性别角色的不完整使得“男孩”身上出现了一种性别的模糊化倾向,而这也是他们脆弱性的来源。但是由于受害者一方在器质上还需要承担家庭的血缘传承的作用,这种侵害则被放大为一种对被害人家族的侮辱与侵害,自然会被社会所禁止和严厉惩罚。
如果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许多没有家庭的男性,特别是一些边缘群体,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既是宣泄自然欲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与其他社会成员连接的方法。身体构成了一种交换的媒介,虽然这是为主流文化所不齿的。
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的逐渐扩大,对于社会的边缘文化与群体的研究也屡见不鲜。而对于同性相奸此类边缘文化的极端事件的系统研究,在本书之前还不多见。
三、寡妇的脆弱身份
中国有句俗语,“寡妇门前是非多”,从社会层面来看,男性配偶的死亡给女性造成了其身份的不稳定性,虽然其丈夫不在人世,民众的想象中仍潜在地为她填补性伴侣的缺失,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缺少男性的庇护也使得寡妇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寡妇自身仍具有“负能量”,性关系和财产关系上,她都成了一个关键的结点。
贞节崇拜严格要求女性在婚前守身如玉,婚后恪守妇道,丈夫死后从一而终,这之间的主线就是要求女性对丈夫的忠诚,特别是在性关系上要求其丈夫是她唯一的性伴侣。但是寡妇会发现她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位置:如果丈夫留下足够多的财产,她可能会面临丈夫的亲戚们对财产的觊觎,他们会逼迫寡妇改嫁以获得财产;如果丈夫留下的财产不够,甚至是债务,她可能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去支撑这个家庭,只能选择改嫁。所以说无论是哪种状况,寡妇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临界点上,还好法律上更多的是给予她支持。
“清代法律用两种方式来评价贞节,表现在帝国法律中就是‘礼’和‘法’:用法条去旌表贞女和殉妇,以及根据受害者的行为去判断对于贞节的犯罪。”*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169.
丈夫故去之后,寡妇会被赋予新的任务:抚育子女以延续先夫的血脉,保存经营丈夫遗留下来的财产。因此可以判断出寡妇的权利较之以前是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在某些时候她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地位。但是她获得这些权利的前提,就是她可以守志,选择孤单一人走完其剩下的人生路程,而这才是朝廷所积极推行的。但是一旦她被发现与其他男性有通奸行为,她不仅会丧失对于先夫财产的保管权,连她自己也可能会被先夫的家属卖掉。通向节妇之路不易,这之中所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困难就在于男方亲属会想方设法让寡妇改嫁。寡妇与亲属的博弈过程是很激烈的,寡妇往往需要作出很极端的行为(甚至是自杀)来坚守其意志,家属也会以捉奸的方式来表示寡妇失节,将其改嫁他人。作者用了很多生动的案例来表现双方的这种争夺,但是官方的态度一般多是偏袒寡妇一方的,除非她与奸夫被捉奸在床。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寡妇无力或者不愿守志,选择改嫁他人,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多面向的结果。虽然礼法要求妻子也必须为丈夫守孝三年,但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有些寡妇会在三年内改嫁,官方处理这类案件时,其处理就十分的暧昧,寡妇会声称为了延续先夫的血脉其不得不改嫁,在人情面前,法律的执行上会陷入十分模糊的状态。
没有财产的寡妇往往选择改嫁,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因此第二任丈夫的财产状况是她安全感的来源。若第二任丈夫十分贫困,寡妇有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成婚。而对于拥有财产的寡妇,她有时需要一个帮手(或来自家内,或来自家外)以帮助经营其财产(这往往成为不稳定性的一个来源),或是招赘一个男性与其一同生活(这往往招致前夫家属的不满)。但对一个守志的寡妇而言,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怀孕,这有可能导致其前半生所经营的一切声誉和财产的毁灭,所以她的反应无疑也是剧烈甚至是绝望的,或是想方设法打掉胎儿,或是万念俱灰选择与告发者同归于尽,但也出现了依靠计谋成功脱离危机的情况。
贞洁既是一种官方的钳制工具以对女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这是历来为人所诟病的一方面,但它有时也成为“弱者的武器”,是女性去维护其权益有时甚至是逃脱罪责的一种工具,制度语言的转化是我们在对寡妇行为的观察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这也是苏成捷所想要重点表达的。
四、雍正朝1723年身份改革
1723年之前,妓女是一种道德标准下的产物,她们被打上“贱民”的标签。帝国通过其文化权力的网络,给她们的性行为,特别是其性质加以规定。帝国将她们排除在良民、社会主流的文化之外,她们有其自身的道德伦理体系。
妓女的身份界定其实是很模糊的,她们和其他人群,如水户、乐户等一起被编入乐籍,官方机构对他们进行控制,他们的子孙后代则也要继承这种身份上的污点。“不是良民”,官方的这种表述使得他们在法律和社会中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歧视性待遇。他们不仅在穿着上受到限制,而且不能与良民通婚,不能和政府官员发生性关系。帝国竭力想把他们与社会主流所分隔开来,以使他们的身份特征更为特殊和突出,从而自动地为社会大众所排斥。这在明朝和清代前期的司法实践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它一方面将妓女的身份污名化,将其职业同道德低下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从良者的一种尴尬的界定。一个从良的妓女失去一切,除了自由。
“我们从元到前清的立法中可以看出:这段长时间内的法律与其说是禁止(通奸)行为本身,还不如说是通过对性行为的规范以使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符合其道德准则。”*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247.但是随着王朝的崩溃以及商品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加剧,政府对人口和户籍控制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当统治者发现固有的道德体系和社会身份秩序已经与现实社会脱节时,一场社会变革在所难免。
1723年,爱新觉罗·胤禛继位,他主导了一次社会改良,将所有的乐户销籍,改乐为良,以使其自新。从出发点来看,与其说是这是一次带有现代性的“部落民解放运动”,不如说是中央政府转向保守的信号。这次的社会改良基于音乐与风化的关联,意图通过社会改良来使之前失序的社会群体各归其位。雍正不仅裁撤了对乐户的管理机构,还允许曾经的乐户的三代子孙可以参加科举,真正是想为其创造一条“自新”之路,而对于妓女重操旧业以及良家妇女卖奸等行为,则是重加责罚,而且责罚的对象则是扩大到嫖客和皮条客。
到了雍正帝之子乾隆朝时期,朝廷则颁布了附加的法律来惩治地方衙门对于妓女卖春行为的失察责任。乾隆帝的目的则是进一步地完善其父的初衷,将这场社会改革的效果能深入到地方层面。但是就如同寺田隆信、瞿同祖和经君健对于这场社会改良不算高的评价一样,中央政府的意图在于解放妓女,却是通过强行压缩其生存空间的方式,妓女本身从法律的灰色地带而变成了违法,朝廷意图压缩其生存空间以将其逼迫进入主流社会中去,“妓女”的污名化实则使其更加难以适应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地方衙门的爪牙(yamen runners)与妓女与皮条客的“合作”,更加剧了清朝地方政府的腐化。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反作用,是生活在紫禁城中的君王所始料未及的。
纵观全书,作者是以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去看待晚期中华帝国时期“性”的转变,但其并不仅仅限于性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分析整个朝廷和社会是怎样去看待这种转变以及其背后的原因。
本书出版于2000年,作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具有美国“新法律史”研究的典型特征,即“注重司法档案在研究中的运用,以及从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第78页。。
在资料的搜集使用上,作者将县级档案与中央档案结合起来,包括巴县档案、顺天府档案、淡新档案以及内阁刑科题本、刑案汇览、官箴书等等。中央政府更关注的是法律的严格使用,地方县衙关注的更多是事件的完满解决,映射到中央档案与县级档案文本上的差异反映出的也是司法话语与司法实践上的差异,这延续了黄宗智在法律社会史研究上的思路。因此在序言的最后,作者说出了他写本书的初衷。“我写本书的动力之一就是转化大量的来自法庭上的证词和判词,让这些材料尽可能地为自己说话。在具体的问题研究以外,我希望与读者分享这些文本所传达出来的不可计量的丰富质感。”*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29.之前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法律条文和机构、制度等方面,虽然在法理和制度层面的描述是明确的,但也切断了法律与历史现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法律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历史学和法学学科边缘的尴尬地位。随着中央和地方所存的司法档案的逐渐开放和为学者所重视和研究,司法档案成为能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进行多面向阐释的珍贵材料,能够展现当时法律和社会面貌的各个侧面,也能获取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从而推动“法律史”向“法律社会史”的转型。
书名也界定了作者的研究视野,晚期中华帝国,这种长时段的观察可以集中注意力于一点,展现客体线性的发展历程。苏成捷在结论处的最后一句也写出了他的研究目的:“这种线性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中国家族’和‘中国价值观’的定型思维,揭露出人们使用的生存策略的多样性,而且可以看清生活的物质条件是怎样帮助人们去挑战具有统治地位的道德与政治秩序的。”*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320.对于某一个具体问题做连续的观察和分析,脱离了按照朝代或是帝王等后发的人为划分的标准的限制,则更容易在变化的历史发展之中去探寻其自身的发展脉络,这也是作者对于西方中国学研究方法的一种继承。
作者对于司法档案中所记载的大量案件进行了整理,特别是对当事人的性别、身份、阶层、年龄等数据进行了统计,建立了一个较为简单但是清晰的模型,以直观而清晰地表现同类案件的主要特点,这种数据统计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步德茂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一书中看到更多的应用。
但是本书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使用司法档案,特别是案件的讼词及判语,其在成文之时就很有可能经历了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初次塑造。清代紧张的满汉关系以及商业的高度繁荣所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阶层的断裂之处也正是意识形态的高度渗透之处,涉案的双方则很有可能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使用官方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是有可能造成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失真。而且传统社会中官府的权力并非是直接控制个人的,民众所普遍拥有的“畏官”情绪也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民间纠纷更多地依靠的是宗族、熟人调停等社会网络来处理的,寻求诉讼至官衙的案件往往是事件处于极端情况之下的选择,若将“非常事件”作为“日常事件”来处理,则容易产生对于当时社会正常状态的误解。因此本书中所大量采用的司法档案等材料,是否能够导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结论还是值得讨论的。此外,本书中还有部分内容也值得考证,比如第33页中对于“宫刑”一词的解释,书中认为“对男性,它意味着阉割,对女性,它意味着被永久性地监狱于一个房间”*Matthew H.Sommer,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of Stanford,2000,p.33.。对于女性所施加的宫刑,即“幽闭”,其早期虽然有监禁的含义,但在封建王朝后期更多的是对女性肉体所施加的刑罚。
性与法,欲与礼,归结起来,还是人性本能与社会文明的冲突与调和。本书从性与法律的角度,为我们开辟了另一条去观察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的门径,从另外一个面向展示传统中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许龙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